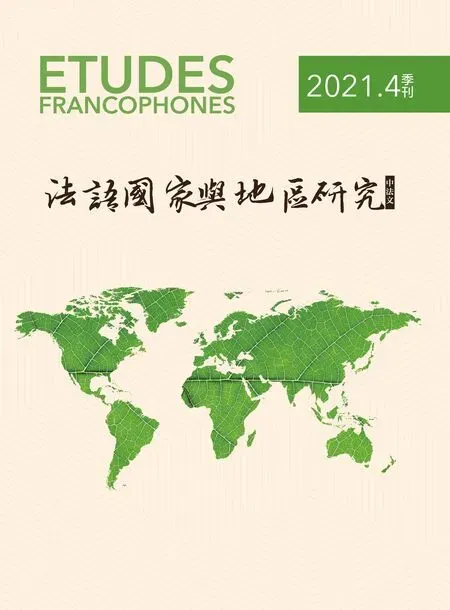让·科克托的戏剧之诗与独白之声
李 诺
内容提要 20世纪法国作家让·科克托在戏剧上追求以“戏剧的诗意”取代“戏剧中的诗意”,用“凸显”和“剥离”的手法彰显诗意,以期完成追求真实与自由的使命。剧作《人声》是科克托创作的一部具有实验意义的独角戏,戏剧的主角由人物简化为单一的声音,借助电话这一道具,作品在虚与实的摇摆中完成了一场单调的合奏、一段复声的独白。这种兼具力量感与脆弱感的声音,既描绘了诗人朝向死亡与自由的奔赴之旅,也展现了个人面对苍茫历史的孤独自白。
引言
让·科克托(Jean Cocteau,1889—1963)是20世纪法国文化界一颗璀璨的明星。从诗歌到小说,从戏剧到电影,从绘画到音乐,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几乎涉足了所有现代艺术领域,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诗的定义。科克托认为,不仅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歌舞剧等艺术类型都是诗的载体。在科克托的作品中,轻盈无谓的姿态和艰深沉重的内涵常常形成耐人寻味的反差,这种反差带来的张力首先溶于科克托所谓的“诗”中,而后诗意的流体肆意铺洒在舞台之上,蔓延至文字之中,流淌到光影之间,诗意因此得以栖居在多样化的文学与艺术载体中,最终成就科克托追求的“小说之诗”“戏剧之诗”“电影之诗”。借由剧作《人声》(La Voix humaine,1930),我们将一窥科克托的诗意如何在纯粹的声音维度下蓬勃生长。
一、戏剧之诗:从视觉到听觉
科克托所谓的“诗”,是一种神秘甚至无法言喻的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是一种操纵着诗人的未知力量。他曾直言:“人们要求别人为他们解释什么是诗。他们不明白,诗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很少招待来客,甚至可能从不招待来客。”①Jean Cocteau.«Le Mystère Laïc».Œuvres Complètes X,Paris:Marguerat,1959:20.诗仿佛一条带电的河流,而诗人作为沟通诗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天然媒介,浸润于其中,承受着诗这一奇幻的流体所带来的快感与痛感,同时创作出种种文学艺术作品,作为诗的承载之物。②详见Jean Cocteau.Le Secret professionnel.Paris:Librairie Stock,1922:59—61.因此,诗人的一次次艺术创作,正是他借助丰富而活跃的想象力将神秘而神圣的诗意以真切可感的形式进行传达的一段段非凡旅途。在文字、图画、声音等可感的表象之下,诗意的狡黠光芒得以明灭闪烁。
融合了语言、动作、音乐、舞蹈等多种表达形式的戏剧,因其具有刺激观众多重感官的天赋,成了科克托笔下最宜于承载诗意的艺术类型之一。诗意在戏剧中该当如何妥帖呈现,成为科克托在数十年的戏剧创作中不断探索的问题。1923年,科克托在出版剧作《埃菲尔铁塔上的新郎新娘》(Les Mariés de la Tour Eiffel)时,在剧本之前加入了一篇宣言式的序言,他在其中首次提出,以“戏剧的诗意”(la poésie de théâtre)取代传统的“戏剧中的诗意”(la poésie au théâtre),这部作品也因此被视为科克托追求“戏剧之诗”的起点。关于这两个看似十分相近的概念,科克托解释道:“戏剧中的诗意如同精巧的花边,人们无法从远处看见。而戏剧的诗意犹如粗大的花边,缆绳织成的花边,甚至就是海上的一艘轮船。《埃菲尔铁塔上的新郎新娘》将呈现一点一滴的诗意在显微镜之下骇人的模样。一场场戏编织得丝丝入扣,正如一首诗中的一个个词。”③Jean Cocteau.«Préface des Mariés de la Tour Eiffel (1922)».Théâtre complet,Paris:Gallimard,2003:36.“戏剧中的诗意”指的是传统戏剧中主要借助语言实现的抒情效果,而“戏剧的诗意”则是将舞台上朴素的对象进行多维的夸张和感性的变形之后呈现的景象。精致的花边如何能演变成缆绳、轮船?这种离奇的放大和畸变,隐喻着科克托对传统审美的挑战:诗意不在于唯美和浪漫,而在于神秘和震撼,因此诗人必须为观众带来新和奇的体验,让观众发觉平凡可感的事物所蕴含的惊人诗意,用即时的情感反应、未经思索的直觉感受去体会诗意,而不是用理智和逻辑去理解诗意。
秉持这一创作理念,科克托在《埃菲尔铁塔上的新郎新娘》中,企图运用“放大”的手法凸显诗意,并且自认为成功彰显了非理性的诗意状态。在这部剧中,人物全部从舞台中央的一台照相机中跳出,只有行动而无台词,两台留声机在舞台两侧进行对话和评论,整部戏气氛热烈、高潮迭起,无论是人物塑造、语言设计还是情节发展,都对传统戏剧要求的逻辑和理性发起了挑战:本应再现、复刻现实的照相机,竟然直接产出和创造了现实,送来了鸵鸟、狮子、新人的孩子等独特的宾客,个个性情诡异、大肆作乱;留声机的对话常常逻辑不通、荒诞不经,甚至前言不搭后语;众人无缘无故地陷入孩子挑起的战争,又奇迹般地走向和平美满的结局。代表逻辑的语言要素在这部作品中落入次要地位,戏剧人物皆来自照相机所象征的图像世界,以形象化的表演呈现了一幅奇异的景象。总而言之,在科克托挖掘“戏剧的诗意”的初次尝试中,他试图将具象的舞台和抽象的诗意融为一体,用夸张的戏剧手法放大“日常生活的诗意”(la poésie de tous les jours),用离奇的愤怒与惊诧抓住观众的眼球,拨开生活中虚假和平的迷雾,让观众正视生活赤裸裸的荒诞底色。
以舞台为放大镜,原本缥缈的“诗”在《埃菲尔铁塔上的新郎新娘》等多部歌舞剧和芭蕾剧中呈现出了“骇人的模样”。而令人惊诧绝不是诗人的最终目的,诗人力图揭露的骇人的模样,实际上映射出了诗人对某种超越现实的“真实”的渴求。科克托在创作了《埃菲尔铁塔上的新郎新娘》几年之后,在1930年出版的一部日记中对“戏剧的诗意”这一概念再次进行了阐述。诗人写道:“不是在舞台上活着,而是让舞台活起来。这种戏剧的真实,就是戏剧的诗意,即比真实更真之物。”④Jean Cocteau.Opium.Paris:Stock,1987:69.所谓“让舞台活起来”,便是不局限于在舞台的框架中上演模拟现实的情节,而是要创造一整套充满活力的新框架、新秩序、新现实。在科克托的戏剧舞台上,诗的意义在于引向高于现实的另一重现实,在于突破由习俗、规矩、理性编织的现实秩序,展现在另一种境界中自由而不受约束的新秩序。后一种秩序因为与人的原初冲动和直觉更为相适,被科克托视为比肉眼看到的生活更为本真的存在。
而追求真实的过程,势必也是寻觅自由的过程。挣脱束缚的努力,在文学世界中的直接体现便是表达上的创新。因此我们在科克托的戏剧舞台上看到,音乐、舞蹈、图像都可能参与到戏剧活动之中;禁忌、丑闻、生死等主题都能以直白的方式上演;演员表演出的含混、疯狂、滑稽可以轻易地取代清晰、理智、连贯。当然,沟通了现实与非现实秩序的诗人、自觉浸润在痛与快并存的诗意流体中的诗人,他的自由是否还具有更为深远的含义,需要我们在分析文本的过程中进一步探索。
真实和自由作为科克托的戏剧之诗中至关重要的元素,无疑是帮助我们打开科克托的诗意世界大门的关键钥匙。如果说《埃菲尔铁塔上的新郎新娘》是一部高唱求真实、求自由的反传统戏剧宣言,创作于1930年的戏剧作品《人声》则更像一部内敛而深沉的小品。高昂嘹亮甚至有些刺耳的呼号声,在《人声》中将化作一曲扣人心弦的婉转小调,追求真实与自由的愿望隐喻其中,更加耐人寻味。
独幕剧《人声》是一台独角戏,无名的女主角在卧室里最后一次打电话给离她而去、明天即将结婚的前男友,电话信号时断时续,不时受到外线干扰。观众仿佛化身女主角家中的偷窥者,她一人的话语是一切信息的来源。最后,电话挂断的一刻就是剧终之时。如果说《埃菲尔铁塔上的新郎新娘》中的一切人物源自一台照相机,《人声》讲述的故事则完全来自一根电话线;《埃菲尔铁塔上的新郎新娘》是一部形象化的戏剧,视觉维度的创新在作者的诗意表达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人声》中,视觉让位于听觉,声音成为科克托在戏剧世界中探索诗意空间的新工具。从视觉到听觉,科克托演绎戏剧之诗的手段从令人称奇的“凸显”转向了多重意义上的“剥离”。
实际上,科克托的确希望《人声》这部剧成为他的戏剧创作中的转折点。这位敢于创新且乐于实验的剧作家,在《人声》的序言中解释了自己进行此番创作的三重动机:首先,剧本的创作灵感源自科克托曾经偶然听到的一场电话谈话,说话人独特的嗓音和长久的沉默令他难以忘怀;其次,有人批评科克托在戏剧呈现中过于依赖舞台布景、机关设置,因此他希望在这部剧中实现极致的精简,仅用一幕戏、一个人物、一段爱情以及现代剧中最平凡的一个道具——电话,来讲述这个故事;最后,他更希望这部剧被视为一个戏剧层面的实验,而不是一个世俗情感故事。⑤详见Jean Cocteau.«Préface de La voix humaine (1930)».Théâtre complet,Paris:Gallimard,2003:447.由此可见,《人声》在科克托追求“戏剧之诗”的漫长旅途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剥离”成为戏剧创作的关键理念,“人声”成为舞台上唯一的表演者。两位对话者的身份、姓名自始至终未被透露,感情纠葛的全貌被话语剪切得零散细碎,甚至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也被彻底剥除,只剩赤裸裸的独白在此间回响。这部戏剧的精简风格,也反映出诗人与1920年代初的先锋派审美取向渐行渐远的趋势:诗未必只能寄寓于眼花缭乱和新奇颠覆之中,“显微镜”之下呈现的那种骇人的景象,也并非真实的唯一面貌。遵从了“三一律”的《人声》体现出了回溯古典主义的趋势,科克托期待着,将诗承载在一种更为深沉和持久的力量之中。
既然如此,在经历多重意义上的“剥离”之后,科克托的这出戏剧呈现了怎样的内核?或许,在剔除了令人分心的“杂质”之后,舞台上纯净的人声就代表着科克托想象中的诗的声音?倘若人声与诗在这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那么诗人追求真实和自由的使命,是如何在这段声音中得到传达的?我们将以真实和自由两要素为寻觅诗意的线索,探究《人声》中的声音如何浸染了科克托所谓的诗的特质。
二、求真之声:复声的独白
诗人剥除了纷繁奇异的视觉效果,寄希望于朴素的声音来演绎戏剧之诗意,但他并不是在进行一场肆意的试验,仿佛将种种感官因素渐次搬上舞台,逐一考验其表现诗意的可能性。诗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声音本身,尤其是歌声,与原初的诗本就是相通相融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最初的诗便也是歌,诗与歌从不离分。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俄耳甫斯(Orphée),是科克托心目中最为理想的诗人形象,对俄耳甫斯神话的改写也是科克托在一生的创作中最为重要的脉络之一。而极具魅力的歌声,正是俄耳甫斯身上最为迷人的特质,他凭借歌声的魔力勇闯地府,试图救妻的故事,是古希腊神话中极为动人的一段传奇。自比俄耳甫斯的科克托,希望探索蕴藏在歌声中的诗意,是自然而必然的选择,因此歌剧《人声》能够传递的,或许正是俄耳甫斯式的、超越时空的诗人之声。
在科克托看来,诗最终应当通达“真实”,而《人声》中这场孤独的吟咏,以独白这一绝妙的形式呈现了一个“人”在真与假之间可能经历的摇摆与试探。当通话的一方被“剥离”,对话也就成了独白。但借助电话这一道具,《人声》舞台上的独白又具备了独特的对话色彩,科克托在序言中将其形容为“独白-对话”(monologue-dialogue)或“双声独白”(monologue à deux voix)。女演员用话语扮演自己,用沉默扮演他人,打造了一场话语和沉默之间的对话、在场和不在场之间的对话、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对话。独白如何能在特定的戏剧空间内具备对话属性?一种声音如何传达两种话语?真与假的裂痕在一人的声音中从何而起?我们首先将从独白的定义入手展开分析。
在传统戏剧理论中,独白往往被简要定义为“一人一声”的舞台场景。例如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Jean le Roud d’Alembert)主编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中,“独白”(monologue)词条被诠释为“一个人物独自出场且独自说话的舞台场景(……)该词由希腊语词汇μoνoς 和λoγoς 组成,即‘独自’和‘话语’”⑥Encyclopédie,Volume X.Exemplaire Mazarine 1,1765:668.原文: «MONOLOGUE,s.m.(Belles-Lettres.) scène dramatique où un personnage paraît &parle seul.[…] Ce mot est formé du mot grec μoνoς,seul,&de λoγoς,discours.».,这种比较朴素的定义至今为众多读者和观众所接受。到了当代,学者对独白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和细化,尤其富有创见的是,许多研究者提出了独白的受话者的问题,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研究独白的交流属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例如,21世纪的《通用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是这样解释“独白”的概念的:“这一术语主要应用于戏剧中,指的是一位演员独自言说的场景,这种话语或是公然向观众说的话,或是演员对自己说的话。”⑦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数据库,Monologue 词条。原文:«Le terme est avant tout utilisé pour le théâtre,où il désigne les scènes où un acteur parle seul – parole soit ostensiblement adressée au public,soit supposée révéler un discours que le personnage se tient à lui-même.»受话者在这里被定义为观众或演员自己,可见独白已经具备了对外或对内的指向意义。在安娜·于贝斯菲尔德(Anne Ubersfeld)的戏剧理论中,受话者的概念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她在《阅读戏剧I》(Lire le théâtre I)中提出了双重陈述理论(double énonciation),认为一切戏剧文本内都有两个文本层,戏剧的话语既是外指向的叙述话语(discours rapporteur),即作者对观众说的话,也是内指向的述及话语(discours rapporté),即发声的人物对其他人物说的话,一切话语都是内指向和外指向的声音交错形成的关系。⑧Anne Ubersfeld.Lire le théâtre I.Paris:Édition Belin,1996:190.在《阅读戏剧III:戏剧对话》(Lire le théâtre III.Le dialogue de théâtre)中,她进一步将独白在述及话语层次的内指向受话者分为三类,即不在场者、自我和超验的存在。可以想见,除自我以外,即使独白存在内指向的受话者(人物),这位消极的受话者也不具备听和反应的能力;独白固然存在外指向的受话者(观众),但观众也只能被置于被动的地位。如此看来,种种现代戏剧理论尽管肯定了独白之受话者的存在,却同时否定了受话者的能动性;尽管发现了独白潜在的交流属性,却同时否定了双向沟通在独白情境下的可能性。由于受话者被置于场外空间,发出独白的人物得以成为单向的输出者,如此一来,双方拥有了不平等的话语权,独白话语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同时其真实性不会受到任何考验。
而科克托希望呈现的,是一场求真的独白。他虽然剥夺了受话者在场的权力,却为其保留了听的自由。换言之,《人声》创造的是一种不完全的“剥离”环境。对于内指向的受话者而言,女主角的情人在视觉上受到限制,只能接受听觉的信息,视觉和听觉信息不对等的偏差,让女主角在诚实与欺骗之间摇摆;对于外指向的受话者而言,观众尽管同时获得了视觉和听觉上的便利,却仅能获取女主角一方的信息,因此聆听女主角独白的过程,同时也是观众探求完整真相的过程。
《人声》中的独白,首先是一种欺骗的声音。从女主角开始与男友对话的一刻起,观众已然看出她在撒谎。女人明明身着家居便服,精神颓靡、心急如焚地在家中等待电话已久,却对男友说,自己刚和朋友吃过晚饭、回到家里,身上穿着粉色连衣裙和皮草,戴着黑帽子。利用视觉的障碍,女人编造了第一重谎言,目的是掩盖自己落魄的样子,塑造出自己对分手泰然处之的形象。这出自我美化的戏码成功骗过了男友,同时让不明就里的观众心生疑惑。接下来观众发现,女人不仅通过撒谎捏造了视觉信息,还有意隐瞒了自己糟糕的精神状态,她不仅用声音描摹了外表肖像,还尝试进行心理自画像。面对男友的询问,她强调自己“仅仅吃了一片”安眠药,尽管之前有点头痛,但现在已经完全“振作起来”了,而且她对男友发誓,自己“精神特别足”,“非常、非常有勇气”。程度副词的重复使用、时间细节的加入,都体现出女人试图增强谎言说服力的努力。深爱着男人的女人希望这段关系能体面地结束,希望自己给男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当男人询问女人是否有看见他的手套时,更加令人心痛的欺骗场景出现了:她一边拿起桌子上的手套,将手套贴在脸上狂热地吻它,一边在电话中说她到处都找过了,但没有发现手套,万一明天找到就还给他。在这场自顾自的独白中,声音与画面的矛盾带来了一出荒唐的“戏中戏”,真实的爱意和强烈的痛苦被掩藏在了虚假的话语和平淡的声音之下。
入戏到深处,女人在虚与实的较量下、在真与假的摇摆中,逐渐陷入了恍惚的境地,似乎开始对自己的谎言信以为真,出现了对声音过分信任甚至恐惧的倾向。就像起初为自己画像一样,她对男友说着“我看得见你,你知道的”,“我的耳朵上长了眼睛”,以臆想的姿态全神投入地描述了男友当下的衣着和动作,甚至在男友打算猜测她的姿态动作时,她下意识地捂住了脸,央求道:“哦不,亲爱的,千万不要看我……”直到此刻,女主角对话语和声音的信念感达到了至高点,她紧紧依附于声音带来的安全感和亲密感,唯恐这种虚妄的亲昵也最终结束,仿佛一位难以出戏的演员,最终将“自欺”和“欺人”混为一谈。
这种欺骗的声音,何以转向真实呢?结合我们关于受话者的分析可知,要想打破独白的单向度,破开真实与虚假之间的屏障,关键在于使受话者和说话者之间产生碰撞:或将受话者引入场内空间,或将说话者引入场外空间。在《人声》中,不在场的受话者寄居于发声者的沉默之中,藏匿在声音的空隙之间,他虽未进入具象的舞台场域,却已然存在于抽象的戏剧空间,实际上一直游走在场内和场外的边缘。所谓边缘,是由电话这一道具充当的,听筒的这一端为场内,那一端为场外,不被看见的安全感为双方创造了欺骗彼此的条件,但通话的不稳定性,恰恰也为说话者和受话者敞开了侵入对方空间、发现真相的机会。
由于电话断线,女人重新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却发现对方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正在家中:他究竟在哪里?他刚才的温柔话语中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自以为聪明的撒谎者,未尝不是愚蠢的受骗者?到了即将分离的境地,双方自说自话、互相欺瞒的游戏有何意义?绝望之际,女人不再掩饰自己的痛苦,坦白了一切:她没有吃晚饭,没有穿漂亮衣服,而是疯了一样等他的最后一通电话,还妄想独自去到他的窗下默默等待;她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几天前吃了大量安眠药试图自杀,直到现在还在发烧;她自知混沌可笑,却无法放手,只能一跃而入深渊一般,苦苦爱着他等着他。从欺骗到坦白,这场复声的独白如《埃菲尔铁塔上的新郎新娘》一样,又一次拨开了美好而虚伪的面纱,暴露了骇人但诚实的真相。重重堆叠的谎言被一层层剥除,令人心惊的、远离理性的真实面貌,在经历了厚重的铺垫后终于畅快淋漓地凸显。至此,在述及话语层面上,让人物在碰撞中袒露真言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而在叙述话语层面,观众作为另一重受话者,也在寻寻觅觅中逐渐拼凑出故事的全貌,仿佛循着声音穿越密林,一点点窥见真相的光亮。
《人声》的观众通过倾听而获取的信息始终是支离破碎的,似乎作者与人物的“表达”远比观众的“接受”更重要(这也符合戏剧独白的特点),台词以表现某种精神状态而非传递实际信息为第一目的,作者仿佛并不在乎观众是否能完全理解每一句话的含义。从细节来看,大量“对”“不对”的回答,以及突然提到的与上下文无关的信息,常常让听众无法通过联想拼凑出完整的对话。女演员在谈到多个人物时都没有给出关于身份信息的暗示,观众只得慢慢等待某个线索在后文出现(或不出现),解开(或保留)人物身份的谜团。剧中有一段台词是作者要求女演员用一门“她最熟悉的外语”讲出的,这段话的内容本身并无特殊性,也不存在对某门特定语言的要求,我们几乎可以认为,作者只是希望借外语达到阻碍观众获取信息的目的。实际上,被剥夺了“知情权”的观众只能随着对话的推进隐约猜测到,交谈的双方是已经分手但仍有感情的情侣,而且观众直到接近结尾时才得知,男人因为不得不与他人结婚才与女人分手,两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正是因此变得复杂缠绵。
纵观全剧,观众探索故事真相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正如戏中那两个无法完全彼此共情的人物,作为受话者与说话者的观众和演员之间也始终存在着隔阂;言语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在这个用声音而非文字写就的剧本中,科克托让观众感知到了“人”的气韵,而非仅仅捕捉三言两语、是是非非。这不由得让我们猜测,或许科克托寻求的“真”不仅是“真相”,更重要的是人的“本真”状态。“本真”何处寻?须剥离肌理,回归自由。
三、自由之声:由生向死的通道
科克托希望《人声》的女演员展现一种持续失血的状态,如同一只蹒跚的动物在不断流血,直到幕落时,房间中应当有满是鲜血的感觉。⑨详见Jean Cocteau,op.cit.,p.452.在阴暗、苍白、凌乱的房间里,温暖、鲜红、黏稠的血液具有别样的生命感。在苍凉的视觉图景之上,演员将生发自内心的丰沛情感和本能冲动灌注于声音之中,出声即是在失血,声音因此具有了血红色的可怖力量感。然而这样的声音又是极其单薄的,为爱所困的发声者孤独而脆弱。电话线如同生命线,从紧握到放手的过程,也是从自我禁锢到寻求解脱的过程。爱的自由,抑或不爱的自由,成为自我的自由,抑或舍弃自我的自由,在向生的踟躇和向死的奔赴之间悄然浮现。
在《人声》中,声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象征着生命力。剧目的开场即展现了无声和有声带来的强烈动静对比:在死寂的房间中,女主角“仿佛被杀害一般”横躺在床前的地上,然后木然地缓缓起身,拿了件外套,在电话前停驻片刻又走向门边。此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她“扔掉”外套,“冲向”电话,“一脚踢开”挡路的衣裳,接起了电话。电话铃声仿佛将她从“死”的状态中拯救了出来,重新赋予了她生机和活力。似乎只有情人的声音能带给她慰藉和希望,能使她充盈活着的动力。
不过接起电话后,女人未能如愿直接与男人通话,而是进入了喧哗的接线台。女人的声音短促而急切,饱含着期待,充满力量感,这种力量感正是来自她对爱人的渴望。她与线路上其他人一语双关的对话,已经对观众做出了暗示。“我们的线路上有好几个人”隐喻着男人和女人的感情中也出现了插足的第三者,“可是您又想让我怎么做呢”表现了女人无依无助的心情,“我的错吗……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暗示了女人无辜受欺瞒的遭遇。当男友终于接入电话线路,女人在形容他的声音不清晰时说“你离我很远很远”,意味着两人关系的逐渐疏远,而她随即提出的让男友“重新拨过来”⑩法语原文为«Redemande-moi»,也有“再来问我、再来找我”之意。的要求,其实暗含着对破镜重圆的期待。无论是焦躁的情绪还是不安的声音,都极具“人”的意味,女人在通话的那一刻似乎“活了起来”,仿佛皮格马利翁手下的雕塑作品从冷冰冰的石像变成了真实可感的女子。
线路错乱、中断重拨的情节在剧中一共出现了三次,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将女主角的状态划分为欺骗与顺从、坦白与疯狂、平静与决绝三个阶段。开场时的第一次断线暗示了剧情走向,通话中途的第二次断线使女人发现了男友撒谎的事实,而线路第三次中断时已接近尾声,女人在第三次重拨后收敛了感情,似乎已准备好结束一切。在第二个阶段,女人在坦白真相之后,开始毫无保留地诉说自己的爱意和悲痛,声音与生命力的关系正是在这里得到了最直白的印证。女人仿佛沉溺于深海之中,而电话线成为唯一能为她输送氧气的管道。她说自己曾做过一个梦:“我在海底(……)靠潜水服上的一根导管和你连在一起,我哀求你不要切断导管。”随后她无不悲戚地说:“这五年我靠你活着,你是我唯一可呼吸的空气(……)现在因为你在和我说话,我就呼吸到空气了。”一方面,女人对男人的声音怀有强烈的渴望,她希望紧紧抓住情人的声音带给她的力量,支撑自己活下去;另一方面,女人对失去对方的声音感到极端的恐惧,对她而言,挂断电话几乎等同于切断为她输送氧气的导管。因此,每当她遇到电话线路不稳定的状况,或者联想到通话结束的片刻,女人就会表现出窒息一般的疼痛感。一想到他即将挂上电话,她就开始哭泣,同时怀疑线路是不是已经切断了;设想到将来他再也不会拨来电话,女人抑制不住悲痛、发出呻吟;当另一位通话者因为串线误听了他们的对话时,她变得十分暴躁,可是面对外人对男人的指责,她又忍不住为自己的情人辩解;而当线路被第三次切断时,她疯狂默念着“我的上帝,让他再打来”,仿佛濒临死亡的溺水者在进行最后的求生祈祷。她迫切地想要抓住传递感情的声波,从中汲取支撑自我的最后一点力量。
然而这种抚慰人心的声音终究是纤薄脆弱的,已然沉入深海的溺水者,仅仅依靠一截导管呼吸,又能维持多久呢?话音会有终了的一刻,苦苦维系的感情也会有彻底断绝的时分。声音作为情感的依托,珍贵又单薄,既是强大的,又是薄弱的,当声音中的力量感逐渐消磨殆尽,女人将如何自处?我们将在第三阶段找到答案。当线路第三次中断并重新接起来之后,女人似乎已经不再奢望改变注定悲剧的结局,转而敞开一切感知器官,竭力感受最后的温存。她将电话线缠绕在脖子上,这样他的声音也就绕住了她的脖颈——声音在她的身上变成了具象可感的事物。她已经可以坦然地说,电话局稍后就会切断他们的通话;她对爱人提了最后的要求,希望他和未婚妻不要下榻他们曾住过的酒店;最后她平静地对他道了谢,一边重复着“我爱你”一边求对方赶快挂断电话;最后听筒掉到地上,这部戏也就结束了。解读平静而决绝的第三阶段,看待女人在禁锢和自由之间的转向,是我们理解科克托所谓自由的关键。
自始至终,《人声》这部剧带给观众一种压迫感,畅快和自由是十分少见的,紧张和困顿是持续存在的:一方面,不完整的信息带来了恼人的失重感;另一方面,电话中传来的声音一边带给女人力量,一边也对她施以牵绊。在舞台上,女人的走动范围和肢体动作都受到听筒线的限制,这种动作上的局限着也象征着她在感情上受困的状态。她心甘情愿地被感情禁锢,甚至盼望着这枷锁再紧一些、再重一些,直到她将电话线缠绕在自己身上,形成彻底被捆绑的姿态。封闭、压抑、围困,《人声》为观众呈现的几乎是自由的反面,而这种溺水般的窒息感直到最后一刻才消除:不停喊着“挂断”(couper)的女人丢下了听筒,这里的“挂断”有多重含义,既是指停止通话,也是指斩断爱情,甚至是弃绝生命。缠绕在脖颈上的电话线越来越紧,为爱所困的女人最终选择了自杀,在经历了极端的禁锢后,她终于获得了自由:不必再苦苦等待他人,不必再为他人而折磨自己,不必在意爱是否还有回音。正如所有欺瞒的声音,都是在为凄然吐露的真相做准备,一切牵制和围困,亦是在为结局猛然彰显的自由做铺垫。科克托曾在一部即兴戏剧作品中写道:“自由在监狱中最具力量。”⑪Jean Cocteau.L’Impromptu du Palais-Royal (1962).Théâtre complet,Paris:Gallimard,2003:1267.在《人声》中,他选择了用极致的束缚反衬极致的自由。
将自由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在科克托的诗意创作中并不罕见。神话中的诗人俄耳甫斯,就以自由穿梭于生死之间的本领为最重要的特征。在科克托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同样具有生命力的状态;生与死不是简单的平行、矛盾或妥协的关系,而是一同呈现了现实本身的二重性。因此我们看到,在科克托的许多小说和戏剧作品中,常常出现这样的人物,他们因现实中的爱情不可实现而奔赴死亡,凭此获得爱自己或爱他人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类人物曾在生的阶段为爱所困,但是他们由生到死的转向绝不是痛苦不堪的,而是骤然畅快的。这便像是走在跷跷板上的孩子,原本沿着沉下来的一端战战兢兢地走向中间,越是接近中点越是心惊,直到轻巧地跨上另一端,反而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对面的平地上:此端是生存,彼端是死亡。在科克托的世界里,死亡和生存一样,是非常自然的,正如我们在《人声》中看到的,女人在探索了一切有关维系生命的可能之后,自主而自觉地亲近了死亡。
作为生命的另一面,科克托笔下的死亡从不可怖,它只不过因过分疏离于我们所熟知的现实,而多了几分异样而轻快的飘逸感。踏上跷跷板的另一端之后体会到的轻盈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自由体验,而做出跨向彼端的选择,是一种更为慷慨的自由气度。科克托在《职业的秘密》(le secret professionnel)一书中是这样书写诗人的“行走”的:“诗人行走在流沙之间,双腿时而陷入死亡之中。他已经习惯如此,就像心脏病患者对疯狂的心悸毫不恐惧、习以为常一样。”⑫Jean Cocteau.Le Secret professionnel.Paris:Librairie Stock,1922:62.由生至死的跨越,模拟着由现实迈向非现实的跨越,而诗人始终是两界之间的媒介。自由而洒脱地回转于生死之间,是诗人无奈的天赋,也是诗无情的呼唤。《人声》中的声音便是这样呼唤着、推动着女人,卸下束缚,听从本心,取道死亡,触碰自由。以超现实的眼光审视现实,以畅快的疼痛安抚不快,诗的自由精神即在于此。
在整部剧中,女人仿佛以抱石投海的姿态一寸寸陷入了死亡的流沙,她的声音如翻腾的海浪,如回旋的暗流,冲刷着谎言,拍击着束缚——而这又何尝不是诗人科克托试图发出的声音。科克托作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家,自20世纪20年代起便是常见诸报端的风云人物,外界多对其风流潇洒的作派、同性恋的身份和一段段恋情津津乐道,人们对科克托个人生活的关注竟一度盖过了对他的才华的认识。《人声》于1930年2月15日在巴黎的一家剧院上演时,诗人保罗·艾吕雅(Paul Éluard)甚至在演出中途无礼大喊:“下流!(……)这些话是您对让·狄博德⑬让·狄博德(Jean Desbordes),法国作家,科克托当时的同性伴侣。说的吧!”⑭Francis Ramirez,Christian Rolot.Notice à La voix humaine.Théâtre Complet,Paris:Gallimard,2003:1678.其言语间尽显敌意和轻蔑,科克托在舆论界面临的处境可见一斑。科克托曾在一部题为《陌生人日记》(Journal d’un inconnu)的作品中叹道:“或许,我既是人们最陌生的诗人,又是人们最熟知的诗人。”⑮Jean Cocteau.Journal d’un inconnu.Paris:Grasset et Fasquelle,1963:24.尽管科克托始终活在世人的瞩目下,他内心的声音却一度被忽视;流言与戏谑纷纷扰扰,他的思想和诗才却不尽为人所知。被看见却不被听见的反差让诗人品尝到了深沉的忧愁和极度的孤单,甚至逐渐演变为一种无法承受的“存在之难”⑯《存在之难》(La difficulté d’être)是科克托于1947年出版的一部散文集的书名。。因此诗人始终在渴望着而又战栗着,思考自己应当如何被听见和被看见、是否要被听见和被看见。他试图在戏剧上通过“凸显”和“剥离”破除迷思和束缚,而他渴望自如地展现的所谓“完全裸露的真相”,何尝不是自己最真的灵魂。
结语
“从前,我们能看见彼此。我们还可以晕头转向、忘记诺言、冒险去做不可能的事,拥抱着爱人、紧搂着爱人,去说服对方。一个眼神就能改变一切。可通过这机器,说结束就是结束了。”⑰Jean Cocteau.«La voix humaine».Théâtre Complet,Paris:La Pléiade,2003:464.《人声》利用电话这一道具,以极简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终结的故事。在舞台上,人物被剥离,对话被剥离,延续爱情的可能性也被剥离;谎言被终结,执念被终结,踯躅求生的挣扎也被终结。在声音的余韵中,回荡着的是对真相的渴求和对自由的归依。
所谓诗意的声音,大抵也是诗人内心的声音。诗所指向的那个神秘混沌的非现实世界,那个“比真实更真”的自由的所在,未尝不是诗人的自我世界。诗人渴望敞开自己,渴望自由发声,这种声音被灌注了诗的精神,同时具备蓬勃的生命力和窒息的孤独感,而它是否真正被听到,则始终是谜团。其实科克托在不止一部戏剧作品中,别出心裁地探索了用声音的艺术进行诗意传达的可能性,以独白的方式实现的单向表达屡见不鲜。如果说他的《人声》是“一个人的对话”,科克托在十年之后创作的另一部戏剧《英俊的冷漠者》(Le bel indifférent,1940)则堪称“两个人的独白”⑱Francis Ramirez,Christian Rolot.Notice au Bel Indifférent.Théâtre Complet,Paris:Gallimard,2003:1739.:后一部作品呈现的同样是一位感情受挫的女人的独白,不过她的受话者(男友)就在台上却一言不发,直到结尾时,她才发现男友早已睡着,根本没有听到自己说的话。在这些作品中,“说”始终比“听”更加坚定有力,听者或在场或不在场,或听或不听,无论如何都具有被弱化的趋势。其实,诗人尽管渴望敞开,却未必期待被接受,尽管渴望发声,却未必期待被听懂。在科克托的世界中,并非一切声音都需要被听见,并非一切矛盾都需要被解开,内与外的撕扯被诗人化作诗意的张力,引着诗人向更加丰富而深刻的超现实倾斜——这才是矛盾的意义所在。一切文学与艺术创作,大概都可算是作者面对苍茫历史的自白。在提笔的那一刻,他已坦然站上了空荡阴暗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