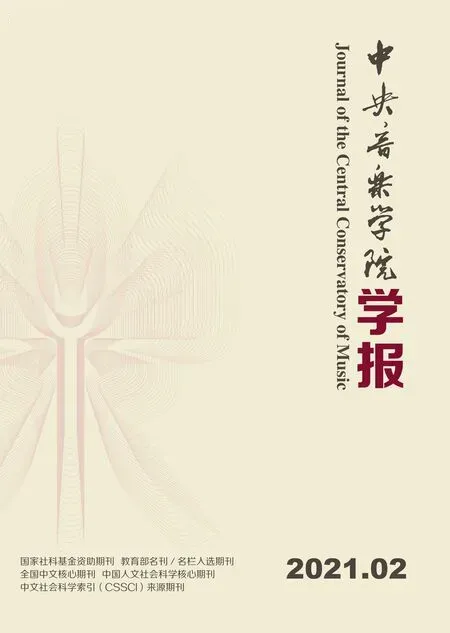民歌的教育传承与中国声乐
肖 璇
民歌是中国音乐文化基因的表征,因它的传统音乐形式渊源(1)如江明惇在《汉族民歌概论》前言所述:民歌是音乐最初的萌芽,一切音乐作品都离不开它,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5—14页。,又是音乐研究“掬水见月”的凭照。自现代声乐学科建立以来,民歌从制度、社会评价、作品等环链中移植至现代教育环境,形成有别于民歌母语传承的文化生态。如今距1920年中国出现第一位具有现代学科意识的声乐教师(2)第一位中国声乐教师是孙继丞,他1919年任教于私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之后有留学回国的周淑安1921年任教上海中西女塾。见孙继南编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84—2000)》,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58页。正好百年,中国现代声乐从“别求新声于异邦”式(3)“别求新声于异邦”为鲁迅1907年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中国文学学习外国文学的口号。“别求新声于异邦”亦可为中国人声艺术20世纪初的现代性建构作注脚。西方美声唱法的主动习得,到如何在传统中重新发现中国声乐、建构人声符号“中国性”表达的自觉,民歌逐渐成为中国声乐主体性建构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以往有关民歌的传承、音乐形态、歌唱民俗、文化内涵等等文章和著述已就古今中外、传统继承等关系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民歌教育传承与中国现代声乐的相遇便是这场讨论的具化,涉及中国声乐多样性、中国声乐未来发展等诸多论题。
笔者的民歌的中国声乐教学研究肇始于2019年带领团队参与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名录建设(理论研究)》子课题。在追溯了20世纪30至40年代延安鲁艺和重庆青木关“山歌社”最初的民歌收集、研究与演唱实践,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三化”(4)“三化”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下民歌声乐教育和民歌展演,以及各大音乐院校建校初期的民歌声乐教学探索等等,民歌向上流动进入中国现代声乐教育的大历史背景之后,团队成员又考察了民歌之于现代声乐教育的考核制度和艺术评价等因素,并抽样对目前中国高等音乐院校的现代民族声乐、少数民族地区民歌传承班的民歌教学进行了微观调查研究。以此较为全面的声乐教学调查为依凭,笔者提出民歌的教育传承概念(5)博特乐图曾提出“学院式传承”,见博特乐图:《高校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传承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传承班的探索》,《人民音乐》,2015年,第1期,第59页。,它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后民歌母语传承空间的扩展。教育传承为民歌进入现代社会多元传承方式的一种,虽不具有其母语地区的即兴性、语境化、原生状态等等的传承优势,却是以现代声乐表演学科自身的方式——风格确立、符号表征、作品改编等,行使着民歌的教育传承之本。无论是教育者呈现在教学观念上的以西为主,还是传统人声和现代声乐创新之间演唱技术的努力调试,民歌向来是中国声乐的风格归趋,中国声乐(6)本文的中国声乐特指中国学校声乐教育和与之有关的艺术实践。从声乐专业命名的改变到教学科研的推行,中国声乐近年来受到瞩目。关于中国声乐从概念到实践的过程,见肖璇:《中国声乐的建构与展望》,《音乐艺术》,2021年,第1期,第100—101页。是民歌的现代命题,但目前民歌的声乐教学是否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后民歌多元传承中的一种?民歌的声乐教学似乎也折射出中国声乐的当下困境。
一、中国声乐教育的当下困境和机遇
笔墨当随时代,民歌亦无出其右。但现代声乐创新的底线应在于传承,创新与传承两者相互触发,相互制衡。一边是西方思想的引入与传统民歌相互作用,呈现形式、内容不同结合(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的复杂样态,但因有了“人”的因素,创新和传承并非必然呈现二元对立局面。所谓今人唱不出宋人之韵,宋人奏不出唐人之音,每次音乐实践都是音乐传统中的自己,民歌传承包含了作为主体的时代表达和传统认同之间的复杂纠缠。虽已抛开新旧二元对立、承认没有不受任何影响的、绝对的音乐本真和自然,但仍不得不注意到,自1979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立项至今的40年,40万首中国乡土民歌以惊人的速度退出社会生活和主流人声艺术表达(7)据前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主任称,1979年开始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动员了万余人,历时30年在全国范围内普查记录,共收集到民歌40万首左右,在此基础上精选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包含近3.5万余首民歌。,某些传统音乐被“改写和发明”后,以碎片的方式栖居于新秩序中。于是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思考如何传承和安放已成为过去的人声音乐传统,更具现实意义。
(一)提高与继承——富有争议的民歌教育传承
步入现代社会的传统民歌,一方面旧有的自然传承空间受挤压、被边缘化,如地方传统节庆、礼仪的锐减或仪式小型化,如本属于两性对唱的民歌已失去“对歌求偶”之需,中原腹地和内蒙古有了现代交通工具的打通,“走西口”之道已是历史尘封……;同时,传统民歌也随着现代传播媒介、网络虚拟空间、学院教育等等拓展了生存和传承的边界。目前富有争议的是,除了少数民族传承班此类有明确传承意义的声乐教学,其他中国声乐教学是否可称为传统民歌的一种传承形式?萧梅在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首届中国民族声乐教学和理论研究”开幕式上谈到,她曾邀请她的学生对现代民族声乐专业的音乐会和教材情况进行调查。学生们通过收集24场民族声乐歌唱家的专场音乐会曲目单,得出重复率最高的9首民歌分别是:《茉莉花》《孟姜女》《马桑树上搭灯台》《走西口》《绣荷包》《亲疙瘩下河洗衣裳》《桃花红杏花白》《嘎达梅林》《洗菜心》。此外,24场音乐会曲目中“在唱”民歌不到35首;从21本、总量为1286首声乐教材来看,传统民歌(不含改编)101首,占总曲目量8%。(8)萧梅在2019年11月“首届中国民族声乐教学和理论研究”开幕式的发言。就笔者近年来对中国声乐课的课堂观察,中国声乐教学和表演中的民歌数量,在各种声乐考核将民歌作为重要类别以后,高校“在唱”民歌曲目数量略多于目前教材刊录的数量。原因是,有部分民歌是声乐教师根据个别学生所在族群和地域特性选择的民歌曲目,还没有来得及收录到教材中,或是由于语言和风格等因素限制了学院之间的广泛传唱。即便如此,音乐学院教学的“在唱”曲目与传统民歌数量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曲目数量是民歌传承的重要标准,目前高校民歌的“在唱”曲目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采录的35222首传统民歌数量上非常悬殊,中国声乐作为一种20世纪后新的人声艺术形式能否、或者是否正在承担传承之职?除了传承曲目数量的有限,民歌在专业声乐教学到底是“提高”还是“传承”?目前标准化的、以混合声为主的民歌演唱确实可以帮助歌手,改善中国传统人声艺术因以“掐喉”来突出“直、亮”音色,形成的声音审美,造成的高音困难、歌唱寿命短的局限;但看似某些演唱技术上的提高,有时却是以遮蔽多样性民歌演唱方法为代价。又因过分强调“提高”,导向了技术或科学至上,无意中以“音色统一、泛音丰富”等评价标准来衡量声乐比赛、教学招生、艺术评论,助长了“科学之名”的声乐艺术权力话语体系建构,它与现代社会生活转型合纵形成的双重压力,使中国传统声乐艺术被挤压、退出中国现代声乐的主流表达。
关于“继承与提高”,1957年全国声乐教学会议明确了新中国建立新唱法的“继承并提高”(9)具体为“我们的任务是虚心向民族传统唱法的丰富遗产学习,向民族民间歌唱家们学习,与他们亲密合作,整理我国民族传统唱法的丰富经验,逐步使它科学化系统化,不拒绝吸收外来的有益经验丰富自己……使我们民族的传统唱法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学者们常将此总结为“继承并提高”方针,刘芝明:《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在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摘要)》,《人民音乐》,1957年,第3期,第2—5页。方针;李凌曾有“学习民间唱法和西洋唱法的‘两种努力,一路向前’(10)张静蔚主编:《李凌论》,中国音乐学院李凌课题组编印,2005年,第77页。”的平衡发展论。中国音乐学院成立初期声乐系主任汤雪耕在《民族声乐的发展和提高》中,明确提到演唱方法继承的必要性,以及对唱法的继承应是以“学会、学像、学真”为其目的(11)汤雪耕:《民族声乐的发展和提高》,《人民音乐》,1963年,第2期,第7页。,以至于后来在中国音乐学院实际的中国民族声乐初期探索中,他明确了女声可有大本嗓子(以真声为主)和真假声并用两种基本类型,“借鉴和传承”倡导下的中、西演唱技法在教学中“孰主孰次”一目了然。如今有民族音乐学家(12)伍国栋曾在笔者承担的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名录建设(理论研究)》子课题的项目评审会上谈到:民歌的鲜活在于即兴性,民歌变体的演变发生与演唱者的即兴分不开,表现为因人而异、因景而异的唱词和音调的变化,而学校声乐教学把民歌最鲜活的东西失去了,高校声乐教学应该注意到民歌的即兴性因素。认为,高校的民歌教学应该注意到传统民歌的即兴性语境。这是音乐学家对现代声乐教学提出的更高要求。但首先需明晰民歌即兴性的强调之于现代声乐教育内在要求和未来发展的意义;如果高校声乐教学仍走标准化、舞台化、技术化不断提高的道路上,民歌即兴性很难在现代声乐教学中达成;只有正确处理继承和提高,不片面、孤立强调提高一方,方可考虑回到民歌即兴性中去接续传统音乐文化的活水源头。
从20世纪初新音乐运动到延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实践,从“土洋之争”至“学院派和原生态民歌争鸣”,“古今、中外”的两对关系的讨论从未缺席,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交织成了一张巨大的意义之网,于不同社会转型的节点,产生了围绕“传承和创新”的各种话题。
早在1961年中央音乐学院时,李西安就曾对刚入学的苗族歌手罗秀英演唱的所有民歌进行了录制,并于中国音乐学院从中央音乐学校分开独立建院、到中国音乐学院工作的1964年后,邀请民歌研究专家耿生廉对其录音进行精准记谱保存,这是他对民歌进入音乐学院后,风格性演唱减弱的担忧(13)刘红庆:《歌行天下:耿生廉民间音乐研究与传播之旅》,济南:齐鲁出版社,2014年,第54—55页。,也是他后来提出“传统与创新两极张力是音乐文化重构和发展的活力,保存要纯正,创新要大胆”的张力场理论(14)李西安:《移步不换形和涅槃而后生:关于中国音乐发展对策的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第50页。的最初实践。随着21世纪文化人类学越来越在知识界成为一门显学,“去殖民化”“文化多样性”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影响着音乐学学者的研究,不断被消解的传统民歌成为大众的田园乡愁和学者多元文化的学术理想。他们厌恶音乐的“同一性”,于是在评介现代中国声乐表演时,“西方”时常被援引为一个背景,成为“文化差异性”的反照。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逆全球化的语境下,有人将“本真性”作为信仰与美德;另外一些人虽亦是接受民歌转译、变化的观点,但仍不满意现实教学中继承和借鉴主次关系,对丧失个体生存价值意义的科学主义多有警醒,以“唯科学演唱技术论”诟病之,并建构原生态民歌概念,提倡学院派向原生态学习,重塑民族音乐精神,把握真正的中国声乐语言,探寻现代中国声乐未来发展方向。虽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决议规定禁用或慎用“本真性”(15)姚慧:《何以原生态:在全球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文艺研究》,2019年,第3期,第144—145页。,但在文化逆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希冀中西声乐文化在声乐技巧上应互为镜像、重塑中国声乐“中国性”的声音却从未消减。
(二)传承与开拓——中国声乐教育的多元尝试
学校声乐教学从建立之初起,均以“通过现代声乐课程承担培养音乐人才和音乐教师”为首要任务,因在百年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逐渐变为了现代教育机构,学校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关系也缓慢发生着变化。坐拥地方传统音乐丰厚资源的广西、内蒙、贵州、云南等地开设的如“广西少数民族歌手班”“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传承班”以及“贵州大学侗歌班”“西安音乐学院陕北民歌系”等无疑是民歌在声乐表演学科中教育传承的一类方式。这些是明确将“传承”或“传统音乐资源”写入教育机构名称、并以“传承”为办学目的的教育机构。另有近年来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诸项目,如2019年4月,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蒙古族长调艺术人才培养”(内蒙古艺术学院承担)和2019年9月国家艺术基金“裕固族民歌表演人才培训”(四川师范大学承担)等等亦可列为民歌高校传承之论域。这类民歌教育传承模式,借鉴了20世纪50年代“三化”呼声下,各大音乐学院施行的“民间音乐家与音乐学院教师共同执教的双轨制”(16)李西安:《对传统音乐传承、变异与创新的再认识》,《人民音乐》,2003年,第12期,第21页。,各地方音乐院校利用地域优势,依就近原则将民间艺人请上讲坛,把民歌传承与现代音乐教学内容和目的相结合,培养的是能融入现代社会需求、又传承传统音乐的双重音乐人才。以上所述的学校在族群民歌的传承和现代声乐教学要求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积累了一些可供推广和借鉴的经验,比如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系,他们在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上,设计了以民歌演唱为中心的八门核心课程体系,以及“声乐教师(主导)+专家组审核(把握方向)+特色教师(指导配合)”的教师团队建构,而教学考核的评价也不唯西方声乐技术为标准,不在“丰富混声共鸣和声音统一”现代声乐审美要求上作强行规定,而是根据壮族民歌审美特点和风格,灵活地运用声乐技术,教师们探索壮语语音的声乐发声练习曲,主动适应民歌的演唱,并注重对壮族特色发声方法的研究和整理(17)刘海燕: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名录建设(理论研究)》子课题《中国民歌的教育传承:地方院校民歌的传承与教学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子课题项目负责人:肖璇。。此种在母语地区的学校教育传承模式也因传统民歌和现代声乐手段的主次分明、能很好保持民歌的原有风格特色,而得到心系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当代命运的音乐学学者樊祖荫、乔建中以及大众的肯定。(18)如樊祖荫和乔建中曾对院校利用地方传统音乐资源的传统音乐学校教育传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详见樊祖荫:《民歌传承方式的新发展——略谈“广西少数民族歌手班”》,《民族艺术》,1996年,第2期。乔建中《西北传统音乐研究·序言》,载张君仁:《西北传统音乐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内蒙古艺术学院和广西艺术学院等地方艺术院校吸吮各自族群母语人声艺术之养分,教学实践中虽然遇到许多的现实问题,但探索者一直在传统承续和现代性的矛盾中探索高校传承的边界和人声艺术创新的底线,在少数民族民歌的学校传承与中国声乐的主体性建构之间权衡。以上这些地区学校声乐教育,在原有母语传承的社会形态逐渐消散的背景下,肩负着民歌的风格性(旋律和唱法)传承和新知识、思想观念开拓的双重职责。
一批汉族和少数民族民歌,或根据民歌特性音调创作的歌曲,因为现代声乐的成功教学和媒体的推广,让更多中国人熟悉,如《走西口》(山西)、《放风筝》(山东)、《斑鸠调》(江西)、《北京的金山上》(藏族)、《嘎达梅林》(蒙古族)等等。各类文化展演和族群文化交流,使地方文化自豪感和族群文化自信得到增强,促使本地区和本民族民歌在各自社会空间得到更好的传承。自从有才旦卓玛、彭丽媛、郭颂、吴碧霞、龚琳娜等成功借鉴现代声乐演绎传统民歌演唱的典范,人们逐渐理解到在民歌自然传承空间变迁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以现代声乐教育形式在高校传承不失为传统民歌的现代之路,亦可丰富中国声乐的多样性表达。他们倾向动态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民歌并非铁板一块。动态音乐史观也并非后现代史学者的专利,当我们回溯早期民族声乐建构历程时,也可听到类似的表述,正是有李凌“移花接木,另有新趣”比喻新唱法的创造,才有了后来现代民族声乐的蓬勃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声乐建构起的中国社会生活音乐景观。
在体系化和标准化的现代教育体制内,“西方演唱技法”(科学化、舞台化)的声音审美逐渐地成为了声乐表演学科的学科范式,于是中国现代声乐学科建立之初,“借鉴”西洋唱法、科学化的学院声乐教育,从集体意识到教学实践逐渐占了上风。现代民族声乐把中国民歌作为艺术风格元素加以重视,民歌加强了民族声乐艺术表达,但创新唱法一直是在保留曲调(风格)基础、加强即兴性和舞台感染力和表现力的方向上探索。现代民族声乐建构之初,有“民族化”这一自上而下的力量“调谐”演唱方法和音乐风格之间的关系,民歌的现代声乐教育尚能以“两条腿走路,以传统为主”展开。此后的民歌声乐教育虽有创新,并取得一定成绩,但在“是演唱技法还是曲调借用”的声乐风格性厘定上缺乏集体思考,某些声乐教育者受庇于民族声乐开拓者所建立的、以西洋演唱技法改造中国人声艺术这棵大树,将自身框定在教学和表演实践的舒适区,以自我复制的“内卷化”方式,使中国声乐丧失应有的艺术活力。
中国现代声乐表演领域向来将“科学演唱方法”作为“政治正确”,“借鉴了西方科学的美声唱法”即意味着对世界上最先进演唱技术的占有和支配,“科学”作为不刊之论,已成为自20世纪初西方美声唱法进入中国后表演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在“科学”至高无上的声乐表演领域,对现有歌唱技术的追问和质疑过于微弱,我们只是在曲目和艺术风格需求时将手伸向民歌,对中国传统人声演唱技巧缺乏应有的研究。而人类学和音乐学常对表演学科不绝于耳的“科学”表述多有诟病,认为其在艺术评价和教育体系之内,以科学之名义来建构艺术的权威性,形成一套封闭系统,让传统人声艺术技巧在此闭环内集体失声,科学性、标准化的强调更是违背了艺术以差异、多样性为美的原则和基础。以上所述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与民歌传承曲目数量上的差距即是在以科学单一技术方法为标准来看中国传统多元的人声艺术,因而其中大部分都无法归入“科学演唱”之类别。比如,中国传统人声艺术中各种形式的颤音演唱方法,与科学演唱方法倡导的“喉头稳定”相悖,中国民歌中存在的“鼻音音色”与西方美声强调音色统一有着一定差距……。有些声乐教师将民歌演唱方法作为“锦上添花”的特殊润腔唱法,大多数仍在科学的“泛音”“通道”的基本概念下采取的“顺着教”的方式加强中国声乐的风格性,但是某些诸如海菜腔和洮岷花儿从头至尾“直声”的审美和演唱技法,又如何能归入到西方美声技法所强调的丰富泛音的科学话语体系中呢?更需警惕的是,演唱方法“科学”至上观念也可能让中国声乐在演唱方法上过度倚靠于西方美声技法的大树,失去自我创新、以及包容中国乃至世界非西方人声艺术传统多样性的文化能力。
二、重构以唱法为核心的中国声乐表达
“唯技术”和“唯本真”张力之间,是民歌与目前中国声乐建构的天然联系。如民歌作为一种符号传承顺理成章的话,中国声乐教学过程似乎也无不进行着民歌的无意识传承:从民歌基本润腔(甩腔、滑腔)和曲调中萃取中国元素,塑造现代声乐艺术风格。但在人声艺术风格形成的三要素中,除了语言(方言唱词、衬词)、音调旋律,还有影响人声音色的演唱方法。注重民歌地域性唱词、确立以方言唱词为主的民歌现代声乐演绎(19)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研究和声乐实践的价值可见钱茸《探寻音符之外的乡韵:唱词音声解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第35—57页。,需要的是声乐表演和教学观念上的更新;民歌(以及说唱、戏曲等)音调旋律对于中国声乐的风格性厘定,并非声乐教学要讨论的范围;而突出中国声乐风格特色唱法的运用,恰恰是中国声乐教学的应承之责,只是它在以科学为纲的现代声乐教学思维中被边缘化。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所谓“顺着教”——教学采取整体性的“以西化中”(20)早在民族声乐建立之初也曾有过演唱技法“民族化”还是“化民族”的讨论。,而在关键性的声乐风格性处理中,教师常常倚赖演唱个体自有风格特征,缺乏主动研究学习传统声乐演唱技法,形成与传统有承续关系的声乐表达,让中国声乐陷入风格性不足的拷问中。人们诟病现代声乐已走到偏向借鉴(科学演唱方法)的一端,只是在以作品为中心,建构声乐风格时将手伸向民歌,取用并裁剪民歌,继而又有传统民歌“成于民间毁于庙堂”的偏执质问。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音乐文化主动融入西方,以西方音乐建构中国音乐教育和学科主流话语,21世纪后人们在现代性的批判下回望传统。重构以演唱技巧为主的声乐风格需要声乐表演学、音乐学和作曲家的共同努力。有关中国传统人声演唱技术的当代境遇,近年越来越受到音乐学学者的关注,他们站在民间演唱技法传承的角度记录它们,并反思传统人声技法与中国现代声乐技法两者的隔离状态。但在中国声乐表演学科,此话题并未形成应有的重视。因此,当21世纪文化价值相对论和文化多样性成为新的话语流,中国声乐表演者和教育者首先应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人声艺术的多样性存在,在反思声乐技术“科学话语”的弊端中,拥抱中国传统民间演唱技术,弥补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裂痕,找回因科学确定性而失去的艺术灵性与生机,建立起中国声乐技术的文化自觉和“本土优先”原则。所谓音乐的“本土优先”,并非大国文化沙文主义,而是“同一性”基础上对多样性世界文化的贡献。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第一,重拾“眼光向下”的学术取向,定期展开民间歌手“引进课堂”和师生“走向民间”的双向流动,采取“课堂教材与民间活态传唱”两种教材并重的方式。学习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民歌声乐教学真正做到“传承而不守旧,借鉴而不崇洋”的一代探索者的教学方法,在承认“传统民歌演唱合理性”的观念指引下研习传统演唱技法,以“先做学生、后做先生”来研究传统的发声法。当传统演唱技巧与西洋演唱技法强调的诸如喉头稳定等观念相悖时,王品素、白秉权等人甘愿放弃“统一声音”的执念,倾向于保持纯粹真假声间转换、民歌多样润腔的人声塑造之法,并制定适合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练声曲来加强民歌的歌唱能力、解决声音问题。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歌传承班利用母语传承和现代声乐教育各自的优势,小心处理着“风格、方法”“口传心授、课堂教学”两对关系,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在笔者承担的课题中,我们也看到某些声乐教育家民歌声乐教学案例已经有“演唱技术服务于风格”“以整体共鸣为主、根据民歌风格不同选择共鸣腔”(21)白宁: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名录建设(理论研究)》子课题《刘辉民歌教学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子课题项目负责人:肖璇。等等的民歌现代声乐教学手段。他们不仅在中国声乐风格性建构中创新民歌的演唱,也在以“人”(演员)为中心的现代声乐教学体系中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民歌资源,传授学生如何掌握合理的歌唱方法、塑造演唱者的声音个性;其次,新的社会空间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最好方式是“知来处,明去处”,即站在西洋唱法进入中国百年、中国声乐在借鉴西洋声乐技术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倡导中国声乐从相似性进入差异,在“两条腿走路、两种歌唱文化穿梭”中完成音乐文化的超越。
回望传统并非意味着急于与“科学”划清界限。现实声乐教学中欲通过民歌特殊演唱方法的补漏来找寻符号化传承丢失的语义,更需要考虑传统民歌和民歌教学演唱实践,两者在现实中是否相互包容和如何达到兼容。首先中国声乐是以中国人声艺术风格为基调的音乐实践主体,而族群和地理是形塑民歌风格的主要因素。中国族群众多,地理跨度大,声乐教师将不同民歌的特殊演唱技法原封不动地传授,或是实现西洋演唱方法与不同族群多元演唱技法的无缝对接,对于具有西洋唱法训练背景的声乐教师在现实教学中会有一定的难度。具体而言,音乐学院声乐表演专业低年级学生应主要以掌握符合歌唱机理的发声技巧、形成下意识的歌唱动作为教学目的,在每周多次的中国传统唱法风格课中,掌握声乐多元化理念和传统人声艺术的鉴赏力。高年级学生则应在发声器官肌肉协调力和人声的敏感度增强下,发展驾驭不同歌唱技术的能力,尝试在西洋唱法和传统唱法两套体系之间自由转换和组合。只有当合理的演唱方法内化于身体、形成牢固的肌肉记忆,培养了一定的演唱能力后,再学习民间发声和润腔技巧时,两者方能更有效地融合,形成中国声乐在继承传统演唱技法下的现代超越。如龚琳娜在学院声乐教学之外的多元演唱技巧探索、沈洋练习呼麦的成功,正是得益于他们多年在音乐学院进行的规范声乐训练。另外,声乐教育者展开传统人声技巧的挖掘和整理,更有利于研究成果适时转化为中国声乐的教学实践,表演学科学者积极与音乐学学者交流互动,借鉴音乐学学者的观点与研究成果,以自身具有的人声敏感、演唱经验等优势展开民间歌唱传承的研究。中国音乐学院20世纪60年代培养的第一批声乐表演学生许讲真,曾于2008年聚焦汉族民歌的润腔,从自我歌唱实践中总结出汉族民歌润腔的规律和特点,形成《汉族民歌润腔概论》,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适用于中国现代声乐的民歌教学的、关于中国传统民歌演唱技术的理论专著。声乐表演者和教育者应在声乐技术上,探索演唱技法“本土优先”和“涵纳西学”的可能,让中国声乐成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声乐的地方性表达,继而迈向中国声乐可持续和开放的未来。
音乐学学者常站在传统音乐的学科领地看待中国现代声乐尤其是民族声乐。现代声乐表演学科虽应该扎根于传统,但其着眼于未来和世界的现代声乐,却有与传统人声艺术不同的文化生态和文化表达。1964年马可在《中国音乐学院建院设想》谈到的“反对盲目崇拜西洋,也反对国粹主义”目前仍有现实意义(22)马可:《关于中国音乐学院的设想》(内部资料),1964年。。学者们一方面将研究的部分目光从“田野”转向现代声乐表演理论,总结近百年来声乐表演的经验,梳理声乐理论流派,打破表演与理论领域的学术隔阂,创建表演、创作与研究为一体的学术团体,形成学科间良性互动,协同创新。音乐学家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记录中国传统人声艺术的语境和演唱方法,以音乐学研究成果影响声乐教学的观念,并有效地转化为声乐教学内容。从20世纪50年代自上而下的收集整理民歌运动、20世纪70年代起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直至2013年上海音乐学院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着手建设的“中国民间歌唱方法数据库”,中国实际已经形成了音乐学学者收集研究民歌、音乐创作者改编民歌、声乐表演者演唱民歌的集体行动。遗憾的是,音乐理论研究和收集的民歌成果对现实的声乐教学的影响甚微,如各类《集成》从未进入声乐教学作品、对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中国声乐的未来建构提供启发。近些年来,音乐学者越来越意识到民间演唱技法在中国声乐教学中的缺失,2018年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与云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传统暨民族民间歌唱方法研讨会”,提供了音乐学理论与声乐表演跨学科交流的平台。笔者2015年曾在中国音乐学院开设《多族群多元演唱方法赏析》,2019年中国音乐学院建立由张天彤担任指导教师的“新山歌社”,萧梅2020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设的《多元文化中的歌唱方法与表演专题研究》课程,均有在高校激活传统人声演唱方法、促进中国声乐可持续发展、让声乐表演者成为传统人声技法真正传承者的考量。
将民歌和其他传统音乐类型素材用于歌曲改编和创作曾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间内音乐民族化的实践内容。当代作曲家更是将民歌旋律以外的元素,如因演唱技法不同而形成的音色和润腔作为作曲家声乐作品创作的素材,以人声意象建构作品风格、塑造音乐形象。如2020年上演的《敦煌慈悲颂》,谭盾将古乐器和不同声部、音色各异的人声吟唱结合,串起六个主题,其中第五个主题《心经》则是以男低音、呼麦、奚琴、女高音的人声交织塑造“咒经”的东方意象和敦煌画面。2020年7月29日上海夏季音乐节“谭盾敦煌慈悲颂”音乐会上,沈洋一人用男低音和“呼麦”两种唱法演绎《心经》主题,可谓是中国现代声乐主动学习中国传统人声艺术,扩展音乐表现力,完成作曲家创作意图的成功尝试。
结 语
传统民歌未来依然会是学院声乐教育考量的重要内容,而声乐风格的确立、音乐符号和内容的历史承续,取决于对待传统的态度和新人声艺术形式的创新。“每个人都在情感上诉诸于历史,而在理智上诉诸于价值”(23)列文森:《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心灵》,转引自季剑青《超越汉学:列文森为何关注中国》,《读书》,2019年,第12期,第16页。,中国声乐探索者应重新审视自己与传统的关系、建立与传统人声技术的历史关联,缓解历史与价值之间的紧张冲突。目前中国现代声乐已在呼吸、共鸣等方面突破发声技巧瓶颈,逐渐走向确立鲜明的人声艺术风格特征、强调文化主体性的学科阶段。演唱方法作为中国声乐演唱风格标定的重要方面,应明晰向传统演唱方法学习什么?教学和研究中具体措施是什么?并突破呼吸、咬字、共鸣等以西方声乐为中心的形式化探讨,开辟一条从传统人声演唱技术探索中国声乐的路径。
中国声乐承担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之责,如明确写入声乐教育的教学目标,对于声乐教育的民歌传承的讨论或许更顺理成章。目前中国高等音乐院校的声乐表演专业虽并未将传承作为教学目的,但中国声乐教育或多或少地进行着传统民歌的传承。从艺术传授形式上看,传统传承和专业教育传承都采用一对一形式,中国现代声乐教学从观念上仍带有“师傅带徒弟”传统音乐师承文化的痕迹,但制度性传承和自然传承之间仍为民歌的教育传承留下诸多讨论的空间。处理好高校传承的边界和传统创新的底线,被民歌滋养的现代声乐教学才能作为一种文化反哺,民歌的多元传播途径和传承的中介力量,亦可成为本地区本族群的民歌母语传承、现代社会当代传承的内驱力。2020年10月,教育部官网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852号建议的答复》(34)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jkw/202009/t20200921_489387.html中谈道:支持鼓励各地各校聘请非遗传承人担任学校兼职美育教师,畅通非遗传承人担任学校美育兼职教师的通道。如非遗的教育传承作为基本政策贯彻,民歌和其他传统人声艺术教育传承也将常态化,这既是扩大非遗受众群体,又是政府利用高校平台优势建设学校、传承人、传承机构为一体的教育传承新举措。但专业艺术院校是否能转变观念将传统人声艺术与已有的演唱专业结合,且以什么方式结合仍是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中国传统民歌未来将参与中国声乐的建构,高校作为传授合法知识的现代场域,应利用现代教育新空间的规范有序,高效传承传统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