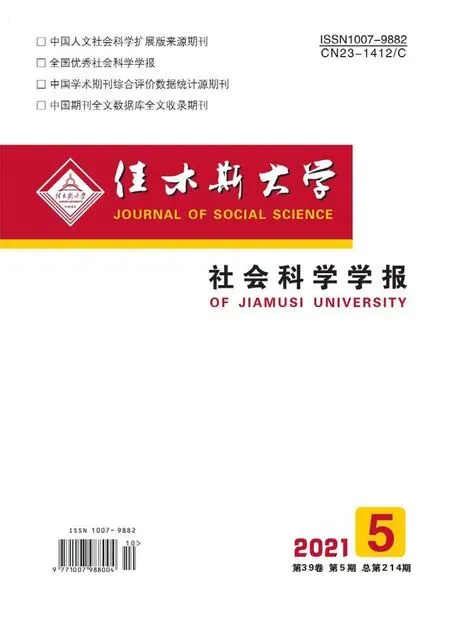教室空间下高校学生的规训教育研究 *——基于福柯微观权力理论
韩 琪,薛天飞,唐义武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米歇尔·福柯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他的大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从而激烈地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其中,福柯以反抗常识的姿态出版了被他视作“我的第一部著作”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由解放性启蒙话语所遮蔽的规训程序,揭示了隐藏在科学心脏地带的基本权力问题[1]332,创造性地建构了微观权力理论。
传统的权力理论通常从政治学和法权角度出发,关心权力由谁产生,重视的是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等显而易见的权力中心。福柯却稀释了权力的政治之维,指出权力的隐蔽性和生产性,思考的重心移至权力如何运作的议题上,以规训和惩罚为载体,权力通过知识的传播和驯顺完成对精神和思想的统治。现代学校是规训应用的典型,教室作为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空间内涵和教育意蕴,充斥着权力关系与规训措施。在高校中,教育中的规训技术在教室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学生进入大学阶段后,个人意识增强,渴望被关注,习惯从自我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敏感、自尊、不成熟是他们的突出特征,并且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能够接触到各种文化思潮,使得大学生不再迷信权威,愿意提出自己的见解。所以在规训教育中面临的来自学生群体的反制也较为明显。
一、教室空间中规训教育的应用策略
规训是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它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也是制造知识的手段。规训权力是一种谦逊又多疑的权力,运用知识对空间和空间进行了精密的划分。虽然其中的模式和程序都十分简单,但却有巨大的侵蚀性。福柯认为规训权力的成功是因为使用了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利中特有的程序—检查的组合手段。福柯在阐释微观权力理论时指出了空间在权力运作中的意义,空间对个体具有单向生产作用。空间不再局限于地理学的意涵,而更倾向于演化成一种媒介,让统治者得以对空间进行规划,实施管控。在现代教育中,教室的空间地位不言而喻,教学活动大多在教室中进行,教室为聚集学生、教师授课提供物理空间。虽然线上教学、户外课堂逐渐兴起,但教室依然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实现知识的再生产。
(一)层级监视
福柯在英国哲学家边沁“全景敞式建筑”(全景式监狱)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全景敞式主义”的概念。这种建筑的四周是环形的,中心是一座眺望塔。眺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为许多小囚室……中心眺望塔里的监督者通过逆光效果能够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活动。[2]224敞式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可以使之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全景敞式建筑”所呈现出的“全景敞式主义”使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光线、目光的统一分配上,隐蔽地制约着每一个人。“全景敞视主义”最极端的标本是监狱,而兵营、学校、工厂等机构同样适用。
教室的空间设置反映了层级监视的权力运作方式,强化了教师作为监督者和学生作为被监督者的角色定位。讲台置于教室的前端和高阶位置,和正前方的黑板或多媒体相辅相成,发挥着集中学生注意力的作用,成为教室的“中心”。在普通的班级教室中,教师的位置高于学生所处的位置,处于高阶,代表了权力关系的上位。即便是容纳多人的阶梯教室,学生虽然在空间位置上高于教师,但教师能够环视教室全景,观察到所有学生的举动,依然是权力关系的上位。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单向路径也强化了教师在权力关系中的高阶位置。福柯否认知识可脱离权力,自我成长到真理的可能性。权力关系造就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这种权力的效应,教师正是通过借助话语实施对学生的规训权力。所以无论是小班教室还是阶梯教室都能够保障到教师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教室里,教师想要达到监控全班的目的,通常会把任务分解给班长或学习委员等班委。这样能够增加监管的层次,减轻教师的负担,形成完整的监控网络,使得监视具体化且切实可行。这样教师只需要对几个班委进行监管就能够有效地管理整个班级。另外,在教室的布置中,一些教室中安装的摄像头也体现了对学生的层级监视。无论摄像头开放或关闭都化作监视的符号,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黑板上方的文字标语,墙上张贴的名言警句或守则规范都以隐蔽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规训着学生的行为举止。
(二)规范化裁决
福柯以波莱骑士孤儿院每天早晨举行的审判会为例,提出纪律分割了法律所不染指的领域,它们规定和压制着重大惩罚制度不那么关心而抬手放过的很多行为。[2]201这里的纪律就是一种规范,规范确立后,统一和同化的功能得以实现。规范化裁决一方面是确立规范,规范的实现需要对空间和时间进行分配,时间控制体现在师生按照统一的时间表进行教学听课活动,将学生的肉体嵌入到时间控制之中。肉体是权力得以施加的载体,权力和知识发生关系离不开肉体。空间控制体现在班级授课制,学生的各门课程被安排在固定的教室中。
规范化裁决另一方面是通过明确的奖惩手段使得作用对象的显性行为和潜在心理都被规范化。“规范化裁决是一种具有双向赏罚的规训手段,它的判断依据是个体的行为举止是否违反行为准则的规范化要求”[3]。一般情况下,每位教师心中都有一套自己的规范化标准。这套标准部分来源于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教学纪律,其他来自于自身的教学经历和执教经验。针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范化裁决,学生的行为不符合规范的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从而矫正学生的行为,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规训惩罚具有缩小差距的功能,因此它实质上是矫正性的。”[2]203但这种惩罚措施非暴力、不激进,例如高校学生在上课时容易窃窃私语,有的教师会让说话的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该同学通常回答不出问题又被全班同学关注,学生在凝视下容易产生不安和局促的情绪,以此达到警醒学生的目的。有的教师会用沉默待之,暂停授课,直到学生意识到不对劲并停止讲话,课堂氛围再次恢复安静。有的教师会直接提高音量,命令班上的学生不要再说话。这些惩罚措施都是温和的、渐进的强制,让学生能够接受并逐渐顺从。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还会通过奖励措施引导学生自发地符合规范化标准。例如高校课堂上学生普遍不主动回答问题,教师会通过给主动回答问题的学生在平时成绩上加分来鼓励学生积极回答问题,与教师形成正向互动。
(三)检查
检查是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在一起,是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规训有自己的仪式,那就是检查,它也是规训程序的核心。在这种仪式中,受检查者作为“客体对象”被权力凝视观看。在传统权力观中,权力是可见、可展示之物,受统治的人置于阴影之中。而在微观权力中,被规训的对象是必须可见的,能够被随时或是经常看见,这种可见的状态转换成权力的行使,这也和层级监视相呼应。
在教室中要使学生实现客体化,称为一个可以分析的对象就需要“书写权力”的介入,也就是对学生进行书写、记录、建立档案等。在教室空间中主要体现为点名、提问和考试。由于高校上课时的座位是不固定的,存在一位教师同时给几个班授课的情况。因此很难掌握每位学生的行踪。教师会采用点名的方式。点名的形式多样,有直接用学生花名册点名,还有软件打卡,手势签到,位置签到等。点名纳入到学生的平时成绩之中,有的教师通过软件实现每节课都能记录学生的考勤的功能,有的教师则是无规律得隔一段时间点一次名,无论哪一种方式,缺席需要履行请教手续,点名规范了出勤纪律。大部分学生都不敢随意逃课。提问是教师活跃课堂氛围,增强师生互动性的常用方式,也是变相考察学生出勤,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常用手段。考试是高校教育中最典型的检查仪式,考试活动通常在教室空间中进行,标志着一门课程的结束。“考试自始至终伴随着教学活动。他越来越不是学生之间的较量,而是每个人与全体的比较。这就有可能进行度量和判断。”[2]210度量和判断正是“书写权力”介入的体现,考试是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通过统一标准度量学生学习情况,学生的成绩档案被保留、被描述、被观察,学生成为福柯口中的“完整的知识领域”,在检查中被迫客体化。检查机制把知识形成类型与权力行使方式联系在一起,检查利用知识将权力行使隐蔽化和正当化。
二、高校学生对于规训教育的挑战和对抗
福柯揭示了现代社会织下的让人无可遁逃的权力罗网,深刻剖析了权力对思想与肉体的规训。他把权力与知识勾连在一起,认为没有处在权力关系之外的知识或真理,但他本人对于权力的分析恰恰是为了唤起人们心中的自我关切,激发个体的反抗意识。正如他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最后写到“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2]354而在《性经验史》中,福柯也谈到虽然反抗是在权力策略范围内,但是并不意味反抗就注定失败,而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4]62在教室空间下,高校学生的反抗行为也同样存在。
(一)显性反抗
在教室空间下,教师为了在权力关系中占据主导,使学生服从管理,往往会采取惩治典型的方法。在课上对不良行为学生进行公开批评教育,有少部分个体意识强烈的学生会觉得在全班同学面前丢脸,或者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自尊心受挫遂通过激烈的言语进行反抗,言语顶撞教师。严重时甚至会发生激烈争执,辱骂攻击教师,踢打桌椅,夺门而出等行为。这种激烈的冲撞行为可归类为显性反抗。
(二)隐性反抗
1.逃离监视空间
全景敞式机制需要监视者和被监视者同时在场,当被监视者在空间中缺位,监视行为就无法顺利完成。由于在高校中,授课教师与学生联系不紧密,课完即走,尤其是大班授课下难以摸清人数,所以有的学生会旷课或者雇其他学生替课答到。还有的会让室友一人冒充多人答到。另外,也会发生点名后学生从教室中溜走的情况。出于对学校规章制度的忌惮,只有极个别学生会冒着被劝退的风险频繁旷课,多数学生还是偶尔缺勤,找别人替自己答到,迟到早退这种比较温和的隐性反抗。
2.外观形象个性化
权力力量通过行使制度化、规训化的技术管理和知识话语,采取诱使、激发的方式使个体自愿接受引导,成为被标准化和规格化的客观对象。学生通过个性化的形象管理对规范化发起挑战,例如穿睡衣、汉服、拖鞋等奇装异服进入教室,化浓妆,带夸张头饰耳饰,头发染成紫、蓝、红等鲜艳发色等。与公开挑战权威不同,反抗者弱化学生形象,放大性别特征,以个性化形象管理的隐蔽方式对抗学校的主流规范秩序。
3.对抗式解码
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对知识进行编码,赋予其语境意义,学生作为知识的接收者进行解码。在解码的过程中,有的学生会对教师赋予的编码意义表示认同,但是有的学生则会进行对抗式解码,刻意曲解教师意图,漠视教师,弱化书写。往往教师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而学生则低头玩手机,打瞌睡,走神等,在教师与自己眼神交汇时迅速避开,身体无法离场就选择漠视。而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以没听清楚作业要求为由少写漏写甚至不写,或是在写的过程中直接抄袭。上述这些简略的书记行为使得教师不能准确度量和判断学习反馈,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书写权力。
4. 群体起哄
青年期的高校学生正处于自我同一性的确立阶段,也是自我意识的确立,发展阶段,他们会考虑到自己的学生身份需要遵守的课堂准则,另一方面也想体验违反教室常规行为,抵御教师主导权力。但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他们并不愿因为激烈反抗被惩罚,于是选择一种温和安全又经济便捷的方式,那就是起哄。起哄这种群体行为既能满足学生表现自我、发泄情绪的需要,又能够借助群体力量逃避处罚。高校教师对于起哄行为多是坐视不理或教育引导,极少会对群体做出惩罚与处置,起哄使得个体的不当行为被群体保护,一定程度上反制教师规训权力。
三、对规训教育的思考
在福柯看来,规训通过施加于人们肉体的精确压力使他们变得驯顺和有用,且规训比暴力的惩罚更有效也更经济。因此在理解规训时,人们往往看到的是规训带来的强制统一和对个体个性的泯灭。在对规训教育进行价值辨析时,大部分学者们对此持批判态度,认为规训与教育理想背道而驰,带来师生关系的紧张,无法促进学生内有精神的健康成长。
如果仅仅将规训视作操控学生肉体和精神的技术手段,规训无疑是异化学生,维护教师绝对权威的工具,但如果摒弃功利主义 ,赋予规训过程以道德价值,那么规训教育就能成为教育实践的规范力量。在教室空间下给予大学生无约束的自由是不现实的,课堂正常秩序的形成离不开引导和强制,这就需要规训教育的出场,需要规范纪律的训练。但实施规训的目的不是强化秩序,追求安静,帮助教师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而是为了促进学生理性发展,帮助学生认识到纪律与规范的道德价值。对高校学生而言,他们尊重的不是教师的权威,而是规范的道德权威,成为一个成熟、自主,具有自控力的理性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坚持“以生为本”,从强调共性走向尊重个性,尊重学生的情感、人格和个性差异,规训行为应是对学生的发展起积极作用而不是扼杀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