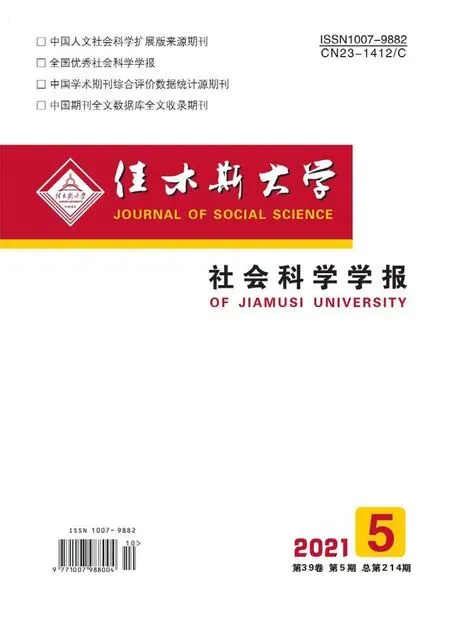创伤记忆的书写与超越 *——论双雪涛的“东北”叙事及转型
刘瑞林
(吕梁学院 离石师范分校,山西 吕梁 033000)
随着宏大叙事被结构与信息的碎片化,整体意义的建构与共同经验的触及已经不可避免地为私人经验的表述取代。如何突破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限,以文学触及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经验业已成为文学写作的症结所在。双雪涛对“东北”叙事建立了个人经验与地域历史的有效联系,在对故地的叙述中触及了集体的记忆与公共的经验。
一、“东北想象”的破裂与重塑
强文化群体对弱文化群体的“赋义”行为在文化共同体内部始终成为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当重工业基地在时代洪流的冲决下溃败后,“东北”也随之被剥夺了声音。一个可堪与“东方想象”相对应的“东北想象”被置于共同体之间,让三个省份在文化认同层面的粘连胜过这片广袤国土上的任何地域。双雪涛基于个人经验的文学书写正是立足于东北由盛转衰的沉寂史,浮现于他文学书写中的人与世界都布满了创伤的瘢痕。被边缘的“艳粉街”作为他文学书写中具有“原乡”意义的基地,海纳着疯癫的病者、底层的盲流、落魄的穷人以及下岗的工人,藏污纳垢却又书写着隐秘的传奇,可以称之为是建构于其个人经验之上的“民间”概念与记忆空间。从空间理论的角度切近其文学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双雪涛文学世界中的“东北”并非地理学上的概念,在他的“东北”叙事中囊括着更宏大的“阶级”的概念。
共和国史上的“工人”不仅是职业身份的标识性概念,同时也被赋予了鲜明的阶级意义。90年代的下岗潮则迅速地将工人阶级从事实意义上底层化,将他们从稳定的集体秩序中下放到混乱无序、朝不保夕的底层求存中[1]。身份的迅速变迁飞快地粉碎了他们的尊严,于是下岗的工人连同废弃的工厂化作了带有着铁锈气味的伤痕被遮蔽于主流历史之外。父辈光荣的泯灭被深刻地印刻在子辈的记忆中,沉默失业的父亲、疏离乃至离去的母亲和整日里为拮据的学费而惴惴不安的孩子,这便是双雪涛笔下“家庭”的基本结构。父辈的“失语”也造成了子辈的沉默,创伤记忆带来的精神裂变也使双雪涛的文学世界成为了展览不断梦呓的病者、支离残缺的残障者与晦涩不语的负罪者的“画廊”。《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因执着于公理与正义而不见容于社会,最终成为与父亲隔床对骂的精神病者的安德烈;《跷跷板》中被埋葬在公共娱乐设施下无名工人的尸首,以及由此蔓延的种种悬疑性的历史线索;《平原上的摩西》中背负着上代人的罪孽的庄树和李斐持枪在湖上划船相会,历史宏大的书写与个人命运的发展相互交缠,在现实的蛛丝马迹中完成了对隐秘历史的揭露。
基于双雪涛对“少年”视角,亦可称为“子辈”叙述的执着中,我们也可以瞥见其写作隐含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立场。他是以“工人的后代”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身份搭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完成自己的文学书写的,他禀赋着独特的创伤记忆、携带着特殊的文化基因与经验。从这些对正义和邪恶有着超乎寻常的执拗的人物身上,我们得以看到双雪涛对历史的回溯与反思。他不仅试图从“工人后代”的立场重新审视、叙述历史,更希望藉由对历史的重塑打破主流叙事中对故地“东北”的赋义性想象。他对于“东北”的叙述中充满了对过去的庄严相待,为沉默的“父辈”发声曾是这一代“新东北作家群”共有的话语目的,双雪涛也执着地在他的文学书写中为“父辈”的失败寻找意义。
不难发现,双雪涛对故地“东北”的叙述与对“父辈”形象的塑造具有同构性。在子辈的成长中父辈始终处于缺席或悬置的状态,抑或在对立中成为子辈成长的催化剂。在双雪涛的文学书写中“父与子”的关系却在冲突中实现了守望与和解,充满着锈味与灰尘的故事中流淌着温情的底色[2]。《聋哑时代》中的父亲潦倒一生,让童年的“我”对物质的困窘有着深刻的体认,并因对贫穷的羞耻与父亲之间日渐疏远。但成年后的我再度检索对于父亲的回忆时,却能追忆起他一生对良善的坚守、他在下棋方面的造诣等闪光的细节;《平原中的摩西》中的父亲李守廉下岗后默默吞咽了尊严殆尽的事实,却不忘帮扶困窘的朋友孙育新。当被警察蒋不凡污指为罪犯,并将女儿李斐撞到致瘫后,沉默的善人愤怒地出手将其重伤。父辈用沉默扛住了时代的闸门,让“子辈”的成长没有被历史的洪流中断。在对“父辈”的后置性反观中,“子辈”也得以获取辩证地看待上代人的洞见,在回望中逐渐实现对“父辈”的体谅与和解。迟来的和解与滞后的言说构成了失落的一代人与他们背负的沉重历史的“回声”,也将落寞的“东北”与无声的工人重新带回公众的视野,在叙述中完成了对其形象的重塑。
纵观当下评论界纷繁的读解,究竟何者在文本中扮演着“摩西”的角色似乎成为了评介者们争论的焦点,但“摩西”所在的时空——“平原”却被悬置在评论视野聚焦之外的暗处。但或许对《平原中的摩西》的命名中,正显露了双雪涛“东北”叙事的终极目的——他理想的归处正是众生平等的一片广阔的“平原”。
二、“精神原乡”的迁徙与位移
打破和重塑主流叙事中的“东北想象”让双雪涛的文学书写与“东北”这个地域同气连枝,与“东北”文化符号的勾连也使双雪涛、班宇、郑执等被冠以“新东北作家群”的名号,在文学评论家的集体推介下在文学界有了一个隆重的“亮相”。浓烈的地域色彩赋予双雪涛的文学写作以殊异的底色,为主流叙事所边缘化了的历史时空为作家敞开了广袤的想象空间。但是对往事的回忆终有被穷尽的时刻,“子辈”的成长是以与沉默的“父辈”作别为代价实现的。对“东北”的书写让双雪涛离开了东北,艳粉街里游荡的小城青年面向了北京熙熙攘攘的都市生活,新的生活经验开始与他的文学世界接壤。
双雪涛已将这种与“东北”作别的写作意向在《北方化为乌有》中着意以元小说叙事的形式暴露,作者直白袒露地暴露了小说的虚构性质,但却让读者越发清晰地明白:这个虚构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的真实历史的难言细节。看似通俗恣肆的谜案情节中回荡着对真相的执着探寻、对正义的不懈追索。刘泳和饶玲玲对故事的叙述一开始便被设置的“写小说”的背景,无时无刻地提醒着读者整个故事的虚构性。但随着刘泳对故事的叙述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完整,读者却愈加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感到心惊。作者有意地藉饶玲玲之口挑破读者的疑惑,并对其予以了深富意味的回应:“她说,你这个故事里面有多少东西是真实的?他说,你这是外行话,永远不要问作家这样的问题。”[3]但随着故事的另一叙述者米粒的登场,两个故事之间的交汇则更令读者心惊,随着刘泳的叙述中缺失的细节被米粒的叙述补充完整,两个残缺的故事如同拼图般严丝合缝地咬合,读者在隐约中已经能够从虚构之河中打捞、拼凑出现实的真相。
但故事却在此刻戛然而止。文本中提及的谜悬案看似在抽丝剥茧地通过叙述不断拆解,然而作者选取的叙述人:善于虚构故事的小说作家刘泳、不请自来又不知所终的女孩米粒却时刻警戒着读者叙事的不可靠性。最终,发生在多年以前北方工厂的一桩凶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在读者心中投射下亦真亦幻的疑影。文本叙述的终极指向绝非悬案的真相,其“元小说”的性质已然暴露了“叙述”本身才是故事的主角。正如《北方化为乌有》中不知来处但又倏忽而逝的女孩所言:“工厂完了,不但是工人完了……最主要的是,北方没有了,你明白吧,北方瓦解了。”[4]往事和故地已经一同化为乌有,于是失落的正义不必被伸张、未知的真相不需被探寻,因为全部的意义已经被时间瓦解了。
这种向“北方”作别的情绪与转型的可能也在其结集《猎人》中得到预示。双雪涛有意从叙事的技巧层面结构故事,尽其所能地运用虚构、想象与拼接等多种叙述的元素,使之脱离现实的绑缚,获得虚构的力量,显示了其笔锋驾驭能力的日渐成熟。“东北”、工人及工厂作为其文学基地具备的独特意义与标识作用正在有意识地被淡化,乃至被疏远。或许这正是双雪涛对于文学的严肃态度及野心的初步显露,“东北”作为故地或可以成为其步入文学书写的因由,却不能遏制作家向新的经验投射观照的目光。也许对于文学写作者来说,文学写作本身并非是从文学生产的意义上被理解的。书写是被治愈的经过,也是被遗忘的过程。当回忆中的“东北”已经在想象的世界里被穷尽、失落的历史与正义已经在虚构中被寻回,随之而来的转型也将不可避免。
但是“北方化为乌有”并不意味着“东北”在双雪涛的文学书写中从此销声匿迹。值得注意的是,在双雪涛的“东北”叙事中,以铁西区为缩影的东北工业兴衰史、下岗工人组成的失业潮以及地域犯罪率在特殊时段下的攀升等等,这些为现实主义青睐的题材却并未予以写实性的再现。城市的膨胀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故地,双雪涛也并未在文学书写中刻意地还原其中的细节。他带有先锋性的叙述让冒着浓烟的烟囱、轰鸣的机械与冷硬的工厂等工业物象成为其所建构的文学空间中布景的道具,读者却能无时无刻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双雪涛以“东北”为基地的成长叙事中,成为成长主体的不仅是生长于中的人,还有成为背景的城。城市不再成为与乡村互为镜像的静态空间,抑或是静止的文化符号。双雪涛以“铁西区—沈阳—东北”为命名的城市代表的不是一种与乡村相对的文明方式,它有着创伤的前身,承载着现实的残酷,有些自己的成长曲线。于其中,我们或许能够瞥见新的城市经验与书写方式的生成。
三、“共有情感”的探寻与超越
及至当下,我们已经不得不承认乡土文学与都市写作的同质化,让对新的文学经验的矿藏的找寻变得分外迫切。如何寻到与当下同质化的文学书写迥异的文学资源,将其与历史接壤并赋予其共性的意义已经成为困扰着文学书写者的常态性命题。双雪涛等以“东北”为叙事基地的文学书写则以一片沉寂已久的土地为基点,呈现了带着历史创痕的一个特殊集群,以寓言性的叙事抽丝剥茧、以悬疑故事的形式叙说密语、以多元题材复现历史的不同侧面。他的文学书写因呈现独特的经验备受瞩目,改写着以主流媒体为渠道对东北的想象性叙述。
对地域经验的呈现与对历史的叙述自然使双雪涛得到瞩目,但真正赋予其文学创作意义的却不仅是对“东北”的书写。地理意义上的“东北”经由审美的转化,变成独具意义的文化空间与历史符号。在这其间,我们能够意识到其中蕴藏着的、某些能够触及人性的“共有情感”,并在对该审美对象的审美过程中完成对于历史的回溯。可以说正是对历史与“共有情感”的触及,使在经济学与政治学层面全面落败的“东北”得以与“大上海”“老北京”等现代都市并置于同一视域中,获取文化学意义上的“筹码”。双雪涛的“东北”及其辐射的共和国的工业史,一定程度上接续了草明、李铁与雷加的工业文学传统。虽然双雪涛对工业史、工人形象及工人生活的描绘是非正面的,但却在无形中拓展了工业文学创作的空间,将之从工厂及工人的生活场景的描述中释放,为工业文学的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
不难看出,双雪涛对“东北”的书写中带有着显著的自叙传色彩,他正是在对成长记忆的重叙中逐渐搭建起了“艳粉街”“工厂”“逼仄的出租房”等文学空间。其中,盘桓着浓厚的“孤独感”的成长叙事唤起了受众共同的情感体验,唤起了集体对共有历史的回忆与反思。与张悦然、甫跃辉、蔡东、霍艳等“80后”作家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去形塑表面光鲜、内里支离的青年“失败者”群像不同,双雪涛等“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在“东北”这一独特的文学空间中,塑造的是负有“下岗工人”身份的中年“失败者”群像:他们惯于在安稳的集体秩序中生存,却不得不流失在街头靠出卖苦力、靠流动的小摊讨生活;他们拥挤在逼仄的物舍,与他们蔑视的地痞、流氓和扒手为邻;他们的妻子因贫穷而舍弃家庭远走,他们的儿女因物质的贫瘠而过早地感受了生活的沉重。他们是在生活的洪流中“失重”的群体。
倘使双雪涛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边缘的“失败者”予以垂青与同情,其文学书写的质地也将泯然于众。但他的“东北”叙事并未以悲悯感伤的追忆撷取浅白的情感质素,而是藉由对故地的叙述申明那片土地即使被遮蔽、却依旧声名显赫的历史,并试图于故地与父辈身上承袭一脉相传的精神力量。这片土地与故人尽管被冠以“失败者”的名号,但是他们的身上也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如《大师》中下岗后沦为仓库保管员的父亲因失业而失婚,潦倒与酗酒摧毁了父亲的健康与尊严。但父亲在棋艺上却造诣颇深,在纵横博弈间昔日的意气风发在父亲身上重新降临,也深深地印刻在儿子的眼中;《平原上的摩西》中,当陈列在沈阳红旗广场上的伟人雕像要被拆除时,沉默的工人群起走上街头抗议。在群起抗议的工人集群中,既有已经成为出租车司机的李守廉,也有已经成为工厂老板庄德增。尽管老工业体系业已溃败,往昔的身份业已丧失,新的身份与阶层正在不可避免地在昔日的集体中划分新的沟壑,但是对“集体”的记忆却使他们在特殊的时刻结成一个身份上的“共名”。他们沉默庄重,共同守卫着“工人”身份不堕的尊严。
双雪涛试图在回溯中把握的正是这样的“高光时刻”,他试图将个人与集体经验乃至国族历史之间建立联系,并从中获得历史的纵深。在这其中或许有某些可以称之为“共性”的东西,能够被转化为抵抗平庸、拒绝遗忘的精神力量,使在都市中漂泊的人类在精神上有所依傍。他的艳粉街中浓缩着沈阳这座城市的神韵,他对工厂与工人的叙说描摹着所有北方城市的剪影,使他的“东北”成为一个层次丰厚的文学的地理空间。同时在他的“东北”叙事中我们能够隐隐地感受到“祛魅”的力量。不仅是被主流叙事塑造了的“东北”逐渐在叙述中向读者敞开,抖落了“想象”的外衣,以新的面目为读者所认识,同时双雪涛也在其间完成了对历史的“祛魅”。当破败的工厂、废弃的车间与工人大院的残垣以群像的形态成为“东北”的布景,一段被遮蔽、被悬置的历史也逐渐暴露了真身。这不仅是东北地域的集体记忆,也是我们国族共有的历史经验,以“东北”叙事介入历史赋予了双雪涛的书写以超越性的意义,更为当下的城市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书写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