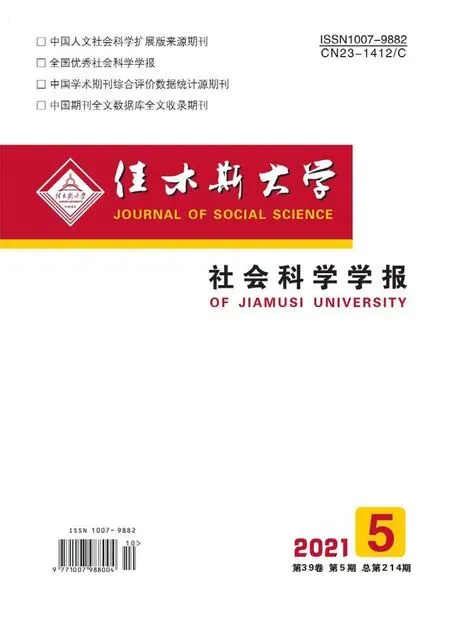清代评点派对王熙凤形象接受倾向初探 *
张彦芸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与管理学院,安徽 宣城 242000)
一、引言
清代《红楼梦》的评点起于脂砚斋,终于王伯沆。本文的研究范围为除脂评外的清代其他评点派对王熙凤形象的接受。《红楼梦》的评点本很多,笔者只选取其中流传广泛并且最具代表性的王希廉、姚燮、张新之三家的评本以及有一定艺术水准并较有特色的几家评本,即:陈其泰、哈斯宝、王伯沆等人的评点。
自20世纪80年代始,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引入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并将其广泛应用于研究实践。接受美学理论的创立者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1]26。在每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历程中,如果将作品本身比作供不同时期的不同读者演奏的管弦乐谱,那么清代评点派继脂评后再次弹响了《红楼梦》这部伟大乐章。王熙凤是极富魅力的一个艺术形象,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对它进行了各个角度、各种方法的阐释和解读。清代评点家们则普遍立足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对其进行冷静客观的谴责或冲动意气的声讨。在这些谴责和声讨中,按照评点家们接受动机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社会教化型,以王希廉、张新之为代表;二是文人自娱型,以姚燮、陈其泰、哈斯宝等为代表。尽管清代评点家们都是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封建文人,有着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但由于各人生活经历的不同、审美情趣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对待同一个人物形象会出现不同的接受态度。
二、社会教化型评点
(一)王希廉:冷静、理性的接受态度
王希廉在《红楼梦批序》中说:“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也;诗词歌赋,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说,其小之尤小者乎”[2]577?他又声明:“语有大小,非道有大小”[2]577,“若夫祸福自召,劝惩示儆,余于批本中已反复言之矣”[2]577。这段话说明王希廉没有把《红楼梦》仅仅看作是一部爱情小说,而是认为该书有着相当大的社会教育意义,因此他评点《红楼梦》的目的就是为了劝善惩恶,进行封建道德说教。王希廉这种社会使命感使得他的评点不是聊以自娱的审美鉴赏,而是具有社会教化意识的文学批评。
正是在这种接受动机的支配下,王希廉这位封建社会的正统文人便以封建社会正统的伦理道德观为标尺来衡量、评价凤姐这个艺术形象。他对凤姐这个艺术形象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审美的观照,而是以一个道学家的身份从头至尾对凤姐其人、其所作所为进行了一番道德批判。如第7回回批:“凤姐夫妇白昼宣淫,其不端可知”[2]591。第15回回批云:“凤姐一生舞弊作孽,不可胜言,……故就铁槛寺弄权及后文尤二姐事最恶最险者细写原委以包括诸恶孽”[2]595。第68回回批云:“此回专写王凤姐阴毒险恶,为尤二姐吞金自尽之由,凤姐大闹宁府,写得淋漓尽致,既显凤姐之泼悍,又见贾蓉之庸懦,两面俱到”[2]630。这些批语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从各个角度对凤姐进行了批判和谴责,如凤姐的淫荡、弄权、贪婪、刻毒阴险、悍妒等。最后,王希廉根据封建社会正统的才德标准对凤姐作了一个总评。在他看来,“福、寿、才、德四字,人生最难完全”[2]581,“王凤姐无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2]581。第110回回批云:“‘心实吃亏’四字是修福延寿真诀,王凤姐与此四字相反,所以无福无寿”[2]655。总之,在王希廉看来,凤姐一无是处。王希廉对凤姐这个人物的接受态度与他评点《红楼梦》的宗旨是紧密相关的。王希廉评点该书的目的是宣扬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希望有补于世道人心。因此他对凤姐的接受不是基于个人主观感情上的爱憎好恶,而是将凤姐变成了他宣教的一个反面教材,如此方能达到他通过评点此书而实现社会教化的功能。王希廉的接受态度较少掺杂个人的主观感情,因此他的评价虽然充满了道学气,但总体上说还是从文本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显得较为冷静与理性。
(二)张新之:主观、意气的接受立场
与王希廉的评点相比,张新之评点《红楼梦》的功利意识似乎更为明确和强烈。他说:“《红楼》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情,较《金瓶梅》尤造孽,以读者但知正面,不知反面也;……;闲人批评,使作者正意,书中反面,一齐涌现,夫然后闻者足戒,言者无罪,岂不大妙”[2]700?他认为《红楼梦》较《金瓶梅》尤为造孽,是因为大多数读者仍将此书当作淫书来读,没有领会该书的真正意图。因此他评注此书的目的与张竹坡评《金瓶梅》的目的相似,那就是化害为益,将其纳入社会教化的轨道。从接受动机上看,张新之与王希廉虽同出于社会教化的目的,但他们的接受视角完全不同。张新之认为该书的真正面目是“演性理之书”[2]701,是用表面上看来风花雪月的文章来阐发《大学》、《中庸》、《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的奇传。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张新之和索隐家们一样玩起了测字、占卦、猜谜的游戏,小说中生动的故事情节被他分析成宣传《周易》等儒家经典的载体,小说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了抽象的概念或某个卦名,如:在第3回凤姐出场时批云:“‘熙凤’与‘西风’音相通,肃杀之令,刑木坏荣致荣府之抄者此人,主金玉因缘而杀黛玉者此人,……”[3]210。另一批云:“开口提钱,见其为当家人,又书中总括财色之人也”[3]212。凤姐刚一出场,张新之便根据凤姐名字读音上的某种关联推断出凤姐是拆散宝黛姻缘,导致荣府被抄的罪魁祸首,并且认定凤姐便是作者借以演义“财、色”二字的载体。接下来的批语都是对这个总观点的补充与阐释。总之,张新之认为凤姐是书中最恶之人,对她的谴责十分刻薄和严厉,批语中多处痛斥她为“禽兽”、弄权致祸者”。同王希廉冷静理性的接受态度相比,张新之的接受立场更加主观和意气。
三、文人自娱型评点
王希廉和张新之为了挽救世道人心,推行社会教化而评点《红楼梦》,姚燮、陈其泰、哈斯宝、王伯沆等人则仅仅为了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批评。他们的评点没有王、张那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评点的动机都是源于对《红楼梦》的热爱,小说评点成为了他们宣泄个人情感的需要。尽管姚、陈、哈、王四人的接受动机相似,但具体到个人的期待视野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对凤姐的接受态度也呈现出各异的风貌。姚、陈、哈、王四位评点家都是宝黛爱情的歌颂者、赞美者,因此四位评点家在评价书中人物时,都以是否“拥林”来划界限,“拥林”者就肯定、赞美;反之则否定、贬斥。基于这个立场,四位评点家都对凤姐持否定的态度。
(一)姚燮:评者主观感情的强烈介入与人世之概的寄托
姚燮对凤姐的接受有两个显著特征:1.评者主观感情的强烈介入。在其对凤姐所做的批语中,经常带有“吾”“我”“余”等字眼,如第3回在凤姐初见黛玉所做的一番“表演”旁,姚的眉批云:“只一寻常寒暄语耳,其口锋之利便如此,吾畏其人矣”[3]211!第69回凤姐步步设下圈套,并借秋桐害死尤二姐。此回姚有眉批云:“咄咄可畏!吾不知此等恶妇天地间有几个也”[3]1730。尤二姐死后,凤姐继续在贾母前进谗言,姚夹批云:“人已死而毒念犹未尽,吾愿生生世世弗遇此等人”[3]1736。这些评点充分流露了批者的爱憎好恶,带有鲜明的个人感情色彩。2.评者人世之概的寄托。姚燮在为凤姐作批语时常常联系现实生活,对社会上的阴暗面予以揭露,大发人生感慨。如第一百八十回中在巧姐被卖时,姚批:“盖作者深恶熙凤之为人,谓宜得此孽报,观世间不少王仁、贾芸一流人,特地捏出几个豺狼,令人发指”[2]698。
(二)陈其泰:“真情论”下的批判与贬斥
陈其泰批点《红楼梦》也是出于个人喜好,对书中人物爱得深、恨得切。他用正统的儒家道德标准来臧否书中的人物,对于凤姐,持贬斥态度。陈最赞赏的是“圣贤之徒”,以宝玉、黛玉为代表;最痛恨的是“乡愿”,以宝钗、袭人为代表;而凤姐则是界于这两种人之间的另一种人——邪慝。如他的第3回回批云:“王熙凤之为小人,无人而不知之;宝钗之为小人,则无一人知之者;故乡愿之可恶,更甚于邪慝也”[2]715。在陈看来,宝钗是个奸诈、虚伪的小人,让人不容易看清真面目,因此更为可恶可恨,而凤姐则是一个为所欲为、明明白白的小人。批者揭示了凤姐的淫荡、贪财、弄权是给贾府致祸的根本,“凤姐夕拥二俊,日进三竿,快活极矣;然多欲所以致病,多财所以致祸,皆于此引起”[2]723。除此之外,批者认为凤姐是拆散宝黛因缘的主谋,“吾意聘薛之言,出自凤姐”[2]755。为什么要这样做?批者推测,“凤姐盖甚利宝玉之死也,宝玉于黛玉,其生生死死之情,孰不知之;岂凤姐之明决,而反未之察耶?是策得行,而黛玉必死,黛玉死而宝玉安得生,则所以杀黛玉,而遂杀宝玉者,计孰便于此哉;……”[2]756。由于过于同情宝黛二人,因此面对破坏二人爱情的刽子手,批者严加痛斥,“因思此策,可见凤姐之为人矣;彼所拒者,癞蛤蟆耳;其他则人尽夫也”[2]755。在这里,批者由于情绪激动,对凤姐的斥责已近乎谩骂,失去了评者应有的冷静态度。陈批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宗旨,那就是“真情论”。陈认为《红楼梦》是一本写儿女真情之作,但这里的“情”绝不是世俗之人所追求的“情欲”,而是建立在人生理想与志趣之上的一种非常真诚执着的感情。因此他对宝黛的纯真爱情极为歌颂、称赞,而对凤姐这种只有淫欲没有真情之人,只能是痛加贬斥。
(三)哈斯宝:是非分明的审美立场
哈斯宝是清代诸多《红楼梦》评点家中惟一的一位少数民族评点家。哈斯宝也极力推崇宝黛之间的真情,但他认为《红楼梦》绝不仅仅描写了爱情,而是在宝黛爱情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寓意。他在《新译红楼梦读法》中说:“《红楼梦》一书的撰著,是因为忠臣义士身受仁主恩泽,唯遇奸逆挡道、谗佞夺位,上不能事主尽忠,下不能济民行义,无奈之馀写下这部书来泄恨书愤的,何以这样说?书中写出补天不成的顽石,痴情不得遂愿的黛玉,便是比喻作者自己的:我虽未能仕君,终不应像庶民一样声消迹匿,总会有知音的仁人君子,——于是有自悲自愧的顽石由仙人引至人间出世,你们虽然蒙蔽人主,使我坎坷不遇,但皇恩与我深厚,我至死矢不易志,——于是有黛玉怀着不移如一的深情死去;这一部书的真正关键就在于此……”[2]772。他在第二回回批里继续阐发这种观点:“清明灵秀之气与残忍乖僻之气相互冲突,‘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这不明明是说自己忠贞之身受奸佞小人谗害,才写下这部书么……”[2]772。哈斯宝将宝、黛、钗之间的爱情斗争阐发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忠与奸的斗争,之所以这样理解,有他自身的原因。他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得志的文人,因此,他在评批中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些评点恰恰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体验。哈斯宝从他对《红楼梦》主旨的理解出发,在评价书中的主要人物时,将他们划分为“正”与“邪”、忠”与“奸”两大对立的阵营。宝黛二人和支持同情宝黛爱情的属于“正”的一方,是忠臣义子;而阻挠破坏宝黛爱情的,如宝钗、贾母、凤姐之流则为“邪”,是奸臣逆贼。哈斯宝认为凤姐是破坏宝黛爱情的奸人之一、贾母的帮凶。批语中多处揭示凤姐的奸诈,如第24回回批云:“由司棋箱中搜出字帖儿,言表姊表弟,这是暗攻宝钗;凤姐看了,不但不怒反而心喜,这是她奸狡素性”[2]803。与其他几位评点家相比,哈斯宝在进行人物评价时旗帜鲜明地把主要人物分为两大阵营:正与邪,忠与奸,忠则赞之,奸则贬之。这种是非分明的审美方式正体现了这位蒙古族文人独特的期待视野。哈斯宝虽然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他还是一位生活在塞外的蒙古人,蒙古族的文化传统自然也会影响到这位评点家的审美心理。在蒙古族文化传统中,一直贯穿有“终极审美意识”,大则极大,小则极小,善则至善,恶则至恶。这种两极化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哈所接受的汉族儒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忠则赞之,奸则斥之的是非分明的审美观念。因此哈斯宝在评点人物时将“忠”和“奸”作为道德评判的主要标准,这也使他的评点别具特色。
(四)王伯沆:正统儒家人格立场下的道德评判
王伯沆是清代《红楼梦》评点的终结者。在清代诸多评点家中,王虽然是生活的年代最近的一位,但王评点《红楼梦》依然是立足正统的儒家人格立场,对凤姐进行道德评判。王评点的动机也是出于对《红楼梦》的喜爱,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同情。因此他评价书中人物时同样界限分明,即对同情宝黛爱情的充分肯定,对破坏宝黛爱情的猛烈抨击。基于这个前提,王对凤姐的批语时时指责、处处贬斥,言辞激烈时近乎谩骂。在他看来,凤姐与宝钗“奸险相同”,并依仗着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的宠爱而为所欲为,干尽坏事。王指责凤姐贪财,有这样一段批语:“《左传》云: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观此文偶忆及之,他日凤姐竟可用此二字作谥”[4]474。王用“饕餮”二字揭示了凤姐对财的贪欲已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对凤姐害死尤二姐的情节,王更是作了详细的分析与批点,他把凤姐的计谋归纳为“一套十全主意”,通过对整个过程的详细剖析,充分揭示了凤姐的奸诈与阴毒。如果说这些评价基本是王根据客观的分析得出的结论,那么他的另外一些批语则完全是从个人感情的好恶出发,对凤姐破口大骂。他还站在封建社会男权立场的角度,对凤姐的某些泼醋行为大为反感,批云:“全是泥腿泼悍态”[4]747。总而言之,在王看来,凤姐就是一个“极不爱脸人,……无耻矣”[4]742!王对凤姐的评价充斥了太多的主观感情色彩,以致于也丧失了对艺术形象审美时应有的客观与理性。
四、结语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接受首先取决于读者的期待视野。所谓的“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的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清代诸评点家对凤姐形象的接受倾向也取决于他们本人特有的期待视野,从而表现出各异的接受动机和接受视角。文中提及的六位评点家或以推行社会教化为己任,或仗着热爱《红楼梦》的一腔激情,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红楼梦》进行认真、细致的批点。这些批语中既有理性的阐释,也有感性的鉴赏,甚至于批语的字里行间,我们可窥见批者的爱憎好恶,可听见批者的嬉笑怒骂。他们对凤姐的评价尽管见仁见智,各有侧重,但基本上都是拘囿于封建社会的道德范畴,以儒家正统的人格标准作参照系对凤姐作出道德批判。清代评点家们之所以用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对凤姐作出如此种种的道德批判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的。清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其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需要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垄断和专制。为此,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再次成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形之下,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容易受这种时代主潮的浸染,再加上传统的儒家道德标准和封建伦理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他们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在评价凤姐这个形象时自然也越不过这个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