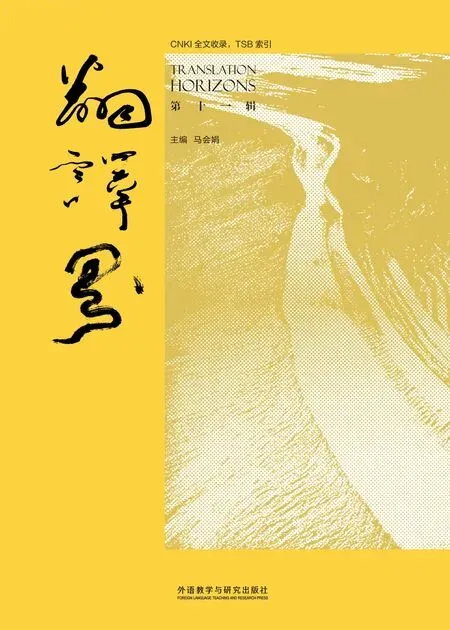福楼拜在中国的百年译介
牛晓帆
湘潭大学
1 引言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是19 世纪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被19 世纪自然主义流派和20 世纪法国“新小说”派奉为思想先驱。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萨朗波》(Salammbô)、《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圣安东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短篇小说集《三故事》(Trois contes)以及在其辞世后出版的《布瓦尔和佩库歇》(Bouvard et Pécuchet)。此外,巴黎的路易哥纳尔出版社(Louis Conard)还曾出版过关于他的《青少年作品集》(Œuvres de jeunesse)和一些零散游记。这些作品从总体上构成福楼拜毕生创作的文学拼图。
福楼拜曾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表示:“我想着印度,想着中国,想着我的东方故事(我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几个片段)……我需要写一部宏伟壮丽的史诗”(Flaubert,1889:293)。与19 世纪的很多作家一样,他对古老的东方和神秘的中国心驰神往。虽然他终未实现前往中国旅行的夙愿,但其作品《坦白》(Un cœur simple)的最初译本在1922年携载着他的期许抵达了中国,成为福楼拜作品在中国漫长译介历程的开端。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福楼拜及其作品的研究热度始终居高不下,不少研究成果从文本分析、创作思想、写作技巧等层面入手,广泛探讨其作品中的人物、情节、主题、修辞、艺术手法等具体内容,并且相对集中于对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的多维研读。对于福楼拜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百年译介状况,至今仍未出现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与阐发,故而本文运用述评结合、量化分析等研究方法,围绕福楼拜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程、译者群体和出版状况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较为全面、深入、细致地呈现福楼拜在中国的百年译介历程,并解析不同时期的译介特点及其成因。
2 道阻且长的译介历程
文化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不同类型的文化是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要素的缩影。外国文学在我国不同时期的译介史也是反映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史的重要因子;换言之,外国文学的译介历程与我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基本上同步展开。具体而言,从清末民初至今,我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政治上,中国逐渐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民主共和,并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上,从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的“双百方针”到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事件促成人们普遍的思想解放,政治经济形态及意识形态的嬗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和阅读趣味。
民国初期的中国处在风起云涌、万象更新的时代节点上,当时的文学界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程光炜等,2011:39)是彼时文学革命的目标和方向。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在刊载于创刊号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陈独秀率先提及福楼拜的名字,将其作为自然主义作家介绍到了中国(熊辉,2016:12)。
到了二三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进入一段黄金时期,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文艺社团相继创立,各种文艺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现实主义(当时学界普遍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不做区分)文学成为引入并译介的主要对象,这为福楼拜作品的大量译介提供了契机。笔者于2019年11 月以Flaubert、福楼拜、佛罗贝尔、佛罗伯、圣安东的诱惑为关键词,在《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和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在1920—1937年,约有12 个(再版数不计)新译本先后出版:1922年,沈泽民翻译的《坦白》连载于《小说月报》第13 卷第1 期至第3 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李劼人翻译的《马丹波娃利》由中华印书局出版,他在1936年重译了这部作品并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作品的另一个译本,即李青崖翻译的《波华荔夫人传》;同年,北新书局出版了法国短篇小说(第一册),其中收录了刘半农翻译的《游地狱记》(Rêve d’enfer);1929年郎芳翻译的《淳朴的心》由现代书局出版;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劼人翻译的《萨朗波》;1932—1934年间,林文铮翻译的《圣安端之诱惑》连载于杂志《亚波罗》第10 期至第13 期;1935年,李健吾节译了《圣安东的诱惑》,定名为《科学与信仰》,刊登在《社会周报》第3 卷第1 期;1936年,启明书局出版了钱公侠翻译的《圣安东尼之诱惑》;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福楼拜短篇小说集》;1937年1 月,生活书店出版了李健吾翻译的《圣安东的诱惑》。倘若将再版次数计入在内,这一时期共有17 个译本相继面世。
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事业缺乏和平有利的发展环境。福楼拜作品的译介与传播明显地受到了该时期历史语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译介数量的不断减少,仅《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三故事》三部作品有新的译本出现,同时,福楼拜的书信被少量选译登载于报纸杂志上。其次,译者人数锐减且出版地相对集中。据统计数据显示,该时期公开发表福楼拜译作的译者只有李劼人和李健吾。这是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像李劼人那样能在动荡不安中凝神聚力完成新译作的实属罕见;而李健吾在此时选择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此时的上海得益于租界身份的庇护,成了一座“文化孤岛”,相较于其他沦陷区,上海的译介出版活动在困境中仍坚持向前,对此,我国的翻译史学界已形成共识:“抗战时期的‘孤岛’译界,虽不如战前和20年代那么景气,但处于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的上海‘租界’地,文学翻译还是成绩斐然的。就翻译数量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仅4年零1 个月的时间里,翻译了近百部外国文学作品”(孟昭毅、李载道,2005:215)。这一时期,福楼拜作品的译本都在上海的出版机构发行,并且半数作品出版于“孤岛”时期,特别是刊登其译作的《戏剧与文学》和《西洋文学》两本杂志均创刊于这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后者更是战时屈指可数的纯文学翻译杂志。可见,福楼拜的作品在文艺活动受限的战乱时期依然受到我国文学界的青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出版机构被整合,翻译管理工作得以加强,“对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这些有影响的大出版机构,则规定其出版范围,这些出版机构在5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再出版翻译文学作品了。翻译文学作品主要归新建立的国营出版机构出版”(查明建、谢天振,2007:561)。这意味着与二三十年代译者和出版社能够自主选择翻译文本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文化机构成为域外文本择取方面的决策者。毋庸置疑,这一时期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翻译成就,但由于“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同上:561)的原则基本操控了翻译活动的全过程,苏联文学成为译介的重中之重,而西方的文学作品甚至一些经典作品则被边缘化,福楼拜的作品也无可避免地被打入“冷宫”。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17年间发行的6 个译本都是此前译本的重印,几乎没有新译作出现。
“文革”期间,福楼拜作品的译介出现了“断崖”式的空白,十年间没有一本译作出版,这与当时特殊的现实状况息息相关。如果说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文学翻译因严格的意识形态管控而日渐式微,那么到了“文革”时期,文学翻译则陷入了清末以来大规模外国文学译介的最低潮(马士奎,2003:65)。在二三十年代颇受译界推崇的欧洲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被拉下神坛并受到严厉的价值审判。1979年,李健吾翻译的《包法利夫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这标志着新时期福楼拜在中国译介的新起点。
新时期以来,翻译活动逐渐回归到重视翻译对象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等范畴,文本的内在属性重新成为重要的评判指标。因此,翻译文本变得更加多元,题材更加广泛,译者队伍更加壮大,这使得福楼拜作品迎来第二个译介高潮。据统计,新时期以来共计60 余部出自不同译者的新译本出版,若算上再版次数,译作数量高达190 部左右,相当于此前译本总数的10 倍。从80年代末起,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译本问世,90年代更有20 余部新译作出版,其中罗国林、许渊冲、周克希所译的《包法利夫人》更是作为经典译本被各大出版社再版至今。当然,其中也混有一些抄袭的译本,如蒋思宇翻译的《包法利夫人》(李景端,2002:31),该“译本”于1995年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发行。
总体而言,福楼拜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程有四个主要特征:首先,对他的翻译活动与中国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紧密相连。不难发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其作品在我国译介的黄金时期,该时期中国处于新旧文学的转型期,各种文学思潮相互激荡,茅盾提出输入西方的自然主义来发展本土文学:“把文学作为娱乐或消遣,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概念;不依赖想象和个人冲动,不企求一下子抓住事物。这是我们的传统描写方法,这是阻碍中国文学进步的两大缺陷。要想改掉它们,引进自然主义就是一剂良药”(转引自金丝燕,2001:328)。这一观点表明我国新文学早期对西方文学的高度重视,由此也可以理解福楼拜在此时作为自然主义作家被选择、被译介主要是出于中国本土文学寻求自身出路的内在需要。其次,福楼拜作品的译介状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1915年为肇始,在二三十年代进入第一个高潮期,之后维持在起伏不定的态势,“文革”时期完全空白,新时期以来在译介数量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经典作品如《包法利夫人》甚至引发复译潮,一度竟有多达137 个版本的译作。此外,在原作体裁的选择上,也由初期主要翻译其长篇小说发展到后来更加全面的通译。相较于《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等长篇小说,《狂人回忆》(Mémoires d’un fou)、《秋之韵》(Novembre)、《庸见词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等作品的译介时间较晚,在近四十年才陆续得到译者的关注。最后,在传播媒介上,早期译作主要见于《小说月报》《世界文库》《西洋文学》等专门刊登外国文学译品的报纸杂志,这些刊物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很高的文化地位;后来则更多以单行本或丛书等形式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等知名出版社还以作品集等“大部头”形式发行福楼拜作品译作,足见福楼拜在我国译界和出版界受到的重视。
3 以李健吾为代表的译者群体
对译者的关注日益成为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直接影响操纵着翻译文本的生成过程和最终效果,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例如,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提出“走向译者”(Berman,1995:73-74),主张对译者进行多维度的考察,提出一系列关于译者身份、行为和使命的话题,比如:译者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译者只从事翻译职业还是也从事着其他职业?译者本人是否也创作一些作品?译者翻译的是何种语言的文本?译者主要翻译的是何种类型的文本,其他类型的文本也有涉足吗?贝尔曼借助现代阐释学来拓展对翻译活动的思考视野,为现代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
1915年,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标志着福楼拜首次以外国重要作家的身份被介绍到中国。1922年,沈泽民译的《坦白》刊登于《小说月报》则标志着福楼拜作品在中国翻译的真正开端。此后,随着国内不同文学艺术流派对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吸收、借鉴和译介,福楼拜引发了越来越多译者的关注和兴趣。据笔者统计,迄今约有70 位译者翻译过他的作品,早期的译者群体以归国留学生为主,如李健吾、李劼人、李青崖、刘半农等;新时期以来,福楼拜作品的译者队伍不断壮大,主要由教学科研单位的学者和教师组成,如许渊冲、罗国林、周克希、王文融、郑永慧、施康强、冯寿农、席继权等。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译作的流传程度来说,李健吾对福楼拜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所做的贡献都极其显著,也备受我国学界推崇;除了《布瓦尔和佩库歇》之外,他译完了福楼拜生前公开发表的所有作品,其中多部还被尊为经典译作而多次重印。因此,以李健吾为例考察杰出译者的翻译生涯和创作实践,或可窥见众多译者在福楼拜译介中共有的历史角色和文学担当。
李健吾自幼喜爱戏剧,青年时代起就从事戏剧创作、表演和批评。192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转入西洋文学系学习法文和法国文学。1931年,他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研究福楼拜的作品,因为他认为“中国需要现实主义”,因而他在留学期间“日夜研读福楼拜”(李健吾,2009b:2)。两年后回国,他就开始撰写《福楼拜评传》并于1936年首次出版。可以说,在三四十年代,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呈现出空前高涨的局面,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却如凤毛麟角。足见这一时期的翻译者虽多,但步入“理论译场”(王友贵,2015:734)的译者却极少,李健吾便是敢于先行的杰出译家。柳鸣九对《福楼拜评传》赞誉有加,认为它“几乎可说是中国三四十年代西学领域中唯一一部国人有独创性的学术力作,至少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迄今仍无同类佳作出其右”(转引自李健吾,2007:2-3)。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健吾因腰病无法远行,只好前往上海法租界避难;上海沦陷后,他一面从事戏剧创作,一面蛰伏家中翻译福楼拜的作品,陆续把《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译成中文,还修订了此前的译作《圣安东的诱惑》与《三故事》。
王友贵指出:“相对于大多数国别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有幸来到中国的法国作家有福气。即法国文学译场还有这样一种稳定,每个优秀作家往往拥有相对固定的中译者。这种状况实乃文学翻译之最佳状态,也是法国作家之幸”(王友贵,2015:713)。在中国的福楼拜译者中,李健吾的译作数量最多,译品质量也被推为上乘,算得上是福楼拜作品的“固定译者”。在翻译方面,他继承了福楼拜的艺术观,认为“创作如若是艺术,翻译在某一意义上最后同样也是艺术”(李健吾,2009a:617)。李健吾的译风简练通达,坚信翻译中只存在一种“最简单的”“最精确的”表达能够再现原作的精神,“无论是创作或者翻译,碰到表现,只有一个真理,‘最完美的表现只有一个’”(同上:621),这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福楼拜“一语说”(钱林森,1994:33)的创作理念,即“一个事物只有一种方式能表达出来,只有一个词能将其说明,只有一个形容词能表现它的特点,只有一个动词能使它栩栩如生”(Maupassant,1962:84)。因此,李健吾认为在翻译中应当耐心寻求“最完美的”的表达方式。应该说,他超越了狭义的译者身份,成了福楼拜锲而不舍的艺术精神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将后者的创作理念内化为翻译准则,这种创作与翻译之间审美相通的特点大概是李译作品“忠实”于原作的根本原因。
李健吾既是妙笔生花的译者,又是才华出众的作家与批评家。他在戏剧、散文、批评等领域均造诣深厚,他甚至作为“创作、评论、翻译、改编、组社、导演以至亲自登台,什么都干,无不胜任”(卞之琳,2005:313)。除了福楼拜,李健吾也翻译过莫里哀、巴尔扎克、司汤达等法国作家的作品,他将莫里哀的戏剧全部译为中文,因而被尊为“莫里哀在中国的首席译者”(王友贵,2015:745)。作为批评家,其批评作品除了被誉为紧密结合了“诗人的激情与学者的冷静”(郭宏安,2016)的《福楼拜评传》之外,还有数量可观的评论性文章,深刻剖析了福楼拜现实主义风格参与其文学批评格局建构的动态进程。在评论穗青的作品《脱缰的马》时,李健吾引用了福楼拜对“艺术的客观观察”(李健吾,2005:174)的观点,认为现实主义的观察不同于科学观察,描写须出于艺术上的需要,“现实主义的观察不是一架照相机,一下子平平地摄入所有的现象。这是一个领路人,一步步把我们带到他所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同上:175),一切现实主义的描写须为主旨服务,因为“主观肇其始”(同上:175)。此外,李健吾还从事戏剧、小说与散文创作,其作品多被收入赵家璧等人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里。曾有研究者做过统计,李健吾一生出版著作至少有85 种,“如此高产,且成就显著,在整个新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张元珂,2015)。
综上所述,以李健吾为代表的众多译者对福楼拜作品在我国的百年传播和接受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无论是翻译家个体的文学理念、创作思想或翻译认知,甚至是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接受的教育和情感经历,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文学翻译活动的生成和流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楼拜作品在中国的百年译介史,其实既是我国译者和读者对福楼拜作品的接受与重塑的历史,也是我国文学界对福楼拜创作思想进行体系化重构的历史。
4 中译本的百年出版简况
在我国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传播与接受研究中,中译本的出版状况是一个结合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的独特研究视角。这一研究思路也许可以挖掘出作家和译者研究、历时性译介进程研究等范畴难以涉及的研究要素,从而较完整地呈现外国文学译介研究的全貌。
截至2019年,福楼拜作品在我国约有80 个不同的译本,出版和再版次数多达190 余次。在百余年的出版历程中,福楼拜可以说是我国出版商最为青睐的法国作家之一,对这一出版简况加以考察可从时间线索和空间地域上呈现出福楼拜在我国的出版历史、传播轨迹和形成机制。
首先,从出版物的类别来看,早期的译作多见于报纸杂志,各个译者的翻译活动大多各自为政,具有很大的分散性。20 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对通俗小说的浓厚兴趣以及新文学刊物的增多为福楼拜的作品进入我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据统计,1905年新创刊的文学刊物数量只有1 种,而1906年至1908年间,每年新创办的文学刊物数均在10 种以上(邓集田,2012:87)。在此背景下,报纸杂志成为民国时期福楼拜作品汉译本发表的重要媒介,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的25 部译作中就有9 部先后连载于《小说月报丛刊》《亚波罗》《社会周报》《华北月刊》《世界文库月报》《戏剧与文学》《西洋文学》《春秋(上海1943)》等期刊杂志上,为福楼拜小说在当时社会的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五四新思潮也为书籍出版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以茅盾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家的号召下,大批读者把目光投向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使福楼拜小说受到了众多出版机构的青睐。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李劼人译的《马丹波娃利》,这是福楼拜作品在中国的第一个单行译本。虽然今天国内出版机构早已不再重新发行该译本。但它在我国的福楼拜译介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是研究福楼拜百年传播历程不可绕过的关键节点。随后,商务印书馆于1927年出版李青崖所译《波华荔夫人传》;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出版机构似乎也意识到了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纷纷加入福楼拜小说翻译出版的行列,如北新书局出版刘半农译的《游地狱记》、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出版李健吾译的《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及《三故事》。许多译作还被收入各类丛书出版,如《马丹波娃利》收录于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波华荔夫人传》收录于文学研究会丛书,李劼人所译的《萨郎波》收录于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李健吾译的《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及《三故事》收录于译文丛书。可见,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得益于各大出版机构的不断推陈出新,福楼拜作品从被译入初期便受到极大的重视,引发普遍的好评,使福楼拜从一开始就居于我国读书界喜闻乐见的外国经典作家之列。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领域从根本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国家对出版机构进行了规范和重组,建立起新的出版管理体制,充分整合出版资源。在此背景下,福楼拜作品的出版迎来崭新的局面:其译本全部以单行本或作品集的方式发行,出版次数超过190 次。不过,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特定时期文化倾向的影响,苏联文学一度成为译介和出版的重心,同时期在我国出版的福楼拜译本基本上是旧译再版。新时期以来,译者群体不断壮大,出现以许渊冲、周克希、罗国林为代表的新一批译者,他们孜孜不倦地重译或复译这位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因此,新译涌现和旧译再版并驾齐驱,此时的出版量呈井喷式的上升态势,约占出版总次数的85%。此外,各大出版机构陆续规划出版福楼拜作品集,如199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郑克鲁主编的《福楼拜短篇小说集》,199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谭立德主编的《福楼拜集》,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福楼拜全集》等。这些作品集多次再版并长期影响着我国福楼拜的阅读市场,表明福楼拜作品拥有长盛不衰的文学魅力,也展示出我国出版机构在福楼拜著作出版方面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一部分译本还以“双语对照”形式出版,表明我国对福楼拜的接受进入新的国际化语境,译者与读者群体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出版机构的策略转变。
其次,从地域上看,我国发行福楼拜中译本的出版机构主要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两地出版的福楼拜译本总和接近全国译本总数的60%。具体而言,在民国时期,上海几乎独揽福楼拜作品的出版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25 部作品(含期刊刊载与单行本)中,就有20 部出自上海的出版机构。这是因为当时的上海凭借发达的工商业、便利的设施条件以及活跃的文艺环境,成了“全国的书业中心”(郑士德,2009:421),坐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型民族资本出版企业和现代书局、启明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一大批有活力的中小出版社;无论是报纸杂志类还是著作书籍类,上海的出版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堪称一枝独秀,仅以翻译文学书籍的出版状况来说,“在其时我国境内出版的全部4,270 种翻译文学书籍(不含出版地未详者)中,上海一地就出版了3,472 种,占总量的81%”(邓集田,2012:189),遥遥领先于同时期其他城市的出版规模。因此,民国时期的福楼拜作品中译本出版几乎是上海这一城市的独角戏。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出版行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代表的一大批国有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也于1954年由上海迁至北京,北京逐步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190 余种福楼拜作品译本中,有71 种出版于北京,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专门出版中外文学类作品的国营机构,出版了大量福楼拜作品的译作,李健吾所译的《包法利夫人》因其“尽传原著之精神、气势”(艾珉,2002:25)得以作为经典译本被该出版社再版十余次。与此同时,上海依然是这一时期的文化重镇,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多次出版或重版李健吾翻译的《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一颗简单的心》及《萨郎宝》,还有周克希翻译的《包法利夫人》,施康强翻译的《庸见词典》等,出版数接近此时国内福楼拜作品译本出版总数的五分之一,表明上海和北京一样都是福楼拜译介出版的中心地带。
无论是从时间上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福楼拜中译本在我国或集中或分散的出版情形,还是从空间地域上探讨福楼拜译本在我国大江南北不同城市的出版格局,这种针对外国文学译本出版状况的研究视角无疑具有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文学翻译研究的思路。对福楼拜在我国百余年间的译本出版状况的评述,也许能增强福楼拜在中国的译介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5 结语
福楼拜作品的译介肇始于中国文学面临变革时局、寻求自身突破的时代。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福楼拜作品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无疑正是中国新文学阵营竭力寻求的“一剂良药”。如果说这种社会功用是他的小说被选择和译入中国的主要诱因,那么文本本身所蕴含的美学与思想价值则是引发百年复译潮流的根本原因。值得庆幸的是,百余年来,福楼拜作品拥有以李健吾、许渊冲、周克希、施康强为代表的优秀译者群体,正是因为他们秉持着忠于原著的精神,福楼拜作品才得以在异乡的土壤中深深扎根,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滋养着戮力前行的中国文学。福楼拜在中国的百年译介历程,既体现为杰出译者群体共同创造的历史结晶,也彰显了弄潮于文化洪流中的重要出版机构的先见之明,表现了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文化主体在我国的福楼拜文艺美学建构进程中各自发挥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