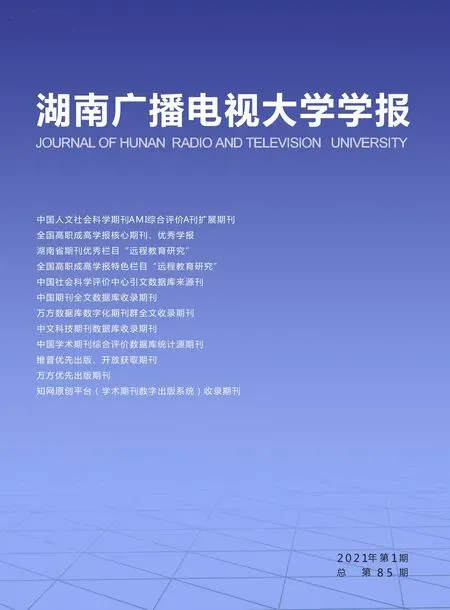国产黑色喜剧电影的溯源与本土化表达
李苗苗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临汾 041000)
不同类型的商业电影丰富了我国电影市场,小成本、制作精良的黑色喜剧电影在其中显得非常耀眼。与大部分商业大片相比,国产黑色喜剧电影的投资成本较低、票房收益相对较高,其灵活多样的视听技法和特效给观众留下了新奇的审美感受。由于影片中故事的趣味性和可看性较高,非线性叙事手法大大提升了观众参与解谜和讨论的积极性。影片对社会问题的想象性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暂时安抚大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对现实的讽刺和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使得黑色喜剧电影颇受市场青睐。
20世纪80年代,《黑炮事件》《错位》等影片注重展现精英知识分子的牢骚与不满,体现了电影对批判讽刺现实主义的追求。然而,故事中的矛盾没有因为影片的结束而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使观众体会到沉重和压抑的现实感。进入21世纪,电影对政治问题的映射逐渐淡化,转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或法理议题。宁浩导演的“疯狂三部曲”(《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疯狂的外星人》),曹保平导演的《光荣的愤怒》《追凶者也》,杨庆导演的《火锅英雄》和饶晓志导演的《无名之辈》等,都属于黑色喜剧电影。这些电影不仅在借鉴的基础上对国外黑色喜剧电影的荒诞内核进行了改造,体现出国产黑色喜剧电影的本土特色与文化品格,而且试图纾解国内多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日益突出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解构社会精英的权威,展现底层民众的尊严与生存智慧。
一、概念辨析
黑色喜剧电影的相关概念包括黑色电影、黑色幽默、黑色喜剧等。
黑色电影这一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早。20世纪40年代,法国电影评论家法兰克受黑色小说影响,将黑色电影这一词语引入电影评论。与传统的电影类型相比,黑色电影所代表的美学风格比较独特、容易辨认。它不是由传统制片厂在制作阶段生成的一个类型概念,而是在电影上映后由观众、评论家群体所催生。黑色常常关乎影片中故事发生的时空环境,通过表现主义的摄影风格和高照明、低反差的布光等,观众可以直观地从画面影像上看到黑色的角落、阴暗的雨天、泥泞的街道,产生一种阴森恐怖的视觉和心理感受。黑色电影中的主人公往往孤独失意、迷恋过去,最终难逃死亡的宿命,其叙事情节和主题内核大多指向都市犯罪、不正当交易和人的堕落欲望、腐朽沉沦等。黑色电影曾风靡一时,如《马耳他之鹰》《双重赔偿》《日落大道》等,这些影片在视觉和心理上给观众带来独特的审美感受。与黑色喜剧、黑色幽默等概念相比,黑色电影概念更容易辨识。国内导演刁亦男受黑色电影的影响,近年来创作了《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这些影片是国内黑色电影的代表之作。
黑色幽默最初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黑色幽默是一种阴郁的幽默,又被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表面上看似轻松的玩笑,实则表达的是一种无奈和荒诞感,可以说是一种用喜剧形式来表现悲剧内容的新文学形式[1]。它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关心人类最基本的问题,认为人类生存在世界上是毫无意义的,人类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权威,恐惧不安和迷茫笼罩人的心灵。黑色幽默的盛行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有直接关系,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不平等引起了深受压迫的黑人的强烈反抗,黑色幽默诞生的时代语境、对种族平等问题的关切态度注定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政治意图。对传统的解构是后现代艺术的主题,这类文艺作品中常常会展现挑战权威、消解中心等行动,但这些反抗行动最终却没有结果。黑色幽默中包含着许多荒诞不经的人物和情节,其特点是笑中含泪,作品通过荒诞的情节来折射人类面对现代理性世界时的绝望内心。这种幽默带来的是一种有品位有格调的笑,相比一般的滑稽,黑色幽默的手法显得更为深沉悲凉。“海德格尔认为,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就必定异化,社会给人以压力并使之就范,它会夺去人的个性,使人失去人格;只有由死亡所引起的内心的苦闷体验,才能使人重新以个别化的方式回到自身,认真考虑自己的一切可能性,严肃地进行选择,回到真正的存在。”[2]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体现出个体对现代社会和他人的不信任感。
从词源学角度可以比较直观地理解黑色喜剧与黑色幽默的区别,这两个词语在英文中分别是black comedy、 black humor。喜剧(comedy)作为名词是一个与悲剧相对应的概念,它被用来指代独立、具体的对象;而幽默(humor)作为形容词性的词语则表示一种事物的属性,幽默与诙谐、滑稽等构成了喜剧的几种常见类型。
《电影艺术词典》对喜剧片是这样界定的:“以产生笑的效果为特征的故事片。在总体上有完整的喜剧性构思,创造出喜剧性的人物和背景。主要艺术手段是发掘生活中的可笑现象,作夸张的处理,达到真实和夸张的统一。其目的是通过笑来颂扬美好、进步的事物或理想,讽刺或嘲笑落后现象,在笑声中娱乐和教育观众。矛盾的解决通常是正义战胜邪恶,影片的结局比较轻松欢快。”[3]从这一定义中可以发现黑色喜剧电影与传统喜剧电影存在多方面的不同,黑色喜剧电影虽然充满喜剧性的人物性格与情节,但在题材选取上较多关注犯罪等社会阴暗面,关注社会边缘人物与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
国外黑色喜剧电影的创作者通过作品反思人类的主体性,揭示所处世界与人生的荒诞性,以嘲笑的方式揭示人类生存的悲剧命运,显示出现代喜剧美学对传统喜剧美学的超越。国外的黑色喜剧电影不同于传统的好莱坞电影叙事过度追求戏剧性情节的变化,而是类似一种叙事的游戏,体现出一种拒绝意义、逃离意义的后现代特征。如电影《两杆大烟枪》中自以为已经掌控局势的赌场老板哈利和助手巴利意外死于小毛贼之手,这是令剧中角色和观众都料想不到的,就像现实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令人猝不及防。这种意外情节的设置恰恰反映了日常生活的巨大荒诞性,以及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可知和深感自身渺小无力的绝望。
二、国产黑色喜剧电影的生成语境与文化内涵
国产黑色喜剧电影是创作者在借鉴西方黑色喜剧电影的基础上,根据当下我国社会语境和观众接受度进行本土化改造之后生成。国产黑色喜剧电影既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又与其生成的语境关系密切,一旦脱离具体的社会语境就很难对其进行有效言说,因此必须仔细考察其生成的具体性与特殊性。国产黑色喜剧电影涉及当下的社会现实,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经历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纠葛,黑色喜剧电影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何种嬗变?有哪些层面的含义是被遮蔽、被误解的?又是如何被移植到当下国内语境中来?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喜剧电影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即已出现,其间虽然遭受了一定的曲折和艰难,但基本上没有间断,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社会充满开放的气息,各种西方文化与理论思潮蜂拥而至,不仅满足了国民对于知识的渴求,而且刺激了被限制许久的文艺创作者的表达欲望,文化艺术创作呈现出多元的发展局面。此时的第五代电影人反思历史与当下,将被压抑良久的创作热情投入电影创作,使中国电影呈现出一派生机。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错位》等影片,成为当时国产黑色喜剧电影的先行者。这些影片通过荒诞的喜剧情节设置、离奇的想象,揭露了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现实弊病,渗透着创作者对国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生存现状、民族劣根性和落后心理的焦虑与担忧。影片中大量新颖的黑色喜剧创作手法的运用,以及批判现实的尖锐和敏感力度,虽然在当时难以被大多数观众接受,但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犀利的社会批判性与深刻的思想前瞻性。
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语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改革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在日益明显的消费文化语境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奉消费至上,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处于底层的个体开始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渺小,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越来越膨胀的欲望、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缺失等问题感到焦虑。过去的精英电影文化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多元化的精神表达诉求。在观众此前的认知里,电影的主要功用在于宣传官方意识形态与开展道德教化;而这一时期电影的宣传教化价值被淡化,商业娱乐性被视为更重要的功能,电影作为一种商品的属性开始被创作者、观众等不同群体接受。人们开始意识到电影是一种可以抚慰观者的心灵、缓解其焦虑和压力的生活调味剂。观众作为电影的消费者,希望从电影中看到对于自身所处的复杂社会中难以解决的生活困境等多重问题的银幕表达。电影创作者也不再只是将电影创作视为纯粹的个性化的艺术探索,而开始融入新的市场运作机制。作为电影的生产者,创作者试图通过影像建构矛盾冲突,在故事中使问题得到一种想象性的解决,以此契合大众内心的诉求和欲望。
21世纪初,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等黑色喜剧电影保留了国外黑色喜剧片中的荒诞叙事与创作技巧,瓦解了传统的主流精英话语,追求大众化、狂欢化的审美趣味,在笑中含泪、悲喜交加的基础上,探索本土化的独特黑色喜剧精神,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内涵。这些影片突破了之前电影对于底层关怀的狭隘阈限,在表现题材上有意拓展至边缘人、平民和中产阶层,积极主动地结合当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症候,从国内正在高速推进的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忘或是被落下的底层边缘人物、普通民众以及中产阶层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出发,引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与真切反思。
三、国产黑色喜剧电影的喜剧性策略与创作风格
黑色喜剧电影进入我国后,在叙事策略和价值取向上均显示出被本土化改造之后的特色表达。西方黑色幽默电影聚焦于种族矛盾问题,在国内则被转化为社会阶层问题;在西方国家展现的是黑人对于白人社会原有秩序的反抗,在国内具体的电影创作实践中,这一核心矛盾被创作者挪移,转变为底层小人物对于中产阶级及精英阶层的嘲讽。西方黑色幽默电影中的不平等结构是一种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这一政治性的议题在国产黑色喜剧电影中则被伦理议题取代,作品中通常展现的是官方与民间、朝堂与江湖、主流与黑道的冲突。“人的心灵深处的这种反制度化、反理性规范的倾向,在各种狂欢活动及喜剧作品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鲜明地表现出来。”[4]影片中小人物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现实生活中观众内心深处被压抑的需求,因为任何亚文化在挑战权威和既有秩序的同时也在被主流文化有效地收编:其视觉形象抑或转化为大量可资生产的物品,抑或被主流文化贴标签和重新界定[5]。
国产黑色喜剧电影在制作策略上一方面借鉴和使用了国外的喜剧创作手法,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质,以两方面的平衡来适应当下国内电影市场的观众审美需求。首先,黑色喜剧电影在叙事手法上大多采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叙事,以多条线索展开交叉叙事。《两杆大烟枪》有七条线索,并在不同的帮派和团伙之间进行交叉叙事。《疯狂的石头》在情节设计、细节铺陈上借鉴《两杆大烟枪》,围绕翡翠宝石这一细节分别从开发商老板、香港的国际大盗麦克、保卫科长包世宏、笨拙胆大的窃贼道哥三人、厂长儿子谢小盟等五组主要人物的不同视点进行叙事。《疯狂的赛车》中的草根小人物耿浩、两个毛贼、奸商李法拉、专业毒枭和警察,同样是几组不同的人物各自成为一条叙事线索。其次,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美学风格,采用了大量的拼贴、戏仿、快速剪辑,利用巧合、误会、重复等编排情节,追求对权威的解构。在《疯狂的石头》麦克取宝石的情节中,可以发现黑色喜剧电影对精英阶层、专业性知识充满了戏谑和嘲讽。这种类似的解构手法在《疯狂的外星人》里也可以看到。在视听语言呈现上,黑色喜剧片常常选择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加直观刺激的技法,如夸张扭曲的画面构图、特殊的拍摄角度、带有地域特色的方言、节奏感强烈的配乐等。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谈到,在报刊书籍繁荣之前,小说传播方式还是以“说—听”为主,小说叙事是“以全知视角连贯地讲述一个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故事”[6]294。“《古今小说》卷二十《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则是全知叙事,一会儿写陈从善,一会儿写紫阳真人,一会儿写如春,一会儿写申阳公,按照时间先后分头叙述。”[6]293国产黑色喜剧电影在叙事推展和场景转换上体现出这种传统叙事模式的特征,这是一种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有别于西方的叙事手法。《疯狂的石头》中包世宏问“三宝去哪里了”的这个镜头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是三宝在北京天安门前的镜头,通过人物对话实现场景的转换,然后引向新的人物线索进行叙事。这种传统的叙事推展与多条线索交叉的现代叙事技巧,以及单镜头画面剪切的剪辑手法,都在彰显国产黑色喜剧电影的中西文化掺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等特征。
国产黑色喜剧电影创作在本土化表达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拍摄手法上大多是模仿西方黑色喜剧电影的摄影技法,如主观镜头的使用、单镜头画面等。在《疯狂的石头》中,为了突出主人公包世宏发现翡翠宝石被偷后的心理反应,导演使用了人物的主观镜头实现主观视觉的呈现。这与《猜火车》《两杆大烟枪》等影片中为了表达吸毒给人带来的幻觉等主观感受时所使用的摄影技法一样,这种手法的使用明显缺乏本土化的美学设计。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指种种创作上的不足,仅仅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加客观、完整地认识和评价黑色喜剧电影的本土化呈现,从而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四、结语
国产黑色喜剧电影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发展映射了国内经济文化繁荣背后民众精神生活需求的变迁。黑色喜剧电影基于国内民众的现实生存经验,将带有本土化、地域性、传统文化品格的精髓与社会议题进行有机结合,并且灵活采用后现代手法进行呈现。每部作品的创作实践与表达在不同阶段提供了一种纾解社会矛盾、表达民众情绪的载体,这无疑体现着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与关切,同时促进了国产喜剧电影的多义性表达。在如今的文化消费语境中,黑色喜剧电影完全可以有效地沟通主流意识形态、电影生产与受众消费,它所负载的批判力既是顺应民意、疏通情绪的良好途径,也是电影人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使命的重要体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