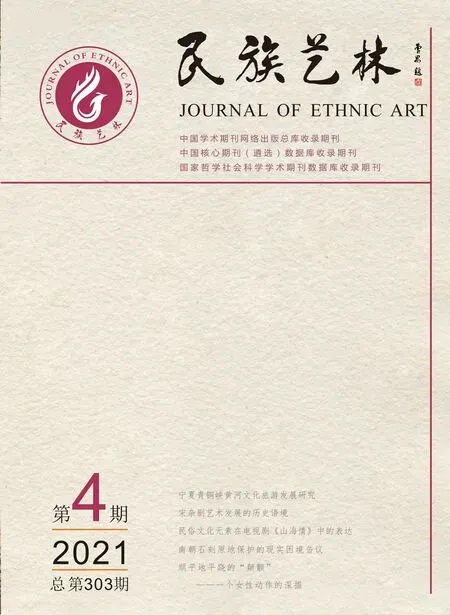地缘文化·典型形象·亲缘伦理:农村脱贫剧《山海情》的三重解读
张鹤炀
(中国艺术研究院 影视学系,北京 100020)
一、地缘文化符号传递情感价值 推动故事情节
“正午阳光聚力于全国性电视剧文化品牌打造,在具体叙事技巧和镜像语言等方面与地域文化特色进行源头上架联。”[1]剧中西北地区自然和文化地理景观与叙事视听内在联系,与现实世界有机融合,奠定西北黄土地色彩的情感基调、大地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召唤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地缘文化推动叙事情节发展,构建了家国共同体,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艰苦奋斗、自信豪迈的地缘情感。
(一)符号化的文化地理景观召唤共情 表达价值理念
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相对应的情感性格和文化观念。剧中多处使用了带有地域色彩的文化景观、标志等作为典型符号,烘托出了自然原始、朴素真实的美感。同时山海之间的情感相依,是追求民族基因中和而不同,生生不息,山水交融的价值理念,体现了“生生谓之易”辩证发展的哲思。方言的使用是该剧的一大特色,这不仅唤起闽宁两地人民的文化认同和共情,还在方言沟通中完成“山海情谊”的升华。
汪曾祺先生曾说“气氛即人物”。正因为脱贫工作是针对某个地区和人口群体而展开,故脱贫题材电视剧与地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性。但很多脱贫题材电视剧中地域特色不够鲜明,例如《花繁叶茂》《绿水青山带笑颜》等电视剧,剧中人物妆容精致,自然山水风光优美,人人操着普通话,建筑民居错落有致等,好像放在哪儿都未尝不可,甚至有些地域特色仅为点缀,“地方性”的薄弱导致了剧集的悬浮。
而《山海情》在塑造人物、传递情感和文化价值理念过程中,使用的地理、空间、环境、场景、人物形象设计都符合宁夏西海固地区的真实风土人情。以整体大面积的黄色为主,黄土高原、土坯房、火车与铁路、蘑菇大棚、土墙巨幅白色标语“涌泉村,水最甜的地方”、小学教室中斑驳的墙皮、带有西北特色的服装、带有高原红的脸颊,皴裂的皮肤等多次重复出现,奠定雄浑苍凉的情感基调,表现了西海固地区生存发展时代变迁的历史进程。
剧集伊始在西海固荒凉的山坳里,新入职的干部马得福带着黄黑的皮肤和红彤彤的脸颊,与嘴里衔着干草的父亲马喊水一同费力地蹬着自行车前进,并用方言沟通移民工作,此时的环境氛围与人物服化道特质融为一体。观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剧中的各种地方元素形成认同;马得宝等人扒火车段落中,沙漠戈壁地貌占据大面积画幅,翻越沙丘、戈壁奔跑、登上火车表达了年轻一代挑战自然、求得新生的价值观念。在该剧的最后,原先黄沙漫天,戈壁无尽的土地已经变成了绿色大地,这种前后的对照互文表征出时代变迁下山海之间的情感联结。这些典型地域风貌“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在访问一个承载着共同记忆的地方时,头脑里通常带着来自电影、电视和其他文本的记忆,以互文的方式唤起集体记忆”[2]。
方言召唤认同,传递情感。“西海固”指宁夏南部西吉、海原和固原。“宁夏境内的中原官话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固原、彭阳、海原、西吉、隆德、泾源6 市县以及东部的盐池县,可分为固海、西隆、泾源三小片,分别隶属秦陇片、陇中片和关中片。”[3]剧中大部分演员都使用方言交流,贴近实际。对观众而言,这种真实感正是他们将剧中放大后的日常生活与自己现实日常经验衔接后的一种认同反应[4]。导演孔笙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当我们进入西海固地区后,对方言的感受就更强烈,那一方人就是如此,他们的性格、喜怒哀乐就是这样。”[5]当陈金山用西海固方言向马得福告别:“饿(我)走了。”马得福回以闽南口音“那我好好刚作(工作)等你回来”。二人互用方言细节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艺术效果,内含着互换身份、闽宁情深的价值归旨,方言成为山海水乳交融的情感纽带。
剧中的“村落名称”的变迁表达了山海相依、互帮互助、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情感。“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6]“闽宁”象征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内外相依、互相帮扶的“山海情”,构筑了想象的家国共同体;“金滩”“涌泉”体现了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和对“水”作为生存发展象征的向往;基于地缘因素的共生共栖也在整村搬迁和团圆宴中获得当代传承,这三处主题和情节体现了传统到现代的时代转换,体现了和谐共荣,肝胆相照的地缘情感。
(二)典型地理特质作为叙事动因推动情节矛盾发展
剧中典型自然地理特质成为情节发展的逻辑动因。“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元素,我国西北地区干旱少雨,蒸发量高,缺水是这一地区典型的自然地理气候特征。因此,大多此类表现西北地区故事内容的影视作品一般都会在剧中以“水”为叙事元素展开故事。《山海情》也不例外,在剧中无论是生活在涌泉村,还是搬迁到金滩村,“找水”都是主要的叙事矛盾点和动力源之一。
金滩村作为吊庄移民的驻地,开荒种地灌溉用水必不可少,同时还需奔走几十里买土改善原先的贫瘠水土。剧中但马得福、李大有等人因灌溉分配不公与隔壁村发生争执,并赶往书记等领导办公现场讨要说法,最终在领导的批评协调下解决冲突。这里“水”这一自然符号不仅推动情节发展,还体现出人性的偏私和对公平的渴求。对“水”作为生命之源的渴求呈现出自然环境对人生存发展的束缚,以及吊庄移民户在贫瘠自然环境中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剧中人物的行为实践将主观价值注入现实空间,使自然地点凝结为一个具有表征意义的空间和地缘符号,与现实共振,成为联结观众和剧集的纽带。
移民也因涌泉村自然环境恶劣,从不愿搬迁到集体反悔,村民们从“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涌泉村“被迫”搬迁至荒凉的戈壁滩,这一过程基于恶劣自然条件而引发,是我国大西北贫瘠地区的真实写照。选择用大棚的方式种植双孢菇是当地人对缺水干旱等恶劣自然环境的抵抗,体现人谋求生存发展的独立意识,以及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念。这些情节单元体现出人最基本的原始欲望和心理冲动,表征出具有全人类大同社会属性的价值。上述三个大小的情节单元中,缺水、干旱、贫瘠等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营造人物冲突和人地矛盾,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也为沿海福建对口支援内陆宁夏的山海情谊埋下伏笔。
二、平民视角中塑造人物形象
该剧主旋律宏大主题与人物性格逻辑相得益彰,不落窠臼、具有鲜明张力,是对新“农村人”形象的荧屏透视。首先,剧中塑造出了马得福、白校长、凌教授三位具有平民英雄色彩的人物,以及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其次,该剧塑造了时代变迁背景下白麦苗、李水花、吴月娟、杨书记等性格独立、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呈现出时代变迁中不同身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主意识的崛起。
(一)平民视角下塑造丰碑式英雄形象和圆形的“农村人”形象
剧中通过一连串情节事件塑造了马得福、白校长和凌教授三位带有平民英雄色彩的形象。神话研究者约瑟夫·坎贝尔(Joseph·Campbell)通过对不同文化中的大量神话中的英雄形象研究得出其冒险模式:分离——传授奥秘——归来。“神话中英雄的每一次出发、冒险、归来模式,就是现实中人类认识自我模式的体现。当英雄以一种新的状态,带着神的恩赐重新回归社会。最后当回到正常世界的时机成熟时,这位被传授奥秘者实际上就像经历过重新出生一样。”[7]
马得福自农校学成归来后借调为家乡涌泉村干部。他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村管理思路和农村发展理念运用到实践中,完成吊庄移民、通电、盖学校、种双孢菇、异地就业等象征着历史使命的基层工作,聚合了时代语境中脱贫攻坚干部的群像特质,发挥出一心为公、知恩图报、责任感强的人格力量,具有平民英雄色彩。白校长和凌教授是脱贫工作中扶志、扶智的典型人物。白校长作为早期到西海固地区支教老师,他扎根当地,苦心劝说家长、追车抢人全力阻拦未成年学生辍学,而要求学生继续上学;家访时虽然被家长冷落、指责或嘲笑,但他仍坚持好言相劝;当感到教育被忽视时,他下决心卖掉闽商捐赠的电脑,换钱给学生买校服参加合唱比赛、整修教室操场;当马德福面临“独木桥”和“高速路”的发展难题和人生困境时,他不计前嫌悉心指导,这一系列情节聚合他为扶志扶智的典型符号。通过这个人物的高尚品格升华了本剧主题立意和价值观念的高度、深度。凌教授探索种菇致富、传递科技扶贫的理念;不惜自付高价货款收购村民蘑菇;在人格遭受侵犯、面对畸形市场竞争时敢于出手等细节表现他为人公正、无私奉献的品格。上述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的设定不仅映射了现实中扶贫工作的复杂,并且升华了脱贫攻坚题旨及其文化意义,通过描写他们在克服典型贫苦环境和接二连三的阻碍性事件的过程,塑造出三个丰碑式的平民英雄形象。
可贵的是,剧集尊重基本人性,敢于直视人物的缺点和不足。在叙事上运用细节描写的手法呈现不同人物性格,避免了一般“命题”电视剧的悬浮感,并未因脱贫攻坚题材而有意贴合主流意识形态、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而是将具有历史向度的、丰富多元的“农村人”形象丰富立体、生动鲜活地呈现在电视艺术作品中。如部分村民宰扶贫珍珠种鸡、自私直率的李大有、善于逢迎的麻副县长、保守拒迁的李老太爷、略带痞气的马喊水等。
剧中主要配角李大有性格张力充足,这人物折射出的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叙事矛盾。身为第一批吊庄移民,他当“逃兵”的理由是“在涌泉村吃黄土,比在金滩村吃沙子好一些,黄土比沙子细”这一细节台词表现了这一人物的斤斤计较,看重利益和有些狡黠的一面。剧中他对移民工作表态道:“你说的千好万好,可未来是啥么,未来就是还没有来嘛!”这句台词不仅体现了李大有作为叙事阻碍的功能,也写出了吊庄移民户的真实性格和心态,细节化地呈现了当时西海固地区生存困境;李老太爷等老一辈的村民,是思想保守封闭的象征符号。一方面他们是情节发展的阻碍者,但另一方面他们是思想观念层“僵化守旧与变革发展”的矛盾体现。安土重迁耽误年青一辈发展,也给搬迁工作带来了困难。此外,马喊水性格粗犷,他对子女教育充分体现了农村欠发达地区的“父权制”的根深蒂固,以及当地一众父母阻碍子女上学、残疾丈夫阻碍水花创业工作等情节,真实地体现了赤贫农村以往的愚昧封建。但故事结尾,此类矛盾一一解决,实现了村民们在新时代和新政策的背景下的命运救赎和自我价值。私欲是每个社会成员具有的原始特点,但人的社会价值就在于所作所为能够尊公轻私,剧中人物的人性融合,从平民视角和正反两方面凸显出剧中角的色生动鲜活。
(二)时代变迁中塑造农村新女性形象
典型性格在情节发展和典型环境中塑造。“马克思提出了审视典型的一个重要原则,即特征性原则。”[8]这种特征是表现出人物之间整体差异性的固定标识,在电视剧作品中表现在每个人物性格最根本的个性上。“所谓特征,就是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9]
剧中用大量笔墨塑造了特征突出、性格鲜明的新女性形象。白麦苗、李水花、杨书记、吴月娟等个性鲜明、重情重义,面对命运困境她们表现出艰苦奋斗的精神,让全剧苍凉雄浑、苦难情深的基调中渗透出细腻柔软的情感表达。
李水花19 岁这年,面对父亲自作主张、包办婚姻,她被以一头驴、一口水窖的彩礼交换给素未谋面的男人。她以“逃婚”这一形式表现出独立女性的反抗意识。但之后不得已凑合的婚姻、丈夫意外残疾、女儿年幼待哺是她面对逆境迎难而上的行动阻碍。一系列的情节和事件从不同侧面塑造出李水花在对待自我命运、家庭环境、相亲邻里的人生态度。她逆境而上、积极参与种菇、追求美好生活。剧中典型场景和视听语言为其人物性格增益。当她拉着板车在夕阳下以剪影的方式、侧跟镜头拍摄时,如同徐徐展开的一张画卷,此时李水花宛若成年女性抗争传统守旧的人物浮雕。落日余晖,她面带微笑、步步坚定如纤夫一般向着象征美好生活和希望的搬迁地区走去。累了便叫女儿和自己喊:“快了,快了!”并大声歌唱为自己鼓劲:“走远咧、越走越远咧,心里的惆怅重下咧,越走越远咧,心里的惆怅重下咧”。丈夫逐渐醒悟,从阻碍者变为情节推动者。二人实现了命运困境中的蜕变发展,成为敢于抗争,先苦后甜的性格符号。
白麦苗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在现代都市场景中独立有志、回馈家乡的新时代女性代表。这一人物聪颖善良、能言善辩、有不服输的劲头,敢于挑战未知,迎难而上,自主把握命运。在宏观政策感召下,作为先期到福建的宁夏女工,她在工作中表现优秀、协助同乡、细心努力,成为职业女性的先进典范。她在福建成为女性职工代表,并走上企业管理岗位。回乡演讲探亲,当看到家乡的生存现状和美好未来时,她毅然决定回乡创业,回报家乡。
此外,剧中几位女性干部形象例如县委杨书记、扶贫干部吴月娟也体现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无私奉献、正直坚强。面对扶贫路上的阻碍她们斩钉截铁,面对欺上瞒下现象不手软,全力协助村民卖菇。同时,创作者也书写了她们在面对命运的抉择、新时代机遇和挑战时的迷惘和两难。但在剧中这些角色始终秉持着独立自强的人格观念,性格鲜明,相互独立,综合了20 世纪末以来女性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变化,以点带面地投射出当代女性独立、自强的典型特质。
三、民族性亲缘伦理和脱贫攻坚时代精神的展现
剧中民族性多层次亲缘伦理作为集体怀旧表达,契合了现代观众的需求。体现了对最根源的“和谐”秩序的家国状态的追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该剧典型化村落从上帝视角反映出时代变迁,审视过往,投射出家国情怀,彰显脱贫攻坚、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一)亲缘伦理思想契合民族文化心理
剧中家族伦理情感契合民族深层文化心理,人物关系中地缘、血缘情感对现代社会亲缘伦理的缺席形成心理补偿。“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延亲属差序向外扩大。”[10]剧中马得福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将不愿搬迁的村民鄙夷厌恶地称为“刁民”,其父亲马喊水极为愤怒地摔碗大骂,讲述了李姓人在极贫的情况下重情重义,对马姓人的帮助接纳,马喊水叮嘱儿子“不能忘了本”。如今为寻找更宜发展的生存地,马姓人带领李姓人搬迁,呈现出“兼爱”“仁义”“以德报德”和追求“和谐”的传统思想。“涌泉村的旧”与“金滩村的新”形成了生死相依的价值和道德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是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价值建构的产物,它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而是存在着为该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一套价值体系。”[11]由此延伸出的“山——宁夏”“海——福建”之间相互帮扶体现了“变易”式发展思想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生存状态。
剧集结尾新一代实地回溯涌泉村这一地理空间中李马两姓传承数百年的情感伦理,跨越时空地深化了李马、闽宁互助依存的思想蕴含,延续了道德共同体在族群的当代传承。剧中年青一辈是当代青年人的荧屏投射,时代赋予其多种命运可能。整村搬迁时,水花的呐喊体现了其对安土重迁等思想束缚的抗争和对自身命运的把控。老一辈人被感化,突破传统桎梏,支持整村搬迁;李大有托白麦苗给在外打工的儿子送土鸡蛋;白校长对学生严格深情的关怀等情节凝结了代际间传统孝悌思想。
社群邻里间帮扶培植了稳固持久的人际伦理关系。“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之间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12]老辈的李马两家在时代变迁中你来我往,互助交融;得宝九死一生寻尕娃;海吉女工异地彼此照料;剧集结尾李大有等村民送别凌教授;水花得福互相协助等故事脉络中,基于挑战自然和把握命运,人物关系升华为互助奋斗情。“邻里关系是在持续的社区交往活动中不断地建立起来,是社区交往行动的结果。社区是指具有共同地域,有较深入的社会交往关系和具有一定共同体意识的居民共同体。地缘上的归属感和心理上的认同感是社区的一个重要因素。”[13]
此剧亲缘伦理的呈现深谙民族文化心理中的乡土性,对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进行诗意、崇高化的点染。这种和谐的思想深刻激发了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的共情和认同。“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14]唤起了观众对具有民族意蕴的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感召。
(二)向往美好生活中彰显脱贫攻坚时代精神
该剧聚焦偏远地区,以一系列平凡质朴的事件情节和真实鲜活的边缘人物,表达了西北贫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展示了脱贫攻坚进程中人民主体地位和家国一体的价值导向。吊庄移民的艰难推进;村民宰扶贫珍珠鸡种鸡;种菇售菇遇到不公正对待等现象还原了实际脱贫工作的意外情况和现实困境。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组织村民种菇、组织女工去福建电子厂工作、据理力争完成通电、筹措资金修缮扬水站,白校长极力挽留未成年孩子接受教育……展示了脱贫攻坚的人文关怀和奋斗精神,凸显了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集体使命感和责任感。如同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民,都和我有关。呈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山海情》的故事从1991 年讲起,通过西海固地区涌泉村搬迁金滩村、闽宁村扩大闽宁镇的现实风貌变化,以马得福、张树成、白老师、凌一农、陈金山、吴月娟、马得宝、白麦苗等党的领导干部、基层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群像为线索,串联起了一幅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艰苦卓绝、奋斗不息的波澜画卷。以典型化的方式呼应了现实世界中脱贫攻坚伟大斗争,表征出“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
剧中通过典型化的段落表现出自20 世纪到当今的时代变迁。故事中的典型情节在经过艺术化的处理之后,往往成为具有深刻价值内涵的象征化段落,起到升华主题的功能,这一点在“叙事”文学艺术历史长河中长盛不衰。在搬迁工作具体开始执行时,马德福带领第一支搬迁队伍自涌泉村向金滩村艰难行进,途中遇上到西北戈壁滩上规模巨大的沙暴天气,搬迁队伍被漫卷而来的黄土扬沙所包围。但一行人并未因此退缩,而是在笃定心志、略作调整后继续前行。此时行进的队伍就像在历史维度中,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守旧走向变革,象征着对美好的新生活道路的艰难摸索。基于地理环境表现出的细节真实和情感震撼,从剧中来讲是村民对扶贫搬迁美好未来的憧憬,更宏观地表征出现实语境中脱贫攻坚征程的跨时代意义。
在《山海情》中孩子们合唱《春天在哪里》参加比赛,加之视听语言的艺术化处理,让这一段落成为剧中带有深刻主题内涵的宏观集体象征。“春天”象征着美好新生活,“孩子”象征着青春活力和民族希望,他们没有专业声乐训练的嘶喊更显真挚纯粹。“好的电影是要创造叙事性与隐喻性相互统一融会的美学意境”。[15]这一段落的视听语言、叙事情节与情感价值符号相契合。升格镜头和叠印效果的使用,将这一对美好憧憬的象征在文本时间层面拉大,将时间空间化处理,舞台上孩子们激烈地演唱、奋力地嘶喊、喜悦的表情和老师热泪盈眶地期盼,作为人物主体的行为,都赋予剧中时空以特殊的情感意义。在合唱表演过程中,运用倒叙的方式,穿插进白老师带领孩子在村路上排练、吊庄移民户盖房垦荒的场景、得福水花等人种菇等镜头,完成了从一场简单素朴的演出到人民群众奏响奋进乐章的情感升华。
四、结语
《山海情》拍摄时间短、剧集小而精,具有历史厚重感,23 集的体量以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贴近生活、扎根人民,进行创作,汇集了具有时代性的宏大主题和接地气的创演模式。剧集以小人物描摹大英雄、以小村落映射大国家、以小事件彰显大精神,在地缘文化、亲缘伦理、时代精神的价值指认中创新且真实地书写了当下农村的荧屏形象。“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该剧从全国山海相依的自然地域为基点,超越到形而上的文化地理和情感地理层面,彰显了贯通时代和跨越地域的历史感和大格局。从各角度综合来看,是农村题材剧创作进程中一部带有一定转折性的作品,也为电视剧回归短剧集时代提供了可参照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