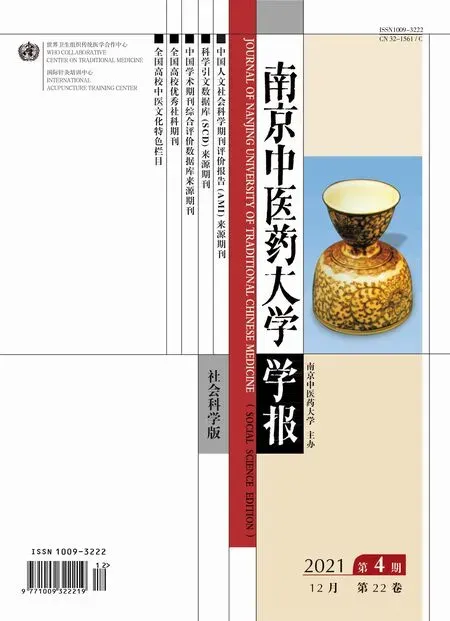中古医籍禁咒方语言特征探析
戚端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中医和巫祝历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医演进的过程,始而近巫,继而巫医结合,最终走向巫医分立,自始至终与巫祝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中医的特点,也是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初级阶段的普遍特点。
通过对我国历代医籍的梳理,不难发现,在中古时期的医方著作中禁咒方出现的频率最高,其内容之多、分类之细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医学的理性尚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取缔禁咒方在医事活动中的地位,而巫医理论经孙思邈等著名医林人士的整理,渐至成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已然成为中古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禁咒方的语言往往晦涩难懂,充满神秘色彩,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阶段医方著作中出现的禁咒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析,以期掌握禁咒方语言的一些规律。
英国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在《人文类型》一书中说:“在巫术的施行过程中通常有三个要素:所用的东西,所做的举动,所说的话。第一类要素是工具或丹药,第二个要素是仪式,第三个要素是咒语。”[1]我们将其所说的第一类要素以及巫方病名共称之为涉巫的“物”,将第二类要素及相关动作等称之为涉巫的“式”,将第三类称之为巫方中的“语”。在整个巫术活动中,最主观、最基本的要素是“语”,即咒语,同时它也是巫术活动的核心,因为“永远有字眼说出来或者唱出来”。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巫术的力量就是咒语的力量,而咒语的魔力是出自于人类对语言的崇拜,禁咒语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人为的、特殊的语言形式。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是从一般语言中分化出来的,在人们的口中成为一种具有“魔力”的语言,造成这种差异的缘由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人们给语言以神圣的框架[2]。
这种特殊的语言具有不同于一般医学典籍语言的特色,常常令人感觉佶屈聱牙。造成这种困扰的原因在于“从语义的角度来看,迷信一类的词语,反映了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相信语言有灵、威力无比的语言崇拜倾向,常与禁忌义、附加义、隐语义有关,利用义位之间不确定的关系,制造一些另类的词语来达到夸张语义功能的效果。因此迷信用语除了借用社会用语赋予新异的意义外,总是能翻造出一些新的词语来。”[3]
从宏观上把握禁咒语的这些特点,有利于我们理解其含义,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阅读时遇到的诸多文本校勘问题。通过对中古医籍中禁咒方的语言进行整体梳理和分析,其语言特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 较强的传承性和稳固性
禁咒语系统是一个较为封闭的语言特殊变体系统,其使用者少,使用范围小,因此从其用词的历时情况来看,一些出自上古传世医籍及出土简帛文献资料中的禁咒语词,在中古医书中仍然继续沿用,具有较强的传承性和稳固性。如以下2例:
(1)禹步
“禹步”一词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其中载有除道巫方,施术者在行除道仪式中要连行三个“禹步”,在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甲种《日书》中也有类似的除道仪式。在上古出土简帛医籍中“禹步”一词常见,如在周家台30号出土医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以及张家山汉墓医简《引书》中都有记载。“禹步”是古代道士作法时的一种特殊步法,此步法在中古医书禁咒方中仍然较为常见。如《千金翼方》卷二十九:“若欲受符印者,以帛若袋子盛挂著左手指勾之,而擎水盆,闭气禹步,依法次第咒请,有效也。”[4]726《千金翼方》卷三十:“太一神人曰:凡欲远行、避难、若为恶人迫逐危厄之中,出门禹步三,呪乃去,可以消灾。”[4]745
(2)画地
“画地”一词,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盗者篇》的一条行禁方。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的“治出血方”中亦见。“画地”是古代巫术仪式中常见的词语,具体又包括五画地(午画地)、直五横和周画地等形式,一般是在施术者念完咒语之后,再以特殊的工具施以画地的仪式。该词在中古的医书禁咒方中仍然沿用,较为多见。如《肘后备急方》卷一:“以其人置地,利刀画地,从肩起,男左女右,令周面以刀锋刻病患鼻,……乃以指灭向所画地,当肩头数寸,令得去,不可不具诘问之也。”[5]129《千金翼方》卷二十九:“若治之,须在净处平地以手小指画地作鬼字,口中阴道病人生时年月日、姓名,以砖覆之,勿令知之,至三七日不开,永差。”[4]728《本草拾遗》卷三:“人卒患心痛,画地作五字,以撮取中央土,水和一升,绞,服之,良也。”[6]另在敦煌卷子P.2661《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中,载有事急迫外出不能择选良日,可画地作“五纵六横”或“四纵五横”并配合咒语的方法:“凡人欲急,不择日而出大门,画地五纵六横,一云四纵五横。”
诸如此类行巫步法和画地作法的具体操作方式,在后代的一些数术类文献中记载颇详,如《增补玉匣记》《类编历法通书大全》等,包括明清以后的本草、方书中皆有所征引。与之相类的还有一些特殊的禁咒词汇,如“诺皋”作为禁咒语的起始发语词放在禁咒语的开头,用以招魂或求助神灵;再如“唾”,一般是配合巫术进行前后所使用的一个动词,用以表示对鬼神和疾病的厌弃。这些特殊的禁咒词汇,一般都是沿用自上古的典籍。这既说明了这些巫术形式是渊源有自的,同时也说明了禁咒语系统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语言特殊变体系统,其词汇具有较强的稳固性和传承性。
2 语言讲究节律,简单押韵
禁咒用语为了体现神秘色彩,造句讲求节律,简单押韵,虽然理解起来较为晦涩,但读起来通常比较顺畅。这一方面是为了烘托气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便于记忆。正如蒙古族的萨满咒语能熟练地运用蒙古族诗歌的押头韵、押脚韵和叠句等基本技巧,具备一定的文学传统性,因此有学者认为萨满咒语是蒙古族民间文学最古老、最朴素的一种韵文题材,是蒙古民间歌谣的源头和雏形[7]。医书中的禁咒语也是如此,以下这段咒文的内容,就明显追求节律,“咒法发日执一石于水滨,一气咒云:‘眢眢圆圆,行路非难,捉取疟鬼,送与河官,急急如律令。’投于水,不得回顾。”[5]145其中,“难”“官”同属于元部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再如:“欲理发,向王地,既栉发之始,叩齿九通,而微咒曰:‘太帝散灵,五老返真,泥丸玄华,保精长存。左拘隐月,右引日根,六合清炼,百神受恩。’咒毕,咽唾三过。能常行之,发不落而生。”[8]329其中“真”“存”“根”“恩”韵部同归真韵,读起来十分通畅。
有一些禁咒用语的内容比较晦涩难懂,句读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果从同韵的角度出发,我们便可以顺利解决。如:“若有水者,卒无器,便与左手贮,祝曰:丞掾吏之赐,真乏粮,正赤黄行无过,城下诸医以自防。毕,三叩齿,右手指三叩左手,如此三遍,便饮之。”此段涉及禁咒语的内容最早见于《肘后备急方》,后世各类文献都有转引,但断句均存在分歧,目前主要有以下四种断句方式:①“祝曰:丞掾吏之赐,真乏粮,正赤黄行无过,城下诸医以自防。”[9]②“祝曰:丞掾吏之赐,真乏粮,正赤黄行,无过城下诸医,以自防。”[10]③“祝曰:承掾吏之赐,真乏粮,正赤黄行,无过城下,诸医以自防。”[11]④“祝曰:丞椽吏之赐真乏粮,正赤黄行无过城下,诸医以自防。”[12]从禁咒语追求押韵的特征出发,我们首先可以推断句④(出自《增补辨证方药合编》)不符合咒语句型简单、追求押韵的语言特点,应该是错误的。此段文字意义模糊,较难理解,疑有残缺,其异文见唐司马祯《修真精义杂论》,文字稍有不同,“真乏粮”在《修真精义杂论》中作“神人之粮”,义似可从。竖排“人之”与“乏”字形体形近易混。“真乏粮”极可能就是“真人之粮”。又据文意,此段咒语的用法是以水为粮,将水以咒法化作粮食,并不是说缺乏粮食,而是以水为“真人之粮”,此粮又承椽吏(即掾吏)所赐而得,文义则通。
又文中“正赤黄行”不辞,当于“行”前点断,“正赤黄”即“日色”。道家认为“正赤黄”的颜色代表了中正之色,是太阳光的象征。“正赤黄”与下文“行无过”三字格对仗,“黄”“粮”“防”三字押阳韵,读起来符合禁咒语的语言特点。综上所述,从词义和押韵的要求出发,结合异文的情况,此段咒语当校读为:“咒曰:承椽吏之赐,真人之粮,正赤黄,行无过城下,诸医以自防。”
3 俚芜杂陈,缺少润饰
黑格尔认为,巫术是宗教的早期形式,具备原始宗教的雏形[13]。这种宗教的早期形式,就其产生之源来说,多出自民间,信众也以民间居多。禁咒语作为巫术的主要表现手段,通常需要通过口头传诵,即使是密咒,也需要在心中默念,因此它的内容形式追求俚俗化,即便是存在一些故弄玄虚的成分,但也多半是简明扼要的,多用短句,体现命令性的口吻。如《史记·殷本纪》:“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天下四方,皆入吾网。’”[14]这是商汤在向鸟兽发出咒语命令,带有不可违逆的口吻,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直接支配。再如民间广为流传的治孩童啼哭不止的咒语:“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咒语本身大多数属于封建迷信的范畴,内容缺乏科学依据,来源出自凭空捏造和个人联想。
原始形态的咒语源自巫祝活动的语言灵力崇拜,因此为了使之具备一定的神秘色彩和神圣性,禁咒的内容也往往掺入了一些固有的文化因素,如《肘后备急方》卷七:“凡猛兽毒虫皆受人禁气,将入山草,宜先禁之,其经术云:到山下先闭气三十五息,存神仙将虎来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把虎两目塞,吾下部又乃吐肺气,白通冠一山林之上。于是良久,又闭气三十五息。两手捻都监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图汝非李耳耶,汝盗黄帝之犬,黄帝教我问汝,汝答之云何。’毕便行,一山之虎不可得见。若逢之者,目向立,大张左手,五指侧之,极势跳,手上下三度,于跳中大唤咄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5]211此段咒文的内容是禁经中的辟虎法,后世较多转录,孙思邈将其录入《千金要方·禁虎法》中。这段咒文内容荒诞离奇,既涉及历史上的名人李耳,又提到了黄帝以及道家天神北斗星君,可谓极为杂芜。需要注意的是,咒语保留了当时当地方言的特色,即将虎称作“李耳”。此说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方言》卷八:“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郭璞注曰:“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触其讳故。”[15]应劭《风俗通义》谓:“南郡李翁化为虎,故呼李耳。”[16]郭璞和应劭的说法显然均是错误的,明方以智证以音转之说,《通雅》卷四十六:“或曰狸儿,转为李耳。”[17]其说似可从,即老虎俗称“狸儿”,其音与“李耳”相近。
禁咒语从内容上来看往往杂乱无章,前后缺乏逻辑性,其创作的过程便具备很强的随意性,语言很少润饰。在一种咒语形成之后又具备固定性——使用内部传承的特定词语组合,不随意改变更替。这一特点也进一步促使它在形成之后几乎不会得到润饰,人们即使不明白它的意思也要照样诵读,这就使得它变成了一种机械僵化的语言。有一些存在校勘问题的,如文字脱讹、句读不当的,则更难理解,如《诸病源候论》卷二十八:“《养生方·导引法》云:鸡鸣欲起,先屈左手啖盐指,以指相摩,咒曰:‘西王母女,名曰益愈,赐我目,受之于口。’即精摩形。常鸡鸣二七着唾,除目茫茫,致其精光,彻视万里,遍见四方。咽二七唾之,以热指摩目二七,令人目不瞑。”[8]563
此段咒文文义明显不通,何谓“赐我目,受之于口”?据前文所言,禁咒语的内容讲究四字格押韵,故疑文中有脱字。今查各本《诸病源候论》均无异文,后世医书转引也多沿此讹,但据正统道藏本《洞玄灵宝真人修行延年益算法》其文作“赐我目药”。又“常鸡鸣二七着唾”文义亦不通,当据该书于“鸡鸣”前补一“在”字。而“即精摩形”至“遍见四方”是伴随禁咒所施行的相关动作。据此原文当校为:“鸡鸣欲起,先屈左手啖盐指,以指相摩,咒曰‘西王母女,名曰益愈,赐我目药,受之于口。’即精摩形,常在鸡鸣,二七着唾,除目茫茫,致其精光,彻视万里,遍见四方。咽二七唾之,以热指摩目二七,令人目不瞑。”
由上可见,短短的一段禁咒方,错误居然这么多,除了文献传抄本身的原因,还因禁咒文本身意义就存在模糊性,很多内容出自个人妄造和臆想,又有一些故弄玄虚的成分,因此后人在校勘的时候也很难发现和校正。
4 言语回环,惯用重叠
巫祝认为语言能支配自然物,从而获得特殊的力量,这种对语言魔力的崇拜使其在创作禁咒语时追求语言和心理的印证,以尽量多的手段给人带来心理暗示。恰托巴底亚耶在《印度哲学》一书中说:“巫术依据这样的原则,即通过造成你控制现实的幻觉,你就真的能控制现实,在它的初级阶段,它就是简单的模拟术。”[18]有实验表明,和谐的节奏能刺激大脑皮层,留下兴奋的痕迹,而不停地重复、持续的节奏刺激可能是咒语引发宗教体验的原因之一[19]。为了达到心理暗示的目的,往往需要叠加使用相同的语音符号。而重叠的词和重叠的音节反复诵读,也能烘托一种神圣的气氛,是语音的一种力量体现,这与法语的一些歌剧惯用颤音作为韵脚以烘托恐怖气氛道理类似。中古禁咒方中惯用重叠词,有一些重叠词是拟声的,如“隆隆鬼鬼”是模拟雷声的:“又当存作大雷电,隆隆鬼鬼,走入腹中,为之不止,病自除矣。”[8]23
而有一些禁咒方中的重叠词纯粹是为了凑足音节,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具体意义,如:“咒法发日执一石于水滨,一气咒云:‘眢眢圆圆,行路非难,捉取疟鬼,送与河官,急急如律令。’投于水,不得回顾。”[5]40“眢眢圆圆”是这段咒语的起始语,没有具体意义,《外台秘要》作“眢眢团团”,《串雅》作“冤冤圆圆”,可见仅仅是语音相同,符合押韵的条件,凑足四字格。
禁咒方有时候需要特殊发声,称为“嘘”或“啸”,或是模仿动物的声音,有时是直接借助动物发声,如:“禳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4]34此则是以雄鸡发声作啸法,又如:“华佗禁方令病患自用手两指,擘所患眼。垂空咒之曰:‘疋疋,屋舍狭窄,不容宿客。’即出也。”[5]154“疋疋”即是啸法的一种。唐代孙广在《啸旨》一书中说:“天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而清,谓之啸。言之浊,可以通人事,达性情;啸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盖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出其啸善,万灵受职,斯古之学道者哉!”[20]此书分啸有十二法:外激、内激、含、藏、散、越、大沈、小沈、疋、叱、五太、五少。其中论及“疋疋”也是啸法的一种,其音或同于“呸呸”,并无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禁咒方是中古医籍中的重要内容,而禁咒语作为行业语体的一种,其词汇体系一部分来自于行业自造,更多则来自于在全民用语基础上的改造和创新。相较于一般的医籍语言,禁咒语具有独特的语言特征,其遣词造句具有一些特殊规律,掌握这些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