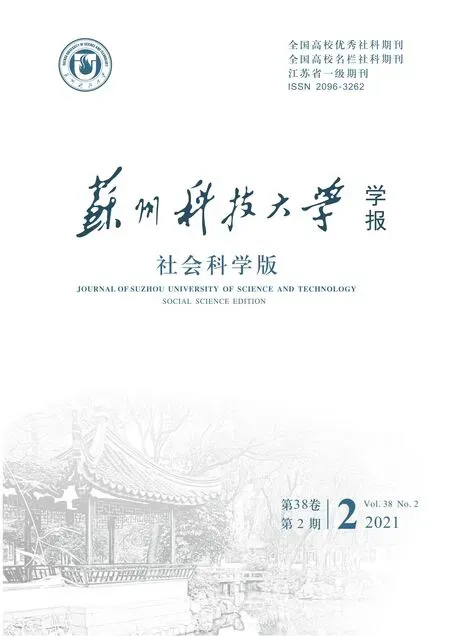逃避自由?*
——也说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逃离》
王秋实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加拿大短篇小说作家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31-)迄今为止一共出版了十四部短篇小说集,20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她被公认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门罗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一个名叫温厄姆的小镇,她的大部分作品的背景都以自己的家乡为原型,主要人物也大多是小镇女性,作品讲述了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在许多作品中,女主人公以“离开”来对抗封闭和压抑的生活环境,于是,“逃离”成为贯穿门罗作品的重要主题。这一主题以最为直接的方式标示在其短篇小说的题目《逃离》(“Runaway”)之中。
短篇小说《逃离》是门罗小说集《逃离》(Runaway, 2004)的首篇,讲述的是小镇女人卡拉在邻居西尔维亚的支持和帮助之下试图逃离丈夫的故事。由于卡拉中途放弃逃离计划、回到丈夫身边,小说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异常难解的谜,令人唏嘘不已。门罗在小说《逃离》中到底要表达怎样的意旨?主人公卡拉究竟为什么在决定逃离之后又反悔?针对这些问题,批评界从女性主义、叙事学、心理分析、事件理论等角度进行过不同的解释。在女性主义研究方面,朱晓映认为,小说家门罗将自己“离开”与“回归”的经历复现在小说人物卡拉与西尔维亚身上,讲述了女性如何通过逃离进行自我探索的故事[1];菲奥娜·托兰(Fiona Tolan)将女性主题与叙事研究相结合,认为卡拉逃离父母和逃离丈夫的行为分别反映了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追求,二者均以失败告终,小说最后暗示两种追求相结合才是女性寻求自由的出路。[2]在心理分析研究方面,拉赫雷·巴哈德(Raheleh Bahador )和伊斯梅尔·佐迪(Esmaeil Zohdi)运用克里斯蒂瓦的“卑贱”(abjection)概念,认为卑贱一方面引诱卡拉通过逃离丈夫冲破男权主义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致使其主体性面临被破坏的威胁,令卡拉最终不得不放弃逃离计划[3]。丁心怡从事件理论角度对卡拉先后逃离父母、逃离丈夫、逃离丈夫而复归(即“对逃离的逃离”)进行评述,认为女主人公在这三次逃离中都因缺乏智慧与勇气而未能完成真正的事件性逃离[4]。笔者认为,学界对于《逃离》的上述解读大多围绕卡拉逃离丈夫这一核心情节,为读者深入理解作品提供了有益的指导。然而,卡拉中途放弃了逃离计划,未能抵达逃离的目的地,意味着卡拉同时放弃了目的地所象征的独立与自由。卡拉为什么会放弃唾手可得的自由?对于这个问题,批评界似乎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卡拉渴望自由,所以唯有对她貌似放弃自由的行为进行分析,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这部作品。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卡拉先后放弃前往多伦多的计划、背弃西尔维亚提供的友情支持,以及刻意忘却失踪的小羊弗洛拉这三个行为,揭示这部作品所展现的当代女性向往自由而不得的无奈困境。
一、放弃多伦多
卡拉中途放弃前往多伦多的计划是《逃离》中最令人不解的核心情节,因为在上车前,是卡拉向西尔维亚哭诉自己如何无法忍受丈夫,如何渴望自由。在交流良久之后,西尔维亚才决定伸出援手,出钱备物,联系多伦多的朋友,以便帮助卡拉从她现实的困难中尽快逃脱出来,去多伦多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卡拉中途放弃这一计划是她个人意志的改变,亦是对于全力帮助自己的西尔维亚的一次重大背叛,是对自己逃离的一次逃离。读者有理由质问:卡拉的心理为什么会在逃离途中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也许卡拉的逃离,并不像西尔维亚所理解的那样是为了摆脱粗鲁霸道的丈夫,追寻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幸福;或者说,并不单纯是这样。
卡拉和西尔维亚都是女性,在她们之间有着毋庸置疑的共同点。但是,小说《逃离》通过卡拉逃离途中的改变,让我们看到她们之间的错位和差距。
卡拉高中毕业之后和克拉克私奔到一个小镇,夫妻俩经营着一个小型的马场。一辆活动房车,一个马厩,一个环形练习跑道,四匹马,一只小山羊,就是二人的全部家当。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教人骑马,另外一些收益来自照看寄养在这里的三匹马,马场的工具和材料要在二手货商店里淘,日子过得很拮据。卡拉勤劳能干,喜欢动物和乡间生活。然而丈夫克拉克暴躁、蛮横、很不讲理,经常与人争吵,动辄大打出手。与卡拉夫妻截然不同,西尔维亚家生活优渥。西尔维亚在大学教授植物学;丈夫贾米森生前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建造了一栋造型别致的房子,还将家门口的小路修得整齐干净。贾米森夫妇二人常在小路上“散步,寻野兰花。她告诉他每一种野花的名字……他称她为他的多萝西·华兹华斯”[5]29。贾米森病重以后,西尔维亚雇卡拉过来打扫卫生,二人之间虽然有了更多交集,但不同阶层间的反差更加直观地体现出来:卡拉一想到行将就木的病人就感到害怕,并不愿意去贾米森家,但是“她需要这笔收入”[5]15;西尔维亚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去希腊散心,而卡拉连逃离小镇去往多伦多的车票钱都没有;西尔维亚为卡拉从希腊带回了著名雕塑《马与骑师》的复制品作礼物,即便是复制品,“这个雕像的价格也是卡拉所不能想象的”[5]20。
生活宽裕的西尔维亚完全不能想象天气状况会对家庭经济乃至夫妻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对她来说,连绵的阴雨仅仅意味着影响开车路况。但对于卡拉夫妻俩来说,这样的天气让二人本就困窘的生活雪上加霜:环形跑道上形成一大片积水,上方的塑料顶棚也遭到了损坏。他们去年夏天是靠教成群结队来这里过夏令营的孩子们维持生计的,而现在就连一些老学员都取消了课程。遇到这样的雨天,丈夫克拉克情绪不好,“连带整个屋子都气氛沉重,他不想操心任何事,只盯着电脑屏幕”[5]9。虽然卡拉为了摆脱这样的氛围跑到马厩找事情做,但是就连马和羊都能感到她的不开心。
卡拉为了活跃家庭气氛和改善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做了各种尝试,甚至跟克拉克说贾米森先生如何趁西尔维亚不在的时候勾引自己,试图用这样的夫妻夜话增添二人间的情趣。后来贾米森先生过世,两人看到讣告,得知他生前曾获得过诗歌领域的大奖,克拉克便日日盘算着如何用贾米森先生的不轨行为去向西尔维亚索要封口费。对于这件事情,无论卡拉如何劝阻,克拉克都不愿改变自己的计划,甚至越发较真起来,连要多少钱、夫妻俩要如何配合都计划好了,三番五次催促卡拉行动。然而,关于贾米森先生的所谓不堪举动都是卡拉编出来的,她甚至连贾米森先生的房间都没有进去过。利用这样一个垂危老人编一些床笫之语确实有些卑劣,但是,卡拉眼看着曾经与丈夫之间的爱火渐渐磨灭,实在太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够重燃二人之间的激情了。自己的苦心反被丈夫用作对他人的敲诈,这让卡拉感到窘迫与绝望。
卡拉所经受的这一切是不能与西尔维亚诉说的,也不是西尔维亚所能体会的,西尔维亚基于自己的社会阶层为卡拉提供的方案或许太过简单。卡拉的痛苦来自经济、天气、情感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她的生活离不开这些因素,她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然是她的丈夫克拉克。卡拉在大巴车上陷入了对自己生活的回忆,忆起当初她如何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与克拉克私奔,“把他看作二人未来生活的设计师,她自己则心甘情愿地做他的俘虏”[5]32。正如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TheSecondSex)一书中所揭示的,女性难以兼顾“个人独立”与传统父权制度下的“女性命运”,相较于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屈从要容易得多[6]。当卡拉乘着大巴车与过往的生活渐行渐远,她越发意识到,尽管克拉克粗鲁蛮横,对待自己毫无关心和体贴,却是“她生活的中心”[2]164。她坚信自己根本离不开丈夫,因为离开了他,她的生活便失去了意义。她突然感到这趟多伦多之行并不是西尔维亚所描绘的那条通往独立自由的解放之路,而是放弃或者丧失自己唯一生活意义的迷途。想到这里,她颤抖不已,用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下车,匆匆结束了这趟不属于自己的逃离之旅。
二、背弃西尔维亚
小说《逃离》的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卡拉烧毁西尔维亚的来信。卡拉折返回家之后的一天,在信箱中发现了西尔维亚给她的来信。在信中,西尔维亚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西尔维亚“恐怕过多地介入了卡拉的生活,错误地认为卡拉的幸福和自由是一回事。她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卡拉的幸福,而现在看来,卡拉要在婚姻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她只希望,卡拉这次的出走和情绪波动能够让她自己的真实情感得以展现,或许让卡拉的丈夫也能认识到他自己的真实情感”[5]44。很显然,尽管卡拉放弃逃离计划是对西尔维亚的重大背叛,但西尔维亚仍然带着长者对年轻一代的关爱与包容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
然而,看了这样一封充满善意和友情的来信,卡拉没有感动,相反,她毫不犹豫地将西尔维亚的信付之一炬:“卡拉刚读完这封信,便把信揉作一团,在水槽里烧掉了。火苗烧得有点大,她赶紧拧开水龙头把火浇灭,然后把软塌塌、有些恶心的黑色残渣倒进厕所冲掉了。”[5]46有学者将卡拉此举解释为对西尔维亚干涉自我空间的抗议[7]84。笔者认为,卡拉的举动来自她更深层的忧虑。
门罗最常书写的主题是母女关系。[8]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门罗许多作品所聚焦的是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在小说《逃离》中,除卡拉跟自己母亲的关系之外,西尔维亚和卡拉在年龄上如同母女,西尔维亚亦将自己对卡拉的喜爱称为一种“移位的母爱”[5]21。作为经历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的女知识分子,西尔维亚同时将年轻的卡拉看成需要帮助的“姐妹”。曾经的女权斗争的经验告诉她,女性的自由和解放有赖于女性之间的“团结”(solidarity)和“姐妹情谊”(sisterhood),女性应联合起来、团结互助。小说中的西尔维亚面对丈夫病重直至去世一度感到“痛苦而恍惚”[5]15,于是向自己的女性朋友寻求帮助和慰藉:她在卡拉的帮助下清理房屋,在玛吉和索拉雅的陪伴下旅行散心,最终从阴霾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新的生活。西尔维亚听完卡拉的故事之后,知道了卡拉对于丈夫的不满,便决定出手相助。在西尔维亚看来,女性遭受的父权压迫具有普遍性,女性应团结在一起,共同反抗压迫、争取自由。她认为卡拉逃离大男子主义的丈夫,正是在挣脱婚姻的枷锁,寻求自由解放。于是,西尔维亚以“姐妹”自居,不仅为卡拉提供金钱和衣物,联系自己在多伦多的朋友为其提供容身之所,更是在精神和思想上对卡拉进行鼓励和引导:
“那好,”西尔维亚说,“现在听听我的建议。我认为你不该住在汽车旅馆,你应该坐车到多伦多去住在我一个朋友那儿。她叫露丝·斯泰尔斯,有一个大房子,她自己住,不会介意有人一块住的。在你找到工作之前可以一直住在那儿。我会给你一些钱。多伦多附近一定有很多马场。”[5]24
西尔维亚全方位的支持令卡拉感到“她的逃离似乎是最合理的做法,事实上,也是身在卡拉这种处境中的人所能做的最有自尊的事”[5]31。
然而,西尔维亚的揣测和干预所体现的正是第二次女性解放浪潮的局限,即认为女性主义运动举世相类。但是她不知道,时过境迁,到20世纪末,当又一代年轻的女性成长起来之后,她们面对的虽然仍有母亲一代经历的问题,可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处境给她们中的每一个人带来了各自不同的问题。年轻一代女性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压迫,她们渴望自由,但又做不了听从前辈们建议的“乖女儿”[9],因为她们在向往自由的同时面临着较之前辈女性更严酷的现实环境,“母亲们”所倡导的女性主义并不能解决她们自己面临的问题。正如耿力平所说:“女权主义不恰当的介入不仅不能帮助女性提高觉悟,反倒证明自身不能适应新时代妇女的实际需求。”[10]
作为老一代的女性主义者,西尔维亚在观察卡拉的生活时,或许不难想象卡拉作为一个下层阶级、没有受过多少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的现实境遇。但是,她忽略了那个差点对她动粗的野蛮男人——卡拉的丈夫克拉克。这个脾气暴躁的男人显然没有听说过什么妇女解放,曾经的女权运动对他没有产生过丝毫的正面影响。卡拉返回家当晚,克拉克就跑到西尔维亚处兴师问罪:
“我来是要告诉你,我不喜欢你干涉我和我老婆的生活。”
“她是个活生生的人,”西尔维亚说,虽然她知道自己最好不要发话,“她不光是你的妻子。”
“我的天啊,是吗?我老婆是个人呢,真的吗?多谢提醒啊。不要跟我耍聪明,西尔维亚。”[5]38
克拉克还要求西尔维亚向他道歉,并把手放在门框上,阻止西尔维亚关门。两人间的气氛一度非常紧张,如果不是小山羊弗洛拉的突然出现为西尔维亚解了围,事情很可能难以收场。卡拉看了西尔维亚的信之后深切地感觉到,如果这样的来信被克拉克发现,让他看到自己与西尔维亚继续保持着联系,那么自己和西尔维亚两人都将陷于危险之中。烧掉来信从表面上看是彻底背弃西尔维亚,实质上,卡拉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秘密的举动在危险的婚姻生活之中获得暂时的自保,也是对西尔维亚的保护。
三、忘却弗洛拉
《逃离》中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是卡拉喜爱的小山羊弗洛拉在小说结尾时的再次消失。弗洛拉是卡拉和克拉克一起养的小山羊,在小说开始时曾经神奇地失踪过一次,令卡拉惦念不已。就在卡拉逃离折返、丈夫克拉克满怀恶意地找西尔维亚算账的时刻,弗洛拉突然出现,化解了一场严重的邻里危机。西尔维亚深受触动,在写给卡拉的信中,激动地称弗洛拉是“最美好的事物”[5]45,是她“人生中的天使”[5]46。
在小说中,弗洛拉聪敏伶俐,它被赋予了某种人性,这种人性体现在它与卡拉充满象征意义的密切关系中。首先,弗洛拉在外貌上与卡拉有着相似之处:卡拉头顶的碎发像“蒲公英”一样[5]17,而当失踪多年的弗洛拉突然从雾中显现,形态也好似一团“蒲公英”[5]39。其次,弗洛拉和马儿们不同,不会让卡拉感到作为主人的“优越感”[5]9,而更像是卡拉的知心朋友。当卡拉心情低落时,弗洛拉会带着揶揄的神情凑过来以示安慰;卡拉与克拉克的感情由炽热变得黯淡,而弗洛拉对克拉克也由亲昵变得疏远;卡拉放弃逃离计划回家后,对西尔维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而弗洛拉面对西尔维亚的抚摸也表现出某种抵触。当然,弗洛拉与卡拉最重要的契合之处莫过于二者都经历了“离开”与“归来”的过程,用景芳洲的话说,弗洛拉的失踪和出现构成与卡拉逃离和回归并行的另一条线索[11]。可以说,小说中的弗洛拉与卡拉命运与共,很多时候成了卡拉化身般的存在。
然而,这样一只天使般的小羊归来不久却再次消失。卡拉怀疑弗洛拉这次消失是被心胸狭隘的克拉克杀掉了:
她只需抬眼朝一个方向望去,便知道要去哪里。……在树林一隅的枯树旁,聚集着成群的秃鹫。
她就会看到草丛里那一小片血迹斑斑的骨头。……那个小小的头盖骨,她能像握一只茶杯一样握在手中。真相便也将被握在手中。[5]47
这份怀疑让卡拉感到“她的肺里仿佛有一根致命的针,呼吸小心一些,就感觉不到它。但是当她需要深吸一口气,就能感觉到那根针依然在那里”[5]46。弗洛拉的消失对卡拉来说无疑是不祥之兆,因为她从弗洛拉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正如科琳·比戈(Corinne Bigot)所言,卡拉此时“意识到自己的逃离计划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12]。面对如此的险境,卡拉决定忘却弗洛拉,放弃自己对于这个挚友般的小羊的牵挂。因为她感觉到,唯有如此,才能在危险的婚姻之中得以生存。正像内奥米·摩根斯坦(Naomi Morgenstern)所指出的,小说《逃离》讲述了一个女性在凶狠暴力、心理极端的男性身边设法生存的故事[13]。
1941年,德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出版了他的名作《逃避自由》(EscapefromFreedom)。在该书中,他讨论了现代人深陷自由与孤独并存的矛盾与困境。面对难以忍受的孤独感与无力感,人们有时无奈地选择逃避自由。在门罗的《逃离》中,面对实现自由的目的地多伦多、帮助自己争取自由的西尔维亚以及追求自由的践行者弗洛拉,卡拉最终都选择了逃离。这种逃离并不是因为卡拉不知道自由的珍贵与美好,而是囿于自身复杂甚至危险的处境,充满了深切的无奈和苦闷:克拉克继承了传统男权的一切恶劣品质,粗鲁蛮横,但这就是卡拉曾经离开家人选择的丈夫,在并没有强大自我意识的卡拉心中,克拉克“占据着重要的位置”[5]34,离开了丈夫,卡拉感到自己失去了生活的中心和方向;虽然身边有西尔维亚这样的老一辈女性向卡拉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但她们从自身的经验和视角出发,无法理解卡拉处境的艰难和危险;小山羊弗洛拉是整个故事中唯一与卡拉有着精神契合的存在,却成了她追寻自由之路上的殉道者,粗暴的男权让卡拉面对自由而以无奈作罢。
门罗通过卡拉这一现代女性“逃避”自由的故事向读者表明,距离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女性仍然面临着诸多压迫和困境。而以西尔维亚为代表的老一代女性主义者,基于自身的经验和视角提出的“自由即幸福”方案,对以卡拉为代表的女性来说并非总是行得通。新一代女性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虽然有了前辈争取自由的经验可以汲取,有时甚至还有前辈直接出面慷慨相助,但是,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关于男女平等的思想并没有在整个西方社会中得到弘扬。特别是在众多社会底层的男性眼中,女人仍旧是女人,男人仍旧是世界的主宰。新时代的女性心中再有自由的理想,面对如此无知凶狠的男性,依然无比无奈。较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前辈们,她们或许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困难,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令当代女性不得不面对自由望而却步。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揭示的,现代人虽然摆脱了种种传统束缚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积极自由[14]viii。同样,现代女性在20世纪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后仍远没有解决自己的自由问题。面对未完的追寻自由之路,弗洛姆勉励现代人须再接再厉,继续为自由的实现而奋斗[14]303。门罗则在小说的最后,以卡拉抵抗着“持续的、浅藏的诱惑”[5]47,既精妙地表现了女性面对粗暴男权的无奈退却,同时希冀女性同胞终将在沉默中觉醒,在退却中积蓄力量,迈出新的一步。女性的自由与幸福不是一两次“逃离”就能够实现的;而是有赖于对每一个人具体的生活情景的关注,也有赖于两性之间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有时还有赖于女性团结起来做出更多的斗争。门罗用自己的小说提出了问题,也为解决问题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艾丽斯·门罗《逃离》中弗洛拉的意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