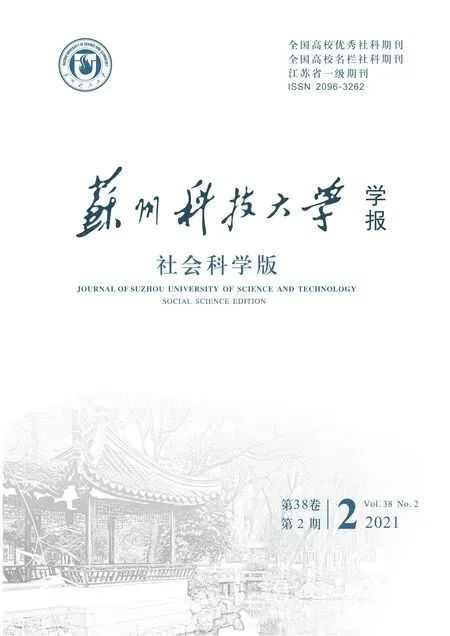马瑞·贝尔的反现实主义叙事*
陈振娇
(苏州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马瑞·贝尔(Murray Bail, 1941-)是澳大利亚重要的“新派”作家之一。他生于阿德莱德,曾旅居孟买两年(1968—1970年),后移居伦敦(1970—1974年)。在伦敦期间,他为《跨大西洋评论》(TransatlanticReview)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LiterarySupplement)撰稿;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文学期刊《西风》(Westerly)上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回到澳大利亚以后,他与其他“新派”作家一样居住在悉尼的巴尔门区。他著述甚丰,短篇小说代表作《当代画像和其它小说》(“Contemporary Portraits and Other Stories”, 1975)好评如潮,奠定了他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中的地位。198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乡愁》(Homesickness)出版,获得“国家图书协会奖”(National Book Council Award)。此后,他接连创作了《霍尔登的表现》(Holden’sPerformance, 1987)、《普通书写:一位作家的手记》(Longhand:AWriter’sNotebook, 1989)、《桉树》(Eucalyptus, 1998)和《书稿》(ThePages, 2008)等长篇小说。1999年,《桉树》荣获多项大奖,其中包括“迈尔斯·弗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和“英联邦作家奖”(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贝尔的文学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此外,贝尔还编辑了一本关于画家伊恩·费尔韦瑟(Ian Fairweather)(1)伊恩·费尔韦瑟(1891—1974),生于苏格兰,是澳大利亚著名画家,受到同行的尊敬。他的作品受到欧洲现代主义、后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影响。后来他在亚洲隐居,20世纪30年代他住在上海和北京,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开创了高度个性化而又独特的线性风格。他的作品与众不同,是一位少有的、能在东方书法传统与西方绘画之间架起桥梁的现代画家。的文集,可见他对视觉艺术的浓厚兴趣。
贝尔受到批评家的高度认可。澳大利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布莱恩·基尔南(Brian Kiernan, 1937-)从众多的“新派”作家(2)20世纪7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文坛涌现了一批无视文学传统、刻意标新立异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与此前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大相径庭。他们将目光从本土作家中移开,转向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作家,主张冲破本土文学的限制,创立一种富有国际色彩的文学。中精心挑选出五位,其中包括弗兰克·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 1938-)、麦克尔·怀尔丁(Michael Wilding, 1942-)、彼得·凯里(Peter Carey, 1943-)、莫里斯·鲁里(Morris Lurie, 1938-2014)以及马瑞·贝尔。[1]贝尔从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新派”作家中的佼佼者。贝尔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共有三部:《当代画像与其它小说》(ContemporaryPortraitsandOtherStories,1975)、《赶牲畜人的妻子与其它小说》(TheDrover’sWifeandOtherStories,1998)以及《伪装与其它小说》(CamouflageandOtherStories,2003)。《当代画像和其它小说》是贝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汇集了他的精华之作,共收录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充斥着荒诞与超现实。作者在作品中表达了他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其中,《许布勒》(“Huebler”)、《26个英文字母》(“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和《赶牲畜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最具代表性,笔者通过分析这三篇小说的叙事手法和特征来透视贝尔的反现实主义创作观。
一、视觉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视觉艺术与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20世纪的许多文艺思潮都与视觉艺术息息相关。贝尔从视觉艺术的角度来观察现实和现实主义,从而对现实主义有着更加独特的理解,《许布勒》就是这方面的杰作。《许布勒》是小说集的首篇,小说中大量的人物画像与小说集的名称遥相呼应。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许布勒曾扬言要真实地再现人们的生存状态,叙事者“我”对许布勒的“雄心壮志”兴趣甚浓,于是推荐了23个人物供他参考。小说中提到的许布勒历史上确有其人,即美国著名的概念画家道格拉斯·许布勒(Douglas Huebler, 1924-1997),小说开篇写道:
有些人刻意避免别人的帮助,我认为道格拉斯·许布勒也属于这类人。至今为止,各种各样伸向他的“触角”都遭到了他的拒绝。看来,许布勒决定独自前行了。
1972年10月,他在巴黎艺术馆的展览上发了一个声明。
他声称,决心要用图画记录每一位世人的生存状况。
等一下。我们来理解一下。
他这样做,是为了能最真实地再现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人的生存状态。[2]3
“我”对许布勒的想法兴趣颇浓,于是用文字给每个人物写了一个“画像”,并决定“把这些‘画像’交给许布勒,助他一臂之力,管他喜欢不喜欢”[2]4。“我”推荐的23个人中有英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澳大利亚人、瑞士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北爱尔兰人和印度人,其中有历史爱好者、建筑师、艺术家、公司职员、为婚姻所困的人、工业党、女性、接线员、模特和不怕死的人,每个人物都独立出现,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小说逐一描写了他们的情感、生活和兴趣爱好等,并以阿拉伯数字排列。这种列举的方法显然有别于其它的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视觉艺术的痕迹,读来有种翻阅相册的感觉。此外,贝尔使用不同的叙事手法来展现每个人物的特征。例如,第15个“画像”的标题后紧跟着两张空白页,第13个“画像”有着独特的版面:“本部分摘自1973年6月16日伦敦的《时代报》,重印于此,只字未动。”[2]23这种拼贴的叙事手法不同于传统的叙事手法,拓宽了人物存在的空间,也使人物的存在方式更具个性化。
贝尔在小说中对画家许布勒提出一些建议,并一厢情愿地付诸行动,至于许布勒是否会接受“我”的建议,或对建议持何种态度,小说都没有明确交代。实际上,真实存在的美国画家许布勒确实发表过这样一个声明,而且,小说中使用的也是许布勒的原话。换句话说,小说开头讲述的内容都是真真切切的现实。然而,到小说结尾,“现实”开始虚化:
许布勒,你是美国人吗?许——布勒,听起来是的。应该是的。你的祖先也许是欧洲人。你结婚了吗?幸福吗?有孩子吗?也许没有结婚。或者不会结婚。我理解。你的父母还在吗?身体好吗?没有问题,经济或其它方面呢?
…………
许布勒,听起来是美国人。你长得是什么样?我的意思是,你怎么描绘自己?你在人群中显眼吗?可能是个野心勃勃的梦想家。告诉我!高吗?你的衣服合身吗?你从事摄影有多久了?不高:弓形腿?肯定很结实吧。许布勒,你需要能量。哪种照相机?柯达胶卷吗?你的肩胛骨中间有一两个疙瘩,你够不着。是不是打扰你了?疲惫让人厌烦。你的表戴在你的手腕上有没有留下痕迹?你到底住在哪儿?是租的房子吗?告诉我城市名。蓝色的眼睛吗?我知道我问得很详细,但对有些人来说很有趣。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一直在思考。我想我们都在思考。[2]38-39
“我”对许布勒的国籍、家庭、婚姻、工作和身体状况等都一无所知,提出了无数疑问。可见,此处的许布勒并不是真实存在的美国画家,而是虚构的人物,是小说家想象的产物。贝尔对前文的内容进行虚化处理,消解了现实,用主观想象取代了客观世界。读到这里,读者恍然大悟,前文的“现实”都是虚构,都是作者建构的产物。可见,在贝尔看来,没有真正的现实,所谓的现实都是虚无缥缈的,是一种幻觉。他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现实主义的强烈质疑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此外,小说开头明确交代,许布勒决心“用图像的方式记录每一个世人的生存状况”,紧接着给出了23个人物的“画像”。例如,第一个出现的是莱丝利·阿尔德里奇(Leslie Aldridge)的“画像”:
他曾获得大英帝国勋章,一个单身汉,个头很高,冷静、富裕,堪称完美,但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温文尔雅。晚上,他经常在俱乐部里嚼着牛排腰子派。
阿尔德里奇迷恋历史,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把历史年代记得一清二楚。他年逾六十,日夜担心自己死去,想方设法地让自己青史留名。他想出了一个较为学术性的想法:发明一个单词。他为此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一次会面时,他把这个词写在信封的背面,就是为了让这个词成为一个正式的英文单词。
据说astronaut这个词是纳博科夫率先使用的,可是,这么普通的新词根本无法满足阿尔德里奇的愿望,多年以来,他一直渴望得到的是字典里的最后一个条目——这可真是莫大的荣幸啊。阿尔德里奇造的词是zynopic, zythm和zyvatiate。
现在,他的问题就是让这三个词中的任何一个付梓。《牛津英语字典》的出版商出于礼貌表示对此有兴趣,实则表示怀疑。出版商们总是要词源,阿尔德里奇正在写信和文章给报纸和杂志,让这几个词落实。迄今为止,他的词早已被世人遗忘。[2]5-6
“画像”描绘了阿尔德里奇的外貌特征、个人爱好、经济状况及其历史功绩等。Portrait一词既可以指绘画作品中的画像,也可以指文学作品中的画像,作者选择使用这个词,意在模糊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而且,值得一提的是,portrait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是写实的,是现实主义的。小说聚焦视觉艺术及其对文字的再现,“我把这些‘画像’都交给许布勒,助他一臂之力,管他喜欢不喜欢”[2]4,这句话显然是对画像这种现实主义视觉艺术的再现形式的挑衅。小说用文字对人物进行刻画,但刻画的内容都是图像的原型。换句话说,这些人物的存在方式都是不稳定的,都是在文字与图像之间飘移浮动。小说结尾,许布勒很可能会拒绝“我”的提议,贝尔进而指出“图像”这一形式的局限性,平面的媒体根本无力展现复杂的人性,文字的表现方式是图像所无法比拟和超越的,从而说明许布勒“雄心壮志”的盲目性。(3)许布勒是美国著名的概念画家。1971年,他启动了一个项目,试图记录世上所有健在的人。他的画作涉及对地图、图表、摄影等知识生成体系的分析,令人迷惑不解,甚至令人怀疑自己的眼睛。换个角度来看,许布勒的意图是用图像记录世人的生存状态,他豪言壮语,野心勃勃,然而,“现实比艺术家的想象还要丰富”[2]38。贝尔不温不火,用冷峻而超然的语言尖锐地讽刺了“许布勒们”。贝尔认为许布勒的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多种多样,差异甚大,艺术家根本无法记录复杂而多维的现实,他对以许布勒为代表的艺术家的无知和狂妄进行猛烈的批判。在贝尔看来,现实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作家的想象,而现实主义却声称其能精确地再现现实。因此,在贝尔看来,现实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它与许布勒的“雄心壮志”别无二致。
二、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贝尔的作品具有元小说的特征,他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经常会跳脱出来,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其进行审视和反思。《26个英文字母》是小说集的最后一篇,也是贝尔的名篇之一。故事的女主人公是英国人凯西·普里德姆(Kathy Pridham),她是一位图书管理员,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市的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工作。她不厌其烦地学会了当地的乌尔都语,但是她只会说,不会阅读。“卡拉奇的男士比女士多——许多从英国总部过去的年轻的单身汉,但是那些巴基斯坦人总是费尽心机地接近她。他们又年轻又懒惰。”[2]174她在一次派对上遇到了当地画家赛义德·马苏德(Syed Masood),并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凯西在画展上看到了马苏德的画,激动不已。他们俩结识后,马苏德带凯西参观他的工作室,凯西很欣赏马苏德的画,在自己的住处为马苏德腾出空间,把自己的备用房间作为他的工作室。相恋之后,凯西发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的变化。她开始变得邋遢,喜欢坐在地板上,穿着巴基斯坦式的无领长袖衬衫,裹着头巾,甚至穿着莎丽去上班。马苏德也露出了自己的本性,他脾气暴躁,甚至当众诅咒凯西。有一次二人争吵,马苏德甚至打了凯西一个耳光。小说结尾,凯西回到了伦敦,打开了一个来自卡拉奇的包裹,收到了马苏德送来的他的自画像,他的容貌又浮现在她眼前。
《26个英文字母》这个小说的标题别出心裁,26个字母所指的显然不是小说内容、人物或主线,而是小说语言的组成要素,小说的意义来自字母的任意组合,或者说是人为的操作。小说题目就表明了小说在语言方面的标新立异,也显示了贝尔对语言本身的关注。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我捏着手指,从中挑出了一些字母。这些字母(或其形象)跃然纸上。它们没有所指,我必须给它加上。word这个单词组成之后,其它字母与它并置,但它并不总是word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要么与我对它的印象相一致,要么和这个单词所表示的物体相一致。
树:我看过远处的树的形状,是绿色的。
我正在写一个小说。
那么,麻烦来了。
“狗”这个词,就像威廉·詹姆斯所指出的那样,并不咬人。我的小说从一个哭泣的女人说起。一天下午,她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哭得伤心欲绝。这些词汇,尤其是“哭得伤心欲绝”能表达出她的痛苦(她的自我怜悯)吗?除了我,哲学家也讨论过词汇的局限性。[2]17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首先,小说中的“我”指的是作者本人,“我”坦言自己正在撰写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就是后文出现的小说。现实主义作家很少会坦白作品的虚构性,贝尔却反其道行之,把构思的经过和创作的过程全都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打破了读者的怀疑悬置,强调了作品的虚构性以及它作为艺术品的存在。[3]可见,贝尔强调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即反现实主义性。其次,小说讨论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狗’这个词不咬人”,“‘哭得伤心欲绝’这个词不能表达她的痛苦”,“词语与我的印象不一致”,这些都说明词汇的局限性以及词汇与现实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说,词汇或者语言本身根本无法真实地描摹现实,而作者用语言书写的凯西与马苏德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就理所当然地与现实划清界限。然而,语言也不是一无是处。“当凯西想家的时候,她经常看London这个词——按顺序排列的六个字母。于是,部分建筑物出现了,只不过有点模糊。她聚精会神,回忆起熟悉的公交车站以及她曾经工作过的建筑物的内部。”[2]175语言这座桥梁虽然能够帮助凯西想起往昔的情景,但是,这情景不够清晰,也不够完整。
小说结尾,凯西肝肠寸断,回到了伦敦,却意外地收到了马苏德的自画像:
帆布上都是油,画得非常像。他的虚荣、傲慢和惹是生非一目了然。
他的脸庞斜倚着茶壶,视线越过茶壶看着凯西在哭泣。
她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他,想起了他的容貌。
语言。语言在纸上的痕迹,等等。[2]183
马苏德脸庞瘦削,面相凶恶,留着稀疏的胡须。[2]176他的自画像栩栩如生,把他自己的神情、心理和性格特征都生动地表现出来。马苏德没用一字一句,仅仅通过一幅画像就成功地让凯西想起过去。这说明视觉艺术有着非常强烈的表现力,而语言的表达力相形见绌,“文学想要反映现实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4]。
《许布勒》和《26个英文字母》都探讨了语言文字与视觉艺术之间的关系。前者认为,文字或文学的内容是视觉艺术所无法再现的;后者认为,视觉艺术的表达力远胜于文字或文学。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似是而非的矛盾之间有着强烈的张力。作者用小说集《当代画像和其它小说》中的一头一尾两篇小说表现了艺术再现的困境,使这一主题贯穿整部小说集,即包括文字和视觉艺术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都不尽人意,都不能完整无误地再现现实。
三、视觉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赶牲畜人的妻子》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自亨利·劳森(Henry Lawson, 1867-1922)创作《赶牲畜人的妻子》以来,同名小说不断涌现,贝尔的版本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这十几个版本中最出色的作品。劳森的《赶牲畜人的妻子》是澳大利亚文学的经典之作,是澳大利亚文学选集中入选率很高的作品之一。这个作品不仅是现实主义的经典,而且是为澳大利亚民族的神话、民族精神代言。贝尔选择重写这个小说,有着明确的用意。
贝尔《赶牲畜人的妻子》的叙事者“我”是一位阿德莱德的牙医,“我”从澳大利亚著名画家拉塞尔·德莱斯戴尔(Russel Drysdale)的画作中认出了自己的妻子海泽尔。“我”遭到了她的抛弃,走进丛林去寻找她,却失望而归。小说开篇前嵌入了德莱斯戴尔的同名黑白画作。画作的背景是澳大利亚内陆,一望无际,只有零散而稀疏的几棵树,赶牲畜人的妻子在画幅的左边,身材高大魁梧,几乎与画作同高,远处停着一辆马车。德莱斯戴尔的画作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用写实的手法对人物和景色进行刻画,描绘了人类所面临的恶劣的、极具挑战性的生存环境。贝尔的小说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初,而这幅画创作于1945年,显然,这幅画不是小说完成以后创作的插图。那么,这幅画与小说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贝尔嵌入这幅画除了揶揄劳森[5],还有别的用意吗?
小说开篇,牙医就指出了一个问题:“也许这幅画的标题有个错误——但也不是很重要——画中的女人不是赶牲畜人的妻子,而是我的妻子。”[2]55这幅画的标题是《赶牲畜人的妻子》,然而,牙医却声称画中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对此,他给出了理由: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大概有30年了,这幅画是她离开不久,和他会面之后画的。注意看,她很方便地把手藏了起来……我说“离开不久”是因为她拿着我们的小行李箱——德莱斯戴尔把它画得像个购物袋,她穿着平时去沙滩的时候穿的沙滩鞋,而且那是1945年。毫无疑问,这就是海泽尔。[2]55-56
这段话中的“他”指的是赶牲畜人,他和牙医的妻子私奔了。牙医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并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他对德莱德戴尔的画作进行了评论——“他画得还比较像”[2]56:
海泽尔骨架很大。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争吵是因为她的体重,她那时重12英石4盎司。她实际上并不高。从画上能看出她又变胖了,这不需要很长时间。看她的腿。她的脸庞不大,很漂亮。她的眼睛总是让我感到惊奇,多么严肃的眼神。这幅画也把这一点展现出来了。总之,这是一张温柔的脸,其他女性也喜欢这样的脸。……海泽尔看起来并不开心。我能看出来,她又改变主意了。好吧,这幅画是她刚离开我不久时画的;但是她在前景,离他很远,好像他们之间并不说话。看到了吗?距离=怀疑。他们肯定吵架了。[2]56-57
在牙医看来,德莱斯戴尔的画作准确捕捉了海泽尔的身体、脸庞和眼神的特征以及她的心理状态,并把这位女性生动地再现出来。正是因为他画得非常逼真,牙医才一口咬定画中女人正是自己的妻子,可见,这幅画是一幅写实作品。然而,在牙医看来,这幅画犯了一个严重的、令人无法忍受的错误,他要迫不及待地指出来。牙医表达了对这幅画的失望心情,他的妻子与赶牲畜的人私奔以后,不知去向,“连个电话号码和联系地址都没有留下”[2]58。他向德莱斯戴尔的这幅现实主义画作求助,试图按图索骥。然而,“这幅画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画的是澳大利亚丛林——但这到底是哪里?南澳?也许是昆士兰,西澳,北领地。我们不知道。你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地方”[2]57。他按照画中的情景去寻找妻子,结果是无功而返。在牙医看来,这幅所谓的现实主义画作根本没有再现现实,它呈现的根本不是澳大利亚丛林,充斥其中的都是谬误、谎言和欺骗,所谓的现实主义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由此可见,在这篇小说中,贝尔没有远离澳大利亚现实主义传统,而是与之进行了一场幽默而又严酷的战役。[6]
贝尔使用了新的叙事手法使小说呈现出上述的景观。劳森的小说使用第三人称叙事,描写了赶牲畜人的妻子带领着孩子与蛇周旋并最终把蛇打死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有赶牲畜人的妻子、几个孩子,还有她回忆中的丈夫。贝尔的小说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人物——阿德莱德的牙医,贝尔从牙医的角度来看待并观察“赶牲畜人的妻子”,并把全知视角变成限知视角,这样一来,牙医的受骗就成为可能。贝尔小说的题目虽然是《赶牲畜人的妻子》,但它真正的主人公是牙医,关注的重点是牙医的生存状态。比如,小说写牙医有明显的大男子主义作风,对妻子有着强烈的占有欲,然而令牙医感到震惊和失败的是,她不但已不属于他,还选择了一个赶牲畜的土著。
贝尔在《赶牲畜人的妻子》中书写了视觉艺术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绘画与文学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小说中提到的画作是现实主义的,是德莱斯戴尔根据劳森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画作,而贝尔的小说在揭露绘画欺骗性的同时揭穿了劳森现实主义小说的欺骗性,可谓一石两鸟。可见,绘画与文学虽然同属艺术门类,但两者并不总是和谐相处,有时,两者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与碰撞,尤其是在现实主义的问题上。
四、结 语
贝尔的三篇小说都高度关注现实和现实主义:在《许布勒》中,视觉艺术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在《26个英文字母》中,文字在图像面前相形见绌;在《赶牲畜人的妻子》中,视觉艺术违背现实,文学揭露了绘画的欺骗本质。贝尔的小说关注现实,但他不是简单而直接地描摹现实,而是通过展现视觉艺术与现实、文学与现实以及视觉艺术与文学等多组错综复杂的关系,来曲折讨论艺术与现实、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
现实主义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从那时开始,以A. G. 史蒂芬斯(A. G. Stephens, 1865-1933)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批评家高度赞赏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一大利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现实主义与左翼联姻,进入另一个发展高潮,以万斯·帕默(Vance Palmer, 1885-1959)和奈蒂·帕默(Nettie Palmer, 1885-1964)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家仍然高度赞赏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对澳大利亚民族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推动力。这些批评家都把亨利·劳森奉为现实主义的经典,将他的作品视为现实主义作品的典范。贝尔坚决反对这种庸俗的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无异于一个“紧箍咒”,极大地限制了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发展。他非常赞同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 1912-1990)的观点,蔑视劳森传统,认为它“枯燥、空洞,近似于新闻报导”,并提出“为什么就因为它是澳大利亚的就必须对它忠贞不二呢?”1958年,帕特里克·怀特在《浪子》(“The Prodigal Son”) 一文中声称:“澳大利亚小说不必是那种沉闷枯燥的、暗色调的、新闻报道式的现实主义的后代。”[7]20世纪60年代,怀特用全新的作品抵制现实主义,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开创一片崭新的天地。然而,怀特无法凭一己之力与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抗衡。70年代的“新派”小说高举反现实主义和反民族主义大旗,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怀特的衣钵,融合了幻想、超现实、对叙事时间和叙事声音的实验、对作者的作用和地位的新的意识,更明确地将小说视为虚构的意识,认为短篇小说只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简单地反映生活。[8]541
贝尔是“新派”作家中的理论家,他十分赞赏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崇拜法国的普鲁斯特和德国的托马斯·曼。贝尔的作品独具一格,不像怀尔丁那样尝遍各种方法,不像彼得·凯里那样放弃写作“新派”小说,也不像弗兰克·穆尔豪斯那样关注叙事的实验性与性写作[8]541,他始终坚持用超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徘徊在现实与幻想(超现实)之间,常常把梦幻当作现实,把现实当作梦幻,发出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反常议论,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他的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给人一种新鲜感,而这种新鲜感就是冲破现实主义牢笼后的新鲜空气。贝尔通过反现实主义叙事有力地打击了澳大利亚的现实主义传统,为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释放出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