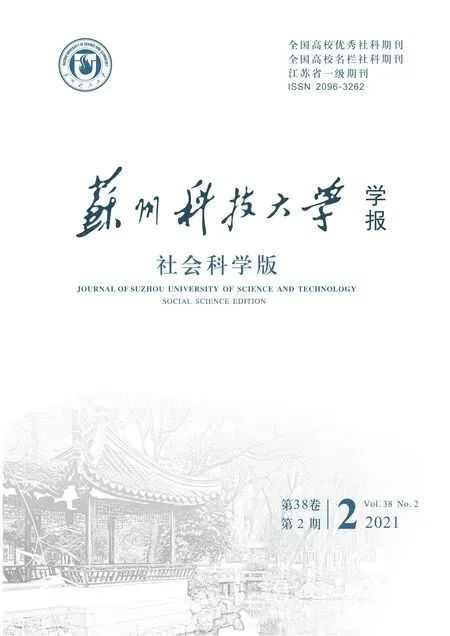诺曼征服后的英格兰郡长角色研究(1066—1216年)*
侯兴隆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英格兰形成郡区制,建立起郡、百户区、十户区三级地方政府体系。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将原盎格鲁-撒克逊地方治理模式和诺曼底公国任命子爵治理地方的经验相结合,建立新的郡长制度,郡长成为郡的最高官员,英格兰地方治理进入“郡长时代”。此后三个世纪,郡长一直是英格兰最为重要的地方官员,直至其地位被治安法官所取代。郡长集行政、司法、财政、军事、警察等职能于一身,他受职于王权,扎根于地方,在地方治理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对于中世纪英格兰的社会变革产生很大的影响。史家称赞道:“尽管郡长制度存在固有的弊端,但它仍是西欧君主所设计的最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1]171
目前,国内外有关中世纪英格兰郡长的研究成果还十分有限,主要有威廉·A.莫里斯的《1300年以前的英国郡长》[2]和《诺曼时代早期的郡长》[3]、D.A.卡彭特的《1194—1258年英格兰郡长的衰落》[4]、戴瑶玲的《诺曼时期英格兰郡守制度探析》[5]、侯兴隆的《试析诺曼时期英格兰郡长权势膨胀的原因》[6]等。此外,与郡长相关的资料多散见于大卫·道格拉斯主编的《英国历史文献集》[7]、海伦·M.杰维尔的《中世纪英格兰的地方政府》[8]、沃伦的《诺曼-安茹时期英格兰的治理(1086—1272)》[9]等。
笔者试图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及现存资料,着重分析1066年诺曼征服至1216年约翰王去世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中郡长对于中央和地方社会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为更深入、直观地认识郡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进而通过郡长了解这一时期英国地方政府体制的特点。
一、国王的地方代理人
中古时期,由于国家治理体系不完善、王权的有限性、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及时等因素,国王无法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因此有必要在各地任命一些忠于自己的封臣作为国王的代理人,以便更有效地维系王国的安定。国王在地方的代理人有郡长、验尸官、执达吏等,其中“郡长是国王在地方政府的主要代理人”[10]387。甚至有人认为,威廉一世最伟大的创造就是代理人制度,这扩展了国王的权威。[11]
作为国王的代理人,郡长在郡中即代表国王治理地方,是王权的象征,一切权力皆源于国王,因此须向国王负责。诺曼征服后,原由英格兰人担任的郡长逐渐被诺曼人所取代,新任郡长皆为威廉一世心腹。虽然郡长在郡中的地位无人能及,有些郡长甚至横行乡里,横征暴敛,但在王权相对强大时,郡长对于国王依然保持着敬畏之心。早期的郡长类似于总督,掌控郡中一切事务,专横地使用其权力。1071年至1095年,担任剑桥郡郡长的皮科特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他肆无忌惮地欺凌剑桥郡的居民和伊利修道院的修士,但即使是皮科特也不得不向国王的法律制裁低头。[12]2
当英格兰政治局势稳定、王权强大时,郡长不仅忠诚于国王,是国王意志的执行者,而且是代替国王治理地方的有力助手。正如莫里斯所言:“除了通过郡长的力量,没有人能够使鲁弗斯(威廉二世)驾驭和管理他在英格兰的所有领土。”[2]57只有通过代理人,国王才能够在国家治理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维系王国的稳定,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更为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类社会矛盾及突发事件。
郡长不仅是王权的代理人,也是它的主要支持者。英格兰政治体制决定了国王和郡长的政治地位,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彼此牵制的关系。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贤人会议起,国王由其选举或罢免,而国王也可以任免“贤人”(包括方伯、伯爵、郡长等)。诺曼征服后,贵族虽再无选举、罢免国王之权力;但是由于王权的有限性及客观因素的制约,国王对地方的统治必须依赖于郡长的支持。如果失去郡长的支持,王权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从而引发英格兰的政治混乱。威廉二世即位之初的封建内战是如此,亨利一世即位初期和斯蒂芬时期的内战亦是如此。虽然郡长名为“国王的地方代理人”,但其并不总是恭顺于国王。
虽然英格兰有制约、限制王权之传统,但国王总是试图突破权力的限制,扩张王权。当王权不断扩张、趋于强大时,郡长才会真正成为国王在地方忠诚的代理人,才会完全履行国王的令状,才会恪守自身的职责。因此,历任国王都试图调整代理人制度,使其更适宜于王权统治并成为国王得心应手的左膀右臂。威廉一世挟征服之余威统御英格兰,原郡长尽数被国王心腹所替换,因此郡长不敢有不臣之心。亨利一世在位时,通过一系列措施,纵横捭阖,弃旧擢新,任用新人担任郡长,从而使得郡长成为“国王的仆人”[13]。郡长从国王的地方代理人向国王的仆人转变的过程,一方面体现了英格兰王权的加强,国王权威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体现了英格兰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渐完善,地方权力的任意性、离心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国王对于郡长的制约性愈发增强。例如,郡长在郡法庭欺压百姓时,国王可以重新予以判决。郡法庭陪审团被唤至伦敦,在国王的法庭上,他们陈诉事实真相,使得郡长不得不将非法获得的土地交出来。[12]3关于王权强大时国王对其代理人——郡长——的权威地位,当时一位伦敦的编年史家生动形象地描述道:“1121年,当郡长们集体提交他们的账目以供审查时,他们露出一副因恐惧而发抖的沮丧表情。”[12]3
亨利一世对于地方代理人的整饬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得郡长制度成为当时西欧最为有效的地方管理制度。亨利二世即位后继续整饬郡政,加强王权,形成一系列对郡长的制衡机制,从而更好地使郡长在效忠于国王的同时履行其代理人的职责,真正做到为国王守护一方的稳定和安宁。
亨利二世延续其祖父亨利一世的政策,在地方政府中使用专业的行政官而不是有影响力的大贵族作为自己的代理人。[10]389-390亨利二世于1170年颁布《郡长调查令》,成立的委员会从15个方面对郡长进行调查,除直接讯问郡长外,委员会还对各郡领主、骑士、自由土地持有人等进行寻访以查实郡长的不法行为。[7]470-472最终仅有7位郡长得以留任,有22位被永久性罢免。随后,亨利二世任命忠于自己的小贵族担任此职以填补空缺。这一做法与亨利一世施行的“弃旧擢新”相类似,使得新任郡长以国王为唯一依靠;也使得国王的权威得以继续提升,王室令状在地方得以更忠实地执行。
翻阅史籍,虽然不时见到有关郡长反叛的记载;但是纵观1066年诺曼征服至1216年约翰王去世这一时期的王权与郡政,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国王在位时期郡政失控、郡长权势快速膨胀,多数时期国王在与郡长的矛盾中掌握着主动权,并没有彻底丧失对郡长、郡政的控制权。正如海伦·M.卡姆所说:“编年史家经常向我们讲述郡长的压迫和敲诈勒索,这完全可以归咎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已经证明,如果它愿意,它有权力惩罚这个不公正和敲诈勒索的郡长。”[12]5尤其到了安茹时期,国王对于郡长的控制更加有力。
二、王权下的叛逆者
如前所述,郡长是国王在地方的代理人,其权力来源于国王,对国王负责,执行国王的令状或命令是郡长最重要的职责。然而,郡长并非国王“忠实的地方代理人”,他时常参与反对国王的叛乱活动,尤其是在政局动荡的诺曼王朝时期。郡长从国王的地方代理人转变为王权下的叛逆者是在特定时期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王国的安定与否、旧有的习惯、职务的家产制属性、西欧封建制的利诱等。
首先,英格兰旧有的习惯法使得郡长拥有反抗王权和暴政的惯例。中古时期的英格兰与古代东方社会完全不同,英格兰强调权力的制衡。无论是国王还是各级领主,虽然在各自领地范围内拥有最高的权威,然而他们并不能完全肆意妄为,抛却下层的意见。研究发现,英国民众“有一种很深厚的自卫力量,使其免受领主的过分侵夺……凭借习惯法,即使在农奴制最严酷的条件下,他们也可以跟自己的领主斤斤计较,甚至在法庭上据理力争”[14]。下层民众尚且如此,遑论作为国王下级封臣的郡长。1215年,包括郡长在内的贵族逼迫约翰王签订《大宪章》即为反抗王权和暴政的典型。《大宪章》主要内容共计63条,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主要是重申贵族的各项封建权利以及防止国王侵夺这些权利。其中第61条明确规定:为保证《大宪章》的实行,应成立由25名男爵组成的委员会监督国王和大臣,如果他们在40天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委员会可以号召全国民众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发动战争等迫使国王改正。[15]因此,在英格兰习惯法的作用下,郡长注定不总是一个安分的“仆人”。
其次,由王位继承所引发的混战为郡长的叛逆提供了契机。英格兰自诺曼征服至1216年约翰王去世共历经威廉一世、威廉二世、亨利一世、斯蒂芬、亨利二世、理查德一世和约翰王七位君主,其时王国版图包括了英格兰和与之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部分领土,如诺曼底、布列塔尼、安茹等。版图的分隔加之当时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给王位的更替带来极大的隐患。事实也证明,由王位继承引发的争议始终是影响英格兰局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多数国王都经历了由王位继承而引发的叛乱。郡长趁此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对王命不再顺从。据统计,威廉二世即位之初,威廉一世时期10个最大的总封臣中有5个在后来的王位之争中参与了反叛。郡长在叛乱中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极力扩大自身的既得利益。当罗杰·比戈德于1088年叛乱的时候,他和格兰德梅斯尼尔就是通过担任郡长一职的便利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在叛乱中的力量。[2]60最为严重的郡长叛乱发生于斯蒂芬即位之初。已于亨利一世时期得到有效遏制的郡长势力再次失控,郡长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在斯蒂芬与玛蒂尔达争夺王位的内战中渔翁得利;并且,一人兼任多郡郡长和伯爵,使很多伯爵领与郡政区重合。在斯蒂芬与玛蒂尔达的混战中,伯爵领由最初的8个增加到22个,在新设的伯爵领中9个为斯蒂芬所创,5个为玛蒂尔达所创。在这样的混战中,“灾难性的混乱持续出现于英格兰和诺曼底各地……每个人都只顾自己”[16]。当然,郡长也不例外,在封建混战的情况下,他对于国王的忠心也大打折扣,叛逆随之而来。
再次,郡长一职的家产制属性决定其对于国王的忠诚具有不稳定性。“家产制的随从大致是从下列任一方式取得其生活资源:a.居住领主家中以维生。b.从领主的仓库或账房支领其配给(通常是实物)。c.使用某块土地的权利,其条件则为服务——‘服务采邑’。d.占有某些财产收入、规费或税入。e.采邑。”[17]诺曼征服后封君封臣制在英格兰建立起来,郡长一职并无薪俸,他们大多为国王的总封臣,从国王处领有土地,为国王提供各项役务。国王与郡长之间并不是以一种契约方式联结起来的,因此,郡长一职带有浓厚的家产制属性。韦伯认为:“由于最初在家长与其依附者之间,并没有以一种契约方式缔结起来的结合关系,因此,存在于支配者与其权力服从者之间的内在与外在诸关系,在此也只能以支配者本身的利害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内在结构为出发点,来加以规则,依附关系本身仍然是基于恭顺与诚信的关系上。”[18]简言之,家产制官职主要依赖于附庸对于国王的顺从,而非“即事化”的职务忠诚;一旦统治者发生变化或自身利益受损,附庸感情化的忠诚也可能随之结束,尤其是以世袭的方式继承郡长之职的贵族。随着继承的延续,后代郡长与国王的关系日渐疏远。这些新一代年轻贵族的崛起使得英格兰局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新贵族反对他们父辈对于国王的忠诚,常常利用自身的武装力量参与反叛。[19]
郡长名义上为国王的地方代理人,但他并非总听命于国王,他们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经常损公肥私。正如弗莱明所说:“国王的官员,特别是郡长,他们从针对英国人以及犯罪的诺曼人采取的行动中获利,常常保留他们所没收的土地与权利。”[20]而且,由于缺乏“即事化”的忠诚,只有对于国王的个人顺从,郡长在一段时期内对于王权的稳定来说存在着不稳定性,这一点在诺曼时期的王位更替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威廉二世、亨利一世、斯蒂芬即位后都曾发生大规模反叛事件,给英格兰各地带来极大的灾难。但是,随着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对郡长一职进行整饬后,郡长一职开始由小封臣担任,他们对于国王的依赖性更强,威胁性更小。郡长的家产制属性逐渐减弱,这使得王权对地方的控制更加有力,地方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最后,西欧封建制的利诱与郡长职能的广泛是郡长叛逆的又一重要原因。诺曼征服后,一种不同于西欧大陆的封建制度在不列颠建立起来。学界对于封建主义的定义主要强调三个方面:“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制相适应的封土制度;三、中央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21]西欧大陆是与之相符合的典型封建制度。在这一体制下,地方领主拥有极大的权力,各自领地等同于一个独立王国,国王并无权力派官吏进行管理。伯爵及其所属伯爵领即为此,伯爵在各自领地内拥有行政、司法、财政、军事等权力,诺曼底公国建立后实行的也是这一制度。然而,这一体制的弊端不言自明。威廉一世正是基于此弊端才于英格兰确立“我的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的原则,而且除边区伯爵领外,其余伯爵均被剥夺了领地与治理权,统归郡长管理。但是,伯爵、子爵、郡长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联系,郡长是伯爵和子爵演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前者的内在属性,即要求限制王权、扩大自身权力,并希望治下领地成为独立于王权管辖的封建领地,进而使自身成长为西欧大陆伯爵一类的地方诸侯。此外,郡长职能的广泛性给予了他叛逆的物质基础,郡长利用受封于国王的大量地产和自身所掌握的行政司法、财政管理、军事指挥等权力,不断扩大既得利益,郡长一职开始脱离国王设立此职的初衷。“从国王的角度来看,郡长制不再是将王权延伸到地方的一种方式,相反成了贵族们离心倾向中的一部分。”[22]
归根结底,郡长有时从恭顺的地方代理人转变为王权下的叛逆者的根本原因是郡长的既得利益与国王发生了冲突。正如A.L.普尔所言:“他们(郡长)的利益并不总是与国王的利益相同,因此他们不可靠,甚至有时参与叛乱。”[10]388中古时期英格兰政出多元,各种势力相互制衡,努力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样一种贵族政治体制中,作为贵族领主第一人的国王与其他贵族相比,他所具有的优势在最初并不明显。因此,诺曼王朝时期王权与郡长时常爆发激烈的冲突,地方郡长不时发动叛乱。但是,随着王权的逐渐加强和地方治理模式的日益发展,国王与贵族之间政治地位的差距越来越大,两者间的利益冲突有所缓解,因此亨利二世之后郡政日益稳定。对于王权而言,虽然郡长有时会成为叛逆者,但这并不是一种常态,“国王的地方代理人”才是郡长的主要角色,即使这个代理人并不总是对国王言听计从。
三、地方权益的掠夺者
郡长及其前身(方伯、伯爵)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产生后,便利用自身职能中饱私囊,变本加厉地掠夺地方利益,从而引起地方极大的愤慨。埃塞尔雷德时期的法律将之称为“贪婪的赋税征收者”。为了抑制这些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多位国王都曾颁布法律予以遏制,然而效果并不明显。在司法上,犯罪之人通过贿赂郡长可以减免刑罚。埃尔弗里克曾谴责他那个时代的地方官,说他们被贿赂蒙蔽了双眼,为司法提供买卖,为金钱出卖自己。沃尔夫斯坦也曾猛烈抨击郡长和其他官员的司法不公。[2]15此外,郡长还通过其他方式掠夺地方权益,如在剑桥郡,市民每年要用自己的犁为郡长服役3次;在赫里福德郡,每年8月郡长会召集一些人为他割草。
诺曼征服后,由方伯(或伯爵)和郡长共同负责的地方政府双头领导体制被废除,郡长成为郡内最高官员,其贪婪的本性更加暴露无遗。郡长不光压榨郡内民众的利益,还千方百计掠夺教会各项收益,强占教会土地,没收教会财产等。伍斯特郡长厄塞和剑桥郡郡长皮科特曾大肆掠夺教会地产,以至于引起教士不满,纷纷向威廉一世申诉。为此,威廉曾派官员赴各地调查郡长的违法情况,并让其归还侵占的教会地产。[23]伍斯特郡的斯·达贝特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郡长,他掠夺了伍斯特郡教会的大量土地,并将之永久占有。
当王权强大时,郡长是国王恭顺的地方代理人,国王的申斥、指责对于遏制郡长以及稳定地方秩序有较大影响;当王权衰弱时,这种指责就显得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了。斯蒂芬统治时期,英格兰政局因内战而动荡不已,身兼数郡郡长的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在内战中纵横捭阖,疯狂掠夺地方利益。他不仅于1143年率部洗劫了剑桥郡沼泽地区的居民,还占领了伊利修道院并将它变成一座堡垒,赶走了拉姆齐修道院的僧侣,将修道院变为他的军事指挥中心。在曼德维尔治下的郡,“一切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土地荒芜,没有任何庄稼。在二三十英里的田野里,既没有牛,也没有犁”[10]147。
除曼德维尔采取的这种极端行为之外,郡长掠夺地方权益主要是通过财政税收和司法审判这两种途经。税收和司法是郡长最为重要的两项职能:前者关乎王国行政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转、对外战争的胜利与否,后者关乎地方社会的和谐稳定、繁荣发展与否。国家治理体系正处于形成、发展之中,行政监督体系不健全,从而为郡长徇私枉法、收受贿赂、中饱私囊提供了便捷之门。莫里斯对此惊呼道:“众所周知,所有的郡长,都犯有敲诈和受贿的罪行。”[2]160自亨利一世起,王室领地开始实行郡长承包税,郡长每年需要缴纳固定税额的赋税。因此,郡长拥有王室领地一定的税收自主权,在征收其他赋税时常常损公肥私。一般来说,只要郡长能够完成应交付财政署的税额,国王就不会过多地干预郡长徇私枉法的行为,除非郡长过分敲诈勒索王室土地权益或未交足税赋,才会受到国王的惩治。中古时期,“虽然郡长通过他们的服务获得了丰厚的土地回报,但他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敲诈庄园民众和征收司法罚金,这被认为是授予其的一项特权”[1]170。可以这样认为,郡长受到国王申斥并非因为敲诈勒索地方,而是因为他将大量的收益收入囊中而非上交国王。1170年郡长弊政大调查时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为调查郡长是否向他人勒索钱财。
司法方面,郡长掠夺地方权益主要体现在诉讼过程中对财产的罚没和案件的最终判决。罚没财产是英格兰司法体系中重要的惩罚措施之一,郡长时常通过罚没被告的财产使自己获利,而且法律允准郡长获得司法罚金的三分之一,因此他对罚没财产乐此不疲。对于小偷来说,一旦被郡长抓获并从速处理,如果案件没有经过郡法庭的审理,郡长就可以没收小偷的财产并将之据为己有。郡长也时常根据法律习惯没收违法者家产,在查抄的过程中中饱私囊。对于郡长这种过分的罚没行为,很多国王都曾予以谴责、制止。《亨利一世加冕宪章》规定:“任何男爵或我的封臣被处以罚金,他将不会把不动产作无限量抵押,就像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时所做的那样,而他只需要根据法庭判决的程度进行赔付即可。”[7]434此外,通过收受贿赂影响司法判决是郡长的另一惯用伎俩。郡长名义上只是郡法庭的主持人而非最终判决的裁定者,判决结果一般由出席法庭的所有自由土地保有人或陪审团共同做出,但当他们的意见出现分歧且势均力敌时,郡长有权采纳他所倾向的判决结果。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司法状态,在实际运作中会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如郡长收受贿赂从而施压使法庭做出他所希望的判决结果。郡长弊政调查时,是否收受贿赂而宽恕行贿者的罪行也是重要内容之一。1170年郡长弊政大调查的结果表明:郡长曾通过司法或非司法途径对百户区、村庄以及个人进行敲诈勒索,而且郡长通常还会给他们或执达吏一部分财物作为封口费。[2]115
虽然郡长在司法审判中会通过敲诈勒索、受贿等影响案件的判决,但是也不可过高估计郡长在法庭中对于郡民众权益的讹诈。郡长不仅要考虑诸多因素,也受到郡法庭出席者和郡法庭其他官员的制约。郡长毕竟不是专制主义下的地方诸侯,其权力是有限的。《亨利敕令集》对于郡长在司法审判中权力的有限性做过如下隐晦的记载:如果郡法庭的审判人对于裁决有不同意见,郡长作为法庭主持人有权采纳他所认可的意见,但是提出各自意见的审判人的爵位和声望都是郡长在决定时必须予以考虑的。[24]此外,郡长如果对于郡法庭强力施压,郡法庭法官有时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与郡长抗衡到底。当萨默塞特郡长罗杰·德·福特向郡法庭施压,要求做出有利于一方的裁决时,大多数法官退出了法庭。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退出法庭似乎是合法的。[25]而且,随着安茹时期司法体系的日益成熟,以及枉裁令状(Attaint)的创制,王室法庭获得了对于地方法庭司法判决的复审权,这也极大地束缚了郡长在司法审判中的不法行为。
总而言之,虽然郡长在其任内会通过多种手段掠夺地方权益,给地方社会造成一定的破坏;但他的权力终究是有限的。郡长对于地方权益的掠夺是有限度的,如果他超越了国王和地方可以容忍的程度,必将受到一定的惩罚。郡长的不法行为多见于诺曼王朝时期,到了安茹时期,郡长职权已经被验尸官、治安维持官、巡回法庭等分割,各种贪赃枉法行为虽然偶有发生,但较之诺曼时期已大为减少。
四、地方秩序的维护者
一般来说,郡长是郡内大土地所有者,无论是威廉一世从自己的首席佃户中任命的,还是亨利一世及后代国王从小贵族中选拔的,他们在郡中都拥有大量地产。同时,以郡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也是由郡内的主要土地所有者所组成的。正如海伦·M.卡姆所说:“英格兰大部分郡的地方政府都是从主要的土地所有者中挑选的贵族来进行管理的。”[12]10这是由中古时期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所决定的,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地位决定其政治地位,政治地位反过来又维护了他们的经济地位。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随着英格兰国家治理体系的初创,“王之和平”观念也逐渐出现,即国王应维护王国境内的和平,制止暴力。[26]民众认为国王有义务维护社会稳定、制止暴力事件以及维护人民权利。然而,由于国王权力的有限性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不完善,维护“王之和平”的重任一开始就落到了地方政府头上,准确地说是方伯、伯爵和后来出现的郡长。维护“王之和平”不仅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义务。作为各郡的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在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维护民众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在郡中的权益。诺曼征服后郡长虽然是国王的地方代理人,但是毕竟身为郡的一员,郡社会的繁荣发展与郡长各项权益紧密关联。埃塞尔雷德时期的法庭案卷显示方伯或国王的里夫(郡长的前身)在5个自治市维护社会稳定。国王的里夫将人们置于维护和平的官方誓言之下,这使他们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就被认为是非凡的守护者。[2]10诺曼征服后,郡长继续履行他前任的使命,维护“王之和平”,稳定地方秩序,促进地方社会繁荣、有序发展。
在郡长的领导下,英格兰各级地方政府恪守职责,忠实履行各项职能,核查十户联保制度,确保将所有符合规定之人编入十户区,相互担保,共同缉捕盗贼。当案件发生后,“只要能看到痕迹,每一个听到呼唤的人,都要帮助其余的人沿着踪迹骑马进行追踪”[27]424。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承担起警察的职能,不仅犯罪率得到有效的控制,破案率也大大提高,基层社会的稳定得到了保证;各级法庭在郡长及其下属主持、领导下致力于审理地方社会的财产继承、侵犯领地等民事诉讼和斗殴、伤害、盗窃等刑事诉讼(杀人、纵火、抢劫、强奸、欺诈等归王室法庭审理),这对于化解地方社会内部矛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需见证所有的货物交易、土地买卖、奴隶释放等经济活动。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埃德加第四法典》就曾规定:每个百户区要选定12名见证人,百户区内所有的货物买卖都必须要由他们见证,否则交易非法。[27]439诺曼征服后,很多早期的治理措施被继承,这为稳定地方经济秩序、减少经济纠纷提供了重要保证。
此外,郡长在地方社会中还履行着警察职能。中世纪的英格兰与同时期其他国家一样都是农业国家,农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导形式,其中土地是核心生产资料,具有不可移动性,因此依附于土地的农民的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无论是村镇、十户区还是百户区,人们彼此群居生活、相互熟识,即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维系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是道德和习惯法,而且农业经济下的古代社会较之工业社会则更加稳定,人口流动性较小,犯罪案件数量较少,因此警察制度的发展非常缓慢。在警察制度产生之前,郡长在郡中扮演着警察的角色。1066—1216年郡长扮演的警察角色表现出警政不分、军警不分的特点。侵犯民众利益的盗贼等囚犯由郡长领导缉捕或由其他人抓捕后交给郡长关押,之后由法庭进行调查、审理、司法审判。如果罪犯在关押期间逃走,郡长将受到惩罚。郡长对于罪犯的监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在财政署记录和1194年王室法庭的记录中均有所记载,而且1166年颁布的《克拉伦敦法令》扩大了郡长的警察权限。《克拉伦敦法令》规定:任何人都不得禁止郡长进入私人法庭或土地以核查十户联保制;任何人都不得阻碍郡长进入私人领地逮捕罪犯。[7]442而在此之前,领主的私人领地(包括属于私人领主的百户区)是不允许国王的官吏包括郡长及其下属进入的。1124年,莱斯特郡的亨科特镇一次绞死了44名盗贼[12]4,这也从侧面表明郡长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拥有相当大的权力。
随着财政署、巡回法庭、地方法官、验尸官等机构和官职的设立,以及安茹时期王权的日渐加强,郡长一职受到极大的制约,诺曼时期郡长那种贪婪的面孔日渐变得和善,地方秩序的维护者成为郡长在地方扮演的主要角色。安茹时期的郡长在地方政府中需谨慎行事,公正地处理各项事务,否则就会受到国王和地方的起诉。例如1202年,林肯郡长没有将杀人犯收监,也没有制作令状,因此他受到了巡回法庭的起诉。[2]147维护地方秩序不仅是诺曼征服后设立郡长的初衷,亦是历代国王试图通过郡长实现的目标。安茹时期,郡长逐渐回归其本来面目——维护地方秩序。
五、结 语
英国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郡长制度是英国地方治理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英国是一个强调传统与继承的国家,若想对今日英国的地方制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必须沿着其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追溯,进而才能准确认识英国的地方自治制度。
通过郡区制度,郡长成为国王治理王国地方的得力助手、维护“王之和平”的执行者。然而,郡长一职本身所具有的离心性注定其不会甘于臣服王权,这使得郡长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两者时而相互依赖、互相支持,时而剑拔弩张、刀剑相向。而且,诺曼征服后,除帕拉丁领地外,其余各郡均由郡长治理,原有伯爵各项权力随之转交郡长,郡长开始作为各郡最高官员统御地方。郡长在各郡拥有大量土地及其他权益,他在扩张自身权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侵害地方权益,从而成为地方权益的掠夺者。但是,郡长作为郡社会共同体的一员,他又不可能完全与郡民众为敌,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地方权益的维护者和受益者,对于地方社会发展和稳定做出了贡献。总的来说,1066年诺曼征服至1216年约翰王去世,郡长逐渐淡化了王权下的叛逆者、地方权益的掠夺者身份,国王的地方代理人、地方秩序的维护者逐渐成为郡长在地方的主要角色。
通过窥视1066年诺曼征服至1216年约翰王去世的郡长制度,可以探寻早期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发展的脚步、地方治理的模式,以及英吉利民族权力制衡的传统观念与实践等,为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英格兰地方制度、封建王权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利于更加全面、清晰、深入地认识中世纪的英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