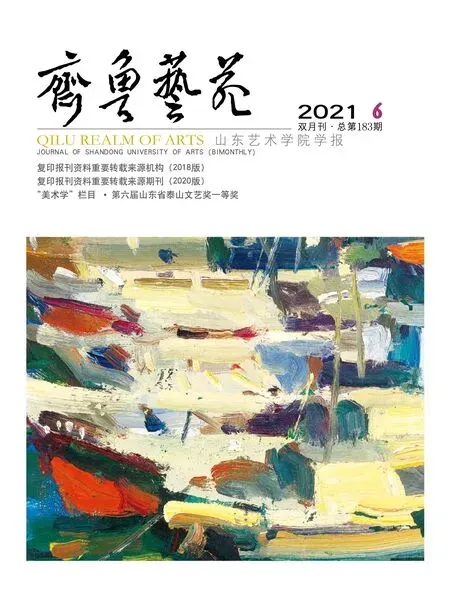认清本质 立足传统 放眼世界
——中国歌剧民族化、国际化之我见①
景作人
(中央歌剧院,北京 100020)
各位代表,各位同仁,大家好。又一次在山东济南与大家相会,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刚才听了很多代表的发言,由衷体会到了很多真识高见,心中觉得格外欣慰。
在本次歌剧论坛所设的议题中,有一个议题是“中国歌剧的民族化与国际化问题”,对于这个议题我很感兴趣,也有着一些切身体会,下面我就谈谈我对中国歌剧民族化、国际化的一些粗浅看法。
先说民族化问题。
首先,民族歌剧的提法究竟何为根本。
如今,民族歌剧的提法在我国十分流行,何为民族歌剧?这是一个带有争论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准确定论的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民族歌剧必须走纯民族化的道路,在戏剧上模仿话剧、音乐剧,在音乐上效仿《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小二黑结婚》等,创作时直接采用民歌旋律,以纯写实的手法来叙述和表现情节。还有一种看法,提出中国民族歌剧必须运用中国戏曲的板腔体音乐,如此才能够得上所谓的民族化标准。另外,有些人强调中国民族歌剧必须采用说唱体裁,即以大量道白来构成情节的表现,摒弃西方歌剧的整体交响性构思,这样才是中国化的民族歌剧模式。
对此观点我深不以为然,依我来看,以上的争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人为所设置的障碍。其实,中国的歌剧就应该是中国民族歌剧,只要它体现的是民族魂魄,表现的是民族精神,运用的是民族音乐语汇,那它就应该属于民族歌剧,绝不应再有什么节外生枝的束缚。
举例来说,张千一的歌剧《兰花花》,其情节是民族的,题材也是民族的,而他的音乐采用了以兰花花主题为“动机”的变化展开形式,这个“动机”从头至尾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难道不是民族歌剧吗?郭文景的歌剧《骆驼祥子》,情节来自于中国文学名著,音乐上借鉴了中国传统说唱音乐(京韵大鼓)的素材,这难道不是民族歌剧吗?孟卫东的歌剧《尘埃落定》,情节来自于藏族文学,音乐带有着浓郁的藏族民间色彩,这难道不是民族歌剧吗?以此类推,前些年的一些实验性歌剧《狂人日记》《夜宴》《李白》《赵氏孤儿》等,采用的都是中国民族历史题材,音乐也采用了古诗词的吟唱方法,难道它们都不应该是民族歌剧吗?而我国幅员辽阔,共有56个民族,如此宽广的疆域和丰富的民族,我们又该怎样去界定其歌剧的民族性标准呢?
还有,中国民族歌剧需要借鉴和吸收传统经典的长处,这是无容置疑的,但借鉴不等于照搬,吸收不等于盲目,《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小二黑结婚》都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它们在那个时代是经典,而放到今天,这些作品的经典意义就不是完整的,这一点也同样是无容置疑的。
我们今天搞创作,思想必须要伸展,眼光必须要向前,对于传统经典中好的要继承发扬,不足的则要剔除,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中的“扬弃”,而不顾客观因素,一切都盲目继承,那最终只能进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死路。
再者,在中国民族歌剧中运用戏曲板腔体的问题,我认为也不应该是绝对的。具体来说,采用不采用戏曲板腔体,都应该由作曲家根据作品的不同需要来决定,而不应该是事先规定和强加上去的。
实践证明,历史上有的歌剧采用戏曲板腔体获得了很大成功(如《白毛女》中的“恨似高山仇似海”,《洪湖赤卫队》中的“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等),但有的歌剧则显得与剧情和整体音乐风格格格不入。因此,我们不应该要求作曲家在每一部歌剧创作中都采用戏曲板腔体,甚至以有没有戏曲板腔体来衡量一部歌剧是否成功。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每一部歌剧都大量采用戏曲板腔体的话,那中国还要民族戏曲干什么?
我认为,重复和累赘是文字与口头的游戏,它们不应该成为捆住我们手脚的绳索,更不应该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阻力。假若一定要说出民族歌剧的定义,那我认为民族歌剧就是中国歌剧,而中国歌剧就是中国民族歌剧(包括民族正歌剧,民族喜歌剧、民族轻歌剧等),二者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我个人觉得,中国这个响亮的名称已经具有足够的份量了,它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包容性和民族自信感的体现。
其次,歌剧创作理念该不该有创新意识。
歌剧作为一种音乐戏剧形式,它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有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理念,除了适应大众需求,迎合观众趣味之外,歌剧创作必须具有鲜明的创新意识。如果理念落后,意识迟滞,那么歌剧本身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而如今的中国歌剧创作,理念落后,缺乏创新意识是人所皆知的事实。在一些所谓的创作中,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信条到处充斥,陈旧的观点始终盘踞在准则之上,而这一切的最大后果,就是忽视了歌剧艺术的创作规律和发展科学,继而使中国歌剧创作陷入到一种尴尬无奈的境地。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的歌剧创作总是被一种无形的“框框”所束缚,创作思想上缺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且大有闭门造车、自娱自乐之势。纵观现今的中国原创歌剧,大多是形式固定、体裁雷同、题材专一、风格近似,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这是非常令人无奈的现状。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歌剧必须依照曾经的经典为样板,即以红色题材为主导,以现实主义为蓝本,以民歌和民族戏曲为音乐主体,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理想的中国歌剧模式。然而我认为,这是一种僵化的固定模式,它的局限性思维,使得歌剧创作由此缺乏了广泛的探讨空间,从而大大降低了艺术借鉴和艺术共融的效果。
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我认为这句话只对了一半,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只有优秀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贝多芬使德意志民族的音乐变成世界性的音乐,威尔第使意大利民族的歌剧变为世界性的歌剧,其中都有着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秀”二字。而我们中国的民族歌剧要想真正达到国际化,步入世界一流水准,也必须要达到“优秀”的程度,否则便只能是闭门造车式的自娱自乐。
接着说国际化问题。
首先,世界的借鉴与世界的融合该不该提倡。
歌剧是一种世界艺术,四百多年前它在意大利诞生后,就依靠它那无可比拟的艺术感染力征服了欧洲,后来又征服了全世界,成为了世界音乐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歌剧艺术在欧洲发展了四百余年,在这四百余年的过程中,它历经了诞生、磨难、衰退、兴起、再发展,直至高潮的阶段,总结出了从形式到内容,从技术到经验的一整套体系,并汇集了蒙特威尔第、贝里尼、唐尼采蒂、罗西尼、威尔第、普契尼、古诺、比才、马斯涅、格林卡、柴科夫斯基、德沃夏克、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布里顿、亨策、肖斯塔科维奇等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无数歌剧作曲家,且有着十余万部各种风格的歌剧作品流于世间。
因此说,歌剧艺术是真正的国际化艺术,如今,威尔第、普契尼、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等人的成就,绝不仅仅是意大利的成就,德国的成就和俄罗斯的成就,它们已经成为了全人类所共有的文化成就。基于这一点,作为后来者的中国歌剧,在创作上向世界看齐,从而努力借鉴和融合人类所共有的文化结晶是理所当然的,这本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问题。换句话说,对于每一位中国作曲家来说,从世界歌剧大师那里虚心学习,从根本上掌握歌剧艺术的创作技法和经验,则应该是一种本能的、自然而又必然的过程。
然而,在现今的中国歌剧界,有些人认为学习西方歌剧创作经验不适合中国歌剧的发展,他们把正确借鉴和融合西方歌剧的优点看作是崇尚“洋腔洋调”,背离中国风格,从而将中国歌剧与西方歌剧在艺术结构上割裂开来。
我本人不反对中国歌剧加强民族风格,也不提倡一味盲目地坚持西方模式。我关心的是,中国歌剧如何能够更好地将中国音乐风格与国际化的歌剧模式相结合,继而使中国歌剧能够成为世界性的歌剧,真正走向世界歌剧舞台。
举例来说,国内歌剧界的有些人士认为,中国歌剧不宜采用宣叙调,认为它的表述方法不自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戏剧特点。然而,人们却从大量的中国传统戏曲作品和曲艺说唱作品中,听到了丰富的宣叙式韵白表现手法(如京剧、昆曲、京韵大鼓、北京琴书等),而这些的表现手法的确都有着中国风格宣叙调的原始雏形。而近年来,作曲家郭文景、孟卫东、杜鸣、朱嘉禾等人创作的歌剧,里面同样有着较为成功的宣叙调,他们在这方面的创作上都有着富有成效的探索,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由此可见,中国歌剧并非不能采用宣叙调,而是我们没有找到它的存在地位与方式,且没有将我们民间戏曲中的“宣叙”手法与西方歌剧宣叙调的形式相结合。为此我认为,中国的歌剧作曲家应该从中国民间戏曲和说唱艺术中汲取养料,只要努力钻研,写出中国风格的宣叙调并非没有可能。郭文景的《骆驼祥子》为什么宣叙调写得那么好?还不是直接吸取了京韵大鼓的韵白特点,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写好写不好中国风格的宣叙调,它的根本取决于我们作曲家的创作功力,而不是其它什么外来因素。
当然,我认为中国歌剧对于西方整体交响性风格的借鉴,应该是有条件、有取舍的,绝不可将其当做一成不变的准则来硬性执行。因为,中国歌剧有着自身的音乐韵律特点,亦有着自身语言的魅力,剧中有些地方用道白和对白来处理也许更为自然,也更会起到清晰明快的效果。
实际上,西方歌剧亦有着多种不同风格的处理方式,他们的轻歌剧、歌唱剧甚至部分正歌剧,也有很多采用对白和道白手法的。由此看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创作歌剧,并不应该由主观意念和硬性规定来决定,而是应该由作曲家本人,根据其创作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及艺术效果来决定。至于观众能否接受,那是一个创作水平和创作质量的问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歌剧的经典是《洪湖赤卫队》《江姐》《红珊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湘的一部《原野》引起了震动,从而推动了中国歌剧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观众的歌剧欣赏能力,而后,又有很多具有先进引领性的歌剧出现(如施光南的《伤逝》《屈原》,王世光的《马可波罗》等)。这些歌剧同样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方式(戏曲、民歌、诗意等),从而使中国观众更为加深了对歌剧艺术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由此看来,观众的接受能力同样是根据作品的不断更新而循序渐进的。
我想,中国歌剧向世界经典借鉴,并不是一个该不该借鉴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借鉴、借鉴了多少、借鉴得是否正确、到底借鉴了没有的问题。反之,还没有取到真经就觉得真经没有味道,这不是自欺欺人,自找没趣儿吗?
其次,中国歌剧创作该不该拥有宽广的目光和前瞻性的思维。
艺术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思想的体现,更是一种带有教化意义的精神感悟和行为指导。因此,对于任何一种艺术创作,都必须具有艺术眼光的深远性和艺术思维的前瞻性,否则它就不是艺术创作,而只是一些重复模仿的技能表现。
纵观当下我们的歌剧创作,这种重复模仿的技能表现比比皆是,很多地方充斥着目光短浅,缺乏前瞻性思维的现象。具体来说,由于死板的条条框框所限,大部分原创歌剧给人感觉无创意、无特点、无亮点,很多作品“戏”一开始,人们就已经估计到情节与内容的结局了,而音乐则是听完第一幕就知道后面几幕的大概情调了(谢幕则是百戏一个样子),根本就没有什么艺术上的神秘感和惊讶效果。再有,很多剧目都是仿照模子创作而出的“描红”式作品,有的看起来像《江姐》,有的看起来像《洪湖赤卫队》,有的看起来像《小二黑结婚》,至于艺术的独创性和新颖性,则是根本看不到也谈不到的。
再有,如今的歌剧创作大有“一哄而上”的趋势,各地团体(包括国有、民办、校办等等)全民皆兵,集体上阵,很多创作团队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歌剧是怎么一回事,照样匆匆上马,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因此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出现了大批“晚会歌剧”“舞蹈歌剧”“民歌联唱歌剧”“戏曲歌剧”等,这些歌剧在艺术上和质量上都经不起推敲,然却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属得不偿失之举。更有甚者,由于错误地理解民族歌剧的性质,致使全国歌剧舞台上到处都是戴着“麦”演唱的民歌演员,而那些真正具有戏剧表现力的美声歌唱家则成为了不幸的旁观者(有的专业团体甚至提出要砍掉全部美声演员),这无疑是一种浅薄的、急功近利的本末倒置现象。
其实,对于真正的艺术创作和实践,我们理应在心中树立一个正确的概念。在今天的社会中,艺术服务于大众是正确和必要的,但若从全面的角度来看,艺术又不仅仅是服务于大众的,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它还应该具有前瞻性、开拓性和引导性。因此,打着文化先行者旗号的艺术,就必须要在创作上拥有探索性和实验性的意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本届歌剧节中,我连续观看了好几部原创作品,说实话,我对剧作家、作曲家在当前情况下的艰辛努力与探索精神深为敬佩,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力争并践行着“歌剧思维”的主导思想,做出了很多了不起的成绩,这是十分令人欣慰和尊敬的。然而,我又不得不说,我们现今的歌剧创作水平,与世界性的国际化标准相去甚远,根本无法与曾经同样走过民族歌剧发展道路的俄罗斯歌剧、捷克歌剧、波兰歌剧、匈牙利歌剧等相提并论。
说到此我联想到一种现象,近年来我有机会观摩了一些戏剧戏曲演出(话剧、哑剧、昆曲等),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启发。看过这些姊妹艺术之后,我个人有一个切身的感受,那就是我国的歌剧创演已经滞后于戏剧和戏曲了,至少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观念、认识、方法)。尽管这种感受很现实、很无奈,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
简单来说,我国的话剧创作(至少从我看的几部中)在创作观念上比较开放,很多剧目探索性强,手法多样,且艺术上束缚较小。有些话剧在思想性和哲理性方面有着较大的突破,有些话剧则具有前瞻性的探索味道,还有一些话剧和戏曲带有大胆的实验性。它们的编排思想,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强烈的艺术追求意味。
而从表演上看也是如此,这些剧目的导演和演员,演出中总是力求从戏中获得一些新的探索和新的表演方式,继而给话剧的发展注入一些开拓性的活力与内容。如此的良性循环,表明了中国戏剧界艺术家们在艺术发展上不落伍的理念,他们并不以条条框框来束缚和左右自己的创作。
然而歌剧就不同了,理念落后,缺乏创新意识;观点浑浊,各种争论不休;目光短浅,缺乏前瞻性思维,这一切都形成了这项艺术发展的致命伤,也是歌剧艺术形式难以摆脱困境,最终走向世界的根本障碍。
为此我认为,我们的歌剧工作者一定要放下包袱、丢下架子,努力向戏剧界同行、戏曲界同行乃至其他艺术界同行学习,学习他们解放思想、刻苦追求,努力攀登新高峰的精神。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我们历代艺术工作者遵循多年的正确文艺方针。我想,我们的歌剧工作者(包括戏剧、戏曲工作者),都应该牢记并坚持这个方针。以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只有“百花齐放”,才能令我们摆脱束缚,解放思想;只有“推陈出新”,才能使我们拥有前瞻性、开拓性和引导性,继而创作出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