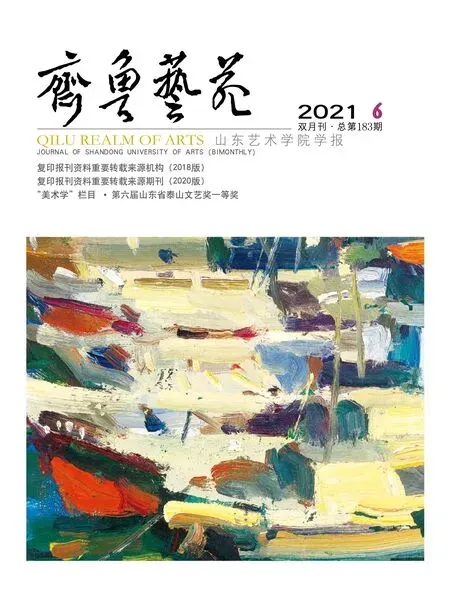当下中国歌剧创作的问题与症结
李诗原
(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032)
如果从1921年黎锦晖《麻雀与小孩》正式公演算起,中国歌剧已有整整百年历史发展进程。经历百年沧桑,中国已成为“歌剧大国”,原创剧目数千部,可排演歌剧的剧场数以百计,拥有大批歌剧从业者;越来越多的国人发现了歌剧这种“舶来”戏剧样式,并逐渐将歌剧纳入文化消费项目;留下了十几部已被历史证明或将被历史证明是可以演得下去的成功剧目。这些都是百年中国歌剧的重大成就。但中国歌剧仍存在许多问题,离“高原”“高峰”、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歌剧的要求还有很远一段距离。其问题和症结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编成歌剧故事
歌剧像任何戏剧样式一样,都必须选择一个题材,讲述一个故事。任何题材内容都可以编成歌剧。但特定题材之下,又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编成歌剧故事。故选择特定题材,讲述一个有矛盾斗争、有思想高度并与歌剧这一戏剧样式相匹配的故事,应是剧本编创的重要原则。
舞台演剧讲述的故事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有矛盾斗争。这就是故事中必有“戏”,应充满戏剧矛盾冲突。如根据话剧《雷雨》改编的同名歌剧就是一个充满戏剧矛盾冲突(繁漪、周萍、周朴园、四凤、鲁侍萍、周冲六人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的故事,并是一个按“三一律”将多重矛盾密集在一起的故事。再如,歌剧《洪湖赤卫队》也讲述了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故事,其中有敌我的二元对立,也不乏韩英与刘闯在思想性格上的冲突,还有白极会与国民党军之间的勾心斗角。歌剧故事必须是一个具有戏剧矛盾冲突的故事,甚至是一个含有多重戏剧矛盾冲突的故事。如果故事没有矛盾斗争,进而据此编成的剧本也就没有“戏”了,于是这部歌剧也难有戏剧性。但当下歌剧在“讲故事”这个环节上却留下了许多遗憾。一些剧目虽选择了很好的题材,却未能诉诸充满矛盾冲突的故事。要么像音乐舞蹈史诗或重大节庆晚会一样,旨在讲述宏大叙事,追求诗化,追求大写意、大抒情,淡化或放逐叙事性和具体的戏剧情节,放逐具体人物形象塑造和人物处境、性格、命运的表现,进而设置几个场景,每一场景讲一个故事或一段历史,并使场景与场景之间在时间上、在情节上保持跳跃性,最终呈现为“情景表演”式的串联;要么诉诸叙事晦涩、时空错乱、逻辑缺失,依仗现代舞台科技所带来的场景转换上的便利,“拉洋片”式地展现一些繁琐的故事,以致展露出类似“蒙太奇”手法(1)关于这种“蒙太奇”手法,参见:徐文正.春风吹放花千树——新时代中国民族歌剧创作述评[J].音乐艺术,2020,(1),P21-33.,最终打破了歌剧的叙事规律,超出歌剧的叙事容量。毋庸讳言,史诗根本不适合歌剧,歌剧只能表现史诗中的具体人物和细节。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剧目中的故事几乎没有矛盾冲突,或者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戏剧矛盾冲突,而只有人物的内心冲突,或人与大自然、人与病魔的斗争;或者只能凸显那种普遍存在或众所周知的矛盾(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并将其诉诸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而非具体角色之间的矛盾,甚至将矛盾的一方切分为不同的人物或人群;或者将戏剧矛盾冲突抽象化,以致在舞台上常常只能看到矛盾双方中的一方。当然,许多题材(尤其是当代题材)都难以提炼出一个具有戏剧矛盾冲突的故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总之,相当一些剧目都未能讲述具有戏剧矛盾冲突的故事。以上正是当代歌剧创作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2)有思想高度。歌剧故事不管它是什么故事,而应是一个具有象征性、隐喻性、指涉性乃至批判性的故事,能够“以小见大”呈现出特定思想主题的故事,并体现出较强的思想性。歌剧所表现的故事绝对不是一些无厘头的故事,而应选择一些具有较强文学性、思想性的故事。当然,这种思想主题也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尤其是那种与歌剧故事没有实际联系且遥不可及的宏大故事,而是一个植入故事及其人物肌体和血脉中的思想主题,并能通过特定的戏剧性手段表达出来。不难发现,当下许多剧目都在讲述一些较平庸的故事,不但达不到“思想精深”的要求,而且还难以概括明确的思想主题。一些剧目将思想主题诉诸抽象、空洞的概念,甚至是一个标语口号,或是一个“标签”,而未能诉诸具有的情节或场景,诉诸人物的思想性格。在当下歌剧编创中,似乎没有人去做这样的功课:将一个思想主题分解为几个层面,并使每个层面诉诸一个场景或一个戏剧情节,最终用鲜活的人物和事件表现这个戏剧情节,进而完成思想主题的埋设和陈铺。于是,当下中国的歌剧故事一些缺乏矛盾斗争,一些缺乏思想高度,一些故事则是两者皆无。矛盾斗争和思想高度两者兼而有之的剧目寥寥无几。综上可作出一个结论:不是所有的故事都适合写歌剧;戏剧矛盾缺位、思想主题缺位是当下歌剧编剧中的主要问题。毋庸置疑,《骆驼祥子》《原野》《雷雨》《屈原》等歌剧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剧本的成功,而剧本的成功就在于原著的成功,也就在于老舍、曹禺、郭沫若这些大师的成功。正是他们原著中强烈的戏剧性、思想性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这些歌剧注入了良好的基因,以致在当代中国歌剧舞台上脱颖而出。
以上是就舞台演剧的一般规律而言,乃剧本之共性。但为歌剧写本子,还有其特殊规律。如果说歌剧是一种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呈现戏剧矛盾冲突的戏剧样式,是一种“音乐戏剧”,那么歌剧所讲述的故事,就不仅仅是一个有矛盾斗争(有戏剧冲突)、有思想高度(有思想主题)的故事,而且还必须是那种真正的“歌剧故事”,即那种能充分凸显歌剧体裁特征的故事。这就是说,“歌剧故事”必须满足歌剧作为一种独特的戏剧样式在叙事及其戏剧性表达上的特殊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内容要让位给形式,剧作家必须服从作曲家。具体而言,“歌剧故事”也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歌剧故事”应是便于编织为“戏剧结构”的故事,而且这个“戏剧结构”还将为作曲家构建歌剧的“音乐结构”提供依据,最终去实现歌剧的理想状态——“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的同一”。所谓戏剧结构,即一个完整呈现戏剧矛盾建立、展开、激化、解决全过程的叙事结构,诉诸剧本,作为歌剧故事的骨架和内涵,不假音乐和其他戏剧表现因素而具有独立的戏剧意义。所谓音乐结构,则是一个根据戏剧结构建构的音乐叙事,与戏剧矛盾建立、展开、激化、解决构成内在关联,但同时也具有不假戏剧结构的独立意义。所谓“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的同一”,就在于戏剧结构以音乐结构为呈现方式,音乐结构作为戏剧结构的派生结构,并为戏剧结构服务。然而,“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的同一性”,正是歌剧(作为一种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呈现戏剧矛盾冲突的戏剧)最重要的体裁特征。这一体裁特征也是确保“歌剧思维”的重要前提,乃歌剧艺术的理想状态。这就意味着,能编织成这种戏剧结构的故事就可以是歌剧故事。但当下中国歌剧中的故事大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歌剧故事,其中也鲜有呈现戏剧矛盾建立、发展、激化、解决全过程的戏剧结构。在这方面,《洪湖赤卫队》和《党的女儿》可以说是范例。但当下的一些剧目却不讲故事或不会讲故事、缺乏细节、结构松散。大多数剧目不但放逐了“三一律”,而且还以时间跨度大、空间转换频繁为能事,故难以形成具有内在结构力(戏剧性)的戏剧结构,更不用说去追求歌剧的理想状态——“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的同一”。(2)“歌剧故事”应是一个考虑到歌剧体裁样式、表现形式、舞台呈现的故事。这首先是歌剧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应满足声部相对齐全、歌唱形式多样的需要。众所周知,歌剧中的声部划分,作为角色的类型化,是歌剧重要的体裁特征。故拟作歌剧故事的故事中,必须具有与上述声部划分相对应的人物,以确保这种声部相对齐全。歌剧的歌唱形式也应多样化,一般有独唱、重唱、对唱、合唱。因此,拟作歌剧故事的故事中就应有适合各种歌唱形式(尤其是合唱)的人物和场面。比如,根据鲁迅小说《伤逝》改编的同名歌剧,其中只有子君(女高音)和涓生(男高音)两个人物,但为保证声部的相对齐全,就增加了女歌者(女中音)和男歌者(男中音)镶嵌于音乐结构中,并设计了合唱队(类似于未出场的群众演员)的幕后合唱。歌剧《雷雨》中的合唱则是作为“显影合唱”配上去的。歌剧《屈原》做大郭沫若原著中的婵娟一角,其目的也是为了使其中的女高音更丰满。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歌剧故事”并不是一个原始故事,而是需要剧作家根据歌剧体裁特征去精心编排的故事。其次是歌剧中人物(角色)的文化形象(文化身份)应与歌剧中的特定唱法、特定声部根深蒂固的文化形象相匹配。众所周知,歌剧中的声部划分是人物类型化的结果,每个声部对于所塑造的人物相对具有思想性格、精神气质上的规定性,尤其是其文化身份、文化形象的规定性。这就要求剧作家对不同声部人物的思想性格、精神气质的设定,应该与声部对于人物思想性格、精神气质乃至文化身份、文化形象的规定性相符。为何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被改编成了多个版本的同名歌剧?内在原因就在于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角色)精神气质上、在文化形象、文化身份上,与美声各声部所固有的文化身份、文化形象极为匹配。比如,其中的林道静形象就主要是一个为女高音所塑造的形象。一般说来,“全唱型”正歌剧风格的歌剧及其“美声”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但它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这关键要看所设计的音乐与“美声”之间是否存在文化冲突。延安首演《白毛女》时喜儿扮演者李波、王昆“洋改土”,就是一个例证。当然,音乐如何写?也须要考虑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文化身份。不是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人物都适合用“全唱型”正歌剧风格歌剧去表现,用“美声”去表现。含有“板腔体”唱段的戏曲风格民族歌剧及民族唱法的适应性更弱。故为这种民族风格编故事、写本子就得选择那种与“板腔体”唱段在文化形象上相吻合的人物。这些都说明,任何题材和故事,只有当它与特定的歌剧体裁及其艺术特征相匹配,才能成为一个歌剧故事。但在当下歌剧创作中,不遵守这种审美原则的情形也不鲜见,常常展现出人物思想性格、精神气质、文化身份与特定唱法、声部所固有的文化形象、文化身份之间存在差异、发生错位。综上也可得出一个结论:歌剧的剧本编创需要剧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戏剧决定音乐(内容决定形式)的审美原则,进而与作曲家密切合作,充分考虑歌剧(戏剧样式)及其类型(体裁形式)对于歌剧故事及其剧本编创上的特殊要求。
坦率地说,当下中国歌剧创作的问题,首先便是剧本编创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将一些不适合歌剧表现的故事搬上了歌剧舞台,而未能考虑故事与歌剧这一戏剧样式及歌剧类型之体裁特征之间的排异性。有的故事的确很精彩、很感人,也很有意义,可以用多种戏剧样式甚至别的文艺形式去表现,但却不适合用歌剧去表现,或者不合适某个歌剧类型去表现,故最终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歌剧故事”。从本质上说,歌剧是一种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呈现戏剧矛盾冲突的“音乐戏剧”,其中音乐所表达出的情感、呈现出的风格、所塑造出的形象,与故事中的人物之间的匹配度是难以把握的。因此,把握匹配度、消除排异性是剧作家的重要任务。指挥家杨洋说“《萧红》的选题很有音乐眼光”[1]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女作家萧红是一个很适合用歌剧去表现的人物。还有,歌剧中的歌唱(尤其是主要角色歌唱和美声歌唱)一般须具有一定的炫技性。这也是歌剧重要的体裁特征或审美追求。但这种“炫技美”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又必须有特定的角色与之匹配。比如,让一个严谨的人或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去炫技就不大合理。这种不匹配在舞台上就显得十分尴尬。由此可见,歌剧(尤其是“全唱型”正歌剧风格歌剧)中的人物,最好是那种性格比较鲜明或张扬的人物,即那种“喜则欲歌欲舞,怒则欲杀欲割,悲则欲泣欲诉”的人物。比如,《驼骆祥子》中刘四爷这个人物,就是一个很好的戏剧人物,在京剧中显然是一个“黑头”,在歌剧中就必然是男低音。这个人物无疑为这部歌剧增色不少。总之,歌剧故事不能一团和气,歌剧人物不能温文尔雅,因为一团和气就没有矛盾冲突,温文尔雅就没有思想性格。这大概也是歌剧的一般规律。“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编创是一部歌剧是否能够获得成功的前提。因此,剧作者对一部歌剧的创作负有重要责任。题材和故事的选择和编撰,戏剧矛盾的建构和呈现,思想主题的设定和提炼,歌剧及其体裁样式之间的配适度,都需要剧作家通盘考虑、系统决策,并作出符合“歌剧思维”的权衡和取舍。然而,这些最终都取决于剧作家对歌剧作为音乐戏剧的认识和理解。这些都昭示出,为歌剧写本子的剧作家必须具有多重、超凡的艺术修养:有作家的底蕴,以保证剧本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有音乐家的素质,不仅能写好唱词,而且深谙音乐表达,进而使自己编织的戏剧结构能给作曲家提供灵感、便利和空间(2)歌剧《骆驼祥子》编剧、著名剧作家徐瑛就曾说:“歌剧编剧我觉得最重要的,除了文学修养,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他要懂音乐。”“歌剧你要更多考虑的还是歌唱,就写的词是要唱的。”(2015年歌剧《骆驼祥子》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时接受记者的采访。参见“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有戏剧导演的思维,懂得舞台调度,以保证场景切换不借助现代舞台科技也能流畅、便捷。但在中国歌剧舞台上这样的剧作家实不多见。
二、歌剧不是“歌的剧”
歌剧中的唱段不同于歌曲,歌剧中的管弦乐并非歌曲伴奏或一般意义上的戏剧配乐。歌剧不是“歌的剧”,而是“音乐戏剧”。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为何中国歌剧总是不能抹去“歌曲剧”的痕迹?这与中国歌剧的百年历程从“歌曲剧”开启相关。中国最早的歌剧样式——黎锦晖儿童歌舞剧,就是“歌曲剧”,并以其儿童歌舞曲为依托;接着的左翼歌舞剧(如《扬子江暴风雨》)、中央苏区的歌舞剧(“小调剧”)也都是“歌曲剧”。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歌剧发展迈出新步伐,于是“歌曲剧”痕迹有所淡化。这就在于,中国歌剧开始了借鉴西方正歌剧的探索。正是在这种探索“全唱型”歌剧的舞台实践中,中国歌剧(如《秋子》)中的一些唱段逐渐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歌曲的咏叹调、宣叙调、咏叙调风格。此其一。其二,中国歌剧开始走戏曲的道路,进而使一些歌剧唱段(如延安原版歌剧《白毛女》第四幕中的唱段)具有板腔体结构特征。但无论是借鉴“全唱型”歌剧的咏叹调、宣叙调、咏叙调,还是借鉴戏曲的板腔体结构,都未能彻底抹去这种“歌曲剧”痕迹。
以致当下,一些剧目仍呈现为一首接一首歌曲的并联,如同晚会上的“歌曲联唱”(即所谓“串烧”),最终就有悖歌剧(尤其是“全唱型”正歌剧风格歌剧)唱段风格,进而有悖歌剧(音乐)的体裁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类似歌曲的歌剧唱段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它有悖歌剧唱段风格,而在于放逐了它作为歌剧唱段的叙事性和戏剧性。其唱词(或称“剧诗”)如同歌曲大多都在抒情而非叙事,不是通过唱词推进剧情,而多为一些有碍故事情节发展、戏剧矛盾展开的内心独白,最终是有“诗”无“剧”的歌曲(song),而不是唱段(aria)。这就与歌剧唱段注重叙事性的审美原则相悖。从音乐上看,这些类似歌曲的歌剧唱段也大多较为流畅、优美,不用一个不协和和弦,不用一个和弦半音或调式半音,甚至像当年解放区小歌剧一样,用简单的分节歌,使多段结构相同的歌词共用一个结构短小的音调。这些都使音乐没有了内在的紧张度,进而也就没有了基于对比的戏剧张力——音乐的“冲突性”,最终也难以表现其戏剧矛盾冲突。这正是这种“歌曲剧”最主要的弊端。究其原因,除创作者力图用类似歌曲的唱段及其大众性取悦听众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大多数歌剧作曲家都是歌曲作曲家。但即使是歌曲作曲家,也有例外。比如,歌剧《屈原》中的唱段,可谓施光南呕心沥血之作。为了写好这部歌剧,最终倒在钢琴前,不得不由他人(史志有)完成其配器。可以说,这部歌剧中的每一个唱段都是经得起推敲的,都具有作为歌唱唱段的叙事性和戏剧性。这就是说,其中一些抒情性唱段作为人物内心独白也具有推进剧情的作用。歌剧《伤逝》亦如此,其中也不乏抒情性唱段,但这些唱段(如《迷人的夏日黄昏》《一抹夕阳》《紫藤花》)也都恰到好处,并与咏叹调(如《风萧瑟》《不幸的人生》《刺向我心头的一把利剑》《告诉我》)形成对比。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说歌剧的唱段只能叙事不能抒情,更不是说歌剧中不能有抒情性唱段,而是说作为歌剧的唱段,无论是抒情唱段还是叙事性唱段,都必须有叙事性和戏剧性,或者说具有叙事功能和戏剧表现功能。不能像一些剧目那样,将叙事和戏剧性表达更多地交给对白或其他因素,留给唱段的更多是抒情。此乃歌剧创作之大忌。
当下一些歌剧成为“歌的剧”也与歌剧中管弦乐的贫弱不无关系。歌剧中的管弦乐包括序奏、间奏、后奏、伴奏和舞台动作(包括舞蹈场面)配乐。对于大部分中国歌剧而言,其管弦乐创作是相当平庸的,姑且不说不能真正承担其戏剧表现功能,就从管弦乐配器而言,也相当“Low”,充其量也就是个晚会水平。就像这些剧目中的合唱还停留在解放区小歌剧水平,与中国当代合唱音乐发展水平严重不匹配一样,其管弦乐创作水平也与不断发展的中国交响乐发展水平不对称。这里就姑且不谈序奏简略,后奏改“回放”或由隆重的“谢幕”所替代,间奏也因现代舞台科技的无所不能而显得多余,就说作为伴奏的管弦乐和配合舞台行动(action)的管弦乐。大多数歌剧中唱段的伴奏都写得比较简单,也就是一个歌曲(不包括晚期浪漫主义艺术歌曲)伴奏的水准,不仅不能与歌唱声部相辅相成(相互融合),或相反相成(对位或对比),并体现出不假歌唱的自身价值,而且还在和声上极其简单,配器上极其简陋。能达到歌剧《骆驼祥子》《屈原》《兰花花》唱段的管弦乐伴奏水平的剧目实不多见,而歌剧《屈原》的配器还是在施光南病逝后由他人完成的。可见这不光是一个创作意识或审美观的问题,还是一个创作态度问题。总之,歌剧中的管弦乐不是歌曲的伴奏或一般意义上的戏剧配乐。当然,这与中国重视声乐的音乐审美传统相关,也与多数观众对其管弦乐的无所谓相关。虽然中国歌剧中的管弦乐不能都写成晚期浪漫主义风格的“声乐交响曲”(如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乐剧”、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的四首歌曲》、郭文景的《蜀道难》),但也不能因为潦草而放逐了作为唱段伴奏、歌剧管弦乐最基本的体裁特征。这种管弦乐的贫弱,就使得一些剧目进一步凸显出“歌的剧”的特征。
歌剧作为一种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呈现戏剧矛盾冲突的戏剧,音乐至关重要。对于一部歌剧来说,如果音乐不好,别的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如何使歌剧中的音乐形成一个独立的音乐结构(至少不看舞台、不看屏幕闭着眼睛也能听得进去),进而使这种音乐结构与戏剧结构相“统一”,乃至相“同一”,更是歌剧音乐创作所应坚持的审美原则。
三、先进的舞台科技是把“双刃剑”
值得注意的是,在导演主导下的当下歌剧创演中,舞美和灯光设计借助先进的舞台科技使人大开眼界。就舞美而言,大多数设计者不仅没有借鉴中国戏曲舞台的虚拟性和写意特征,但即便是按西方戏剧在舞美设计上的写实性原则,其制作则也有必要做一些“减法”,进而使舞台装置作为象征性或标识性实物存在,以体现出“简约”的原则。然而,中国歌剧舞美设计就常常令人匪夷所思,非但未能认识和把握中国戏曲的虚拟性,而且还打破了西方歌剧节俭、实用的舞美设计原则,以致比西方歌剧的舞台还要“真实”。这只能说另有原因。笔者以为,这种追求“真实”甚至“逼真”的舞台制作,显然对“三精”(“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3)“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简称“三精”,语出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原则中的“制作精良”作了片面或错误的理解。这种近乎奢华的舞美设计,不仅极大提高了整部歌剧的制作成本,还挤占了一部歌剧用于编剧、音乐创作、歌剧表演上的经费,最终必然影响到歌剧的质量,而且这种精美、奢华的舞美设计还将极大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以致减弱甚至放弃对于戏剧、音乐、表演这三大主体上的审美追求和审美判断。同时也应看到,隐藏在这种高成本舞台制作后的科技化装置,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舞台场景切换和调度上的便捷性,但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歌剧创作中戏剧结构设计和音乐创作上的难度,并最终使歌剧走向“异化”。于是,作为歌剧音乐重要组成部分的间奏曲(幕间曲)也可以不要了,或者就一二十个小节,因为更台速度飞快。
当下歌剧的灯光设计也堪称一绝。由于制作上的不计成本,一些顶级制作团队往往还能通过装置和灯光将一个舞台切分为多个空间,让演员在不同的空间表演,进行立体呈现,以致出现了中国歌剧特有的表现形式——“隔空对唱”。这就是在两个角色(一般为男女主角,其中一人不在场)置于舞台不同方位,独唱时用一柱灯光跟踪,对唱时用两柱灯光分别跟踪并将其隔开造成不同的空间,重唱时两个空间合一,完成穿越时间、跨越空间的对话。在传统歌剧中,对唱只能是在同一空间(境遇)中进行,而不能“隔空”,最多只能像一些剧目中的合唱采用“幕后合唱”或“显影合唱”(如《洪湖赤卫队》第四场《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一曲中,韩英和赤卫队的互动就处理为“显影合唱”(4)参见:洪湖赤卫队(剧本)[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60,P43。)一样,将那个不在场的人物放在幕后(如歌剧《江姐》第二场《革命到底志如钢》中就将演唱《红梅赞》的彭松涛放在幕后)。显然,这种穿越时间、跨越空间的处理方式实质上来自电影“蒙太奇”手法,只能放在歌剧电影中(上述这段“显影合唱”在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中就运用成了镜头的转换和剪辑),如果出现在歌剧舞台上就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歌剧中“对唱”的本质(同时空、同境遇的交流与对话)。
还是由于制作上的不计成本,电子视频(LED)普遍使用,以替代传统底幕(画布或幻灯片)。这本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问题是这种电子视频搞得太花哨。由于这种电子视频可以在幕后通过遥控操作,故在演出中切换得十分频繁。这样,歌剧舞台上充斥着“拉洋片”“蒙太奇”等有悖歌剧创演规律的现象。一些剧目两个小时就操作了几十个场景,甚至还借助电子视频和舞台数字技术将电影“闪回”“定格”“特写”及推、拉、摇、移等表演手法和镜头语言搬上了歌剧舞台。这些电子视频及数字技术的运用拓展了舞台空间,增强了艺术表现力,但同时又对歌剧作为舞台演剧、作为音乐戏剧的体裁特征进行了残酷的挑战。从这里也不难看出,无所不能的现代舞台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给舞台转换和调度带来便捷,又使歌剧创演偏离其本来的轨道。这是值得深思的。
四、歌剧评论应成为真正的“啄木鸟”
加强歌剧评论,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歌剧的特殊规律,围绕中国歌剧的创作表演问题、舞台呈现问题、运营传播问题进行歌剧理论建构,力戒歌剧评论庸俗化,引导观众从盲目“叫好”转向理性感知、客观评价。这无疑也应成为共识。但当下歌剧评论却具有庸俗化取向,未能成为真正的“啄木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他说:“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2]他还指出:“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3]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歌剧评论没有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去写。能给一部失败的歌剧提意见、提建议的人都很少,更不用说提出颠覆性意见。
中国歌剧为何搞得不那么好,除认识问题、创作水平问题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洪湖赤卫队》等剧目那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5)参见:欧阳谦叔.歌剧探索三十年[J].音乐研究,1984,(2),P50-70;张敬安,欧阳谦叔.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谈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音乐创作[J].人民音乐,1977,(3),P17-20.郭文景的歌剧《驼骆祥子》之所以成功,就因为这部歌剧他写了三年,何况此前还有交响合唱《蜀道难》及室内歌剧《狂人日记》《夜宴》《诗人李白》打底。不少剧目都是作曲家的处女作,此前不仅没有写过歌剧,甚至连交响音乐也没有写过,但这些剧目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样的歌剧可能好吗?一些剧目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民币,还有几十位具有高级专业资格的艺术家参与歌剧创演,但弄出来的东西不尽人意,在本子和音乐上还不及革命战争年代作为战时文化的剧目,而只有舞美、灯光、“服化道”上的“高大上”。这绝对不只是一个认识问题或艺术创作水平问题,而是关乎创作者的态度,关乎创作者的价值取向。那么,歌剧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三精”(“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曾指出:“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4](P8)这就强调了“思想精深”的重要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题材决定论”,不要盲目以为革命历史题材歌剧就可以不顾艺术质量。“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文化和旅游部原部长雒树刚曾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援引毛泽东的这段话阐述“艺术精湛”的重要性。(6)参见:雒树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J].毛泽东研究,2019,(1),P10.由此可见,“艺术精湛”也十分重要。2019年4月1日,笔者在深圳参加张千一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的专家审听会,会上一位领导同志曾说,“主旋律”题材的作品如果搞不好,那就等于“拉倒车”。这句话是很精辟的,也具有理论勇气的。但当下一些革命历史题材歌剧在本子和音乐上都是贫弱的,在表演上也不尽人意。当然,推动新时代中国歌剧从“高原”到“高峰”,不仅需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还需要“制作精良”,“三精”一“精”也不能少。什么是“制作精良”?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淡到《包法利夫人》和《红楼梦》时所说的那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5]。这种精神就是“工匠精神”。但对于歌剧创作而言,“工匠精神”不能只落在舞美、灯光和“服化道”上,更要贯彻在剧本和音乐创作上,在“表导演”上;不能把“制作”仅理解为歌剧的后期制作,而应包括前期的剧本编创和音乐创作、导演构思、唱段排练。否则,不仅不能写好剧本、写好音乐、搞好“表导演”,而且还会让后期的豪华制作挤占了这三者的创作经费。总之,对“三精”的认识、理解、把握,是推动新时代中国歌剧从“高原”向“高峰”迈进的重要审美原则,也是新时代中国歌剧评论所应坚守的评价标准。
结语
中国歌剧的问题主要在于创作,而创作问题又主要在于剧本编创。第一,许多剧目都未讲述真正意义上的歌剧故事,而选择了那些基本没有戏剧矛盾冲突的故事;即使选择了一个具有戏剧矛盾冲突的故事,也未能将展现戏剧矛盾冲突作为叙事的中心任务和关键环节。第二,许多剧目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捉襟见肘,不是没有塑造出具有典型性人物形象,就是使人物形象塑造脱离特定文化与历史语境,乃至脱离戏剧情节的上下文,以致缺乏生活依据、缺乏艺术真实、缺乏戏剧支持;或是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背离戏剧发展逻辑及其内在依据,以致使戏剧矛盾的最终解决显得突兀、生硬。第三,许多剧目以跨越时空进行史诗性宏大叙事为能事,并将宏大叙事切分为若干“情景性表演”,而未能在一个相对“狭小”的时空内“以小见大”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以致戏剧矛盾冲突未能诉诸连贯自然、生动可感的戏剧情节,甚至因此而彻底放逐戏剧性。第四,许多剧目未能遵循歌剧艺术的独特规律,放逐歌剧的体裁特征,不仅未能构建起那种适合音乐呈现的戏剧结构,而且还在人物设计时忽视了声部相对齐全的要求,在情节设计时忽视了演唱形式多样的要求,或弱化了唱词的叙事功能,将唱词写成了一般的歌词。当然,以上还都是一些表层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剧本的文学性、思想性问题以及思想性(或思想主题)表达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和艺术问题。音乐创作也问题多多,除音乐创作上的技术性和艺术性问题之外,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歌剧作曲家在整个歌剧创演中丧失了其主体地位,既未对编剧提出必须按照歌剧特殊规律写本子的要求,又未对导演不以音乐为中心进行艺术传达的创作思路进行矫正。上述歌剧创作中的问题和症结使我们有了一些关于歌剧的“常识”:第一,歌剧故事不能一团和气,必须充满矛盾斗争,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戏”;没有矛盾斗争,不仅不耐看,还会让作曲家在“巧妇难为无米炊”中把音乐写得不中听。第二,歌剧人物不能温文尔雅,必须有棱角、有性格、有特点,便于塑造为典型性的舞台形象、艺术形象,乃至文化形象,并成为戏剧矛盾冲突的主体。第三,歌剧唱段不能过于好听,太好听、太流畅就会离“谱”,必须具有承载戏剧性的内在张力和紧张度,且不能沉溺于抒情而放逐叙事,因为歌剧不是“歌的剧”。认识和把握这些“常识”,或许就能使歌剧创作离失败更远一些,离成功更近一些。总之,推动新时代中国歌剧创新发展,向“高原”“高峰”迈进,需要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歌剧艺术的特殊规律,树立和增强“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不断推进原创剧目的“经典化”,提高原创剧目的成活率;歌剧理论评论应具有问题意识并勇敢针砭中国歌剧创演的问题,并切实起到指导实践和“啄木鸟”的作用。这些应该成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