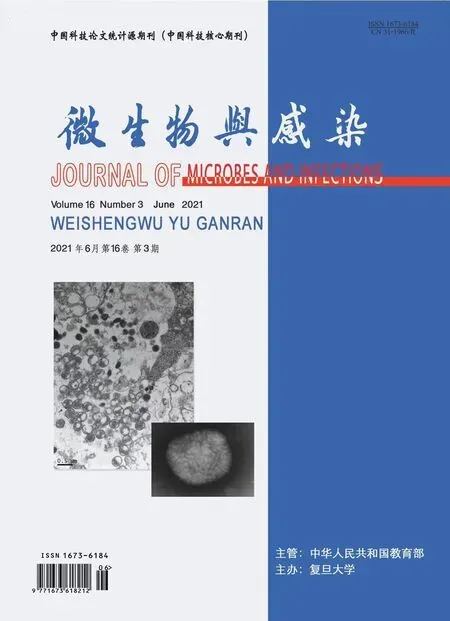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和2019冠状病毒病治疗研究进展
傅掌璠,艾静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上海市传染病与生物安全应急响应重点实验室,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上海 200040
冠状病毒属于冠状病毒科,目前基于其基因组结构可分为4个属(α、β、γ、δ)。α冠状病毒和β冠状病毒仅引起哺乳动物感染,例如动物胃肠炎以及人类呼吸系统疾病,大多数以轻度上呼吸道感染为主,中枢系统以及急性肝炎极为少见[1],γ和δ冠状病毒主要感染鸟类。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暴发,SARS实验室确诊病例达 8 096 例,其中774例死亡[2];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造成实验室确诊MERS 2 494 例,其中858例死亡[3];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于2019年末暴发并蔓延全球,至今(2021年5月20日)确诊超过 16 552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43万例[4],目前这些数字还在持续上升。冠状病毒可以跨越物种,对人类造成危及生命的感染,并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当前对于这些新的冠状病毒所致疾病的诊治仍在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中,现针对3种传染病的治疗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期望对临床诊治有所帮助。
1 SARS-CoVs和MERS-CoV简介
SARS-CoVs (SARS-CoV和SARS-CoV-2)和MERS-CoV属于冠状病毒属,具有27.9~30.1 kb的大型单股正链RNA基因组。大多冠状病毒结构相似:开放阅读框(1a/1b)占基因组2/3,编码非结构蛋白多聚蛋白pp1ab,随后被两种病毒蛋白酶,即3C样蛋白酶(3C-like protease,3CLP)和木瓜蛋白酶样蛋白酶(papain-like protease,PLP)裂解,产生病毒复制所必需的非结构蛋白。下游开放阅读框编码结构蛋白,包括刺突(spike,S)蛋白、核衣壳蛋白、包膜蛋白和膜蛋白,以及非结构蛋白[5]。S蛋白不仅能介导病毒结合受体(SARS或COVID-19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MERS为二肽基肽酶4)进入靶细胞以及帮助病毒扩散,还能诱导机体对病毒产生免疫反应,形成细胞免疫,同时它又是中和抗体作用的靶点[6]。此外,SARS-CoV-2的S蛋白比较长,这是三者之间唯一差异显著的地方,可能是SARS-CoV-2能快速传播的原因[7]。包膜蛋白和膜蛋白共同指导病毒颗粒的组装,并且膜蛋白在病毒出芽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核衣壳蛋白是一种RNA结合蛋白,与病毒复制转录相关,其与中枢疾病和肝炎的发生有密切联系[1]。
2 SARS、MERS与COVID-19的临床特征
MERS、SARS以及COVID-19多发生于成年人(MERS中位年龄为50岁,SARS为40岁),临床特征大致相似,感染初期临床表现呈非特异性(发热、咳嗽、肌痛、呕吐、腹泻等),随着病情的发展,轻者无明显症状,重者出现呼吸衰竭。患者的实验室检查常见异常结果为乳酸脱氢酶升高、转氨酶升高和淋巴细胞减少等。与另两种疾病相比,COVID-19存在一定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8-9]。
就传染性而言,最强非SARS-CoV-2莫属,其基础繁殖率(R0)达2.5[10],SARS-CoV较低为2.4左右[11],MERS-CoV最弱,R0为0.69[12];病死率与R0相反,MERS略高一筹为40%[13],SARS为9.6%[13],COVID-19为2%[14]。成年人感染SARS-CoV-2后,5~6 d出现症状和体征(平均潜伏期5~6 d,范围1~14 d)[10];SARS-CoV感染到发病时间为6~7 d(平均潜伏期4 d,范围1~12 d)[11];MERS-CoV平均潜伏期5 d,范围2~13 d[13]。
3 治疗
目前尚无针对性疗法,一般根据病程进展的情况,在积极支持治疗的同时再辅以抗病毒治疗[5],我国的中医中药治疗也应用于实际治疗中[15]。鉴于SARS至今再无病例,下文以COVID-19为主进行介绍,并与MERS的治疗方法进行对比。
3.1 支持治疗
支持治疗包括:①住院隔离, 卧床休息;②适当补充体液;③根据病情监测生命体征;④及时给予有效氧疗,包括鼻导管、面罩给氧和经鼻高流量氧疗;⑤抗菌药物治疗,但应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16]。
3.2 抗病毒治疗
3.2.1 核苷类似物核苷类似物,例如利巴韦林、瑞德西韦可以抑制冠状病毒RNA聚合酶。冠状病毒复制时,在RNA聚合酶作用下,核苷类似物参与形成病毒的遗传物质,形成无作用的RNA链,导致病毒复制无效,使病毒致病性大幅下降[17]。
我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16][以下简称《诊疗方案(第八版)》]不推荐单独使用利巴韦林治疗COVID-19(单药未缩短转阴时间,也没有降低死亡率[18]),建议联合干扰素(成人每次500万U或相当剂量,每日2次,雾化吸入)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成人200 mg/粒和50 mg/粒,每次2粒,每日2次)[16]进行治疗。
SARS流行期间,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与利巴韦林联用有显著的抗病毒治疗作用[19]。对于MERS,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联合干扰素-β1b治疗可改善MERS-CoV感染的普通狨猴预后[20]。2020年5月,香港招募了127例COVID-19患者,86例患者在早期使用利巴韦林与干扰素-β1b、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三联抗病毒疗法进行治疗,结果显示,联合用药可以显著缩短转阴时间,但该试验还缺乏大规模双盲试验验证[21]。利巴韦林曾被用于单药或联合干扰素治疗SARS和MERS[22-23],但与未接受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治疗的患者反而需要更多的输血治疗[22],且未明显降低病死率[24]。因此,利巴韦林的安全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瑞德西韦用于治疗COVID-19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诊疗方案(第八版)》[16]无推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及《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均发表了瑞德西韦的临床研究数据,结果均显示该药有积极作用[25]。但在中国武汉进行的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中[26-27],并未观察到该药改善病情、降低病死率的作用。瑞德西韦的治疗效果仍需更多设计严谨的临床试验证明。
3.2.2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洛匹那韦是一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蛋白酶抑制剂,可阻止gap-pol多聚蛋白的分裂,产生无感染力的病毒颗粒,被批准用于抑制HIV的复制。洛匹那韦通常与利托那韦联合使用,以延长洛匹那韦的半衰期[28]。
《诊疗方案(第八版)》[16]不推荐单药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国内外的临床研究均表明,单药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无效[18,28]。我国在2020年3月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开放的临床试验:除标准护理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单药给药(400 mg/100 mg,每天2次,共14 d),结果显示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并未改善COVID-19患者的预后,反而增加了胃肠道不良反应的发生率[29]。
3.2.3 中和抗体的被动免疫疗法使用患者恢复期血浆或单克隆抗体(mAbs)进行治疗是疾病干预的潜在快速途径。这种方法有如下优势:随着病例数量的增加,恢复者数量变大;只要这类人群的抗体效价足够高,并且愿意捐献血浆,就可作为一种低技术要求且比较安全的治疗选择。此外,人类的mAbs生产技术已经成熟,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方式相对简单[5]。一项包含32例SARS-CoV感染和严重流行性感冒的描述性研究分析发现,与安慰剂或无治疗相比,在症状出现后早期给予恢复期血浆,可使患者病死率显著下降,但这类研究通常缺乏对照组,并具有中度或高偏倚风险。这种疗法应在设计周密的临床试验中进行并开展研究,MERS-CoV感染也应如此[30]。现已有团队在阿卜杜拉国王国际医学研究中心招募MERS重症患者进行随机对照试验[31]。在动物实验中,接种MERS-CoV后,分别在6 h和48 h时用高滴度超免疫血浆或mAb m336[32]处理普通狨猴,两种疗法均能减轻狨猴的临床症状,但仅在超免疫血浆组中发现实验动物呼吸道病毒载量减少,且达不到预防的效果[33]。恢复期血浆由于要依赖痊愈患者的捐献,产量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研制出能中和病毒的“人造”抗体是关键。有研究给转染色体(Tc)牛接种实验性MERS-CoV疫苗,以产生大量完全人的多克隆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随后在Ad5-hDPP4受体转导小鼠经MERS-CoV感染前或感染后12 h、24 h和48 h施用单剂量IgG抗体(TC牛生产),显示此种疗法可迅速导致其病毒滴度接近或低于检测极限[34]。
迄今为止,基于SARS-CoV S蛋白的受体结合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 ,RBD)、S1或S2区进行设计,已开发出多种体外有效的mAbs[35]。
美国再生元(Regeneron)公司的REGN-CoV2抗体鸡尾酒疗法已进行随机、双盲试验,所有参加试验的患者均经实验室确诊为COVID-19。试验中的患者按1∶1的比例随机分配,一组一次性输注8 g REGN-CoV2(高剂量),另外一组输注2.4 g REGN-CoV2(低剂量)或安慰剂。这项研究显示该药降低了病毒载量并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症状[36]。据美国礼来(Eli Lilly)公司报道:一种LY-CoV555抗体(从COVID-19患者体内采集抗体经大量克隆获得)也降低了病毒滴度并且无明显副作用[37]。虽然mAbs效果显著,副作用小,但是成本高昂并且难以大量生产。
对于治疗SARS已经进行动物试验的mAbs有80R、S3.1和m396,均可能单独或联合使用,以开发针对SARS-CoV的有效抗体疗法[35]。MERS相关的mAbs有20多种,其中大多数是人抗体或人源化抗体[38]。遗憾的是,目前这些研究仅停留于体外实验阶段,尚无可靠的已发表的临床试验结果证明其安全有效。
3.2.4 糖皮质激素《诊疗方案(第八版)》[16]推荐对于氧合指标进行性恶化、影像学进展迅速、机体炎症反应过度激活状态的患者,短期内(一般建议3~5 d,不超过10 d)使用糖皮质激素,建议剂量:甲泼尼龙0.5~1 mg·kg-1·d-1[16]。
Horby等[39]发表的一项随机、开放性对照试验中,比较了接受地塞米松治疗(每天1次,每次6 mg,口服或静脉连续给药10 d)与仅接受普通护理患者的结局,发现短期使用地塞米松能降低已机械通气重症患者的病死率,但轻症患者可能没有效果。糖皮质激素也是SARS和MERS重症患者常用的药物,有抗炎、抗渗出、抗高热、抗纤维化作用。但一般不长时间应用,以防止继发感染[40-41],及避免股骨头坏死和脂质代谢紊乱的后遗症[42-43]。
3.2.5 潜在的治疗方法主要分为蛋白酶抑制剂和旧药新用两大类。
对于蛋白酶抑制剂,SARS-CoV和MERS-CoV的2种蛋白酶(3CLpro和PLpro)对于病毒的复制至关重要,因此成为研究抗病毒靶向治疗的焦点。野漆树甙、草乙素和果胶素可有效阻断SARS-CoV 3CLpro的酶活性,可以将这3种类黄酮作为模板来设计抑制剂[44]。具有疏水性或糖核结构的黄酮类化合物可以作为开发有效的MERS-CoV-3CLpro抑制剂的模板[45]。针对病毒复制所需的解旋酶,抑制剂可从N末端金属结合结构域、铰链结构域和NTP /解旋酶结构域3个结构域着手进行设计[46]。目前,针对COVID-19的治疗,此类药物并无研究进展。
针对冠状病毒的特定抗病毒药正在开发中,现有疗法和药物都不尽如人意,而旧药新用可能为将来其他的抗冠状病毒疗法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这些药物在体外和动物研究中被证实具有有益作用,则可作为抑制病毒的第1道防线[47]。
《诊疗方案(第八版)》不推荐使用羟氯喹或联合使用阿奇霉素。磷酸氯喹的用法:18~65岁成人,体重>50 kg,每次500 mg,每日2次,疗程7 d;体重<50 kg,第1、2天每次500 mg,每日2次,第3~7天每次500 mg,每日1次[16]。氯喹对T细胞有抗增殖作用,并减少干扰素-γ、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等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抑制先天性免疫的激活[48]。
巴西进行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开放的羟氯喹单用或联合阿奇霉素临床试验,患者按1∶1∶1的比例随机分配,3组分别为仅接受标准护理、接受标准护理加羟氯喹(剂量为400 mg,每天2次)治疗以及接受标准护理加羟氯喹(剂量为400 mg,每天2次)并联合阿奇霉素(剂量为500 mg,每天1次)治疗,疗程连续7 d。这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结果显示,羟氯喹单用或联合阿奇霉素没有改善轻、中症患者的临床症状[49]。同样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以及JAMA的有关羟氯喹单用或联合阿奇霉素的试验结果,均表明羟氯喹无效[50-51]。
已批准药物包括洛哌丁胺、伊马替尼、氯丙嗪、甾醇代谢抑制剂、蛋白质合成抑制剂(依美丁、茴香霉素和奥美西汀甲琥珀酸盐),这些药物在体外筛选试验中显示出抗MERS-CoV和SARS-CoV的能力[52],须进一步研究能否应用于抗SARS-CoV-2,且需临床试验的验证。
3.3 中医中药治疗
我国传统医学历来对传染病的治疗颇有心得,中西医联合治疗可能取得较好的疗效。在SARS及COVID-19暴发之际,我国采用中医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分期分证,可能有减轻病情、缩短病程、减轻后遗症的作用[15-16]。
4 结语和展望
冠状病毒的暴发流行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无针对冠状病毒的特异性治疗方法。大量研究停留于体外或者动物实验阶段,特别是mAbs这种有潜力的药物,亦缺乏设计严谨的大型多中心临床试验,现有的临床研究存在明显偏倚,难以扛起重任。只有针对冠状病毒致病机制深入研究,才有希望设计出新药或者旧药新用,以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解决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