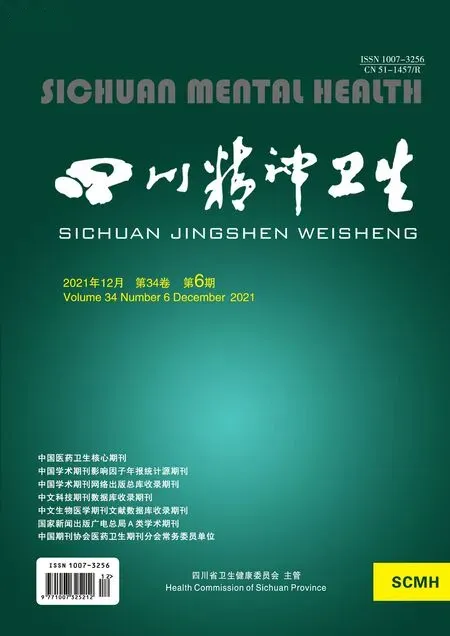抑郁障碍临床研究的基本科学问题
李凌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11)
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俗称抑郁症,是抑郁障碍最主要的一个亚类,目前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对此高度关注。中国脑计划中的疾病脑第一期研究主要涉及三个疾病:老年人痴呆、成年人抑郁症和青少年孤独症,可见抑郁症的重要性。那么,抑郁症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从宏观角度讲,几乎和所有的精神障碍一样,包含三个问题:第一,缺少客观诊断标准。目前抑郁症的诊断还是根据现象学、即临床表现来诊断,在对临床表型的判断中,会混杂很多主观因素,信度不足。第二,缺少根治方法。当前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对症,虽然有效,但结局并不令人满意。第三,病理机制不清。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会患抑郁症?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目前尚不清楚,假说很多,但都还没有最后的结论[1]。以上三个问题导致目前抑郁症的临床诊治面临重重困扰。在此重点讨论抑郁症诊断和治疗这两个领域中目前比较前沿的观念、研究结果及困扰。
1 诊 断
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公认的主流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有两大体系,一是美国的DSM系统,另一个是WHO的ICD系统。这两个系统在精神障碍诊断分类中基本相同,但唯有一个大类不一样,即情绪障碍或者称为心境障碍。在DSM-5中,情绪障碍一个是双相障碍,一个是抑郁障碍,二者是完全分开的两个大类,就是说它们在类别上几乎是独立的;但在ICD-11中,抑郁障碍与双相障碍同归于心境障碍,即抑郁障碍是心境障碍中的一个亚类。这说明抑郁障碍是一类非常有争论性的障碍,同样也说明按照症状学来诊断,抑郁障碍在诊断归属上也容易产生分歧。20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主要是从神经生化的角度研究生物标记物的分类,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扩展到从心理学特质、影像学、遗传学的角度来研究分类,并希望找到一些稳定的标记物作为诊断依据,但至今为止还没有最后的结论。2015年以后,影像学研究越来越多,2016年的一项研究[3]提出,根据静息态下6种神经环路的模式将抑郁障碍分成8个亚类,且作者认为这样的分类下疾病的临床表现也不一样。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磁共振将来能够作为诊断工具,那么有可能其信度就比根据症状来分类更稳定、一致性更好。2017年的一篇文章[4]报道,使用fMRI评估1 188例抑郁症患者,根据影像学特点,采用机器学习分类方法将其分成4个类型,这4个类型的临床表型也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根据TMS治疗的反应,作者发现第一类和第三类患者的治疗反应较好,第二类和第四类患者的治疗反应较差。说明这种分型确实是有类别的特点,否则患者的治疗反应应该是一样的,或者边界是模糊的。这也提示,磁共振或其他的影像学工具可能有助于在临床工作中找到一些具有诊断意义的标记物,来提高分类的精准性。但是根据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分类仍存在很多问题,目前有一些瓶颈没有突破。第一,特异性不明显,比如抑郁症、双相障碍、焦虑症有很多共同特点,包括前额叶、边缘系统、海马杏仁核等都存在问题。第二,分析方法不稳定,采用不同的方法分析同一个资料,结果不一致。不同参数、不同设备、不同时间得出的结果存在差别,这种对结果稳定性的干扰因素目前尚无法完全排除。且目前尚无公认的判断正常大脑的标准,更何况抑郁障碍本身就有异源性,如有的抑郁障碍患者伴焦虑,有的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有的是忧郁型特点,还有患者抑郁障碍特征不典型,有很多不同的亚类。这些临床表型的混杂性也给寻找诊断标记物带来困扰[1]。当然,临床工作是希望不管磁共振还是其他影像学都能够有稳定的分析方法,故寻找一些诊断标记物可能是有意义的。如果诊断的问题未解决,研究样本的异质性高,实际上也会影响机制研究和新药开发等。
2 治 疗
2.1 药物治疗
目前抑郁症的治疗有三大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药物治疗。不管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抑郁,均可使用药物治疗。2009年的一项研究[5]对20世纪80年代到2007年抑郁障碍临床药物研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均有50%的患者治疗有效,2000年以后依然还是有50%的患者治疗有效,三十多年间,安慰剂效应从30%上升到了40%,但其中有一个稳定的结果,就是药物治疗有效率高于安慰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药物治疗是有效的。2017年美国的一项研究[6]把FDA的200项研究(包括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接受目前所有的药物足疗程治疗后,三分之一以上的患者对现有的药物治疗甚至包括认知治疗均无反应。这些患者有什么特点?为什么治疗无反应呢?是神经递质的问题,还是病理机制不同?这些问题值得思考。这项研究还有一个结果,可能对临床医生有所启迪:初始治疗有效的平均时间是5.7周,临床治愈的平均时间是6.7周,所以在临床工作中切勿“急于求成”,如治疗两周就换一种药,甚至一周就换一种药,最后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即使把所有的药都尝试了,却也找不到一种有效的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主流的抑郁障碍治疗指南基本都提到治疗4周以上才调整治疗方案。
2.2 心理治疗
目前关于抑郁障碍心理治疗的研究也较多。2021年的一项研究[7]显示,认知行为治疗、人际关系治疗、精神动力学治疗以及行动激活疗法等几乎目前所有推荐的抑郁症的心理治疗方法,均优于等候治疗和一般的关注,不同方法之间的效果虽有一些差别,但差距并不大,说明心理治疗是有效的,而且这些心理治疗方法的可接受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020年的一项研究[8]结果显示,不管单用心理治疗还是单用药物治疗,其效果均不如药物治疗联合心理治疗。轻中度的抑郁症患者可以单用心理治疗,但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则不太主张单用心理治疗。因此,精神科医生要学习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师也需要了解精神医学知识。联合治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关注的话题。
2.3 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也是目前抑郁障碍研究领域的热点。在物理治疗兴起的众多原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有一点“江郎才尽”的感觉,如前所述,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治疗无效,所以,在物理治疗领域寻找新的方法,直接采用一些物理的方法调控患者神经精神的变化,从ECT到现在的TMS、DBS、tDCS、迷走神经刺激技术、三叉神经刺激技术等,都是通过刺激这些神经的某些神经元、神经核团或神经环路来改善抑郁症状。从临床研究的证据来看,这些方法似乎都有效[9],物理治疗成为难治性抑郁障碍最后的“救命稻草”。但真正用于临床抑郁症的治疗目前主要还是ECT和TMS,后起的这些物理治疗方法的效果仍然不如ECT。然而,这些物理治疗方法为什么有效?目前并不十分清楚。
关于物理治疗目前有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证据[4],如短时3分钟采用不同波段进行治疗等于30分钟的疗效,联用不同的物理治疗方法对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睡眠障碍等,尤其是相对偏功能性的轻度精神障碍进行治疗,效果比较突出。一项关于tDCS的研究结果[10]显示,tDCS的疗效优于安慰剂,但不如西酞普兰。总体来说,关于物理治疗效果的研究阳性结果较多,物理治疗的神经调控领域值得高度关注。
3 新药研发
如前所述,现有的治疗方法对三分之一的抑郁障碍患者效果不佳,所以需要寻找一些作用于新靶点的抗抑郁药物,如谷氨酸类药物、阿片系统调节剂、胆碱能调节剂、抗炎剂、神经激肽-1受体拮抗剂、加压素拮抗剂和神经再生促进剂等[11]。目前已经上市的两个新药,一是GABAA受体的变构剂,有理论认为围产期妇女GABAA受体减少,生产后如果恢复不及时,可能导致产后抑郁,GABAA受体的变构剂则可用于调节。研究结果显示其效果明确,静脉给药,治疗第一天就可产生效果,且疗效可维持30天。目前正在研发GABAA受体变构剂的口服剂,起效可能相对较慢[12-13],其疗效差异表现在治疗半个月以后,比SSRIs类药物的治疗效果好,且不良反应相对较少。二是氯胺酮,20年前的一位精神科医生对7名患者静脉给药,发现其起效很快,7名患者在2~3天内症状改善明显,且效果优于安慰剂组[14-15]。后来右旋氯胺酮被发现,鼻喷剂于2019年上市,但目前尚未在中国上市,还是很期待的。对于临床上很多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和急性期抑郁症患者,若能够快速给予有效的抗抑郁治疗,可增加患者的治疗信心,然后再等待其他的抗抑郁药物起效。
与免疫系统有关的抗炎问题,目前有很多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炎性因子水平增高[16],但它与影像学诊断研究一样,特异性不强。实际上所有的疾病都会产生免疫系统的变化,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患者的免疫系统变化差异不大,没有特异性,但有一些研究思路值得关注:如果抑郁症患者体内炎性因子水平增高,如IL-6水平增高,则患者对抗抑郁药物治疗无反应的可能性增加[17],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果对体内炎性因子水平增高的抑郁症患者同时给予抗炎治疗,是否可增加抗抑郁药的疗效呢?Kappelmann等[18]研究表明,抗炎因子确实可以改善抑郁症,有低到中等程度的疗效。因此,能否采用一些非甾体抗炎药治疗炎性因子水平增高的抑郁症,从而提高抗抑郁药的疗效?
本文由陈霞编辑根据李凌江教授在上海市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学术年会上的演讲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