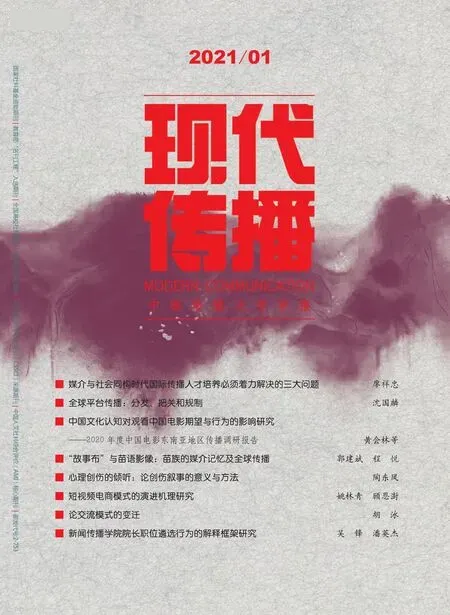“故事布”与苗语影像:苗族的媒介记忆及全球传播
■ 郭建斌 程 悦
2020年3月笔者之一①在云南省富宁县木央镇进行田野调查时,关注了“Hmoob苗族风”的快手用户,随后又添加了该用户李文②的QQ。李文当时的快手粉丝数量是9.5万(截至12月底,该数据有所下降,为9.2万)。据作者的初步观察,该用户所发布的“作品”大多是苗族③电影。翻看他以往上传的作品,每个视频都有不少点赞和评论,比如他上传的作品《老变婆1—16》④,评论区的留言中点赞次数较多的一条就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这种电影的?”此外还有大量的类似 “求更新!”“快更啊,这都是苗族同胞的等待”“怎么不更新完呢?快点更新!”等催促更新以及寻找视频资源的留言,李文会利用粉丝急迫等待更新的心理来获取粉丝为视频的点赞,他不会把电影全集一次性上传,而是把一个电影剪成多段,每段十分钟左右,每隔一段时间上传一次,他认为这种方式更容易得到更多的“赞”。
在写作本文时,笔者在快手上对用户名中带有Hmoob⑤的用户进行过初步统计,大约有294个。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也了解到,手机普及之前,苗语影像在当地苗族中产生过较大影响。时过境迁,伴随着手机的普及,原来通过影碟机观看光碟的方式逐渐转变为通过移动终端来进行观看,包括上述李文在快手账号上发布的那些苗语电影,大多是曾经VCD或DVD时代风靡过的苗语影片。
无论是当下“风行”的短视频,还是此前的光碟,其实均是伴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推陈出新而出现的,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现代传播媒介在苗族群体中普及之前,乃至更为久远的苗族文化历史时,所看到的却是无文字的苗族通过刺绣、“故事布”来记录、诉说自己民族的历史以及离散的辛酸。上述所有,宽泛地来理解,均具有“媒介记忆”的意义。
基于田野调查和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促使笔者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苗族是如何通过“故事布”来实践媒介记忆的?“故事布”背后又承载着怎样的苗族全球离散的历史?离散之后,苗语影像是如何成为苗族媒介记忆的书写方式、成为维系苗族“全球”联系的纽带的?在当下的新媒体环境中,苗族又是如何通过短视频等来续写其媒介记忆的?
这样的讨论,一方面,可以拓展我们对于媒介的理解,尤其在某些特定族群(或民族)中,在现代传媒进入之前,其实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原生”媒介;另一方面,当拓宽了对于媒介的理解之后,我们看到无论是“故事布”,还是苗语影像,均是一种与既往的“媒介记忆”研究所关注的对象有着较大不同的媒介形态,因此其记忆的书写与传播也与既往研究中的发现有所不同。
一、文献综述
1.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
除了“口耳相传”,人类的记忆,均是以某种特定的媒介作为载体被记录及传承的。这里所说的媒介,不仅限于现代传播媒介,也包括在现代传播媒介出现之前所有在人类传播活动中具有“中介化”意义的“中间物”⑥。但凡在这些“中间物”上以图形或文字所书写的内容,无论是对于过去的书写,还是对于当下的书写,一旦被“记录”下来,均具有“媒介记忆”的意义。这样一种对于媒介及“媒介记忆”的宽泛理解,与当下众多的聚焦于大众传媒对于“媒介记忆”的讨论所有不同。如,以受众为出发点讨论春晚和媒介记忆,即春晚是谁的和什么样的集体记忆⑦,通过“节点记忆”来考察中国互联网历史的媒介记忆⑧,研究民国时期中共报刊对“九一”记者节的纪念报道折射出的民国新闻界的历史意识和集体记忆⑨,讨论地方媒体如何建构汶川地震的集体记忆⑩,通过历史和不同的媒介场景,探究南京大屠杀创伤建构与记忆形塑的过程,讨论大众传媒过度对“创伤”媒介书写带来的问题,提出媒介记忆与历史记忆协同互动新路径,考察媒介记忆的独特性以及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交互关系所产生的利弊作用,通过“媒介记忆”来对融媒时代的民族文化传播问题进行讨论,以及对现代媒介语境下的民间文学保护的探究等等,不一而足。关于国外媒介记忆相关研究情况,有学者做过较为系统的综述,并这样写道:“近20年来,美国人文学者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围绕着‘犹太大屠杀’等创伤性历史事件的媒体表征问题提出了多个‘媒介记忆’理论,探讨了文学、摄影、电影及其他各类媒介和‘记忆’之间的关系。”除此以外,从事媒体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费·D.金斯伯格(Faye D.Ginsburg)在对原住民媒体(indigenous media)进行讨论时所提出的“银屏记忆”(Screen Memories)概念,对于本文有一定启发,但是金斯伯格所讨论的“原住民媒体”,与我们所考察的苗语影像并不相同。
2.关于“故事布”的研究
所谓“故事布”(story cloth),在相关的苗族研究中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是指1975年苗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特定刺绣,这种刺绣比传统抽象的视觉符号更加生动具体,人、动物、村庄、战争……这些具体的事物较为清晰的勾勒出了他们的经历。有学者认为,在一个特殊环境下,苗族改造了传统的花布(paj ntaub),使用新的技术和图案来把刺绣变成有待出售的商品,比如墙上的挂饰和桌子装饰,这些手工制品会吸引对针线活感兴趣的买家,并将其卖到国外赚取收入。美国学者杰拉尔丁·克雷格(Geraldine Craig)曾在泰国和老挝进行过关于苗族纺织刺绣品生产制作的田野调查,他提到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证据表明苗族刺绣风格从花布到故事布的转变和创新。还有学者关注苗族刺绣的数字化呈现手段,探讨了“故事布”所呈现的苗族的经验、历史和迁移。在中文文献中,有少数文献对“故事布”做过介绍,如有人认为“故事布”将抽象的传统苗族刺绣进行具象化,记录了Hmong人迁徙历史、传说故事和生活礼仪。
3.关于苗语影像的研究
战后移民的苗族渴望曾经的故乡,关于东南亚,尤其是关于老挝的影像作品帮助他们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搭建起了桥梁,并为其带来了心灵的慰藉。有学者在20世纪末就曾考察过苗语影像,认为此前美国的苗族文化研究者只关注传统的民间叙事,而视频作为一种新型的叙事形式,与传统的苗族视觉表现形式故事布具有同样的功能。贝尔德进行过比较详细的有关苗族的电影制作、电影市场方面的研究,他强调苗语影像对强化苗族记忆以及身份的重要性。苗族学者李亚(Gary Yia Lee)曾关注苗族音乐磁带、视频、纪录片和电影对本民族的影响,他认为苗语影像不仅帮助观众看到生动的苗族文化,而且通过观看用苗语讲述的故事,让出生在西方的子孙后代依旧保持他们的母语。散居海外并怀念过往,使苗族人通过互联网、国际旅行、音乐和视频来彼此联系。这导致了一种新的跨国意识,一个涵盖了他们现在生活的国家地理边界的全球性身份。路易莎·沙因(Louisa Schein)关注苗族寻根过程中男性对故土女性的情色欲望如何折射在影视作品中,苗语影像中经常将这些没有声音和权力的女性描绘成被男性凝视的对象,“故土”成为男性性幻想的对象,“性”成为人们对遥远地方的一种新的期待。沙因认为,从影像的跨国生产和发行,到观众参与和塑造他们想消费的剧本,进而煽动他们回到故乡去追求跨境的情色关系,媒体与这其中的许多方面都息息相关。另外,有学者发现,在苗语影像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并不仅仅是柔弱、依附且完全被男权操控的。以上研究均是对海外苗族(Hmong)的研究,对于中国国内自行生产的苗语影像,也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如张祺对贵州西部方言苗语影像的案例研究,Jenny Chio对贵州少数民族乡村视频的研究,不再赘述。
二、作为媒介记忆的“故事布”
“故事布”是苗族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维持生计所进行的一种文化创造。有研究者这样写道:
一块典型的故事布是围绕 “逃难故事”来进行视觉叙述。从逃难前的生活、逃难过程及最终结果,是故事布的基本叙事线,但每一块故事布都有变化,或者只描述其中一部分内容,例如呈现逃难前的老挝苗寨生活,或者逃难经历等等。与之前的绣花图案相比,故事布的图案更直观。
2019年10月,笔者之一到明尼阿波利斯的苗族文化中心(Hmong Cultural Center),看到一幅“故事布”。该“故事布”讲述了苗族在中国的情景。“故事布”的底部是有关苗族逃难的经历,由于越南战争,苗族跨过湄公河逃往泰国,成为泰国难民营中的难民,最终,他们有机会从曼谷机场前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由于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口述历史以及纺织品就成了记录历史、民间故事和神化传说的载体。在苗族的传说中,他们曾经是有书面文字的,但是由于他们言说或书写苗文并不具有合法性,苗族妇女只能通过她们复杂精妙的刺绣,将文字记录在裙子里,以此作为对统治者的抵抗。纺织刺绣中使用的几何图案和设计通常描绘历史事件、神话和精神实践,或代表与苗族生活世界中的那些与生计息息相关的物品、动物和植物,甚至苗族妇女裙子上的褶皱据说也象征着与苗族创作神话相关的丘陵和山谷。
由此可知,虽然“故事布”只是苗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刺绣形式,但是苗族刺绣作为一种历史的书写方式,是由来已久的。关于这方面,很多学者进行过讨论,不再赘述。在这里,本文想聚焦于“故事布”,从“媒介记忆”的角度对其进行讨论,这是既往相关研究较少涉及的。
对于“故事布”而言,所谓媒介,自然就是布,而上面所呈现的图案、造型等等构成了所谓的媒介内容。虽然“故事布”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是作为一种旅游商品,但是这一商品由于与民族传统工艺、历史遭遇等结合在一起,因此具有了某种历史叙事的意义。由于“故事布”本身是一种“个人书写”,因此,它与大众传播媒介那种组织化的书写方式不同,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在苗族刺绣网(HmongEmbroidery.org)上,还看到一幅与笔者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苗族文化中心所看到的“故事布”相似的另一块“故事布”,不过,虽然二者的主题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具体的呈现方式却存在较大差别。
这个“故事布”,左上方,一个村庄正在被飞机轰炸,飞机携带一种名为T-2霉菌毒素的化学武器,俗称“黄雨”。在右上方,两个人正在挖山药,其他人正在采集树皮和树叶作为食物。一些人付钱给老挝或泰国商人,让他们坐船过河(湄公河);穷人坐竹筏或香蕉树干漂过河。在河的另一边,泰国警察正在对苗族进行询问。
另外,由于“故事布”是一种民间创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虚构”,它与新闻报道基于事实的书写也不相同。
三、苗语影像与媒介记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美藉苗族开始用苗族语言制作家庭录像,后来一些人到泰国旅游,进而又去往老挝,探亲的同时也作为游客进行游览观光,他们开始拍摄自己的旅行,以捕捉自己的记忆,同时也为其他同胞带回珍贵的“回忆”。由于景致的相似,泰国的Khek Noi成为了苗族电影拍摄的重要取景地,苗族大多数电影都是在这里拍摄完成。贝尔德认为在许多苗族电影制作人的心目当中,该地可以被称为“Hmollywood”,可以与好莱坞或宝莱坞等其他重要的电影制作中心相提并论。
如前所述,学者们对海外的苗语影像进行过较多的讨论,由于海外苗族在异国他乡均为移民,因此,几乎所有的讨论,均是从“客居者”的角度来进行的。我们目前的田野调查地点是云南文山,在苗语中,对于云南文山,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Bangdala,意思是“发源地”“故乡”。据说老挝、泰国等国家的苗族,均是从云南文山流散出去的。因此,我们在云南文山所观察到的一些资料,可以作为海外苗语影像研究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下面所呈现的,是笔者之一在调研期间了解到的情况。
在田野调查中,多个报告人都提到了一部苗语电影——《诺丫与彩奏》(影片苗语名为:Nuj Nphlaib thiab Ntxawm)。这部电影是一个名叫Ger Vue的美国苗族导演于2001年在泰国拍摄制作的,直至2003年该电影作为海外苗族与文山苗族的文化交流物品,被文山苗族协会引入,所以该电影在片头处有“文山州文山海外苗族民间文化交流协会联合制作”的字样,简单来说就是海外苗族和文山苗族之间文化资源的共享。据报告人说,在这部电影之前,已经有若干苗族光碟在市场上流通,但大多反响平平,而《诺丫与彩奏》进入中国之后所引发的热潮,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苗语影像空前绝后的巅峰时期。这部苗语电影是根据苗族古老的神话传说改编而来的,故事的内容大致是:男女主角初次见面便一见倾心,但彩奏的善良和美貌被老虎精所觊觎,老虎趁诺丫外出吹芦笙之机,夺走了彩奏的魂魄,诺丫得知实情后便苦练武功,锻造兵器,追到老虎的洞穴并将老虎斩杀,然而此时彩奏已有孕,不久后生下两只小老虎。彩奏不忍将小老虎杀死,便将它们藏于山林的草丛中,诺丫发现后怒斩其中一只,另一只侥幸逃跑,数年后小老虎长大回来寻仇,彩奏阻止了“父子”二人的互相残杀,复仇的老虎精也最终放下了怨恨,回到森林中。这部苗语电影全方位地反映了苗族的文化与习俗,不仅拍摄的地理环境和生活场景与现实相近,其中的诸如木叶、刺绣、服饰以及芦笙等元素都是苗族所熟悉的,尤其是芦笙的旋律几乎贯穿于整部电影。神话故事是一种集体记忆,而这种记忆可以通过媒介来保存、讲述和传递,“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每一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都有一些本群体价值认同下的心理倾向,或是精神层面的社会动力结构。”
2004年,木央镇D村的陶虹为家里添置了电视和VCD播放器,这是整个村子最先购置播放器的家庭。在陶宏的记忆里,《诺丫与彩奏》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观看苗族光碟成了那时村里人重要的休闲娱乐以及社交的方式。早期村里看到的苗语影像大多是在海外拍摄制作,然后通过如前文提到的苗族文化交流活动,或是私人的探亲访友等方式流入中国。由于苗族群体对苗语影像的需求量巨大,所以复刻和贩卖盗版苗语光碟成为20世纪初中国西南边疆苗乡一种利润颇丰的生意。张鹏看到了这一商机。
张鹏是他们村仅有的两个大学生之一,2010年,张鹏从省城的一所专科院校毕业后,带着自己的妻子,以复刻苗语光碟为业。据张鹏回忆,每年过年前的11月、12月份是一年当中生意最好的时候,有时候仅一天就能赚1000元左右。据张鹏介绍,相比普通话的电影,苗语电影在市场上更受欢迎,其中销量最好的是《诺丫与彩奏》《龙女与孤儿》《天上仙女》等几部,而这些影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根据苗族的神话传说翻拍而成的。
张鹏认为,与光碟相比,手机视频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手机上的苗语电影和MV都是高清的,不仅免费,选择较多,而且观看便利,只要有网络随时都可以看。而对比起来,购买光碟要花钱不说,播放的视频质量就要差很多,而且光碟很脆弱,容易受损且不便于保存。另外,苗族当中少部分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翻墙软件浏览国外的网站,曾经苗语光碟垄断苗语影像市场的局面不复存在,张鹏夫妇渐渐发现这一行赚钱越来越难,2012年他们决定暂时把刻碟的机器闲置,到东莞一家手机配件工厂打工去了。
在过去近40多年的时间里,海外苗族在泰国等地生产出了不少了苗语影像作品,这些作品,主要的流向是美国,也有少部分流向了中国,回到了海外苗族的“故乡”。上文所说到的《诺丫与彩奏》在苗族的“故乡”所引起的反响,或许不亚于居住在美国的苗族。有研究者曾在文山进行过“苗语影像”的调查,在陈琳访谈中当地人时也讲到过《诺丫与彩奏》这部影片。陈琳这样写道:
一个80岁的苗族老人说:“这个故事我们刚懂事时就听说了,今天终于才得见。”影片中的人物性格、形象或品行也会对苗族人产生作用,一个妇女曾把她不孝顺的儿子拉来看碟,看完《诺丫·彩奏》后对他说:“你们夫妻不好,要学诺丫和彩奏啊。”
苗族利用影像技术之前,他(她)们通常是通过刺绣来进行历史书写,“故事布”也成为海外苗族一种特定的“媒介记忆”方式。当苗族掌握了影像技术之后,同样地,影像又成为了一种重要的书写文化、保存记忆的方式。苗语影像中的那些历史题材,更多触及的是苗族的神话、传说等。如果说“故事布”主要是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那么,像《诺丫与彩奏》这样的反映苗族神话、传说的电影,则是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自己听,甚至是通过这样的影片,散落在全球苗族实现着一种文化共享。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的:“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为苗族文化的共享提供了新的手段,他们通过跨越国家媒体传播的文化边界,来对抗自己的文化被有意地纳入国家想象之中。”
四、新媒体环境下的苗族媒介记忆的书写
2012年,张鹏停止了光碟销售,到外地找工作谋生。而过去的8年,也正是中国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高速普及的几年。网络以及手机在苗乡的普及,使得这里的媒介景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田野调查中笔者了解到,现在不少当地苗族使用“快手”App,该平台上汇集了大量的诸如苗族服装、苗族电影、苗族歌曲MV、苗语教学、苗语搞笑视频等各类与苗族相关的短视频。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发现,但凡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苗族,几乎都有用“快手”刷视频的习惯。随即笔者也注册了一个快手账号,通过与他们一起观看,关注不同的苗族快手账号,并加入诸如“苗族交流群”等类似的QQ群,以此来观察苗族群体如何利用手机软件观看苗语影像。
与“抖音”“火山”等短视频App相比,“快手”聚集了数量更为庞大的苗族用户。本文最开始所提到的李文,只是其中的一个,传播苗语影像的片段,也只是李文的快手账号所发布的内容的一个主要方面。通过快手平台的影响和号召力,李文还搭建了一个由快手衍生的苗族交流社区,名为“苗族歌曲交流”QQ群,该群创建于2019年8月,半年的时间这个群已经有一千四百余成员加入。李文的快手简介是:“要歌曲的加QQ群,我快手发的歌曲群文件里面都有哦,群非免费,需要的可以加进来,我找歌需要时间,下载歌曲需要流量,会员充值也需要钱,我也不容易,谢谢!”通过QQ扫码,付费三元,笔者也加入了该群。李文认为与其他同类QQ群相比,他的群不论在价格或是服务质量上都是性价比极高的。他自己也曾经尝试加入过其它类似的苗族歌曲群,这些群收费从五元到几十元不等,但李文认为其他群的服务没有他做得好。他这里所说的服务,其实就是把近千首苗语歌曲按照经典、伤感、DJ、说唱以及苗族恐怖故事音频等进行归类,方便大家下载。李文获取苗语歌曲的渠道跟电影一样,都是通过YouTube下载,他也会根据群成员所提供的视频,再用技术手段将视频转化成音频发给对方。群内成员偶尔会@李文,建议他上传自己想看的电影,比如有人让李文上传经典电影《老虎抢亲》(即《诺丫与彩奏》),但李文认为这部电影快手上许多用户都在传,而且优酷上很容易搜到,考虑到视频可能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所以他并没有完整地上传该作品。尽管如此,李文知道《诺丫与彩奏》的主演Kwm Lis以及Ntxhoo Lauj在苗族群体中的影响力,他偶尔会更新两个主演曾经演过的其他电影,并用鲜明的字体标题标注出来,比如打上“诺丫苗族电影”“彩奏苗族电影”的字样,尽管这些电影的故事情节已经跟诺丫、彩奏毫无关系,但他知道只要这么写大家就会知道主演是谁,并且会想打开看。事实证明,这些内容的观看、点赞和评论的次数确实都很可观。
李文认为,快手平台鼓励原创视频,但他的作品都是从别的地方下载来的电影或MV,要想成为热门比较困难,虽然他的快手账号有接近十万的粉丝量,但有时候播放量却只有几千甚至更低。李文早前发布的一个“苗族男神——朵杨”的作品,播放量超过一百万,而且前期的作品播放量都很高,但是越往后的作品,即便是再好看,播放量也上不去了。李文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作品不是原创,而且不够优质。目前这些作品的播放量基本都是来自他先前积累的粉丝,所以维持好目前已有的粉丝更重要。群里不少苗族人也想试图打破李文对于影像内容的垄断和把关,会向他请教如何搜索苗族视频资源。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李文一般都卖几个关子,从不做正面回答。
根据笔者调查了解的情况,在国内苗族群体中能够浏览YouTube网站的人并不多,对苗族文字具有识读能力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他们对于自己所需苗语影像资源的检索。尽管如此,大多数苗族都知道Hmoob代表着苗族、苗语的意思,因此只要能够浏览YouTube网站的人,他们仅仅凭借关键词“Hmoob”或“Hmong”,就可以检索到海量与苗族有关的音乐和视频。如卡斯特所说,“人们倾向于基于他们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网络来构建他们的身份,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让我们对如何制作和消费文化内容更加深思熟虑,因为数字媒体迫使我们自己做出编辑选择。换句话说,广播媒体强化了诸如民族主义、宗教或种族等大型文化类别,而数字媒体允许我们通过全球和本地网络,用那些我们感到亲近的内容来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
由于全球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的日益普及,全球苗族又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实践其全球联系、文化共享,同时,也创造一种新的“媒介记忆”方式。通过互联网、手机所实践的“媒介记忆”,有些内容是此前苗语影像的延续,至少在当下,我们所观察到的还主要是对苗语影像“媒介记忆”的“复制”,同时,这种“复制”也并非是完整的“复制”。如前所述,也有学者关注过苗族刺绣的数字化呈现,但是如何通过互联网来续写苗族的“媒介记忆”,前景似乎还不是十分明朗。此外,诸如快手之类的手机短视频使得媒介内容更加碎片化,这样一种“媒介记忆”方式,是否又会使得历史与文化变得更加凌乱?
五、结语
正是在民族离散过程中,产生了像“故事布”这样的特定媒介形态。这一特定的媒介形态,与苗族传统工艺直接相关,这些手工艺品所讲述的是当时苗族在离开家园时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在我们看来,“故事布”作为一种特定的媒介形态,具有“媒介记忆”的意义。另外,在苗族向全球离散的过程中,刚好又是影像生产由专业化逐步转向大众化的过程,因此,苗语影像应运而生,并且随着人际的流动在全球的苗族群体中广泛传播。从苗语影像的内容来看,与“故事布”讲述悲欢离合的离散故事不同,它更多取材于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并进行着某种传统的重塑。这就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所进行的“记忆”实践。从媒介形态来看,它与既往关于媒介记忆研究中所指的媒介并无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生产方式以及传播的范围来看,苗语影像又与既往媒介记忆研究的对象有较大差别。这种差别,简而言之,苗语影像更具“银屏记忆”的意味,即通过影像来使那些既往通过口传的方式传播的内容“载体化”“标准化”,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扩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手机短视频,又为全球苗族的联系、记忆书写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或方式)。由于短视频等形式目前还是新生事物,因此在内容生产上会较多地征用既往那些广为流传的苗语影像的内容,但是在具体征用时,又不是对既往苗语影像内容的完整、简单的复制,而是进行一种再生产。同时,在数字传播时代,苗族文化的数字化工作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中苗族文化到底如何延续,苗族如何通过新的媒体来进行记忆书写、储存?进而如何进一步实践苗族的全球联系?结果又将会是怎样?笔者将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关注。
注释:
① 本文的田野调查均由程悦完成,具体的调查时间是2020年2月26日至3月20日。
② 本文中的调查对象均为化名。
③ 本文所说的苗族,指的是苗族Hmong人支系。
④ 《老变婆》是根据苗族民间传说改编而来的电影,老变婆非人,但可以幻化成人,它们喜欢欺骗诱拐小孩并将其吃掉。
⑤ “Hmoob”译为汉语即“人”或“人类”的意思,是该群体一直以来的一种自我称呼。在中国境内,“Hmoob”人及其他苗族支系一起被称为各类“苗”。越战后,部分老挝“Hmoob”人在泰国难民营滞留期间,“Hmoob”这一自称逐渐为外界所接受,他们到达美国后,英语语言对他们的称呼“Hmong”,即源自其自称“Hmoob”的音译。中国境内的Hmong人有200万,境外所有国家居住的苗族都是Hmong人支系,几乎无论分布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Hmong人,均可以用母语交流。参见黄秀蓉:《“Hmoob”“Mab”及“Suav”:美国苗族“Hmoob”人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104页;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页。
⑥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0页。
⑦ 谢卓潇:《春晚作为记忆实践——媒介记忆的书写、承携和消费》,《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期,第155页。
⑧ 吴世文、何屹然:《中国互联网历史的媒介记忆与多元想象——基于媒介十年“节点记忆”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9期,第75页。
⑨ 赵建国:《媒介记忆:民国时期中共报刊对“九一”记者节的纪念报道》,《新闻大学》,2018年第6期,第63页。
⑩ 徐开彬、徐仁翠:《汶川十年:汶川地震的媒介记忆研究》,《新闻大学》,2018年第6期,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