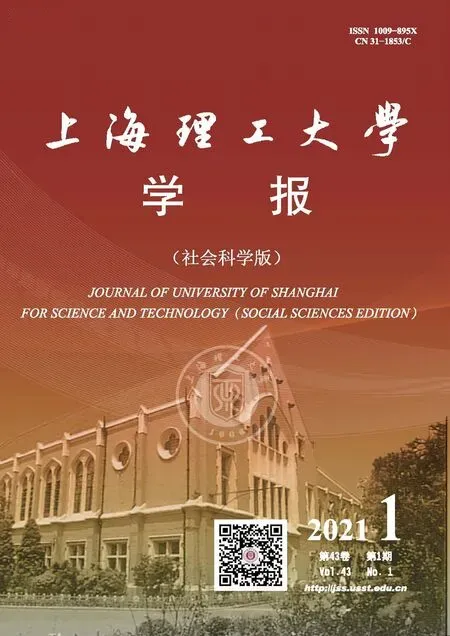她们自己的“百纳被”
——互文性理论视域下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研究
孙 蕾
(天津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87)
在非裔美国女性作家群中,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 Hurston)、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格罗丽亚·内勒(Gloria Naylor)是公认的标志性人物。这几位作家身处不同年代,在美国文学史中扮演着各具特色且举足轻重的角色。赫斯顿在以哈莱姆文艺复兴为发展背景的非裔美国民族第一次革命浪潮中,作为少有发声的女性本族作家,对本族文化的原创性和模仿性进行阐释,意在通过作品体现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尤其是其作品《他们眼望上苍》中,颠覆了传统的非裔美国女性的懦弱无声的形象,塑造了一位有主见并拥护本族文化的新女性形象。沃克在基于民权运动的第二次民族革命浪潮中,以其代表作《紫色》塑造了一名社会底层的黑人妇女寻求自我的艰辛历程。而后,莫里森作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作家,提倡黑人之间以及黑白之间的大融合,成为非裔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内勒作为当代非裔美国女性作家的后起之秀,以处女作《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一举成名,构建了一系列黑人女性面对社会多重压力,相互扶持的故事,同时该书被搬上荧幕,好评如潮。
一、理论基础
法国符号主义学家、女权批评家克里斯蒂娃[1],在继索绪尔和巴赫金之后,创造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文学理论概念。她将文本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强调了作家、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本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随后,法国先锋学派代表罗兰·巴特在其《作者的死亡》等著作中,正式将广义的互文理论从符号学中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热奈特[2]在已有的互文性理论基础上,提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这一概念,具化了互文类型的种类:互文性、类文本性、原文本性、承文本性和广义文本性。他从狭义互文性角度,具体阐述了互文性在文本中的实践运用。广义文本性指所有文学体裁之间的政治阶级性。进入到后现代主义时期,互文性理论又分别被哈罗德·布鲁姆和J·希利斯·米勒赋予了新的内涵。布鲁姆[3]是从心理分析角度来研究文本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诗学误读”理论,认为前后文本之间存在着作者(诗人)之间的动态和对峙的关系。而米勒[4]则认为文本之间除了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之外,还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犹如“寄生”和“寄主”的依赖关系一样。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大而言之是将文本的语义置于社会意识形态中,与社会文本发生互动关系,讨论了文本、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小而言之,是指一位作家的所有作品会因其生平经历和人物塑造的特点,产生关联互动,或两位或者多位作家由于自身对社会的认知、传统经典文学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某种文化共性的影响,会在叙事风格和文本主题等方面,产生微妙的勾连关系。而热奈特偏向于实际操作的角度,从狭义角度论述了互文性在文学中的应用。侧重于写作技巧等微观方面,强调通过模仿、反讽、典故等方式与前文本发生互动关系。
通常,互文性研究的难点来自于自身的复杂性和隐秘性。互文性的产生是需要作者、读者、评论多方维度参与构成互动关系的构建。其次是互文性本身就存在着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读者的阅读体验和作家的创作经验,都可能造成关于互文解释的不唯一正确性的现象产生。
针对互文性理论视域下非裔女性作家的文学批评,盖茨[5]首次肯定了赫斯顿和沃克作品之间的“前辈文本与后辈文本的关系”,其中后者是以混搭无意意指,即“一种不是没有深刻目的性,而是没有否定性批判的修正方式”,表达了对前者的崇敬之意。沃尔[6]以重新审视哈莱姆文艺复兴历史为前提,列举了这一时期女性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姊妹情谊,意图揭示出这些文本间形成的“她们自己的文学”的有机脉络关系。蒙哥马利[7]则强调了当代女性作家内勒的文学价值,并将其同沃克、莫里森并称为当代非裔美国女性文学中的“圣三一”。由此可见,国外学者一直试图挖掘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在创作主题和叙事风格等方面是否存在着传承性的隐形纽带。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赫斯顿、沃克和莫里森作品之间的关系上,也有少数学者,如方小莉[8]从生产性伴随文本和解释性伴随文本角度,就沃克、莫里森和内勒的作品进行研究,探讨非裔美国女性性属思想和社群观念的变化,从而构建了一个黑人女性的作家群。
二、向本族内部寻求力量
广义互文强调将文本的语义置于社会意识形态中,与社会文本发生互动关系,从而讨论文本、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赫斯顿、沃克、莫里森及内勒的代表作都有意指涉非洲文化元素,以及源于非洲文化并融入本国特色的非裔文化元素,凸显了作家群多次回归本族文化的意图,希望通过指涉本族文化元素,从而为非裔女性独立寻求新的解决方案。非洲文化元素在小说中的指涉是指非洲宗教观泛灵文化;而非裔文化中的精髓,即蓝调布鲁斯音乐、姐妹情谊和百纳被文化,也以各种形式勾连于作家群的代表作中。
作家群都有意识地在非洲宗教观中汲取创作力量,并挖掘其文化内涵。博哈南和科廷[9]认为非洲宗教起源于上帝造万物的故事,而后随着上帝的隐退,整个宇宙自成一个完美而缺乏动力的系统,而动力需由人类和宇宙生物提供。确切来讲,人类和精神能量才可以使宇宙运转,而这精神力量是世间万物体现的,即万物有灵论。赫斯顿在其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中,使用了非洲民间故事中上帝造人的情节来塑造珍妮这一人物。在传统非洲故事中,人由上帝创造后,具有唱歌和发光的能力,但是遭到了天使的嫉妒,被剁成碎片并裹上难看使之失音的泥巴,成为颤抖的泥丸。珍妮正犹如这小泥丸,虽然在父权社会和白人社会里被丑化,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但还是努力使自己焕发出光彩并顽强唱出自己的歌。在赫斯顿笔下,珍妮被赋予了非洲文化符号内涵,从而焕发出黑人女性争取独立的光芒。沃克[10]也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中,宣称自己不相信有超乎自然界的上帝存在,认为上帝存在于自然界,可能上帝是人类,也可能是一片树叶或者一条蛇。王成宇[11]认为这恰好吻合了非洲宗教观中的泛灵论,认为上帝不是唯一的神,而世间万物才是主导世界的灵魂。在《紫色》中,聂蒂提及了非洲独特的屋顶树叶这一文化意象。此段叙述虽未被施以重墨,但沃克意图通过非洲奥林卡部落中盛传的屋顶树叶救命的民俗故事,来凸显非洲人民自发的自然宗教观。树的意象也是来源于非洲文化,认为树代表大自然母亲,具有神灵的能力。茜丽最终背离了基督教的上帝,而领悟到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上帝不是她也不是他,而是它”[12]。莫里森也注重在非洲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力量,《所罗门之歌》中的非洲人飞翔的传说和《柏油娃》中的兔子和柏油娃的故事,都很好地说明了莫里森对非洲传统文化的重视,她重新挖掘其文化内涵。
非裔本族文化,是非洲文化经过长时间在美洲大陆的沉淀和衍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首先,蓝调作为非裔音乐的主要代表类型,不仅是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更是非裔本族人民面对生活的苦楚、劳动的艰辛及爱情的浪漫时,展示内心情绪的最好表达方式,是独特体验的情感宣泄方式。贝尔[13]评价蓝调是一种社会仪式,是一种仪式化的并保留至今的语言形式,其反复出现的表演性强化了生活秩序感,并保存了群体的共享智慧。在沃克的《紫色》中,作为一名黑人女性爵士歌手,莎格被赋予了启蒙他人并解放他人的能力。她为了鼓励茜莉重新发现自我价值,特地为其创作了一首蓝调歌曲《茜莉小姐之歌》,这无疑对丧失自我的茜莉是个极大的肯定,从而加速其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后,莫里森也曾公开表示叙述和音乐一样,不可能完全表达文本的含义,其中空白点需要读者填充[14]。在《宠儿》中,她借鉴了爵士蓝调中的即兴演奏的节奏特点,将其运用到小说叙事策略中,如有关丹佛出生情节的描写就被不定期地安排在小说叙事里,与蓝调的即兴演奏特点如出一辙。莫里森将非裔文化元素借鉴到叙事技巧中,体现了作者继沃克之后对非裔本族文化的挖掘。霍尔[15]认为内勒也试图尝试借鉴蓝调的节奏感,将其中的抒情式因素、暗指因素及自白式因素融入至创作的黑人女性形象之中。不难看出,这一作家群,虽身处不同年代,但都反复以蓝调的文化内涵为切入点向前作者致敬。
其次,姐妹情谊这一主题也反复出现在这几位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中。在《紫色》中,沃克构建了聂蒂、茜莉和莎格等女性角色之间的姐妹情谊,通过女性间相互倾诉,而且将其扩展到非裔女性群体内部,来达成种族平等和两性和谐的美好愿望。《他们眼望上苍》也是呼应了这姐妹情谊,赫斯顿通过构建珍妮与菲比的这段姐妹情谊,探讨了非裔女性自我争取解放的艰辛历程。《宠儿》所表述的姐妹情谊则超出了血亲、肤色、种族、阶级以及个体差异性,体现的力量也更为强大。在内勒的《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的每个独立的小故事,无论是依娃小姐对女主人公玛蒂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提升,还是后来玛蒂对其他女性人物的精神救赎,都呼应了前面女作家所提倡的姐妹情谊。
最后,百纳被的文化寓意也是作家群的互文关注点。赦赫兹[16]研究认为百纳被历史可追溯至古埃及、古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时期。其起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远归的十字军的所穿旧而缝补的内衣,而演变成用以御寒的被子;另一类则是西非当地妇女将具有不同象征符号的布片缝补的被子,而后此传统被美国非裔妇女社群所保留,成为主要群体活动之一。缝制过程本身既暗示了重塑非裔女性支离破碎的主体,又代表了非裔女性精神上的解放历程和追求完整的完美结局。沃克赋予了百纳被独特的文化隐喻,即非裔妇女的美学传统,也即妇女之间互帮互助的姐妹情谊。尤其是在作品《日常用品》和《紫色》中,缝制百纳被被隐喻成为非裔女性建立联系,获得女性意识觉醒和自我身份认同的方法。百纳被不仅是“一份非裔美国女性的文化遗产,更是女性主义诗学观念的恰当体现”[17]。莫里森的《宠儿》借用百纳被这一母题,提到了由祖母保留的被子作为传家宝,而后被赛斯和宠儿重新缝补并完成的百纳被的意象。这无疑是勾连了沃克对被子的隐喻意义,即非裔妇女的家族历史的美学传统。在内勒的《戴家奶奶》中,米兰达将萨菲娜的紧密而坚实的衣料垫在下面作底衬,来支撑她母亲的残破不堪的布料。这无疑使非裔女性之间的互帮互助的姐妹情谊得到了升华,同时也互文了《紫色》中莎格、索菲娅和茜莉之间通过缝制百纳被,相互依存、团结互助而形成的独特文学力量。
三、经典仿写与解构
从狭义互文角度讨论,互文理论主要体现在几位非裔美国作家的写作技巧上,即对圣经故事的改写和颠覆,如引用、典故、副文、模仿等。作家意图通过对传统白人经典文化的引用、模仿和戏仿,利用文学语言对意识形态的传承以及颠覆作用,从而展现了美国非裔被白人种族歧视异化和被非裔男权社会压迫的双重屈辱生活。而这颠覆意义不仅印证了小说本身以及它与先前文本的互文牵连,更凸显了作家群的创作思想内涵之间的观照。
仿写是向经典西方文学提出挑战的第一步。在《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找寻自我的过程和圣经中“出埃及记”如出一辙。“出埃及记”中的摩西依靠上帝的力量带领受难的犹太人逃离埃及,在上帝应许之地迦南重新生活,建立属于本族人的国家,意在重归自由且简朴的生活,以实现真正的独立。珍妮在两次婚姻中像“骡子”一样忍气吞声地生活,不仅在家中的女主人身份不被肯定,而且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也被忽略。最终,她像摩西一样,逃离了双重压迫的家庭环境,完成了女性的自我觉醒,在第三次婚姻中找到了内心的迦南,实现了物质精神双独立。赫斯顿模仿“出埃及记”中的叙事结构,意在仿写出非裔美国女性中独立灵魂的觉醒。
内勒在《林顿山》中借用但丁的“地狱”写作框架,建立了黑人中产阶级社区林顿山。在内勒笔下的这个具有中产阶级特色的文明社区,表现光鲜亮丽,但实质危机重重。由于奈迪德家族为了追寻“美国梦”,而不惜实行父权与男权统治,更恶劣的是他们抛弃自己的本族文化,最终滋生了种种罪恶,使林顿山沦为了人间“地狱”。同时,这也互文了莫里森的《天堂》中的黑人小镇鲁比镇的建立。
在继仿写之后,沃克、莫里森和内勒相继尝试利用文学语言对白人意识形态进行颠覆。《紫色》以伊甸园神话为前文本,指出基督教白人男权文化造就了对黑人女性的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把迫切唤醒黑人平等意识的莎格比作伊甸园里的那条具有反叛精神的蛇。同时,在《紫色》中,茜莉和聂蒂之间的信件互往,也是借鉴了圣经的“使徒书信”典故。一封封来自非洲的信件不仅是妹妹对姐姐的牵挂,更是聂蒂在汲取了非洲本族文化的力量后,对美国本土未觉醒的黑人女性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吼声。
莫里森的《宠儿》也是对圣经伊甸园神话进行颠覆和嘲讽,揭示了名为“甜蜜家园”的种植园实质上是一个充满虚伪和罪恶的地方。虽然在当时奴隶制已被废除,但是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地位非常卑微,她们承受着来自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虐待。所以,当赛斯在逃亡之路上面临被奴隶主捉回“甜蜜家园”的危险之时,宁愿手弑亲女,也不愿意让孩子重蹈覆辙再次经历她的苦难。这无疑就是对白人社会宣称的充满祥和和自由的南方庄园制度的一种辛辣的讽刺。
内勒也在《贝利小餐馆》中将圣经中的夏娃和玛利亚的形象进行颠覆重写,重新对黑人女性形象进行书写。在圣经中,夏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名女性,唆使亚当一起品尝了智慧之果,从存在伊始就受到歧视,被认为女性是一切灾难的祸根。而玛利亚作为“圣母”的贞洁形象,一直在圣经中扮演着纯洁、母性、奉献的角色,是父权社会标榜的圣女的象征。《贝利小餐馆》中的女主人公萨拉,在世俗的眼中,应该是个靠卖身为生的肮脏堕落的妓女,但其内心渴望自由,并拥有梦想。内勒通过塑造萨拉以及其他黑人女性,用以颠覆圣经中对女性的非“夏娃”即“玛利亚”的二元对立的刻板形象,意图表现出非裔美国女性在双重压迫的社会环境下,依然努力争取自身独立与梦想。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名非裔女性作家深受圣经经典文学的影响,但是在狭义互文视域下,沃克、莫里森和内勒更善于使用语言艺术来改写和颠覆白人经典文化,质疑并声讨白人男人对社会统治的合理解释,并迫切呼唤建立一种崭新和谐的种族观和两性世界观。而赫斯顿在这一方面只是具有一定的萌芽思想,只是开始尝试仿写主流文学,并没有在写作技巧上对经典白人文学进行大量的、深度的颠覆。
四、结束语
本文在广义互文理论和狭义互文理论视域下,将不同代表时期的4位非裔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挖掘,分析作品之间彼此的互文指涉以及作家对同一经典文学文化的互文仿写颠覆关系,来释义非裔美国女性文学中的文化传承性。
以上文本之间彼此的指涉作用而产生微妙的勾连关系,造就了4位非裔美国女性作家之间的文化书写的传承关系。这4位作家虽身处不同时代,虽个人倡导主题各有侧重,但在作家群中却一脉相承,彼此指涉并勾连非裔文化因素,希冀将祖先的文化之根隐喻在现代的写作文本之中,并在此肌理上,用语言力量将白人文化符号进行仿写和颠覆,从而力图编织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她们自己的“百纳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