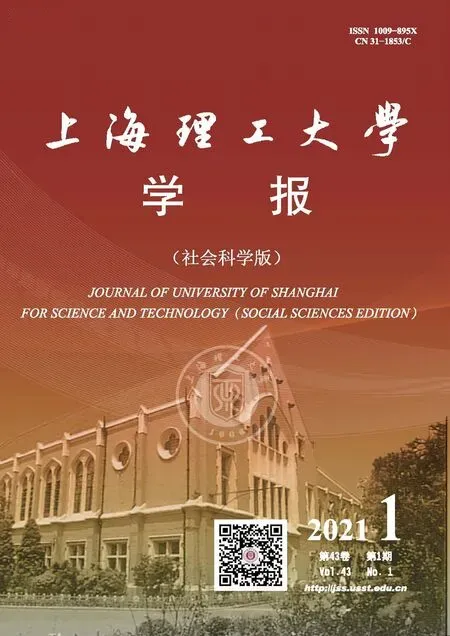摆脱束缚的语言游戏
——布赖恩·卡斯特罗《上海舞》的解构探析
颜静兰,陈晴雯
(华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7)
《上海舞》(ShanghaiDancing)是澳大利亚小说家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1950—)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主人公安东尼奥·卡斯特罗在父亲死后,从澳大利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中国,开始依靠探索和回忆慢慢重构家族的历史故事。《上海舞》被认为是卡斯特罗所有作品的总结。布赖恩说该小说的创作深受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他和乔伊斯都身处异国他乡,凭借记忆和想象在小说中描绘自己心中的一座城[1]。小说时间和空间的杂糅性使得读者经常陷入分辨真与假、写实与虚构的困扰当中。作者自称这是一部虚构的自传性小说,打破界限,打破束缚才是其创作的初衷,如果拘于探索所谓的“真相”,反而会陷入作者的迷宫之中。德·曼曾说:“阅读中的可能性决不能够想当然。”[2]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既认为语言能够制造“现实”(reality),又认为文学所表现的现实只不过是虚构物(fabrica-tion),因此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3]。后现代主义小说作家以不确定性作为其创作原则,解构小说创作中一切确定的元素,用无中心来充当中心,用不确定来给予确定,用零散化来构建整体[4]。集中体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创作方法的多元性、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后现代主义小说书写的过程是一个解构的过程,小说的阅读同样需要一个解构的过程。被誉为“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的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声明:“我的歌中之歌是不确定原则。”[4]15不确定性充分展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解构主义立场,所有被确定的所谓“中心”被一一消解,剩下的是作者乃至读者的自由创作和对话。
定位不明确的自传一直是卡斯特罗的写作风格,在他写的小说和文学评论作品当中,他一直在重复构建一系列家庭故事[5]。《上海舞》主人公与作者卡斯特罗的多国背景相似,但决不能由此便将主人公与作者划等号。卡斯特罗也自称这是一部虚构式自传,但他书写自传并不是为了塑造一个受到社会敌意对待的民族或杂合的自我,而是想在自传中寻找挑战社会趋势的机会,挑战这种由社会来明确定义作为“他者”的自我的现实[6]。这种反本质主义,挑战权威的创作意图本身就已冲破了确定性,使得小说充满不确定性。卡斯特罗不否认文学理论与其文学写作之间存在联系,他认为写作是一种赋权的游戏,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们都不能忽视理论知识的创造力,因为理论可以创造出最为别出心裁的文学[7]。在《上海舞》中,无论是人物、情节还是场景,都存在解构主义的影子。卡斯特罗自称其在文学创作中用批评理论来颠覆体裁[8]。而大多数针对其作品的批评性评价也认为其作品受到西方后结构主义学者们的影响甚大,如德里达、巴特和布朗绍[9]。德·曼认为将自传定义为一种文学体裁必然是有问题的,任何作者在写作时都会受制于其个人经历,自传与虚构小说之间并非两极对立,而是不可分辨的。自传并非是一种体裁,而是一种存在于任何文本中的阅读或理解的形式[10]。《上海舞》小说的呈现方式或许因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些相似,这却恰恰是作者受到德·曼影响的印证。
一、法国解构主义先驱德里达的思想和希利斯·米勒的解构文学批评
(一)法国解构主义先驱德里达的思想
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于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访学期间宣读了《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这一论文,向自柏拉图以来的经典思想发出挑战,自此“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问世。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文字与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批判、延异(différance)、播撒(dissémin-ation)。德里达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分歧源自文字与言语的第一性问题。他颠倒了传统对文字和言语的序列,认为传统西方哲学排斥文字,将文字(writing)视为言语(speech)的再现,视言语为意义的直接、自然表达,他们的这种“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是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可分割的,而除了文字与言语的关系问题,其他的哲学问题不过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同版本的说法而已[11]。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始终是在场(presence)的形而上学,其对无处不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是空口,而是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词“différance”。Différance的一个意思是差异(dif-ference),主要诉诸空间;第二个意思是延迟(différé),主要诉诸时间[12]。延异是不能在在场与不在场这个对立上构想的结构与运动[13]。德里达认为文本与文本之间始终是一种互文关系,因而对文本的阐释就形成一种“阐释的循环”[12]。这给予了解释、批评文学作品一定的自由。在其1972年出版的论著《播撒》中,德里达又提出dissémination这一新概念,意在强调文本理解的无主次性,所有信息都像种子一样播撒。德里达反复强调无中心,延续其一贯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在于破除该文本的终极意义,打破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闭环,形成开放的文学创作。
(二)希利斯·米勒的解构文学批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传入美国后,耶鲁学派将解构主义的思想应用于文学批评,其代表人物为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这四人中,希利斯·米勒将解构主义视为文本阅读和阐释的原则和策略,提出了一些解构文学批评的理论概念:异质性、线条意象和文本的重复。
米勒在转为解构主义后,一直追随德里达,一贯强调文本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由此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14]。他认为语言的本质或根源是隐喻性的,而文学是由语言构成的,甚至文学的本质基础就是语言,那么文学文本的意义就是不确定的,无中心的[15]。米勒指出文本的异质性体现在它同时诉说两种水火不容的事物,一种是指示性的,有其本源,另一种是对指示性进行解构,没有本源,只是语言置换的自由游戏[16]。一部作品中的多种意义就像是一个容器中的各种物质混杂在一起,它们互相沾染,互相影响,分不清谁是影响源,谁又是被影响的,这便是文本的异质性。米勒还强调,良好的阅读不应只有对主题内容的各种道德倾向,还应对文本的异质性做出回应[17]。
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叙事是一连串随意的事件关联组成的一条线,这其中有开头、中间和结尾[18]。而希利斯·米勒认为叙事线条像阿里阿德涅之线,能够引导人们走出迷宫。从线的一端出发走向出口,正如阅读文学作品时无意于一次性简化所有乱如麻的线索,而是从一个切入点慢慢追溯。与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同,站在解构主义立场的米勒认为叙事线条不存在所谓开头和结尾,而中部则被各种因素分解[19]。叙事文本所谓的开头并存于叙事线条之内和之外。在叙事线条之内,开头作为文本的实际内容;在叙事线条之外,开头作为“布线人”,是故事的源头和基底[18]58。小说就像辩证法一样,依赖于世代的循环,起源于父子、母子或母女的关系传承[18]60。如此一来,叙事线条便永无开端,可以无尽地往前延伸。按此逻辑,叙事文本的结尾也同样没有真正的结束,我们无法判断叙事是否完整。米勒将叙事结尾归为两种方式:“打结”和“解结”。如果结尾是一个细心构成的“结”,那么作者或者读者依旧可以将其“解开”。而如果结尾是一股股并列的线,那么作者或读者可以将其“打结”。正如婚姻的结果是繁衍后代,而后代的出生是下一代婚姻的起点一样[18]54。叙事线条的中部则是非连贯性的。读者想看到的叙事不是一眼望到头的直线,而是扑朔迷离,无法捉摸的曲线,其中可能也掺杂着其他难分主次的各类线索,使得中心分离成无数个中心,最终消失。
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一书中以《德伯家的苔丝》为例,指出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他认为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这些重复的现象,小至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隐喻,大至事件、场景、主题等。这些重复在文本内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与生成作品的外部因素交织在一起,这些因素包括作者的精神和生活,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心理、社会或历史的真实情形,其他作家的作品,神话传说主题,作品中人物或其祖先意味深长的往事,整部小说开场前的种种事件[20]。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可能会自发地留意到这些重复现象,并赋予其独特的解释。
二、《上海舞》的异质性
米勒认为异质性是文学的特征。异质性是指文本表达出的多重并且甚至矛盾的意义,而读者必须要抵制把它们统一为一个观点一致的强烈欲望[21]。他提出:“最佳的解读是那些最好地说明文本的异质性,最好地说明文本所展示的一组明确的可能意义的解读,这些意义是系统地相互关联,是由文本决定的,而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22]
在《上海舞》这本小说中,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一词完整地出现在第一章节“开往中国的慢船”中十多次,且常单独成段出现,在之后的章节中,也偶有舞蹈的闪现。作者似为“上海舞”进行定义,却前后又无统一的逻辑性可言。“上海舞”可以是这一章的主题,可以是整部小说的开端。每一次出现都是作品给予我们的符号。如:“上海舞。听上去既像是上层社会生活,又像是下层社会生活,或许二者兼而有之。”[23]1上海舞一词,既可以指向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也可以是脏乱底层社会的无名狂欢象征。在当时的战乱年代,上海被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所占据着,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舞蹈却是打破一切身份地位束缚,人们共通的方式。又如:“上海舞印在了我的脑海里。”[23]2“上海舞”是叙述者安东尼奥记忆中小时候父亲在俱乐部所跳的茶舞和穿着长筒丝袜和高跟鞋的女人。安东尼奥强调:“上海舞,我骨子里的东西。”[23]3“上海舞”对叙述者安东尼奥来说,是存在于自己出生地的东西,在回到出生地以前,所有有关“上海舞”的印象都源于父亲,自己与“上海舞”犹如自己与“父亲”一般,回到出生地寻找父亲的痕迹,也是寻找“上海舞”。安东尼奥又特意指出:“上海舞。从一根古老的线轴上抛一根线:得到的是方向的迷失和稳定性的消除。”[23]4“上海舞”是叙述者寻找父亲和祖先们历史足迹的一条线索,但是要捕捉父亲非常难,他放浪形骸,在上海的上流社会各处混迹,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叙述者安东尼奥还将上海舞称为:“无名氏。梅毒。”[23]14将“上海舞”称作无名氏,说明“上海舞”的捉摸不透,又比作梅毒,说明“上海舞是种瘟疫,是令人厌恶、令人羞耻的传染病,代表人们无法克制的欲望。安东尼奥最后总结:“上海舞,一种经历,一种生命礼仪。”[23]18“上海舞”有如女性分娩般,既有痛苦,又有喜悦,但它是每个人都拥有的经历,抛弃一切都要进行的舞蹈。“上海舞”是典型的在上海这个鱼龙混杂,阶层复杂的地方所有的现象,是当时人们的群体记忆。小说中它始于上海,但不只在上海,在“台风警报”一章中讲到某个圣诞夜爆发了舞蹈病;在“情感生活”一章中,父亲醉酒后跟“我”说,母亲被迫与一个日本上校跳了舞。上海舞在生活中继续、蔓延、渗透、记录。
语言游戏(Sprachspiel)是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后期所提出的哲学概念。该概念最初是指“孩子刚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方式”,“是语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语言,在这些原始形式中,思想的过程相当简明。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一种与其他行为举止编织在一起的一种活动,人类是这种活动或者说游戏的参与者,在游戏中感受到乐趣,同时也遵从一定的游戏规则[24]。维特根斯坦在讲到私有语言时如是说:“这种语言的语词指称是只有讲话人能够知道的东西;指称他的直接的、私有的感觉。因此另一个人无法理解这种语言。”[21]198《上海舞》这部小说中所出现的“上海”也可称为某种“私有语言”,但作者仿佛在与读者玩语言游戏一般,在他的世界里,他可以指定自己的游戏规则,叙述者可以随意定义一个众所周知具有明确且固定意义的词。在“开往中国的慢船”这一章中,叙述者给予“上海”辞典式的定义:动词,下药或让人失去知觉,然后登上一条需要人手的船[23]19;名词,(澳新语言)一只弹弓[23]23。叙述者用其私有语言“上海”来造句:It is also possible to be shanghaied by nostalgia.[25]怀乡也可能会被“上海”(下药)。这是属于叙述者当时的直接感受,在上海的记忆浓缩成一个专属于叙述者的动词和一个名词,说明上海对他来说印象深刻,是一个使人混沌,使人迷失的地方,无法整体形容,但又散于细枝末节,像儿时记忆中的弹弓一样清晰可触。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以“语言”为中心的,而语言的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自由地创造自己的“世界”的象征。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时代,而世界文学也随之处于全球化语境之下。卡斯特罗是一个澳大利亚华裔作家,身上流着葡、中、英三国的血液,掌握多国语言,是Arianna Dagnino所指的跨文化作家(transcultural writers),这些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家因为经历文化异位,感受着与一般人不同的跨文化生活方式,精通双语或多语,使得其肉体经历着多元文化、地理、领土,而精神则沉浸于多样差异性和流动、不确定的身份[26]。《上海舞》是一部英语写成的小说,但并不是一词一句都是英语。作者以其跨文化的身份和立场,在小说中也灵活穿插其他语言,巴赫金则称之为异质语(heteroglossia)。他认为语言的发展过程同时受到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影响,向心力使语言使用趋于统一和稳定,而离心力则使语言发生创造性的变化,产生异质的、杂合的语言[27]。巴赫金提出无论以何种原则创造出来,异质语都是一种以词汇的形式将特定的世界观概念化的独特语言现象,它们有着自己的存在目的,意义和价值[28]。异质语的存在从语言层面丰满了小说的内容,丰富了小说的读解意义。以下是小说中异质语的举例。
(1)…for once given voice,the baby coughed and bawled and caterwauled,puta!puta!puta!,in time with the wheezing boilers.[25]2其中puta不仅是一个拟声词,也是葡语和西语中妓女的意思。
(2)Desaparecido[25]37是葡语和西语中的“失踪者,去向不明者”。
(3)Profiter de l’occasion.[25]46这是法语中“把握机会”的意思。
(4)Diminuição,my Uncle Meme said,is a relaxation;a partial remission of penalty…[25]84中的Diminuição 是葡语中“减少、削弱”的意思。
(5)Pasah:(Hebrew) to pass over,to spare;to limp or to dance in a limping fashion.[25]94其中的pasah 是希伯来语。
(6)Os:(Latin),bone;mouth.Os!He sur-faced just as the ship pitched,and his leg was wedged by the steering column,dislocating his hip.[25]99
os是拉丁语“骨头”和“嘴巴”的意思。作者在文中给出了该词的原意,却并未按原意来使用,而更像是一个生动的拟声词。
(7)She hung these out so often that the locals began to refer to her malady asosoroshii,terrible,dreadful.[25]110Osoroshii是日语恐れしい,意为“可怕的”。
Soon they called her Osore;the terror.[25]110Osore即日语恐れ,意为“害怕,恐怖”。
(8)The elders gave him a native name to make him special and called himkatalininganwhich in Tagalog means a person of great natural ability.[25]116kataliningan是通用于菲律宾群岛的他加禄语,意为“具有极大天赋的人”。
(9)Mostly though,he remembers Shanghai,that dangerous,fluid,shifting place of rainy evenings,sleeting afternoons,umbrellas,gowns and scented women with small feet andqipaoslifting in the wind.[25]137Qipaos是汉语“旗袍”。
(10)We called him Ah Gúng,or Grandad,and he wore felt slippers and stayed in his room when we came,closing the door on us.[25]139Ah Gúng是粤语外公的叫法“阿公”。
德里达在谈及言语与书写的第一性问题时,提出在文学与诗歌写作当中,突破性是更具稳妥和穿透力的,而所谓突破就像是中国传统意象对庞德诗歌创作的影响,具有跨文化的历史意义。如德里达一样,卡斯特罗认可在跨文化的沃土之上,多语种所带来的解放可能性与创造潜能可以避开单一语种所框定的身份认同和所谓的现实[29]。
三、《上海舞》的线条意象
米勒对线条意象产生的兴趣颇浓,在《阿里阿德涅之线:故事线条》一书中,他指出线条意象无论指称何物,“线条的主题、意象、概念或形式结构其实并不是引导走出迷宫的‘线索’,而是自身构成迷宫。沿线条的主题向前走,并非要简化有关叙事形式缠结不清的问题,而是要从某一特定的切入点来追溯一团乱麻的复杂走向”[30]。《上海舞》这部小说共60个章节,除末章无标题外,其他章节均有标题(包含枕边书,即叙述者的随笔),每一个标题都存在意象,如“开往中国的慢船”“突然冒出的尼日利亚人”“世界屋脊”“台风警报”“建筑”等等,然而整部小说以这五十几个标题串联起来并不存在时间、空间和逻辑的顺序,它们都是一个个独立的意象,构成以这个意象为中心的五十几个篇章,作者的思绪到哪里,小说这座迷宫便拐向哪个路口。但是标题必是这一章节的主题,是作者思绪的源头。“建筑”一章讲述威利舅舅给“我”打电话叫我到他的黄金别墅居住,我乘坐飞机到香港,并从过去的记录开始回忆舅舅、婶婶和外公,建筑犹如一个记忆宫殿,慢慢打开过往。“摆渡”一章由“我”乘船回到香港开始,在渡船上我回忆到母亲曾经在颠簸的船上难产生下了我的孤独悲惨经历。
(一)毫无头绪的开端
传统的叙事文均是具有开头、中部和结尾的一个统一体,而米勒认为叙事线条的开端和结尾都不可能存在,中部也被各种因素所分离[19]。《上海舞》这部小说犹如一个没有入口和出口的迷宫一般,从一开始,读者从“开往中国的慢船”开始,跟随叙述者搭上去往上海的船,读者并不知道叙述者为什么来到上海,来到上海之后要干什么,只能跟随叙述者眼前所展现的东西继续读下去。正如米勒所说:“开头巧妙地遮盖住了源头的缺失所造成的空白,因为这一空白既处于文本的线条之外,又作为不完整的信息所组成的松散的线股处于文本的线条之内,而这些松散的线股将我们引向尚未叙述的过去。”“上海舞”便是一根线,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父亲提及过的,从而勾起浑浑噩噩度过四十年的“我”回到中国的欲望。然后,“我”开始凭旧照片在上海找寻父亲曾经存在的痕迹。真正导致“我”来到上海的却隐藏在小说的中部“葡式免治”一章中,“我”与鲁西·阿恩霍尔特的失败婚姻导致“我”急于在澳大利亚浑浑噩噩的四十年中找寻一个出口。
(二)叙事线条中部的非连贯性
叙事线条的奇特之处在于无法区分相关的和不相关的时间,无法将离题的成分与笔直狭窄的主线条区分开来[19]。后现代小说呈现出对开放性情节的召唤,表现为因果关系的消退,情节平淡、朦胧乃至支离破碎[3]。《上海舞》整部小说每一章节都是迷宫的一扇门,读者随叙述者“我”从“开往中国的慢船”开始,仿佛瞬间移动般进入迷宫之中,之后的每一章节都是迷宫的一个房间,而打开房间的门便是章节的标题,是由作者的思绪变成的,因而叙事线条是作者赋予读者的一根根断绳,绳子的两端曾与哪一段绳连接,读者不知道,作者也不知道。在第一章以及“叙述者的枕边书”后,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叙述者父亲的遗嘱,而并未交代叙述者是如何得到遗嘱的,下一章“突然冒出的尼日利亚人”里,“我”又回到了香港;之后,叙事场景在巴西、上海、香港、澳门、悉尼、伦敦、利物浦、重庆、大西洋的无名小岛、长崎等世界各地转换,时间也从17世纪到20世纪来回穿梭,在这个迷宫中,读者随叙述者不断流浪,不断接触从过去到现在形形色色的人物。卡斯特罗认为文学中真正的创造是将一些起初互相并无联系的概念和形式重新结合在一起[31]。《上海舞》中的各个章节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场景犹如走马灯一样呈现在读者眼前。一开始以孑然一身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叙述者安东尼奥也随着小说的出场人物渐渐绘出以他自身为起点,自下而上的两个家族族谱。作者似乎在小说开始之前就给出了答案,又似乎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与主人公安东尼奥相连的人物关系,但安东尼奥对自己身份认同的不确定并不是简单一纸图谱可以分明的。在小说中,他可能对自己与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有了一些进步,但他不会变成一个完全安于自己身份位置的人[32]。
(三)戛然而止的结尾
米勒认为不存在叙事线条的结尾,至多只存在结尾的感觉[19]。笔者认为在这个迷宫中,并没有所谓的出口,因为整部小说并无所谓“完整性”可言。文章最后,读者又随叙述者回到了甲板上,跳起上海舞,船并不知道驶向何方,整部小说恍如一个跨越了几百年的梦,在最后一刻,作者点醒读者,该关闭思绪回到现实中来了,同时,小说迷宫也在此刻消失,所有的房间、所有的门都一并消失在了不知驶向何方的船。如果说叙述者整个家族的历史是这部小说暗藏的脉络,那么叙述者作为整个家族的最后一代,他的结局就是故事的结局,然而作者并未交代叙述者的去向,他的人生、他的爱情、他的事业、他的旅行,一切都不确定。
四、文本的重复
米勒在其《阿里阿德涅之线:故事线条》一书中指出任何小说文本都是由横纵两轴的交叉交织构成的,横轴称为“线条”,纵轴称为“重复”。而在其另一部重要论著《小说和重复》中,他指出,重复有两种形式:一是文本内的时间、场景、母题、人物、意象等的一再出现;二是文本内的话语符号对文本外的某种事物或精神观念的再现或复制[33]。在《上海舞》这部小说中,叙述者共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姐妹,两两分别是亲姐妹,姐妹们的出场频率很高,在第一次交代清楚姐妹们与叙述者的关系后,作者依旧重复使用“half-sister(s)”,强调叙述者安东尼奥没有一个亲兄弟姐妹。作为父亲第三次婚姻,母亲第二次婚姻所生下的孩子,安东尼奥无法感受到家应该带给自己的温暖,同时家族的复杂关系使他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就像在漂泊的船上出生之时一样,一直是一个无根之人。
小说中安东尼奥的舅舅威利的黄金别墅(Mason d’Or)多次出现。在“建筑”一章中,威利舅舅要我住进他的黄金别墅,自此之后,“动乱”“收藏”“窥视癖者”“重建”“回归”这几个不连续的章节均出现了我住在黄金别墅时的情节,黄金别墅似一个线索,串起一条时间线。别墅是外公维吉尔·容传给舅舅的,住在黄金别墅期间,安东尼奥通过别墅里的东西回忆起舅舅、外公,从而断断续续地回忆起自己的母系家族的历史。在别墅中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却已踏过了千山万水,跨越了几个世纪。
台风是亚洲太平洋出现的天气现象,台风中心平静如水,四周则风雨晦暝。小说中有一章标题为“台风警报”,另有一章标题为“台风”。“台风警报”一章中作者重复了三次“英国没有台风”,欧洲虽有各种风暴,但是没有“台风”。在“台风”一章中,叙述者称“中国的大风叫台风”[23]386。在叙述者眼中,“台风”象征着中国,它的到来是汹涌的,而身处中国,则像身处台风中心一般,让他感到平静得窒息。叙述者从澳大利亚来到中国,卷入“台风”中,卷入自己家族历史的洪浪中,当离开中国时,一切就像台风过后一样恢复平静。对于一个无根之人来说,何处是归处便是无处是归处。
五、结束语
本文以解构主义的视角,从异质性、线条意象和文本的重复三个方面来分析《上海舞》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作者以其炉火纯青的语言技巧在小说中布下一个个谜题,创作的过程是一个游戏过程,而阅读更是一个解构谜题的游戏。
布赖恩·卡斯特罗的小说《上海舞》讲述的是记忆与忘却,主人公安东尼奥一心回到出生地寻找关于家族的历史,却最终放下了要寻找的所谓真实。他甩掉了精神忧郁症,看到它被勾在窗台上,而“这个破东西”让他受了不少罪[23]408。甩掉忧郁症并不是任由自己成为一个身份不明确而无根的人,而是放弃这种狭隘的界定,解放自我。
卡斯特罗以其对多元文化的感受和理解,创造出《上海舞》这样一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后现代小说。他曾称作家们一直身负一种名为“非此即彼”的残酷重担:这是因为人人都想要理性而不是模棱两可[8]291。他不希望读者和外界评论者们给他贴上“华裔”“澳大利亚”作家的标签,对于他的作品的解读也不会盖棺定论。后现代主义小说语言游戏的主角是读者[1],读者打开小说的那一刻便是小说新生命开始的时刻。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文学文本存在多种混杂的元素而使得文本意义难以确定,多股叙事线条也分解了意义中心,而各种形态的重复现象使得文本又充满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