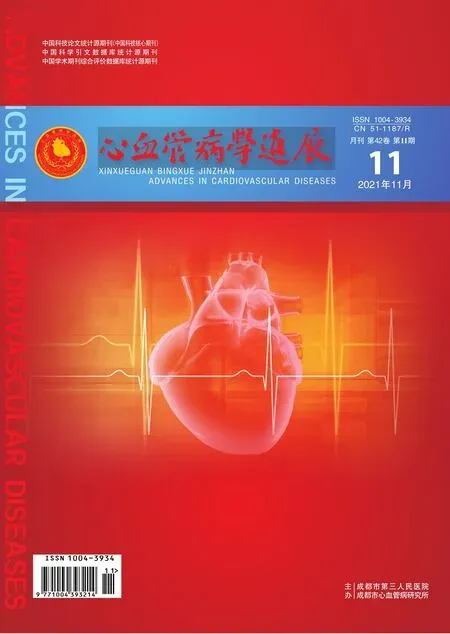无导线起搏器应用进展
荆炜林 谢瑞芹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河北 石家庄 050000)
自1958年第一台起搏器问世以来,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科技的进步,起搏器的发展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全球每年植入起搏器例数近百万[1],其中绝大部分为传统起搏器,然而传统起搏器有优势,但也有一些弊端,如存在术后导线及囊袋相关并发症的可能。无导线起搏器(leadless pacemaker,LP)是近年来的新技术,它将脉冲发生器与感知/起搏电极合为一体,避免了电极导线连接和囊袋制作等过程,它的问世无疑带给人们新的思路,给一些需起搏器治疗的特殊人群带来可替代的选择。现从LP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1 LP的种类
在1970年就有人尝试在犬体内安装了第一例LP,但由于电池技术的限制,仅维持了66 d,随着高密度能量电池和低耗能电子元件的发展,LP在临床中的应用成为了可能。目前临床常用的有两种,一种为圣犹达公司的Nanostim无导线起搏器,另一种则是美敦力公司开发的Micra经皮起搏系统(transcatheter pacing system,TPS)。
两种起搏器对比可发现,其体积均足够小,可通过股静脉直达心内膜,且寿命相仿。Nanostim无导线起搏器的优势在于其感知模式为温度传感,具有良好的频率适应性;而TPS起搏器则可兼容1.5 T和3.0 T磁共振成像,但目前也有新型扫描仪可替代磁共振成像以减少起搏器的电磁干扰[2],但二者固定方式和感应方式的不同使其相关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还需进一步对比研究。
2 LP的应用人群
2.1 获益人群及禁忌证
由于起搏模式的限制及技术要求,无导线起搏并未作为常规治疗方式推广,更多作为一种替代疗法。就目前而言,众多学者以及奥地利心脏学会专家共识认为其适应人群主要为单腔起搏且预期心室起搏率低的患者[2]。LP的主要禁忌证包括:植入机械瓣膜患者,心内膜存在导线患者,下腔静脉或股静脉异常患者,近期发生急性心肌病患者等。另外,由于目前起搏模式的限制,一些病窦综合征、血管迷走性晕厥或房室传导阻滞伴心动过缓的患者也暂不作为无导线起搏的首选。
2.2 应用人群扩展
2.2.1 儿童和老年人群
LP在成人中的作用逐渐被公认,也获得了明显的益处,相比之下,儿童患者的植入经验和随访数据更为有限。Mahendran等[3]报道的在1例4岁高度房室传导阻滞患儿体内成功植入了LP,LP有可能造成儿童血管损伤,小儿血管和心腔较小是LP的重要限制因素,因此在植入前应评估血管宽度与扩张鞘管是否匹配。另Morani等[4]成功在软骨发育不全的侏儒症患儿身上安装了1例LP,术后无并发症出现。LP在儿童中的应用正在逐渐增加。
同时在年龄≥90岁的老年患者中LP的应用也逐步得到验证。El Amrani等[5]对129例患者植入TPS,其中年龄≥90岁患者41例,年龄<90岁患者88例。研究对比手术时间、手术成功率以及术后并发症等,结果显示LP对年龄≥90岁的患者同样安全有效。
2.2.2 特殊需要人群
在一些特殊病例中,LP的优势也得到凸显。当患者静脉出现多次感染,再次安装有导线起搏器可能引发菌血症甚至危及生命时,LP可成为患者的一个有效选择。Parker等[6]为1例65岁静脉入路反复感染患者选择了LP,患者经过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及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植入3年后反复感染,抗生素效果不佳,首要目标便是减少感染,最终选择了LP。术后2个月随访,阻抗及阈值均良好。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阳性患者的心脏情况也在不断研究中,这些患者的心功能影响还有很多未知。Cakulev等[7]报道了1例COVID-19阳性患者出现了房室传导阻滞和心房颤动(房颤)相关的异常停搏,考虑停搏可能是COVID-19感染的表现,对患者进行了LP植入,术后患者症状得到改善,但由于患者的特殊性,远期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研究表明,有4.5%~20.0%的心脏移植患者需植入起搏器,高感染风险和低起搏依赖性使心脏移植患者成为LP的理想选择。通过长期随访,证实了无导线装置在这类特殊患者中的可行性和可接受的安全性[8]。并提出术前心脏三维重建有助于预测植入LP的手术难度[9]。随着技术的发展及经验的积累,LP将使更多特殊人群的需要得到满足。
3 植入方式和途径
3.1 常规植入途径和方式
与传统起搏器不同,LP植入时,术者通常以患者股静脉为入路,通过导管将设备送入右心室间隔部位,获得稳定持续的感知和起搏参数后释放固定。TPS的放置需一个23 F鞘管,在扩张血管时,锥形Coons扩张器是一种有效和经济的工具,相对并发症低[10]。当导管进入体内时,大多数导管以“鹅颈形”可顺利将起搏器放入心室进行固定。LP最佳固定位置为右心室间隔部,其次为右心室心尖部,而右心室游离壁相对薄弱,此处固定会增加心肌穿孔的风险[11]。印度一项研究[12]也表明右心室间隔部植入更具有生理性。LP植入时间相对短,其植入困难程度除与术者经验和患者配合有关外,另一重要因素则与右心室间隔突出小梁有关。 Garweg等[13]对126例患者分析显示,手术时间与间隔边缘小梁突出部分的存在呈正相关(P<0.001),与手术次数呈负相关(P<0.001)。
3.2 非常规途径和植入方法
股静脉是常规途径,但也并非唯一入路,当股静脉畸形或其他原因不能作为入路时,也可考虑其他静脉作为入路,如左锁骨下静脉、髂静脉和颈内静脉等[14-16]。确定入路后,在导管进入心腔内的过程中,除了传统的“鹅颈形”导管方式进入,亦可根据患者的血管情况调整导管形状。Nakamura等[17]报道了1例92岁女性由于脊柱侧凸和严重驼背使得起搏器导管的尖端无法直接指向右室间隔或心尖,于是尝试改变导管形状为“环形”,使导管尖端可朝向右室间隔的下基底部,成功释放,术后无严重并发症。
Gerdes等[18]报道了1例76岁患有永久性房颤和伴缓慢心律失常的男性患者,其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严重扩大,在TPS植入过程中,输送系统向前移动和顺时针旋转时,尖端要么在右心室流出道中向高处滑动,要么移到右心房,因此无法获得有效起搏点。随后尝试使用一个“圈套”样辅助装置固定输送系统的近端部分,在尖端施力,最终获得了良好的稳定性和电位。这些新方法为起搏器植入提供了新思路。
3.3 与其他手术的联合植入
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常伴有安装起搏器的指征,传统起搏器植入感染风险大,对瓣膜有潜在损伤,LP为这些患者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有1例51岁女性患者,在接受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和二尖瓣瓣膜置换术后出现严重的心动过缓,Gul等[19]对其进行LP植入术,进一步证实了其在瓣膜病术后的有效性。有1例71岁的女性患者进行三尖瓣边缘修补术后,患者出现房颤伴心动过缓,考虑传统起搏器的导线会干扰修复部位,LP成为了最佳选择,最终在三维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的辅助下,使用更小的导管,找到了合适的起搏位点[20]。
有些伴有瓣膜病患者本身存在植入起搏器的指征,相关学者尝试在外科手术换瓣的同时,可视下完成LP植入。Shivamurthy等[21]对15个瓣膜手术同时安装LP的成人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纳入患者年龄(67.5±17.0)岁,伴有房颤14例(93%)。有5例患者(33.3%)行单纯三尖瓣置换术,其余患者行多瓣膜手术,包括同时行三尖瓣修复/置换术,随访(151±119)d,所有患者的阻抗/阈值均正常且稳定。进一步证明了瓣膜手术中植入无导线心脏起搏器安全可行,这种联合起搏方法可简化有单腔起搏指征的瓣膜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处理,减少患者的手术花费及痛苦。
对于一些房颤合并起搏器指征的患者,能否在只穿刺股静脉的同时进行房室结消融及LP的植入呢?Chieng等[22]通过回顾14例同时接受TPS置入和房室结消融治疗的房颤患者验证了这种联合手术方式的可行性,而且在中短期内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因此LP可联合多种手术同时进行,一次手术解决患者多个问题,减少患者的手术次数,减轻患者的手术痛苦。
4 LP的安全性
4.1 长期安全性
LP作为新技术出现,其短期安全性得到初步验证[23-25],而它的长期安全性还有待随访研究。Sanchez等[26]在研究起搏器依赖患者中使用LP和使用经静脉起搏器(transvenous pacemaker,TVP)诱发心肌病的研究中,纳入2014—2019年左室射血分数≥50%的所有起搏器依赖的LP或TVP患者,其中131例TVP患者和67例LP患者纳入研究,TVP组平均随访时间为(592±549)d,LP组平均随访时间为(817±600) d。LP组心肌病(3%)的发生率明显低于TVP组(18.7%)(P=0.02),进一步证明LP在术后起搏器相关心肌病方面更安全,分析其可能原因与LP安装时心肌损伤小以及无导线相关并发症等因素有关。
另外,Oliveira等[27]对多中心植入LP患者进行大数据分析,通过回顾性分析研究发现,在纳入的4 739例患者中,随访1~38个月,4 670例患者LP植入成功(98.5%)。随访期间有248例患者(5.23%)发生并发症,最常见的是起搏问题如阈值升高、移位或电池故障(1.43%),穿刺部位相关并发症如出血、血肿或假性动脉瘤(1.37%),以及与操作相关的心脏损伤如心脏穿孔、压塞或心包积液(1.01%)。随访期间有360例患者死亡,其中11例与手术或器械有关。而传统起搏器植入患者仅穿刺相关并发症就占4.67%[28]。总的来讲,LP的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低,对于有单腔起搏指征的患者,LP是个安全的选择。
4.2 特殊人群的安全性
4.2.1 高龄患者
Pagan等[29]比较了TPS起搏器和传统TVP在高龄患者中的应用,选取包括2015年12月—2019年11月在Northwell卫生系统6家医院接受两种方式治疗的所有年龄≥85岁患者。在年龄≥85岁的患者中植入了183个TPS和119个TVP,平均年龄(89.7±3.4)岁,男性占47.4%。结果发现TPS植入:(1)成功率为98.4%;(2)与TVP组相比,手术相关并发症无差异,是安全的,手术时间明显缩短[(35.7±23.0) min vs(62.3±31.5) min,P<0.001]。由于目前无导线起搏模式为心室按需型/心室按需型频率应答式(VVIR),Loring等[30]在研究QRS波群时限和心室功能正常的有起搏器指征的患者过程中,将1 284例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分为两组,全自动双腔起搏频率适应(DDDR)组(n=630)和VVIR(LP)组(n=654),结果发现DDDR和VVIR起搏的患者死亡率、卒中或心力衰竭发生率相似,但VVIR起搏显著增加了房颤的发生风险。
4.2.2 瓣膜置换术患者
瓣膜置换术后需起搏器植入的患者也越来越多,LP感染风险更小,有可能成为这类患者的首选方式,其安全性也逐渐得到认可。Garweg等[31]对比了170例安装LP的患者,其中54例(31.8%)有瓣膜手术史,包括主动脉瓣置换术后28例,二尖瓣置换术后10例,三尖瓣成形术后1例,多瓣膜手术后15例,所有患者(n=170)均成功植入,无任何与手术相关的主要并发症。随访12个月后起搏器工作均正常,两组患者射血分数均有下降,无明显差异,考虑与右室起搏比例相关,进一步验证了LP在瓣膜介入术后是安全的。
4.3 特殊并发症
无导线起搏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安全的,但在众多成功植入患者中也不乏出现特殊并发症等事件。Razeghi等[32]对155例植入TPS起搏器患者进行随访,其中15例患者在植入术后平均226 d出现菌血症,革兰氏阳性菌感染占菌血症的73.3%(n=11),经过适当的抗菌治疗后,所有患者的菌血症都得到了改善。也有报道1例患者LP安装后不久出现恶性心律失常,分析其恶性心律失常很可能与既往冠心病病史相关,术后合并急性冠状动脉缺血是导致患者恶性心律失常出现的重要诱发因素[33]。Gumireddy等[34]也报道了1例85岁患者,有着10年房颤病史,术前超声心动图显示射血分数为56%,无局部室壁运动异常、轻度二尖瓣反流和轻度三尖瓣反流,但LP植入术后15 d便出现了二尖瓣反流严重杂音。另外,术后右室假性动脉瘤[35]等并发症也偶有发生,因此术前全面综合评估患者的手术风险是必要的。
5 无导线起搏面临的挑战及展望
目前无导线起搏面临的电池寿命问题以及单腔起搏问题成为现代技术发展的热点方向。有学者提出利用压电能量收集系统对来自心脏的动能进行收集,从而实现长久供能,但此供能装置需限制在1 cm3体积内,并在心率范围内获得固有频率,这无疑给科研人员带来挑战。另一挑战则来自于起搏模式,由于起搏模式的限制,仅能满足单腔起搏模式,适用范围窄,如何达到心脏同步化治疗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018年Bereuter等[36]报道了双腔无导线起搏的动物实验(猪)结果,为双腔无导线起搏带来了可能,但由于双腔起搏过程中的信号衰减造成的能量消耗使其应用到临床尚需时日。同时LP与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和心脏再同步化治疗等设备的联合应用也在尝试探究中。
随着LP植入时代的到来,新型起搏器的研究如火如荼,这将使越来越多的植入人群从中获益,越来越多的植入技巧被发现验证,其安全性也逐渐得到验证。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其不足与应用限制。由于LP的兴起,很多数据还停留在小型非随机试验阶段,仍需大型随机对照试验验证其优越性。相信随着术者经验的增加和手术器械的完善,LP会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为更多患者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