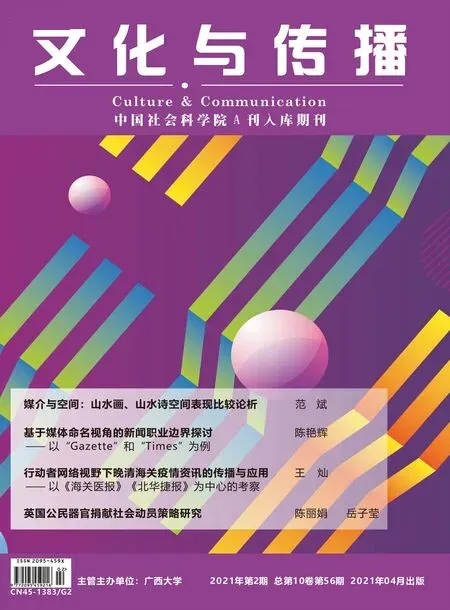论纪实影像中艾滋病感染者的污名化呈现
徐仁萍 林进桃
一、前言
艾滋病自1981年首次在美国发现以来,已经从一种致死性疾病转变为可控的慢性疾病,但人类至今仍没有找到完全治愈艾滋病的办法。尽管现代医学努力将艾滋病阐释为一种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免疫缺陷疾病,但一度被称为“世纪绝症” “二十一世纪瘟疫”等的艾滋病,却难以避免地被赋予了许多带有道德色彩和价值判断的意涵,艾滋病感染者甚至被建构为面目可憎的“人民公敌”。苏珊·桑塔格这样形容艾滋病:像癌症一样“入侵”,却又像梅毒一样“污染”[1]。
艾滋病不仅是一个难以攻克的医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社会难题。在人类与艾滋病相抗争的40余年的历史过程中,国家和社会致力于给公众普及艾滋病知识以达到为艾滋病“去污名化”、减少和消除社会恐慌的目的,大众媒介无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在艾滋病的污名化过程中大众媒介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往往是通过大众媒介来了解艾滋病以及艾滋病感染者这个群体。在媒体纪实影像中,创作者们通过镜头、语言、主题、情节等的选择来让观众更加直观形象地了解艾滋病。但其过分渲染贫穷,刻意凸显死亡,其直接效果就是在大众脑海中深深地刻上一个个饱含着穷苦、无知、可怜、无助的符号,这些符号形塑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第二身份。本文通过剖析艾滋病感染者形象在纪实影像中的呈现,结合戈夫曼污名化研究的相关理论,考察媒体为了达到给艾滋病“去污名化”的目的,是如何采用了“污名化”的影像进行叙事的。
二、“污名化”与艾滋病的污名化
(一)“污名化”的提出与发展
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是现代社会科学界最早描述污名化问题的人,他在研究法国人将胡格诺教徒驱逐出法国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现象:一个群体把人性的低劣强行施加于另一个群体的身上并加以维持,在此过程中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污名化”( stigmati-zation)就是这种权力关系不断发展直至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2]。“污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他在《污名:管理受损身份的笔记》一书中,将污名从形式上分为身体污名、个人特质污名和种族身份污名,他指出污名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3]。由于某个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不被社会所期望或不名誉的特征,污名就是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贴上的具有歧视性、侮辱性或贬低性意涵的标签,从而降低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最终直接导致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此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们都基本沿袭了戈夫曼对污名化的解释和分类,他们分别从社会心理、日常生活道德体验、认知情景、符号(标签)互动、身份威胁、偏见歧视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污名化问题[4]。
(二)艾滋病的污名化
艾滋病被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简称 AIDS),“获得性”的意思是指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后天的日常生活过程中通过某些不当行为获得的。也就是说,造成人们感染艾滋病毒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他们采取了某些危险行为,而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是谁。可见,“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这个名称就体现出生物医学界从一开始对艾滋病就带有某种歧视和偏见,它虽然强调了艾滋病的生物学属性,但同时也赋予了艾滋病某些社会文化内涵:它是因为某些“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是与某些“高危人群”相关的疾病。
艾滋病逐渐被建构为一个带有道德判断的符号。一方面是因为艾滋病本身经过性和血液传播的医学特征,意味着感染艾滋病与一些倍受道德谴责的危险行为相关,因此大多数人认为患者自身对感染艾滋病负有主要责任。艾滋病的高致死率和至今仍不可治愈的特征,使得人们认为一旦被诊断为HIV感染或艾滋病基本上就相当于宣告死亡。且艾滋病人在后期常常会出现所谓的“典型艾滋外貌”,表现为极度消瘦、皮肤损伤、流血流脓等,这会严重地伤害到病人的自尊心,甚至破坏他们的正常社会交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外部世界建构出来的艾滋污名,从一开始我国就认为艾滋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是遥远的“他者”的疾病[5]。当艾滋病刚刚出现在“我们”中时,早期的医务人员面对艾滋病感染者全副武装、如临大敌,甚至以各种原因将他们拒之门外。医务工作者的这些过度保护措施成为人们应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重要参照。此外,部分媒体在描述艾滋病的原因与影响时,把HIV隐喻为“生命杀手”,把艾滋病防治工作看作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并常常会过度使用一些富有煽动性与火药味的语言。这些有意或无意地把艾滋病建构为 “人民公敌”的做法,使得艾滋病感染者在面对身体折磨的同时,还要面对更为可怕的社会歧视。
三、纪实影像中艾滋病感染者污名形象的呈现
自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在我国发现以来,媒体便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艾滋病感染者作为边缘群体往往“无法表述自己,只能被别人表述”[6]。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关艾滋病的影像逐渐出现在荧幕上,其中不乏一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纪录片,如《好死不如赖活着》《颍州的孩子》等。也有了第一部由艾滋病感染者拍摄的纪录片《我们的生活》。艾滋病感染者似乎有了言说自己的权利,但是实际上,他们依然无法摆脱媒介文本的束缚,更多时候依然属于被“言说”的一方。本文通过对包括《中国艾滋病实录》《艾滋病人小路》《好死不如赖活着》《在一起》《颍州的孩子》《宠儿》《朱力亚的故事》等在内的纪实影像中艾滋病感染者形象建构的深度剖析,解读其中的四类“典型化”的艾滋病感染者形象,即愚昧的贫困者、无知的吸毒者、不洁性行为者和被标记的“艾滋孤儿”。
(一)愚昧的贫困者
贫困往往与艾滋病相伴相生,因为贫穷而感染上艾滋病,因为感染上艾滋病而变得更加贫穷。在中国某一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血浆”经济横空出世。血液成为人们欲望的化身和财富诉求的出口,尤其是在某些偏远的农村,卖血、采血行为竟一度流行。由于一些“血头”“血霸”的非法采血行为和违规操作,导致艾滋病病毒在有偿献血的人群中爆发传播。
在艾滋病的纪实影像中,许多作品都呈现了一个个愚昧的贫困者形象。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讲述了马深义一家面对艾滋病及其痛苦挣扎的人生经历。陈为军导演用近一年的时间跟踪拍摄了马深义一家,从影片中可以看到,这个家庭家徒四壁、脏乱贫乏。影片开头就用了一个近一分钟的长镜头来呈现马深义的妻子雷妹犯病躺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哭喊的场景。此外,影片中还大量展示了雷妹病情突然加重而痛苦的特写镜头,她躺在板车上,失去神智,仅靠喝一点奶粉续命,苍蝇就在她的口中进进出出。影片最后还直接呈现了雷妹死亡后躺在屋里草席上的镜头。这些镜头在唤起人们怜悯之心的同时更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中国艾滋病实录——血之灾》把关注的视角放在了贫穷落后的艾滋病高发地区——河南新蔡县。影片开头借艾滋病感染者张从彬之口交代道:“光那个1999年22岁的死了俩,在2000年又死了五六个,2001年死了四个,2002年死了八个。光我们这个东组,年轻人就死了接近有四十个……”这个长达30秒的镜头用一串冰冷的数字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艾滋病的残酷。张从彬在回忆当年村民们争相卖血的场景时,讲到他们为了四五十块钱甚至不惜违反国家规定,一天卖两次血。不可否认,这些影像为消除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和误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无形之中也使观众对艾滋病感染者愚昧贫穷的刻板印象得以强化。
(二)无知的吸毒者
毒品这颗“毒瘤”在社会中存在已久,吸毒行为本身并不会感染艾滋病,但吸毒者确实比普通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一是因为当人们采用静脉注射毒品与别人共用未经消毒或消毒不规范的针头时,便可通过血液传播的方式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人;二是因为许多聚众吸毒艾滋病感染者常常伴随着不安全的性行为,艾滋病便可通过性传播或母婴传播的方式垂直传播给他人。吸毒行为本来就会严重伤害到人的身体,而吸毒者再感染艾滋病则无疑加速了他们走向死亡的进程。
刘绍华老师在其著作《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深度剖析了四川凉山州的诺苏青年们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染上毒品、感染艾滋病的原因。影片《中国艾滋病实录——毒之祸》再一次将视角对准了四川凉山州。21世纪初,诺苏青年们纷纷去往昆明、成都、北京等地方打工,但由于语言不通、文化障碍等,他们难以找到合适的谋生手段,因而走上了一些违法犯罪的道路,如偷东西、吸毒、贩毒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毒品带回了家庭,带回了凉山州,使得吸毒成为了当地民俗,很多家庭因此家破人亡。记者来到凉山州美姑县,采访了九口乡瓦屋村村民吸毒艾滋病感染者阿牛呷铁,镜头前的阿牛蹲着,讲话无力,神情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艾滋病导致他全身免疫功能衰退,以至于每天都要拉五六次肚子。阿牛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显得一无所知,只是机械地回答“不知道”“不记得”等,塑造和呈现出一个苍白无知的吸毒艾滋病感染者形象。当被问及他如何面对死亡时,阿牛绝望地哭诉道,“等待死亡就是希望”。采访中,阿牛呷铁很少直视镜头,影片主要采用俯拍镜头,阿牛呷铁的形象显得渺小可悲。影片还展现了另一位吸毒人员甲巴古子的葬礼,妹妹甲巴阿娣抽着烟向记者平淡地复述着哥哥前一天因吸毒致死的场景。除了展示艾滋病感染者的无知且无畏外,影片还用特写镜头呈现艾滋病感染者后期瘦骨嶙峋、眼眶凹陷的恐怖模样,从而建构出“年轻无知、走向死亡”的艾滋病感染者形象。
(三)不洁性行为者
不洁性行为包括卖淫、嫖娼、婚外性行为以及同性间的性行为。我国艾滋病感染者纪实影像中,涉及卖淫、嫖娼、婚外性行为的内容较少,本文中所探讨的不洁性行为主要是指同性间的性行为,尤其是男性,因为男同性恋者间的无保护性行为更容易传播艾滋病毒。艾滋病最早发现于同性恋群体中,“道德败坏”“罪恶深重”的失范者就是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的代名词,他们遭受着社会强烈的歧视。
早期,艾滋病在美国被称为“同性恋瘟疫”“男同性恋者免疫缺陷症”等。初期的美国电影中所塑造的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形象也往往背负着另类、怪物等污名。1985年,一位来华旅行并曾有同性恋史的美籍阿根廷男青年被发现是国内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当时,中国普遍认为艾滋病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产物,是道德不检点、性开放导致的罪有应得的行为,这样的观点至今仍没有完全消失。《中国艾滋病实录——同之恋》采访了三位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小海诉说自己遭遇歧视的经历,阳光无奈地面对家庭的压力,罗宾疑惑男同性恋的婚恋伦理等问题。片中对酒吧这一空间的呈现多使用摇移的手法,拍摄焦点不固定,时常模糊失焦,从而产生不规则感。这样的画面对应着人物生活的失序与混乱,容易使观众产生偏见,即艾滋病感染者是由于狂热与不洁的性生活所致,是咎由自取。而同期声“许多人都将只能一个人孤独地走完自己的余生,即便是再去寻找爱情,往往也只能把目标限定在艾滋病感染者群体当中”,这样的解说凌驾于故事之上,使得镜头下的艾滋病感染者被呈现为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他者”。
(四)被标记的“艾滋孤儿”
“艾滋孤儿”本来是指“艾滋病造成的孤儿”,但在媒体长年累月的报道中,“艾滋孤儿”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带有负面意涵的符号。纪实影像中有着大量“艾滋孤儿”形象,他们有的感染了艾滋病毒,有的并没有感染艾滋病毒,但他们身上都背负着同样的标签——“艾滋孤儿”。“艾滋孤儿”就好像烙印一般被永远地镌刻在这些无辜孩子的身上,并始终贯穿于他们的成长与生活之中,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形成一堵坚硬的围墙。他们从一出生就与死亡相伴,弱小稚嫩的心灵还要遭受他人异样的眼光,就好像是“傍晚的朝阳”。
在纪录片《颍州的孩子》中,高峻三岁的时候就没有了父母,他整日与一头猪和一台收音机为伴,沉默寡言,他的眼神里没有希望和光亮,满是空洞和无助。在面对小高峻的抚养问题时,小高峻就犹如一块“烫手的山芋”一样被扔来扔去,他的大伯由于担心自己的孩子与高峻同住一个屋檐下遭到歧视而拒绝收养他,叔叔则因为怕影响自己结婚而不愿意抚养他。影片结尾,高峻缓缓地沿着旁边有一座坟头的乡间小路走向远方直至消失,似乎暗示着他终将惨淡的人生。黄家三姐弟在面对采访时,曾多次哽咽,在镜头前几度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长时间积存的压力、自卑和恐惧情绪就好像堤坝泄洪般展现出来。《中国艾滋病实录》中有大量凉山地区的艾滋孤儿,片中对出镜的艾滋孤儿采取了背部拍摄、正脸马赛克的表现形式,这种看似保护艾滋孤儿隐私的做法,恰恰说明他们的正常生活受阻,是“被标签化的群体”。而《毒之祸》中对与奶奶相依为命的艾滋孤儿吉克阿呷,则采用了正面拍摄的方式,由于艾滋病发作,吉克阿呷的头和脚长了两个大疱疹,镜头赤裸裸地呈现疱疹血淋淋的特写画面,再一次使艾滋孤儿的形象刻板化。
四、以污名化对抗污名化:对当下艾滋病去污名化的反思
纵观当下的艾滋病感染者纪实影像,很容易发现这些影像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即以污名来解说污名,以污名化来对抗污名化。Parker和Aggleton认为,当下反污名实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污名是社会认知的产物,那么产生污名的社会认知就必然是有偏差的,是需要纠正的[7]。也就是说,艾滋病的污名化是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社会认知。因此,为了减少和消除人们赋予艾滋病的污名,就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给受众提供完整且正确的信息。例如,在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方面,通过大众媒体向受众传达艾滋病的感染途径、防范措施、注意事项等信息来减少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和焦虑;在人们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方面,倡导以同情和宽容的社会心态来看待艾滋病感染者,并鼓励与他们接触;同时应增强艾滋病感染者应对污名的技巧。但是,这些艾滋病反污名干预措施在实践中被证明几乎是没有效果的。
在这些纪实影像中,艾滋病感染者身上在某种程度上都被打上了贫穷、无知、变态等诸如此类的具有负面意义或消极内涵的刻板化标签。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提供治疗和预防的常识外,其不当报道与呈现却又使得艾滋病及艾滋病感染者被污名化。抵御与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国家层面应该制定和完善艾滋病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艾滋病感染者的合法权益;医护人员应该为艾滋病人提供良好的医护服务和心理治疗;社区和家庭要为艾滋病人营造一个理解、友善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此外,还要避免在宣传教育中采用“恐惧策略”,即试图采用恐吓的方法达到让人们改变自己的不良行为的目的,这样的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强化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与歧视;而对于掌握话语权的纪实影像创作人员而言,更要对艾滋病问题保持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在报道框架、报道话语中尽量减少预设的偏见,淡化对艾滋病患者痛苦画面与典型艾滋外貌镜头的呈现,避免对贫穷进行过分的渲染,对死亡进行过于详细的刻画等。
五、结语
在中国当下纪实影像中,无论是愚昧的贫困者、无知的吸毒者、不洁性行为者,还是被标记的“艾滋孤儿”,他们或是极度贫穷的、或是年轻无知的、或是扭曲变态的、或是十分不幸的,他们的个人生活状态与“我们”有着明显的区隔。在诸多影像中,创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艾滋病感染者最痛苦不堪的场景、最弱小无助的画面、最孤苦冷清的镜头,试图通过这些形象化的展示使公众对艾滋病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殊不知,正是通过这些标签化的影像呈现,创作者们有意或无意地完成了对艾滋病感染者形象的刻板化塑造乃至污名化呈现。在媒介文本里,媒体的建构会强化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刻板印象,社会的固有认知又会影响到创作者本身,如此循环往复,艾滋病感染者将难以超越创作者所建构的文本结构,公众对于艾滋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偏见与污名化将长期持续存在。如何在媒介中正确地塑造和呈现艾滋病感染者形象,是国家、社会和媒体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