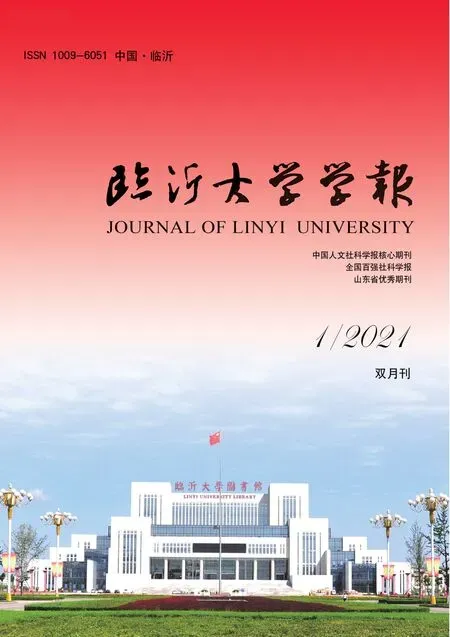反乌托邦与女性主体性的消解
——里奇“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视角下的《一个人的战争》和《说吧,房间》
王 潇 ,许庆红
(1.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2.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引言
艾德里安娜·西塞尔·里奇(Adrienne Cecile Rich,1929—2012,以下简称里奇)是美国现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西方性别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社会活动家和著名诗人,其诗歌才华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里奇女性主义理论的形成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被主流文化牵引着做父权制规约下的妇女,到60年代其女性主义思想的萌发,再到70年代她建构了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到80年代后里奇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对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身份政治的探讨,其核心内涵是政治相关性和现实人文关怀。”[1]里奇的探索和实践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理论(lesbian feminism)[2]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林白在《语词:以血代墨》这篇随笔中坦言她受到艾德里安娜·里奇思想的影响,明确指出“以血代墨”这个词让自己首先想到的是眼泪、压抑、残缺与呐喊,这个词“惊心动魄,最早由美国女性主义诗人里安所提出”[3],作为女性写作最重要的特质,使女性声音从细小变得洪亮,从禁闭到走出禁闭、走向广阔天地。里奇“以血代墨”的创作思想从皮肤到心灵给了林白巨大的震撼和启示。以往对林白小说的研究,从女性主义视角着手的研究开始最早、成果最多,尤其是从身体写作和个人写作入手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在有效解读林白小说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多问题。首先,女性主义理论十分庞杂,而现有研究对此不加分类,笼统地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林白的小说,引用各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的个别最知名的语句,汇总到一处解读林白的多部小说,对理论本身不加区分,没有深入细致的论述。其次,缺乏对林白小说文本的细读,偏向于总体把握其多部小说,对其众多小说的特质一概而论。
国内对里奇的研究呈上升趋势,从早年散落在美国文学史著作中的零星介绍、作品翻译,到里奇的诗歌、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诗学,比如,许庆红对里奇早中期诗歌、女同性恋诗学理念以及性别诗学思想的研究。国外对里奇的研究十分深入和广泛,从里奇的诗歌到散文、再到女性主义思想都有深广的论述,但对林白的研究十分稀少,多是研究陈染的同时捎带上林白。迄今为止,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将里奇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理论与林白小说结合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尝试运用里奇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概念解读林白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及其姊妹篇《说吧,房间》,发现林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里奇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为解读林白的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一、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的乌托邦色彩
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抒发了对15世纪英国时政和社会环境的不满,为了解决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广大人民的疾苦,莫尔设想出了一个理想的国度“乌托邦”,乌托邦城市也因为其太过理想而不可能实现成为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4]卡尔·考茨基认为莫尔的乌托邦幻想开天辟地般地描绘出与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5],引导人们思考当时盛行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弊端,乌托邦思想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对惨苦现实的批判和讽刺,在于美好的社会生活理想对被压迫人们的激励、希望和继续坚持生活的动力及斗志。[6]
里奇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这一术语指涉女同性恋关系贯穿每个女人的生活和女性认同经验的整个历史,而不仅仅是一个女性已经或有意识地想要与另一个女性发生关系的事实。如果将其扩大到妇女之间更多形式的主要的交集,它包括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共同反抗男性暴政时的相互联系、给予和接受政治实践支持等。里奇认为,“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存在于所有妇女的生命体验中,从婴儿吸吮母亲的乳汁到妇女年老去世时同性们对她身体的抚摸、帮助她料理后事,女性可以看到自己在这个连续体中的进出,无论她们是否认定自己是女同性恋者。这种连续统一使女性能够将自身身份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如八、九岁女孩子们亲密的友谊,以及12—15世纪被称为“贝干诺派”(Beguines)的女性群体——她们共享房屋、将房子租给她人或者将房屋遗赠给室友,在镇上工匠区廉价的小房子里,“她们”独自修行基督教美德,衣着朴素,生活简朴,不与男人交往,她们以纺织工、面包师、护士等职业为生,或为年轻女孩开办学校,并设法摆脱婚姻或女修道院的限制而独立生活,直到教会强迫她们分散。里奇将这一现象与公元前7世纪萨福开设的女子学校里著名的“女同性恋者”们联系起来,与被报道出来的非洲妇女中的秘密女性联谊会和经济网络联系起来,与中国的抵抗婚姻姐妹会联系起来。[7]55同样,里奇认为,“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使女性能够联系和比较不同的个体进行婚姻抵抗的例子。例如,19世纪美国女性诗人狄金森从未结过婚,与男人有着脆弱的建立在交流知识层面上的友谊关系,在她优雅的父亲家里自习,给她嫂子休·吉尔伯特写了一辈子充满激情的信。凯特·斯科特·安顿·赫斯顿结了两次婚,她虽然经常遭受贫困的烦扰,反复经历着职业上的成功和失败,但仍然坚持摆脱两段婚姻。这两位处于截然不同环境中的女性都是反对婚姻的人,致力于自己喜爱的写作工作和自我,男性们被她们过人的智慧、永不间断的魅力和生活寄托所吸引。[7]51-57
不得不说,里奇建构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理论具有强烈的女性本质主义倾向和乌托邦色彩,是女同性恋者的理想化社会组织形式,而这种女性共同体在现实社会中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的乌托邦色彩源于她对现实生活中女性毫无知觉地被“强制性异性恋”机制所操控、女性不惜牺牲自我也要奋力进入男性建构的人类共同体的痛心疾首。她在自己的著作 《生为女人:作为经验与成规的母亲习俗》(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中说道:
“除了男人行使于我们之上的权力,以及我们对自己内心一些被否定被拒绝的事情的察觉,在表达男性创造意识的基本话语中,女人也感到了男人的权力……这些权力在我们面前设置了衡量人类渴望的尺度,而且我们经常渴望与那种权力结盟(在一本我那代的高中年鉴中,最有智慧的学生之一这样写道她的抱负:嫁给一个优秀的男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为直接分享权力走得最远的就是与男性权力有所联系。那权力是多么微不足道和渺小,意味着我们活得无助而脆弱。大多数女人对权力的看法是与男性或与对力量的利用分不开的,常常两者都是。”[8]
在男权社会,女性在出嫁之前一直被束缚在小小的闺阁中,长期处于与外部世界隔离的状态中,女性走出闺阁迈向有限的社会的唯一合法途径便是与男性的婚姻关系。对于现实生活中男性通过强制性异性恋机制将男性的性合法化强加在女性身上,以及女性不惜牺牲自己努力进入男性建构的“共同体”以谋求自身的社会价值、获得社会和他人的认可,里奇的愤然和痛心以激进的方式表现出来,勾勒出脱离现实的纯粹女性共同体,即“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
二、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的断裂
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和《说吧,房间》中对女性现实生活、生存状态、女性欲望和心理进行了真实、细腻且大胆的刻画,呈现了众多基于女性情谊、女性关系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但是,她笔下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最终以女主人公女伴的不辞而别、失去联系、死亡和女主人公与女儿的被迫分离而断裂,这反映出林白具有自觉的现实主义写作意识的同时也具有反乌托邦的现实意义。
《一个人的战争》中林多米害怕自己是天生的女同性恋,惧怕自己脱离正常人群,下意识地否认自己对女性身体的渴望和对女性的关爱,她强调自己与女性的关系中没有肉欲,只是美的欣赏,希望别人眼中的自己“在一个同性恋者与一个女性崇拜者之间,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9]30。南丹写给林多米两封充满同性恋激情的情书,第一封情书“南丹说同性之爱是神圣的。最后她说她爱我”,而林多米面对南丹第一封信的真情告白却“十分冷静,一点儿都没有呼应她的热情”。[9]40-41南丹给林多米的第二份情书 “满篇都是对同性之爱的热烈赞美”[9]46,南丹的情书唤起了林多米内心深处自然产生的对女性的爱欲与渴望,仿佛戳破了自己一直竭力隐藏的惊天秘密一样让她感到不安和惊恐。林多米在看过南丹的信之后神情恍惚、心不在焉,无法专心工作,只想着赶紧回到宿舍把这封叙说出自己内心真实情感和想法的信烧掉。因为女同性恋关系是社会的禁忌,自己会因此被认为变态和不正常,如果选择跟相爱的女性共同生活,会成为被双重边缘化的他者,而林多米本身“十分害怕我是天生的同性恋者,它像一道浓重的黑幕,将我与正常的人群永远分开”[9]45。由于自己的女同性恋倾向而使自己脱离正常人群是她万分恐慌的事实,赤裸残酷的现实让林多米不得不对南丹更加防备,刻意掐断南丹对自己的性幻想。也正因为现实社会对女同性恋的不解和歪曲,林多米反思“我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我们互相爱慕,但在最后关头我还是逃跑了,她指责我内心缺乏力量,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9]29。可见,林白反乌托邦的现实主义情节设置终于使南丹绝望地离开了林多米,将林多米这一人物形象描写得自私、懦弱、胆小,却很真实。小说中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以北诺、姚琼、南丹的一一离去和林多米的否认逃避而断裂。
在林白的任何一本小说中,都不存在不切实际且不合常理的纯粹单性世界,无论女性是否是女同性恋,她的生活中总是与男性有不可避免的交集,男性的世界更是少不了女性,女性是男性社会身份认同的关键标尺之一。《说吧,房间》中林多米与韦南红多年时隐时现、断断续续的姐妹情谊在两人的分离、聚首、互诉衷肠中逐渐清晰。南红在经历了男友不辞而别、堕胎、上环、大出血、盆腔炎、失业之后仍然向林多米倾诉道“我不能停止对男人的爱,没有办法”[10]95。存在于两人关系中微弱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以南红最终因宫外孕大出血导致的死亡而断裂,只留下离婚、失业、孤独绝望的林多米在荒凉的世间里,从此她只能从内心不停地发出无助且无声地嘶喊。女性的声音从细小到宏大,从淹没到显现,但无论女性如何疯狂地呐喊都会被男权社会的男性权力所抹去而陷于沉寂,在父权异性恋的社会中,女性的声音往往不被倾听,无论发出多大的声音。男权社会充耳不闻。
“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还存在于母女连心的深厚情意中,体现在林多米对女儿扣扣无限的爱意上。林多米每每亲近自己的女儿内心都充满感动[10]94,女儿身上每一点小小的变化都让林多米激动不已,长第一颗乳牙、开始颤颤巍巍地会走路都给她莫大的喜悦。[10]152然而,林多米与女儿扣扣建立在母爱之上的女性共同体却因为她的离婚、失业而断裂,她想到:“当初我要是知道我会落到没有生活来源的地步,会养不了扣扣,扣扣上幼儿园也会成为问题,我一定重新考虑是否离婚。”[10]165她后悔自己离婚的决定,自责不能没有经济负担地跟女儿一起生活。她不得不把扣扣送到老家,让自己的母亲帮忙照看扣扣,自己则远赴深圳《深港建设报》求职,想稳定之后接女儿过去同住。可是没多久《深港建设报》却下马,自己又再次失业,没有经济来源和稳定的住处,林多米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前夫闵文起给了女儿二千块抚养费后去外地工作,联系不上,迫于经济的压力林多米不得不与女儿分离,她同女儿原本亲密无间、紧密联系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不得不以遥遥无期的断裂而呈现。
三、林白的反乌托邦意识
林白立足于现实社会对女性生存状态进行描写,其作品中自然流露出反乌托邦的意识。她作品中自觉的现实主义写作意识表现在《一个人的战争》和《说吧,房间》中既有对女同性恋关系、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的建构,又有对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的解构,从而消解了女性的主体性。
里奇认为真正的女性关系在父权社会本质上都是女同性恋,她建构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是不需要男性或反对婚姻的女同性恋团体,其刻意将男性排斥在外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流露出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与里奇不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创作源于作者自己的生活事实和她对两性现实社会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在她现实主义为主的写作意识下,林白所建构的女性联系是脆弱又不稳定的存在,具有反乌托邦色彩的现实主义倾向。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是受到强制性异性恋机制的操控却不自知,否定自我并努力进入男性建构的人类共同体。
《一个人的战争》中,林多米有意识地压抑自己从小对女性身体的渴望,极力否认自己对女性的爱情。她逃避与姚琼的身体接触,故意疏远南丹,冷漠无情地回应南丹对自己烈火般的激情,防范南丹对自己表露出的同性恋爱欲,尽快烧掉南丹给自己写的情书,亲手割断自己所有的女同性恋情感,与她爱的和爱她的女性们皆断了往来,分离失散。因为她害怕被定义为女同性恋,惧怕被定义为心理有病而与正常的人群分离。林多米义无反顾地跳进异性恋矩阵,希望通过与男性的恋爱和婚姻证明自己是正常的,从而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可,顺利进入男性“共同体”。林多米说自己三十岁之前没有爱上过一个男人,这让她觉得自己的人生白活了,觉得自己是个脱离正常人群的人,于是她在三十岁即将到来之际下定决心一定要疯狂地爱上一个男人,随后就遇到并疯狂地爱上了电影厂的青年导演N。
《说吧,房间》中,韦南红辞职到深圳闯荡,找到在珠宝城搞销售的工作,最初借助男友老歪的帮助完成了自己第一笔大买卖,卖掉了六万块钱的货。“这是南红做成的第一笔业务,多日来的小心翼翼、看人眼色、受人冷眼、解雇之忧一扫而光,六万元的效益犹如一只巨大的救生圈,南红坐上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10]46她付出的代价就是和老歪发生关系,并在老歪觉得不方便的时候单方面和韦南红轻而易举地一刀两断。在南红与林多米的诉说衷肠中,林多米发现南红在深圳的每一次工作变动和生活机遇的转折背后都与某个男朋友有关。[10]32
林多米切断了自己跟以前所有朋友的往来,跟闵文起结婚。“结婚很匆忙,闵文起是二婚,我当时已经过了三十岁,觉得自己老了,而且对爱情没有什么信心,只急于摆脱旧的环境。N城使我腻味透了,我当时借调到市里一家文学杂志社帮忙,单位让我赶快调走”,闵文起“当时还在部队搞宣传,说是通过部队到北京很容易”。[10]50林多米借助和闵文起的婚姻摆脱之前感情、工作和生活上的困境,顺利将工作调到了北京并在婚后生育了女儿扣扣。
在林白的这两部小说中,女性借助与男性的恋爱、婚姻等关系试图更好地进入社会,得到工作岗位、经济收入、安全感,获得妻子、母亲的社会身份,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同。但是对男人而言,女人和车、房并无差别,女性是高度物化、符号化的存在,她们是代表男性个人魅力、社会身份、地位、成功与否的价格标签。[10]39因此,男权社会中男性所建构的“共同体”是不包括女性的,就像时代发展到现代社会,仍然有许多男人赞成于勒·拉福格说言:“不,女人不是我们的兄弟;她除了性器官以外,没有别的武器,……不管她是热爱还是憎恨,都不是坦率的伙伴。”[11]在男性建构的“共同体”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权力关系的不对等现象随处可见,更何况“其实这些男人根本就不想同女人共命运”[12]。这种不对等包括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女性为了迎合男性的性而进行的堕胎、上环、忍受职场性骚扰等。林白笔下的女性人物有意识地否定自己的性,轻视或无视周围的女性联系,想摆脱“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奋力想要进入男性共同体,很显然,这是林白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写及其反乌托邦现实主义写作意识的有力再现。
四、女性主体性的消解
人的主体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包括发扬人的自身特点,作为主体在认知和处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中能够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不断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主体性的高度弘扬。[13]人应该承认自己的主体性,并且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否则,这种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14]24尽管人的生命自觉总是从其对独特自我的意识开始的,但人的完整意义上的个体生命是由他所属的群体(社会、文化)支持和塑造的。人的生命意识的发展是不断突破自我的中心走向群体的过程,人需要在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可、承认他人和社会的过程中建立个体的主体性。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才能获得日益完整而深刻的生命自觉,人的主体性才能实现自我超越,即个体主体在群体生命中才能得到确证和张扬。[14]30-34人的主体性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但人的主体性的生成、成长和实现则是充满矛盾和曲折的过程,在社会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对于相当大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的主体性不是一种确定性和普遍性的事实。[14]30-34
理想的社会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场所,是我们相互了解、互相信任、能够平等地互相依靠对方的人类栖息地。女性为了进入人类共同体,得到一份并不稳定的安全感,耗尽心力、欣然接受失去自由的昂贵代价。[15]但即便如此,由于男性建构的共同体是不包括女性在内的,因此女性无论付出多大代价,试图真正进入男性共同体的愿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个过程也是女性的身体和心理被束缚的过程,是女性主体性被消解的过程。
林多米下定决心进入异性恋矩阵之后单方面对青年导演N一见钟情,她忘我地爱着N,渴望能和N步入婚姻的殿堂,有他们两个共同的孩子并携手共度一生,然而N却在一开始就强调自己是不婚独身主义者。林多米无限地包容N,独自承受堕胎。但N毫不怜惜她对自己的情谊和付出,反而只会利用林多米对自己的爱情控制、盘剥她的文学劳动创作为己所用。林多米渴望N的爱情和婚姻,为了获得幸福、找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入人类共同体付出巨大的努力,受到了从身体到精神上的种种伤害,然而最终因N的无情背叛而幻灭。“像一个弃妇,一夜之间苍老了。我整整一个星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不想吃饭也睡不着觉,我整夜吸烟,我的脸上新长了许多细小的皱纹,我的嗓子全嘶哑了,整个没有了样子。”[9]186这场全情付出的爱情伤透了林多米的心,她只想离开这个伤心之地逃往北京,并最终通过嫁给一个年长的男性逃离了伤心之地,逃离那段悲伤的感情,却没能通过异性婚姻进入人类共同体,反而被他人诟病,成为男性共同体口中为了达到去北京的目的,不择手段出卖自己感情和身体的无耻之徒[9]188,她试图通过纯洁的爱情或没有感情的婚姻寻找自我认同、融入人类共同体的所有努力都以失败而幻灭,她的一生一直都是她孤独地对抗全世界的一个人的残酷战争,一场明知结局却还要继续忍受的失败的战争。
韦南红在男人那里一次次地被抛弃,经历了堕胎、上环、大出血等各种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但她还是无法停止对男人的爱并不断牺牲自己满足男性的性欲望,试图进入男性共同体。她轻视与女性朋友间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却不能够停止对男性的爱,为了满足有妇之夫史红星的男性性欲望,她忍受剧烈的疼痛,主动到私人诊所接受上环手术,上环不到一个月就与史红星发生关系,导致盆腔炎大出血,失去了健康和工作,她卧床期间却没有得到史红星的一点关怀,反而得到史红星因嫖娼被抓的消息,南红最终死于宫外孕大出血。
林多米通过与闵文起结婚顺利进入男性共同体,解决了工作和住宿问题,却因为不能容忍闵文起的婚内强奸而导致丈夫出轨,两人婚姻关系破裂,两人的离婚又直接导致了她成为唯一一个被单位解聘的人,从此踏上漫长而艰难的求职之路,也因为缺乏经济基础而不得不被迫与女儿分开。两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努力进入男性人类共同体的幻想,也都随着男朋友的利用、背叛和抛弃,与丈夫的婚姻关系破裂而土崩瓦解,一切成空后只给女性留下身体上和精神上无尽的伤痛,彻底消解了女性的主体性。
结语
里奇所构想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是将所有男性排除在外的,仅由女性组成的女同胞间互助互爱、相伴共度一生的女性共同体。这种世外桃源般的女性共同体组织无论在理论层面或实际操作层面皆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而林白作为一名中国当代作家,在其反乌托邦现实主义创作意识下,《一个人的战争》与《说吧,房间》两部小说中基于女性情谊、女性关系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都以断裂而告终,消解了女性的主体性,女性最终不得不与现实的男权社会妥协。林白既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她基于社会现实的文学创作又反映出一定的反乌托邦意识。林白作品中女性主体性的迷失说明“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这一女性乌托邦在中国男权社会现实下难以实现,体现了林白的反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写作倾向。两部小说的结尾所呈现的与现实妥协的痕迹反映了林白的性别建构所表露出来的悲观主义自觉意识,彰显了林白女同性恋写作的复杂性。
——以南丹发展旅游产业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