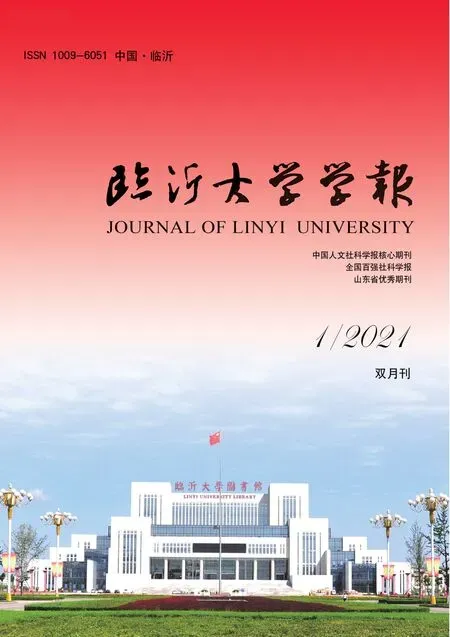浅议《周易》“象思维”及其在传统设计思想中的体现
高 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250300)
“象思维”是《周易》独特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象”在《周易》中首先指卦象,其次指卦爻辞中通过语言描述呈现的物象,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虽然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概括性,但却不是完全固定的抽象概念,而是包含着时间维度的、具有更丰富的阐释空间的生成性范畴。
《周易》卦象以数位排列的规律来呈现,所谓的“数”(指阴阳数,即爻的属性是阴或者阳)与“位”(指爻在卦象中的位置,六爻组成一卦,爻位自下而上称为初、二、三、四、五、上)都具有时间属性,因为不同属性和位置之间反映的不仅仅是空间的不同,而往往是某种事态发展阶段的不同。《周易》原用于占卜,所以卦象本就是一种表现事态变化趋势的符号系统,它不是静止不变的“象”,而是处在不断流动变化中的“象”。卦象往往通过语言(即卦爻辞)的描绘呈现出某种具体的事或物的“象”,但此“象”是与易理相对应的。《周易》不是通过明确的理论语言来解释道,而是通过生动的“象”使道自然呈现出来,并且卦爻辞的语言风格是极简约而生动的,目的在于呈现出一种情境,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想象和形象的“象”。也就是说,其呈现的“象”既不是超越于时间的固定的“象”,也不是在具体时空环境中的具象,而是一种具有流动性和生成性的,在抽象与具象之间的特殊范畴。
《周易》通过“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制器尚象”三个重要命题揭示了“象思维”的基本原则,而这三个命题与传统工艺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是一脉相承的。
一、“观物取象”的设计方法论意义
“观物取象”原本是解释《周易》卦象的形成方式的,即通过观察万物而得到卦象,但“象”这一概念在《周易》尤其是《系辞》中并不仅指卦象,因而“观物取象”也就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尤其是思维方法论的意义。“观物取象”所描绘的“象”缘起的方式及“象”作用于人类文明的方式,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有近似之处。在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中存在着二元论的难题,按理性主义哲学的观点,现象与感性能力相对应,本质与理性能力相对应,后者是一种脱离感性的共相,只能以抽象概念的形式把握。这样,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知识就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西方哲学一直在努力填补这条鸿沟,但最终并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试图克服不可知论,但最终还是留下了“物自体”这样一个理论缺陷。
胡塞尔提出“本质直观”的哲学方法,从思维方式的根底上打破了这种二元论。他认为并不存在超越于现象之外的本质,作为观念的本质与感性现象只是现象呈现的不同方式,因此对本质的把握与对感性现象的把握一样,都是通过“直观”进行的,只不过对本质的“直观”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直观方式。我们之所以说“本质直观”具有方法论层面上的重要意义,是因为它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迷信,即本质总是隐藏在现象之后的,是和现象根本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因此对本质的把握一定是与对现象的直观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方式,这其实是一种西方人已经习以为常的成见而已,并无真正的依据。而现象学首先通过“还原”的方法将这种成见“悬置”起来,将所谓的本质观念和感性现象都还原成完全没有任何设定的“纯粹现象”,然后通过分析不同种类“纯粹现象”的内在结构,揭示了本质观念在直观中的构成方式。这种对本质的理解,与西方传统哲学很不相同,从本质到现象不再泾渭分明,而是成为了过渡的过程,作为“纯粹现象”的本质不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观念,而具有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这与《周易》“象”的观念就有了相通性。
关于“观物取象”,《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1]510《周易·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故谓之象。”[1]487表面上看起来,这里的“象”似乎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名词具有形象的意思,二是作为动词具有摹仿的意思,故此学界常将《周易》“观物取象”的方法与西方的“摹仿论”相比较,但这种比较并没有真正理解“象”的意义。摹仿论中摹仿的对象和结果都是现成的形象,《周易》则明确区分了“象”与“形”两个概念。《周易·系辞上》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1]497这里的“形”才是可以被直接把握的实体性的形象或者形式,是与“器”结合在一起的具体的东西,而“象”则是单纯的显现,是超越于“形”之上的道器之间的中介环节。它既不脱离形象,又将形象之外的意义蕴含于其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观物取象”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感性的摹仿,也不同于纯粹理性的抽象,既不脱离于直观,又不局限于具体形象,因而更接近现象学所说的“本质直观”方法。张祥龙教授认为:“这象是最原来意义上的、凭它自身就能被直接领会的引发结构。一般意义上的观念、表象、概念、结构、符号、象征、图像,都做不到这一点。”[2]因为概念、表象等都是显现的结果,是一种完成的状态,而“象”则是一种生成的状态,“观物取象”就是通过“观”将“象”,即事物的意义生成出来。
可见,在《周易》中“象”与“观”有深层次的联系。“观”是《周易》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成中英认为:“观是中国古典哲学最原始的起点。……‘观’是指全面而又动态地认识和理解宇宙中所包含的整体事物;‘观’是方法、是活动、也是过程。”[3]“观”是一种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特殊方法,与一般的观察和认识不同的是,它不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把握,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把握。《周易·观·彖》说:“中正以观天下。”[1]153《周易·观·象》说:“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1]154“观”包含“观民”“观天下”的含义,显然是指一种能够把握世界运行规律而使“天下服”的根本方法。在《周易》中,“观”与“象”的意义在某个层面上是相通的,因而“观”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也有相近之处。
这种相近之处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观”所包含的特殊心态与现象学“本质还原”方法或“悬置”方法有内在相通之处。所谓“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1]152,意思是祭祀时先要酝酿恭敬虔诚之心,看完前面往地上撒酒的降神仪式就可以了,不必看后面向神献飨的仪式,也就是说,保持这种虔敬之心比祭祀本身更为重要。这种特殊的心态正是“观”这种方法的关键所在。《老子》也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4]73;又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4]134这里的“观”同样强调无欲、虚静的心态。这种心态在祭祀活动中是在对仪式的直观中排除掉杂念,直接把握到仪式蕴含的内在意义,而在观象活动中也同样具有排除杂多现象的干扰,直接把握其内在意蕴的意思。
另一方面,“观”的对象不只是单纯的感性现象,而是在现象中“观”到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象”。“观物”与“取象”不是两个分离的过程,而是“观”的一体两面。《说文解字》说:“观,谛视也。”[5]也就是说,“观”不是一般的看,而是对事物的深度审视,它本就是一种特殊的观察方式,是直指本质的特殊直观。同样,“观”与“象”也不应分割为行为与对象两极,“观”就是使“象”显现出来的过程,而“象”只有在“观”中才能显现出来,二者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说,“观物取象”是《周易》提出的独特的认识论原则,是“立象尽意”和“制器尚象”的前提和基础。《周易》认为,人类文明创生和文化创造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之下才成为可能,而造物活动作为推动文明发展的根本力量之一和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要以这一原则为前提和基础。
二、“立象尽意”与设计的意象构造
“立象尽意”原本也是就卦象的作用而言的,《系辞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1]504可见“立象尽意”恰好与“观物取象”相对应,从相反的角度解释了卦象的形成。但这一命题同样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周易》之“象”不是简单的形象,而是包含着“意”的“象”,“象”是“意”的源泉。 而“意”与“象”的关系又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或象征关系,“象”的意义不是可以被语言完整表述的抽象意义,而是生成过程中的意义,无法用语言完全传达出来。“象”之所以成为《周易》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因为它蕴含着单纯物象之外更深邃、更丰富的意义,“意”与“象”之间的关系,用后世文艺理论的命题来表述,就是所谓的“言有尽而意无穷”[6]。
所谓的“意无穷”是指,“意”总是在鲜活的情境之中才能展现出来,事态的变化在时间之流中遵循着自有的规律,在特定的时机呈现出特定的情境,又在特定的情境之中展现出不可言说的“意”,之所以不可言说,就是因为它是变动而非固定的。因而能够“尽意”的“象”,就是这种特定情境在《周易》中的具体呈现。如钱钟书所说:“象虽一著,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7]这精当地概括出了“象”的特性,之所以能“孑立应多”,就是因为能“守常处变”而非一成不变,这样变动不居,始终处于生成状态的“象”才是真正意味无穷的“象”。
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立象尽意”的思想演化为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意象”。“意象”理论在当代美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相关论著、论文汗牛充栋,甚至有学者认定其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概念。然而在当前理论界对“意象”概念的阐释中,有一种主流的观点把“意象”理解为“意”与“象”的结合。这种观点古已有之,到王夫之关于“情”与“景”关系的论述而趋于成熟,到王国维的“境界”论又吸收了西方美学的观念而逐渐演化为具有现代性的理论形态,但这种解释与“意象”概念的本义并不完全符合。
“意象”概念由《周易》“象”的概念演化而来,是后世学者在对“立象尽意”这一命题的进一步阐发中提出的。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8]“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即有一种超越于“言”之外的、现成的“象”存在,又有一种超越于“象”之外的、现成的“意”存在。实际上,王弼不是否定“象”,而是否定把“象”理解为固化的形象或符号。他主张不能僵化地依据《周易》文本的字面含义来理解“象”,更不能僵化地依据固定的卦象来理解“意”,一旦“象”被限定住了,那么“意”也就丧失了它鲜活的生成性,变成了干瘪的教条。另一方面,王弼的易学思想明显受到道家影响,《周易》文本中的“象”毕竟是有所本的,即卦象,而道家著作如《老子》中的“象”则更多体现为“虚象”而非“实象”。《老子》说:“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4]229这里的“象”已经不是感官所能把握的了,《周易》之“象”区别于实在的“形”,而《老子》之“象”则根本上是无形的。《老子》与《周易》,尤其是《易传》思想本就相通,经过王弼的阐释,道家思想对易学,进而对传统文艺理论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学传统中,这种偏于道家的对“象”的理解衍生出了强调“象外之意”的“意境”理论,是“意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意境”理论强调的是,以有限之“象”体现无限之“意”,这比将“意象”简单理解为“意”与“象”的结合要更为深刻,也更符合“立象尽意”的本义。
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开始了将《周易》之“象”向文艺理论的“意象”转化的努力。《文心雕龙》虽是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却受儒家经典、尤其是《周易》影响至深。其《神思》篇说:“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9]493这是“意象”这个词首次被作为美学概念使用,刘勰虽未对“意象”这个词作进一步的解释,更未单列一篇讨论“意象”问题,但结合该书的整体语境,此语应与《周易》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易学研究有一定关系。更能够体现刘勰的“意象”论思想的是《隐秀》篇,《隐秀》篇说:“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9]632“隐”与“秀”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二者的关系可以有两种解释,或解释为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或解释为审美意象的两个层面。如按前一种解释,则“隐”就代表着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特质,所谓“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9]632;如按后一种解释,则“隐”与“秀”就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说明审美意象的特质,这种解释更为贴近我们对“意象”概念的理解,也更符合文艺作品中广泛存在的美学现象。
“意象”虽然主要是文艺理论的概念,但它在设计美学思想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器物制作从结构到装饰,都不仅仅出于实用目的或单纯的美观,而是蕴含了更为丰富的意义,这就使实用器物除了其实际用途之外还承载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义,具有了与文学艺术相当的地位和价值。也就是说,器物的设计过程,首先当然是从实用目的出发的,在满足了特定的实用功能之后,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装饰,以实现基本的审美功能。这种装饰只是设计活动的低级阶段,如此制造出来的器物也仅仅是颇为美观的器物而已,它无法承载更多的文化意义,自然也就无法与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相提并论。但在中国的设计传统当中,高级的器物设计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装饰美化,对器物造型、材质、色彩、结构等各方面的设计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蕴含着丰富的意义。
器物的设计主要通过“象征”的方式呈现出超出具体物象的丰富含义,其所提供的“象外之意”在本质上与文学艺术中的“意象”是一致的,都是对天地自然之道的某种隐晦的指涉。如《考工记》说:“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10]180在工艺设计中,色彩的象征意义被广泛运用,并且通过与“五行”的对应将器物的色彩、形态结合起来,对应于自然物象。李砚祖教授说:“在设计上,循天时、守地气、尊重自然的设计观念,还导致了对自然物的仿象和再现意识,……这种对自然物的‘仿象’或‘仿生’设计,其思想根源在于古人对自然的尊崇和敬畏观念。”[11]79-80这种基于象征原则的设计美学思想,尤其体现在与礼制相关的礼器、礼服、重要建筑等的设计上,即以装饰的或选材的方法赋予器物以象征的意义,并且往往是将器物设计为天地宇宙的缩影,从而呈现出天地人和谐的宇宙观。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12]281《周礼·夏官·弁师》说:“五冕……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12]458可见,根据器物及其材料的质地、颜色、形状、结构等等,都可以产生相应的象征意义。
如上所述,“立象尽意”的设计思想在具体的器物设计活动中常常以象征的手法体现出来,而这种象征的模式与西方的象征理论也有可比较之处。西方传统的象征理论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这就难以避免出现程式化的状况。经过中世纪宗教思想的影响后尤其如此,如在文学、绘画、雕塑乃至建筑等艺术类型中都存在这种状况,这种程式化的象征所能够承载的文化意义只会越来越贫弱和固化。而现代象征主义文艺理论则将象征深化为文学艺术内在的本质和规律之一,视为文艺审美价值产生的内在机制,因而程式化的象征手法不应被当作真正的象征,发现某种具象与特定内在深层意蕴之间的联系并以创造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过程才是真正的象征。这种理解显然更符合“立象尽意”的设计思想。
在中国传统设计思想和实践中,器物设计中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有高下之分的。传统社会中,在官方“礼制”思想和民间习俗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器物设计的规则同样容易产生程式化的倾向,如日月星辰等天象、珍禽异兽等物象、各种色彩、器物和建筑的体量和形制等等,都逐渐具有了相对固定的象征意义,并且它们出现在何种器物中以及以何种方式出现在器物上,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或习惯,这就导致了器物设计逐渐丧失了“意象”的美学价值。但更深刻的、更具有创造性的象征手法还是广泛存在的,特别是在与传统士大夫生活有关的器物、园林等的设计中更为集中。这是因为,一方面,士大夫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和审美素养,使他们能够产生更复杂、更精微的审美追求,并且懂得如何创造出更新颖、更精美的器物;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尤其在宋明之后的某些时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开始相对摆脱了严格的礼制规范,具有了比较自由的创造精神,使他们能够在器物设计中体现个人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寄托。因而,以他们的需求为目标设计和制作出来的各种器物,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就灵活得多、自由得多,其产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也就丰厚得多。
三、“制器尚象”与《考工记》的“知者创物”思想
《周易》关于“象思维”的思想中,与设计思想关系最紧密的是“制器尚象”这一命题,《系辞上》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1]495对这个命题前辈学者曾有不同的解释,如顾颉刚将其理解为圣人观卦象而“制器”,从而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不符合人类实践活动的实际规律;而胡适则认为这里的“象”不仅指卦象,而是泛指各种自然现象,“制器尚象”就是指古人通过观察自然而总结规律乃至发明创造,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摹仿论的色彩。二者观点虽异,其思维方式则是相通的,都是将“象”理解为某种现成的对象。
但“制器尚象”的“象”和“观物取象”的“象”是同一个“象”,都带有方法论的含义,而不是简单的对象。事实上,所谓“圣人四道”中的辞、变、象、占,都具有方法的意思,即辞是言的方法,变是动的方法,占是卜筮的方法,而象是制器的方法。这里,作为制器方法的“象”同样与现象学“本质直观”的方法有相通之处,不过“制器尚象”不是在从“物”到“象”的过程中,而是在从“象”到“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这种“象”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不论是认知还是物质实践中的创造性活动,都必须经过一个和“象”有关的中介环节。物质实践活动是认知活动的逆向的过程,即从观念到实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象”或者本质直观同样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象”的这种中介作用在艺术创作和器物的发明创造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一个设计理念或者一个设计目标,开始是作为比较抽象的观念而存在,这种抽象观念很难直接在设计实践中实现出来,这时就需要想象力发挥中介作用。想象力是分不同层次的,它可以是对感性形象进行加工改造的具象的想象,在一般的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中人们讨论的主要就是这种想象。但它还可以是将感性形象与抽象观念连接起来的特殊想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就曾深入论述过“先验想象力”的问题,认为它是将感性经验与知性范畴结合起来的关键环节,这种所谓的“先验想象力”与现象学所讨论的本质直观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13]
因此,所谓“制器尚象”表明的是,在人的各种创造性活动中,“观象”的过程,即在现象中洞察本质,是一个基础条件。《淮南子·说山训》中说:“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见鸟迹而知著书,以类取之。”[14]《后汉书·舆服志》也说:“后世圣人观于天,视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携龙、角为帝车,于是乃曲其辀,乘牛驾马,登险赴难,周览八极。”[15]表面上这是一种简单的摹仿论,但如果作深一层的思考即可知,在自然现象与器物制作之间是有着明显的界限的,此界限绝非二者表面的相似能够解释,即便古人真的是见飞蓬转而作车,此中仍旧包含着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即“观象”这个中介环节。也就是说,在观察自然现象与发明制作器物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摹仿环节,而是经过了复杂的感性现象与抽象观念的转化过程,首先通过“观象”在自然现象和人的社会生活中获取某种关于器物制造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又不是完全抽象的观念,而是在想象活动中与感性形象结合在一起的观念,因此,在人由观察活动转向制作活动之时,这种观念自然就在想象力的作用下融入到器物设计之中了。
而在更能够体现人的创造力的审美中,在想象力发挥着更重要作用的审美心理活动中,尤其是在将审美渗透于器物造作的工艺制作活动中,“制器尚象”就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了。根据人的某种功利性需求而设计器物的基本结构,当然需要想象力发挥作用,而将器物设计制造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蕴含着超出实用功能之外更丰富意义的产品,则需要更深刻的想象力。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制器尚象”的“象”解释为想象,正如不能把“观物取象”完全等同于本质直观一样,但如上文所述,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制器尚象”的设计思想还与《考工记》提出的“知者创物”思想有内在的联系。《考工记·序》中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10]159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工匠的地位并不高,在所谓“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仅高于商人,因而“百工之事”应当算不上什么高尚的事业。但《考工记》却将“百工之事”抬高到“圣人之作”的地位,这其实并非是对现实的工匠以及手工生产活动的溢美,而是有其特殊的理由。《考工记》一开篇即提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10]159,这是从政治的角度肯定了手工业的重要地位,但在这“六职”之中,百工本身的地位仍然不是最高的,“百工之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仅有“巧者”(即工匠),而且有“智者”(即圣人)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并且后者的作用要远比前者更为重要。关于圣人创制器物的传说,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如伏羲制琴、黄帝制舟车等等,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本来是因解释文明创生的,在《考工记》的设计美学思想中则演化为“智者”与“巧者”或圣人与工匠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中,“智者”的作用是“创物”,即发明创造各种器物,这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显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巧者”的作用是“述之”,即运用工艺技术将圣人的发明创造实现出来,这当然也是重要的,但却不能与圣人的事业相媲美。
而“知者创物”的观念则明显与《周易》的“制器尚象”是一脉相承的,李砚祖教授认为:“此论与《周易》中将‘开物’归集为圣人为同一思路,这应看做是当时社会的共识。‘圣人’即智者,‘创物’并非自己动手去做,而是‘设计’。用今日之概念,即‘设计者’、‘创作者’为当时的智者和‘圣人’。”[11]79《周易》认为圣人通过“观象”理解“天道”,进而可以有各个方面的文明创建的成就,“制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它不是单纯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通过“观象”体察到“道”,然后才能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可见,《周易》的圣人“开物”或“制器”思想,与《考工记》的智者“创物”思想遵循的是同一个思路,那么“智者创物”自然就与圣人“制器”一样,是一个必须通过“观象”才能实现的过程。比如,《考工记》中提到百工“审曲面执”的工艺制作方法论,即“审视曲直,观察形势”[10]161的制作原则,与“制器尚象”也是相通的,“执”通“势”,工匠制作器物时审视的不仅是材料的固定形状和材质,而且是要把握和顺应它的“势”,不是凭借人的理念和力量把外在的形式赋予对象,而是在直观中发现对象内在蕴含的“势”,并将其实现出来。在这里“势”与“象”是相通的,它不同于“式”,即现成的结构、形式,而是带有将某种形式或意义生成出来的意思。
更重要的是,在古人看来,“知者创物”之所以重要,还不仅在于圣人通过“创物”活动给国家人民带来了现实的福利,更在于“创物”活动本身就是符合“天道”的,是“天道”在人世实现的一种形式,这种人事与“天道”相符合的观念在上古经典中广泛存在,《周易》尤其如此。圣人“制器”或“创物”的过程就是通过“观象”使“道”寓于“器”之中,从而使工匠制作器物的活动能够符合天道,如此其产品才具有真正的价值。王夫之在其《周易内传》中指出:“制器尚象非徒上古之圣作为然,凡天下后世所作之器,亦皆暗合阴阳刚柔虚实错综之象,其不合于象者,虽一时之俗尚,必不利于用而速敝,人特未之察耳。”[16]也就是说,“制器尚象”不仅是圣人把握天道的方法,也不仅是工匠制作器物的手段,而是使二者融合为一体的最根本的设计原则,应通过器物设计制造活动,使人们日常生活所用之器都能够符合“天道”,也只有如此,设计制作出来的器物才能行之久远。总之,《考工记》“知者创物”的观念就是《周易》“制器尚象”观念在设计美学上的直接体现。
综上所述,《周易》蕴含的“象思维”思想既是一种独特的认识活动的方法,又是一种独特的实践活动的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对以《考工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追本溯源,从“象思维”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设计思想有别于西方设计思想的独特之处,对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传统设计思想的精神内核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