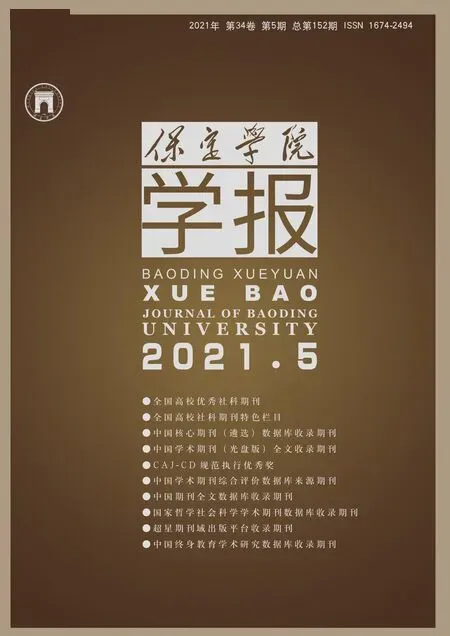“大言炎炎”:《庄子》言说态度试论
于 畅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大言炎炎”仅是《庄子》中并不突出的一句话,对其的解读也止于字句含义的解释。“大言炎炎”参考注家解释,应为“大言淡淡”。“大言淡淡”实际上是《庄子》关于言说的一个重要层面,即言说态度层面。言说态度不像对“言”直接论说的思想观念与显示于文辞的表现形态那样显明易见,但可以说它是《庄子》之言的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层面,对于理解《庄子》之言说有其独特的意义。
一、“大言炎炎”释义及界定
“大言炎炎”出自《庄子·齐物论》,其文曰:“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陆德明引李轨所注音称:“李作淡,徒滥反。”[1]57王叔岷《庄子校诠》:“淡、炎正、假字,《老子》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卷子本《玉篇水部》引口作言)孟郊《荅友人诗》:‘道语必疏淡。’所谓‘大言淡淡’矣。”[2]49钱穆《庄子纂笺》引章炳麟:“‘炎’,同‘淡’。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也。”[3]11参考以上注解,可证“大言炎炎”之“炎”是“淡”字。
《说文》:“淡,薄味也。从水,炎声。”“淡”由薄味引申出诸多含义,《庄子·应帝王》:“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1]300-301“淡”与“漠”并列,可见“淡”有淡漠的含义,且“游心于淡”可见“淡”与“游”有所关联。《庄子·山木》:“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1]682此就亲友交往关系而言,是子桑雽答孔子“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何与”之问。由此可知“淡”与“疏”相对应,“淡”有疏淡之义。此外,“淡”还有隐约义,例如《列子·汤问》:“二曰承影,将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际,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识其状。”[4]187-188此处“淡淡”有隐约不清的含义。
《庄子》既有“大言炎炎”,又有“大辩不言”“大道不称”等主张不言的说法。《老子》中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的观点,认为至大之道超越于有形、有限的声音、形体以及名称言语,有限的名言无法完全显现大道,认为“道常无名”。《老子》主张“不言之教”,认为“大辩若讷”,名或言是人为强加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人为的言有违于自然之道。《庄子》的“大辩不言”“大道不称”与《老子》的这一观点之间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而《庄子》在主张言之有限的基础上,对言作出了更为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剖析。与《老子》有所不同的是,《庄子》着重标示出言的变动不定,言的不可靠导致其对道的不可呈现;而另一方面,言的变幻不居又导向了《庄子》自身言说的好为大言、汪洋恣肆。
《庄子》的表述中既推许大言又提倡不言,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嫌,需要对这似乎矛盾的情况加以辨析。《庄子》关于言有较多的审视和思量,对言的直接论述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道与言的关系。庄子认为:“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五者园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1]89-90庄子强调言的未定性,“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人各有其言,变化无定,所以言不能够完全地呈现道。
其二,谓言。庄子既否定言与道的统一性,同时也区别言与所言对象的差异,即“谓”的命名客观上建立了所言对象之外的一个言的存在,而非对应所言对象本身。“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一本身与“谓之一”的言是不同的,言一出口则有谓,有谓就已经偏离了原本所言之物。而谓言在物之外形成了概念的物之“然”,物本身之外有所“谓”之物。“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马其昶曰:“各有所行以成其道,各谓其物为然,而异己者为不然,皆私也;非真是所在。”[3]15人各有“谓”,于是有彼此不同之谓,有是非之辩言。
其三,辩言。辩言在《庄子》中事实上为是非的表现形式。庄子认为争辩之言出于分别,求于是非。“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言原本的沟通作用在辩言的“不能相知”中被翻覆向反面,而“辩也者有不见也”在为求显明是非而“辩之以相示”的时候,反而执其一端,遮蔽了其他可能性。在辩言中,每个人都自执一端,无处求正。
以上可见,庄子对言主要是持怀疑的态度,并加以审视和剖析,而称许“不道之道”“不言之辩”。这些论述都可以划归于“不言”之言。可以看出,“不言”之言基本上对言这一概念与现象加以直接的审视。“不言”之言可以称为论说对象,此时的言不是话语口出之言,而是作为一个与道相关的言的概念和现象,是探讨的对象。而通过对言这一对象的探讨所形成的“不道之道”“不言之辩”的主张,则可认为是对于言的思想观念。
“大言炎炎”之言在《庄子》中少有直接的述说,而主要是反映在具体的言说之中的。“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一句是对不同的言的形容,其后是对人多种不同意态的形容,既是形容,与“不言”的段落相比可见,应不属于对言的具有哲思的观点,而是对言的运用中的状态的表述。简言之,这是运用中的言。《庄子》所用的言,就如惠子诘难庄子所说:“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此处指的是庄子自身所用的言说,它的表现是“大而无用”,既内容丰富,蕴含广博的智慧和无限的理解空间,且表达恣肆,具有磅礴的气势与光怪奇异的想象;又疏淡无为,不措意追求言说的用途或接受。庄子在对“言”持怀疑态度下的“妄言之”,既包含“不言”的观点,也带有对言说的自如和自恣的态度。淡淡大言可以说就是这种运用在文章之中的言说的态度。“大辩不言”“大道不称”与“大言炎炎”属于言的不同层面,“不言”之言属于所论之对象,“大言炎炎”之言则归于所用之言说,“大辩不言”“大道不称”等是对言这一现象的观点,“大言炎炎”是对言在运用中的态度。而对言的观点也影响着言说的态度,庄子对言的怀疑与反覆倾向使得他对言不会特意谋求推行和接受,不专门追求言说的辩论、劝谏、教化作用,不会非常看重其言说的实用价值,一定程度上促使生成淡淡大言的言说态度。而与“大言炎炎”相对的“小言詹詹”则是与有彼此是非的“谓言”“辩言”相联系的言说态度,是“大言炎炎”要超越和消解的对象。
二、《庄子》淡淡大言的言说态度
《庄子》的语言在总体上是可以用“大言淡淡”来形容的。《庄子》想象光怪,文气恣肆,从表现形态看一般不认为其淡薄无味。此处“大言淡淡”所说的是一种言说态度,而非表现形态。“淡淡”主要呈现为三个方面:“游”的立论态度、隐约的命题态度、疏淡的审视态度。
(一)“游”的立论态度
《人间世》中有接舆歌的故事,接舆意态与同样记有此事的《论语》不同,《论语·微子》中说“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而《庄子·人间世》则是“楚狂接舆游其门”[1]189。相比较可见,《庄子》中的接舆具有“游”的态度,而《庄子》中的接舆作为庄子的代言,其“游”的言说态度也就是庄子的言说态度。“游”的态度可归纳为游刃有余之言、游戏笔墨之言、游于无穷之言三种表现。
言的游刃有余,主要是指《庄子》的语言运用流利自如,举重若轻。一方面,庄子喜欢提出概念,如“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等等。命名诸多概念也体现了庄子对论述语言清晰而自如的把握。另一方面,在遣词用句上,《庄子》言辞流丽,毫不拖沓,语言往往轻描淡写,在行若无事中述说深奥哲理。李世熙在为《南华雪心编》作的序中称:“夫庄子非有意于为文,而其文之天然入妙者,一若造化自有此灵境。”[5]4如前文所举例的《人间世》中的“接舆歌”。相对比可见,《庄子》的“接與歌”比《论语》增加了更多的字句,在语言的运用上较《论语》更为流衍和优美,也蕴含了更多的感喟情绪。刘凤苞评曰:“以下变调,乃庄子接续楚狂之歌而长言永叹之,化板为活,有崩云裂石之音。”[5]112此是庄子言辞运用相对纯熟的表现。再如喻世道之危曰:“游于羿之彀中。”林希逸评:“游彀中数语极奇绝。”[6]88其比喻往往精切而奇异,又信手拈来地说出,没有费力措意雕琢的意状。如讲“三籁”时形容风吹山木:“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陆西星称:“数句描写窍穴,意态如画。”[7]15其语言传神尽态而不流于琐屑,浩荡而往,气势磅礴,流丽而不见刻意用力处。
《庄子》在述说思想时,常反复消解,层层递升,甚至自行否定或怀疑自己之前的言论。这种消解、否定和怀疑又往往是以轻松甚至带有玩笑意味的态度说出的,显现出游戏笔墨的效果。郭象称其“不经”“狂言”[1]3,一方面是奇绝光怪的想象与宏大旷远的气势,另一方面亦与其游戏的态度不无关联。游戏笔墨的言说态度在立论中体现为不断质疑和消解的言说方式。如《齐物论》在对是非、名言等进行一系列析说及破除之后,破是非、名言的立论本来已经充分,而庄子却又反观自身,对自己的言作出质疑:“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1]84-85其思维是清醒而冷静的,言说态度则是轻松的、游戏般的。在反复消解、不断怀疑的思想下,庄子将自己之言定义为妄言,与思想相应形成的言说态度是戏言的,轻描淡写而非严肃训教;庄子看待立论的眼光则是清醒冷静的,甚至可以无情地对自己也加以否定,而这否定又是轻轻提出,并不表现出他的冷静尖锐。林希逸在《庄子鬳斋口义·发题》所云“又其笔端鼓舞变化,皆不可以寻常文字蹊径求之”[6]1是《庄子》难读处之一,就与游戏笔墨的鼓舞流衍、变幻不居有关。庄子以自己的理论为妄言姑言,游戏笔墨的淡然态度消解了言的权威性和论断性,暗示诸子论辩之言,即使是他自己的言,也并非断言,从而在言说态度上以戏言破除了断言。
《天下》篇形容庄周之言云:“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林希逸解释为:“谬悠,虚远也;荒唐,旷大而无极也;无端崖,无首无尾也。”[6]505《庄子》游戏笔墨的态度体现为荒唐、谬悠,而其文势大而远,则呈现出游于无穷的意态。《庄子》常写极大的事物,可谓“好为大言”。例如对鲲鹏作极尽其大的描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又常常将极大与极小相互转化,如“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这些“大言”,想象毫无限制,其思入于无穷。郭象评价说:“其言宏绰,其旨玄妙。”[1]3言的宏大甚至夸张并非出于现实认知,而是一方面出于表达玄妙之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游于无穷的言说态度形成的立论风格。言说态度有时会逸出题旨,产生意图之外的意味。庄子作“大言”并非完全针对于立论的目的,其目的性和指向性不强,就如《逍遥游》中对藐姑射山神人的形容之辞“大而无当,往而不返”,令人感到“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游于无穷的大言使得立论的言说溢出庄子要表达的论点,甚至模糊立论说理的意图本身,而蕴含更多的解读方向,使其意旨更显得玄妙难解,包蕴无穷。《庄子》中的许多寓言都有巨大的解读空间和多样的阐释角度,并且本身具有审美意义,而这些对说理并无直接的用处。申说理念固然是其意图,但庄子并不把自己的言说完全指向这意图,而在其中带有颇多兴趣的意味。游于无穷的言说态度在文学方面对后世有广远的影响。例如文言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的创作,美学与观念上追求“审美惊奇”和“非常书写”,价值上寻求“游心寓目”的快感,就深受庄子这些谬悠荒唐之言的影响[8]。其背后自然也受到“游”的言说态度的影响。《庄子》“大言淡淡”的态度,映射在立论的言说上,对“谓言”“辩言”执著于彼此、是非的指向性、措意性加以消解。同时“游”既是立论态度,也是庄子所标举的体道的境界,“游”的言说态度也是在展示思想层面对道的体悟。
(二)隐约的命题态度
《庄子》有“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之语,在言说命意时其态度是隐约而非直言的。正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说:“然庄生弘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1]5《庄子》中存在着众多的模糊与争议之处,较为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命意的隐约,以问句代判断;论题的隐约,以形象代陈述;寓意的隐约,以寓言代说理。
命意的隐约,《庄子》常以问句代判断,如《齐物论》南郭子綦回答天籁之问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不仅没有描述所谓天籁的具体状态,且以问句言说。“怒者其谁邪”既有可能是有“怒者”而未知的疑问,也有可能是并无“怒者”的反问,或自知“怒者”是谁而隐含不明言的设问。问句本身的非确定性,相比判断句的结论固化,与庄子无待的思想观念更有一致性。在这多意的问句中,天籁的含义变得隐约不清,从而给庄子所怀疑的有限的言带来命意的开放与自由。“庄子哲学是开放性的批判哲学。其突出的开放性首先表现为视野博大和胸怀宽广”[9]319。判断的言说是明晰、固化的,有特定的命意之所谓,所以执一端而有是非对待。而庄子的问句,命意是不确定的,所“谓”有多种可能,从而消解“谓言”之执与“辩言”之争。言说的“谓”被敞开了,使得有限的言说获得意义的自由。问句客观上将结论的权力让给读者,带有模糊性、可变性,且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促使其意旨变得隐约、多义,成为对言加以淡化的言说态度的一个方面。常用问句的言说很多时候也与前文论及的“游”的立论态度有关,带有兴趣和情绪意味的态度,会倾向于用更有情感倾向也更轻松的问句,而非严肃的判断,来对一些观点加以言说。这一倾向同样对言说起了隐约化的作用。
论题的隐约,以形象代陈述。例如《齐物论》中有:“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1]71-72并不直接陈说,而用“指”“马”这种形象的事物来言说。由此产生了阐释的多种方向。如有认为“指”“马”是名家的“指物论”“白马非马”等名学的名词,以消解名言与其所指称对象的对应性表达了对名言的否定。如杨国荣认为“指”即概念,“非指”则是概念所指称的对象。“通过运用概念来表示概念所指称的事物与概念本身并不一致,不如直接消除概念本身或不使用概念来表明以上关系”[10]。有把“指”释为手指,“马”为算筹。《礼记·投壶》载:“胜饮不胜者,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孔颖达疏:“为胜者立马者,谓取算以为马,表其胜之数也。谓算为马者,马是威武之用,投壶及射,亦是习武,故云马也。”[11]317而将“非指”之非理解为非我之指,以彼此是非解释。如郭象说:“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则彼指于我指独为非指矣。”[1]74正因为庄子没有直接陈述在这一段要说的论题,而是选择了“指”“马”这样的形象来言说,形象具有的丰富性导向了阐释的多义性,呈现出不确指、不固定的表达效果。陈述言说是分析的,庄子认为“道昭而不道”,分析的明晰会偏于某一端,不见其余,损害道的完整,也不能够真正把握和传达道。而形象某种程度上消解言说的分析倾向,以隐约的表达包容无限的意蕴,其言说效果是体会式的。形象比陈述具有更大的包蕴性,能容纳更多的含义,如果说前文所说的开放性是言说之“放”,形象所带来的包蕴性则产生言说之“收”的效果。
寓意的隐约,以寓言代说理。如《养生主》的“薪尽火传”故事,有生死说(郭象、成玄英、林希逸等)、形神说(陆西星等)、道说(钱穆等)、个体生命与宇宙大化说(李存山等)[12]111等。再如《齐物论》“尧欲伐三国”故事中所用的“十日”比喻:“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有认为是肯定十日,十日喻德之无为而无不在,照之以天,则德被天下,如司马彪、林希逸、陆西星等。有认为否定十日,十日指有为之害,有意有为地去向他人推行自己的德反而是有害的,如郭象、成玄英、郭嵩焘等。在诸子文学中,寓言并非《庄子》所独有,但庄子对寓言的态度却与其他诸子不同。其他诸子也有常用寓言故事的,但多是将寓言作为说理的辅助。寓言并不是他们的主体或核心内容,而是表达道理、提升文风、益于理解的道具。在寓言的前后一般还是要说理的。简言之,是以寓言助说理。《庄子》则不然。在《庄子》中,寓言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篇幅,且很多时候寓言是不依附说理而独立存在的,很多篇章甚至是一个个寓言的连缀。在寓言的前后,多不再另外说理。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庄子》说的不是用寓言作工具辅助的理,说的就是寓言,可称为以寓言代说理。而寓言这种言说形式,正是由隐约的言说态度所选择的。有所言就会有落实的意旨,一旦言说落实就不再具有无限的命意方向和内涵,也就无法接近于道。寓言的虚构性以虚言消解有言之实,以寓言代说理使得言说态度倾向虚灵,既近于道的存在与体会状态,也是出于庄子尚虚的审美倾向。庄子对语言的运用既游刃有余,隐约就不是客观的力有不及,而应该是主观态度的点到为止,体现了言说态度隐约的偏好。庄子出于“言未始有常”的言说观念,以及消解、否定的思维方式等原因,倾向于制造言说的模糊,将言说导向“无常”,包含无限的变化与可能,偏尚虚灵缥缈的言说状态与言说意趣。庄子令他的言说“曼衍”而“广”,实现“对‘言’不尽‘意’的一种反向利用”[9]313。庄子认为“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相示的言说因彰显而偏颇。庄子以“怀”的隐约态度进行言说,摆脱“谓言”“辩言”对言说的制约固化,以期用隐约之大言更好地传达出大道。
(三)疏淡的审视态度
庄子常常将所观对象向外推却疏离,以站在事物之外的视角看待世间的各种问题,以“冷眼”观世,其审视世事的态度是疏淡的。疏淡的审视态度可分为三个层面:外物、外我、外言。
一是外物。《大宗师》有女偊对南伯子葵讲“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的过程,先是达到“外天下”而后“外物”而后“外生”等等。物在《庄子》中是一个包含比较宽泛的概念,动植物、人都属于物。《人间世》中栎社树对匠石说:“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将人与树都视为物,本身就是脱离人自身的疏淡的审视角度。外物的态度采取超脱事物之外的视角对事物进行审视,站到旁观、远观立场上加以言说。庄子往往取是非两端之外的角度,例如论是非时庄子举出民与湿寝、民与猿猴木处对正处的不同观点,民、麋鹿、蝍蛆、鸱鸦对正味的不同观点,人与鱼鸟对正色的不同观点,得出结论“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这一论证过程是站在人类与动物物种之外的视角,论说不同个体各有其是非。外物的态度下,庄子往往不为世间成见所囿,而疏离于表相,以怀疑的眼光从旁观的角度加以审视。例如栎社树所说:“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表达了对“文木”所代指的追求有用的成见评价标准的反驳。在外物的视角下,是非差异只是同样的执于一端,评价对错好坏的标准也并非固定不变,“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庄子对事物采取疏离的视角,在差异与变化的基础上归于同一,对世物则倾向于脱离人世的束缚和伤害,自由无待。《庄子》有多处“游乎四海之外”“游乎尘垢之外”的言说,所处之世的人命危浅和道术相裂,促使其对人世持疏淡外离的态度:对危难的生存境遇,希望到这境遇之外的“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从而脱离危害和困苦;对争执的道术境遇,认为可以“天钧”“两行”“道通为一”。泉涸时鱼之间的相濡以沫,一方面是艰难生存的危世使然,一方面是社会性价值所褒扬的道德,而向外一步再看,则“不如相忘于江湖”,危世生存不如保有安宁自在的生命,称扬所是不如忘是非、无是非。无论所看待的事物、习见常理等社会性价值还是所处时代的境遇,都被庄子视为欲“外”之“物”而以疏淡的态度加以审视。
二是外我。“无己”是《庄子》的重要观点,在言说态度上体现为外我。自身的主张和立场一般是言说固有的,庄子却往往舍弃甚至否定自身,用外我以至无我的态度进行言说。庄子对“我”有冷静的审视,认为“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与“彼”相对而生,由彼我之分产生不同是非的观念。姚鼐解释“吾丧我”说:“一除我见,则物无不齐。”[3]9“我见”是言说产生偏见的重要原因。庄子在言说态度上也持“吾丧我”的态度,往往跳出自身的观点,从外我的角度审视问题。如谈梦时,从“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开始,显示梦觉之间的直观差异,“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是从梦中而言,梦中的状态是自我观点固守而不自觉的;再到“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大梦也”提出大觉,则由固我中脱离一步,有所审视,“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是说有假觉,则对这审视又生质疑与审视。论说层层向外衍伸,由梦至觉,已是站在梦外来审视梦,而又对所谓觉产生怀疑,又有假觉,是再到觉外审视觉,又将“我”更加疏离。在论梦与觉之后,指出“丘也与女,皆梦也”。这是站在丘、女两个人之外的立场上讲的,丘与女都是身处大梦之中而未觉。更向外一步,又说“予谓女梦,亦梦也”,“我”说你是在梦中,从知而言,“我”也是自以为知,实则也是愚者;从言而论,“我”既有“谓”,言的判断一出口就是进入是非之中执其一端,便是也在梦中。此时的角度是站在自身与他人之外,甚至对自己之前的判断也加以否定和超脱,是以更疏离的立场加以审视。梦、觉、大觉、假觉、丘与女、予谓女梦是对“我”的认知外之又外、疏之又疏的言说过程。在言说观点时,渐次地从“我”的视角疏远出来,不断以“外我”来谨慎地审视事物,从更广大的视域看待世事。而对“我”本身的形体存在,庄子也持“外我”的态度,对形体的残缺认为“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对自身的利害生死也不以为意,“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外我的言说态度,对观点的自我立场和形体的自我存在,都持疏远外置的态度。
三是外言。言是“未始有常”的,庄子既对有局限的言有所怀疑和审慎,在言的运用上则很大程度地发挥了言的变化不居,甚至常有自己否定前文所言的表达方式。如《齐物论》有:“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1]96-97对提问皆以不知回答,从言说层面看是对言的疏离,弃置言背后的知的重要性,淡化言的判断作用。“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可将“物之所同是”作为一部分,解作是否知道物都同样是自是非彼的,也可作“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是否知道物的同一,可以说都是对是否知道物之道通为一的问题。前文已论述物各自有其是非故通为一,却又以不知答之,而下一问答更是对“不知”的不知,再是对物是否无知的不知。以“外言”的态度进行言说,对言怀疑的审视使言不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消解其固定性。言本身成为可以反复否定和超越的存在,在层层否定中梯级递升。庄子不把言视作具有德、功价值的“立言”、有判断意义的“谓言”“辩言”,认为言有局限,不能完全表达出道的含义,对言的观念是“不言”,而在言的运用中态度是“外言”。理念上认为“不言”,但在言的运用时并不能真的没有言说,且庄子可能不是认为一定不能有言,而是不执著于言,持疏淡的态度,在言之外进行言说,有言而忘言。
三、言说态度与表现形态
《庄子》对言的思想观念与言说态度分属于其“言”的不同层面,淡淡大言的言说态度在《庄子》的言说中具有重要地位,包含“游”的立论态度、隐约的命题态度、疏淡的审视态度三方面。与言说态度不同,《庄子》的表现形态是汪洋恣肆的,淡淡大言的言说态度与汪洋恣肆的表现形态是什么关系,对言的思想理念与二者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加以探究。
前辈学者诸多研究成果中有许多是以《庄子》的某某态度为题的,如政治态度、人生态度、审美态度等,这些态度与本文所希望探究的“言说态度”不属于同一个层面,应归于思想观念范畴①对与本文所要探究的《庄子》言说态度类似的概念和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张梅《〈庄子〉的语言艺术——卮言——从庄子的立言态度与立言方式谈起》(《先秦两汉文学论集》2004年6月)一文认为,《庄子》具有不强立是非、姑且言之的立言态度与不从正面立论、以文为戏的立言方式,立言方式即卮言,并提到此立言方式体现了这一立言态度。但这篇论文的主体是卮言,而不是立言态度及其与立言方式的关系,也就自然没有对此的更多论析,且所说的立言态度与本文要探讨的言说态度定义、范畴、思路等都不同。李明珠《庄子简省的创作态度、美韵及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4期)是以“简省”为主题的,所以也基本没有关于创作态度的界定或与其他概念界分的论述,且其中创作态度与创作艺术并没有区分论述。。从思想观念层面看待言,是对言的态度,而非言说过程中自身采用的言说态度。涂光社《〈庄子〉心解》有一节论述《庄子》论“言”和用“言”,论“言”主要是“言”“意”之辨的讨论,用“言”则是寓言、重言、卮言的运用[9]315。对言的“论”与“用”分别开来进行论述的思路,对于本文划分言的思想观念和言说态度有借鉴意义。对言的思想观念是关于言的理论观点,言说态度则存在于言的运用过程。《庄子》对言的思想观念催生并影响其言说态度,这一方面在前文已有论述,另一方面言说态度又并非完全是思想观念的复制,对言的观念实施在言说上会出现变化、偏移与混杂。在思想观念层面,《庄子》中认为“大道不称”“大辩不言”,这与《老子》所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的观点是有一致性的。在言的实际运用上,《老子》认为“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其对言的思想观念与言说运用中的态度显现为基本统一的面貌。《庄子》的言说态度,在推许无意、自然的方面与之相类,这也是“不言”的思想观念在言说态度中的体现。而由于对言的观念差异、个性所喜等,在其言说态度中有诸多趣味、审美、情感的倾向。这与《老子》的“无味”不同,也较《庄子》思想观念层面“不言”的主张有所变化。简言之,如果笼统地将对言的思想观念划归为理性的层面,言说态度则在理性上加入了感性成分,成为理性与感性的混合,呈现出对思想观念既承续又偏移的状态。
庄子在其思想观念与自身意趣的多重因素下形成独特的言说态度,而其表现形态是汪洋恣肆的。汪洋恣肆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自由的言说形式,纵恣曼衍,是动态的展开。淡淡大言的言说态度则具有超越性质,更多地是静的意味。二者看似不是一致的,但事实上《庄子》之言正是从淡淡大言的言说态度转化到了汪洋恣肆的表现形态。
在淡淡大言的言说态度中,可以归纳出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从淡淡大言到汪洋恣肆具有可能性,分别是自如、自娱、自忘,三者也分别对应着言说的三个限制层面。其一,自如。前文已经说过,庄子对言的运用是游刃有余的,对言说可自如运使,达到任其自然的境界。言说突破词不达意的困难,而创造言不尽意的效果。言说态度的自如使言没有技巧上的限制,达到能言。其二,自娱。对言说艺术的兴趣和审美意韵包含在言说态度之中,成为言说展开的重要动力。言的第二个限制是发出言说的动力,希望言说、愿意言说甚至以言说为乐,才能真正使言展开。言说态度的自娱倾向提供了言说的动力和乐趣,达到想言。其三,自忘。言深层的一个限制是言说者自己,言说的自我立场使说出的言只围绕“我”之所见,符合“我”之利益,追随“我”之情绪。自我是言说的发出者,言要跟随自我,而自我在世间又是有无数牵扯,有诸多所待,从而令言也成为有待的。庄子的言说态度则不固执于自我立场。在庄子的言说态度中,立场是可变化的,“我”之言是可否定的,自我是可消解的,其自忘的态度使言说达于忘言。通过言说态度的自如、自娱、自忘,言突破技巧、动力、自我的多重限制,能言、想言而忘言,实现言说的巨大自由。表现形态的产生是复杂而有许多偶然性的,并不能断言淡淡大言的言说态度必然产生这样的表现形态,但它具有的这些因素能够使言实现汪洋恣肆的表现形态成为可能。
对言的思想观念经过理性与感性的糅合形成言说态度,言说态度呈现出表现形态。如果从思想观念直接到表现形态,这之中是存在矛盾的。主张“不言之辩”“不道之道”的观念如何呈现为汪洋恣肆的形态,这之间很可能有一个过渡。且思想观念在付诸表现的时候,出于人之心、发诸人之口或笔,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主观与感性因素的影响,甚至言说本身就会使思想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变动。思想观念经过复杂因素作用的过程形成言说态度,言说态度促使表现形态呈现出来,言说态度可以说是从思想观念到表现形态的摆渡之舟。
“大言炎炎”实则为“大言淡淡”,其作为《庄子》的言说态度,具有“游”的立论态度、隐约的命题态度、疏淡的审视态度三个方面。《庄子》之言,存在“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的思想观念、“大言炎炎”的言说态度、汪洋恣肆的表现形态三个层面。“大言炎炎”的言说态度在思想观念与表现形态之间发挥了过渡作用。从言的思想观念到言说态度,理念在实际书写过程中经过了感性与审美的参与,表现出既承续又偏移的样貌。言说态度以其自如、自娱、自忘的特点使得形成汪洋恣肆的表现形态成为可能。《庄子》之言的三个层面之间,既具有一定的差异,又形成相连续的言的论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