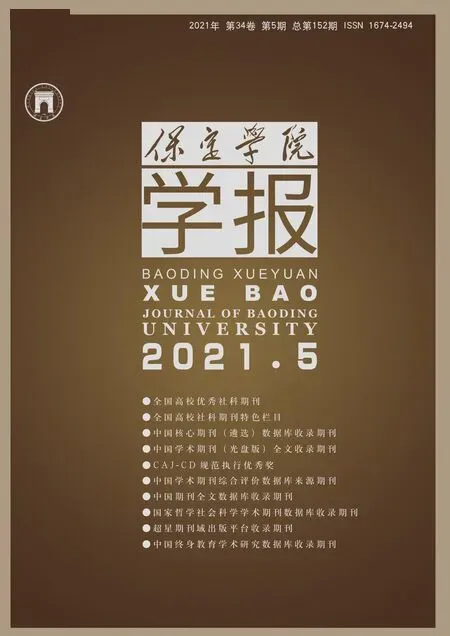论崇宁年间宋徽宗与蔡京的矛盾和妥协
李兆宇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宋徽宗与蔡京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多有讨论,相关认识不断深化。早期研究成果如:林天蔚《蔡京与讲议司》[1]、任崇岳《论“元祐党人案”》[2]以批判宋徽宗君臣之腐败亡国为主,突出他们是一对狼狈为奸的君臣。随后研究成果注意到他们的分歧与斗争,并以蔡京四次罢相为关注点论述宋徽宗既需要蔡京的理财手段,又时刻防范其权力膨胀。刘美新《蔡京与宋徽宗朝之政局》[3]、曾莉《蔡京宦海沉浮研究》[4]、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5]、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6]均对这一认识作了析论。方诚峰论述了“公相体制”这一在政和、宣和年间逐渐形成的制度安排,指出它既限制了蔡京的权势,又最大限度利用了蔡京的才干,但方先生对崇宁、大观年间宋徽宗与蔡京关系互动则未展开论述。讨论崇宁年间二者关系的专文有藤本猛《崇宁五年正月政变——对辽交涉问题上宋徽宗与蔡京的对立》[7],将蔡京首次罢相定义为“自上而下的政变”,罢相原因是宋徽宗与蔡京在对辽战略上的分歧,但藤本猛先生并未总结归纳导致此次罢相的其他原因。李洁《北宋徽宗时期苏州钱狱研究》[8]指出发行当十钱导致的经济混乱是蔡京罢相的原因之一,杨小敏《政事与人事:略论蔡京与讲议司》[9]则注意到蔡京借变法契机培植私党的过程,裴真《翰林学士与宋徽宗朝政治》[10]注意到蔡京与侍从官的勾结。上述成果为进一步探究崇宁年间宋徽宗与蔡京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参考,也在解释蔡京为何得以迅速复相这一问题上留下了进一步解读的空间。
一、崇宁初期:宋徽宗与蔡京的合作
漆侠先生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中对宋徽宗改元崇宁和召见蔡京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概括,指出是元祐党人的极端言行、蔡京与宋徽宗在艺术上的共同兴趣、蔡京与内廷的结交、曾布与韩忠彦党争等因素促成了宋徽宗放弃调和新旧两党的政策并召见蔡京[11]。这仅是蔡京得以入朝的原因,而他能被宋徽宗信托并借总揽绍述之政、推行改革而成势,是因其政策可解决旧党未能解决的军政与财政困局,尽管其方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一)宋徽宗另谋辅臣的原因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罢知枢密院事的安焘在奏言中陈述哲、徽之交朝廷内外的困局:“自绍圣、元符以来,倾府库,竭仓廪,以供开边之费。大臣用以为迁延固宠之计,故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罄竭,未有甚于今日。”[12]654是言大体属实,自元符二年(1099)洮西安抚使王赡乘河湟诸部内乱,提孤军攻入青唐,随后被吐蕃部族与西夏两线夹击。宋徽宗甫立,朝中反对这一鲁莽军事冒险行动的臣僚以其带来的财政压力为由劝说宋徽宗放弃鄯湟二州。韩宗武直言国库亏空的原因是“开境土以速边患,耗财赋以弊民力”[13]10312。宋徽宗的潜邸旧臣徐亦言青唐“自收复以来,岁费亿万计,皆仰给内郡,是徒有得地之名,无获地之实”[12]650,进一步主张“请自今勿妄兴边事,无边事则朝廷之福,有边事则臣下之利”[13]11026。
相比无条件弃地,执政大臣曾布提出弃鄯保湟的对策,即撤出鄯州,使之作为缓冲地带,巩固对湟州的控制,实则是消极防御。建中靖国元年八月,陈瓘上《国用须知》抨击曾布的政策“缘边费而坏先政”[12]655,一年内六次征调诸路钱物以供边费。第六次仅从广西路便征钱一百万缗。甚至崇宁元年(1102),讨索国债的商人拿出章惇开边和曾布弃地之时购买的债券:“合三百七十万缗不能偿者。至会罢边弃地之费,乃过于开边也。”[12]668曾布之策耗资更多且寸土不得,又“侵削十路百姓,只得绢一百万匹,未足以充陕西三两月之费”[12]655,造成了更大的经济与边防压力。
此时在朝中占多数的元祐党人不断上书指陈时弊,却无系统的解决方案。而汲汲然以争论正邪是非、忠奸善恶为己任,对外奉行军事保守主义乃至投降主义,其实质是对宋徽宗再行绍述之政的担忧,以及对新党的倾轧。任伯雨是其中的代表,他“居言职仅半载,所上一百八疏,皆系天下治乱、关宗社宫禁者,细故不论也”[14]924,殊不知他们所不屑讨论的“细故”,恰恰是亟待解决的国计民生之要害。曾布与韩忠彦的党争固然会引发宋徽宗的反感,但是他们对军国要务的束手无策,使宋徽宗最终失去耐心并决意召用曾任翰林学士的蔡京。
(二)崇宁之初:宋徽宗与蔡京的合作
崇宁元年三月,宋徽宗命内侍童贯至杭州办差,赋闲在此的蔡京得以与童贯结交并入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四月,蔡京入对,据此后的政治走向可推知,蔡京显然向宋徽宗建议尽逐元祐之臣而绍述神、哲之政。闰六月甲子,宋徽宗令诸路帅臣监司“荐举善最有闻、治状异等、能惠养烝庶、劝课农桑者”[15]637。闰六月三十日,又诏诸路帅臣监司“选智谋宏远,纪律严明、可备将帅者,或守边肃静、敌不敢侵、可以委任镇防者,鸷猛果毅、虣勇罕伦、可以率励士众破坚拔敌者”[16]5803。表达了对可以救时应务的能臣干吏之需求。七月,蔡京拜右仆射,宋徽宗对其寄予厚望:“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历观在廷,无与为治者。今朕相卿,其将何以教之?”[12]663委蔡京以提举讲议司并拟定改革的具体方案。相比旧党不屑讨论“细故”,蔡京关注的问题更切中实务。八月,蔡京上言:“臣伏读手诏,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及尹牧事,皆政之大者,臣欲每事委官三员讨论,并乞差充检讨文字,有见任者,令兼领,不可兼及在外者,并权罢见任,赴司供职。”[17]703要求有关官员专一事权,以保证效率与执行力度。
但不应无视蔡京在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时,也尽显他迎合皇帝、加重剥削的一面,其对钱币、茶、盐等经济领域的改革,均无异于“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18]461,为宋徽宗的福利设施、兴学运动和军事拓边等政策提供财政支持,并满足宋徽宗的土木工程营造与享乐之欲。崇宁二年(1103)蔡京进呈调整盐钞法后收入的三万缗钱,宋徽宗惊讶道:“直有尔许耶!”[19]2212可见蔡京对钱物的聚敛能力超出宋徽宗预期。
此外,蔡京协助宋徽宗对以“元祐奸党”为名的不同政见者展开政治迫害,并推进对河湟吐蕃的拓边活动。至崇宁三年(1104)九月,蔡京炮制出了309人的元祐党籍及元符末上书系籍人名单,后由宋徽宗御书、蔡京抄录的“元祐党籍碑”刻石颁布全国,对元祐党人的政治权益、文字著作、亲属师友以及学术政见进行全方位打击,标志着这一政治迫害达到高潮。在西北,宋军在王厚与童贯的率领下收复湟、鄯、廓三州,陕西、河东沿边帅臣也对西夏展开了积极的攻势,进而巩固了对西夏的战略包围。蔡京运用简单粗暴、颇具争议但却又立竿见影的手段,暂时压制了旧党未能解决的财用、党争、边事矛盾并获得圣眷。参与讲议司事务的臣僚在此后多获推赏并出任要职,成为蔡京执政的人事基础。在逢迎宋徽宗的过程中,蔡京稳固了自身权位,也埋下了日后与宋徽宗矛盾激化的种子。
二、崇宁年间宋徽宗与蔡京矛盾的积累
随着拓边活动的大体稳定与朝中政治势力逐渐倾向一元化,蔡京权势也逐步扩张,一再刺激着宋徽宗对权臣专政的警惕。二者之间矛盾不断积累并集中爆发于崇宁四年(1105),直接导致次年蔡京的罢相。
(一)人事分歧:蔡京对私党的包庇
1.广布私恩
蔡京在杭州与童贯结识时,曾表示国家府库皆是天子私物,理应供内侍近从取用。童贯返京“大播此语,于是宫人近习,人人恨不得蔡内翰即日为相矣”[20]。此事清晰反映了蔡京对内廷宦官的拉拢结交之态。且宦官群体实际之得利远不止此。“崇宁二年二月,辛酉,立殿中六尚局,北司之盛自此始”[21]438。二年五月,又废内侍寄资法,按旧制从内侍到东头供奉官“止一转则大使臣;若在内庭,只许暗理资级,恩数俸料并未该受,谓之寄资,转出方正授以所寄之官”[12]672。废除寄资法后,内侍们只需在官名上加带入内内侍省若内侍省字,就可以直转正官而不用寄理,相关待遇亦不减。这一系列规定的调整对内侍拉拢备至。蔡京对同僚表示“三省,枢密院胥史文资中为中大夫者,宴则坐朵殿,出则偃大藩,而至尊左右,有勋劳者甚众,乃以祖宗以来正法绳之,吾曹心得安乎!”[22]为了报答对他有汲引之助的童贯,蔡京力荐其担任王厚的监军,并不惜压下蔡卞的反对,支持童贯帅边熙河兰湟秦凤路。
对同僚,蔡京“于寄禄官俸钱、职事官职钱外,复增供给、食料等钱”[18]1966。对内外卫士,蔡京“增侍立食钱,因禁中有盗,环皇城置巡铺卒,日给钱一百五十”[12]684,相比旧例增加了近十倍。又趁小陇拶入降之时,请宋徽宗登楼受降,用南郊大典的成例支赏士卒,意在用私恩收买之。时任泾原经略使的邢恕趁陕西行俵籴法而加倍俵之,造成弓箭手大量逃亡。得知此事的宋徽宗“谕宰执曰:‘泾原弓箭手可惜,闻恕虐用其人,今逃者已千余户矣。’蔡京庇恕,乃谕使者奏恕俵籴奉法可赏。诏迁一秩”[12]679。有过不罚而反倒受赏,其包庇党羽、固结人心之举可见一斑。
2.伺察人主
崇宁年间的侍从官多是蔡京党羽,他们利用接近宋徽宗的便利,伺察宋徽宗的言行并向蔡京传递消息。典型者如许敦仁,他与蔡京有州里之旧而任监察御史,又迁为右正言、起居郎。许敦仁曾向宋徽宗建议车驾行幸之时不要只有当值的侍从官陪侍,而是众人一起扈从宋徽宗,显然有利于扩大蔡京党羽在侍从官群体中的影响力。拜御史中丞后,竟又上章请宋徽宗五日一视朝,因而获罪,宋徽宗“以其言失当,乖宵旰图治之意,命罚金,仍左迁兵部侍郎;他日,为朱谔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处之自如”[13]11203-11204。尽管许敦仁被罚金降官,宋徽宗仍余怒未消地要逐走他,只因蔡京庇护而未果。许敦仁亦因而“处之自如”,此举亦是对君主赏罚之权的侵蚀。
为了进一步为其党羽创造服侍内廷的机会,蔡京请求仿古制设置三卫郎官。意在选择公卿子弟,入卫侍从,体现所谓法先王宿卫之意。但宋徽宗对此评价道:“京又令其子修为作亲卫郎,欲日伺朕动作”[12]689,表达了对蔡京伺察朕躬的警觉。崇宁四年,时任门下侍郎的赵挺之对蔡京专权的情状进行揭露:“今内外皆大臣之党,若以忠告于陛下者,乃以为怀异议,沮法度。此大臣恐人议己之私,欲以杜天下之言尔。”[12]684
(二)和战分歧:蔡京对辽、夏的强硬外交
1.宋军西北拓边的暂止
崇宁四年三月,宋军收复银州。此战指挥官陶节夫曾供职讲议司,又是蔡京提拔的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故相关史料对其功劳多持否定。李华瑞先生在其《宋夏关系史》中已作析论,兹不赘述[23]。概括而言,陶节夫的拓边行动对西夏屯粮、险要之地多有控御。他随后官拜枢密直学士,并被委以经制五路边事,宋徽宗也向边臣垂询灵武等地可否攻取,可见宋徽宗对继续拓边的支持和对陶节夫功劳的认可。
然而北宋对西夏的经略引起辽朝的警觉,崇宁四年正月,辽“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等讽宋罢伐夏兵”[24]。闰二月癸酉,宋徽宗“止诸路进兵讨伐夏人”[21]448。辽朝的干预迫使宋徽宗暂停西北拓边行动以免两线作战。蔡京对辽态度却颇为强硬,他以辽朝外交文书用语悖慢为由起草了辞令严峻的回复,宋徽宗不满道:“夷狄当示包容。今西边方用兵,北虏不宜开隙。”[12]685
蔡京这一看似突兀的行为源于对政局反转的担忧。经过数十年的政治倾轧,休兵息民、怀柔避衅等主张,往往与元祐政见等同,这正是蔡京所警觉的。元祐党人虽然罢废,但社会影响却绝不可能在短期内根除。所谓元祐党人虽可以具列出309人的名单,但对元祐政见潜在的同情者们却大有人在。蔡京的政策始终伴随着多方争议与批评,宋徽宗此时的政策倾向一旦改变,那些不久前才被用暴力手段压抑的反对力量便找到了宣泄口,辅以宋徽宗对蔡京权势的忌惮,以及对其党羽无由建功的不满,届时蔡京地位必然动摇。崇宁四年五月十一日,宋徽宗在辽使辞归之际敲打蔡京等人道:“夷狄遣使,及西陲未靖,异端之人汹汹,幸此以摇政事。”[16]9756蔡京反倒指示其党羽对辽、夏采取了更具挑衅性的措施,试图挑动边境紧张局势,保固权位。
2.林摅使辽与营建四辅
崇宁四年五月,曾在讲议司供职的龙图阁直学士林摅担任辽国回谢使,本职是答复宋廷有意缓和边境局势。蔡京指示林摅激怒辽廷,后者“至虏廷,故为悖慢不逊。虏甚骇,绝其饮食,几欲杀之”[21]450,而蔡京随后的举动则表明林摅此举未必是虚张声势。崇宁四年七月,蔡京建言设置四辅郡以拱卫京师,理由是“汴都地平无险阻,以兵为险。请依汉三辅置京畿四郡,以侍从官为之”[12]687。建制辅郡和在畿辅地区扩军以拱卫京师,本也是宋徽宗的意思。崇宁初期,参与裁定六尚官制的左司谏姚祐就曾“建议置辅郡以拱大畿”[13]11162,宋徽宗亦未反对。于是此时,宋徽宗批准了南以颍昌为南辅,以襄邑县改名辅州为东辅,以郑州为西辅,以澶州为北辅的四辅筹建计划。起初的四辅建制据蔡絛《国史补》所言为“仿汉三辅,尽萃兵于辅郡,仍各增屯至五万人。以近臣领之”[17]846。后来臣僚弹劾蔡京的奏疏中亦称其“建四辅郡,屯兵数十万,遣门人为四总管”[12]694。可见四辅原计划总计屯兵约二十万。在明知林摅此番出使会造成何种后果的情况下,蔡京以京师无险可守为由,在汴京周边修筑城防并驻屯重兵,很难不被理解成是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宋辽战争。
蔡京对西夏则酝酿着规模更大的拓边计划。崇宁四年六月,蔡京奏请陶节夫经制五路,后者下令诸路进筑城寨并上奏:“既城银州,又得石堡,而夏、洪、宥皆在吾顾盼中矣。横山之地,十有七八,兴、灵巢穴,篱落浅露,皆可以计取。”[12]686宋徽宗明确驳回道:“北戎遣使和解西边用兵,朝廷既许其扣关请命矣,安用经制五路为!”[12]686罢去了陶节夫经制五路的职掌。
八月,得知林摅出使言行的宋徽宗大怒,贬责林摅并另遣礼部侍郎刘正夫使辽,同时以御笔“付三省、枢密院,更制陕西、河东军政六事。三省、枢密院同奉御笔自此始”[21]451。试图通过御笔强化对中央决策层和前线军事的控制力。九月,宋徽宗以铸成九鼎为由大赦天下,并对元祐系籍人开放党禁,此举引起蔡京党羽的抵触,使他们在具体执行时对相关人员只进行了量移。十二月,宋徽宗再次以御笔形式下令:“四辅屏翰京师,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两万人为额。”[17]861对四辅兵力进行了明显的削减。针对有司阳奉阴违,对九月赦宥诏书所提及的元祐党人只做量移处理的行为,宋徽宗又以御笔手诏指示道:“其诬谤深重,除范柔中、邓考甫不放外,余并依已降指挥,放还乡里,令亲属保任如法”[17]861。
陶节夫拓边西北和强化京畿防务,宋徽宗均在原则上支持,但不愿蔡京将其权势继续渗入军务。更对其在处理辽、夏邦交问题中违逆上意甚至挑动边事等行为既怒且惮。蔡絛《国史补》亦供认:“四辅始置,兵亦未及五万,制度犹未就。时三卫诸郎既多勋戚子弟,或不能副上意者。时谤言至谓鲁公反设此以囚人主。”[17]846随着崇宁五年(1106)正月的星变,一场由宋徽宗发动、针对蔡京的罢相行动开始了。
三、崇宁星变:蔡京的罢相与宋徽宗的妥协
崇宁五年正月,彗星经天,宋徽宗下诏:“以星文变见,避正殿,损常膳,中外臣僚等并许直言朝政缺失。”[14]934并从中书侍郎刘逵之请,毁元祐党人碑并放宽党禁。此举催化了蔡京等人对政局再次反转的忧惧,以至蔡京见到被毁的党人碑后厉声说道:“石可毁,名不可灭!”[12]688但细究毁碑后约一年的政局可知,宋徽宗最终妥协并复相蔡京,这一罢相行动以权力调节的方式暂止。
(一)罢蔡京而存绍述
正月乙巳,宋徽宗下诏:
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今既谪累年,已足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刻石,已令除毁,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纠。[17]868
毁碑、诏求直言、收用元祐党人等措施,释放了蔡京将罢相的信号。大观元年(1107)三省统计“崇宁五年上书观望者五百余人”[21]465,这其中既有遭受政治迫害意图翻身者,也有出于公心痛陈时弊者,亦不乏观望投机者,但共同之处多是对蔡京及其政策的否定,这与宋徽宗的初衷存在些许误差。
宋徽宗之初衷是蔡京必罢但绍述必存。在崇宁五年正月丁未的大赦诏中,他首次明确表态:“深虑鄙贱愚人妄意臆度,窥伺间隙,驰骛抵巇,觊欲更张熙丰善政,苟害绍述,必寘刑典。”[19]2078正月丁巳,宋徽宗再次诏称自己对元祐党人“惟以示恩,顾岂复用。尚虑奸朋妄意,私议害国,士大夫狃于邪说,胥沦溺以败类,朕甚悼焉。布告天下,明谕朕意勿惑”[17]875。一再强调这次罢相行动的打击底线。二月丙午,蔡京罢相。赵挺之担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逵以同知枢密院事加中书侍郎,但二人在朝中却相当孤立。蔡京则仍居留汴京,其党羽张康国、郑居中、刘正夫等人尚在朝,因此“京虽罢相,退居赐第,然政令大纲,皆与闻之”[12]690-691。
崇宁五年三月,辽使牛温舒等人至宋,辽军也在边境集结示威。宋廷“人情汹汹。张康国、吴居厚、何执中、邓洵武皆谓势须与北虏交战”[12]689。仍试图渲染宋辽紧张对立的形势。宋徽宗表示:“朝廷不可与四夷生隙,隙一开,祸孥不解,兵民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之意哉!”[13]11094这次宋辽交涉以宋方答应归还崇宁以来占领的西夏境土而告结束。随着边境局势趋缓,宋徽宗的政治倾向益发明确。在三月亲试举人时,他将蔡嶷擢为第一,因其应试文中写道:
熙、丰之德业足以配天,不幸继之以元祐,绍圣之缵述足以永赖,不幸继之以靖国,陛下两下求言之诏,冀以闻至言,收实用也。[17]883
蔡嶷深体宋徽宗罢蔡京而存绍述的微旨,宋徽宗将这份应试文字传抄诸路。又以深得王安石渊源之学为由,诏蔡卞入朝兼任侍读,以星变已消为由罢求直言,将银州和威德军降格为银川城与石堡寨,却并未归还西夏。这些举动均表明宋徽宗此番只罢蔡京,并不根本否定崇宁以来的政策,他不满的只是蔡京对君主权威的侵夺,但对蔡京用以聚敛财富取悦君主、开拓边境建立功勋等政策并不排斥,宋徽宗想要通过这次罢相实现的目标,是在没有宰执专权的前提下继续推行蔡京的政策。这也构成了二人再度合作的潜在基础。
(二)宋徽宗妥协与蔡京复相
蔡京罢相的直接原因是他公然违逆宋徽宗的对辽、对夏战略,深层原因是其权势的扩张引起了宋徽宗的警惕。如今罢去蔡京,其党羽非但没有瓦解,也没有产生新的党首,反而进一步宣示着蔡京在朝中强大的影响力。另外,蔡京罢相后留下的财政问题越发突出,继而影响了御前财物的供应,而新任宰执又无法妥善解决相关问题。这些原因使得宋徽宗对罢去蔡京的决定产生了动摇。
1.蔡京党羽的影响
蔡京罢相后其党羽张康国仍知枢密院事、吴居厚任门下侍郎、邓洵武等人分列尚书省各部,侍御史余深、石公弼等人亦在言路。崇宁五年夏,宋徽宗本要将陶节夫调离鄜延路,“未数日,(张)康国再陈鄜延非节夫不可为,遂令节夫依旧在任”[12]686,同知枢密院事的刘逵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并不大,更毋论赵挺之、刘逵等人亦并不团结,“挺之多智,而逵甚专。事或不出于上,挺之虑有后患,每阴启其端,而使逵终行之。逵欲取以为功,亦不悟挺之之计,故直前不避”[12]691,这加重了他们在宰执群体中的孤立性,刘逵“甚专”也不会为宋徽宗所喜。崇宁五年三月宋辽交涉之际,赵挺之“语同列曰:‘主上志在爱民息兵,吾辈义当将顺。’时执政皆京党,但唯笑而已”[25],尽显对赵挺之的轻蔑与不屑。
蔡京党羽依然可以交通内廷,直接打探宋徽宗对时局的态度并传递密谋。翰林学士郑居中利用自己外戚身份,往来于内廷与郑贵妃之父郑绅家,将宋徽宗对时局的态度变化带出宫外。最终与礼部侍郎刘正夫合谋向宋徽宗进言:“今所建立,皆学校礼乐,以文致太平,居养安济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遣怒?挺之所更张不当。”[13]11103宋徽宗顺水推舟表达同意。蔡京之党羽仍在朝中不遗余力地影响朝局,是促成蔡京复相的一大原因。
2.当十钱问题折射出的经济困局与宋徽宗私欲
崇宁二年为支持西北拓边,宋廷发行当十钱以解决钱荒问题。但不久就产生大量盗铸现象。崇宁五年二月,监察御史沈畸指出若放任盗铸则“未期岁,而东南之小钱尽矣。钱轻而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愈困,此盗贼之所由起也”[17]879。东南地区是宋王朝的经济命脉,层出不穷的钱荒与盗铸行为愈演愈烈,甚至会激起民变继而危害国家安全。
宋徽宗虽也对发行当十钱有所不满,曾表示“终痛革之者,犹谓以利不以义”[17]886,但赵挺之等人对当十钱的调控措施,使得“营造已罢,它费一尊祖宗规范”[12]690,导致上供御前的钱物打了折扣。崇宁五年五月,宋徽宗在听完左正言詹丕远论述当十钱之害后表示:“京失!京失!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听此等人语言,不为国家长久计。人臣事君以利,只此便可见京相业。”[17]890但宋徽宗并未对詹丕远推心置腹,甚至故作惊讶道:“当十钱并行,本以便民,今却反为民害如此,非卿有陈,朕不知也。”[17]889事实上,早在崇宁四年六月,尚书省已向宋徽宗奏报过私铸当十钱的问题:“访闻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率以船筏于江海内鼓铸,当值官全不究心,纵奸容恶,理须别行措置。”[19]2293此时宋徽宗对詹丕远所奏佯装不知,显示了他在痛革弊法与保障御前财物来源之间、在一己私欲和百姓公利之间取舍之难。
宋徽宗随后对詹丕远暗示道:“京只为作事无法,于财用未尝以不足告,力引《周官》‘惟王不会’之说,此何意?”[14]935继而又表示:“今日且不要他,及只说国是断合如何?”[14]935言下之意已经很明显:徽宗只是不满蔡京行事专横,对他的理财能力却颇为赞赏,对于“国是”,则更希望在没有蔡京的条件下继续按照蔡京的方略施行。詹丕远继续以蔡京误国,不可不罢为言,宋徽宗“默然。寻诏丕远昏缪迂阔,差知兴化军”[12]690。赵挺之等人先后采用减少铸造、严颁铜禁、换行小钞和官方兑换收买当十钱等措施,可盗铸仍屡禁不止,进一步加重财政混乱并影响中央收入,最终影响宋徽宗享乐逸豫。而盗铸现象屡禁不止,是由于军费开支的压力使宋廷被迫允许西北沿边地区使用当十钱。进而诏“当十钱许京师与陕西、河东行用,陕西不与府界连接,虑未至通快,可令郑州、西京亦许行用”[19]2297。恢复了非边境地区对当十钱的行用。参与盗铸的还有很多士绅之家乃至地方官员。崇宁五年十二月壬戌,中大夫、龙图阁直学士、知苏州蹇序辰因纵容私铸而落职。两浙一带的盗铸情况也是由于:
州县容纵,不加严戢,间有告获,又置不问。部使者怀私观望,不时举发,以至私钱盈积,散流民间,延袤江淮,充斥畿甸。[19]2298
这一尴尬的局面使宋徽宗“颇悔更张之暴”[13]11103。蔡京的党援亦不失时机奏称那些应诏赴京注拟差遣的元祐系籍人“窃恐浸久,有害绍述,宜略为防限,以示好恶”[19]2094,崇宁五年七月、十一月,宋徽宗两次下诏对元祐系籍人中哪些人可以到京、在京停留的时间、所注差遣的限制作了进一步规定。随后郑居中和刘正夫先后鼓动宋徽宗复相蔡京,侍御史余深、石公弼等迅速弹劾刘逵:
怀奸徇私,愚视一相,乘间抵隙,取熙宁以来良法美意而尽废之。陛下息邪说以正人心,而逵擢上书邪等者;陛下勤继述以绍先烈,而逵用更改熙丰法令者。惟欲权出于己,引致朋邪,呼吸群小。[12]691
赵挺之、刘逵遂相继罢去,大观元年蔡京复相。蔡京以绍述神宗、哲宗变法为口号,将经由提举讲议司所培养的党羽安插在朝野。使绍述政策、宋徽宗的功业、蔡京的相业、及其党羽的利益,在理念路线和人事组织上都形成了利益捆绑。否定其中任一方都终将否定的矛头指向宋徽宗,因此蔡京的权位与影响极难根除,只可不断调整。罢去蔡京容易,可如何使朝局在不需要蔡京的情况下,仍能按照宋徽宗期望的秩序运转则难。赵挺之、刘逵、乃至后来的张商英这些宰臣,均无法像蔡京这般聚敛地方财物以供上用,其中张商英虽能迎合宋徽宗对祥瑞崇拜的喜好,却也对激进的财政支出和拓边活动不甚支持,故不能久任。宋徽宗的言行表明他对正邪、忠奸、义利及作为君主应该如何抉择等问题有清晰认识,他对蔡京一党之妥协,实质是对自己“惟王不会”“丰亨豫大”私欲之妥协。其妥协本身昭示了这是一场失败的罢相。
四、结语
崇宁年间宋徽宗与蔡京的合作、矛盾及崇宁末蔡京罢相与复相事件,深刻改变了北宋晚期历史的走向。它是宋徽宗统治初期的政治挫折,使他对皇权与君臣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执政特色也逐渐由调和各方政治力量变得更具独裁色彩。大观初,叶梦得为宋徽宗论:“《周官》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所谓废置赏罚者,王之事也……今徒以大臣进退为可否,无乃陛下有未了然于中者乎?”[13]13133宋徽宗不禁喜道:“迩来士多朋比媒进,卿言独无观望。”[13]13133暂时向蔡京妥协的宋徽宗在大观年间迅速开始收揽权柄,并不断为朝堂补充新鲜血液以打造自己的政治力量。大观元年二月二十日他“令从官各荐人才”[16]5807。次年三月一日又诏:“博访人材文学之士,处之于文馆;干敏之士,处之于寺监丞簿。求心计之才于漕计之属,养智勇之士于将帅之幕。”[16]5807同时大力提拔宦官群体,大观元年十一月壬子朔“置符宝郎四员,二员以内臣充,掌禁中符宝”[14]939。次年二月更是赐宦官梁师成进士出身。此时最活跃的宦官是负责拓边洮州、积石军的童贯,宋徽宗赞许其“寔宽西顾之忧;事不辞难,克称忠权之重”[15]344。最要者,宋徽宗不遗余力对宰执群体中的蔡京党羽进行分化瓦解。他曾以相位收买蔡京的死党张康国,“阴令沮其(蔡京)奸”[13]11107,后者遂在西北边帅自辟官属的问题上与蔡京唱反调。宋徽宗还在宰执群体中插入侯蒙,使其“密伺京所为”[13]11114。至王黼拜相时,宋徽宗终于言道:“群臣多宰相门人,如黼独首出朕门下”[26]。以《宋史》为代表的官、私史书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为润饰宋徽宗对臣僚牵制瓦解的帝王用心,有意将这些宰执的历史形象涂抹成投机小人或拥有道德缺陷,渲染他们皆见利而合、又因分赃不均而决裂。这一点是需要揭露的。这一连串措施均浸润着宋徽宗制衡蔡京权势的考量,深刻改变了宋徽宗的政治性格与宋徽宗朝的政治生态,其影响遍布宋徽宗统治时期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