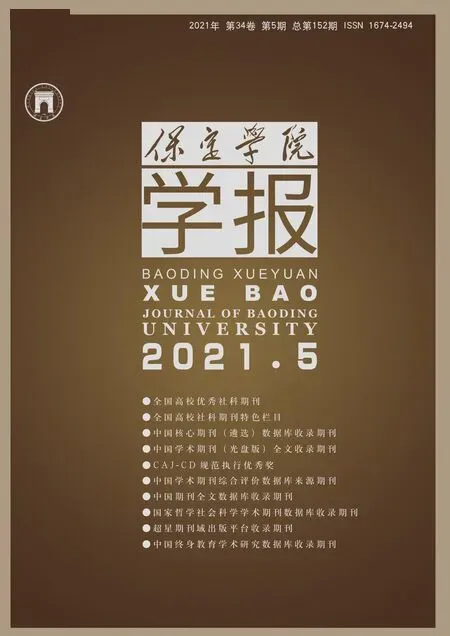辽金元时期河北境内契丹人的分布与融合
陈瑞青,吴玉梅
(1.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2.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契丹族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其迁徙分布以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问题历来受到学界关注。如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对金朝契丹人西迁、北撤以及留居原地等都有精辟的论述[1]。冯继钦《金代契丹人分布研究》则通过定向研究,探讨了金代契丹人流动分布的总趋势:一部分向西迁徙,一部分撤回北方,一部分随金军南下,大部分则留居在原住地[2]。此外,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第四卷)[3]、夏宇旭著《金代契丹人研究》[4]以及罗贤佑著《元代民族史》[5]也对契丹人分布有所涉及。辽金元时期,河北地区作为契丹人重要的舞台,曾有大批契丹人生活在这里,然而目前学界对河北境内契丹人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拟从辽金元时期契丹人在河北的迁徙分布与民族融合两个维度进行探讨,以期有裨益于学界。
一、辽朝建立前后契丹人内迁河北
辽朝建立前,契丹已经开始陆续向中原地区迁徙。唐太宗时期,曾在契丹、奚生活的东北地区设立饶乐、松漠两个都督府。唐朝中叶以后,设置幽州、平卢两节度使以控遏契丹。此时有许多契丹人归附唐廷,被安置在羁縻州。同时也有部分契丹人迁到幽州,叛将安禄山军队中就有很多契丹将士。唐朝灭亡后,契丹势力在北方日益壮大,逐渐控制了幽州(今北京市)至柳城(今辽宁朝阳)地区。五代时期,契丹势力进一步壮大。天福三年(938),后晋石敬瑭为获得辽朝支持,割让幽云十六州予契丹,使辽朝控制了河北中北部地区。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后,开始向南部的迁徙。后周广顺二年(952)十月“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数十万口,契丹州县亦不之禁。诏所在赈给存处之,中国民先为所掠,得归者什五六”[6]885。在这些从瀛、莫、幽三州进入中原的人口中,除了原来被契丹掠走的汉族人口外,也有部分契丹人在内。辽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后,河北地区不仅成为辽朝重要的赋税来源地,而且也是辽与中原政权对峙的军事前线。为加强对河北地区的控制,辽朝开始向南京道、西京道大规模移民,众多的契丹贵族、官员、平民和军队官兵留居河北。陈述先生在《契丹政治史稿》中罗列了华北地区的许多地名,并推测“这些村庄命名在当时,主要住户可能是契丹人”[1]126。在今天的河北、内蒙古、山西、北京等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契丹墓葬,说明当时契丹人大量迁入华北地区,且在此地世居的史实。
辽朝在境内设置大量的投下军州,涉及河北的有中京大定府泽州(河北平泉县南)和北安州(河北承德市西)。因此在河北承德地区,聚集了大量契丹贵族,对境内的汉、奚、契丹等族进行统治。1977年文物普查时,在杨家北沟发现《耶律加乙里妃墓志铭》。志主“姓耶律氏加乙里妃”死于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享年五十九岁。耶律加乙里妃出身契丹豪门,“父阿骨轸,遥辇常衮,世袭二王之后,□三公之先,怀卫社之长,□蕴斯时之大略,斯名不缀,厥德弥芳”。可知耶律加乙里妃的父亲阿骨轸在辽朝享有较高地位。据郑绍宗先生研究,志文中的“阿骨轸”就是《辽史》中的耶律贤适。据《辽史》载:“耶律贤适,字阿古真,于越鲁不古之子。嗜学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景宗立,以功加检校太保,寻遥授宁江军节度使,赐推忠协力功臣。时帝初践阼,多疑诸王或萌非望,阴以贤适为腹心,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保宁二年秋,拜北院枢密使,兼侍中,赐保节功臣。三年,为西北路兵马都部署……乾亨初,疾笃,得请。明年,封西平郡王。”[7]1273同时,在承德平泉还发现辽大长公主墓,该墓位于承德平泉县蒙和乌苏乡头道营子村八王沟。据墓志载:“大长公主为辽景宗、萧皇后之长女。名为观音女。”其丈夫为“北府宰相萧继远”。在景宗时期,大长公主被封为“齐国公主”。到了圣宗加封“晋国大长公主,赵魏国长公主”。重熙十五年(1046)冬薨于龙化州(即今内蒙哲里木盟奈曼旗八仙筒一带)。并于第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葬于马盂山(即今平泉县柳溪乡光头山)[8]。1973年,在承德县八家公社发现契丹符牌。符牌上有契丹文字,是用汉字笔画的构件重新组合成的,释读为“敕宜速”[9]。1972年,河北隆化还发现了辽代“契丹节度使印”和“金”字人形铜押印各一方[10],都说明河北承德是契丹人重要的聚居区。这些居住在承德的契丹人开始和汉族通婚。
由于张家口地区坝上草原水草丰美,故契丹人移民张家口地区的时间较早。其中鸳鸯泺(今张北县西北安固里淖),为契丹乙室部司徒居地。据《辽史·营卫志》记载:“乙室部。其先曰撒里本,阻午可汗之世,与其兄益古分营而领之,曰乙室部。会同二年,更夷离堇为大王。隶南府,其大王及都监镇驻西南之境,司徒居鸳鸯泊,闸撒狘居车轴山。”[7]385鸳鸯泊即今张家口市张北县的安固里淖。辽建国不久,将契丹乙室部迁徙至鸳鸯泊。辽圣宗时,在此地设有四时行帐,官署林立。据《辽史·兵卫志》记载:“其南伐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7]397辽朝末年,都统耶律马哥即屯兵于此。金朝灭辽时,辽天祚皇帝曾仓皇从居庸关出逃,至鸳鸯泺避难。据《金史·太祖纪》记载:金兵俘获辽护卫习泥烈,言说辽主在鸳鸯泺畋猎,可袭而取之。天辅六年(1122)三月,金朝都统完颜杲出青岭,宗翰出瓢岭,追辽主至鸳鸯泺,辽主慌忙逃奔西京。宗翰派遣挞懒袭击辽都统耶律马哥,耶律马哥被迫出逃,挞懒收其群牧。驻扎鸳鸯泺的契丹乙室部牧群被金朝收编。在河北张家口市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墓壁画中人物形象及服饰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明显反映出契丹与汉族两种生活习俗并存、相互融合的地方特色。而乙室部的另外一个聚集地“车轴山”则在今唐山市丰润区南10公里的车轴山。乙室部在河北北部地区游牧生活,还统领契丹军队,在军事上起到了镇守作用。辽代在云、应、蔚、朔、奉圣等州设置五节度营兵,亦于各州设置乡兵。其中,蔚州治所在今张家口蔚县。
除了河北北部地区外,在河北中南部地区也曾生活着一些契丹人,辽太宗天显年间归辽的定州人梁文规,其子梁廷嗣甚至得到了以大水泺之侧地四十里,“契丹人凡七户皆赐之”[11]3188,其宠遇不可谓不高。保定易县《易州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中的题衔有:“都维那右监门卫大将军、知易州军州事、沿边巡检安抚屯田劝农等使耶律迁。”[12]487在耶律迁所任职官中有“沿边安抚使”一职,一般而言,只有在辖区内有少数民族的情况才加此使职。内蒙古昭乌达盟出土的《耶律琮神道碑》,耶律琮曾任“涿州刺史、西南面招安巡检使、契丹、奚、渤海、汉儿兵马都部署”[12]59。这说明在涿州境内存在大量的契丹、奚族士兵。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称梁济世“为雄州谍者,尝以诗书教契丹公卿子弟,先得其国书本以献”[13]6320。这说明在雄州(今河北雄县)的契丹贵族子弟已经开始接受汉族儒家文化的教育。统和五年(987),辽圣宗“尝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下妇人迪辇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刈”[7]925。这说明契丹乙室部已经渗透到河北藁城一带,并且已经由游牧转向从事农业生产。
在辽与北宋对峙时期,辽朝边界地区时有契丹官员、将士越界归附北宋,说明宋辽边界居住的契丹人不在少数。在幽云十六州的契丹人,其主要是防遏北宋的契丹官兵。统和二十一年(1003),辽朝供奉官李信投宋,报称:“(辽)国中所管幽州汉兵,谓之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约万八千余骑,其伪署将帅,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当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后四镇诸军约十万八千余骑,内五千六百常卫戎主,余九万三千九百五十,即时入寇之兵也。”[13]1207从李信的言论可知,辽朝军队中一部分是汉族、奚族,担任主力的是由契丹将士组成的常备军。
二、金元时期契丹人在河北的分布
在金灭辽的过程中,契丹贵族开始分化,一些生活在河北地区的契丹贵族投靠金朝。1942年河北省兴隆县梓木林子村出土《萧仲恭墓志》,该墓志为契丹文小字,墓志刻于金代天德二年(1150)。字刻于汉文志盖背面,共70行,5 100余字,是现存契丹小字石刻字数最多的一件。据《金史》载,萧仲恭和天祚帝是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二月壬戌被俘于余睹谷(在今山西应县)。八月被押解至京师,丙午,天祚帝被降封为海滨王。萧仲恭应于此时降金,《越国王乌里衍(萧仲恭)墓志铭》说他降金后“太宗时授右院宣徽,任职少府监两年”。《金史·萧仲恭传》亦称:“太宗以仲恭忠于其主,特加礼待。”[14]1839皇统八年(1148)为行台尚书省左丞相,封淄王。同年拜尚书右丞相,封济王。同年复任中书令,监修国史。同年复任太傅领三省事,封郑王。天德元年(1149)迁封曹王,仍领所知之事。同年封某王,同月再封鲁王,除燕京留守。天德二年自鲁王迁封越国王。金代,在地方任官的契丹人中,移剌众家奴较为著名,移剌众家奴“积战功,累官河间路招抚使……赐姓完颜氏”[14]2576。有的契丹贵族则对金军采取抵抗措施,如天会九年(1131),耶律余睹举兵抗金,“尽约云中、河东、河北、燕金郡守之契丹、汉儿,令杀女直之在官、在军者”[15]117。由于云内节度使耶律奴哥告发,事情败露,遭到金廷镇压。这些起事的契丹人或被杀,或外逃流散各地。又如正隆五年(1160),河北大名一带的契丹人追随王九发动起义,据史书记载:“契丹边六斤、王三辈皆以十数骑张旗帜,白昼公行,官军不敢谁何,所过州县开劫府库物置于市,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贼至,而良民不胜其害。”[14]2783这次契丹人的起义最终也遭到了金朝的镇压。大定三年(1163),金朝解散了所有曾参加起义的契丹猛安谋克,将原管人口分散到女真的猛安谋克中去。大定十七年(1177),又彻底解散了其余的契丹猛安谋克,将契丹族原有的组织形式打散,形成女真、契丹交相杂居的局面。
辽朝灭亡以后,契丹族由统治民族沦为被统治民族。金朝治下的契丹人多数生活在长城以北,他们没有南迁,也没有被编猛安谋克,主要分布在西京路、北京路以及金朝西北边境,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契丹人仍以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为主,被时人称作“乣人”或“乣户”。另外一部分契丹人则追随金军南下伐宋。金朝为扩大领土,集重兵于燕云及黄河以北地区。金朝军队以女真人为主体,同时还还包括契丹、奚等族。随着战事的平息,金朝开始将这些南下的契丹人组织起来,戍守屯田。皇统五年(1145),“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授以官田,使其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15]153。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金朝在燕山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实行屯田,内迁的女真人、契丹人开始计户授田,形成大大小小的女真、契丹聚落。为巩固和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金朝在占领区也大搞屯田实边,内迁人口中既有女真人也有契丹人。据《大金国志》称:“废伪齐豫后,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15]173金廷设置军屯,有意将契丹、奚族与汉族百姓杂处,用以加强对新占领地区州县的控制。辽朝灭亡后,大多数留居河北的契丹人接受了金朝的统治,据史书记载:“河东、河北州、县领防守,每州汉人、契丹、奚家、渤海、金人多寡不同。大州不过留一千户,县、镇百户,多阙额数。”[16]337这些生活在河北、河东地区的契丹人被编入猛安谋克,成为金朝治下的平民。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金代女真研究》一书中推测,金天会年间(1123—1137),燕云地区大的州置一个猛安,县、镇则置一个谋克。这些被征服地区的契丹人和内迁女真人一样,都要被编入猛安谋克,为金朝提供赋税和兵员。据《金史》记:“(大定二十年十月)诏徙遥落河、移马河两猛安于大名、东平等路安置。”[14]157关于遥落河,史籍中缺载,已不可考。《金史》中临潢府有“移米河”,在兴安岭西附近,可能就是“移马河”。三上次男指出,这次迁徙两猛安户与女真户杂居的目的,就是让女真户监控契丹户。同时,这两个猛安名称与女真猛安名称明显不同,应当就是大定初年契丹叛乱被镇压后,被迫迁往各地的奚、契丹人的一部分[17]511。总之,遥落河、移马河两猛安是从临潢府或更北的地方迁到大名(治今河北大名)、东平(治今山东东平)两路的契丹、奚猛安。
此外,在永清县、安肃县(今河北徐水县)、大名、霸州等地都有契丹人居住生活[3]140。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围困开封时,李纲上奏:“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18]1126册784可见,当时金朝军队中一半是女真人,一半则是契丹、奚和渤海人。天会四年(1126)十一月,金军统帅完颜宗翰攻陷怀州(今河南沁阳),宋人范仲熊奉命前往郑州养济,路上与燕人同行,于是问道:“此中来者是几国人?共有多少兵马?”番人答道:“此中随国相来者,有鞑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博啰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戛斯家、有火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见得数目,其从河北随栋摩国主者兵马更多,为拘占数国路,大金正军不过十万,煞有生女真人唤做扫地军便是也。”[19]734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南下金军中不只女真人,而是包括契丹、奚、党项在内的多民族组成的军队。
在蒙古灭金的过程中,留居河北的契丹人认为复仇的时机到来,纷纷举兵抗金。成吉思汗率兵南下时,始终不肯仕金的霸州人移剌捏儿认为“为国复仇,此其时也”,率亲党百余人主动投附成吉思汗[20]3529。同在霸州的契丹人石抹孛迭儿“仕金,为霸州平曲水寨管民官。太师、国王木华黎率师至霸州,孛迭儿迎降,木华黎察其智勇,奇之,擢为千户”[20]3576,参加了蒙古军队灭金的一系列战斗,被升为龙虎卫上将军、霸州等路元帅。冀州人贾塔剌浑,“太祖用兵中原,募能用砲者籍为兵,授塔剌浑四路总押,佩金符以将之。及攻益都,下之,加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左监军,便宜行事”[20]3577。耶律秃花,世居桓州(治今内蒙古正蓝旗四郎城),蒙古军攻打金朝边界时,充当蒙古军队向导。后跟随木华黎攻打山东、河北等地有功,总领也可那颜,封为濮国公。桓州人石抹明安,1212年成吉思汗命其帅蒙古军队攻占抚州(今河北张北),又命其与三合拔都,帅兵由古北口南进,攻取河北诸州,兼管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
一些投诚的契丹人在河北取得军功并在河北居官,如舒穆噜“行省太师统诸道兵破大名,侯遂隶帐下,拜馆陶招抚使,俄迁东平大名招抚使、元帅左监军留事、东平行台。严公以取磁州功,遂兼知州事”[21]1196册284。也有一些归顺蒙古大军的契丹人,参与了平金最后留居河北,如耶律忒末,“国兵至,金徙于汴,忒末及子天祐率众三万内附,授帅府监军,天祐招讨使,从元帅史天倪略赵州平棘、栾城、元氏、柏乡、赞皇、临城等县,籍其民五千余,置吏安辑焉。岁辛巳,太师木华黎统领诸道兵马,承制加忒末洺州等路征行元帅,与天祐略邢、洺、磁、相、怀、孟,招花马刘元帅,有功。木华黎又承制授忒末真定路安抚使、洺州元帅,进兵临泽潞,降其民六千余户,以功迁河北西路安抚使,兼泽潞元帅府事。壬午,致仕,退居真定”[20]4383。还有一些金军中的契丹士兵,也乘机叛金,如金宣宗南迁开封走到大都城以南的涿州时,随行的契丹军队在斫答、比涉儿和札剌儿的率领下叛变,并和同样叛金的塔塔儿的军队联合作战[22]237。当时参加蒙古军队作战的契丹士兵人数,史无明载。成吉思汗十年(1215),契丹人石抹阿辛率领北京(治今内蒙宁城县境)等路民一万二千户降蒙,所部军皆猛士,因身穿黑衣而被称为黑衣军。这支军队被蒙古派遣到各地驻扎,其中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其主力驻扎在河北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固安一带。
另外,元代大都(今北京市)及其周边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契丹人,契丹人耶律楚材受到成吉思汗信任,被任命为“总裁都邑”,就是因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契丹人居多”[20]3610。元代还有在地方上居官的契丹人,如耶律泽民曾任大名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其死后他的儿子耶律泰亨袭公爵,“中统改元,复长大名路课税所事”[21]1196册296。元代在北京周边地区生活着大量契丹人,并形成一些以契丹语命名的村寨,如昌黎县有达子营、黑各庄;滦县有野里庄;蓟县有黑家庄、科科庄、野王庄、律家庄;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姓刘,宝坻县还有达子庄、达子屯、哈剌庄[1]177。
三、河北境内契丹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
辽朝时,契丹族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并且开始和汉族通婚。辽太宗下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7]45,对上层契丹族与汉族通婚表示认可。辽圣宗、景宗时期,契丹族与汉族通婚的现象更加普遍,如河北韩知古家族多与萧氏通婚,尤其是他的第五子韩匡美曾两度娶萧氏女为妻。韩德让的族弟韩瑜原配夫人和继室夫人都是萧氏,其子韩槆先后三娶,有两位夫人姓萧。不仅上层通婚,而且在下层民众中也存在通婚现象,余靖《武溪集》载:“四姓杂居,旧不通婚,谋臣韩绍芳献议,乃许通婚。”[23]104韩绍芳的建议为进入中原的契丹族与当地汉族通婚扫清了障碍。辽代后期,曾流行这样的一首民谣“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24]349,生动地表现了契丹与汉族通婚的自由。
在生活生产方式上,处迁居鸳鸯泺的乙室部还保留了游牧方式,辽时在此设置官牧场。与汉族接壤的一部分契丹族,由于受到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半牧半耕的经济生产方式,租种汉族边民荒地,效仿汉族耕作方式,耕田播种,“秋熟则来获”。迁居内地的契丹族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苏辙在出使辽朝时,见到汉族与契丹族农耕的景象,写下“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佃”[25]397的诗句。苏颂的《使辽诗》也写道:“农夫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26]170这首诗中的“杂夷”是奚、契丹、渤海等少数民族的统称,他们和汉族生活在一起,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圣宗时期,又新增设了一批新的州县,其中有定霸县、保和县、宣化县、兴仁县、易俗县等,由临潢府所辖。这些北部州县的契丹人“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7]438。契丹服饰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具有中原汉族特色的衣裳分制、右衽长袍、妇女下衣为裙的现象,有些契丹人甚至直接着汉服、说汉语,这些都表明内迁中原的契丹族无论在生活习惯上,还是在精神面貌上都已经开始汉化。
金元时期是契丹族迅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金朝继续在乙室部游牧之地设置牧场,有些群牧主要由契丹族构成。金朝将契丹和女真一起编入猛安谋克进行南迁,这些进入中原的契丹人逐渐适应了内地的农耕生活。金朝后期,为了防范契丹反抗,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20]3511。金章宗明昌十二年(1191)还下令“罢契丹字”,同时,金朝还鼓励契丹与汉人通婚,“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契丹、汉族昏姻以相固结”[14]991。这些内迁河北的契丹族与汉族、女真族杂居在一起,交相婚姻,“俾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14]1961。
元朝时,实行四等人制,契丹被列入第三等汉人中,到至正二十一年(1361)时,“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20]263。从这条记载来看,那些生活在内地的契丹人和女真人已经不再使用本民族语言,而是使用汉语,在元廷看来他们已经等同于汉人了。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中记载,元朝时的“汉人”之一就是“契丹”[27]13-14,可见很多内迁的契丹人已经汉化了。元朝法律规定:“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28]193虽然元廷有意保留各民族婚俗,但是散居各地的契丹人逐渐突破“同姓不婚”的禁忌,与汉族、蒙古族以及色目人通婚的现象更加普遍,如大同路千户萧公男娶了真定等路奥鲁都总管王仲位之女为妻。再如,大名路征收课税所长官耶律泽民的两位夫人,一位是汉族刘氏,一位是契丹萧氏。而且自元朝始,契丹人出现改汉姓,如将“石抹曰萧”“移剌曰刘”。据虞集《吏部员外郎郑君墓碣铭》载,碑主郑大中“先世本契丹贵族石抹氏,后改从汉言曰萧氏者是也”。因幼时被千户郑公收养而改姓郑,“郑氏有以石抹氏改者,自真定讳显者始”[29]675。
总而言之,随着疆土的扩大,辽朝占据河北中北部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契丹族活动的重要舞台。辽朝成建制地将乙室部迁徙到鸳鸯泺,在坝上地区形成以游牧为主的契丹部落。辽朝将幽州设为南京后,使河北广大地区成为畿辅,在这里生活着大量契丹人,既有达官贵人,也有普通民众。内迁中原的契丹人,长期与汉族杂居在一起,交相婚姻,促成了契丹人与汉族的融合。金元时期,尽管契丹人的身份地位发生变化,但是作为河北地区重要的民族,一直受到女真、蒙古的倚重和防范。无论是上层有意识的消弭契丹特性,还是民间无意识的交往融合,内迁河北契丹人的民族特征逐渐消失,至元朝中后期,已经和汉族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