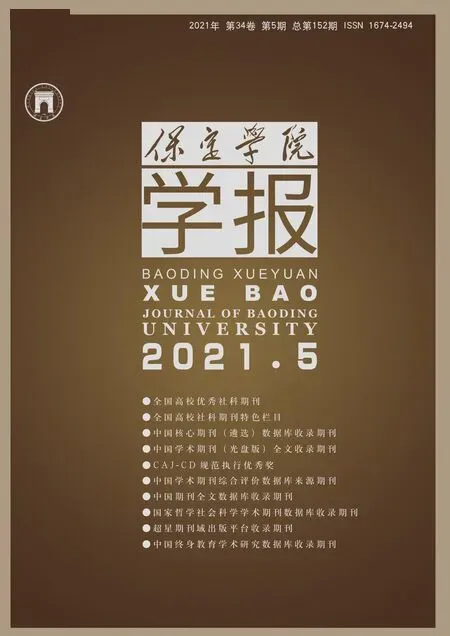从“学”到“文”:桐城流派性质之转变
——以桐城诸子义理、文章之辨为视角
赵 明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桐城派发生于康雍之际,起于方苞之时的说法向来为人所惯知。往日虽有数家点明真相,然零星之语始终未能动摇人们固有认知①早在清代吴敏树就已一语道破:“今之所谓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吴敏树《与欧阳筱岑》)。周作人也指出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85页)。而后漆绪邦、王凯符《桐城派文选》(1984)、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1988)、马积高《理学与桐城派》(1993)和陈平原《桐城文章流变》(1996)亦发表此类观点,可惜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出,“桐城”创派的真相才真正得以厘清:“桐城派的真正创始者,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姚鼐。”[1]1而后人误将方苞认作开山,其实也正是姚鼐精心“制造”的结果。在汉学独当的重压下,尊宋的姚鼐出走四库,产生开宗立派以抗汉学的念头。终于在为其师刘海峰祝寿时迈出了制造“桐城”的第一步:“囊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2]姚氏借他人之口,拉入乡贤方苞、刘大魁,草创出“方—刘—姚”桐城派传承谱系,而后在《刘海峰先生传》等文中又多次强调。而他后四十年的书院讲学生涯,更为“桐城”成派打下了牢固的现实基础。曾国藩的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历程:“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3]从最初的势单力薄历经数十年渐渐发展壮大,代代传承,延续有清一代,终成有清最大文章流派。然桐城派是否如今人所言,自始至终都属文章流派?似未必然。事实上,桐城派在发展过程中,流派性质发生过转变。王达敏已对姚鼐建立桐城派进行了深入考察,揭示出其创立“桐城”,造“方—刘—姚”古文传承谱系,上追唐宋八家文统,又尊程朱之学,欲实现文统、道统而一。目的在于树宋学之帜以抗汉学,学术之争是首要因素,回归辞章只是出于对自身能力的考量。如王达敏所说:“汉宋之争成为桐城派建立的根本动力。”[1]103欧明俊在此说基础上对“桐城派”界说进行反思,也认为如果放在历史语境中来考察,桐城派最初其实是一个“学术”流派,应称为桐城“学派”①参见欧明俊《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期。吴孟复也曾说过,就桐城而言,不仅有桐城文派,还有桐城学派、桐城诗派。但他口中的“桐城学派”是指由明末清初方学渐、方以智、钱澄之等人构成的群体,非姚鼐建立的桐城派本身(见吴孟复《〈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序》,《吴山萝诗文录存》,黄山书社,1991年版;吴孟复《“桐城文派”及其历史渊源》,《桐城文派述论》,合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吴怀祺又在其父基础上将此意义的“桐城学派”延续至有清一代,与“桐城文派”并行。突出的是桐城诸子文章之外的成就,如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见吴怀祺《桐城学术与时代》,《桐城派研究》第十五辑,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与本文所论的桐城派建派之初具有的“学派”属性意义不同。。而至于晚清,桐城派却越来越强调“辞章”本身,宋学成分浓重的“义理”渐被冷落。“学派”逐渐发展为“文派”。梅曾亮作为姚鼐之后的桐城领袖,在从“学”到“文”的转变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后曾国藩、吴汝纶等接续此衣钵,走得更远,“桐城”终成“文派”。从姚鼐推举的“义理、考证、文章”在各个时期桐城各家的不同侧重可以一窥桐城流派性质变化的轨迹。
一、“桐城”宗旨:“义理、考证、文章”的提出
“义理、考证、文章”②“义理、考证、文章”在诸家口中有不同的称呼。如“义理”又称“理义”“经义”,“考证”又称“考核”“考据”“制数”“训诂”等,“文章”又称“辞章”“词章”,义同名殊。此标题取于姚鼐《述菴文钞序》。为古今学问之途,最早提出是在戴震《与方希原书》一文中,其曰:“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4]在这里,戴震指出“理义”“制数”“文章”为学问之三途,明确将“文章”置于最末之位置,并未比较“理义”与“制数”。而其著名的“轿夫与轿中人”之喻,则表明了两者之高下:“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5]452此余英时“狐狸与刺猬”之喻揭示戴氏学术之真最切。所以,“义理、考证、文章”在戴震学问体系中有一个明确的次序,即义理为上,考证次之,文章最末。然而后来段玉裁述戴氏之学,却无形之中变换了侧重。其曰:“始,玉裁闻先生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5]451-452段氏虽明言其师的追求在义理,但言语之间却将“考核”放在了最紧要的位置。此移形换影之功后被姚鼐弟子方东树一眼看穿,指出“此宗旨专重考证”,并责备段氏“竟以考核为圣人之急务,方共蔑弃义理、文章,专事考核”[6]325。方对段的责备固然有其自身立场,而段以考证为重,又何尝没有用意?所谓“针尖对麦芒”,两者正是汉宋之争中对立的双方。戴、段以后,孙星衍、焦循、凌廷堪等汉学者皆闻风而起,扬“考证”抑“文章”,希冀由考据上达圣人之道,视辞章为不足道。汉学主流而外,另有章学诚、袁枚等皆有参与。袁枚既批“考证”也批“义理”,独举“文章”。章学诚则视“考证”“文章”皆为载道之器,似以“义理”为最高,“考证”“文章”等而视之,居于次。如其所言:“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学问、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以之者,道也。”③参见章学诚《与吴胥石简》。文中章氏所谓“学问”即汉学家所尊之“考证”。王达敏先生认为:“在章学诚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论中,义理地位最高,考据次之,辞章又次之。”(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68页)观章氏之论,似未必然。可以说,戴震开其先,汉学内外的学者无不受其影响而产生思考④观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与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即可知戴震在当时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以及章、姚等人与他的交往经历和学术恩怨,可以说,姚鼐、章学诚“无不在其笼罩下运思”(王达敏语)。。也可以说,“义理、考证、文章”的关系是这一时期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而产生此问题的背景自然是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争。姚鼐标举“义理、考证、文章”同样是由上述背景而来,并使之成为桐城派的论学宗旨。
姚鼐在《述菴文钞序》中曰:“泰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7]《复秦小岘书》亦曰:“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不可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8]80梅曾亮曰:“先生挺桐一元,兼包三味。”[9]最能概括其师主旨。在姚鼐看来,就学问之道而言,“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缺一不可,兼收善用才是最理想的境界。然而又如姚氏所言:“一塗之中,岐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迳域,又有能有不能焉。”[8]80可见姚鼐虽然提出这一兼收三者、回归道术未裂之境的学术理想,但也清楚地认识到实践中的困境:各人才性的限制是实现这一学术理想的最大障碍和现实难题。故而又言:“若如鼐之才,虽一家之长犹未有足称,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杰兴焉,尽收具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为群材大成之宗者……”[8]80因自身才力有限而将希望寄托于后世君子,自信必有“豪杰兴焉”,足以说明三味兼包之难。事实证明,后世君子同样受限于这一客观条件,姚鼐所说的这一困境后来也被桐城后学反复强调。如方东树曰:“夫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二者区分,由于后世小贤、小德,不能兼备,事出无可如何。”[6]325曾国藩亦曰:“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于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10]587而梅曾亮更以为不仅后世小贤不能兼备,自古孔门大贤便不能兼:“昔孔氏之门,有善言德行者,有善为说词者,此自古大贤,不能兼矣。”[11]在共同面临的此种困境之下,桐城诸子不得不根据其“才性”有所偏重。姚鼐《尚书辨伪序》:“学问之事有三:义理、考证、文章是也。夫以考证断者,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犂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12]姚氏创立桐城一派,正是出于对汉学家专重考证,轻视义理、文章行为的不满,故而宗宋儒之学,倡韩、欧之文,欲合“宋元以来学问、文章之统”,以抵抗当时最盛之汉学。所以正与戴震、段玉裁相反,斥考证为末是桐城内部的共识。在桐城内部,诸人的差异主要在于对“义理”“文章”的关注前后存在不同偏重。简而言之,即对文与道偏重的不同。
二、理胜于文:作为“学派”的“桐城”
姚鼐在《停云堂遗文序》中说:“士不知经义之体之可贵,弃而不欲为者多矣。美才藻者,求工于词章声病之学;强闻识者,博稽于名物制度之事,厌义理之庸言,以宋贤为疏阔,鄙经义为俗体。”[13]此处姚鼐对士多为词章、名物之事,于经义、义理“弃而不欲为”的行为表示惋惜,以为经义之体最为可贵。他在《次韵赠左兰城》中又道:“属将道域深攀援,更觉文章小技轻。”[14]显然,姚鼐以经义为贵,文章次之。其曰:“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15]若套用戴震轿夫、轿中人之喻,正是“诗文”为轿夫,“义理”为轿中人,即“文以载道”。由此可见,戴、姚二人所恃不同,然所求皆在“义理”,可谓殊途同归。
事实上,姚鼐虽以文章立派,然向来以儒士自期。据《姚惜抱先生年谱》和《姚鼐与乾嘉学派》综观姚鼐为学历程,可概括出其学有三变:青年时期乐于诗文创作,以文士自待。至京师,受风气影响,转向考据,不欲为文士。此以乾隆十九年(1754)姚鼐入京参加礼部大试为界。转入考据,任职四库馆,渐觉与汉学异趣,最终于乾隆四十年(1775)辞官南归,又转归辞章,着力建设“桐城”。在这之中,宋学义理始终是姚鼐一以贯之之道。且受汉学冲击后,愈加坚定以此为立身之道,从考据回归辞章的根本因素便是出于对义理的维护。由此可知姚鼐仅早年短暂作为文士,而后始终以儒士自待,在创建“桐城”时期也不曾改变。此心声早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有所表露,在引程鱼门、周书昌二人“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之语后,姚鼐便开始夸述桐城为钟灵毓秀之地,才人不绝。昔有浮屠之盛,而“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即有暗指自身之意。《稼门集序》又有言:
今世之读书者,第求为文士,而古人有言曰:“一为文士,则不足观。”夫靡精神,销日月,以求为不足观之人,不亦惜乎?徒为文而无当乎理与事者,是为不足观之文尔。……窃以为古今所贵乎有文章者,在乎当理切事而不在乎华辞。[16]
如王达敏考察姚鼐之所以用辞章与汉学相抗时所说,考证和义理非其所长,故而回到早年所擅长的辞章。也就是说,姚鼐回归辞章是出于对自身能力的考量,并无意以此立身。文章之于姚鼐和考证之于戴震本质相同,在他们的学问体系里,文章、考证都只是作为载道之体而已。姚鼐创立文派的目的依然是抗汉学以举宋学,学术之争是首位因素。此所以姚鼐不求为文士,而以儒士自期。因此,开派之初的桐城派更具“学派”性质。
姚鼐之后,弟子中继承此衣钵的主要是方东树。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安徽桐城人,因著《汉学商兑》举宋学与汉学相抗而闻名。同门管同论方东树:“同少时,性喜为文,与海内文士往来,而桐城方君植之为之冠。其后,同更忧患疾病,四十以来,悟儒者当建树功德,而文士卑不足为,以语他人,怃然莫应也,植之独深然之。盖植之之学,出于程朱,观其《辨道》一论,明正轨,辟歧途,其识力卓有过人者,宜其文之冠于吾辈也。”[17]管同初以文士视植之,实在有以己意揣测植之之嫌。而悟当为儒者之后,独植之为知交,足以知植之之所向。方氏尝自述其学:“十八九时,读孟子书,怃然悟学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为,性喜庄、老及程、朱、陆、王诸贤书,读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发者。”[18]又云:“少时亦尝泛滥百家,惟于朱子言有独契,觉其言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曾、思、孟无二,以观他家,则皆不能无疑滞焉。”[19]可见方东树实与其师姚鼐一样,很早便倾心程朱,以儒者为业。门人方宗诚所言:“先生气质刚毅,生平以明学术正世教为歆,研经考史,穷理精义,宏通详确,而一归于醇正,言必有宗,义必有本,不欲为无关系之文,故其文茂实昌明,而不尽拘守文家法律。尝自言其文于姚门不及管异之、梅伯言。又尝以为吾固深知文,然实无暇致力于此。”[20]361-362如此,方氏于“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次序即使不明说,也可猜测出大概。方东树生平致力于维护程朱、对抗汉学,其所作《汉学商兑》正是对江藩所作《汉学师承记》的强攻反驳,尊宋学者以其为嘉道间著述有功于圣道第一人。《汉学商兑》中谈及“义理、考证、文章”:
夫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二者区分,由于后世小贤、小德,不能兼备,事出无可如何。若究而论之,毕竟以义理为长。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也。[21]又谓:“文章者,道之器”,“文之所以不朽天壤万世者,非言之难,而有本之难”[22]200。舒芜说:“在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的体系当中,义理是灵魂。方东树的主张,其实就是要桐城派一仍旧贯。”[23]想必此言深中方氏之心。
由上可见,从姚鼐到方东树其实都是作为汉宋之争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树“桐城”之帜,以文为器,务在抵抗汉学,维护圣道,始终在学术之争的范畴中。故而以“儒者”自期,而不以“文士”自命。乃至后来方宗诚、戴钧衡等方东树的门人仍积极维护圣道,都可视为汉宋之争的余波。所以这一时期的桐城派实质上是作为“学派”的桐城派。这一点从对方苞的评价中也能看出。方苞本以学者立身,宋学根柢深厚。至于身后被姚鼐拉入文统,文章被姚鼐等人推崇甚重,以为“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24]。但依然不忘望溪“学者”特质①姚鼐《与管异之》:“《古文尚书》之伪,此已是天下定论。望溪虽学者,而其人敦厚而识滞,又似未见阎百诗之《古文疏证》,故执其误而不知返。”姚鼐《惜抱轩尺牍》,第67页。,方东树对方、刘、姚之文进行比较,认为“侍郎之文……是深于学者也……”[22]201而姚鼐之所以引方苞入“桐城”,看中的也正是方苞具备的“学”与“文”两种特质正与其“文”“道”二统合一以抗汉学的创派意图相契。是故此时桐城派的“学派”性质明显胜过“文派”性质。
三、始以文自期:走向“文派”的“桐城”
如果桐城派沿着姚、方理胜于文这一脉走下去,“文”或许会渐渐淡出,最终成为一个纯粹的“学派”。蔡长林指出的晚清以来的文人治经现象为我们这一猜想提供了可能。毕竟,文章与义理作为桐城派两大构成,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两方中的任意一方倾斜都会流于极端。然而,就“桐城”外在形势而言,自江藩《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汉学商兑》两军对垒,汉宋之争达到高潮。随后高潮渐息,汉宋学逐渐向合流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汉宋调和、兼采的趋势。一般认为方东树《汉学商兑》即“标识着汉宋相融的新发展”[25]。“义理”与“考证”逐渐失去争论的必要,尊宋者也无须同往日那般强调“义理”,“义理”呼声由此渐弱。同时,自嘉庆以来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人倡导骈文欲与桐城古文抗衡,使得文派之争渐起,即一直延续至民国的“骈散之争”。这导致桐城诸子重心不得不发生偏移,更关注“文章”本身。再从“桐城”内部走势来看,姚鼐之后,对桐城派的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并非方东树,而是姚氏另一弟子梅曾亮。桐城派的道路由此走向了另一种可能,即对“文章”的关注逐渐胜过“义理”,“桐城”开始向“文派”方向走去。
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早年喜好骈文,后经好友管同劝告,始知班马韩柳之文可贵而转向古文创作,与方东树、管同、刘开①曾国藩时将刘开替换成姚莹,见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后多有人承此说。同为姚门“四大弟子”。至道光中叶,管同、刘开等已相继谢世,方东树在地方漂流,势单力薄。独梅曾亮于道光十二年(1832)北上返京,隔一年入赀为户部郎中,十八年后方辞官南归。“京师十八年是梅曾亮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桐城派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②参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222页。王达敏将梅曾亮在都时间定为道光十三年(1833)到道光三十年(1850)。《桐城派编年》则定为道光十二年(1832)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见俞樟华、胡吉省著《桐城派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据吴常焘《梅郎中年谱》,则为道光十二年到道光三十年。。梅氏有诗云:“记年十八谒翁时,迢递桐乡感墓碑。昔日语言追悟晚,近来文字就订迟。瓣香自愧无余子,流别争传有大师。定论漫期千载后,喜君先已辨渑淄。”[26]此为感念师恩之作,悔追悟师教太晚,近来始知就订文字,表明他继姚鼐而后自觉承担斯文之统的心意。由此可以看出,梅曾亮有明确的传播、壮大桐城派的责任意识。在京期间,梅氏隐于朝,安贫乐道,专意诗文,赢得京师中人尊敬,如朱琦所谓“迹虽友而心师之”[27]。同时又以古文为系,频繁召集京城文人士子举行集会活动,以文会友,诗酒唱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桐城古文经梅氏之手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发展③梅曾亮在京期间对桐城古文的传播活动具体可参见魏泉《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载《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据《清史稿》载:“居京师二十余年,与宗稷辰、朱琦、龙启瑞、王拯、邵懿辰辈游处,曾国藩亦起而应之。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28]桐城后学更言“我朝之文,得方而正,得姚而精,得先生而大”[29],“时学治古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所传”[30],“天下之文章,固在于先生”[31]。虽然不无夸张,推崇过甚,但也足以想见梅氏在当时的影响以及之于“桐城”的意义。而梅氏在“义理”“文章”上的选择也决定了他成为桐城派性质转变中的关键一环。
关于“义理、考证、文章”,梅曾亮有自己的见解。对于章句考证之学,梅氏早年自道:
间以暇日游心章句,但两载所得,似语无成处者差少,于古人之秘思曲致,未有得也。昔尝谓博闻强识,则所业自胜,今知此自两事。昌黎自谓:“于古人书,但求义理,不暇及名物经制。”此古人之善用所长耳。[32]
此文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梅氏二十四岁,学问尚未成熟,正处于泛观博览的选择期。面对当时炽热的汉学潮,也难免涉足浅尝。而发觉与自身才性不合便从此放弃考证。对于义理与文章,梅氏之侧重与姚、方不同。尽管他也主张文章之道与经义相通,反对范晔将《儒林》《文苑》二分:“至范蔚宗《后汉书》,始歧而二之,而史之例遂沿而不可止,不亦惑哉!然此非独为史者失也,即世之文士,亦群囿于其说而不能自拔。若以文章之道本不可通于治经者,此则学术之异,倍本塞源……”[33]然而“文章”“经义”同兼实为难事,故曰:“昔孔氏之门,有善言德行者,有善为说词者,此自古大贤,不能兼矣。”面对同一困境,二者之中姚鼐选择了“义理”,而梅氏选择了“文章”。故继而曰:“谓言语之无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为言语,亦未可也。”[34]前半句是对文以载道的认同,而后半句则是对文章独立性的肯定。姚鼐、方东树向来喜说前半句,后半句却未尝言过。而至梅曾亮,显然有了文道分离的意图。方东树自言“其文于姚门不及管异之、梅伯言。……吾固深知文,然实无暇致力于此”[20]361-362。管、梅重文章,方氏重义理,方氏一针见血地指明他与管、梅之间的差异所在。从梅曾亮居住京师这段时期来看,他也的确选择了“坦然以文字自期”的道路。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在《赠汪写园序》中议论归有光在“文词”与“事功”中所作的选择,其曰:“夫古之为文词者,未有不言事功者也。至熙甫,而人始以文人归之。”[35]梅曾亮生平十分推崇归有光之文。其以“文人”言归氏,甚有“夫子自道”之意。有学者用“文人情怀”和“学者情怀”区分梅曾亮和前辈方、姚,以为相对于姚鼐深厚的“学者情怀”,梅曾亮此时具的则是“文人情怀”,并由此指出这一时期桐城派的选择是回归“文人”[36]。这的确把握住了梅氏的路径和桐城派从“学”到“文”的走向。
四、文胜于理:作为“文派”的“桐城”
梅氏而后,曾国藩、吴汝纶等继续沿着这条路进行,并彻底改变了桐城派的性质。关于曾国藩与梅曾亮的关系,向来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问题主要出在曾国藩身上,他一面高度赞扬梅伯言,所谓“单绪真传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37],一面又不肯承认受其影响:“余官京师,与梅君过从凡四年,未得毕读其集……”[38]交往四年都不曾毕读梅氏文集,似乎受其影响微弱,骄矜之情溢于言表。彭国忠认为曾氏之所以有此纠结之态,是因为梅曾亮在太平天国时期被太平军尊为“三老”,惹曾国藩不满。直到数年之后,才又逐渐肯定梅氏。但无论如何,曾国藩在古文上受梅曾亮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湖南省图书馆所藏梅曾亮写与曾国藩的十一通书信足以证明①关于两人关系,非本文讨论重点。具体可参见彭国忠《曾国藩与梅曾亮文学关系新论:基于新材料的考察》,《学术界》,2020年第9期;谢海林《曾国藩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之关系发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且梅曾亮在京宣扬桐城古文时期,曾国藩正值青年,是梅府常客,常参加梅郎中举行的文人集会,相与诗文唱和。曾氏尝作《送梅伯言归金陵》:“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碧海鳌呿鲸鱼掣,青山花放水流时。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39]“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明显是对梅曾亮的褒奖,推举其继方姚之后,为嘉道时期桐城古文的领军人物。而“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则显然有承接梅氏接续桐城之统的自任之情。事实上,曾氏甚至有迈过梅氏,直追姬传之心②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然被其好友朱琦揭穿:“自曾涤生……之属,悉以所业来质。”(朱琦《柏枧山房文集书后》)。不过,关于义理与文章的侧重,曾氏的确是沿梅氏一路而来。首先,他在姚鼐所举“义理、考证、文章”的基础上,又加一门“经济”,这是他对桐城派的一大贡献③并非曾氏本人的创造。早前王鸣盛就已经分为四类:“夫天下有义理之学,有考据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词章之学。譬诸木然:义理,其根也;考据,其干也;经济则其枝条;而词章乃其萌叶也。譬诸水然:义理,其原也;考据,其委也;经济则疏引灌溉,其利足以泽物;而词章则波澜沦漪,潆洄演漾,足以供人习玩也。四者皆天下之所不可少,而能兼是者,则古今未之有也。”(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25《王戆愚先生文集序》)。而对于这几者的关系,曾国藩的认识有过变化。曾氏早年“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40]。而后来他却多次强调文道分离,强调文章的独立性:“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家当,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10]587甚至直接了当地说:“仆常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41]为了追求“文章”之境,不惜剥离“义理”。而当初桐城先辈开宗立派,正务以文为器而求理。两下对比,发展至此时的桐城派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其实曾国藩本意并非如此:
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蕴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词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42]
可见曾氏追求的是一种不露痕迹的言理方式,“即将以‘理’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道德修养‘内化’到作者的胸中,使作者之情与所悟之理水乳交融,相合无间,使文学既能表现情感,又能使情感的表现自然地合乎道德理性”[43]。然而如上文多次言及,兼包之境实非常人所能及,在实践的过程中就难免有所偏颇。所以无论如何,对文辞的强调,渴望摆脱义理之束缚成为这一时期桐城派发展的趋势。
由于曾国藩的巨大影响力,他对桐城派的宣扬和再造被后世誉为“桐城中兴”,他所引领的“湘乡派”作为桐城一派的支流反而成为桐城文章的中流砥柱。而吴汝纶作为曾门四子之一,同时又因桐城人的身份,重新把桐城派拉回正轨,成为桐城派新一代领袖。然其道路则在梅、曾的基础上越走越远,用关爱和的话说,可谓是“走向否定的极端”[44]。吴氏不仅多次表示“生平于宋儒之书,独少浏览”[45],“向未涉猎宋明儒者之藩篱”[46],而且彻底将考证、义理排斥于文章之外,其曰:“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者义疏之流畅,训诂之繁琐,考证之该博,皆于文体有妨。故善为文者,尤慎于此。”[47]在吴汝纶看来,文章不再是说经说道的载体,反而说经说道妨碍了文章创作,义理几成文章的罪人。吴氏又云:“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也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48]此与当初段玉裁移形换影的做法蔼然相契。戴震本意以义理为上,段氏虽解其师之意,却偷将“考核”放置于最紧要处。吴汝纶虽言“道胜文至”为上,然“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看似是“文以载道”之说的翻版,言语之间却把“文章”作为了最紧要事。由此可知“桐城”为“文派”之趋势至此已不可挡。所以无论是曾国藩还是吴汝纶,皆开始多从文章立场评价方苞。曾国藩虽盛赞望溪为“一代大儒”,然而却因文道分离的主张对方苞进行批评:“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家当,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10]587吴汝纶接续其师之说,以为“以义理之说施之文章,则其事至难,不善为之,但堕理障。程、朱之文,尚不能尽餍众心,况余人乎!方侍郎学行程朱,文章韩欧,此两事也,欲并入文章之一途,志虽高而力不易赴,此不佞所亲闻之达人者”[49]。以上言论明显不同于姚鼐、方东树对方苞的评价之语。
当此时,已至于晚清。桐城派除分衍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外,又有恽敬和张惠言为首的“阳湖派”,吴德旋门人开启的粤西古文之学,以及严复、林纾为代表的“闽派”等。这些自命为“桐城后学”的文人以文为重,多以“文章”倡“桐城”。如果说桐城派在建立之初尚属“学术流派”,至于此时“桐城学派”已然成为“桐城文派”。尽管吴氏弟子如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又开始讲宋儒之学,提倡文以载道,欲以义理之学施之文章,似又重归原初“学派”之势,然余晖已尽,随着民国时期掀起的文学革命,在新式人物的叫骂声中,桐城派被迫继续身处“文章”领域,在时代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在“文章”路上越走越远,终被后世以纯粹的文章流派视之。
五、结语
桐城派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成为有清最大文章流派,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回到最初,姚鼐欲将“文统”“道统”并举而为一,桐城文学谱系被他建构出来,又高举“义理”之帜以抗汉学,使桐城派得以产生和发展。然而“文”“道”合一的理念却难以落实到桐城诸子的实践中去,兼顾不及,必有所偏颇。“义理”之帜在“桐城”开派初期尤为显著,起到对抗汉学的作用。姚鼐、方东树等皆可谓宋学卫道之士,所以在建派之初,“桐城”的“学派”意义远大于“文派”意义。而至于梅曾亮,却一转桐城派“义理”为重的传统,始“以文字自期”,改变了“桐城”的转向,又经过曾国藩、吴汝纶等桐城派领袖的继续发挥,“桐城”最终完成了从“学派”到“文派”的转变。至于近现代,又自然进入纯文学领域,开派先驱于卫道之士终以文人之姿进入后人视野,似与本意有违,却似乎又是必然之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