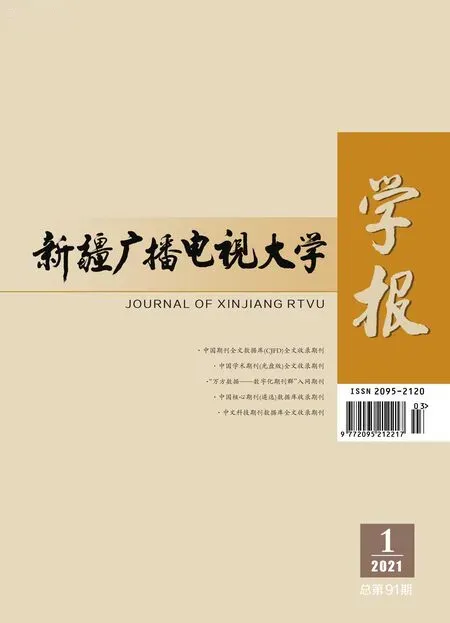论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自然意识
张喜燕
(西京学院,陕西西安 710123)
引言
“自然”在沈从文的小说世界里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有人甚至以批评的口吻说沈从文有“天真的自然崇拜”倾向[1]。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像沈从文这样把小说的社会性母题扩展到对自然的观照、随处关注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在这种复杂关系的展开中把握和阐释人性与人的生存状态,并把这种关系理解为一个民族文化中基础性的二元对立之一的作家,并不多见。从当代人的价值观念看,沈从文在这方面的思考具有突出意义。毫不夸张地说,人与自然的关系,自20世纪后期以来,已成为探讨人类文化及其命运的世界性课题,其重要性还在日益增加。
沈从文对自然的强烈关注带有某种广义的浪漫主义的特征。自卢梭以来,“自然”和“自然状态”成为许多哲学家和文学家心仪的对象。卢梭笔下充斥着“自然”“自然人”“自然感情”和“自然状态”一类词语。他说:“我并不从高超的哲学中的原理推出为人之道,可是我在内心深处发现的为人之道,是‘自然’用不可抹除的文字写下的。”[2]234崇尚自然,是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作家的普遍态度。照罗素的概括,“浪漫主义者注意到了工业主义在一向优美的地方产生的罪恶,注意到了那些在‘生意’里发了财的人的庸俗,憎恨这种丑恶和庸俗。”[2]273这样,作为近代文明的对立物,自然和与其密切相关的人性便开始进入思想者的视野。无疑,沈从文对自然的关切之情同样包含类似的心理。虽然他在《从文自传》里用了很多篇幅述写自己从童年开始就对自然的种种性状产生极大的兴趣(包括形、色、味等),但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更多的是由于后来城市生活的刺激才从理性的高度反思自己这种童趣蕴涵的人生意义。
“自然”一词在中英文中有不同界定,其英文的含义对我们准确理解沈从文的自然观念提供了某些有价值的线索。《现代汉语词典》关于“自然”的释义有三条:一是“自然界”;二是“自由发展,不经人力干预”;三是“表示理所当然”。《新英汉词典》在我们通常译为“自然”的Nature项下,除了“自然界”的含义之外,还有“本性”“人的原始状态”“人的本能或需要”等含义。这样,“自然”这个词便具有了十分浓厚的人文色彩。沈从文的自然观念中同样具有十分浓厚的人文色彩。“自然”在沈从文构建的理想世界中,与湘西人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两者和谐相处的基石。当然,“自然”在沈从文的精神世界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存在。它作为生命的母体与存在处所,一方面博大宽怀,可亲可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3]265。它的和平安详反照着现实空间的剑拔弩张,它的清静幽雅映衬着文明世界的喧闹浮华。另一方面,自然又残忍冷酷,经常给人以不期然的打击,甚至是摧毁。在沈从文看来,自然具有某种神秘的威力,人们可以反抗它,但对其施于人的种种后果却应该坦然接受,这似乎带有某种宿命论的色彩。沈从文这种对自然“既敬且畏”的态度,反映出其某种自然主义的倾向。按照林毓生对“人文精神”的界定,“自然与人的同一”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沈从文小说中的自然崇拜,正深刻地体现出这一点。
一、对自然的认同
湘西由于偏处中国一隅,交通的闭塞造成了生产力的落后,人们靠“天”吃饭,对自然有一种极大的依赖感和亲和力,加之民族歧视和地域观念,历史上湘西作为苗民的聚居地,遭到清乡、改土归流的影响,更使这里成为一个封闭自足的地域系统,因此出生成长在这里的沈从文,受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颇深,并在他的创作中有所反映。在沈从文的笔下,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具有灵性,是生命的自由存在方式,神奇而丰富。自然,在这里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外部存在这一客观意义,而成为与生命紧密相连的有丰富寓意与灵性的存在。
首先,自然的本质是和谐与美,对自然的认同也就是对美与和谐的认同。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令人心怡、近乎完美的,无论急流险滩铸成的雄奇,还是青山绿水造就的柔媚,都浑然天成,没有一丝雕琢的痕迹,更不会带给人任何不适感。“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疏疏的松林……”(《三三》);“虫声像为露水所湿,星光也像是湿的,天气太美丽了”(《旅店》)。沈从文善于从自然中发现美,并将这种美诉诸文字,为他的小说涂抹上一种柔美和谐的色调。同时,自然又博大无边,不可分割,“宇宙是个极复杂的东西,大如太空列宿,小至蚍蜉蝼蚁,一切分裂与分解,一切繁殖与死亡,一切活动与变易,俨然都各有秩序,照固定计划向一个目的进行。”[3]278沈从文从人文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自然界万物都井然有序,自成一体,不需要任何的粉饰或涂改,“边城”世界的清静幽雅、农家生活的恬淡自如像一块块璞玉,恰是因为沐浴了自然的光芒而熠熠生辉。
其次,自然又具有某种神秘性和象征意味。它的生成变动往往暗示着或悲或喜的人性世界的变化。《边城》的结尾描写到在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渡船被冲跑了,山路变成了“黄泥水的小河”,菜园地也被山水冲乱,白塔业已倒坍,一切自然的和谐秩序都被打乱了。显然,这些已成为一种不祥的征兆,老船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去世的。“自然”是神化的产物,是决定一切的外在力量,人接受自然的恩赐或惩罚,形成了沈从文作品中某种程度上的宿命意识。甚至,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有人类早期自然宗教的影子,自然被当作神灵,人们对它顶礼膜拜。他曾写到一个有趣的风俗,人们为了乞求健康,常常拜树木为“寄父”。“一株树或一片古怪石头,收容三五个寄儿,照本地风俗习惯,原是件极平常的事情”[4]321。在这里,自然已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实体,它已被美化和神化,代表一种最高的标准旨范,成为湘西人心目中的图腾,信奉它,就能够带给人平安与幸福。
从人文意义上讲,对自然的这种归属和认同是超验的、神圣的。
但是,人又不仅仅听从自然的摆布,为了生存,人们又不断地反抗,在宿命与抗争之间寻求一种最佳的生存方式,沈从文的小说同时又表现了这种反抗意识。在《边城》中,与自然的搏斗已成为一种“愉快的冒险行为”,“使人见及不能不为之喝彩”;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寄予着人们征服自然的愿望同信心,竞争的胜利者成为“勇武”的象征,并受到推崇,生命在与自然的对抗中焕发光彩。认同自然,但不屈服,敢于抗争,在抗争中磨炼意志,造就健康的生命,这是人文精神最可宝贵之处。
二、人与自然的契合
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自然即神,她无所不包,具有伟大的母性,既孕育生命,又“长养”生命。沈从文不像众多现代作家极力在与自然和社会拼搏中呼求生存的意义,而是让“生命和一切交溶在光影中”,力求生命与自然保持一种既定而安详的和谐,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境界。
(一)自然的人化
自然的人化就是让自然景物带上人文的痕迹,使人同自然契合。用极富人性的眼光看待自然,自然在这种描述下显得安静祥和,宛如具备了人的品性。无论花草树木,还是鸟兽虫鱼,在沈从文的笔下都是可亲可爱的。小狗在广场中央悠闲地散步(《冬的空间》);小牛在田塍上“眺望好景致”(《牛》);“南瓜棚上纺织娘咯咯咯拖长声音纺车”(《萧萧》)。用心观察自然、体悟自然,发现自然的神韵,是人文主义者必须具备的心理基础,沈从文毫不例外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心“总在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4]110,他饶有兴味地描述着自然之物,表现出一种“对‘自然’倾心的本性”[3]268。
(二)人的自然化
人的自然化就是让人具有自然的属性,使人同自然契合。自然是生命本体,生命只有融入自然,才能感受自然,获得升华。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表现的就是人的自然化、生命与自然的融合。沈从文也曾说过,生命“从阳光雨露中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3]284沈从文对那种贴近自然的朴质生活十分赞赏和向往,他认为冷静客观地欣赏自然必然是肤浅隔膜的,只有融生命于自然,才能真正用心体察自然,才能达到那种至真至美的人性最高境界,他的小说集中地体现出这一人文精神。首先,由于自然的影响,人的活动、性情等都带上了自然的痕迹。湘西恶劣但纯净的自然环境潜移默化并沐浴着湘西人的灵魂,使他们的性格中沾染了这种大自然的习性——勇敢、乐观、豪爽。水手们行船时“常用互相诅骂代替共同唱歌”,就是因为受自然限制较多,“脾气比较坏一点”[4]345。除了气候、环境、地形对性格的影响,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自然界还直接作用于生长在山林之中的人物心灵深处,影响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愁。“黑猫”因为“满天的星子、满院的虫声”,“虫声像为露水所湿,星光也像是湿的,天气太美丽”的缘故,而使“一种突起的不端方的欲望,在心头长大”[5]。同时,由于作者情感的渗入,又使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影响到人的情绪。憧憬着爱情的翠翠触目皆是虎耳草的翠绿新鲜;而黄昏日暮,当她一个人体验着“泥土气味、草木气味、甲虫气味”,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漂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时,又想起了死去的母亲,突然感到无边的孤独和“薄薄的凄凉”。[6]人的自然化甚至体现在人名的使用上,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虫一兽,沈从文顺手拈来,皆可成为人物的名字。“菌子”因为长得又瘦又高,象株菌子;“狒狒”形象地勾勒出统治者龇牙咧嘴、耀武扬威的丑态;“翠翠”则是由于“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而随意拾取的名字。
自然化的少女是沈从文心目中最高人性的典范。他不像现实主义作家把女性当作背负着各种社会关系的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梦中的理想,正如他借小说人物之口所说,往往“把心目中所想象的女性清洁灵魂寄托到这个陌生女人身上去”。这些女人皆非某个具体个人,而是提炼所有女人的“好处”铸捏成的“精雕”,她们大多出自山野,带着大自然清新的气息,仿佛是借天地之灵气孕育的精灵,自然赋予她们诸多美好的品质,使她们成为美的最高典范。“翠翠在风日里长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双眸子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边城》)。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以无限贴近自然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采,在他眼里,自然化生的万物都是完美和神圣的,女性由于具备了自然的清秀、甜柔、妩媚等气质,更成为美好人性的象征。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要求及其充分体现,二者相互渗透,自然因为有了人的活动而更加完美,人由于与自然的精神契合而成为美的最高典范。
三、城市:自然的叛离者
人类所置身的世界本无“乡村”与“城市”之分,是历史的不断发展,才打破了单一而固有的农业格局,使城市出现了。城市作为文明的产物与先进的生产力,物质的繁盛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但是文明总是有代价的。人文主义者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入透视现实,他们对都市的异化表现出本能的关注与焦虑,并且不断寻求解决的方式[7]。沈从文在小说描述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人性的戕害。在沈从文看来,与乡村风光优美、物产自足、人性淳朴等文化总体特征相对,在城市里,金钱的地位空前上升,它肆无忌惮地侵蚀着人性,人们在声、色、权、利中挣扎浮沉,城市愈来愈繁华,而人在其中也愈来愈变成非人。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城市作为自然的对照物,作者对其涉及不多,但无论如何表述,他的宗旨只有一个:对叛离自然的都市的厌恶和讽刺。
沈从文展示了异化的自然带给人的不适感。他不像茅盾那样以全景式的勾勒展现都市的复杂形态,也不像以刘呐鸣、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那样刻意捕捉都市充满强烈刺激的感觉和印象,而是以体现人性的变异为宗旨,描绘形形色色的都市文明病[8],与此相适应,“自然”在都市形态下也呈现出一派混乱污浊的景象,此种景象尤其呈现在他反映城市贫民生活的作品中。这里充斥着腐烂、肮脏、混乱和龌龊。“阴沟脏水”散放着臭气(《腐烂》),“野狗”在“广场中拉屎”(《腐烂》),“肮脏的江水逆流入港”(《夜的空间》),还有“一些日晒雨淋腐烂无主的棺材和同棺材差不多的船只”漂浮在江面(《夜的空间》)。更能体现沈从文对这种异化的厌恶,是同一状态(情境)下自然与非自然的尖锐对立。《腐烂》在描写了“难以忍受的恶臭”,肮脏的垃圾堆和满头癣疥的小孩之后,叙事空间移向天空,“天上有流星正在陨落,抛着长而光明的线,非常美丽悦目!”异化的自然,在这里已成为城市腐烂堕落的象征符号,表达出沈从文鄙弃城市文明,认同乡村文明的文化态度。人与自然的契合,不过是要求人类在自然社会中去体现自然人性。沈从文在《箱子岩》中这样描述湘西社会的生活图景:“湘西人在这个地方,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每日看过往船只摇橹扬帆而去,看落日同水鸟。虽然也同样有人事上的得失,到恩怨纠纷成一团时,就陆续发生庆贺同仇杀,然而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4]284这里的人在自然社会中自在自得,宁静和谐,其生命自生自灭,又代代相传。沈从文似乎透视了现象世界中生命运动的轨迹,他将生命的存在投向自然,并将自然看作是一种具有人文意义的文化现象;他要求未来的人们以自然文化为生命归宿,遵循自然规律与生命发展规律,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的状态,以此去寻求生命的永恒意义和终极价值。
在沈从文笔下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湘西人对待自然所持有的非纯粹的功利主义态度。在湘西人的自然观念中,有的是敬仰、畏惧,以及似朋友间的和谐共处、亲人间的相濡以沫。当然,也有从自然获得生存必需品的期盼。这一切构成他们对自然的复杂情感,远非一种单纯的功利主义态度所能概括。重要的是,这种态度包含的人文精神折射出湘西人对于一切相对于个人存在的外在物(包括他人)的态度。按照沈从文的理想,人际关系的纽带不应该仅仅是金钱或其它某种利益,而早期中国社会城市化及商业化进程却恰恰体现为这一点,资本逐渐侵蚀着人性,对此他深怀厌恶与忧虑。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已经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9]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正是人对待他人态度的折射。当人沦落为他人的工具时,自然则沦落为人的工具。沈从文在大城市里的体验(人际的以及人对自然的纯粹功利主义态度)极大地拓展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某种批判性视野,使他在建构自己的理想境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并在这种关系的审视中折射出作家对于人际关系的理想主义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