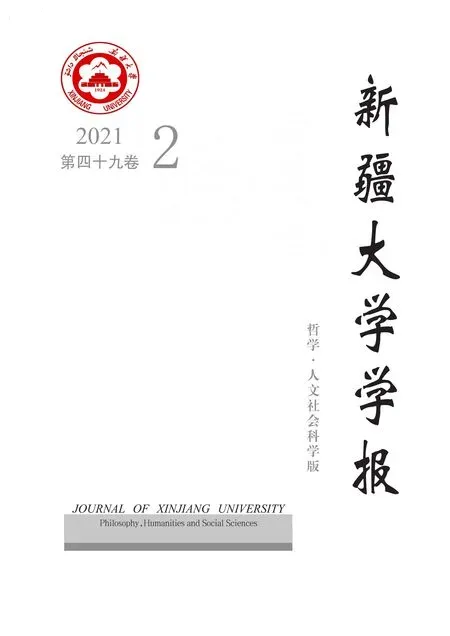隐喻机制:中国现代小说风景书写的一种叙写策略*
郭晓平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271000)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因为对情节的强调,风景常常作为叙事空间和场景,被有限制地书写。直到五四时期,小说家们破除了小说叙事结构的禁忌,建构起以人物心理和环境氛围等为中心的、有别于传统小说的的小说范式。①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8页。这种现代小说结构范式的转型,在理论层面上固然离不开对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借鉴,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却直接来源于小说家在中国现代化语境下的探索和创造。风景书写就是中国小说现代性特征的一种重要体现:一方面它可以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中心,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成为话语表达的载体,饱含丰富的现代内涵。可以说,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风景书写都成为中国小说现代化实践的重要战场。
不仅如此,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风景书写还成为文学实践到达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和策略。正如王晓明所说:救世宗旨和社会担当,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驱力。在近代,“思想启蒙、社会批判乃至政治革命的责任”[1]成为中国文学的历史使命,也影响着作家的文学表达方式。因此,文学实践对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来说,成为救世的手段和途径。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学话语实践的生物链。此时,风景所具有的主客体相召唤、能指与所指相交融的器物性特质,与小说家强烈的话语实践意图“一拍即合”,成为倾注现代话语,表达现代思想的重要选择。被现代话语“发现”和“打造”的风景,最终成为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标志。
但是,仅此还不够。具有了文本的话语预设,还要有读者的接受和响应。这样的风景话语必须能够具有干预力和影响力,才能实现话语实践的目的。为此,小说家们还必须在风景书写的叙事方式和策略上花费心思。风景,这个现代话语的“谜语”,谜面的设计中必须包含着很多的“指向标”,导引读者寻找到谜底。这种“指向标”就是本文在寻找的小说风景的修辞叙事机制。也就是说,作者利用何种叙事策略来完成风景意义建构,同时又能正确引导读者进入风景意义场域,领悟、理解和认同小说的情感态度、道德倾向甚至价值立场,最终达到劝说和说服读者接受道德感化和情感感染的修辞目的。
风景书写的修辞机制提供的就是话语干预和观念表达的叙事技巧和策略,是导引文学实践到达现实实践的一种途径和策略。从总体上来说,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上,修辞维度赋予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景以话语性、认知性和张力性等有别于传统风景的现代特质。
“救世宗旨和社会担当,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驱力。在叙事层面,修辞机制成为风景话语由文学实践层面到达现实实践层面的途径和策略。”[2]在这里,本文无意对风景的话语内涵多作分析,而更关心的是作者如何将丰富复杂的话语诉求编织成风景,又是如何安放到小说的整体建构中。同时,又是如何与读者建立协同和干预关系的。因此,在借鉴以往风景叙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更多聚焦在作者的话语介入和对读者干预的叙事策略上。这为进一步考察风景发生和呈现机制问题,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维度和思路。
在风景修辞策略中,隐喻作为直接介入的劝说性因素,成为很多小说家自觉的叙事选择。它具有的联通外在形态与内在意义的修辞功能,在小说风景书写中不但很好地完成了形式到意义的转化,成为彰显作品主题内涵和作者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重要而有效的修辞手段。而且,形象性的隐喻修辞代替概念性的议论和评说,还为读者理解小说的内在意义,提供了形象化的暗示和引导,最终实现对读者内心活动干预和控制的修辞目的。
一、风景话语的置换机制
隐喻将主观界与客观界、抽象意识转换为形象审美,建构和编织着由人文元素与自然元素相融合,主观界与客观界相渗透,形象性与抽象性完美统一的风景空间。读者被自然审美元素吸引的同时,也会在小说家的隐喻修辞导引下,由客观自然界向主观意识界发生转移和引申,并与自我固有的情感、意识和认知思维方式、经验等相结合,发生联想,产生共鸣,引起思考,并在自我的意识中进行再加工,最终形成读者的自我认知。
(一)文化矛盾架构中的话语置换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耳膜上来。……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3]39(《沉沦》)
郁达夫对自然的迷恋如他自己所说:“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4],而他对日本的风景也是极为推崇:“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獭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与夫岸上的渔户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总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来。”[5]但是,当美丽的风景被置于国家意识和地缘情结的矛盾中,风景中的自然元素与人文元素的错位就在所难免。美丽的自然风景置换为鬼蜮般冷漠的国家权力,最终成为扼杀主人公的刽子手。“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3]75主人公的呐喊回荡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充斥的风景隐喻话语场中,也必将烙印在具有共同地缘情结的读者心中。
这也就是说,在小说中,风景被置于一定意识形态的“文化矛盾的架构之内”,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才能更好的得以凸显。风景此时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历史动力”。这样的隐喻修辞机制“产生于并潜在地重塑人们的体验以及由体验获得认识的方式”[6]85。这样的民族和国家意识,在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中,常常置换为一种风景意象,承载着小说家对民族忧患的焦虑和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想象。中国现代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黄河”、“长城”、“长江”等风景,正是出于民族抗战的宣传或民族价值的认同、民族自信心的召唤、民族灾难和命运的忧虑。
黄河的惟一的特征,就是它是黄土的流,而不是水的流。照在河面上的阳光,反射的也不强烈。……
……常常被诅咒成泥河呀!野蛮的河,可怕的河,簇卷着而来的河,它会卷走一切生命的河,这河本身就是一个不幸。[7]285-286(《黄河》)
在战争语境中,风景所具有的稳定质素被打破,就会使人产生持续的心理焦虑。而激发热情的爱乡爱国“地方感”常被作为建构国族认同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但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萧红的《黄河》将其自然形态与民族象征的意义结合,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和美德的写照,成功将自然家园风景置换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风景。在这里,面对家园沦陷、战火纷飞,萧红有意识地将对民族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忧虑付诸到黄河的意象中,将自然形态的“黄河”,飞升为民族物恋化的对象,完成了“自然的民族化”。同时成功完成了与国族同胞共同的家国情感的链接。
可见,风景与民族、本土、自然的天然联系,使它带有“隐喻的意识形态的效力”。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民族国家危在旦夕。出现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必然带有更为深重的文化政治和权力因素。尤其是当风景被置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夹缝中,其“隐喻的意识形态”特征就更加明显了。
(二)权力关系的辐射与延展
“风景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个动词;风景有为,风景是‘文化权利的工具’,是一种‘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阶级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实践。”[6]12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严格等级秩序的产物,隐喻机制将人文政治与自然风景并置,人文社会成了自然权力关系神秘化的镜像。在物恋化认同的相似层面上把自然风景权力关系的神秘和神圣置换到人文政治中,“天赋人权”随之成为权力话语不证自明的真理。
杨纯站在山顶上,他觉得是站在他们作战的边区的头顶上。千万条山谷,纵横在他的眼前,……冰雪伏藏在她的怀里,阳光照在她的脊背上。瀑布,是为了养育她的儿女……[8]114(《蒿儿梁》)
这是孙犁小说《蒿儿梁》的一段风景描写。出现在这片风景里的自然元素组成了一个关系网:“千万条山谷”高高在上统辖一切,周围是“伏藏在她的怀里”的“冰雪”,为她“养育儿女”的“瀑布”,为她带来温暖的“阳光”……这样的统辖与臣服的意义关联显然表述的是一种权力等级关系。但这只是整个隐喻机制的表层。隐喻机制将喻体与缺席的本体联系起来,自然风景元素的意义关联置换为人的权力关系,缺席的本体于是也在这样的叙事策略中被赋予了喻体所具有的特定意义。当然,将喻体与本体联系起来的工作,也必需有读者的参与。在小说家展开自然风景描写的同时,隐喻机制就已经在悄悄引导着这种意义转换。正是基于人类共同的认知思维方式,读者的经验和知识参与进来,最终完成了意义关联的最后一环。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置换机制,不仅昭示着权力的等级关系,而且还代表着权力的辐射性和延展性。
太阳光像流水一样,从麦田、道沟、村庄和树木的身上流过。这一村的雄鸡接着那一村的雄鸡歌唱。这一村的青年自卫队在大场院里跑步,那一村也听到了清脆的口令。[8]235(《小胜儿》)
在这里,自然元素组成的权力关系网中,不仅有太阳与平原上的麦田、道沟、村庄、树木等组成的普照与被普照、施恩与被施恩的权力关系,而且这样的权力福泽也在扩展和辐射。雄鸡不仅是太阳恩泽的受惠者和见证者,而且是权力真理的传播者。这也就意味着太阳的普照,正在从平原延展和扩大开去。扩展到哪里呢?在这里读者就需要再次上场了。读者的知识和经验,很快补足了修辞机制文本未完成的部分。太阳的恩泽就在读者的大脑里完成了从平原到山岗到高原到大地扩展的宏图。
这还仅仅是隐喻修辞机制的表层。小说家将“雄鸡”与“青年自卫队”并置在一起,静态的隐喻修辞转变为动态的意义传播和扩散,隐喻机制又再次导引读者完成意义的关联。雄鸡报晓本身就是一层隐喻,而“一村又一村”的动态传播态势和速度又成为另一隐喻。具有同样传播动态结构的“青年自卫队”,就在这种紧密的隐喻并置中,成功地呈现出意义置换的强劲态势。最终,在读者的意义联想中得以完成。意图导引如此鲜明和紧密,从而确保意义内涵准确无误地最终传递给读者,几乎没有给读者什么选择性的余地。
在这里,隐喻机制置换不仅发生在喻体和本体、自然风景和人文意识之间,而且最根本的发生在小说家和读者之间。具有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场域、共同的话语诉求,小说家、修辞机制文本和读者之间才会共同的完成了这样的风景修辞叙事。
(三)隐喻本体的缺席
这样的隐喻置换机制也常常需要隐喻主体的缺席来实现。风景隐喻机制中,具有相同的隐喻关系的自然元素和人文元素,被置于密切的意义关联中。而喻体的并置同样带来的是对相似结构中隐喻主体的关注。而人文元素主体的缺席,刚好提示了读者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关注,读者不禁要调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进行联想式的思考和找寻,而在这种思考和找寻中,小说家成功将读者导引到风景的语义场,在意识的碰撞中,将风景的意义关联和内涵传递给读者,从而最终使得缺席的意识形态内涵得以凸显。这种风景修辞的隐喻机制就好像密室寻宝,意义的关联和缺失,都是一种提示和导引,最终指导读者找到意义内核。而读者也在这种游戏中,不断地需要调动自我的知识、经验甚至情感,在不断地参与中最终和小说家共同分享这种找寻机制的快乐。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风景是一个承载了太多政治话语内涵的范畴,甚至可以说,美学风景其实就是政治话语的一种表述模式。伴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景真正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①参见李政亮《风景民族主义》,《读书》,2002年第2期,第79-86页。
二、小说结构的关联机制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景书写中,出现很多自然风景现象的描绘。比如说高山、大风,比如说水、月光、大雪等。这些风景书写不只是审美性的点缀,而是包含着小说家的主观意识和时代观念。但是,如何将意识形态包裹在风景书写中,既具有审美意蕴又能将其中的人文内涵传递给读者,并产生共鸣,这确实考验着小说家们的艺术智慧。
(一)主题内涵的表达主体
风撒欢了。
在旷野,在远方,在看也看不见的地方,在听也听不清的地方,人声,狗叫声,嘈嘈杂杂地喧哗了起来。……而那些零乱的纸片,刮在椽头上时,却呜呜地它也付着生命似的叫喊。[7]369(《旷野的呼喊》)
“风在四周捆绑着他,……树在摇摆,连根拔起来,摔在路旁。……风便作了一切的主宰。[7]393(《旷野的呼喊》)
这是萧红的小说《旷野的呼喊》中的两段有关风的描写。描写风的作品在中国古代比比皆是。比如唐代李峤著名的五言诗《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古今两位作家都在写“风”,仔细比较你会发现,在基本层面上两者的书写手法和技巧都一样:首先就是反衬。在李峤的诗作中,作者用了“三秋叶”“二月花”“千尺浪”“万竿斜”来反衬风的形态和力量。而在萧红的“风”,也是用了大量的事物来反衬“风”的肆虐。“屋顶的草”“墙囤头上的泥土”“鸡和鸭子们”“高粱叶”“灰倭瓜色的豆秆”“红纸片”“树”等事物的形态也都在反衬着“风”。其次,两者都赋予了“风”主体性的行为能力。在李峤那里,风的存在是由树叶等作为证明的,由此,我们才能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在萧红笔下,风的这种主体性更加得到强调,而且被赋予了更多的人的行为意识。
但不同的是,同样是出现在风景画面的事物,风和其他事物的关系是不同的。在李峤诗作中,风与“叶”“花”“浪”“竹”权力等级关系并不明显,仅仅是一种自然事物形态的描写。但在萧红那里,“风”与其他事物之间构成了一组紧张的权力等级关系。“风”是“一切的主宰”,这种主宰权力是建立在对其他事物摧残的基础上的。风景中的事物不是平等、和谐的,而是一种施虐与被虐、欺凌与被欺凌的权力关系。而且,除了“风”之外,被虐和被欺凌的事物都是与乡村生活有关的,是有明显的地域指向的。这样的“风”,不是一般的“风”,而是东北乡村的“风”。这就给“风”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的标签,从而由自然形态转化为人文形态。
(二)与情节和人物的关联比照
风景不仅成为小说主题内涵的表达主体,而且它与情节和人物也形成了某种互喻关联。在小说中,人物刚好也被划分为两类,分属权力主体的两端。两种权力关系并置在一起,就在小说的结构层面上形成了一种隐喻关系,必然发生意义关联。风景和人物互喻的关系中,风景成了某种主题隐喻的喻体,而小说情节和人物成了隐喻主体;在这种互喻中,人被物化,剥夺和抽离了人的资格和权力,凸显的是权力主宰者的暴虐和底层民众如草芥般的生存状况。此时,风景与人文社会互相渗透,从而使得风景由背景的存在,上升为小说主题的表达主体。也正是在这种结构层面的隐喻中,小说家用意识形态的主题观念,将读者层层包裹,在自然和人文的互相渗透中,读者的意识导向被较为严密的框定。从对风的自然现象体验到对权力关系内涵的体察,到结合时代历史对小说主题内涵的最终把握,读者始终被小说家设定的层层隐喻机制的叙事策略所带领,最终达到和作家的意识合谋和共鸣。
“隐喻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诗学问题。”[9]隐喻机制将人文元素艺术化地注入到风景中去,在丰盈风景内涵的同时,也使得风景具有了观念表达的主体性,在艺术作品中最终获得独立的地位。由此,自然的“风”不仅变成了萧红的“风”,而且成了时代的“风”,最终定格为文学的“风”。在读者心目中,生生不息,传唱不止。
(三)风景隐喻与民族历史记忆
这种结构性的关联隐喻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大量存在:
飞速的伸着怕人的长脚的水,在夜晚看不清颜色,成了不见底的黑色巨流,响着雷样的吼声,凶猛的冲了来。[10]412(《水》)
水滚滚的流进来,水流的声响,像山崩地裂震耳的随着水流冲进来。巨大的,像野兽嘶叫的声音吼起来。[10]417(《水》)
丁玲用隐喻赋予了“水”表层和深层的两层含义,同时还赋予了“水”主体性的身份和行为能力。这就使得“水”与劳苦大众在两个层面上形成了权力的紧张和对峙关系,而这两层权力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关系隐喻。自然主体的“水”和隐喻主体的“水”都是权力的拥有者,它们都是底层民众苦难的制造者。在这种隐喻关系的关联机制中,小说家完成了对权力施暴者控诉的政治诉求。隐喻机制将主题内涵鲜明地集中在了“水”上,在自然意象向政治权力的转换中,凸显了小说的主题意蕴。贯穿小说的“水”,作为小说主题表达的独立性主体,成为小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水”于是不仅是丁玲的“水”,而且成为时代的“水”。在文学史上必然留下鲜明的一笔。
在此,丁玲完全具备了新小说家的特质:“正确地理解阶级斗争”“站在工农大众的利益上”“看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11]72,从而获得了批评家冯雪峰的肯定和赞扬。而当时的批评家们对《水》的解读,刚好印证了隐喻机制对“水”的权力政治内涵的成功“易位”和对读者的限制性准确引导。虽然夏志清对丁玲“忘记了在灾荒下灾民的心理状态”,“陷于抽象的概念”,缺乏“对人类生存的具体存在现象”“发生很大的兴趣”[12]193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但是,这对当时面对政治观念的转向,急于找寻新的表述方式的丁玲来说,隐喻机制也许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与此有着相同结构的还有胡也频的《北风里》。
踉踉跄跄地低头走去,仿佛是到了桥边,风力更大了,这因为我向北转,风就是从北面吹来的。……
几乎是两种力相击的形势,我和风,不断的抵抗着,奋勇而终于艰难的迈步;……[13]283(《北风里》)
“风”在这里同样具有隐喻的两重意义,同样与“我”在两个层面上构成了权力压迫关系。“北风”成为承载意识形态主题内涵的独立主体,脱离了自然物象,飞升为具有确定意义的文化权力。“北风里”代表了处在20世纪20年代进步青年共同的文化处境,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感同身受;而在权力压迫下艰难抗争的身影却具有了穿越时代的力量,必将激励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因此,“北风”不仅具有了文化意义,而且具有了文学史意义。
江上横着铁链作成的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终于渐渐吞蚀在夜色中了。
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崖石,激起吓人的巨响。[14](《山峡中》)
湖水被禁固约束,失掉了可以活动的地方,便如一个被幽囚的兽,挣扎着,呼号着—……湖水也这样冲击着堤岸,日和夜,响着波涛忿怒而又空洞的伤激的声音。[13]471(《湖堤上》)
天亮了不久,这个夏天最大的一场雨就下起来了。它吞噬了所有别的声音,自己在屋顶上吼叫着,跳跃着,……[15]91(《七年忌》)
雾的浪潮,一片闷都都的窒人死命的毒气似的,在凄惨的大地上浮着,……[15]598(《鹭鸶湖的忧郁》)
郁达夫对小说中“自然风景和天候的描写”十分重视,这些“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的感觉”,同时“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16]。老舍也在《景物的描写》中指出:自然风景与人密切相关,风景书写“是一种心理的、生理的,与哲理的解析”,“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17]。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雨、雷、雾、电,都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时代氛围、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广大民众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况息息相关。有心的读者必能看到隐藏在小说风景隐喻修辞机制后的颠倒的“装置”,拨开自然风景的云卷云舒,穿越暴雨冷风的层层阻隔,真正感受到时代历史的血雨腥风、风潇雨晦。
与此同时,我们说,中华民族不仅有着苦难深重的历史,更有着为了独立、自由和美好而斗争的不屈勇气和为之奋斗的坚强意志。
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象用黄蜡抽成的丝子,……
太阳一出来了,……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棂,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棂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7]854(《生死场》)
小细蔓的生命力正是茅盾所说的“原始性的强力”,正是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万物永远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正是有了这种“原始性的强力”,一个民族必然会走出苦难的严冬,迎来欣欣向荣的春天。
春天来了,春风带着黄沙,在塬上飞驰;……可是草却不声不响地从这个缝隙、那个缝隙钻了出来,一小片一小片的染绿了大地。……从路边乱石垒的短墙里,伸出一枝盛开的耀眼的红杏,……呵!这就是春天,压不住,冻不垮,干不死的春天。[18]289(《杜晚香》)
三、主观情感的感染机制
隐喻不仅是沟通客观界和主观界的桥梁,隐喻还是主观情感共通性的感染机制。建立在意义关联基础上的隐喻发生机制,将风景建构中包含的丰富人文观念内涵,通过置换、类推、关联等叙事手法,在小说家和读者之间建立了意识形态沟通和共通的交互机制。引起读者的思考,并且使其参与其中;不仅如此,小说家还将丰富的身体体验和情感元素融汇在风景书写中,将自然风景感觉化和情感化,形成了具有强烈主观感受性和体验性的风景隐喻文本。这样的风景文本不仅表现在风景人化和人的风景化双向过程中传递的情感倾向性,更重要的是小说家将这种人对自然的感受和体验,作为共通性的心理感受推己及人,以期使读者感同身受、产生共鸣。
这种“可以群”的感染机制,2 000多年前就已经被孔子所发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何谓“群”?孔安国剖析为“群居相切磋”,朱熹认为“和而不流”。也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交流、沟通思想感情的作用。而隐喻是实现这种感染机制的重要手段。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人类是宇宙间具有最热烈的社会结合欲望的动物”,而且存在着“最多的有利条件适合于社会的结合”,因为“自然”与“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有着“平行的情感或原则”。这是“美感产生的重要的心理条件”[19]。正是人类之间的“平行的情感或原则”,使得隐喻修辞所建构的风景情感密码,可以为读者所感知、感受和感染,从而获得诗意美感。一旦在情感上达到共鸣,风景叙事“倾向性”的价值观念也必然为作者和读者所共有。风景叙事在这种隐喻感染机制中,真正实现了感性情感共鸣向理性观念融合飞升的超越性价值。
(一)喻体的“有意味”选择
小环是一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不知方向,她惊恐的翅膀痉挛的在振动;……[7]8(《王阿嫂的死》)
张地主走来了,她们都低下头去工作着。张地主走开,她们又都抬起头来;就象被风刮倒的麦草一样,风一过去,草梢又都伸立起来;[7]7(《王阿嫂的死》)
后来张地主手提着蝇拂,和一只阴毒的老鹰一样,振动着翅膀,眼睛突出,鼻子向里勾曲着,调着他那有尺寸有阶级的步调从前村走来,……[7]6(《王阿嫂的死》)
小说家用隐喻修辞将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编织和勾连在风景的语义场中,两相比照,突出的是两种元素的相似性意义符码。这种自然与人文同质同构的部分,成为一种意义指向,表达着小说家的主观情感,同时也为读者的阅读接受指引出了意义路径。在这种隐喻机制中,人与自然现象同时出现在风景场中,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中,将一方的意义符码,艺术化地移植到另一方,凸显出两者相似性的同质同构部分。而这种相似性的建构,本身就表达着鲜明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
在以上三个例子中,喻体的选择本身就带有了情感倾向性和价值判断。小环——蝴蝶、农民——麦草、地主——老鹰组成的隐喻相似关系中,凸显出的是人与自然物象的相似性情态和形态话语:美丽弱小者的惊恐,普通民众的软弱,统治者的阴毒。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未曾说出的权力隐喻关系:那就是弱小者共同面对的强权势力。大风——蝴蝶、强权势力——小环组成的这种权力压迫关系,读者在隐喻的逻辑关系中,就能很容易地推导和延展出来。而在这样的意义关联和推导中,风景权力场中的逻辑关系进而转变为一种情感投射关系,也就产生了情感倾向性内容。对弱小者天然的同情、对施暴者本能的愤恨,这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在隐喻关联中被感染和激发出来,作者和读者的情感在风景隐喻场中交汇和激荡。
(二)风景的感觉化和心理化
风景隐喻的情感感染机制不仅体现在对喻体的选择和权力压迫的凸显中,还体现在人对外界自然环境的直接感受中。自然元素通过人的机体和心理的感受机制,直接被转换为带有主观感受的人文元素。而这种主观感受的投射本身含有的情感倾向性很容易被读者所感知,追随作者和叙述人,融入情感和心灵的风景中。
外面冷得非常,……半轮寒月,高挂在天空的左半边。……
他在海边上走了一回,看看远岸的渔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细浪中间,映着了银色的月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里开闭的样子。[3]74(《沉沦》)
郁达夫在这里用了“寒”“鬼火似的”“山鬼的眼波”这些带有强烈感觉色彩和鲜明情感倾向性的词语,在隐喻修辞中将客观风景转换为主观风景,风景超越了客观自在,具有了主观自为性,成为一个感觉化和情感化的风景空间。读者在这样的风景叙事中,不仅由身体体验感知天气的温度,而且由相同的文化元素感知主人公与外在环境的紧张状态。不仅自然是冰冷的,而且人群社会也是吃人的魔鬼。与此同时,在风景由客观向主观不断变换模样的过程中,也会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什么使得给远航者指示方向、带来希望的渔灯,竟然变成了鬼火,招引人们走向死亡呢?甚至连高洁的月光也成了山鬼的眼波,充满杀气。死亡的压迫感无处不在,美丽的风景在主人公眼里变成了鬼蜮世界。其中的转换让人不寒而栗。主人公心理情绪必然形成一种心理威压,向读者扑来,引起读者相似的情感和情绪反应。一旦情绪和情感合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就变成了顺理成章。于是,小说家再次将风景变为鬼蜮世界、主人公遭受冷漠歧视的罪魁祸首指向人文政治,此时,在弱国子民的悲愤中,国家意识最终凸显。“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3]75主人公个体感伤的呐喊必将上升为群体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尊严,主人公的痛苦代表了全民族的痛苦。在这种个体到群体,自我情绪到人文政治的转化中,始终贯穿的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心理机制和共同认可的人文政治观念。正是在这样的情感和情绪导引下,隐喻机制成为一种感染机制,将小说家、主人公和读者联系起来。也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机制的普适性,《沉沦》中主人公的呐喊才具有了穿越时代的感染力。
郁达夫非常喜欢用这种感觉化的风景隐喻策略:
因为这幽暗的天空里悬着的那下弦的半月,光线好像在空中冻住了。[3]172(《怀乡病者》)
他朝转头来看看西南角上那同一块冰似的月亮,又仰起头来,看看那发喇叭声的城墙里的灯光,觉得一味惨伤的情怀,同冰水似的泼满了他的全身。[3]173(《怀乡病者》)
“好像”“似的”“冰似”“觉得”一连串的词汇在这里呈现出极具感觉化的月夜风景。这风景不是被看到的,而是被感觉到的。主人公的主观情绪强烈地投射到了眼前的风景物体上。在空中冻住的光线,冷灰似的街灯,哀寂的喇叭声,冰似的月亮,都是“颠倒”的风景。唯因看风景的人将主观意识投射其上,客观实在的风景,才变成了具有人的感觉化和情感化的主观自为。主人公带着“一味惨伤的情怀”,看到的只能是“冰水似的”风景。
萧红也善于在小说中营造感觉化风景:
雪地好象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刚强。我一直看到那远处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7]225(《手》)
在这里,不得不佩服萧红艺术的敏感性。“雪地”——“碎玻璃”——“闪光”“刚强”——“刺痛了我的眼睛”,这一连串的修辞,其主体还是“雪地”。在这里,萧红赋予了“雪地”,坚硬而能反射阳光的特性,而“刚强”的隐喻,却将“雪地”又赋予了人的品性。在这期间完成了隐喻主体的置换。表面上“刺痛的是我的眼睛”,但其实却是“我”的内心。视觉感觉转换为心理感知。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不仅有闪光的雪地,渐行渐远的王亚明和叙述人驻足送别的眼睛,更为清晰的是弥漫在风景里的对命运多舛的小姑娘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愤慨。在这里,隐喻感染机制将雪景变成了情景,这情景也必将深深刻印在读者的“眼睛”里。
她飘飘摇摇在雪地上奔跑,风在她周围叫,黄昏压了下来,她满挂着泪水和雪水,……[18]250(《在医院中》)
丁玲用隐喻将风雪的冰冷与陆萍内心的冰冷联系在一起,但使得陆萍心寒的却不仅是风雪,还有缺失的喻体。与其说是风雪刺激着陆萍,使得她再次被冷风吹醒,不如说是心里的“冰冷”“呼应”了自然的风雪。所以风会“叫”,黄昏会“压下来”,这些都不只是打在她的身上而是打在她的心里。正是这种心理的感受,不但将风雪的威力放大,而且将人与环境的紧张,(不论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峙放大。那种纠结在风雪中的呼喊,也必然会在读者的心里回荡。
小说中的爱和恨,代表着作家的情感向度和价值判断标准。当自然和心理建立有机的关系,风景最终变成了情景,这种烙印在读者心中才是最美的风景。在中国现代小说中镌刻在读者心里的还有鲁迅《药》里的“死一般的静”,面对“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心中的“悲凉”,周文《雪地》里“白得怕人”的雪、窒息的白雾……中国现代小说中感觉化的风景比比皆是。
小说家们将浓重的主观情感透射在客观风景之中,用隐喻机制在客观风景与主观情感之间架设起情感共融的桥梁,将客观自然转换为主观感受。隐喻机制不仅是读者理解风景的导引装置,而且是感受情感的移情装置。正是有了这样的机制,才能很好地将小说家和读者的自然意识、身体体验和情感心理熔铸在一起,在情感的碰撞和共鸣中,将小说的风景飞升到超越性的境界,浮现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历史中。
四、风景隐喻修辞的发生机制
隐喻修辞机制的发生是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上。基于隐喻的“互动论”认识,我们对小说风景隐喻修辞运作机制的理解也应该看到其复杂性。既看到它是一种认知思维方式,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审美生成方式和文本表述方式。尤其是对小说风景书写的考察,不但要注重其风景建构的自然和人文元素的关系,而且也要充分考虑小说家——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要看到时代的客观因素,同时又要体察到小说家的个性因素。虽然影响隐喻修辞的发生有诸多原因,但归结到一点,就在于它提供了小说家和读者之间产生契合交流的话语场域。
(一)风景话语的“诗性智慧”
话语场域也就是小说家的一种话语编织机制,它实现了中国现代小说主体与风景客体相渗透,小说家的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相交织,审美意蕴与意识形态的有机融合。
小说风景书写的发生正如一切文学艺术的发生一样,包含着审美意识与权力意识、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等双层维度。小说家如何在风景书写中,将两方面有机融合,确实考验着小说家的功力。而隐喻修辞本身具有的体验性和超验性,正好可以承担这样的叙事功能。
隐喻修辞将人与外在环境联系起来,将人作为中介和参照物,以人的感受和体验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从而实现了风景内在的审美意蕴和意识形态内涵的外在化。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古代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在茫然无知时,“人就把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20]。身体不是并列器官的总和,而是“协同作用的系统”,将自己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身体就是“生存的固定形态”,“是认知表达的中介”,是由已知向未知映射、转移的过程。这样的认知思维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修辞过程。但与此同时,这种隐喻指向的是意义和概念世界。这就以人的体验为平台,将自然意象与其背后的超验的意义联系起来,从而将风景的意识形态外在化。
叠锦般的湖波,漾着溶溶的月。雨过的天空,清寒的碧琉璃一般。湖旁一丛丛带雨的密叶,闪烁向月,璀璨得如同火树银花。地下湿影参差,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
……他觉得浸在大自然里,天上,地下,人间,只此一人,只此一刻。……[21](《悟》)
这是冰心的问题小说《悟》中的一段风景书写。《悟》是《超人》的姊妹篇,思考的问题诸如“地层如何生成,星辰如何运转……”依然是人生的意义。但这种基于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风景书写中却被隐喻转换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正是人在自然的审美体验中,主人公得以感悟人生的真谛。所以,夜雨初霁、湖光潋滟的纯净和光明,给了主人公以心灵的洗涤和启迪。只要你打开心扉,心存美好,世界就会报之以温暖,就像主人公投入柔波,全身心地沉浸在大自然中。在这里,人是感知自然和感悟人生的媒介和中介。正是人的体验和体察,将对自然美景的感知和对人生真谛的感悟联系在一起,从此岸到彼岸,最终将自然的夜湖美景上升为人生光明温暖的心湖意象,自然意象最终化为超验性的意义主题,从而实现了主题意蕴与自然审美意识的有机融合和张力平衡。
隐喻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话语表述,这种话语形式中的语词与所指的意义结合在一起,话语本身就构造意义,无需人们进行感知便可以直观地显示意义”[22]。隐喻修辞的体验性和超验性,使得具体可感的自然物象飞升为抽象思辨的意识形态。驻足于此岸而遥望彼岸,立足此在又超越此在,由己知抵达未知。由此可见,隐喻决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同时也是人的自然性和精神性、自在性与自为性、物质性与超越性的双重生存维度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隐喻修辞的体验性和超越性,开拓了风景文本的意义空间。同时,也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实现了和读者的对接。他们或者陶醉于自然美景的审美体验,或者因为其中的意义内涵而引起思考,获得感悟和启迪;在感性和理性、客观和主观等多个方面,与小说家产生共鸣、碰撞,在体悟中不断延展风景文本的意义内涵。
(二)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平衡的深沉焦虑
隐喻修辞主体认知思维的统一性,只是为小说家和读者之间的契合交流提供某种普泛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它还必须具有其必然性。具体到中国现代小说,这种必然性就在于时代具体语境下中国现代小说家们强烈的主观意识和迫切的经世致用的功利意图,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平衡的深沉焦虑。
李泽厚先生在分析儒家的仁学结构时指出:“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23]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舍生取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这些“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体现和传承的都是民族基本观念、情感、思想、态度。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在近现代社会,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为中国的救亡图存而奔走而呐喊。中国知识分子更是走在了“先觉者”的前列,站在各自的文化阵线上,在启蒙与救亡的两个维度上,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
洋务派的“器物改革”和戊戌君子们的政治制度的改良均以失败告终,这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粱启超的《新民说》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思路,奠定了中国近代启蒙主义的基础。虽然康梁变革最终失败,但是梁启超开创的“小说界革命”,却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地位,给了小说以“科学的尊严”。在此基础上,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者提出了“陶铸国魂”,遗憾的是成功的革命却被失败的启蒙所葬送。五四新文化先驱们接过了历史未完成的“人”的解放与觉醒的启蒙任务,同时高举“立人”的大旗,以“人”的解放和觉醒达到整个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与觉醒。正是基于思想启蒙的历史自觉,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相继离开他们最初选定的事业,走上倡导文学,以文学作为启蒙民众、改造国民精神的道路,以图“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
而在这其中,小说成为很多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首要利器。虽然小说产生最初还只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班固《汉书·艺文志》),但是在近代知识分子眼里它却是可以发挥“新人心,新人格”(梁启超《新民说》)的精神教育的作用。而在现代小说家眼里,“小说为文学之大主脑”,更是承担着“改造国民性”、促进社会进步和鼓舞民众士气,抗击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说家们,从开始文学创作,就是有着明确而坚定的创作目的和态度。他们将“文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进而将“文学的世界就等同于现实的世界”,像鲁迅先生那样相信读者会把小说当作现实的复本来读。对读者的期待,或者说对读者的影响力的考量,在小说家们创作之初就深埋在了心里,这成了经世致用,实现改良人生和社会进步功利目的的出发点。
除了“忧愤深广”的鲁迅之外,怀揣这种创作态度的作家还有很多。他们将这种自觉、严肃的文学态度,投射在小说风景书写上,使得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景必然带有了极强的主观性、想象性。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景书写从来都不是纯客观的和唯美的,而是主观的、合目的性的;它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动词,风景的书写和呈现方式本身就是意义建构的一部分。但是,仅仅具有意识形态的功利性还不行,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审美性。也就是说,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强调的正是文学本质复合特性的有机融合与统一,它包含着人类普遍性的情感和诉求,具有超越阶级、集团和种族的倾向和特性。尤其是自然山水风景,作为特殊的审美对象,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必然吸引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愉悦的审美感受中,领悟其中的思想内涵。因此,中国现代小说家们纷纷选择隐喻装置,将强烈的主观意识、社会进步的功利诉求等悄悄转换为自然风景的不同呈现方式,将抽象的观念变换为具体可感的审美对象。这种修辞机制很好地实现了客观的自然风景与主观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架构作用,将意识形态隐喻化的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艺术审美性。
柄谷行人在他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曾经提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个比拟:“在土著的思想中装饰即是脸面”,或者说“装饰创造了脸面”。前者赋予了后者“社会性、人的尊严、及其精神性意义”。脸面和装饰的关系,正是柄谷行人所说的“风景的发现”。[24]46因此,所谓“风景的发现”就是在“颠倒”中发现的“被视为无可质疑不证自明的那个装置”[24]146。在这里,隐喻修辞机制就是发现风景的“装置”之一,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它将素颜的意识形态涂抹上自然风景的万种风情,使得自然与文化、政治、民族国家等人文意识内涵有机融合为一体。读者在感受自然风云的审美变幻中,以小说的具体语境为依托,运用隐喻思维,按图索骥,寻找和感受其中的意义关联,将自然的油彩不断洗刷和剥离,最终到达话语场域,与小说家在精神终点交汇。
(三)“向外转”的慌张
隐喻修辞的延展性和模糊性,扩展了小说风景文本的意义表达空间,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小说家现实经验的缺乏和观念认识的不足。中国现代小说家面对自我的心灵和自身的生命体验,常常有着更深刻和清晰的感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说家本身常常作为隐喻中介的原因。但是,向外转,在面对未曾体验的现实斗争,或者还不够深入了解的政治等方面的意识观念,常常会有手足无措的慌张。隐喻修辞的模糊性,刚好可以营造一定的艺术空间,使其超脱在现实之外,形象化、艺术化地展现抽象的概念和意识,补足现实体验不足的短板。但是,这样也会带来一定的概念化风险。这种隐喻修辞的补足作用,在左翼小说和抗战小说、解放区小说中都会广泛存在。
比如丁玲的《水》,以1931年十六省的水灾为小说背景。但是,这时的丁玲对左翼革命认识很少,更缺乏实际的斗争经验。作为好友沈从文认为丁玲等人的行为“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他们“过分相信革命的进展”……憧憬于“明日光明”,彻底的被“社会革命公式”“弄得稍稍糊涂罢了”[25]。虽然隐喻修辞形象化地表现出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11]72,但是却“陷于抽象的概念,而对人类生存的具体存在现象,不能发生很大的兴趣”[12]558的“席勒化”倾向。“没有生活的真实,只有感情的真实”,“以概念的向往代替了对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斗争的真实”,“以站在岸上似的兴奋的热情和赞颂”替换了“生死斗争中痛苦和愤怒的感觉与感情”[26]。冯雪峰的批评可谓是准确而中肯。对“水”的隐喻修辞,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客观再现的艺术缺陷,但是却也造成了丁玲前期“莎菲式”艺术个性的丧失。
同样的情况,在萧红的创作中也存在。萧红的小说基本都是以抗战为背景,但是萧红始终缺乏亲身参与抗战的经历。甚至当萧军准备投笔从戎,参加抗日义勇军时她极力阻止,认为才华横溢的萧军不值得去战场牺牲自己。考察萧红在这十年的生活,我们发现,萧红的创作生活虽然都是在抗日的时代背景下,她本人也曾在1927年参加过抗日游行,接受过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的洗礼。1933年间在青岛参加了“牵牛房”组织的进步文人的抗日活动,参加为抗日筹款的画会义卖和宣传抗日的“星星”剧团演出。同年8月,二萧还合写了《跋涉》。1938年二人奔赴山西临汾,在李公朴创办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那里创作了《旷野中呼喊》《北中国》等作品,也参与了很多革命活动,但是没有亲身参与抗战却是事实。“一般而论,萧红在《生死场》一书中途转变小说主题,在小说中的一场起义前也未能仔细说明起义的动因,再加上本书最后三分之一笔调的松散,都一再显示出萧红是在尝试着描写她不太了解的题材。”[27]面对直接的抗战经验的缺乏,萧红选择了带有鲜明抗战地域符号的东北,用其恶劣的自然和天候作为风景书写的喻体文本,由自然的暴力造成的紧张关系来比附抗日战争的时代氛围以及外族侵略的血腥和残暴。这是用具体、经验的概念去理解抽象、新鲜的概念,并在两者之间寻找相互的关联,从而达到宏观的、本质性的把握和呈现的目的。这种“概念性的隐喻”和“规约性的隐喻”方法,是有感召力的。它不仅呼应了当时文坛对抗战伟大作品的经典生成的召唤,而且《生死场》被称为“最早出现的抗战小说”而为民众广泛接受。但是,隐喻机制也只能是萧红现实生活经验局限下的无奈选择,也难免存在“概念化”的倾向。
综上所述,小说风景书写的隐喻机制的发生,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从风景隐喻修辞的运行机制来说,它建立在人类共同的认知思维基础上,从隐喻修辞文本建构上来说,其中有时代精神的影响,也有作家个性、经历、艺术倾向等的选择和考量。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现代小说的隐喻风景,不仅具有丰富的意义内涵,而且具有一定的审美冲击力。在保持二者张力平衡的基础上,对不同时代的读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