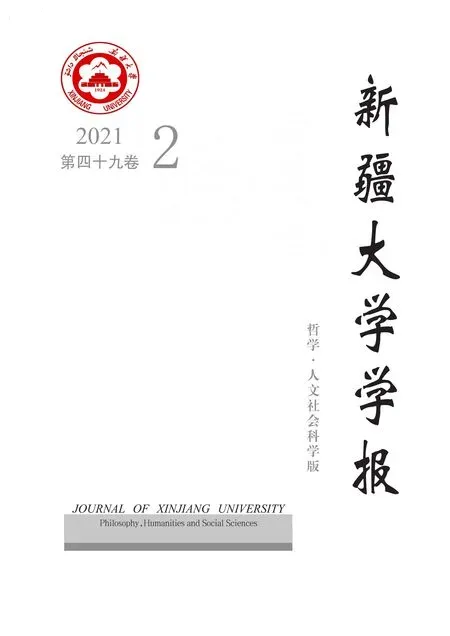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历史变迁、阶层互动与叙事建构*
许多娇,王文奇
(1.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2.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几十年来欧美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涌现出一批比较知名的学者,如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不同学者因研究旨趣与方法不同,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中出现了侧重点的差别,如厄内斯特·盖尔纳在工业社会的来临与民族主义的出现之间建立了关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强调民族的建构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生成,安东尼·史密斯重点研究族群认同中的文化因素与历史记忆等。与这些学者相比,作为历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自己回归历史真实又兼具独到判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①
霍布斯鲍姆的著述甚丰,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持续而深入,在其专著《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方案、神话与现实》(英文题名“Nation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中文译本将题目缩略为《民族与民族主义》)中他着重探讨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变迁及对民族国家的塑造,兼及民族主义向全球的流散;在其重量级的通史性著述“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的前三部,也都辟有专章讨论欧洲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与《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方案、神话与现实》形成相互补充。此外,在其主编的论文集《传统的发明》,在其访谈录《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在其研究工人阶级的专著《劳工的世界:对劳工史的深入研究》,在其评论20世纪文化与社会的专著《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在其发表于《过去与现在》《纽约书评》等报刊杂志的论文或评论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思考与阐释。通过对霍布斯鲍姆这些著述的梳理与分析,我们会发现,虽然霍布斯鲍姆因其通史性写作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但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中真正专擅的是被他称为“长19世纪”(即1789年至1914年)的欧洲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笔者认为,霍布斯鲍姆在对欧洲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与演进的研究中,在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深入分析阐释。其一,通过回归历史事实,看到了欧洲历史变迁中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其二,通过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到了欧洲不同阶层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动与接纳中的共性与差异性;其三,通过文本分析看到诸多“传统的发明”,看到欧洲民族主义叙事的建构性特征。
一 历史变迁与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对现代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现代性是建立在三个基本价值之上的:一是工具理性,二是个人权利,三是民族主义”[1]。现代性指明了一种时间维度,即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古老的现象,而是在历史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因应历史潮流而出现的。霍布斯鲍姆就直言,“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2]10,这是霍布斯鲍姆展开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基础性立场。
确定了从现代主义立场展开分析之后,还需要确定什么是民族主义。为了便于进行社会史考察,霍布斯鲍姆赞同并援引了厄内斯特·盖尔纳对民族主义的界定,即将民族主义作为一项政治原则,“认为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应该是一致的”[3]。这一定性显然只是描述了民族主义的目标指向,并没有给民族主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内涵或外延,也不是一个简约的分析模式,但这正是霍布斯鲍姆选择这种民族主义定性的原因所在。作为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他敏感于历史的流动性,认识到历史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民族或民族主义不可能有一个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避免用先验设定的民族主义概念去划分和推演历史才能更加符合历史事实。霍布斯鲍姆所要关注的是历史变迁中民族主义演进的复杂性及其对民族、民族国家塑造的波折性,用霍布斯鲍姆自己的话来说,“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社会会呈现出力量的拉扯”[4]127。
就民族主义诱发的思潮与行动来说,社会力量拉扯的结果是,在“长19世纪”中欧洲民族主义的内涵随着时代演进产生着变化。霍布斯鲍姆注意到,从宏观层面来看,欧洲民族主义从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从具有限制性的民族原则向不具限制性的对民族自决权的强调的转变。在具有限制性的民族原则时期,能够强调自己是国族、具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国家必须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国家,也就是要求其具有一定的地理规模和人口规模,并且倾向强调该民族要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有独特的民族文学与官方语言。这显然更适合欧洲那些清晰可辨的大国,或者说已经成型的国家。意大利的马志尼被霍布斯鲍姆看成19世纪欧洲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和运动家,只有理解了19世纪普遍盛行的具有限制性的民族原则,才能够理解这位倡导民族独立的代表性人物为何会反对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独立运动,因为爱尔兰被认为面积太小、影响力太弱,不符合当时的民族原则。
根据霍布斯鲍姆的判断,具有限制性的民族原则在欧洲大概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在一百年间,这种民族原则的存在,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民族主义的出现,缔造民族国家的呼声与诉求,在欧洲并不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而是一种建构性力量,民族主义主张是通过民族主义整合民族国家内部各自为政的状态。这一点霍布斯鲍姆基本上承袭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历史进程的判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阐明,民族的整合是一种历史进步,这是“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5]。
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欧洲各国内部也有某些地区在争取自治,但霍布斯鲍姆考察后发现,这些争取自治的运动基本上都没有明晰的独立建国倾向。在具有限制性的民族原则时期,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主张,都没有特别强调单一或纯粹的血统、统一的族裔或语言文化,因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接受的。老字号的民族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无一例外都是多民族、多语系国家。
从19世纪70、80年代开始,情况出现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感到民族主义与他们产生了更紧密的关联,民族原则的限制性开始淡化,即便没有悠久历史、广大地域的政治共同体,也开始努力强调自己的族裔特性,甚至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不仅芬兰人和斯洛伐克人这些此前被认为是‘不具历史’的民族在进行民族运动,像爱沙尼亚人和马其顿人这类除民俗学热衷者外,此前几乎根本无人过问的民族,也开始兴起‘民族运动’”[6]175。
如何合理地解释这种转变的生成呢?霍布斯鲍姆从历史变迁入手寻找原因。综合霍布斯鲍姆在多部著述中的论述,他大概给出了几点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通讯网络的建立,“由于19世纪快速进展的交通与通讯革命,特别是铁路与电报系统的日新月异,即使是最偏远地区的国民,也都被紧拉在中央政府的制度之网中”[2]98,这种更为紧密的关联网络的形成加强了民众之间的直接或间接联系,便于形成更为紧密的共同身份认同;比如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共同市场的扩大,在一些大都会中新兴社会力量在不断壮大,这部分新兴力量的识字率也迅速抬升,他们成为国家或政府要进行社会动员的主体性力量,而国家或政府进行社会动员时,运用民族主义宣传是最佳手段;比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出现,使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增强,同时也使不同的民风民俗和传统习惯产生更多碰撞,在这种碰撞中对其他族群或其他文化群体的区别对待也就更为明显,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这既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欧洲各国仇外情绪普遍存在的刺激因素,也是推动民族主义原则出现转变的重要原因。此外,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欧洲各国的政治民主化以及行政现代化的加速,需要更广泛的民众支持,政府为了获得民众支持需要不断宣传自身代表国家、代表民族,这也促成了民族意识的更广泛的传播。
伴随着民族原则的转变,对民族自决权而且是不设定限制性条款的民族自决权的强调日益占据主导。“1857年时,在19世纪民族主义伟大先知马志尼的构想中,‘民族的欧洲’包括12个相当大的实体。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原则出现了26个国家(如果将爱尔兰包括在内便是27个)。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便说明了新旧假设之间的不同。”[6]174
从大的历史潮流来看,的确出现了民族原则从有限制向无限制的转变。但具体国家、具体地域、具体民众在民族认同上仍旧存在复杂性。因而霍布斯鲍姆还不断在著述中强调那些在民族认同上存在模糊或产生歧义的欧洲案例,比如他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切割得只剩一小块领土的奥地利居民,几乎都举双手赞成加入德国,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么狭小的幅员,能够在经济上存活下来”[2]34;他还谈到在法国洛林,一个世纪内洛林的官方语言和国籍发生了五次变化,农村生活也变成了半城市的工业生活,而一个半世纪里,他们的疆界被重新划分了七次,于是对洛林的民众来说出现了认同上的模糊,“柏林人知道他们是柏林人,巴黎人知道他们是巴黎人,但我们是谁?或者,引用另一次采访的话,‘我来自洛林,我的文化是德语,我的国籍是法国,我用我们省的方言思考’”[7]。正是这种历史变迁中展现出的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才是真实的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经验,也是霍布斯鲍姆作为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之一。
二 民族意识与阶层意识的交错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非常注意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展开对民族主义思潮与行动的思考。在霍布斯鲍姆去世后,罗伊·福斯特在纪念霍布斯鲍姆的文章中曾颇为准确地指出,霍布斯鲍姆历史研究的重要旨趣之一就是“民族意识与阶层意识之间的关系”[8]。
虽然民族主义指向的是一个民族整体或者说整个民族国家的团结一致,但霍布斯鲍姆在研究欧洲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时,通过梳理历史发现,不同阶层对民族主义思潮与行动的推动和接纳存在着差异。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民族主义在欧洲的成型,是伴随着历史著述、文学创作等知识分子的创造物出现的。但知识分子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原初推动力量,原初的推动力量是乡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代言人。①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邦《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75页。知识分子包括哪些人呢?霍布斯鲍姆认为可以包括教师、中下层神职人员、学生等。这些“‘民族理念’的骨干,他们出版民族杂志及其他出版物,组织民族社团,试图建立教育和文化机构,进行各种更直率的政治活动”[9]。
作为民族主义推动力量的乡绅、资产阶级属于经济精英,作为民族主义代言人、宣传者的是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中的一部分又转变成政治精英。当精英阶层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宣称和动员中实现合作时,他们动员的目标指向了中下层民众。这是现代政治动员与前现代政治动员的最大区别,现代政治动员一定要面向所有民众,“一般人民对‘民族’的归属感和效忠问题,变成最重要的政治议题”[2]100。
那么中下层民众对精英阶层进行的民族主义动员反响如何呢?由于19世纪末之前,欧洲“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与学者在记录国家大事的时候,都不曾注意到广大的群众”[4]307,就出现了一种状况,也是底层研究专家斯皮瓦克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发出的重要疑问,“底层能说话吗?”①See Gayatri C.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Can The Subaltern Speak?: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edited by Rosalind C.Morr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p.21-78.霍布斯鲍姆坦承,由于历史上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没有办法书写自己的历史,因而难以对19世纪末之前普通公众对民族主义思想的接受进行具体细微的考察。但根据19世纪末的一些史料,霍布斯鲍姆仍然看到了中下层民众在民族意识上与精英阶层之间的错位。当阿尔巴尼亚的精英分子开始推动民族主义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阿尔巴尼亚平民阶层当中,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出他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认同感”[2]62。此外,如果考虑到“长19世纪”期间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发展在士绅、资本家与农民、工人之间造成了阶层冲突,并且出现了农民反对士绅、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社会运动,不同阶层之间形成紧密的身份认同并非易事。
那么,是否底层就不会与精英阶层共享民族认同呢?也非如此。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仍旧展现出了历史复杂性。我们知道,从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勃兴,同时也形成了跨国工人团体,那么工人阶层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呢?霍布斯鲍姆在其《劳工的世界:对劳工史的深入研究》中曾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移民到波士顿的爱尔兰劳工,和他在格拉斯哥定居的兄弟,和去悉尼的第三个兄弟都还是爱尔兰人,但他们同时也是三个国家不同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假定他们只有对自己国家的民族认同或者假定他们只有对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都是不对的。同样,假定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或对阶级的认同永恒不变也是不对的。”[10]
也就是说,尽管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中下层民众与精英阶层难以共享共同的利益,也难以在很多方面共享共同的经验与情感,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动员对中下层民众效果微弱,毕竟有些共同的文化因素是能够被全民共享的。霍布斯鲍姆认为存在着“民族主义原型”,这是形成民族认同的历史文化基础,在欧洲不同国家,都可以找到“民族主义原型”,比如历史上英明的君主、圣女贞德、古老的传说等,甚至某些宗教传统或仪式也能够形成跨阶层认同,这些全民共同的历史记忆都是“民族主义原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享的民风民俗、生活习惯也是如此,“由于受到18世纪晚期横扫全欧的浪漫主义影响,欧洲各国都掀起一股崇尚单纯简朴以及尚未腐化的乡居生活之风,也开始重新发现不同人群特有的民俗传统,而着手整理方言民谣,更是这场尚古之风的重心所在。这场极富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适为日后陆续崛起的数波民族主义运动,奠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2]124。霍布斯鲍姆在其“年代四部曲”中还都辟有专章介绍文学艺术,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民族凝聚力和动员力不可小觑,尤其在“长19世纪”。因为从文本传播的受众来看,显然文学作品的受众最为广泛,跨阶层传播也最为明显。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中,霍布斯鲍姆谈到,在这一时段内,文学作品与文学家的民族性得到彰显,歌德、席勒等人用德文创作作品,莱奥帕尔迪、曼佐尼创作的是意大利文作品,普希金创作的是俄文诗歌,裴多菲是匈牙利民族诗人。这些文学家、艺术家以其作品参与了民族建构,“公共事务和各类艺术之间的联系,在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或统一运动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尤为牢固”[11]。
由此可见,民族意识与阶层意识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错的情况。民族意识既是全民的,又在不同阶层间有差别。精英阶层的某些民族主义动员未必能够在中下层民众那里得到直接、积极的反馈,但精英阶层与中下层民众仍旧会从共享的历史记忆,共有的风俗习惯,共赏的文学艺术等要素中构筑出共同的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意识与阶层意识的交错,是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中的又一创见。
三 民族主义叙事建构的神话与现实
霍布斯鲍姆除了关注历史变迁与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民族意识与阶层意识的交错,他还十分注意民族主义叙事的建构性。在其主编的论文集《传统的发明》中他之所以使用“发明”(invention)一词,在其《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方案、神话与现实》一书中他之所以使用“神话”(myth)一词,都在指向民族主义叙事的建构性特征。所谓建构性,是指通过文本叙事改变或忽视某些历史事实,形成完整、连续、统一的民族叙事。
霍布斯鲍姆之所以对欧洲民族主义叙事的建构性特征非常关注,一定程度上也是要对之前欧洲历史学家们习以为常的西方中心论叙事进行纠正。正如另一位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重要学者安东尼·史密斯指出的,西方一些历史学家长期保有一种看法,认为西欧的民族国家在18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出现之前就已经形成,但“在西方之外,民族的形成则是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而形成的”[12]。也就是说,这些持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家认为西方的民族是古老的、连续的,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已经形成后的一种思潮,而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意识则是被刻意塑造出来的。这种看法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欧洲历史上伴随着不断的王室联姻和相互征伐,各国边界往往会有多次变动,加之还有持续的个体或群体迁移,使民族主义者所强调的祖国有可能并不是他们父祖的真正生存定居之地。可以说,欧洲各国在民族主义思潮出现之前很少具有稳固不变的民族认同存在。在欧洲真实的情况是,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才开始建构完整、连续、统一的民族叙事,“已有的传统习俗活动,如民歌、体育竞赛和射击等,出于新的民族目的而被调整、仪式化和制度化”[13]7。
霍布斯鲍姆在大学时代就关注到了欧洲历史叙事中的这种“神话”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会对神话与创造进行系统地陈述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学校教师、信徒与僧侣、教授、新闻从业人员、大众媒体幕后的制作人”[4]12。作为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家的志业之一就是要发现“意识形态和政策经常被包装为事实”[14]80。
同时,霍布斯鲍姆对欧洲民族叙事的建构性的关注,也可能与他身为犹太人的切实所感有关。作为犹太人,他明确知道犹太人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意愿是被建构出来的,“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的历史神话和他们返回这块土地的梦想,在19世纪结束之前一直不被认为是一项政治计划……因为他们认为在弥赛亚到来之前,他们还不能返回耶路撒冷。当然,他们相信总有这么一天,而且他们仍然认为弥赛亚还没有到来。实际上,只是在1967年,犹太教内部才第一次具有接受以色列国的倾向,因为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这使他们认为,他们实际上进入了弥赛亚即将到来的时期”[15]38。
在具体考察欧洲民族叙事的建构性特征时,霍布斯鲍姆不断强调其“发明”性。霍布斯鲍姆明确指出,1740年的英国国歌,1790年至1794年的法国三色旗,都是“发明”出来的。“历史连续性也需要被发明,例如或是通过半虚构或是通过伪造来创造一种超越实际历史连续性的古老过去。”[13]8霍布斯鲍姆对欧洲国家建构历史连续性叙事问题,进行过多个案例的考察。比如从历史来看,雅典从来不是希腊的首都,但是当希腊在1832年宣布独立时,“有些人要求回到那种与真实的历史没有太大关系的显赫过去,于是选择该城作为首都”,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过去被重新设计了”[15]42。
在欧洲一系列的“发明”性、“神话”性叙事中,霍布斯鲍姆关注最多的是对语言共同体的强调。语言共同体曾被18、19世纪欧洲的一些思想家作为识别民族的首要要素。比如被后来学者认为是民族主义思想先锋者之一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就曾在18世纪晚期强调语言民族主义。以赛亚·伯林对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过总结性评述,他认为在赫尔德看来,“同一个民族的人说共同的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习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传统”[16],共同语言的重要性被排在了首位。但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语言只是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诸多标准之一,语言并非最主要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区分不同民族的要素。
霍布斯鲍姆承认欧洲地方语言的使用在19世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他指出,只有当地方语言具备能够动员大众的能力时才会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强调,才有可能成为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本民族语言,进而成为国语。从社会史角度来看,欧洲各地方语言成为各自民族语言,还要与印刷术的推广,识字率的普及,教育的大众化发展结合在一起,19世纪及之后确立的民族语言并不是自始至终就作为民族语言而存在的。即便一种民族语言确立了其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崇高地位,也不意味着这种语言真的就在19世纪形成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全民通用。霍布斯鲍姆举例说,即使在意大利建国的1860年前后,“也只有大约百分之二点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意大利文”[2]70。此外,在欧洲还存在一种奇怪的历史现象,即一国的文献记录或民族动员有可能是用另一国的文字书写的,比如“芬兰文学会里的各种文献记录,也都是以瑞典文写成;甚至芬兰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大师斯奈尔曼,也是以瑞典文撰写其著作”[2]125。
所谓语言共同体,所谓民族语言的一致性,在霍布斯鲍姆的分析下,显示出这是民族主义者们在19世纪对历史进行的刻意的人为建构,同时也使我们知晓直至今日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仍对欧洲的历史真实刻意掩饰。通过对欧洲民族主义叙事的建构性的关注,霍布斯鲍姆将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行了呈现,也把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推进一步。
但需要指出的是,霍布斯鲍姆根据欧洲历史经验和研究专长所得出的是对欧洲“长19世纪”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精辟分析,这不代表他得出的结论能够同样适用于亚非拉所有国家。如果说到民族的古老和连续,事实上亚洲一些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国家要远比欧洲更胜一筹。霍布斯鲍姆就承认,“像中国、韩国或日本,其组成分子的同质性之高,在历史上倒是相当罕见的”[2]76。霍布斯鲍姆提供给我们的思考,不是提供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分析模式,而是通过对自身真实历史的梳理和发现,寻找到深入研究某一区域或某一国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