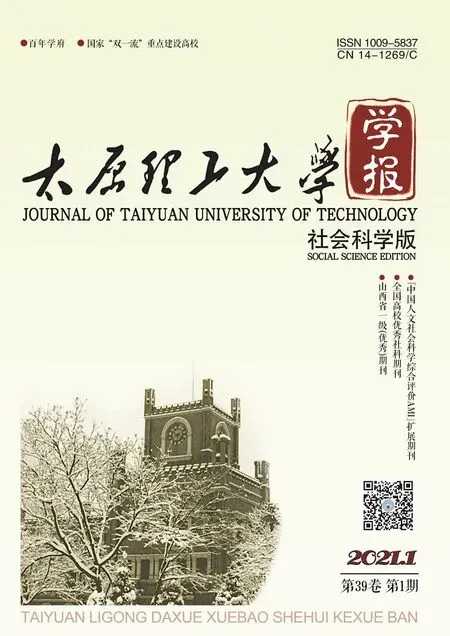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的逻辑进路
苗贵山,王婧然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一般来讲,政治哲学探讨的是国家对待其公民的道德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何种社会秩序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国家依据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来组成,以及国家作为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就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来讲,是把意志自由看作人的本质,强调善或正义就是具体自由的实现,而具体自由就是君主立宪制政体范围内,市民社会成员个体的主观自由得到国家法制的保障与政治国家的客观自由得到个体的尊重的有机统一。进一步讲,个体的特殊性自由必须以政治国家的客观自由为普遍性精神的向往,个体的特殊利益必须以促进政治国家的普遍利益为活动的目的。这就是黑格尔所诉求的自由的国家伦理。黑格尔自由的国家伦理促使“《莱茵报》时期”初期的马克思对之热情洋溢地赞誉。但是,随后马克思在思想上经历了黑格尔自由的国家伦理精神与现实的物质利益的纠缠,由此在思想上遭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从而产生了对作为个体自由与利益体现的市民社会与作为普遍自由与利益表征的政治国家之间究竟谁是谁的决定者的“苦恼疑问”[1]2。马克思对“苦恼疑问”的思考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原则的前提,这就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与法哲学置“现实的人”的利益于不顾的缺陷进行法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性分析,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理论原则。循此认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开始对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政治解放的本质进行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批判性分析,由此产生了对政治解放所宣示的普遍的人的解放与它确立的政治共同体宣布其成员享有利己主义的权利之间的矛盾的“困惑不解”[2]185。“困惑不解”为马克思由对国家与法等“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市民社会这一“原本”的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批判性分析提供了理论研论的动力,这一转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实现。在其中,马克思通过对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进行细微的政治经济学剖析,得出了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又是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结论,这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端。异化劳动的现实意义在于表明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中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成正比,对此马克思称之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所造成的“历史之谜”。而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2]297。这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做了理论准备。由此我们可以说,从“苦恼疑问”到“困惑不解”再到“历史之谜的解答”,构成了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的逻辑进路。
一、“苦恼疑问”:黑格尔国家伦理遭遇私人物质利益纠缠的痛苦情绪
古典自由主义强调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以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即不受侵犯的“消极自由”为原则。为了保障这种“消极自由”,主张个体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来组成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国家是实现人的自然权利这一目的的单纯手段。对古典自由主义把人的自由权利自然化、国家组成契约化及国家手段化的做法,黑格尔甚为不满。他站在思维与存在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立场上,把绝对精神理解为其自由本性的自我实现过程,一方面实现了对自然权利论进行现实化与历史化的“改造”,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社会契约论任意性不满基础上的重构。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的进展阶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程是“精神”作为抽象的、可能性的或潜在力的“自由”隐没于“自然”之中,“自由”是“精神”存在的依靠特质,“精神”也知道自身是自由的,只不过最初自由是潜在的或可能的;第二阶程是“精神”与“自然”发生分离并与“自然”相连而发展成为特殊的自我意识,“精神”以人的激情和欲望等主观性的东西作为实现其自由的手段;第三阶程是特殊的自由意识提高到了普遍性的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它以国家这一伦理实体作为自己的实现形态,国家是客观意志自由的存在,自我意识作为主观意志自由融入其中,因而国家是道德的“全体”,是具体自由的“现实”。这里,绝对精神运动的第二与第三阶程,若与《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人的意识发展的六个阶段——“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客观精神、宗教和绝对知识”相对应的话,第二阶程对应的就是作为“主观精神”的“意识、自我意识、理性”这三个阶段,第三阶程对应的就是“客观精神”的阶段,也正是在主观精神发展过程中,以及在主观精神向客观精神迈进的过程中,自我意识作为“苦恼意识”这一痛苦情绪而出现,实质在于它认识到了自身作为特殊性与普遍性实体之间、变动不居与永恒不变之间、非本质的现实性与本质性之间的对立,因而自我意识要努力达到普遍性、本质性与永恒性。当然,在黑格尔那里,“苦恼意识”是历史发展着的,在“主观精神”阶段,伴随着主奴关系产生的自我意识便是“苦恼意识”,在“主观精神”向“客观精神”迈进的阶段,作为自由意志进一步规定的“法权”意识(平等的人格、对物的占有的所有权尊重、契约与交换基础上的公共生活的法则)仍然是基于自身所感受到的自身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实体分裂的苦恼意识。于是,黑格尔基于个体与国家相互承认的理论指出“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以此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位:一方面,个人的自由的人格权利在市民社会领域中获得明确的承认的同时,其特殊利益获得完全发展;另一方面,个人承认把国家作为自己实体性的普遍精神并认识与希求它,个人通过自身利益的实现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甚至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这才是自我意识在市民社会中作为“苦恼意识”的痛苦情绪的化解,也是国家力量之所在。这样一来,黑格尔不仅完成了对自然法理论的历史化与现实化的改造,也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基于国家与个体相互承认基础上的和谐关系,而不是对抗关系上的重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他下决心去研究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问题而产生的“苦恼疑问”,在本质上就是黑格尔所认为的在作为“客观精神”的抽象的法、道德与伦理阶段,作为原子式的个体的自由意志进一步规定的法权意识所感受到的自身作为特殊性与普遍性实体相分裂的痛苦情绪即“苦恼意识”的直接再现。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是要寻求一个绝对的共同体来消融特殊的主观自由与普遍的客观自由之间的对立。因此,马克思在其整个理论活动中对黑格尔所倡导的伦理国家的思想都是钟情的。从理论活动早期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到《论犹太人问题》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理论活动中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共产党宣言》,直至《资本论》及其手稿,我们都可以从中窥见黑格尔的国家伦理。既如此,马克思才拿它用来观照现实,要求现实要趋向理想。而当现实达不到理想要求时,思想中的痛苦情绪即“苦恼疑问”就会随之产生。具体来讲,马克思最初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的国家伦理进行了积极肯定。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赞扬黑格尔从整体的、自由的、法律的角度来论证国家,并像黑格尔那样,“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3]228。在“《莱茵报》时期”初期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提出国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主张。即使是之后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看到了黑格尔的国家伦理受到林木所有者私人利益的冲击而使其理性的光辉黯然失色时,马克思仍然还强调用国家伦理来解决每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斥责颓废的私人利益为“下流的唯物主义”,以此来彰显黑格尔的国家伦理的理性光辉。但是,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发现政府当局并没有打算消除葡萄种植农民的贫困,从而把农民的贫困归结为政府管理的贫困,在触怒了政府致使《莱茵报》被查封时,马克思才开始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产生了怀疑,由此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产生了“苦恼疑问”,即到底是理性国家统摄市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决定理性国家。此时,马克思朦胧地意识到,人们在研究国家问题时很容易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而忽视了所存在的客观关系(利益)对私人与政府当局的行动的制约作用。
在“《莱茵报》时期”与“《德法年鉴》时期”之间,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舞台退回到了书斋,通过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与法哲学的批判,在“苦恼疑问”的解答上开启了对现代政治国家问题的法哲学思考,追问政治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与本质。对政治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把它明确为私有财产,正是私有财产决定私人与政府当局行动的“关系”。马克思赞赏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分离的观点,但并不苟同他所主张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他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家庭与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的规定者被设定为被规定者。所以,马克思指责黑格尔没有阐明官僚政治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内容,而只对组织形式做了阐释,换句话说,官僚政治“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2]59。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的“伦理国家”就是一种“国家形式主义”或“国家的唯灵论”[2]60,它根本不能解决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具体的统一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伦理国家”的精神形式表示了失望,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丢掉黑格尔的“国家伦理”精神内容。在之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否定私有财产而寻求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具体的统一,从而开辟了与黑格尔囿于私有制而寻求国家伦理实现的不同路径,这也构成了马克思终生的理论研究方向。
二、“困惑不解”:政治国家的普遍性是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的虚幻呈现
正是认识到黑格尔的官僚政治在本质上以私有财产为原则,而在形式上表现为“国家的唯灵论”,所以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必然会转化为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制度及其唯灵论本性的政治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正如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一样,普遍事物的被意识到的真正的现实性只是形式的,或者说,只有形式的东西才是现实的普遍的事物”[2]80。这里,马克思所言的“普遍事物”指的是政治解放所确立的现代国家从理论上讲应当维护普遍的人的利益,或者说以普遍的人的解放为目的。这应当是“被意识到的真正的现实性”,但是在市民社会中“被意识到的真正的现实性”只是形式的东西。现代国家并没有真正地实现普遍的人的利益或解放,换句话说,现代国家只是把形式的东西当作现实的普遍的事物来对待。因此,在“《德法年鉴》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认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解放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政治解放只是市民社会中的有产者这一部分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鼓动全社会的人起来去从事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革命,它所诉求的权利还只是历史性的权利,或者说这种权利还只是有产者的权利,而不是普遍的真正的人的权利。对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称这是他“困惑不解”的地方。这种“困惑不解”在本质上是他在“《莱茵报》时期”遭遇到的黑格尔的国家伦理与私人物质利益纠缠时所产生的“苦恼疑问”的现实性继续,展现为政治国家的普遍性是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的虚幻呈现。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产生的“困惑不解”,其现实根源在于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政治解放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表现为政治解放造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离,以及如此相对应的人的身份及其活动的二重化。人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法人”(公民)身份与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私人”身份在分化的同时,人在“政治共同体”中过着普遍的类生活与在市民社会中过着特殊的尘世的生活。类生活是人按照自由与平等的政治精神所参与的政治共同体的普遍事务,因而人是社会存在物;尘世的生活就是人按照利己主义的原则所参与的基于自身需要与享受的交换活动,因而人是尘世存在物。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生活是“国家唯心主义”的完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自由与平等为内容的政治精神脱离了人的私有财产、出身等级、文化程度与职业的差异等现实的非政治差别的内容,而把人作为抽象的公民来规定并使之参与普遍的政治生活,享有政治权利。人的尘世生活是市民社会的抽象的“唯物主义”的完成,享有私人权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间都把对方看作是实现自己利益目的的工具。
显然,政治共同体中的“国家唯心主义”与市民社会中的抽象的“唯物主义”是对立的。马克思指出,这是现代性的弊病所在,是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在心理上与理论上的“谜”,而谜底就是现代国家从形式上讲是为了保障其作为公民的所有成员的普遍利益,但是从内容上讲是维护和实现有产者利益的政治组织。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中人们所诉求的包括自由、平等、财产与安全在内的自然权利,从实质上讲是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自由就是在独立地享有自己财产的基础上任意地处理自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权利,这是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平等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作为独立的原子,法律所规定的人格上的同等性;安全就是上述权利必须得到保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认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政治解放还不是普遍的、真正的人的解放,它所诉求的权利还只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社会中有产者的一种历史权利,不是所有人的真正的权利。也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颠倒了人的普遍解放这一根本性目的与私有财产的解放这一手段的关系,抑或说政治解放在实践中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这是导致马克思“困惑不解”的根源所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要想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必须超越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解放,为此必须探讨谁是解放者、为谁解放、解放的条件这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既然资产阶级是政治解放的解放者,那么与此对应的无产阶级就是人类解放的解放者,是为了实现作为无产者的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而要实现人类解放,必须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为此,马克思以卢梭的“公意”口吻讲道,要实现人类解放,个体必须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赋予人的抽象的公民身份复归于真正的类存在物,也就是把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变成类生活、类劳动与类关系。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在制度上敢于为人民请命,通过改变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使得单独的个体成为国家整体中的一部分,个体从整体中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在实践中所造成的政治国家的普遍性是市民社会特殊性的虚幻呈现的弊端。
三、“历史之谜的解答”: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对于“《德法年鉴》时期”针对政治国家的普遍性是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的虚幻呈现而提出的“困惑不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它继续深化为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所造成的“历史之谜”。对于政治国家的普遍性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的虚幻呈现,马克思将其进一步解释为:“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2]302。这里,马克思所讲的“普遍意识”指的是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的普遍的自由意识,但是“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2]296。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由的普遍意识只是资本统治下的现实生活的抽象,而资本统治下的现实生活就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劳动异化的呈现,这是资本与劳动矛盾运动的结果,因而对劳动来讲,异化劳动体现的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马克思称之为“历史之谜”。马克思从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与人格化的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把资本所造成的异化劳动的“经验”与异化劳动的扬弃所诉求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人的“类特性”理论相结合,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这一“历史之谜的解答”。“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297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一“历史之谜的解答”的论断,从理论渊源的角度讲,是集恩格斯的“两个和解”与黑格尔的“两个公设”的理论于一身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针对康德政治哲学只讲意志自由的自我同一性而丢弃自然的客观性内容,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没有内容的形式”所导致的个体意志自由与自然情欲的割裂、个体的特殊的主观性自由与共同体的客观的普遍性自由之间统一缺乏自然的客观性内容这两方面的缺陷,提出了“两个公设”。“两个公设”是在道德与客观自然之间、道德与感性意志之间设定的和谐,而“现实行为的运动本身”是联结“这两个设想的中项”[3]292。前者讲的是个体的自由自律的道德与个体本身的自然欲求不能割裂而要和谐统一;后者讲的是个体的自由自律的道德与他人的感性意志的自由不能割裂而要和谐统一。“现实行为的运动本身”作为联结“两个公设”的中项,讲的是作为自由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实现的自我运动,它与自然相分离并与自然联结,从而以人的自然欲望为手段,最终通过自己的劳作而达到道德与客观自然之间、道德与感性意志之间设定的和谐。对此,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绝对精神与人的自然欲望作为历史的经纬线进行相互交织,从而描述了作为自由的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世界历史的进程,即从绝对精神作为潜在的自由,发展到与自然相分离并与自然相联结的自我意识,再由作为特殊性自由的自我意识提升到普遍性自由的高度。而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从作为与“主观精神”(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相对的“客观精神”(抽象的法、道德、伦理)的运动来把善看作是具体自由的实现,而具体自由就是作为个体抽象的自由人格与平等相待的道德相统一的个体的主观自由和特殊利益与共同体的客观自由和普遍利益的有机统一,也就是个体与共同体具体统一的国家伦理。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实体即主体”方式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实现的自我运动的哲学遭到了恩格斯的批判。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曾指出:“边沁在自己的经验中犯了黑格尔在理论上犯过的同样错误;他没有认真地克服二者的对立,他使主语从属于谓语,使整体从属于部分,因此把一切都颠倒了。”[2]545-546这里,恩格斯所言的边沁与黑格尔所犯的同样错误,指的就是他们企图在承认私有制原则的基础上来调和个人特殊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的矛盾,但都没有真正克服这一矛盾。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对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个人特殊利益与作为人与人关系的社会普遍利益的统一抱有渴望之情。这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把国民经济学所论证的个人利益看作是社会普遍利益的链条,从而提出“两个和解”的主张得到了印证。恩格斯针对国民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在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私人利益的相互吞噬的社会现实,提出“两个和解”的思想,“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是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2]449。
黑格尔的“两个公设”与恩格斯的“两个和解”,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这一“历史之谜的解答”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前提。但是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包括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的哲学是从“天上降到人间”,从意识出发来解释社会生活,而不是用社会生活来解释意识。尽管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但是他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绝不是唯物主义者,他把自然与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没有理解为感性活动,因而他不懂得感性的实践活动在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统一中的革命性意义,当然也就不懂得从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只能求助于宗教式的“爱”。在这方面,黑格尔要比费尔巴哈深刻得多,正如恩格斯所讲,黑格尔的自由的绝对精神的运动的哲学是以强烈的历史感为基础的。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历史感的基础首先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劳动理解为外化范围内的人的自为生成,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是消极的一面是黑格尔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也就是说劳动在黑格尔那里,只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所凭借的手段。但是,黑格尔对马克思立足于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从而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理论贡献,不仅仅在于黑格尔把外化的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更为深层次的地方在于:一方面,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市民社会的时候,不仅仅是把它作为需要的体系来阐释,更为可贵的是他看到了市民社会中存在的由于私人利益的竞争所导致的财富不平等的积累,以及工人阶级的贫困等现象,这为马克思论述工人的异化劳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黑格尔也是受到了国民经济学在这些方面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的思维范式,为马克思站在劳动的否定之否定的角度论证共产主义也有着直接的作用,即正像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所造成的自我意识的虚假性,而在对古希腊社会中自我意识的普遍性进行肯定的基础上论证自我意识的伦理性一样,马克思立足于私有财产运动的经验事实,首先设定“自由的有意识的人的活动的人的类特性”(肯定),然后到从资本主义“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论证异化劳动(否定),最后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否定之否定)。作为否定环节的异化劳动的消除,就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环节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实现,它是资本主义财富生成(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与分配(人与人的矛盾关系)环节的矛盾的解决,因而也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所造成的“历史之谜的解答”。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私人劳动,而是联合劳动。劳动进入了公共的政治生活领域,它不再被资本所支配,而是被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自由地支配。
四、结语: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共同体与个体关系合理化何以可能
综上所述,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的逻辑进路展现为一条清晰的路线图:由法哲学批判意义上的“苦恼疑问”发展到政治学批判意义上的“困惑不解”,最后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历史之谜的解答”。自休谟以来,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共同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就构成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休谟以同情心的道德感将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耦合起来,卢梭则以公意将共同体与个体联结起来,康德则以纯粹的自由意志来祈求特殊利益服从普遍利益,黑格尔则以理性的国家伦理来调和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对于马克思而言,寻求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共同体与个体关系的和谐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其理论建构的终极目的。初涉社会的马克思以黑格尔的理性的国家伦理来寻求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一致性,但遭遇到了私人利益的拷问。“苦恼”的理性最终使得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以私人利益为原则的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根基,黑格尔的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理性国家只是从表面上来实现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共同体与个体关系的和谐,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所确立的政治国家在宣言的层面上以普遍的人的解放为口号,但在现实中却是特殊的有产者的解放。对政治解放的“困惑不解”使得马克思探寻实现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共同体与个体关系的真正和谐的途径。通过对国民经济学所追逐的私人利益,以及私有财产基础上所产生的异化劳动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找到了解决“困惑不解”问题的方案,即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确立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所实现的普遍利益不再是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确认的单个的私人利益的集合体,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通过自主性劳动的联合来共同享受其劳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