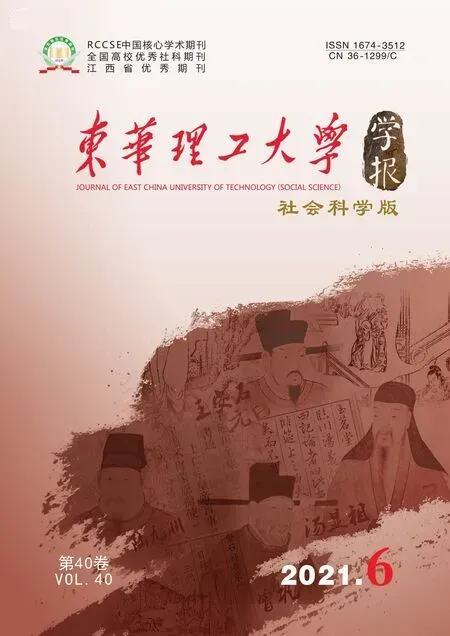陆学与禅学之辨
蒋九愚, 宋 从
(1.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2.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陆象山(1139—1193)与朱熹(1130—1200)是南宋著名思想家,其二人重建的新儒学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极大,其二人学术思想上的异同之辨,也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学术公案。朱、陆异同之辨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儒佛异同之辨。宗朱子学的明代学者陈建在《学蔀通辨》中指出:“朱子未出以前,天下学者有儒佛异同之辨,朱子既没之后,又转为朱陆异同之辨。”[1]113“若不辨陆学与禅佛同异,而徒与朱子较同异,已落在枝节,非根本之论也。”[1]184陆学与禅学的异同问题,成为朱陆之辨的焦点,影响深远。本文立足历史事实,摒弃历史上朱陆之辨中的学术门户偏见和当今继续捍卫这种门户偏见的立场,力求客观全面展示陆学与禅学的关系。
1 陆学:“全是禅学”还是“孟氏之学”
从历史上看,在朱、陆论辩中,双方批评对方都是禅学。在陆象山去世后,朱熹批判陆学更加坚决。明代陈建在《学蔀通辨》中说:“朱、陆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没之后,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1]111朱子反复指责、批评陆学“全是禅学”:
近闻陆子静(按:陆象山)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也。然想其说方行,亦未必肯听此老生常谈,徒窃忧叹而已[1]23。
如陆氏之学,在近年一种浮浅颇僻议论中,固自卓然,非其畴匹,其徒传习,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间者。但其宗旨本自禅学中来,不可揜讳。……陆子静所学,分明是禅”[1]138。
朱子公开指责陆学“全是禅学”“分明是禅”的观点,极大地左右朱子学继承者对陆学的评价,当时“天下皆说先生(按:陆象山)是禅学”[2]425。明代宗朱子学的陈建编撰《学蔀通辨》,严厉批判陆象山“援儒言以掩佛学之实”[1]110“分明是禅”:
自老庄以来,异学宗旨,专是养神。《汉书》谓佛氏所贵,修炼精神。胡敬斋曰“儒者养得一个道理,释老只养得一个精神。”此言实学术正异之纲要。陆象山讲学,专管归完养精神一路,俱载《语录》可考,其假佛老之似,以乱孔孟之真,根底在此。而近世学者未之察也[1]113。
陆学下手工夫,在于遗物弃事、屏思黜虑,专务虚静,以完养精神,其为禅显然也[1]111。
象山师弟作弄精神,分明禅学,而假借儒书以遮掩之[1]152。
面对朱熹及其后学的批评,陆象山及其后学也不甘示弱,反复申辩陆学不是禅学,而是继承并弘扬孔孟道统的“圣学”。陆象山认为自己的学术思想来源并非始自佛教,而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2]471。检阅陆象山言论,他确实在阐发自己思想时大量引证《孟子》,这表明他非常自觉地以《孟子》作为自己学术思想的经典依据,“因读《孟子》而自得”并非全是虚语。陆象山曾在无极、太极之辨中公开反击朱熹平时“私其”禅学“以自高妙,及教学者,则又往往秘此”:
尊兄(按:朱子)两下说无说有,不知漏泄得多少。如所谓太极真体不传之秘,无物之前,阴阳之外,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语,莫是曾学禅宗,所得如此。平时既私其说以自高妙,及教学者,则又往往秘此,而多说文义,此漏泄之说所从出也。以实论之两头都无着实,彼此只是葛藤末说。气质不美者乐寄此以神其奸,不知系绊多少好气质底学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行一言之过,兄其毋以久习于此而重自反也[2]30。
陆象山指责朱熹在无极、太极之辨时,实际上落入了佛教“不属有无”的禅学思维(详见后文分析),“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行一言之过”,其原因在于朱熹久习于佛教禅学。象山去世后,继承其学术思想的后继者,极力为陆学辩护,强调陆学是儒学、“圣学”,而不是佛学、禅学。袁甫在绍定五年(1232)《释莱告文》中称赞陆象山为“真孟子复出”:
先生之学,得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先生立言,本末具备,不堕一偏,万世无弊。……象山先生家学有原……而先生又杰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奋然必以古圣人为师。发明本心,嗣续遗响,以大警后学之聋瞆,天下以为真孟子复出也。言儒释之异趋,谓释氏为私,吾儒为公,释氏出世,吾儒经世,故于纲常所关尤为之反覆致意。洎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间,格心事业,斯世深望矣[2]524。
明代中叶,以复兴陆学为标帜的王阳明努力为陆学非禅学而辩护,赞扬“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
至宋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孟之宗,……自是而后有象山陆氏,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按:周、程二子),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传。……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2]538。
清代李绂针对《学蔀通辨》而作《朱子晚年全论》,强调陆学绝非禅学,自始至终严守孔孟之道,而朱子却于早年偏离孔孟,“徘徊于佛老”:
陆子之学,自始至终,确守孔子义利之辨与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于佛老,中钻研于章句,晚始求之一心[1]575。
朱熹晚年确实说过:“《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吾人晚年只合爱养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1]292清代李绂据此反过来批评明代陈建指责“象山讲学,专管完养精神一路,其为禅学无所逃矣”[1]154的说法:“朱子亦用‘爱养精神’之说,而陈建以精神之语诋陆子,岂不谬哉?”[1]575从上述可以看出,在朱学及其后继者看来,陆学是禅学;但在陆象山及其后继者看来,陆学不但不是禅学,自始至终都是儒学、“圣学”,并批评朱学“私其”禅学。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专门就朱熹批评象山心学“阳儒阴释”的传统看法,做了详尽的批评分析(1)详见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二章第八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牟先生作出结论:“吾所以不厌其烦,详为征引,逐条疏解,其主旨非专为象山辩护,乃意在去朱子之禁忌,明圣学之宏规,显静涵系统与直贯系统之面貌,不因其主观不相契之蔽而泯此中‘真问题所在’之实,且进而祛除流俗对于宋明儒概视为‘阳儒阴释’之诬枉也。”[3]145
实事求是地说,朱子有很高的佛学修养,超过了北宋二程,朱子本人更是深受佛学的影响(2)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说:“程、朱犹近于佛,陆、王反合于儒,此前儒所不审耳。”(《十力语要》卷二《与周开庆》)。。陆象山批评了朱熹在无极、太极之辨中“漏泄”了自己深受禅学影响的事实,尽管他平时“往往秘此”。陆学是不是禅学,关键是要先看陆象山自己的儒佛之辨。
2 陆象山的儒佛之辨
批判佛老、明儒佛之辨,乃是宋明新儒家自觉坚守的普遍价值立场,几乎所有的宋明新儒家尤其是程朱、陆王都坚持了这一点。即要弘扬所谓新儒学,提倡儒家价值体系,首先必须批判对儒学价值体系已经造成极大威胁的佛老,尤其是佛教(禅宗)。宋朝的新儒家知识分子把历史上对杨墨(杨朱学派、墨子学派)、老子道教的批评,转移到对佛教、禅宗的批评,因为当时佛教、禅宗在思想界影响极大,“弥漫滔天,其害无涯”。宋代新儒家,特别是二程(程颢、程颐)将批判佛教作为自己捍卫儒家价值信仰体系的一个思想标帜。北宋的二程批评佛教说:“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课闢,唯释氏之学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释氏盛而道家萧索。方其盛时,天下之士往往自从其学,自难与之力争。惟当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4]38程颐批评佛教说:“如杨、墨之害,在今世则已无之。如道家之说,其害终小。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 ”[4]3但是在如何批判佛老上,宋代新儒家略有差异。陆象山辨别儒佛的方法及其态度,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其彰显出一种新的特点。
第一,陆象山从儒学和佛学(禅学)的思维表达方式上去分别。在无极、太极之辨上,陆象山指责朱熹在解说“太极”时落入了佛教禅学般若思维表达方式之中。朱熹一会儿说“太极”是“有”,一会儿说“太极”是“无”,一会儿说“太极”是“不属有无”。朱熹这种“不属有无,不落方体”的思维表达方式,正是佛教、禅学有无双遣、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佛教般若学表达方式。被陆象山批评的“两头都无着实”的佛教般若学思维表达方式,正是儒家思维所要反对的。在儒家看来,说“有”就是“有”,说“无”就是“无”,既不能从“无”说“有”,也不能从“有”说“无”,“有”与“无”都是定说。陆象山认为,“有中说无,无中说有之类,非儒说”[2]463。后来倾向于禅学的程门弟子游酢(字定夫)举禅说“正人说邪说,邪说亦是正,邪人说正说,正说亦是邪”时,陆象山批评道:“此邪说也。正则皆正,邪则皆邪,正人岂有邪说?邪人岂有正说?此儒、释之分也。”[2]460在陆象山看来,游定夫(因趋禅而被胡宏批判为“程门罪人”)这种“正中说邪、邪中说正”的思维,完全是“有中说无,无中说有”的禅学思维。
陆象山从哲学思维方式上去判别儒佛,体现出他儒佛之辨的一个特色,这不同于二程主要着眼于政治伦理层面去判别儒佛。程颐批评说:“释氏有出家出世之说。家本不可出,却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于世,则怎生得出?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饮而饥食,戴天而履地。”[4]195“禅家出世之说,如闭目不见鼻,然鼻自在。”[4]64从上述批评看,程颐对佛教的理解,比如对佛教出家、出世的理解,完全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上,没有领悟佛教缘起性空的般若思维方式,可谓显得有些肤浅。程颐对佛教思维、佛教义理的深刻之处(超出经验思维的部分)往往不甚领会,造成他对佛教的批评多局限于经验伦理层面上,仅限于“以迹上观之”,缺乏理论上的分析比较,但是他客观揭示了儒家知识分子在接触佛教过程中不自觉地受到佛教深刻影响这一事实。程颐说:“释氏之学,更不消对圣人之学比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穷其说,未必能穷得他,比至穷得,自家已化而为释氏矣。今且以迹上观之。佛父出家,便绝人伦,只为自家独处于山林,人乡里岂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贱所轻施于人,此不惟非圣人之心,亦不可为君子之心。释氏自己不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而谓他人不能如是,容人为之而己不为,别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绝类也。”[4]149在程颐看来,佛教义理“未必能穷得他”,一旦深入了解佛教义理,往往会被佛教义理所征服,“比至穷得,自家已化而为释氏矣”。程颐自己没有深究佛教义理,一方面反映他对佛教理论的某种拒斥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他害怕被佛教所征服的恐惧感,所以他不得不采取简单的、经验的办法,仅仅“以迹上观之”,简单地从君臣、父子、夫妇的宗法伦理层面去批判佛教、明辩儒佛之别。
第二,陆象山从公私义利、道之偏正的层面去分辨儒佛。坚持义利、公私之辨,突出人道的核心价值和地位,是宋代新儒者共有的基本信念,陆象山自觉地坚持这一点:“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2]470陆象山在《与王顺伯》的书信中详细地表达了自己“以义利二字判儒释”[2]17的观点。在陆象山看来,儒家在天、地、人“三道”中,以立人之道的仁、义为价值旨趣,故“曰公曰义”;释氏以“生死事大”、脱离生死轮回、除灭一切烦恼为价值旨趣,尽弃以仁义为宗旨的“人道”,故“曰利曰私”。陆象山反复从公私、义利的层面去批评“释氏立教,本欲脱离生死,惟主于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2]399。佛教只着眼于个人生死轮回解脱的立场,忽略天地万物,走向自私自利,公私义利的差别就在于此。陆象山说:“吾儒无不该备,无不管摄,释氏了此一身,皆无余事。公私义利于此而分矣。”[2]474
陆象山从义利之辨出发,进一步批评释氏之“道”实为“大偏”,儒家之“道”实为“大中”,一“中”一“偏”,儒、释差别判然。陆象山对佛教特别是大乘经典,有较深入的了解。他谦虚地说自己“虽不曾看释藏经教,然而《楞严》《圆觉》《维摩》等经,则尝见之”[2]19。《维摩经》《圆觉经》《楞严经》等佛经,正是中国大乘佛教所宗重要经典,这些经典主要立足大乘佛教“一切皆空”、佛性本有的价值立场,大力宣扬大乘方便法门,具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如《维摩经》有“欲贪为本”“三界是道场”“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等说法;《圆觉经》有“不敬持戒,不憎毁禁”“诸戒定慧及淫怒痴,具是梵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等说法。上述说法,在旨为辨是非、明善恶的儒家价值思维看来,是不可容忍的。正如朱熹批评所说,“释氏不分是非善恶,皆欲扫尽,一归空寂,所以害道”[1]211。陆象山认为,佛教“淫房酒肆尽是道场”之类的所谓“不舍一法”,实际上是不明是非善恶、不分公私义利,遗弃了“人道”规范,故其“道”实为“大偏”。儒家立“道”,以“人道”为中心,统贯“天道”“地道”,故其“道”为“大中”。佛教立“道”,以“生死事大为中心”“释氏既为人”,却背弃“为人自当尽人道”[2]470的原理,至少遗弃了“人道”,天、地、人“三道”并不周备,故其“道”为“偏”。陆象山通过儒释两家所立之“道”的比较,得出结论说:“佛老高世一人,只是道偏,不是。”[2]467陆象山从道之偏、全(中)辨儒佛之异,与北宋程明道的观点一样。程明道批评佛教说:“释氏说道,譬之以管窥天,只务直上去,惟见一偏,不见四旁,故皆不能处事。圣人之道,则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见也。”[1]138
陆象山从义利(公私)的角度去辨析儒佛之异,其理论思维与北宋二程一样。程颐批评说:“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佛氏总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圣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异端造作,大小答费力,非自然也,故失之远。”[1]142程颢批评佛教说:“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尽极乎高深,然要之卒归乎自私自利之规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间,有生便有死,有乐便有哀。释氏所在便须觅一个纤奸打讹处,言免死生,齐烦恼,卒归乎自私。”[1]152陆象山从公私义利、道之偏正的高度,去辨别儒佛之异,与北宋二程并无二样,却遭到朱熹的批评,说陆象山“论释氏义利公私,皆说不着”[5]3884,这属于明显的门户之见。朱熹批评道:
向来见子静与王顺伯论佛,云:“释氏与吾儒所见亦同,只是义利公私之间不同。”此说不然,如此却是吾儒与释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时,何缘得有义利不同?只被源头便不同,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5]3885。
陆子静从初亦学佛,尝言“儒佛差处,只是义利之间。”某(按:朱熹)应曰:“此尤是第二着,只他根本处便不是。当初释迦为太子时,出游,见生老病死苦,遂厌恶之,入雪山修行,从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弃之不猛,屏除之不尽。吾儒却不然,盖见得无一物不具此理,无一理可违于物。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具实,从此一差,方有公私义利之不同,今学佛者云,识心见性,不知是识何心?是见何性?”[1]210
应该说,朱熹从虚、实上辨儒佛之别,“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具实”,从理论思维上显得更高,超出了陆象山,但其内容还是以仁义礼智之道德伦理原则为立论依据,与陆象山一样,实际上还是公私义利之辨。朱子对佛教的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指责佛教遗弃儒家人伦道德而陷入自私、不义,“释氏灭天理、去人伦以私其身”,佛教的修身立足于自私。朱熹批评说:
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5]3932。
所厚者,谓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当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释氏灭天理、去人伦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则虽至于六度万行具足圆满,亦无以赎其不孝不弟之刑也[6]2039。
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灭绝尤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以此言之,禅最为害之深者[1]211。
由此看来,朱熹批评陆象山用公私义利去辨儒佛“是第二着”,这只表明朱熹好逻辑分析的性格罢了。
第三,陆象山从是否“主经世”“主入世”上去明儒佛之别。陆象山认为,儒家以“经世”为价值旨趣,佛教以“出世”为价值旨趣。他说:
来教谓“佛说出世,非舍此世而于天地外别有乐处”。某本非谓其如此,独谓其不主于经世,非三极之道耳。又谓“若众圣所以经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经世异于出世,而别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岂是别有妙道?[2]20
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往往主张即世而出世,并非“舍此世而于天地外”别寻一个涅槃乐处,但是非舍此世仅仅是佛教为出世而设的“方便”,并非以“入世”作为立教的宗旨,只有“出世”才是佛教立教的目的。所以,“入世”(非舍此世)在佛教那里,只是“方便”,并非“究竟”。尽管佛教有大乘菩萨入世普度众生之说,但是改变不了它“主出世”的性格和价值旨趣,故佛教宣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世间皆苦、一切皆空、涅槃寂静等教义,旨在引导众生离开一切把握不定、处处是苦的此岸世界,去追求无烦恼痛苦、远离生死轮回的彼岸世界,即涅槃乐处。佛教认为,在世间之外“别有妙道”,与此相反,儒家所主经世之道,并非在天地之外,而“乃天下之常道”,横贯天、地、人“三极”。陆象山说:
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2]9。
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焉耳。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顺此理哉?[2]142
儒家所主经世之道,并非天地间外的“别有妙道”,而是充塞宇宙天地之间。正如二程所言,“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4]38“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4]77。通过上述分析,陆象山用“主经世”和“主出世”来判分儒、释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抓住了儒佛二家各自的思想主旨和价值趋向。
陆象山非常自觉地从儒佛思维表达方式、公私义利与道之偏正、主出世与主经世等三个大的方面,去分辨儒佛的差异,这表明他对佛学有比较深刻的领悟,更表明他并未偏离宋代新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批评佛教、明儒佛之辨,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基本价值要求,如朱熹所言,“程氏之门千言万语,只要见儒者与释氏不同处”[6]1970。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理和价值层面上,陆象山强调儒释之辨,其价值宗旨在于批判佛教,弘扬儒家孔孟之道。但是陆象山批评佛教的态度是辩证的、相当理性的,他一方面批评宋代佛教“今之僧徒,多担夫庸人,不通文理”[2]19,另一方面他赞赏佛教徒修道精进的精神。陆象山的《赠僧允怀说》赞赏允怀法师:“怀上人学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门庭,建藏之役,精诚勤苦,经营未几,骎骎向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国之士大夫,举能如此,则父兄君上,可以不诏而仰成,岂不美乎?”[1]190这种既批评又赞赏的辩证理性态度,完全不同于宗朱子学的明代陈建之极端狭隘的浅陋态度。明代的陈建据此批评佛教以及陆象山说:“奸僧诳诱愚俗,罔夺民财,以尊夷狄之法教,崇无君无父,沦灭三钢之门庭。此明王之所禁,而圣贤之所必斥也。象山乃亟加褒誉,美其经营,嘉其勤苦,至欲使子弟士大夫举效之,颠倒错乱,尚孰有甚于此!”[1]190
陆象山这种批判佛老的理性态度,也体现在他对“陋儒”的批评上。在陆象山看来,儒家的衰微,首先不是因为佛老的入侵,而根源于儒家自身,根源于“陋儒不能行道”“败坏父祖家风”。陆象山说:“异端(按:佛老)能惑人,自吾儒败绩,故能入。使在唐虞(按:尧、舜)之时,道在天下,愚夫愚妇,亦皆有浑厚气象,是时便使活佛、活老子、庄、列出来,也开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孙,败坏父祖家风。故释老却倒来点检你……今之攻异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点检,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须是先理会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2]438-439在陆象山看来,儒家批判佛老陷入了一个误区,仅仅着眼于“异端之名”去批评,这是非常肤浅的做法,根本不了解儒家“异端”的本来含义。陆象山认为,在原始儒家孔子那里,“异端”这一话语的含义并非专指佛老。陆象山说:“异端之说出于孔子,今人鲁莽,专指佛老为异端,不知孔子时固未见佛老,虽有老子,其说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恶乡原,《论》《孟》中皆见之,独未见排其老氏。则所谓异端者非指佛老明矣。”[2]177在陆象山看来,孔子本人并无佛老异端之说,孔子心目中的“异端”乃至“乡愿”;若专指佛老为“异端”,则违背了原始儒家孔子的本意!批判佛老,先要反思批评自己,须找到自己“得有以使之服”的理由,在此基础上方可批判佛老。陆象山通过考察“异端”这一话语的本来含义,其目的在于批评当时儒家批判佛教的肤浅与无知!在陆象山看来,真正的“异端”并不专指佛老,而是违背儒家“天下正理”的一切异说。陆象山说:“异端岂专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绪,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穷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为说,亦是妄说。其言辟佛老者亦是妄说。今世却有一种天资忠厚、行事谨悫者,虽不谈学问,却可为朋友。为是谈学而无师承,与师承之不正者,最为害道。”[2]194陆象山认为,伤害儒家“天下正理”最大者、“最为害道”者,并不是佛老,往往是“借佛老为说”的某些“近世穷理者”,这才是最大、最有害的“异端”。
陆学与程朱理学都非常重视扬儒抑佛的儒佛之辨,二者在对待佛老的态度和价值要求上,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朱熹及其后学批判陆学“全是禅学”的评价实含门户之见。宋代佛老、特别是佛教(禅学)在当时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民众中影响极大,“与儒学鼎列于天下”。陆象山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之发展、兴盛状况:“佛入中国,在杨子(按:先秦杨朱学派)之后。其事与其书入中国始于汉,其道之行乎中国始于梁,至唐而盛。韩愈闢之甚力,而不能胜。王通(按:隋朝大儒)则又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浮屠老氏之教,遂与儒学鼎列于天下,天下奔走而向之者盖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祸福归向之者则佛、老等,以其道而收罗天下英杰者,则又不在于老而在于佛。”[2]298面对佛教有如此大的影响,捍卫儒学价值信仰的陆象山不得不采取更加理性、富有成效的儒佛之辨。针对陆象山的儒佛之辨以及在宋代佛老影响很大的思想背景下,现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高度评价陆象山“真能正视佛老而以儒者真实生命顶上去”的态度和智慧:“佛老影响如此之大且久,其义理如此深远,而若不能予以正视,采‘鸵鸟政策’以自护,视彼方(按:佛老)若不可触者然,造作禁忌,动辄斥人为禅,则其斥责之无谓与不相应盖不可免。此即为浅陋。自此而言,朱子之造诣不及象山远甚。”[3]150陆象山对佛教的态度,不同于程朱,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开放的理智心态,敢于正视佛教,不把佛教当作禁忌,不采取“鸵鸟政策”以捍卫儒学道德价值信仰,其主动接触佛教,故在思维方式、实践工夫等方面不自觉地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
3 陆学的禅学化表现
陆象山批判佛老,并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但这并不能说明陆学在思想内容上完全没有受到禅学的重要影响。朱熹及其后继者对陆学的批评,并非完全无中生有,只是偏颇罢了。事实上,陆学在思想理路、为学工夫等许多方面,与禅学相似或几乎一致。这首先表现在陆学对“心”的理解上,与禅学一致。
我们一般用“心本论”和“理本论”去指认陆象山、朱熹各自的思想特征及其本体论上的理路差异。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准确。因为陆象山既“主唯心”,又“主唯理”(3)民国学者陈钟凡就用“惟理一元论”来概括陆象山的宇宙本体论,并与朱熹的理先气后的二元论相区别,并且认为这是朱陆学术根本主张之不同,从而导致双方在其他学术问题如无极、太极问题上的反复辩诘:“盖一主惟理之一元论,一主理先气后之二元论,反复辩诘,累千百言而不休,盖其根本主张不同也。”(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从“唯心”意义上讲,陆学是“心本论”;从唯理意义上讲,陆学是“理本论”。“心”与“理”在陆学那里是同一个层次的哲学本体范畴,也就是“心即理”。陆象山说:
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岂有限量?程明道所谓有憾于天地,则大于天地者矣,谓此理也[2]161。
塞宇宙一理耳。上古圣人先觉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于是有辞、有变、有象、有占,以觉斯民。后世圣人,虽累千载,其所知所觉不容有异[2]201。
从上述看出,在陆象山那里,“理”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即使“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2]147再看他“心即理”的思想: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2]273。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2]149。
从陆象山对“心”“理”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定来看,陆学已将“心”“理”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从“理”上说,他与朱熹无别,从“心”上说,二者思想理路明显有异。朱子言“心”,主要落在形而下的气边上,心是气之灵,是认知活动主体,主要起灵明知觉的作用,主要是认识论范畴,而不是一个本体论范畴。朱熹说:“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心者,气之精爽。”[5]219“心”对“理”的知觉就成为“道心”,对“人欲”的知觉就成为“人心”,所以朱熹强调道心、人心之辨,这恰恰遭到陆象山的批评。在陆象山那里,“心”既是知觉主体,又是“无有不善”的道德本体,更是宇宙万物本体,心即一切,一切即心。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理”,“心即理”“理即心”,不容许“心、理为二”,不容许“道心”“人心”之别。陆象山这种范围古今、包揽宇宙的宇宙本体之心,实际上与禅宗所言之“心”,极其相似。禅宗《坛经》云:
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7]25。
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7]37。
通过比较,陆学“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中的无所不包的“心”,实际上与禅宗所论之“心”几乎一样。禅宗主张“自心”是万法的本原,“自心”是成佛的根本依据(即心即佛),“自心”既是抽象的本体心,又是众生当前的现实人心。正如学者指出,陆象山的心论与禅宗的心性论“不论在思维方法上,还是思想内容方面,都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8]198。当然,陆象山的“本心”不能完全等同于禅宗的“自心”,因为陆象山出于儒家道德意识立场而赋予自己的“本心”以儒家伦理性格,可以说“本心”是一种道德实体,而禅宗所讲的“自心”已经超越了儒家道德实体的范畴,反对包括道德实体在内的一切实体,禅宗“自心”乃是基于缘起性空的世界观,乃是宇宙之实相(无相之相),具有浓厚的非道德实体主义色彩。从儒家思想史上看,陆象山的心本论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本心论思想。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已经蕴含了后来陆象山“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本论思想。有学者认为,“在孟子那里,最高的范畴是‘天’,而不是‘心’,‘心’只是一个表示道德情感和生理学的概念,是思考的器官”[9]。这种观点完全是对孟子道德心性论的误读。陆象山强调自己的学术思想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思想。这是儒家思想史事实,陆象山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本心论,将孟子的道德本心论与宇宙本体论做了更加自觉的融合。从政治伦理意义上讲,陆象山的心本论、朱熹的理本论以及禅宗的自心论,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异,都强调了仁义道德,“程朱与陆(按:陆九渊),儒与僧,说的意思一致,真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10]。
在具体的为学工夫上,陆学与禅学极其相近。陆象山不重视知识文字之学,与禅宗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精神相同。禅宗自达摩以来,确立了“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立教传法原则,成为禅门与其他佛教宗派相区别的重要标帜。禅宗二祖慧说:“故学人依文字语言为道者,如风中灯,不能破暗,焰焰谢灭。”[11]1285三祖僧璨说:“即文字语言,徒劳施设也。”[11]1286四祖道信要求修道者:“决须断绝文字语言。”[11]1287五祖弘忍在给神秀开示《楞伽经》说:“此经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11]1230六祖慧能更明确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12]禅宗在六祖以后更是否定经教文字,斥责“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净故纸”[13]。禅宗贬斥经教文字,旨在要求学道者返本“自心”“自性”,因为“一切法尽在自性”,既然如此,在实践工夫上,只要“识本心,即是解脱”[7]37,只要明自心见自性,就解脱成佛了。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解脱成佛,完全是自身的心性工夫,“唯心证了知”,与知识、经教文字无关,经教文字往往成为障道因缘,“徒劳施设”,必须断弃。我们再看陆象山说: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闲说话,渐渐好,后被教授教解《论语》,却反坏了[2]455。
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2]444。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2]461。
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2]447。
陆象山反对“只是解字,不求血脉”,强调“不得闲说话”“自立自重”,这与禅宗强调“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自悟自修”“自性自度”的思想完全一样。陆象山轻视语言文字的原因,因为文字语言须以道德为本、“弗畔于道”。在陆象山看来,文字语言与道德实体之间的关系是:道德是“本”、是“实”,文字语言是“末”,文字语言须以道德为本、“弗畔于道”。陆象山说:“文字之及,条理粲然,弗畔于道,尤以为庆!第当勉致其实,毋倚于文辞。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诚其实,必有其文。实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习,所重在末,岂惟丧本,终将并其末而失之矣。”[2]145在陆象山看来,有德者必有其言,语言文字如果脱离道德这一实体之本,必将导致道德的丧失和语言文字自身的丧失。陆象山这种“毋倚于文辞”的道本言末语言观,固然有针对宋代流行的重“道问学”而轻“尊德性”的弊病,但也反映了宋代儒家忽视语言逻辑的根本问题所在。陆象山道本言末的语言观,不仅深受禅宗“不立文字”的语言观影响,也是对孔子语言观的继承和发展。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这种重视实践德行而轻忽文字的语言观,奠定了以后正统儒家的发展方向,陆象山继承了孔子这个传统。这与西方哲学,无论是传统西方哲学还是现代西方哲学(包括现代人本主义西方哲学)重视语言的传统很不一样。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中国哲学传统,有一种忽视语言逻辑的特征,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言,“儒道佛都不重视语言。所以中国传统有一种反语言学的倾向”[14]131。
陆象山反对朱熹“存天理、去人欲”“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而主张更为简单的“剥落”“减担”的方法。陆象山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2]458这种慢慢“剥落”的方法,与禅宗“渐修”的禅修方法实际上是一样的。陆象山主张“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2]469,这种当下直觉的修养方法,与禅宗“顿悟”的禅修方法实际上是一样的。陆象山说:“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才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彻骨彻髓,见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轻清,自然灵。”[2]468陆象山这种“内外无所累”的“无累”精神,与慧能禅宗“无念”“无相”“无住”的精神旨趣实无差别。在为学功夫上,陆象山强调“尊德性”的“易简功夫”,即“提撕省察悟得本心”的功夫,具有浓厚的禅学色彩,故朱熹批评陆象山“流于异学而不自知”:“子静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以过人者。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榨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1]41
朱熹指责陆学“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为禅,这虽然是夸大之词,但是确实揭示了陆学深受禅宗“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思想之影响的事实。通过上述分析,陆学深受禅学的影响是一种客观事实,正如有学者基于中国思想史的视角指出,“佛教或禅宗作为历史悠久、思辨性的思想体系,作为在宋代仍很有势力和影响的宗派,对陆九渊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15]574。朱熹对陆象山的批评,在相当意义上击中了陆学的要害,因为他本人对佛学有较深入的了解。朱熹说:“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钦夫(张栻)、伯恭(吕祖谦)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朱熹)便识得他。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5]3882富有较高佛学修养的朱子对陆学的批评意见,值得我们注意。
4 结语
陆学与禅学之辨,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朱陆异同之辨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关键之处。要正确理解陆学与禅学的关系,我们要超越历史上朱、陆之争的护教门户意识。陆象山非常重视儒、佛之辨,自觉批判佛老,坚守儒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朱熹一样“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1]76。陆象山具有浓厚的儒家道统意识,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可以从他关于儒、释、道三教在历史上的兴衰评价中看得出来:“孟氏没,吾道不得其传。而老氏之学始于周末,盛于汉,迨晋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学出焉。佛氏始于梁达摩,盛于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贤者出,吾道其兴矣夫!”[2]473由此看来,不能说陆学“全是禅学”“阳儒阴释”。
陆象山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这是历史事实,故不能出于护教主义立场,而独断地说陆学自始至终“孟氏之学也”,独断地坚持“象山言本心即性、心即理,纯是孟子学”[16]67。综合历史上的上述意见和我们对陆学的考察分析,陆学实际上是禅学化的新儒学,其思想既来源于传统儒家特别是孟子的思想,如陆象山自己所言,“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但是也大量吸收了佛教禅学思想。陆象山对佛教、禅宗的批评,具有更多的辩证理性主义色彩,他对佛教、禅宗的了解也相对更加深入,其批判佛教、禅宗的水平已经超出了同时代新儒家的思想水平,也非二程、朱熹所能比拟。这说明陆学这种禅学化的新儒学,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一点往往为已有研究成果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