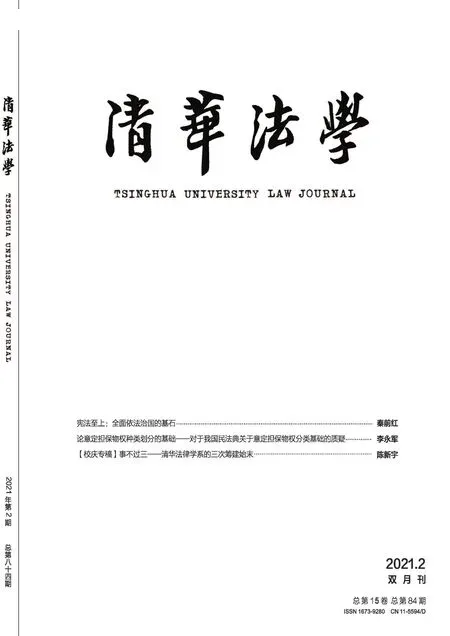人们因何团结?
——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科学主义、责任伦理与法治
张剑源
一、提出问题
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实践经验的总结,既是对未来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一种经验积累。同时,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对中国经验的一种有效解读,可以形成与既有理论的对话,为我们准确理解中国式治理等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分析样本。从过往来看,如何有效控制住病毒的传播、如何形成较优的防控体系、如何处理好由疫情所引发的各种社会伦理问题,是绝大部分有关公共卫生和疫情研究所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1)参见李广德:《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25-43页;苏玉菊、王晨光:《论公共卫生规制的伦理与法律原则——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平衡》,载《行政法论丛》(第16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308页;武汉大学公共卫生治理研究课题组:《防疫常态化下公共卫生治理的思考与建议》,载《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6期,第1-7页。然而,就此次疫情防控社会科学领域既有研究来看,关注政府能力、关注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的研究成果较多,(2)比如王绍光回顾了我国预防为主的防疫疾控体系及其所经历过四次危机,指出“预防为主”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举措中,落实到人员与资金的配置上;王旭从行政组织任务的角度,讨论了重大传染病危机应对中组织结构的优化问题;陈武等学者分析了政府应急管理举措与疫情分布的时空关系;王轶、陈伟等学者探讨了疫情防控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参见王绍光:《预防必须为主——中国疾控体系的四次危机及其教训》,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2期,第65-69页;王旭:《重大传染病危机应对的行政组织法调控》,载《法学》2020年第3期,第76-93页;陈武、张海波、高睿:《新冠疫情应急管理中的管制政策与疫情分布的时空关系——以2020年春节期间湖北省各地区应对策略为例》,载《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年第3期,第16-28页;王轶:《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载《法学》2020年第3期,第36-48页;陈伟:《新冠疫情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解释扩张及其回归》,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5期,第18-29页。对有关疫情期间民众参与及其影响的研究成果则较少。这一状况并不利于我们对疫情防控经验的整体把握和理解。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疫情防控来说,国家层面的组织动员和社会层面民众的回应与参与,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样重要。只有将民众的回应和参与与国家的组织动员结合起来观察,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对疫情防控的效果和经验有更为准确的把握。
基于此,本文将提供一个在公共卫生危机时候民众积极回应和有效参与疫情防控,并与国家形成有效互动的具体分析样本。无论是媒体报道中常出现的“逆行者”形象、事迹,抑或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自觉“宅”在家、自觉配合防控工作的开展等,实际上都是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民众回应和参与最直观的展现。在本文中,我们将这种民众的参与和互动称之为是一种人们基于互相负责的“社会团结”。在面对疫情时候,人们因何会团结在一起,以及是什么因素在保障着社会团结的维系,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3)关于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团结”和“分化”的讨论,可参见张剑源:《再造团结: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195页。另外,为了更清晰的把握这一问题,本文还将在比较的视野中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毋庸置疑,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候,不同国家的话语和政策建构还是呈现出较大的不同。除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团结”话语外,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还广泛存在着很多基于“自由主义的”或“个体主义的”话语体系和政策建构,更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自主。对不同模式的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团结”在此次中国的疫情阻击战中的独特性及其意义。
文章将分别从科学主义、责任伦理、法治三个维度,来探讨此次阻击战中团结是如何塑成这一核心问题,并将会在最后一部分对“团结”这一经验的意义进行一定的讨论。本文中,“科学主义”并非一个过往研究中所讨论的“唯科学主义”的概念,(4)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而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概念。强调科学知识对人们行动的影响,但并不否认其它因素对人们行动的影响;强调科学知识对人们行动的外在型塑,但更强调人们在掌握科学知识基础上科学意识的形成与内化。“责任伦理”则是指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在维护人际关系、维护集体和维护国家安全及秩序时候的富有责任感的个人心性和集体意识。
二、文献回顾和进路
将医学和疾病问题纳入社会、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研究,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其中,有两个概念尤其重要,一个是“躯体化”、一个是“隐喻”。前一个概念在凯博文(Arthur Kleiman)等学者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有较为系统的讨论。在他们那里,“躯体化”主要是指,个体的苦痛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表达出来,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求医模式。也就是说,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5)[美]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9页。后一个概念则主要来源于桑塔格(Susan Sontag)的阐释。在她看来,在疾病被赋予的某些道德判断之下,潜藏着有关美与丑、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或怪异的审美判断。(6)[美]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不难看出,“躯体化”概念所强调的是一种“忽视”的状态,深刻揭示了个体生理病痛之外,外界社会对个体的影响;而“隐喻”概念所强调的则是一种“过度”的状态,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对个体生理病痛的“过度解读”,甚至污名化。
沿着这样一种“超越医学”的框架,学者针对公共危机产出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刘绍华在其有关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的研究中,特别强调对个体意识的关注。(7)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8页。凯博文在有关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的研究中,实际上也持相类似的观点。(8)同前注〔5〕,凯博文书,第196页。而与这种根源于现代性论述的观点不同,波斯纳(Richard A.Posner)提出的应对公共危机的方案则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非此即彼”,而应该是一种平衡。他说:思考宪法权利的恰当方式是天平这个隐喻。一边秤盘装的是个人权利,另一边则是社区安全,由于各自利益的砝码改变,这个天平需要并接受不时的调整。在一种更广的意义上,公民自由也取决于国家安全,因为公民自由就是安全和自由之间的平衡点。(9)[美]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154页。福柯在其有关“生命政治”的讨论中,对过去那种“自由主义治理技艺”进行了反思。虽然他并不截然否认自由的价值。但是,在福柯那里,自由应当是一种——不同于过去那种单纯的政治自由或经济自由的——受规范、受约束的,作为一种治理关系的社会自由、秩序自由。(10)参见莫伟民:《使治理正当和合理的原则与方法——福柯视野中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第59-66页。他认为,新的治理术与“自由主义治理技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抽取公共卫生、环境、出生率、发病率等知识,并确定干预和权力的领域。(11)[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286页;[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6-89页。
不难看出,在“现代化”理论的感召下,自由主义依然是在公共危机研究中一种较为主要的理论阐释。虽然从福柯到波斯纳,以及更多学者那里,已经注意到个人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关系问题。然而,似乎较优的选择和策略都应该是被规训的、被规制的,或者是需要通过司法才能确认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家长式”的危机应对观念,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民众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候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以及国家与民众互动的重要性。无独有偶,在一本三位英国学者撰写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的小册子中,我们看到了颇不一样的论述:
控制传染病的关键是了解当地的人们怎样看待疾病——疾病是怎样产生的,会对人们及家人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会感染患者?这些问题对患者和其周围的人来讲非常重要,对他们提出的建议也应该是根据他们的观念来进行解释。理解地方观念可以使得给出的建议更为人们所接受并能够照做。……(12)[英]约翰·沃利、约翰·怀特、约翰·赫布利:《发展中国家改善公共卫生指南》,解亚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16页。
不难看出,这种基于特定语境的解释,可以克服非此即彼,以及“家长式”的主观判断。实际上也提供了一种理解危机应对的有效进路——并非先入为主的,或非此即彼的理论套用,而是基于特定语境的解释。本文将沿着这样一种进路展开讨论。接下来,无论是对科学主义、责任伦理,还是对法治的讨论,最主要的是剖析在以上特定因素作用下民众的积极回应和参与,以及这些回应和参与在与国家的互动中是如何促成“团结”生成,进而有效应对危机的。
三、科学主义

虽然也存在一些特例,但以上还是一种相对普遍的卫生治理迈向科学道路的基本历程。这一历程在中国生发的时间相对较晚,但过程相仿。虽然现代科学最早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然而,即便李约瑟也并不否认,在传统中国,生物学领域中国人并没有落后,医学更是中国人世世代代深感兴趣的一个领域。(17)[英]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页。到了19世纪,严复等对西方著作的翻译,以及大量向西方学习技术的具体实践有力推动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人们对科学有了更广泛的认知和接受度。(18)比如1952年底,《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中就指出:“大力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普遍提倡勤洗衣、勤洗澡、不喝生水、不吃生菜生肉、不随地吐痰便溺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普及预防疾病知识。对于劳动卫生和妇婴卫生知识,尤应注意宣传推广。”
就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说,2020年1月20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当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的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同时,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同一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记者会,高级别专家组通报新冠病毒已出现人传人现象。(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载《人民日报》2020年6月8日,第010版。自此,所有人打破观望,无论是政府、医疗机构,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开始投入到整个防控阻击战之中。一系列防控措施和倡议陆续出台,包括但不限于“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的确立,“科学佩戴口罩”“注意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等指导意见的提出等。(20)参见《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做好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病例医疗救治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很明显,是科学的判断,而非意义阐释,主导了防控措施的确立。基于此,在政府与民众、专家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以及更广泛的疫情防控参与主体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21)关于“风险沟通”,可参见戴新月:《社会、心理、话语:新冠疫情初期的河南基层风险沟通》,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26-38页。而那些基于科学知识的政策措施也才能对民众及其行为形成有效引导。
如果与传统时期的“仪式治理”进行比较,不难看出,随着对疾病、病毒认识的拓展,传染病防控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已经从一个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问题,转化为了一个人与病毒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时候,人首先要做的不是与意义世界的对话,而是与病毒的“短兵相接”。“消灭病毒”成为了科学意义上最重要的传染病防控目标。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多数人似乎也都意识到了,只有科学佩戴口罩再出行,甚至尽量不要随意出行,主动报告、主动就医、主动隔离,才是明智之举,才是富有责任感地站在与大多数人一起来与病毒作战(而非站在纵容病毒肆虐)的一面。在这个时候,有效的风险沟通取代了隔阂和不信任、团结取代了分化。而正是科学在其中起到了尤其关键的推动作用。
四、责任伦理
然而,无论如何,在防控措施与人们的具体行动之间,我们还是或多或少看到了一种人们具体行动的受约束性。那么,这种受约束性是否与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相冲突呢?民众对这种约束究竟是自愿服从,还是被迫地遵守?
很显然,如果用抽象的“个体主义”“对抗式”或“权利”话语来讨论我们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很可能会得到任何外在的约束都是与个人自由相冲突的结论。因为在“个体主义”理论话语的脉络中,个人自由才是最为重要的价值。甚至,在很多时候,个人主义坚决反对任何强制性,亦即反对对任何并非以平等适用于一切人的规则为基础的权利提供任何保护,而不论这种保护是依据法律还是依凭强权。(22)[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1页。然而,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的角度看,抽象的个体主义和自由理论往往最容易忽视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所赖以存在的具体情境,在很多情况下还会遮蔽住例外状态、特殊情形下对个体权利和个体自由予以限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关于这一问题,西方学者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反思,比如涂尔干在其有关“集体意识”的研究中就认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23)[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2-43页。波斯纳在其研究中也认为:“我们越感到安全,我们就会给个人自由加上更多的砝码;我们越感到危险,我们就会给安全加上更多的砝码,尽管我们承认这两个利益相互依赖。”(24)同前注〔9〕,波斯纳书,第154页。而西方国家的法律实践中也有很多案例对这类问题进行了积极回应。比如1905年发生在美国的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Jacobsonv.assachusetts)。在一个天花流行的特殊时期,雅各布森不愿意接种天花疫苗,他觉得是否接种疫苗是他的个人自由,况且他也对疫苗的科学性存有疑问。于是将试图强制要求其接种疫苗的马塞诸塞州公共卫生部门告上了法庭。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在健康、安全和繁荣的公共福祉要求下,个人以及财产均应服从于各种形式的限制和负担。(25)参见汪建荣等主编:《用法律保护公众健康:美国公共卫生法律解读》,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5页。相类似的,在美国发生的维罗尼亚校区诉阿克顿案(Vernonia School District 47Jv.Acton)中,就维罗尼亚校区对校队队员进行毒品检测是否合理和合法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斯卡利亚大法官代表多数大法官撰写的判决意见中明确表明:“有些危机是真实存在的,当它们确实存在时,它们恰恰是我们说过的令人信服的国家利益,可以证明对宪法权利的限制是正当的。”(26)Vernonia School District 47J v.Wayne Acton, ET UX., ETC.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些来自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回应,无不表明,在例外、紧急状态或特定情境下,个人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的辩证,实际上与常规状态下的情况是有着较大不同。情境的差别决定了例外和紧急状态下个人权利受约束的可能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表明,例外和紧急状态下对个人权利适当的限制和约束,可能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公共安全的建立和延展,甚至反过来促进个人更大的自由的实现。正如波斯纳所说的,“没有人身安全,可能就没有多少自由”。(27)同前注〔9〕,波斯纳书,第48页。
回到此次新冠疫情阻击战的具体情境中,可以看到,基于科学的决策和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绝大多数人应该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只要每个人都相信科学、自觉地遵守防控秩序,紧紧团结在与病毒作战的一方,我们一定会更快地战胜病毒的传播,进而更快地复归到常态化的生活中。而事实的确也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可以看一段一名农村基层干部在对老百姓出行进行劝返时候两人的对话:
(发现一名没戴口罩的村民)
干部:去哪啊?
村民:北甸子
干部:上北甸子。不是,去哪啊?
村民:上山攒树去(修枝打杈)
干部:攒树去?自己家的啊?
村民:啊,自己家的。不行啊?
干部:行是行啊……现在不这时期嘛。现在最好不要出门,虽然不接触啥。
村民:上山,就在这旮瘩。行吗?不行就不去。(准备掉头)
干部:回去吧。过一段时期的。行吗?过两天攒树不也行吗?
村民:行行……
……
干部:另外,出门戴口罩。可能没有的话,没有今天就不出门。现在这形势太紧了。
村民:知道知道
干部:挺严峻
村民:我寻思自己山上。
干部:回去吧……看新闻么天天
村民:看,多重视
干部:多重视啊。咱们就是重视
村民:我寻思自己的坨子
干部:都是为咱自己好
……
村民:谁家也不去。
干部:是。
村民:行。谢谢您啊!
(村民自愿掉头返回)
这段对话来源于网络平台上一个真实的视频,视频的名字为“一名乡镇干部教科书式劝返”。(28)可参见《一名乡镇干部教科书式劝返》,来源于腾讯视频网站,https://v.qq.com/x/page/h3066g8zqdf.html,2020年4月18日访问。整个“劝返”的过程,干部话语轻柔,村民极力配合,没有任何剑拔弩张的气氛。在北方冬日阳光的映衬下,还显得有些许温馨。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个例,并不可能说明所有人都是自觉服从的。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不服从管制的行为曝光出。但是,在整个中国,无论如何,还是配合、服从的为大多数,不服从的为少数。关于这一问题,除了可以从社会生活实际中进行观察外,既有研究实际上也支撑了这一判断。(29)一项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开展的调查研究显示,95.44%的被调查者能够基本做到在公共场合戴口罩;95.02%的被调查者能够基本做到减少外出、不聚会。范鹏、成兆文等:《新冠肺炎疫情期民众心理与行为分析及对策建议》,载《社科纵横》2020年第2期,第3页。只不过不配合的行为容易引起众怒,进而会在媒体(包括自媒体)上被放大。配合和服从却成为了稀松平常的常规。
那么,这种占大多数的配合、服从,除了上文讨论过的科学知识的普及、政策的引导,以及有效的风险沟通外,还有没有其它因素在发挥着影响呢?无论如何,科学知识的普及和防控措施的确立,终归还是外在于人的一种干预。它推动了人们去团结在一起,与病毒斗争。但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更为自觉地参与和配合,相信还必须是一个每个人深植内心的内在心性和行为倾向问题。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这种人们内在的心性和行为倾向称为是一种责任伦理,意指大多数人所保有的那种克己、充满信任,并愿意为他人负责的道德伦理。
关于这一问题,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一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后,就曾作出过一个有关中国人极富责任感(Responsibility)的论断。在他看来,在中国,无论是家族、邻里,还是社区,人与人之间“彼此负责”都是极为普遍而重要的。明恩溥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的这一经验就是,为了维护国家体制的安全,要求每一个人都严格地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30)[美]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陶林、韩利利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181页。而梁漱溟先生对此问题也有过较为精辟的概括。他说:
由是乃使居此社会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自古相传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3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纵观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人们的具体行动,很显然,无论是外国人明恩溥,还是梁漱溟先生的洞察和判断,都在此次疫情爆发之时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正如上文所述的那个“劝返”案例中的村民,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更大多数自觉配合与参与的民众,在疫情防控和整体安全建设面前,基于内在的责任伦理,大家所表现出的实际上都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心性,而毋宁是一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发自内心的遵从和配合,而并非一种强力的驱使。因此,这里所说的责任伦理,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萨维尼意义上的“民族的共同意识”“民族信念”或“民族精神”。(32)参见舒国滢:《德国1814年法典编纂论战与历史法学派的形成》,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1期,第92-111页。
以上是关于责任伦理结构性的一面。然而,必须注意到的是,即便这种责任伦理对人们的行动有着有着很强的型塑效应,但是社会情境的复杂性还是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人的行动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影响。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观念、意识和具体的行动之间,是如何达成一致的?就此次疫情中的情况,有研究发现,公众对疫情防控制度的感知、公众对疫情防控的制度信任,以及公众对疫情防控的制度遵从行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在三者之中,正是疫情防控制度信任在制度感知和制度遵从行为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33)徐彪等:《公众疫情防控制度感知对遵从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载《公共管理评论》2020年第4期,第1-26页。也有学者认为,是“同理心”发挥了类似于“中介”的作用,“人们将同理心化为互助和集体行动……正是由于中国社会成员广泛的同理心促成了抗疫期间‘万众一心’的集体行动”。(34)孙凤等:《疫情给公众认知及行为带来哪些改变》,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S1期,第18-21页。而事实上,“制度信任”“同理心”正是人们的责任伦理在特定情境下的一种具体化。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形下,它们连通了人们的感知、态度和具体行为,帮助人们实现从感知到制度遵从的潜移默化的转变,促使人们在与病毒“短兵相接”的危急关头,都能够负有责任的、团结一致地对抗病毒。
总之,在中国社会,大部分人所具有的责任伦理是一种相对内化的历史心性,有其稳定性。同时,在特定的情境下,还会成为一种观念和行为之间较为积极的“中介”力量,保证信任的生成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负责和团结一致。正因为此,责任伦理成为了疫情防控时候人们积极行动以及社会团结生成的一种核心的内在力量。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违反防控措施、破坏防控秩序的人,会被看作是不负责任的人,没有公共观念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不利于团结一致抗击病毒的人。
五、法治
如何应对这些“不利于团结一致抗击病毒的人”呢?显然,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社会团结的形成和有效运转,除了需要有科学的普及,需要广大群众以“责任伦理”为基础的互相负责外,也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来对那些破坏团结的行为予以规制,同时对好的经验予以确认和保障,才能保证社会团结的制度化、规范化,直至稳定和有序。在这种时候,“愿望的道德”——那种人们发自内心自愿遵守的,善的生活的道德——显示出了其固有的局限性。它无法对那些潜在的,或已经形成的异化现象形成外在的制约。也因此,个体的异化和不受控制将加剧风险的可能,进而影响到整体的团结。在这种时候,责任感就有必要通过特定的机制转化成为一种义务,一种“义务的道德”以及特定的规则。这实际上也就是富勒(Lon L.Fuller)所说的:
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它会因为人们未能遵从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而责备他们。(35)[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页。
这正是法律必须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外在的角度来看,法律除了需要基于科学判断,对越轨行为作出限制和规制外。实际上,在特定情境下,救援、支援、以及互助,实际上也不断地在通过制度化的努力而成为现实。总之,法治在团结的阻击战中,至少发挥了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是法治的“回应性”,是指通过法律对那些破坏团结的行为予以有效回应;第二个是法治的“弥合性”,是指在法律框架下为团结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创造着管道。接下来,我将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讨论,具体分析法律和制度是如何型塑团结之边界,为团结提供外在保障的。
第一,法治的“回应性”,也就是法治作为一种“底线”,对破坏团结的行为予以回应和规制,以保证疫情阻击战依然是在一个有序的状态中运行。在这方面,刑事司法的运作尤其具有代表性、最为集中反映了法律对破坏疫情防控行为的规制。比如早在202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就专门出台政策文件,对特定时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罪名适用作出具体规范。(36)参见2020年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再比如,从2020年2月至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陆续发布数十个依法惩处或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37)2020年2月至4月,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三批共26个“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了五批共32个“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6个案例为例,通过分类可以看出,这些案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不执行卫生防疫机构按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造成他人被感染,或引起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第二类,拒不配合防控管理,以暴力方法阻碍执法或管控,造成他人受伤或死亡;第三类,在疫情防控期间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诈骗、招摇撞骗、寻衅滋事、非法经营、销售伪劣产品和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进而扰乱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第四类,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些案例中的情形,有的对疫情防控产生了直接影响,甚至产生了病毒传播的严重后果;有的则在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同时间接影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通过这些案例,我们看到了那些对疫情防控秩序造成破坏的具体情形。同时,也可以看到法律和司法努力促进疫情防控秩序恢复、型塑社会团结边界的主要面向。除此之外,法治的“回应性”实际上还体现在各级人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检查;以及行政机关通过严格执法,对公共卫生治理落实不到位的情形、破坏公共卫生秩序的行为予以规制等。(38)相关事例,参见蓝峰:《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载《呼和浩特日报(汉)》2020年10月6日,第004版;张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卫生监督执法模式探索与思考》,载《中国卫生法制》2020年第6期,第91-93页。总之,法律的介入,一方面对那些破坏团结的人进行了惩罚,对潜在的团结破坏者形成威慑,避免少数个体的“越界”行为对整体防控努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向那些维护团结的人、守法和遵守规则的人传达出积极的信号,使人们相信,团结抗疫的局面无论如何都是国家和法律所全力保障和维护的。
第二是法治的“弥合性”。这一点与上边所讨论的法治的“回应性”有一定的关联,但又存在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指国家在法治框架下,在保障团结和整体防控的同时,也不忽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同时对整体防控中那些相对弱势的群体给予特殊的保护和照顾,使那些相对弱势的个体不会因疫情的整体防控而“掉队”,进而促进整体社会更大的团结。首先,是在维护社会整体安全的同时,不忽视对个体权利的保障,进而弥合社会整体安全与个体权利之间潜在的紧张。比如2020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中就指出,审理涉疫情劳动争议案件时,“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不难看出,这实际上乃是一种在法治框架下维护劳资关系稳定,进而避免分化,努力促进更大范围团结一致抗疫局面的基本措施;其次,是努力增进社会中那些相对弱势群体的福祉,以促进不同群体之间在抗击疫情时候更大的团结。比如2020年2月11日,民政部办公厅就曾发出过《关于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通知》,针对困境儿童提出“确保生活兜底到位”等要求;再比如2020年2月28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对于受疫情影响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因家人被隔离收治而无人照料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以及社会散居孤儿、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要组织开展走访探视,及时提供帮助,防止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这些政策和举措,从法治的角度平衡了公共安全维护与个人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以法治的方式努力避免相对弱势的群体被忽视,进而促进阻疫情防控时候更为坚固的社会团结。(39)相关研究表明,公共卫生法治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于实现公共卫生安全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平衡。参见申卫星:《公共卫生法治的价值取向和机制建设》,载《光明日报》2020年4月3日,第11版。
总之,法治对那些破坏团结的个体及其行为给予了积极回应,旨在努力恢复团结抗疫的局面;同时,对疫情防控中那些相对弱势的个体和群体给予了规范化、制度化的保障,努力建构更为坚固的社会团结。它以一种相对刚性的外在力量,在底线处保卫着社会团结,实际上也与大多数人所保有的责任伦理形成了有效呼应和配合。也就是共同保卫着绝大部分人以责任伦理为基础所营造的那种团结抗疫的局面。
六、理解危机中的社会团结
耶林说过:“私权,而不是国家法律,才是一个民族政治发展的真正的学校!如果人们愿意了解,在需要时,人们的政治权利和国际法的地位如何捍卫。那只需留意一下,个人如何在私人生活中主张其自身的权利即可。”(40)[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然而,在中国,此次疫情阻击战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人们相信科学。这与近现代以来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卫生服务在基层的广泛推开密切相关。(41)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参见刘雪松:《毛泽东与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载《党史文汇》2020年第2期,第18页。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也确立了“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也正因为科学知识和理念的积淀,以及对科学的信任,在疫情发生时候,人们会很快地进入到一个有关人与病毒(而非人与意义世界)的分类系统之中。团结一致对抗病毒成为普遍共识。这一时刻,对于社会团结的生成是至关重要的。在短短几天内,为了切断病毒传播的链条,城市一个一个地寂静下来。人们结束春节的热闹氛围,并迅速投入到一个关乎自己、也关乎他人的“战役”之中。正是科学,促成了有效的风险沟通,有效避免了在疫情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启动了团结、推动了团结,并成为了疫情发生时候团结生成的一种基本的推动力量。
在疫情面前,人们克制、让渡、互信、团结,普遍实践着“克己复礼”这一古老的智识传统。正是因为保有这种“责任伦理”,加之自觉遵从于基于科学的政策引导,人们相信,不随意外出、自觉佩戴口罩、配合检测、自觉隔离等措施,不仅仅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他人负责,进而是为整个社会负责。它是内在于人心的,是一种更接近于富勒所说的“愿望的道德”的心性,实际上也正是中国人“四海兄弟”的一种具体呈现。因此,“责任伦理”成为绝大部分人团结生成的一种最重要的内在保障。
人们构建起了一个与病毒对抗的团结的共同体,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共同体就自然而然地有序、稳定。事实证明,在危机和复杂的局面面前,团结的共同体的边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以及其它相关案例中,可以看到,无论如何,违法、“越界”行为还是时有发生。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很多在疫情防控期间处在相对弱势状况的群体和个体,仍需要得到特殊的关注和帮助。在这个时候,法律以一种相对刚性的外在力量出场。执法、司法领域的具体实践,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回应和规制了那些破坏团结的行为;同时,法律也弥合了整体与个体的潜在紧张,保护着那些相对弱势的群体和个体,成为了保障疫情防控、保障社会团结的一种重要的边界型塑力量。
总之,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科学主义、责任伦理和法治,共同交织起了一张“网”,使得危机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成为可能。在其中,科学以及基于科学的政策引导是社会团结生成的推动力量;作为内核,责任伦理保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互相负责”的集体意识的形成,从内部凝聚着社会团结;法治则从外部型塑着社会团结的边界,保障着社会团结的稳定和有序。
七、余论
从全球范围来看,关于如何有效应对疫情的讨论,从疫情爆发开始就从未停止过。而事实上,全球各个国家也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应对方案和策略。毋庸置疑,侧重于整体性的团结策略和侧重于个人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策略,乃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种面向。当然,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实际情况下也会适时作出一些调整。但是,这两种面向,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总体上型塑了此次疫情应对最主要的样貌。
相较于“自由主义”或“个体主义”的应对方案来说,团结一致应对疫情的方案,在中国,除有助于疫情快速得到有效控制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更为深远的和可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对我们自身经验的重新发现和思考。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一种被很多学者称为是被动的、防卫的现代化过程中,(42)相关讨论可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越来越多源自于西方的话语,在思想和社会实践领域逐渐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固然,“移植”来的新东西在某些方面会带来一些新的气象和积极的影响。然而,在一些情况下,移植来的“话语”和“表达”,不仅没有带来现代主义所预设的那种变化。相反,还产生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后果”。比如阎云翔在其研究中就发现,“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并没有带动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公众社会的负责”,以及“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情况。(43)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晓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页。在这种时候,反思“移植”话语及其实践,重新回到我们自身的经验和话语体系中尤为重要。
就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来说,团结而非个体自由至上成为了关键。危机时候民众那种有别于个体主义或自我中心主义的——基于配合、自觉地服从和参与的——对团结的坚守,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成为科学和法治两个关键因素之外,尤为关键和重要的一种内在力量,甚至还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的传播、国家动员和法治的生根落地。一方面,大多数人信守互相负责、遵守规则的理念,所以更趋向于统一的行动。这为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基于科学的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使科学和基于科学的政策的推动作用有了较为稳固的根基,进而从根源处避免了知识的离散不整及其可能会带来的社会分化;另一方面,责任伦理相对稳固地保障着人们的制度遵从,从内部维系着社会团结,这为社会团结的生成节约了大量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法治可以较为集中于针对特定情况的“回应”,以及实现对特定情形的“弥合”,有力地保卫着社会团结的边界,进而保卫着疫情防控的整体秩序。
这种力量将我们的关注视角拉回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场景之中,给了我们更多重拾自身经验、反思“移植”话语的可能。这正如一个多世纪以前,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一位西方人——所提出过的一个颇为有意思的讨论。他说:
有人说过,讲英语的民族,人们的血管中流淌的是某种不守法则的血液。这种血液使我们蔑视法律,一遇到约束就躁动不安。……也正因为我们勇敢的祖先这一特点,个人自由观念和天赋人权的学说没有经历了很长时间等待就得到确立了。但是,既然现在这些权利已经很好地确立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清醒一点,多多少少强调个人意志服从公众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努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呢?在这方面,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很多东西要向中国人学习吗?(44)同前注〔30〕,明恩溥书,第181页。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句褒奖的话。但是,引用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沾沾自喜。我想说的是,一场疫情,千头万绪,会让我们更多的重新认识和审视自己、重新认识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国家。回过头一想,诸如责任感、“克己复礼”一类的历史心性和智识资源,为何能在一场危机中发挥出如此大的能量呢?明恩溥说,他们应该有很多东西要向中国人学习。我们又何尝不应该更多地在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中不断学习和继续前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