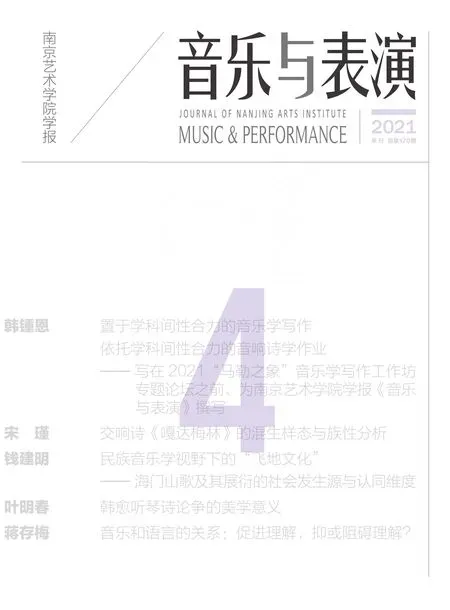静心·格己·古雅:《溪山琴况》中的乐境创构观 ①
—— 兼论与明代江南审美文化的关系
田婧媛(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教育高等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明代中晚期江南审美文化呈现出互通相生的两种倾向:一方面是受苏轼、陈献章等的影响,强化追求自然天趣、生意盎然的审美意境,推动江南文人关注自然和个体心性。如陈献章说“自然之乐,乃真乐也”[1]192-193、沈周的“心得之妙”[2]1088、文徵明的“至理在吾心”[3],以及之后的王阳明心学、李贽的“童心说”等强调凸显心性、纵情而抒。另一方面,前后七子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文艺创作主张“崇古尚雅”,研习古人诗书画,由表及里,“格物致知”的追寻和领悟古人质朴、高洁的人格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都呈现出“师古为心”和“化古为新”的创作观与境界观。此时,徐上瀛的《溪山琴况》也深受江南审美文化的影响,将形而上的乐理与研习和演奏相贯通,既追寻自然,又崇尚古雅,凸显出江南审美的诗意性与生活化。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多关注其中的道禅哲学等文艺观,而忽略了孕育出《溪山琴况》的明代江南艺术大环境。由此,本文从心性、研习和意境三方面进行研究,勾连诗书画艺术,以展现独特的江南审美特质。
一、自然之境,意造心像
江南文化在江南多水的地域特征与历代文化的交错和沉淀中,逐渐成为文人性的地域审美与代名词,也因此蕴含着独特的人文素养。明代中晚期,随着苏轼、陈献章和陆象山等关注主体性的主张传播与发展,江南审美更强化自然生机与个体意识。如陈献章说:“何须看画本,千丈在胸中。”[1]551自然中的物象与心境融通,绘画意象便由心生发,摆脱对景描摹,随之“率吾性情盎然出之,无适不可”[1]763,艺术旨在自适,关注生命本体意识。沈周作为江南地区的文人代表也说:“天池有此亭,万古有此月,一月照天池,万物辉光发。”[2]1099自然与人心相印证,文人以自然之心传递自然之意。其后,吴门画派以及江南地区都将这一主张落实于书画实践和日常审美中,并在体悟自然和感通心性中构建人格境界,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文人修养。
古琴作为文人性艺术形式之一,自然而然地受到时代影响,且类比观点与主张,规范自身的乐理。如徐上瀛说:“故当先养其琴度,而次养其手指,则形神并洁,逸气渐来。……有一种安闲自如之景象,尽是潇洒不群之天趣:所为得之心而应之手,听其音而得其人。此逸之所征也。”[4]78“琴度”是人格境界。一方面弹琴可以蒙养心性,另一方面人格精神的提升也带动乐境的生发,自然而然地“逸气渐来”。随后,人格与技巧相契合,得心应手,以琴声传递出主体的思绪和精神。
关于人格修养的内涵,徐上瀛引朱熹的话:“朱紫阳曰:‘古乐虽不可得而见,但诚实人弹琴,便雍容平淡”[4]77。镇定的气魄与从容的心态支撑琴声的呈现。这里,“雍容平淡”贴近于理学中的人格修养。从心而出的平淡、自然是古琴的审美旨趣。又如他说:“本从性天流出,而亦陶冶可到。如道人弹琴,琴不清亦清。”[4]77“道人”潇洒、散逸,是山林的化身,自然意境的流露。可见,徐上瀛主张的心性不是肆意的纵情,而是一种清逸,贴近自然的流露。这也是江南审美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质。
江南审美文化的发展脉络中,诗书画乐一直是文人自由精神的媒介,从中获得畅游与摆脱时空的限制。如张彦远说:“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时,坐究四荒……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5]在自然天地中抚琴畅神,陶冶心性。沈周说:“酒散襟裾爽,琴清徽玉秋。因之写高致,得似晋风流。”[6]423诗书画乐都是文人的雅趣与寄托情感之物。文徵明说:“静听涛声翠霭阴,松风一曲寄琴心。先生已得琴中趣,何事泠泠弦上音?”[7]1119自然之声便是琴声,自然与琴相通,人复归自然之境中。“此心应与山倶静,不是深山养不成”[6]157,文人以自然的旋律跳动着自然之心。明代众多文人画中,也描绘着山林中抚琴的景象。古琴之声仿若与自然生机融为一体,清雅、淡然的音律中,文人又仿若进入另一个悠远的世界。在此,古琴创构出一个独属于文人自己的精神空间,排除世俗的繁杂和纷扰,自得一份愉悦与欣喜。
《溪山琴况》中的“淡”况也旨在呈现一个精神空间。“舍艳而相遇于淡者,世之高人韵士也。而淡固未易言也。祛邪而存正,黜俗而归雅,舍媚而还淳,不着意与淡,而淡之妙自臻”[4]69。“淡”是古琴的至真之境,自在自然之间的显现,而非刻意寻求,是与心性的契合。也由此,这不仅是音律的问题,更是主体自身心性的感知。徐上瀛说:“故清者,大雅之原本,而为声音之主宰。”[4]54清洁、干净的声音是“大雅”之声。“大雅”是一种化归自然的境界,无杂质。在这样的“大雅”之音中,“古人以琴能涵养性情,为其有太和之气也,故名其曰‘希声’。”[4]132《溪山琴况》中描述的场景,是一幅幅的自然山间、鸢飞鱼跃的景象,亦如董其昌提出的“烟云供养”[8],在艺术中蒙养心性。最终追寻一个邈远、自在的大化之境。
文人的自由在艺术中被激活,古琴的旋律也与自然生机相萦绕,超越空间的限制,也越过当下的人生处境。乐节、乐章都以更抽象的听觉方式凝聚出自然的气质与精神,也由此暗合着主体的情感、人格。诗书画乐都依托心性而生。可以说,江南审美文化创构出的文人性空间中,艺术与艺术相依,成为文人的精神支柱。
二、规定技艺,格己研习
明代时期,江南经济繁荣,艺术品收藏和鉴赏之风盛行,文人“目鉴”到更多古人的作品,在研习与探索中,艺术的恒定性创作标准得以确立。如书法中强调以王羲之为宗,颜真卿、孙过庭、米芾等为支系;绘画方面,董其昌在“集大成”中提出“南北宗论”,为文人画明确画理与创作方式。可见,此时的江南审美文化关注艺术实践,强化自身技能的训练和研磨自心,以便自如顺畅地通过艺术语言呈现人格境界。
(一)格己琴艺
徐上瀛关注心性的呈现,强化通过技巧和技法体现出主体的内在精神。也因此,主体的技艺也与“清”相关,“指上指清尤为最:指求其劲,按求其实,则清音始出……此则练其‘清骨’,以超乎诸音之上矣”[4]54。劲道与技巧、左右手的配合等都恰到好处、从容不迫。 “从有而无,因多而寡,一尘不染,一滓弗留,止于至洁之地:此为严净值究竟也。”[4]94也因此,反复的练习,逐渐的揣摩,最终掌握古琴的演奏技巧。
同时,“指既修洁,则取音愈希;音愈希,则意趣愈永。吾故曰:欲修妙音者,本于指;欲修指者,必先本于洁也”[4]94。修妙音须连指,连指需妙音入手,两者相辅相成。也即是入门需正,开始练琴就以高标准要求自己。随之,不断的研习、捉摸,逐渐达到至高境界。
徐上瀛在此反复的强调弹琴的技术性问题,这也是陆象山所说的“格物者,格此者也”[9]。“格此”就是磨炼自己。由此,练就“清骨”达到“诸音之上”的演奏。“清骨”与清旷的人格修养相通,这也是强化着古琴演奏重在由技向道,技艺与思绪融通,创构出超然、高妙的乐境,而绝非刻板的对照琴谱的演奏。又如“必融其粗率,振其疏慵,而后下指不落时调。其为音也,宽裕温庞,不事小巧,而古雅自见。”[4]66“古雅”也是“清”的象征,主体是经过长期研习,弃精巧,返璞归真的表现。
关于弹奏古琴时左右手的用力方式与配合,徐上瀛也有说明:“左右手指既造就清实,出有金石声,然后可拟一‘亮’字。”[4]88左手清,右手实,延续古琴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演奏规律,弹奏出的音色将响亮,拨动人心,且余音无声之际也使人“神游于无声之表”[4]88。随之,“但能体认得静、远、淡、逸四字,有正始风,斯俗情悉去,臻于大雅矣。”[4]82左右手配合下的琴声,和谐、圆融,无艰涩和磕绊。整体的乐境“有正始风”也即是魏晋风骨。追寻魏晋,便是追寻古人以放浪形骸之外,潇洒、散逸的精神境界投入艺术创作,创构出空灵、苍古的艺术意象。而这也是江南审美文化所推崇的审美境界。如同时期,董其昌推崇黄庭坚的“书法清遒超朗,知其胸不挂一尘也”。[10]105他的《琵琶行诗卷》中笔力苍劲,提转轻盈,疏朗的行距创构出一幅空灵、淡雅的书法意象。在画论中,文徵明评画:“思致清远,无一点尘俗气。”[7]1366作品都全然的由心而生,诠释着主体高洁、清旷的人格境界。艺术家在长期的研习中掌握艺术规律,同时也摆脱外界纷扰,回归和自省内心。
可以说,主体反复的揣摩和研习古琴的流畅、轻重与和谐等问题不仅是技艺的研习,更预示着对主体心性的蒙养,完整的古琴研习经历了“格己”—心意—自然之道的抵达,也是从技法层将心性、自然相联系。
(二)心境清旷
首先,演奏前的心绪调整阶段。徐上瀛说:“地不僻则不清,琴不实则不清,弦不洁则不清,心不静则不清,气不顺则不清”[4]133,这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典型,僻静的环境中主体能够平心静气,调整节奏,不被外界打扰的进入准备阶段。随后,调整心绪,“未按弦者,当先肃其气,澄其心,缓其度,远其神”[4]133,先于琴曲,抵达乐境。亦如明代晚期李日华认为绘画“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10]261。艺术创作时须先调整呼吸和节奏,抚平烦躁,澄净心绪,在心中构造一种境界,自然而然地进入创作或演奏的艺术意境中。这也展现出,江南审美文化精微、细致的关注环境与器物,严谨的寻找和衡量创作环境。这是清雅、高洁的文人趣味,也是将文人的审美追求落于实处。
在演奏中,主体心境一直以“故欲得其清调者,必以贞静宏远为度”[4]56“贞静宏远”是对自然之理的感通。主体沉浸在自然的生机中,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随之,在平静、高远的心境中弹奏。古琴的音色和节奏,契合着自然之理,人与琴、物与我相生,情绪与韵律共生间,带动指尖的婉转,在闲适、虚怀的境界中感知,并以个体生命体验带动指法演奏。因此,静心是得“清调”的前期。亦如苏轼说:“适意无异逍遥游”,闲适、自适是人生之本,无功利状态是适合艺术创作的本源。“然后按以气候,从容宛转:候宜逗留……皆是一度一候,以全其终曲之雅趣”[4]56。调整呼吸,顺着琴谱的节奏弹奏,以琴谱带动技法带动主体感知,准确的呈现乐境中意趣与情思。
乐章转换时,“至章句转折时,尤不可草草放过,定将一段情绪缓缓拈出,字字摹神,方知琴声中又无限滋味,玩之不竭:此终曲之细也。”[4]114主体专注于当下的演奏,把握好每一个乐节和音符,细细体验和感受,而非预想下一个乐节。随之,自然的过渡,“‘昌黎诗: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其宏细互用之意欤。”[4]114细腻与恢宏的演奏转化在瞬息间完成,停留于前一乐节、或拖延至下一个乐节,都没有把握住节奏的变化。情感随乐章的转变也是干脆、利落。亦如李日华说:“‘以喜气写兰,以怒气写竹’。盖谓叶势飘举,花蕊吐舒,得喜之神;竹枝纵横,如矛刀错出,有饰怒之象耳。”[10]226在此,物象以人性化的方式呈现,一幅画中,绘制不同的物都需切换不同的心境,以契合对象特质,凸显独特性。可以说,无论是古琴还是绘画的完成,都需要主体高度的情绪配合。情感的投入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要素。
(三)余音缥缈
江南审美文化中的“水隐”观念,将一切艺术都变得极具意象性,也更加的追寻自然意境中那缥缈、无边,只可体验、感受,而无法阐明的妙境。董其昌说:“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朝起,看云气变幻,绝近画中山。山行时见奇树……看得熟,自然传神。”[11]画家游弋在变幻的景致中,汲取自然生机与生命意识,从而传神写照的将山林呈现于纸墨上。江南文人以自然山水淘洗心性,无时无刻不在遥望着自然之境。
古琴的乐境呈现也以自然之境为旨趣。徐上瀛说:“时为岑寂也,若游峨眉之雪;时为流逝也,若在洞庭之波。”[4]59这乐境,独属于个体性灵,是邈远的想象空间。这玄外之意的获得,不仅是通过反复的研习,更需要主体内心审美感知的升华,才能在体验中获得和创构出超越琴声之外的乐境,且通过声调语言传递于知音。
“诸声淡则无味,琴声淡则益有味。味者何?恬是已。味从气出,故恬也。”[4]73一般乐器平淡后是一种无味、干涩,而古琴的“淡”是“恬”,淡中见欣喜、淡中有滋味和回味,是对自然生机的欢喜,而非禅庄哲学中的五色无味、空寂世界的诠释。可以说,这便是一种审美通感和艺术通感,不仅是听觉,更由听觉蔓延入其他感官,从而化入精神,调动起主体的回忆、思绪,即使声音消失,回味无穷的思绪,逐渐的生发出独特的美感。亦如同时期江南文人陆时雍说:“气韵高雅,意象更入微茫”[12],何良俊说的“微婉而深切”[13]都关注那些幽微隐约,引起内心悸动的审美特质。这也正是江南审美侧重感性、体验的审美主张。
可以说,徐上瀛对古琴理论的诠释,是基于长期的研习与演奏而形成的,古琴是与自身精神相似的器物,高超的琴技也意味着塑造出一个清雅高洁的自己。这也与同时期关注技艺实践的其它艺术主张相共通。因此,明代江南审美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完成来自日常的践行,从细微处入手,亦步亦趋的磨炼技艺也是将内在审美自觉与外在审美行为相统一,将人格理想落在实处。
三、以古为雅,归复自然
明代人心涣散,党争伐割,为延续文脉,文人寄希望于学古,主张以古人简朴、安宁的精神净化风气。江南审美也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崇古拟古。此时,文人阶层的文化主张都以期在古人精神的指引下打破奢靡、虚弱的社会风气,创造独属明人的审美意境。古琴作为古乐的传承,一直追求古人的审美旨趣,《溪山琴况》更加注重古雅、古韵,强化与其他乐器的差异。
首先,推崇古琴是对上古之音的复兴。“调无大度,则不得古,故宏音先之。盖琴为清庙明堂之器,声调宁不欲廓然旷远哉!”[4]110广袤、邈远的古调才能呈现出恢宏大气的高格。亦如:“盖指下之有神气,如古玩之有宝色,商彝周鼎,自有暗然之光,不可掩抑,岂易致哉?”[4]90古器虽经过时间氧化而脱落曾经的外貌,但其精神依旧,即是黯淡无光,也依然透出铿锵、坚毅的光芒。可以说,这不是视觉形式的动人,更是主体在通感、感知中体验到的古器那无形的气质。而崇古尚雅,便是强调人从感性欲望中挣脱,摆脱人为的故作与束缚,自觉地实践古人内省式的境界中,以“从心所欲不逾越”的心境,开启悠然自适的畅神境界。
徐上瀛从古今对比的角度说,“丽者,美也。于清静中发为美音。丽从古淡出,非从妖冶出也”[4]85。清丽、秀美的旋律源自古音,带着古人的精神与气韵,悠远而绵长,也只有内心宽广的演奏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然必胸次磊落,而后合乎古调;彼局曲拘挛者,未易语此。”[4]111上古之音属于回荡和叩问心灵的声音,内心的情韵,随着音律的婉转而和缓流露。“淡音而会心,吾知其古也。”[4]64古琴发出的“淡”声是有厚度和力量的意义,穿透心灵,引起震颤的声音,而非一时的欢愉感。反之,“声争而媚耳”,表层音律的叠加,美感仅限于音乐本身,而不能牵引人的思绪。也因此,“效颦者”[4]85只模仿了表象形式,浮夸而繁杂,俗态百出,毫无意蕴。
明代时期,文人强化对雅与俗的划分和剖析。杨士奇从雅俗之辨的角度说,“雍雍古与淡,淳雅之音,盖使人襟宇澄净,气志皆融”[14],淡淡古意,使人沉静心灵,退去浮躁和杂乱,回归平静、安宁的心境中,悠远弥久。戚继光认为琵琶、三弦琴、胡琴和月琴等是“时之俗乐”[15]257,“俗调如嚥肉食饴,而雅调如嚼玄嗽苦,滋味深长,万听不厌。”[15]257,使听觉获得刺激,让人兴奋或哀伤,“俗乐”刺激人的感官神经,而“雅乐”,深远绵长,是壮丽之美的代表。随之,徐上瀛明确了这种“淳雅”来自古音,古琴的音律之美在于呈现出古拙、古朴的乐境。上古之人与自然相依,物我两忘中毫无对理智、欲望的追求,全然的放松状态。古琴以此为旨趣,便将获得同样的欣喜。《溪山琴况》是以古为雅的代表。这样的“雅乐”中含有着士人精神,清丽、简洁的乐声,凸显澄静胸次、潇洒率性的人生追求。亦如当时的书画艺术,复兴晋唐、探索宋韵等,都是为了倡导由俗返雅,以古生新,而非以俗为雅,穷奢极欲的流于鄙俗。
其次,以古为雅也是回归自然之境。“试一听之,则澄然秋谭,皎然寒月,湱然山涛,幽然谷应;始知弦上有此一种清况,真令人心骨俱冷,体气欲仙矣。”[4]56空谷幽兰,归于自然。自然之境中主体回到至真之境,回荡自己内心的世界中。“吾爱此情,不絿不竞;吾爱此味,如雪如冰;吾爱此响,松之风而竹知雨,涧之滴而波之涛也。有寤寐于淡之中而已矣!”[4]70自由舒适、物我相合在自然中,是乐境的至乐之境。自然、自由的境界便是美的境界,也是古人将精神自由于一体的审美境界。
从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先秦乃至汉代,音乐存在的意义都在于使人进入绝对的美、原初的“道”,是体道和悟道的媒介。如老子说:“大音希声”;《淮南子》:“听有音之音者聋,听无音之音会者聪;不聋不聪,与神明通。”[16]这里是一种无言之美。“无音”世界的静谧感使人超越感官体验,剔除理智、欲望和分析等,内心世界自在呈现。古琴作为一种生发出悠远、沉静之声的乐器,也随之成为“大雅”之音。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理即是道的主张影响下,将古典美学中追求形而上的无声之音,落入对有声世界的把握,音乐更趋向自然之声。而明代江南审美文化尤其强化对自然的体悟和感通。也因此,《溪山琴况》的古琴批评主张,便重在感知自然的空灵之境。这一方面是以老子“大美无言”的主张,作为古琴艺术的形而上观念的旨归,另一方面也将形而上的观念实践于古琴艺术中。《溪山琴况》以诗性的语言对艺术范畴进行归类,每“况”相互勾连与交叉,诠释古琴的弹奏技法与境界,将形而上的体道、悟道等哲思,以诗话性表达方式落实于乐论与实践中,推动古琴理论的发展。同时,这种诗意性的言说方式,也源自江南审美语言。
总之,明代江南审美文化不仅探究在鸢飞鱼跃的自然之境中安顿心性,也关注艺术形式、创作技法,并以艺术语言传承精神文脉。《溪山琴况》受大环境影响,重构古琴理论,从自然精神、规定琴技、古雅境界,这三方面集成出古琴的审美内涵,体系化地诠释也改变了一直以来的形而上言说,也使古琴更进一步融入江南文人审美化的日常生活,成为诗意“栖居”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