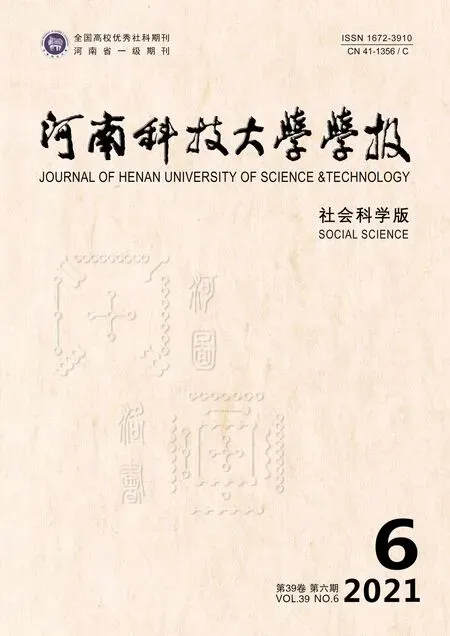李杜诗篇中的洛阳书写与家国意识
黄 婕
(河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471023)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大分裂时期,思想、民族、宗教等碰撞融合,赋予中国文化新生的力量。隋唐时期再次形成统一帝国,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活动空间都有飞跃性提升,愈发习惯用诗这一简练的语言形式抒发情感和反映生活。“中国文学史上,特别突出地存在着两个‘shi’的世界——平声的‘诗’和上声的‘史’。对把握波澜壮阔的中国文明也极其重要。”[1]
一、唐诗中的洛阳
唐代的洛阳既有魏晋故都的特殊地位,又是长期比肩长安的东都,城市命运与王朝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浩如烟海的诗作中,唐代诗人对洛阳表现出格外的偏爱。以地名为关键词检索《全唐诗》可知,题目或内容中出现“洛”的唐诗有1 215首,远超“长安”的696首、“扬州”的116首、“金陵”的114首(1)根据郑州大学全唐诗库电子检索系统(http://www3.zzu.edu.cn/qts/)2020年9月1日检索的结果。。诗歌是一种个体视角的多向性的叙事,“洛”字频繁在唐诗中出现,说明这个时期的洛阳与整个唐时代的文化现象与文化元素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唐诗中的洛阳书写是阅历、年龄、阶级、生活背景各异的文化阶层从众多角度、不同立场对这座城市的观察和认识,具有现实属性和社会属性。被誉为唐诗最高峰的李白和杜甫,作品中都存在大量、持续的洛阳书写,虽然呈现出来的洛阳形象风格相异、各成一体,但以安史之乱为界,超越具体地域范畴成为一种象征,明显是被作者有意识地注入了家国意识。
二、安史之乱前李杜的洛阳书写
(一)李白的盛世洛阳:繁华与深情
李白出身成谜,诗人自己也语焉不详,有“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2)本文引用李白诗文出自清代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杜甫诗文出自[清]仇兆鼇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白本家金陵”(《上安州裴长史书》)、“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赠张相镐二首》)等数种说法,令后人困扰。方家多有考证,结论不同,甚至有人提出了李白是洛阳人,因少年犯事而举家外迁之说(3)王元明持此看法,出版著作《中国唐代诗人研究——李白新论》(新加坡新社2000年版)。。此虽一家之言有待考证,但洛阳无疑与李白渊源深厚。
李白一生羁旅,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史书明确记载有多个时期曾居留于洛阳。他往来于洛阳时正值唐朝鼎盛,在繁华的洛阳城中呼朋唤友、赏花饮酒,不亦乐乎。“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古风十八》)记录繁花如锦的街市人家;“朝发汝海东,暮栖龙门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描写深秋清寒中的龙门夜色;“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洛阳陌》),刻画陌上乘车赏花公子风度翩翩、惊艳了众人。
李白深受道教影响,但从其“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又可见鲜明的儒家烙印。长安仕途受挫,李白断绝出将入相的抱负,转向山水诗情,还表现出对隐遁修行的向往。东都市井繁华、周边多山川风物,成为李白访道问友、纵情诗酒的好去处。
天宝三载(744年),44岁的李白第一次与33岁的杜甫相会于洛阳,这次会面,被闻一多称为“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2]。此外,高适、元演、崔成甫、岑参、元丹丘等,都曾在洛阳及周边一带与李白结识或交往,这座古城是见证李白与“海内贤豪青云客”的聚散之地。其《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
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
海内贤豪青云客,就中与君心莫逆。
回山转海不作难,倾情倒意无所惜。
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梦思。
不忍别,还相随。
天子脚下的长安是权力博弈的政治中枢,孤高自傲的李白深感“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同样繁华的东京洛阳既远离暗流汹涌的政权斗争,又可与意气相投之士恣情诗酒,惺惺相惜,正合他意。李白傲岸不羁的表面之下深藏一颗赤子之心,他理想中的友情洒脱畅快,是以洛阳为背景的:“君马黄,我马白。马色虽不同,人心本无隔。共作游冶盘,双行洛阳陌。长剑既照曜,高冠何赩赫。”(《君马黄》)
春风沉醉的夜晚,诗人也会触景生情:“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春夜洛城闻笛》)朋友们天各一方时,诗人无限牵挂,在心目中设定的再会地点还是繁华喧闹的洛阳街市:“仆在雁门关,君为峨嵋客。心悬万里外,影滞两乡隔。长剑复归来,相逢洛阳陌。”(《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即使多年后时移事易,诗人仍然怀念“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叙旧赠江阳宰陆调》)的意气风发。
这个时期的李白既有笑傲王权的磊落,也有寄情诗酒的飘逸,笔下的洛阳形象有两个特征:一是繁华美好,二是充满深情。这不仅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也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投影。即使偶尔抱怨都市生活的喧嚣浮华,说“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烦”(《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言语之间仍然可见洛阳所承载的愉悦美好。
(二)杜甫的现实洛阳:故乡与逃离
杜甫祖上数代居于洛阳周边,出生地有巩县笔架山下、偃师首阳山等说法,均在洛阳一带。其十三世祖杜预文韬武略过人,“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还特意要求使用“洛水圆石”,认为“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3]。杜预是杜甫最崇拜的先人,他的《遗令》将世代祖茔设置在洛阳,相当于冥冥中已经把杜氏家族与这片土地紧紧绑定在一起。
杜甫祖父杜审言多次任洛阳丞,也葬于首阳山下,留下不少关于洛阳的诗文,如“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春日京中有怀》)等。杜甫4岁时生母早丧,长期被寄养于洛阳仁风里的二姑母家。他撰写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对姑母的哺育之恩感激涕零。反映杜甫青少年时代的诗作存留不多,诸如“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等极富有生活气息,但很少把“洛阳”写入诗里。其《壮游》: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
这篇自传性的叙事诗是了解杜甫人生轨迹的重要材料。他少年时期的活动范围以城东建春门附近的仁风里为主,少时已颇有诗名,有机会接触河南府尹韦济等当地官僚名士,生长在世代奉儒守官的中原传统家庭中的正统儒家气象依然可见。
青年杜甫身在洛阳却向往外面的广阔世界,19岁开始四方漫游。期间回洛次数并不多,有重要事务才会停留在家,比如24岁回洛参加乡贡进士考试,竟未中第。诗人怀着尴尬与愤懑出游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地,30岁回洛结婚,直到33岁在洛阳得遇李白。
杜甫对洛阳的怀乡之作都在战乱离家之后。他多次游览、住宿于龙门。留下了“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游龙门奉先寺》)和“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龙门》)等名作。然而诗文流露出的情绪并没有局限于所处之地,比起眼前的清幽古寺和壮丽皇居,他着眼于更大的宇宙,两首诗文的后半部分都是对人生和世界显现出诗人有生之年征途不止的壮怀。
那时的杜甫不仅无心流连眼前的风景,甚至因科举不利而厌恶东京的浮华虚伪。他特别不满充斥城中的投机钻营之辈,以至于对洛阳的生活也持一种否定态度。《赠李白》开篇即“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一个“客”字,尽显诗人刻意与这座城市划清界限之意。也许自哺育他成长的姑母卒于仁风里,这座城的熙熙攘攘于杜甫来说就只剩下了“为名而来、为利而往”。刚直质朴的他深感怀才不遇,认为这里的生活是“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赠李白》),表明宁愿去吃食不果腹的蔬食粗饭,也不愿沾染上恶俗的腥膻之气的高洁志向。这与少年时代的“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壮游》)一脉相承,虽生斯长斯却对这里的势利庸俗心生抵触,一心想逃离。
三、战乱中李杜的洛阳书写
(一)杜甫心中的“家”
万国来朝的大唐一片歌舞升平,755年被玄宗倚为“安边长城”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一个月便攻下东都洛阳。44岁的杜甫身在长安,猝然发生的战乱让他有家不能回,开始隔空追忆当年、真正审视故乡的存在。洛阳在杜甫诗中的形象迅速发生变化,曾经的不屑与否定情绪再也没有出现在其诗作中。其《遣兴》:
我今日夜忧,诸弟各异方。不知死与生,何况道路长。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怅望但烽火,戎车满关东。……生涯能几何,常在羁旅中。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烟尘阻长河,树羽成皋间。回首载酒地,岂无一日还。丈夫贵壮健,惨戚非朱颜。
诗中的洛阳不再是虚伪浮华的名利场,而是亲友嬉闹、充满愉快回忆的地方。在追忆因为战乱而回不去的故宅以及亲朋畅游的美好时光时,诗人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只有在洛阳时才是主人,才能“送客”,此后就只能“客子念故宅”“常在羁旅中”了。《遣兴》组诗中的洛阳书写,让洛阳在杜甫诗篇中完成了从物欲横流的名利场到充满成长回忆的“家”的角色转变。文末“回首载酒地,岂无一日还”,诗人一边回忆故园,一边相信总有能够回去的一天。
然而现实残酷,担任华州司功参军的杜甫曾于758年底回过一次洛阳陆浑庄的旧居。此时的洛阳虽然从叛军手中被夺回,但久经战乱、面目全非,诗人不得不承认“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得舍弟消息》),这是杜甫最后一次回家。759年,杜甫辞官带领全家彻底离开洛阳,开始“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逃难》)的生涯。但不管走到哪里,诗人始终心系家乡洛阳,遂有了“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恨别》)等诗句,这都是写给故园的情书,正如诗人自嘲的,“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五盘》)。
宝应元年(762年)冬唐军收复洛阳,正流寓梓州的杜甫于次年才听到这个消息。52岁的诗人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被清人浦起龙赞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4]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并特意加上自注:“余田园在东京”。
可惜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的洛阳一带仍然战乱不止,加之从蜀到洛,路途遥远,贼寇横行,事实上杜甫根本无法带领一家返乡。随着年龄增长,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烈:“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至后》)得知友人将赴洛阳,立即委托他访问东京旧宅,还连写多首诗作相送:“平居丧乱后, 不到洛阳岑。……十载江湖客, 茫茫迟暮心。”(《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在日暮时分面对滔滔江水悲从中来,作 “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天边行》)。洛阳成为杜诗中的一个符号。770年杜甫病逝于岳阳附近,临终嘱咐要入葬洛阳杜氏祖茔,然而这个心愿直到四十余年后才得以实现。813年孙子嗣业历尽千辛万苦才将其遗骸背回洛阳,与祖母杨氏合葬于首阳山下——诗人终于魂归故里。
(二)李白心中的“国”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其十九)》
这首诗作中的文学价值常被提起,浪漫逍遥的仙境与污秽血腥的人间形成强烈反差,袁行霈特意以此对比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5]。
实际上,相比于文学价值,这首诗更适合分析李白的经历和思想。历代学者都试图据此分析安史之乱初期李白的行踪,明代朱谏认为此时李白在庐山隐居,清代王琦则吸收借鉴元代萧士赟注提出的“此诗似乎记实之作,岂禄山入洛阳之时,太白适在云台观乎”,认为“此诗大抵是洛阳破没之后所作,胡兵谓禄山之兵,豺狼谓禄山所用之逆臣”[6]。览久美子认为当时李白在往南方避难的途中,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考证《奔亡道中五首》,认为李白当时在洛阳周边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郁贤皓则认为此诗为天宝十五载春初在华山作,李白当时正在梁苑(今河南商丘)至洛阳一带,目睹洛阳沦陷,乃西奔入函谷关,上华山。[7]
李白以往的诗歌多带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而其晚年作品中与“洛阳”相关现实事物反复出现,并伴随着大量用典。如《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双鹅飞洛阳,五马渡江徼。何意上东门,胡雏更长啸。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太白昼经天,颓阳掩余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开篇即用三个与洛阳相关的典故,借五胡政权皇帝石勒,强调和比喻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和征兆。
除此以外,还有“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扶风豪士歌》)“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奔亡道中五首之四》)“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猛虎行》)等,都较多地加入细节描写,相对写实地渲染当时洛阳的惨状,读来惊心动魄。
因文风差异,有人曾疑这个时期的白诗可能为伪作,清代王琦多方考证后将李白晚年诗作收入《李太白全集》。事实上,不只是诗风,这个时期李白的行事作风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几乎完全摒弃了以往对归隐山林、求仙入道的追求,也没有偏安一隅等待时局改变,而是以实际行动实现匡扶天下、济世救民的宏愿。
小川环树指出,李白将59首诗自命为《古风》时,就已经显示出欲一扫当时世上安逸沉滞,重振建安雄风之意,他亲自承担起这个责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8]。是中原横溃、洛阳失陷激发了李白的爱国心,他比任何时候都关心时政,拜托姓武的门人护送妻儿到安全的地方,骨肉生死离别之际叹息“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赠武十七谔》);为了避难不得不向北逃难,沿着太行山行进时感慨“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前行无归日,返顾思旧乡”(《北上行》)。
他报国无门,当永王李璘为讨伐安禄山招募将领时,立刻加入永王幕僚追随永王。期间作品多为安抚军中的情绪、鼓舞士气之作,如“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即使奔逃流亡也心怀天下、不改其志,“欃枪扫河洛,直割鸿沟半……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南奔书怀》)。
李白从璘的历史真相曾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邓小军指出作为亲历者之当时实录,从璘前后所作一系列相关诗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9]。“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永王东巡歌之五》)此处的“河南”指洛阳。直白的情感抒发和语言表达,很难与当年“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岸洒脱联系起来。平实的词句中包含对“诸侯不救河南”的愤怒、失望,以及无奈之下对“贤王”的期待,一如其自述 “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与贾少公书》)的悲情。
胡骄马惊沙尘起,胡雏饮马天津水。
——《江夏赠韦南陵冰》
胡马渡洛水,血流征战场。千门闭秋景,万姓危朝霜。
——李白《狱中上崔相涣》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
——《赠张相镐二首 时逃难在宿松山作》
异族铁蹄下的洛阳激起李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之志。尽管他晚年辗转流亡,因反叛罪名入狱,却时刻关心洛阳收复,却以史笔写出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诗。当从流放地被赦免时恰闻两京收复,他立刻作《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胡兵出月窟,雷破关之东。左扫因右拂,旋收洛阳宫。”可见收复洛阳几乎已经成了李白的执念。可惜759年史思明又称大燕皇帝,再次攻陷洛阳。761年,李光弼在洛阳北邙与叛军展开苦战,无奈仍是大败。此时已61岁高龄的李白在金陵靠人接济度日,得到消息后请缨加入李光弼军幕府,途中病倒,被迫返回。次年十月洛阳终于被唐军收复时,距离诗人的病逝仅一个月。李白临终是否得知已无考证,但从被认为是临终绝笔的“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终歌》)来看,也许那是诗人对中土洛阳最后的牵挂。
四、李杜诗篇中的洛阳与家国意识的形成
作为共同经历过盛唐荣光的李杜,双峰对峙,并列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世人印象中李白的诗作是乐观浪漫主义的代名词。如吉川幸次郎所论:“李白与杜甫的诗相反,忙着歌颂人间的快乐。”[12]《沧浪诗话·诗评》中“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之语已经深入人心。然而,所谓“飘逸”和“沉郁”是指整体风格,具体到安史之乱时期李杜诗篇中的洛阳书写却不尽然。国破家亡中,杜诗的“洛阳”总是与家人、故园相伴,哀婉深情;李诗的“洛阳”则总是与民族、国家相连,沉重惨烈。
(一)家国意识与文化认同
安史之乱前,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青年杜甫久居洛阳,曾经讨厌东京喧闹奢华、追求名利的都市性格,为了与这种势利的风俗划清界限,他故意不把这里当作故乡而渴望离开,一再强调自己是“客”。可当洛阳沦陷、真的回不去时才深切感受到洛阳对于自己“家”的意义,其认知经历了从浑然不觉、到心有抵触、再到强烈思念的过程。杜诗中的洛阳书写也从喧闹浮华的“载酒地”到魂萦梦系的“家”,情感寄予由“所历厌机巧”的年轻气盛,到“天边老人归未得”的悲凉沉郁,令人寻味不尽。
李白道教与儒教并存的思想特质常被论及,被称为“谪仙人”的他曾经四海为家,并不特别将情思拘泥于一乡一地,很享受洛阳的繁华喧嚣和远离政治中枢的逍遥。松浦友久认为,李白虽有《静夜思》《春夜洛城闻笛》等表达故园之思的名篇佳句,但都是象征性的表达,缺少持续性地对某一具体地点表达怀乡之情,是因李白“社会关系的非恒常性、客寓性”[11]所致。因此,与杜甫诗中切实的怀乡情结相比,李白晚年的洛阳书写多是民族、国家的象征,能代表多数文化士人对洛阳的普遍认识。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分裂与文化融合后,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来临,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压倒性的实力造就唐代士人普遍具备的乐观大度、开放自信的精神特征,人们或豪放洒脱,或自由浪漫,或克己守礼,迥异的个人性格表象之下都深藏着强烈的文化自豪感。然而,异族的铁蹄击碎了这份自信,鲜花如锦、游人如织的洛阳转眼间成为胡尘蔽日、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迫使士人不得不直面国家与文化存亡的危机。打着“清君侧”名目起兵的安禄山,一入洛阳便即帝位,随后攻下长安,并没有继续进攻四川和江南,而是把长安的府库、兵甲、文物等统统迁往洛阳,甚至后宫美人、演奏《清平调》的梨园弟子、御苑中饲养的珍兽等都不放过,俨然有改朝换代、长期盘踞中原之势。东京洛阳沦陷并成为异族王朝的新都,意味着现实中唐王朝的“国破”,同时也意味着华夏文化被颠覆和否定。正是这突如其来的现实刺激迫使文化阶层的家国意识逐渐呈现,李杜诗篇中的“洛阳”恰好承担了连接现实与家国意识的功能。
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族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如《战国策》中对“中国”的描述:“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12]尽管大唐统治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人,但自称“老子后裔”,目的就是建立大唐政权继承华夏文明的正统性。盛唐的开放包容也源自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特质。有学者指出:“多重力量共同促成了以安禄山为代表的安史胡文化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以文化共同体的视角观之,‘安史之乱’产生的诸多原因中,国家之民族文化政策至关重要。在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迥异于儒家礼乐文明的安史集团,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离心力。”[13]安史之乱与普通政权之争或农民起义的性质不同,企图动摇华夏文明的根基,必然是文化士人最不能容忍的地方。
以文化自负的唐代士人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不厌其烦地强调洛阳被“胡”所占,正是源于人们不能接受异族企图建立新的王朝取代华夏文化。李白曾经对“胡姬”“胡乐”所持有的欣赏包容态度,是建立在对汉文化热爱和极度自信的基础上。其晚年诗作中洛阳伴随着“胡”字反复出现,“狄犬吠清洛”“胡马渡洛水”“洛阳三月飞胡沙”等措辞明显体现了诗人以华夏文化为正统的自觉。“澄清洛阳水”“志在清中原”等誓言,既是有意识赋予洛阳象征性意义以维护心目中“国”的完整,也出于对华夏文化的捍卫。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 ”[14]二人文学作品的价值毋庸赘言,其思想、人格的影响力也在时代发展中越来越得到肯定。随着李杜诗篇的广泛传唱,洛阳书写在打动人心的同时,无形中推动了家国意识的形成。如果说洛阳在杜诗中的故园形象是身份认同,在李诗中与“胡”的对立则是民族认同,这两种认同归根结底都出于文化认同。唐代诗歌主潮由盛唐的理想主义浪漫诗潮向着盛中唐之际的现实主义写实诗潮嬗变,唐代文化由盛唐的多元开放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向着盛中唐经世务实、 主尊儒学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转型的表现[15]。在这场危机中,李杜诗篇中洛阳形象的改变引领和推动唐代诗歌的转型,同时也是唐代文化思潮嬗变的一种先行体现。
(二)洛阳承载家国意识的原因分析
洛阳能够成为李杜诗篇中家国意识的载体并非偶然,除了当时安史之乱的现实因素以外,还与它特有的亡国之痛与文化之殇密切相关。
1.历史根源——国殇。“家国”一词属于政治哲学范围,来源于《礼记》《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尽管王朝更替,由华夏文化衍生出来的汉文化一直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源自礼乐制度的儒家社会所提倡的家国观,影响中国数千年而不衰。洛阳是经过反复占卜、在被认为是“天下之中”的位置上建起的,周公在此制礼作乐,从诞生伊始就被赋予了天命和正统的光环。
文化认同感是在与周边的关系中自然形成的。一直处于汉文化中心地位的洛阳经过数次王朝更替,每次都伴随着黍离之悲。五胡乱华以洛阳城的失陷为标志,异民族政权打破华夏汉族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原地区的主人。对于长期怀有华夷意识的汉人(这里指基于对华夏文化的认同而形成的群体)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国破家亡的同时,文化方面的优越感也被击碎。北魏统一中原后,为与江左南朝争夺华夏正朔,迁都洛阳借河洛的地望强调自己的汉化程度和正统性。北朝文人因为政治或自身文化认同的需要,强调河洛中原的文化中心地位;南朝文人则出于对故国的怀念而凭想象对洛阳进行美化处理。在长期南北对峙中,双方对洛阳的认识和定位一致,即在强调“华夏正统”的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方面,中原核心位置的洛阳是最前沿、最正统的“汉文化”的象征[16]。
安史之乱相当于历史的重演,和平时期并没有特别在意的家国意识,随着家与国的丧失而变得格外鲜明。“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杜甫《洛阳》)李杜之外的诗人也多将“胡”字写进关于洛阳的诗作中,都是在有意识地强调华夏文化属性。“天津桥上多胡尘,洛阳道上愁杀人。”(冯著《洛阳道》)“胡骑北来空进主,汉皇西去竟升仙。”(韦应物《洛阳吟》)等等。中唐后赵匡、啖助、陆淳提倡《春秋》,韩愈写《原道》攘斥佛老,也是源自对汉文化存续的危机感。
2.文学传统——乡愁。乡愁本身就是渴望文化认同的一个表现,原指在异国他乡怀念故里的一种情思。海德格尔的名言“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可以理解为文化阶层终生都持有寻找文化认同与自我归属的渴望。松浦友久提出:“‘洛阳’这个地名带有独特的含义,这个韵味无论是‘长安’、‘金陵’还是‘成都’都无法替代。”[17]指的应该就是洛阳文化内涵中自带的乡愁意象。
早在西晋就明确出现了洛阳的秋风与乡愁的关联性——张翰在洛阳“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苑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忘,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18],以至于秋风、洛阳、乡愁的组合形成一种文学传统沿袭下来。此后的“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张籍《秋思》)和“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张说《蜀道后期》)都有延续这一传统的痕迹。
“衣冠南渡”以来,即使江南富饶,终究不能完全抚慰文人们丧失故土、民族受辱的痛心之情。故都洛阳,不仅仅是在政治意图上必须夺回的战略目标,也是南朝文人集团用于怀乡的共同心象风景。橘英範发现《乐府诗集》中以《洛阳道》为题的诗作多达18首,但大多数在诗作中反复吟咏洛阳的南朝诗人实际上从未到过洛阳。他们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洛阳形象多为“俊男美女在春光明媚的大道上邂逅的繁华都市”[19]。对这座城市的美化书写,说明洛阳从整个时代的追忆对象演变成了寄托理想的载体。
南渡士人对故都的怀念中交织了亡国之恨与民族屈辱感,深化了乡愁的内涵。“传闻合浦叶,远向洛阳飞。北风尚嘶马,南冠独不归。”(《遇长安使寄裴尚书》)“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陈子昂《春夜别友人》)“可怜江浦望,不见洛阳人。”(宋之问《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武元衡《春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齢《芙蓉楼送辛渐》)“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王湾《次北固山下》)“醉来忘却巴陵道,梦中疑是洛阳城。”(储光羲《新丰主人》)这些名作令洛阳的文学乡愁意象更浓。2006年日本朝日新闻出版的洛阳特辑被命名为《乡愁之都》,可见这种乡愁超越了狭义上的一己之乡的故土概念,逐渐成为一种对文化原乡的精神依恋。
五、结语
大唐国力鼎盛时期,整个社会对异族文化呈现友好包容态度,而文化阶层在安史之乱新的生存状态中开始对社会和文化问题进行深度反省和思考,以李杜诗篇为代表的唐诗中,洛阳书写体现出家国意识,与中国文化的构成与走向有关联,是社会心理积聚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现象。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谱系里,“家”是个体人生的起始之地,国之基础;“国”是民族与文化认同的体现,家之延伸。因主张文明冲突论而著名的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并且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20]。洛阳的文化内涵具备家国之思的基本特质,加上李杜两大文学巨擘的反复书写,终于成为特定历史时期中承载家国意识的象征。
在诗歌中注入家国意识也由此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传统。宋代以后中原再次板荡:“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文及翁《贺新郎》)“戎虏乱中夏,星历一周天。干戈未定,悲咤河洛尚腥膻。”(张元干《水调歌头》)再次呈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是对李杜诗篇中洛阳书写的继承与发扬。伴随着亡国之痛与文化之殇,家国意识经过沉淀,形成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凝聚力,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