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热烈而忧伤
孙逸飞

一个人在历史上和文学上的形象常相差甚远,魏文帝曹丕常常以篡汉和逼迫兄弟的阴谋家形象出现于史书,直到民国时期,人们还常常以曹操比喻袁世凯,以曹丕比喻袁克定。相比之下,被逼七步成诗的曹植则显得光风霁月,文采飞扬得多。但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了一句公道话:“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当你翻开曹丕的文字,能感到热烈的生命和忧伤。
他给朋友的书信《与吴质书》充满淡然哀伤的感怀气质,你很难想象这是出自手握重权,就快要被立为魏王世子的人。你可能也很难想象他为什么能代表这类忧伤的情绪。按大家的印象,他是皇位争夺的赢家,他弟弟曹植应该比他更有资格感怀。毕竟曹植是传说中被逼迫七步成诗的人。
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这个乱世刺激了文化思想的活跃,文人们开始用道家、佛家思想以及个体情感来消化生命短促、人生无常这些困惑,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人们的苦恼、焦灼、哀伤和悲凉情绪混合在一起,又被玄学思想所调和,就酝酿出了感怀。
曹丕虽然贵为世子,但成长极为坎坷,建安二年(197年),曹丕随曹操南征张绣,张绣先降后反,曹操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遇害,年仅十岁的曹丕乘马逃脱。而曹操长期在立嗣上狐疑不决,难免不影响下属。时间一长,下属间渐渐形成了拥丕派和拥植派两个集团。拥植派中的杨修是个智谋过人的奇士,又身为曹操的主簿,消息特别灵通,对曹植十分有利,在他出谋划策之下,曹植在这场争夺战中渐占优势,“几为太子者数矣”。这些经历对曹丕的身心带来严重压抑,也间接成为曹丕登位7年就去世的原因之一。

这种矛盾性,跟曹丕文学上的感怀特质如影随形。在建安二十年(215年),曹丕见到时节推移,想到昔日的朋友、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死去两年多,心生感伤,就给他的朋友、当时的朝歌令吴质写了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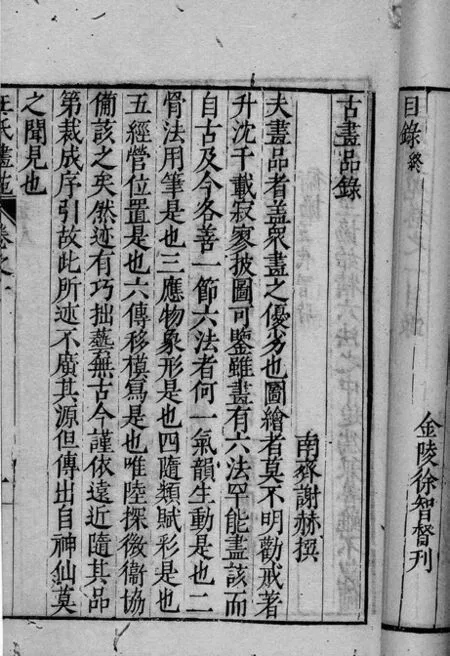
完全忘掉曹丕的身份,哪怕不知道作者是谁,这封信我们今天读,还是会感动。信的开头,曹丕以亲密的朋友口吻问候吴质,解释说:“我们各有职务,不得见面。”他的文字初看平淡,其实文字技巧很高。
曹丕说,“我现在总是怀念我们昔日在南皮的时光。”他的这段回忆很驰骋,我们看一下原文:
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弛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
就在这美好之中,可曹丕却突然捕捉到了人生的无常。话锋一转,接着说:
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这一下立意就高了。按说以他的身份,享乐是应接不暇的,一件赏心乐事接着另一件,不应该对哀伤如此敏感;但他强烈地感知到生命的终极问题,并且很有节制地描述了出来。
接着曹丕写道:“我当时就说:这样的快乐不会永久。果然,我们这群朋友天各一方,有的已经作古了。如今又是五月仲夏,又是万物生长;我驾车出游,又是随从吹奏音乐,又是文士幕僚们坐在后面的车里。季节相同,物是人非。我纵然忧伤又能如何?还是请你多保重吧。”
想必吴质接到这封信,也要感慨万千。曹丕把和吴质的情感沟通、升华到了生命体验的高度。
对写作者来说,如果感受不到相应的情绪,就写不出到位的文字。“好兄弟一辈子”可能是顺嘴一说,而写出“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样的句子,要情感到了才行。读曹丕的文章常常能感觉到他写作时的深情。
曹丕有一句名言,写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作为一个王朝的创立者,但他知道权力和王朝是短暂的,也不介意直接说出来。“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曹丕的父亲曹操就在军中设摸金校尉,大肆发掘坟墓以充军需。他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在政治上,他确实干了不少残忍的事情,而在头脑里,他又经历了反思的过程,知道现有的一切不过如此,早晚会腐朽。所以,他才把文学看得这么重,确信这是人生中唯一能长存的事物。他的文学态度是真诚的。
认识到人生的短促莫测,该怎么办呢?曹丕的答案是通过理性加以忘怀。他文字能做到含蓄节制,就是因为后面有理性。我们今天对曹丕的印象,真是来自文学,来自他敏锐的、微妙的情绪感怀。这些篇章打败了时间,也正是我们说“文章千古事”的意义所在。
延伸阅读:
《三国志》《文心雕龙》《典论》《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