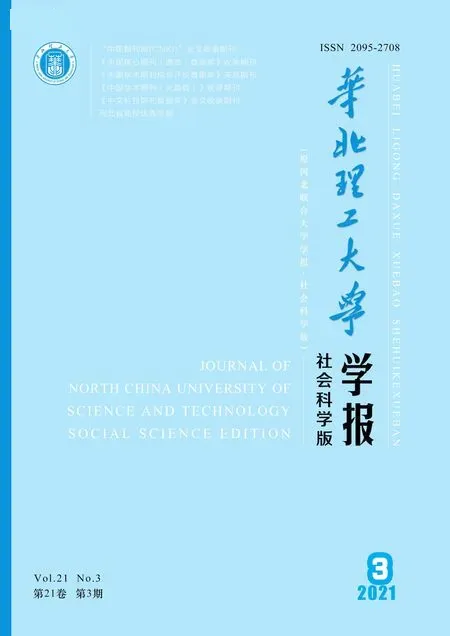功能视阈下《罗密欧与朱丽叶》序诗本土化汉译探析
王雪彤,王治江
(华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唐山 063210)
前言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早期悲剧之一,创作于一五九五年,讲述了发生在两个仇家中一对无辜儿女罗密欧和朱丽叶之间的悲惨爱情故事,可以形象地比作英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如周总理曾经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比喻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莎翁共创作有37部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其著名悲剧之一。自二十世纪初期莎剧开始在中国传播,先后至少有8种译本问世,分别是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田汉译本,1943年文通书局出版的曹未风译本,194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曹禺译本,1947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朱生豪译本,1967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梁实秋译本,199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孙大雨译本,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方平译本,201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光明译本[1]。
在剧作的结构形式上,该剧有一个区别于其他莎翁剧作的显著特点,那就是在剧前有一首开场诗,以十四行诗的形式简洁明了地介绍了该剧的故事梗概,这一特点与《牡丹亭》的开场诗很相似,也与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每一回的开头诗很有些相似,这种文本结构在其他莎剧作品中并没有使用,因此该剧的开场诗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特殊文本结构。
一、序诗文本类型及功能分析
以下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戏剧开场诗原文:
Two households, both alike in dignity,
In fair Verona, where we lay our scene,
From ancient grudge break to new mutiny,
Where civil blood makes civil hands unclean.
From forth the fatal loins of these two foes
A pair of star-cross'd lovers take their life;
Whose misadventur'd piteous overthrows
Doth with their death bury their parents' strife.
The fearful passage of their death-mark'd love,
And the continuance of their parents' rage,
Which, but their children's end, naught could remove,
Is now the two hours' traffic of our stage;
The which if you with patient ears attend,
What here shall miss, our toil shall strive to mend.
Catherina Reiss依据核心功能将各类题材的文本划分为四种文本类型:信息文本(informative texts)、表达文本(expressive texts)、操作文本(operative texts)和多媒体文本(audiomedial texts)[2]。前三种为文本的主要类型,信息文本是以传递信息为主要功能的文本,如教材、科技文献等等;表达文本是以抒发情感为主要功能,如私人信函、文学作品等;操作文本是以提供操作指南为主要功能的文本,如说明书、使用手册等;多媒体文本则不以文本功能划分,而是按照文本的介质特性划分的特殊文本,以声、像等多媒体形式存在的文本,以音乐、图像等辅助实现上述三种主要功能,如电影、广告等音像制品。
莎剧作为文学作品,整体上属于表达型文本。戏剧前的序诗,既以一个完整的结构而独立存在,又紧紧依存于戏剧正文,就好像是论文的摘要,概括戏剧的主要剧情和大意,或者评书说唱的开场白。从功能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序诗属于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叙述剧情梗概,又以诗歌的特殊形式存在而具有美学功能。因此,序诗以信息文本为主,同时也是表达型文本,是信息型文本和表达型文本的混合体。序诗是典型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诗共14行,每行5个音步、10个音节,每个音步由一轻音和一重音组成,押韵格式为abab cdcd efef gg,其中第9行love和第11行的remove为眼韵,结尾音节读音虽然不同但外形完全一样。而诗歌最后的两句则具有召唤听众耐心听戏的祈使功能,是个lead-in。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既是信息文本,又是表达文本。因此,在翻译中,译者要充分认识到这种特殊文本的两大基本功能,尽量在译文中同时再现原文的剧情信息和诗歌的美学价值,最后还要传递出对听众或观众的感召力量。
二、序诗四种译文的对比分析
我们在此选择了朱生豪[3]、梁实秋[4]、曹禺[5]和方平[6]的四种译文,经过对比分析发现,四位译者均照原文的样式翻译了该诗,各具特色,都基本忠实传达了原文的思想内容,同时尽可能地再现了原文诗歌之美学价值,这也正是诸位翻译家所追求的目标。
首先从形式上来看4个译文,都对应了原文的14行,且都以隔行押韵的形式基本对应了原文的abab cdcd efef gg的韵脚格式,除了曹禺译文中第9行的“惨变”难以与第11行的“消弭”合辙押韵,可以看出各位译家都在努力向原文靠拢,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原文。朱生豪译文句式工整,每行十个字对应原文的10个音节,若按照两三个字组成一个意群为一个音顿划分,难以对应原文的五音步。但是朱生豪译文每行都是4个音顿,十分整齐,行数和押韵方式符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韵式,读来朗朗上口。梁实秋的译文按照原文格式,符合十四行诗的韵式,但是译文各行音顿数不统一,有4个音顿的,也有5个音顿的,多的甚至达到了6、7个音顿,造成了各行长短不齐。从诗行长度来看,曹禺的译文最为不整齐,从音顿数量来看也是多少不一,多的甚至达到了八九个,比如第3、4、7、11、14行,其参差度比梁实秋译文更甚。方平译文的整齐度仅次于朱生豪译文,每行十一二个字,各行均为5个音顿,很好地对应了原文的5音部,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方平的译文无疑是最接近原诗的。但是从诗性来看,则朱生豪的译文效果最佳。曹禺的译文总体感觉更口语化一些,如“很早他们结下了私怨,如今爆发出新的斗争”和“是今天台上所看见的悲欢离合,在短短两点钟的时候。”梁实秋的译文用了过多“的”和“之”字结构,如“他们的不幸的悲惨的结局”、“以及双方家长之长久的仇恨斗争”和“这便是我们的两小时内的剧情”,使得诗歌散文化了一些。但是,若从与原文字比句次的角度来看,梁实秋的译文则最为贴近原文。
标点符号的使用上来看,朱生豪和梁实秋都没有在诗行中间使用标点符号,而其他两位译者均像原文那样在行中使用了标点符号,尽管不一定与原文严格对应。
几个译文中,曹禺和方平开头就说明了下面要讲述的是场戏,方平译为“这本戏”,曹禺译为“我们的戏”,两人在译文的结尾用了“演的分明”和“演个分明”以呼应开头的“戏”。朱生豪和梁实秋都在开头译成了“故事”,因此两人都在结尾也以“细听”来呼应。朱生豪和梁实秋的译本作为读者的“案头之本”为目的,而方平和曹禺则更侧重把莎剧作为剧本来翻译,追求的是“台上之本”。这些翻译家所追求的目的不同,由此也可略见一斑了。
几个译文都译了两家声望、声威相等或类似的意思如朱生豪的“门第”,而如果译文中有了“巨族”或“大家族”之类的,那么所谓的声望相等也就自不必多言。
“Where civil blood makes civil hands unclean.”一句,朱译为“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梁则译为“使得市民的血把清白的手弄脏”,方平译文是“私斗叫清白的手把血污染上”,基本大同小异,曹译为“私争的血污了和平的手,为了两家互相的残杀”,可以看出各位译者都将两个civil理解为不同的意思,可能是从搭配的关系来考虑的,但是这样让人读来容易理解为他们之间的争斗殃及其他无辜的市民。其实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里的civil绝不指一般的市民,而是特指作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两大家族,他们是同乡,是邻居,所以他们之间的争斗可以说是内斗,是争斗中彼此的鲜血撒溅在彼此的双手。两个civil是同样的意思,不然如果照四位译者理解的那样,其不是说这些人还是无辜清白的了?凡是参与械斗的人便不再“清白”和文明,更无“和平”可言。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对恋人才是无辜的。也许莎翁原意就是要通过重复使用这个词来加以强调,强调那些无谓的纷争给参与者自己带来的灾难,因此可以译为“同胞的鲜血染红了同胞的双手”,或者“亲人血溅亲人手”。
原文第5行中的fatal一词,朱译为“命运注定”,梁译为“命中注定”,曹译为“上苍派定”,意思都很准确,曹译文属于归化,符合目标语文化语境。
原文第6行“A pair of star-cross'd lovers”,朱译为“一双不幸的恋人”,梁译为“一对命途多舛的情人”,曹译为“一对苦命的爱人”,方译为“一对苦命的鸳鸯:恩爱不到头的恋人”。用“不幸的”“苦命的”对译star-crossed没有问题,可方平却增加了“恩爱不到头的”显然累赘啰嗦,可能是为了凑音顿数量而为之吧。关于lovers到底译成什么为好呢?我们感觉朱生豪和方平译为“恋人”比较贴切,而梁实秋的“情人”和曹禺的“爱人”则相对于中国文化语境来看不很合适,“情人”略带贬义,而“爱人”则一般指法律上承认的合法夫妻。方平使用的“鸳鸯”倒是切合中国文化,属于归化译法。
原文之第7-8行,“Whose misadventur'd piteous overthrows,Doth with their death bury their parents' strife.”朱生豪译为“他们的悲惨凄凉的陨灭,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意思基本准确,不过把doth with译成“和解”把宾语换成了“尊亲”很搭配,尽管与原意“消除了他们父辈的仇恨”不完全对应。朱生豪的“陨灭”和曹禺的“毁灭”则比较贴切。其他三个译本分别译为“埋葬了……纠纷(梁实秋)/冲突(曹禺)/斗争(方平)”,都比较合适。梁实秋和方平用“结局”对译overthrows显得分量有点轻。对“misadventur'd piteous”这个双重修饰语的处理上,四个译本也有明显的差异,朱、梁和曹都用了双重修饰语对应,只有方平把他们分到了两个小句中,译为“可怜他们俩的结局,真叫人心碎”,实际上是重复了piteous的意思,“可怜”和“令人心碎”是一个意思,misadventured所表示的他们的命运之“悲惨,不幸”没有反应出来。诸译文中不十分精准的措辞,显然是受了诗歌翻译中的追求押韵之苦,看来因韵害意的问题在诗歌翻译中是个很难避免的通病。
原文之第9-12四行为一个大的主系表结构(主谓结构),前三句为三个并列名词短语作主语。朱、梁、曹译文均遵循了原文的句法结构,而方平则把原文译成了四个结构完整的主谓句,其间逻辑关系也由原来的因果关系(或者施动关系)变成了并列关系。第12行“Is now the two hours' traffic of our stage.”,本意是说这段与家族仇恨交织在一起的生死恋情,将是我们两个小时的舞台剧要传递的信息,朱生豪的译文省略了“两个小时”这一次要信息,而其他各译文都保留了时间概念,但曹禺译成“在短短两点钟的时候”显然不妥,容易让现代读者误解为戏剧将在两点钟开演。梁实秋译文“这便是我们的两小时内的剧情”,与方平的译文“正戏就要上场——演两个钟头”意思比较贴近原文。其实,如果为了迁就押韵和句子表达的流畅等,这里的时间信息不是个重要问题,实际属于冗余信息,因为作为戏剧观众基本都知道一场戏大概演多久,没必要特别交待,因此可以省略。
最后,第13-14行“The which if you with patient ears attend, What here shall miss, our toil shall strive to mend.”,除了朱生豪按照惯常的逻辑颠倒了两句的先后顺序,其他三位翻译家都遵循了原文的顺序,朱生豪和方平都意译了最后一句为“交代过这几句提纲挈领”和“交代过大意”。特别是曹禺和方平两句译文都分别以“细听”和“分明”结尾,朱生豪和梁实秋也都使用了“细听”一词,只是位置不同而已。
经过对比分析发现,整体上四种译文都很贴近原著,但是若从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舞台演出角度评价,上述译文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三、序诗新译——本土化翻译的尝试
为了充分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场序诗的舞台表演形式,我们从网上搜索了一些较为完整的演出视频资料。1994年,英国柯芬园皇家歌剧院上演的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场序曲(开场诗)为几十个人的合唱,歌词完全与莎剧原著一致。2009年11月6日,美国普洛威登斯学院戏剧系演出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场序诗是由男女对口朗诵的。由此可见,这首开场诗在舞台演出中基本是两种主要传达形式,或演唱或朗诵。
“原文主要功能的传递是判断译文质量的决定因素。”[2]戏剧中的序诗和唱词等,因兼具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和美学功能,在翻译中译者在准确传达原文意思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到它的美学功能,应该尽最大努力再现原文的风格之美。特别是这段文字,除了有诗歌的性质之外,译文还要考虑它的可说唱性,要兼顾其音乐感,要做到读来朗朗上口,诵来声声合辙入韵,符合剧前开场道白的基本特征。
受中国传统说唱艺术和传统诗歌形式的启发,笔者尝试着翻译了这一段序诗,保留原文十四行,每行七言,邻行押韵:
话说名城维洛那,
住着望族两大家;
宿怨未了生新仇,
血雨腥风不罢手。
两家世代仇恨深,
无辜儿女情爱真;
为情殉葬实堪怜,
终让世仇化云烟。
可叹一段生死恋,
怎奈父辈仇更怨;
难成眷属赴黄泉,
一场悲剧传人间。
开场只把梗概讲,
众位耐心听端详。
著名莎剧翻译家方平指出,我们不必像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们那样,不理会莎剧原是舞台脚本,而仅仅把它看成书斋中的经典读物,这会约束我们的研究视野,因此限制我们的研究成果;多少向演出本靠拢,是会有助于一般读者的理解和欣赏的[7]。在这一精神鼓舞下,充分考虑到原文本信息功能和表达功能以及在舞台演出中的感召祈使功能的有机结合,新译在形式上采取了本土化策略,选择了中国传统的七言诗歌的形式,同时在诗行安排上保留了原文的十四行诗的特点,保证了序诗外形上的整齐。韵脚采用邻行押韵的格式,更适合诵读说唱。内容上不拘泥于和原文的字比句次,采取以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的方法,对原文内容进行了适当概括和调整。
本土化翻译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在文本形式上去除带给读者或听众的陌生感,而不会对原文本内容所负载的异国情调有任何影响,恰如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论述化境翻译观时所说的那样,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仿佛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总结的诗歌翻译四种形式之一就是“类比形式”(analogical form),即在诗歌翻译中采用目的语文化中相应的诗歌形式,从而发挥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相似的功能[8]。该翻译方法曾经流行于十八世纪,目的是追求译作和原作在外形上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等”,属于“形式派生式”(form-derivative)[9]以目的语文化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献给大众,有利于世界文学经典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和传播。岂不记得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歌《爱情与自由》,在国内有多种翻译版本存在,译者既有著名文学家矛盾,又有精通匈牙利语的翻译家兴万生,可是任谁都能顺口吟来的则是殷夫翻译的那四句译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原因何在?窃以为首先译者在形式上采取了为大多数人所赞成的以诗译诗的处理方法,其次在内容上既涵盖了原文思想而又高度凝练,最后最为关键还是在于译文没有拘泥于原文的结构安排,而是采取了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本土四行五言诗歌的形式。
四、结语
“莎剧精妙和正确的译文及演出,应当雅俗共赏;莎剧决不仅仅是一个个故事,它们还是一篇篇戏剧诗章。”[10](孙大雨,1987)莎剧也不仅仅是学者的案头经典,它们还是舞台演出的剧本。因此,在莎剧翻译实践中,译者不仅要顾及到原著的诗剧特性,同时还要顾及到译文也会成为在目的语文化中舞台演出的剧本这一特殊应用功能。《罗密欧与朱丽叶》序诗也不例外,它是舞台演出的开场前奏,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形式和中国本土文化中的传统诗歌形式相结合,以适合中国传统说唱艺术形式,让广大听众和观众以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去接受欣赏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经典,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