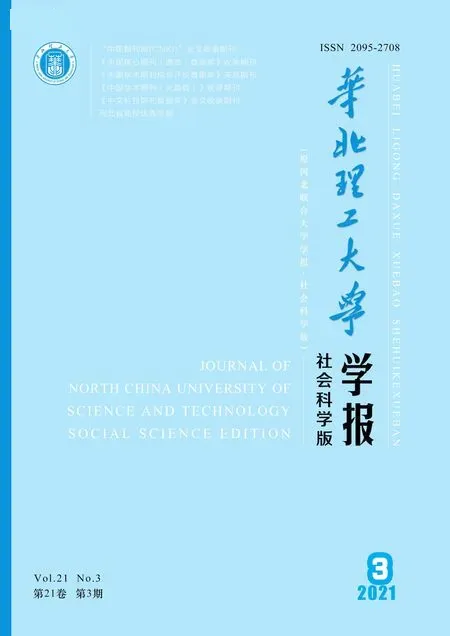鲁迅与匈牙利文学
李 杨
(华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唐山 063210)
引言
国人最初了解匈牙利文学,莫不会提及鲁迅先生所著《摩罗诗力说》。这是一篇文言文所著的论述,最后一章节用相对较短篇幅介绍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每每提到裴多菲,读者印象最深刻莫过于“爱情诚可贵……”,鲁迅先生和这首诗歌的译介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除此之外,鲁迅先生还译介并参与译介了匈牙利的诸多作品。在物质文化条件相对落后,资讯相对匮乏的一百多年前,鲁迅先生以敏锐的视角注意到裴多菲和匈牙利文学,至少在文学传播和译介方面,都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鲁迅先生翻译的匈牙利文学作品,学界更多提及裴多菲诗歌的译介,而对于后世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有过多少的推动作用,并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描述。本文以追本溯源为目标,将鲁迅先生所翻译匈牙利的作品一一诠释,这些工作的完成不但是出于对伟人的敬畏,同时也为明晰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初衷。
一、鲁迅与匈牙利文学的缘分
1902年4月,鲁迅开始了日本留学生活。留学伊始,他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最初只为研习日本先进医学,治病救人,光耀门楣。1904年9月始,正式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所学课程除了日文讲授之外,“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1]这里所涉及“腊丁”为拉丁语,“独乙”为德语。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为鲁迅之后的文学翻译活动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这也就是鲁迅后来能够翻译很多的除了日本以外国家文学作品的原因。1906年1月,鲁迅在课堂上看到日俄战争幻灯片时,遭到日本同学“万岁”欢呼声之耻辱,决定弃医从文,3月便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将学籍挂靠于东京独逸语学会所属的德语学校,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了阅读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事业。
在东京期间,鲁迅最重要的精神生活就是去书店寻觅、购买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他经常光顾东京的外文旧书店,从旧书店购买德文杂志,从中找到相关书籍的出版信息,再通过东京的丸善书店向德国订购,收到原版书籍需要两三个月时间[2]。如此,鲁迅积累了大量日后翻译的文学作品,基于国内现状,鲁迅在这期间阅读最多的是充满反抗、复仇之声的“弱小民族文学”,尤其是表现弱小民族苦难生活的作品。这些诗人和作品后来由鲁迅译介给国人,《摩罗诗力说》中所论述的九位作家作品就是青年鲁迅最早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的缩影。正如他晚年回顾所写道: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得共鸣……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3]
参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鲁迅先生一生的翻译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1903年至1918年,这是青年鲁迅用文言文翻译和向国人介绍外国文学的阶段;中期1919年至1928年上半年,这是鲁迅用白话文致力于弱小民族文学和日本文学翻译的阶段;后期1928年下半年至1936年10月,是鲁迅先生致力于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苏联小说译介的阶段。巧合的是,鲁迅先生在每个阶段,都参与翻译了匈牙利的文学作品,这三个阶段也代表了鲁迅翻译并推广匈牙利文学的三个阶段。
二、早期翻译的匈牙利文学作品
鲁迅和周作人先生阅读过的匈牙利文学的相关资料有籁息(又译“赖息”)的《匈牙利文学史》(又名《匈牙利文学论》),卡尔别列斯的《世界文学史》和雪尔的《世界文学史》。后两部作品涉及裴多菲的内容较少,后人所著文献中自然少有提及。目前所著文献中可知,周氏兄弟最初涉猎的是利特尔的《匈牙利文学史》(英文版)。周作人在《旧书回想记》中这样介绍了此著作的作用:“可是籁息博士的《匈牙利文学论》也于一八九八年在那书局出版,非常可喜,在我看来实在比一九零六年的利特尔教授著《匈牙利文学史》还要觉得有意思”。[4]
1908年8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裴彖飞诗论》发表在杂志《河南》第七期上,署名“令飞译”。受语言限制,这部论著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译校阅。据周作人回忆:“这本是奥匈人爱弥耳赖息用英文写的《匈牙利文学论》的第二十七章,经我口译,由鲁迅笔述的,所译应当算作他的文字,译稿分上下两部,后《河南》停刊,下半不曾登出,原稿也遗失了……”[5]籁息的这篇论述是他的专著《匈牙利文学:历史的与批评的研究》第二十七章中《裴多菲,匈牙利诗歌天才的化身》的部分,现存的鲁迅与周作人两位先生合译的《裴彖飞诗论》翻译出了籁息原著篇幅的45%。虽然这篇《裴彖飞诗论》是“残篇”,但是它与稍早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一道,成为中国最早译介裴多菲生平和创作的文献。
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裴彖飞诗论》,其中除了向读者展示匈牙利的文化风俗和风物习惯,也描写了匈牙利的自然景观。以文学的视角阐述了诗人裴多菲诗歌创作的非凡创造力。同时采用了大量的论据论证了裴多菲在匈牙利文学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鲁迅和周作人先生的合译基本达到了译介的目的,同时也符合鲁迅先生提出的“直译”的基本翻译标准,只是译文表述依然沿用了《摩罗诗力说》的古奥风格:
……使其求索如是,仅得裴彖飞一人而已。裴彖飞在匈牙利诗人中,独能和会摩陀尔特钟之诗美,与欧土鸿文,具足无间。使心解诗趣者,威能赏析。疆域之别,言语之异,无由判分。盖诸有其诗,亦犹其乐,不以内外今昔,起其迁流,裴彖飞之诗……[6]
这段译文能够很好地体现鲁迅在这一时期,翻译语言受到当时文言文风的影响,采取了奥古难懂的风格。其主要评论裴多菲是一位真正民族的诗人,他的诗歌一方面融合了匈牙利语与欧洲文学的特征,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诗歌之美。
鲁迅的翻译理论并不成为体系,更精确地说,是鲁迅先生关于翻译活动的理解和评论。这些内容都散见于他的一些书信和杂文集中,他翻译的主导思想是“直译”而不赞成“归化”或者“意译”的方法,希望通过“直译”保持作品的风骨和异国情调。但很显然,在他文学翻译初期的这部译作中,译文受到了当时目的语文言文汉语的影响。但是鲁迅先生还提倡“复译”和“重译”,体现了他对于文学翻译的热爱和严谨的风格。这一时期翻译的作品,是鲁迅先生想要通过文学评论的形式,把异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精神传授于国人,以适应当时时代的发展。
而与《裴彖飞诗论》同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刊登于1908年2月和3月的《河南》杂志第二和第三期上,其中最后一节对裴多菲生平思想和创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论。鲁迅赞赏裴多菲为民族独立而献身的崇高追求。青年鲁迅作为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希望在当时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中也能有像裴多菲一样的精神界之战士。最后鲁迅总结并发问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为国之萧条痛感悲愤,为国将沉沦痛心疾首。《摩罗诗力说》同《裴彖飞诗论》在同一年先后发表,看似巧合,却传达给读者近乎相似的观点。
三、中期翻译的裴多菲诗歌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当时,很多有识之士留学归国,投入到中国的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借助国外留学的语言优势,大量的外国文学被译介到中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独秀所办《新青年》杂志,刊载了大量的外国文学译稿。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欧美派”和鲁迅为代表的“俄国和东欧派”。鲁迅的独特视角关注的是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与进步,希望当时的中国也能从中“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找到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当然,鲁迅在这一时期也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但其中更加关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变化。不论是俄国,日本还是东欧各个弱小民族的文学,这些作品的译介除了文化传播之外,更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借鉴这些国家和民族能够迅速融入现代文明世界的经验,希望中国这个深厚古老文化之国,早日找到突围之法则,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25年1月12日《语丝》周刊第9期上刊发了鲁迅翻译的裴多菲的两首诗歌,《我的父亲的和我的手艺》和《愿我是树,倘使你……》,1925年1月26日的《语丝》周刊第11期上,又刊载了另外三首分别是《太阳酷热地照临》,《坟墓里休息着……》和《我的爱——并不是……》。在《鲁迅译文全集》中统一称作为《A. Petöfi的诗》。
《我的父亲的和我的手艺》中后四行为:“你用了你的家伙击牛,/我的柔瀚向人们开仗——/所做的都就是这个,/单是那个名称两样。”这首诗涉及到了裴多菲父亲曾为屠夫的职业,意思是虽父亲为屠夫屠宰牛羊,而我则挥动柔瀚(这里指“笔锋”)向禽兽一样的恶势力开战,虽职业名称不同,却与父亲殊途同归。表现了裴多菲战士一般的革命勇气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这首诗歌的译文,较前一阶段奥古的文言文译文,多了很多白话文的元素,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这一阶段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仍然保持了自己“直译”的原则,目的就是要唤醒沉睡的中国人民,这其中不仅仅包括知识分子,还有普通百姓,给他们提供精神食粮,同时也提供了中国文学改革的新范本。
这一时期,鲁迅译介的特点首先从文言文的使用转向白话文表达;其次对于“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和译介是五四运动后翻译和文学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其中对于匈牙利文学的喜爱和对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青睐,强调了捍卫“弱小者”的生存和抗争之权力;最后也正是这一时期鲁迅的译介活动,向读者充分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碰撞和血缘关系。
四、后期译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世界文艺的一部分,鲁迅后期的翻译活动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左倾转向,成为了世界文学“变红”的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作家和翻译家,开始关注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鲁迅密切地关注到了国内和国际文坛的变化,从1928年下半年开始,他把翻译的重心转向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的翻译。在他后期8年的翻译实践中,鲁迅的15部译著里有5部无产阶级革命文论。在此期间,鲁迅翻译的作品倾听了涌动着革命风云的苏联黑土地上人民的心声;自省、摒弃并更新了自我的社会观念和文艺思想;通过译介和评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及苏联文学作品融入到当时波澜壮阔的世界红色文化思潮中去。鲁迅的译介实践典型地呈现了现代中国文学家和翻译家们不断突破自身环境限制,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动向。
匈牙利的文艺理论界也同样出现了“红色”。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鲁迅译介了匈牙利作家安多尔加博尔(Andor Cabor)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约5400字),翻译自1929年10月的德语杂志Die Links-Kurve(《左曲线》)第1卷第3号,并将译文发表于1930年9月10日《世界文化月刊》创刊号上。安多尔加博尔(1884-1953)是匈牙利的讽刺作家和新闻工作者,1933年起旅居莫斯科,深受苏联文化影响。鲁迅所译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开头部分指出,无产阶级文学是艺术,同时也是一种“倾向”,借由文学来进行“煽动”和宣传,无产阶级文学是“市民阶级的文学技术的自觉继承人”:
在人类历史上负有最深入改革的重荷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也必然要同样地有它自己特殊的文学……只有他们才能完全地从那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立脚点来体验无产阶级及他们那解放的战斗……[7]
也就是在同一时期,鲁迅撰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章,一方面与梁实秋论战,一方面反驳“硬译”的说法,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者应该是出身无产阶级且具有革命实践经验的人。这与加博尔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中的观点及其一致,即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有自己的作家群体而这些作家是为革命而奋斗的勇士。这一阶段鲁迅为译介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因此鲁迅被后世称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普罗米修斯”。他引他国革命之火,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将为人民和为革命的翻译并介绍外国文学的思想保持如一,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勇士。
五、匈文学译介的影响
鲁迅不仅自己热衷于匈牙利文学的译介,同时也帮助推介其他翻译家翻译匈牙利文学,尤其是裴多菲的作品。早在1923年,冯至因拜读鲁迅先生《丝语》期刊刊登的鲁迅译《裴多菲诗歌五首》,作《Petöfi Sndor裴多菲山陀尔》的文章介绍他坎坷的一生。曾在延安革命圣地红极一时的裴多菲诗歌《自由与爱情》是由白莽(殷夫)翻译后由鲁迅校阅后发表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除此之外白莽还翻译了裴多菲的作品《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发表于鲁迅主编的《奔流》第二卷第五号上。而白莽所译这些皆为德译版本,是鲁迅一直珍藏的书籍。同一时期,帮助使用世界语翻译的孙用校阅裴多菲的长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原名《雅诺什勇士》)。在鲁迅的影响下,解放后孙用和兴万生等成为翻译匈牙利文学名著的专家。
鲁迅在匈牙利文学的译介方面主要翻译的作家唯有裴多菲,在《希望》(见《野草》)一文中,鲁迅说:“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他痛感当时中国的萧条状态,欲借匈牙利之“先觉之声”来破国之积弊。但因鲁迅为国人开先河,介绍匈牙利文学来中国,才有后世众多作家翻译家一直关注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更可喜的是解放后中匈友谊进一步加深,不但匈牙利的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被译介到匈牙利。改革开放后尤其“一带一路”提出之后,中匈在文化和文学交流方面更上一层楼,回首思虑,唯有感叹和感谢鲁迅先生译介裴多菲的诗歌和“弱小民族”的先觉之声,给予中国突破自我的信心。这不但是中匈两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所共享的文化源泉。翻译是文学的再创造,引用裴多菲本人的表述来形容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吾心如反响之森林,受一呼声,应以百响者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