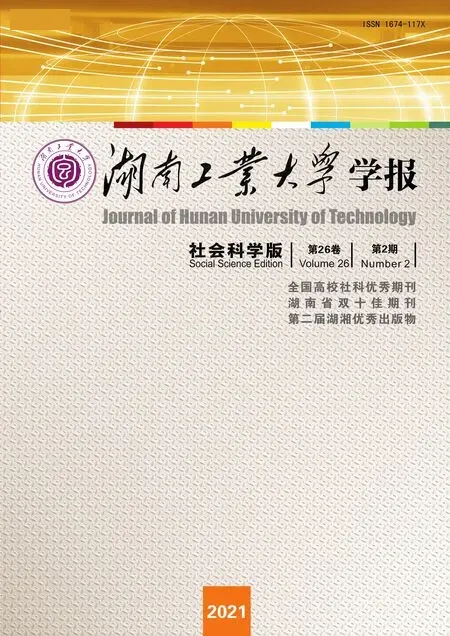中国先民早期审美意识生成论
易小斌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中国先民早期审美意识诞生于何时的问题,学界历来见仁见智,其中有两种观点影响较大:一种观点认为,先民早期审美意识大致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滥觞于东周末年,兴起于汉魏两晋;另一种观点认为,先民早期审美意识的诞生与中华文明起源同步,“第一把石刀的制造者,即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位艺术品的创造者,亦即人类最早的审美意识的体现者。”[1]笔者认为,我国先民早期的审美意识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生成论强调的不是状态,更不是起点或终点,而是意义延绵生成的过程。因此,研究中国先民早期审美意识生成的意义,并不在于探讨其诞生的逻辑起点,而在于研究其动态的生成过程。格罗塞说:“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2]原始先民常常为生存所困扰,他们最初对美的感受是自发的,他们在探索自然和生产生活中创造出了自己所需要的潜藏着审美因素的原始文化与原始艺术。这些原始文化与艺术包括图腾崇拜、神话传说、文字符号、音乐、绘画、建筑等等。通过对这些原始文化与艺术的研究,我们可以弄清楚中国先民早期审美意识是如何生成的。
一 审美形象的原初建构
图腾崇拜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原始文化形态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阿尼史纳伯人“dodem”一词的拉丁化变体“totem”,意思为“它的亲族”,“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3]162。图腾崇拜的出现,使原始先民的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新的转变。有了图腾意识的支配,原始先民开始运用超越现实的方式来表现各个氏族、部落的起源、生存和繁衍的故事;同时,审美意识开始注入服务于图腾崇拜的神奇诡怪的形象塑造和神秘怪异的情节设计。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图腾”一说,但古籍中关于图腾和图腾崇拜现象的记载以及上古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文化遗迹,其内容十分丰富。如《山海经》羲和、常羲等日月神形象,迷榖、帝女之桑等植物神形象,鸟、鱼、蛇、兽等动物神形象,龙、凤等动物复合体形象,以及其他“人兽同体”等神怪形象;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象牙鸟形器”“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木鱼”;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的“鱼纹”“人面衔鱼纹”“鸟纹”“蛙纹”等纹饰;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红陶小动物形象;等等。这些文化遗存都具有图腾崇拜的特征,同时也是原始先民在审美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审美形象设计。
我们可以通过《山海经》中动物躯体分解重组或“人兽同体”的图腾形象来具体分析其蕴涵的原始审美形象及其生成机制。《山海经》中的这类图腾,王小盾先生称之为“变形图腾”[4]。这些变形图腾,往往是通过把兽或人的身体构造进行分解,然后把这些分解出来的身体部件进行重新组合,重构成一个“人兽同体”或者“异兽同体”的形态怪异的形象,如鸟身而龙首、龙身而鸟首、龙身而人面、人面而马身、马首而人身等,就是通过兽与兽或人与兽“整体变形”而重构的形象。异兽之间、人兽之间的形象拼接,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由于原始先民逻辑思维并不发达,他们往往借助于较为发达的形象思维,充分利用自己特有的形象记忆力来构建图腾形象。中国先民对于图腾形象的构建,或者出于对某物种的亲和感,或者出于对某物种的神秘感,或者出于对某物种的敬畏感,或者兼而有之,从而将种属迥异、形象悬殊的物种“身体部件”图像信息进行创造性重组,塑造出超自然、超现实、超人的怪异形象。部落成员往往会产生一种现实错觉,认为这些图腾形象是一种神圣的真实存在,从而产生莫名的亲和与敬畏感。因此,图腾形象的审美设计,无论是施于拟形化造型的实用工具、实用器具上的图案装饰,还是施于穿戴物的造型或者身体上的纹身,都表现出超现实性、神秘性的基本特征,同时还强烈地表现出先民重组世界、重组生命体的强烈愿望。这些图腾形象设计不仅显示出强烈的原始文化意味,同时也展示着原始审美形象意蕴,因此,也可以说,图腾崇拜是原始文化与早期审美形象的中介符号。有学者认为:“图腾的文化功能,在于唤醒氏族的群体意识以及群体意识隶属下的生命意识。可以说,人类原始图腾意识、观念与行为的发生,一开始就本在地存在着通往哲学、美学与艺术审美之发生的历史性契机。”[5]与其他人类文明相类似,中国先民的图腾文化也属于中国最古老的原始文化,后世许多文化现象包括审美现象,都与图腾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二 审美思维的原始创生
神话是各民族文化起源的精神母体之一,各民族文化从野蛮迈向文明之际,一般都经历过一个神话传说和神话思维的阶段。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说:“文化生存的基本形式起源于神话意识。”[6]苏联神话学家梅列金斯基也说:“在种种古老文明中,神话堪称哲学和文学发展的起点。”[7]关于神话的定义,学界对此历来就有多种不同的界定,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8]高尔基说:“一般来说,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9]鲁迅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10]尽管学界对于神话的定义莫衷一是,但是所有关于神话定义的观点无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神话是原始先民的集体创造,属于原始思维的产物。神话并非文人的个人创作,即使出自(或托名)个人,其实质仍是原始先民们集体无意识的折射。上古先民的神话思维与先民早期审美思维的创生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先民的神话思维直接孕育了审美思维。
摩尔根认为,神话产生于低级野蛮社会阶段,在这一阶段,“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此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3]539中国神话的艺术水平虽不如长篇巨制的西方神话,但其发展历史却同样源远流长。母系氏族时期的中国先民即产生了万物有灵观,中国上古神话就是在这种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考古发现,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会在死者的坟墓中撒抹一种红色的矿粉,这应该属于一种巫术礼仪,神话的因子或许蕴含其中;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彩陶中的鸟兽造型、鱼纹蛙纹等文饰,具有原始图腾的表征,或许同样具有了神话的色彩。不过,目前暂未发现在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即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神话。在中国,母系氏族社会崩溃、父系氏族社会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夏商周时期。夏商两代相关文献阙如,但在殷墟发现了大量甲骨文字。现存记有文字的殷墟甲骨片有15 万余片,上面记载的文字约有1400个字已经释读了,还有约2800 多个甲骨文字尚未释读。夏商周时期,甲骨文字和青铜器上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神话史料。《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集的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这些诗歌中出现了不少神话因子,甚至保存了较为完整的早期神话故事。如《大雅·生民》追述了农神后稷(周的始祖)的神话事迹;《商颂·玄鸟》记载了商的始祖契的神奇降生及建立殷商的故事;《大雅·崧高》《小雅·信南山》《小雅·大东》等诗歌中分别出现了甫侯申伯、大禹以及牛郎织女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这些诗歌均具有一定的神话文化因子。《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其书名或曰“上古之书”,或曰“崇尚之书”,或曰“君上之书”,更有人解释为:“公开的皇家文档”(“尚”意为摊开、展平,“书”即文字记录)。《尚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汇编,各篇中汇聚了大量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或者说保留了大量神话文化因子,尤其是《虞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等篇什,俨然就是相传夏朝之前的新兴王朝——虞朝的历史神话故事汇编。东周时期,蕴涵神话的典籍大量涌现,如诸子著作、《左传》、《国语》、《楚辞》,均存在丰富的神话研究资料。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有关地理博物、神话故事、祭祀巫术、仙山瑞兽的记载极为丰富,是保存中国神话材料最多的一部古书,被称为中国神话的根基与起源。
上古先民对自然的认知程度极为有限。自然界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又是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源头。人类无法驾驭自然,对于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自然现象也无法进行科学的解释,于是人类借助幻想将其拟人化、神化,用人类自身的特征去诠释自然现象的特征,将自己的意志加诸自然。黑格尔说:“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气氛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成认识的对象。”[11]古希腊的创世神话中五大创世神创造了世界一切;基督教的创世神是上帝耶和华,上帝创造了自然万物,又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有了人类;在中国古代“盘古开天”神话中,风云雷电、日月星辰、山河田土、草木珠石、雨泽、黎甿等均为盘古的“垂死化身”。这些神话表明,不同地区的人类文明,对于自然万物的产生有着大同小异的认知观点:自然万物都是由人化的神创造的,或者直接由人化的神灵化育而来。尽管这些认知是虚幻的,但这些虚幻的认知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表达了人类用自身的特征、用自己的意志去解释自然,并试图征服和支配自然的愿望,因此其在虚幻中有现实的影子。上古神话中体现的先民征服和支配自然的愿望,虽然是虚幻的,但先民创造神话本身的过程,却是一种集体创造的思维行为,也是先民对客观世界认知的最早的思维行为。中国先民根据自身的特征,借助于幻想化的原始思维方法,以神话传说的方式,将对世界的认知、对自然的诠释流传下来。在这种神话传说的生成和流传过程中,同时也孕育了先民们早期的审美思维。在中国的上古神话中,流传下来众多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如《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有兽焉,其名曰駮,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有青兽焉,状如虎,我曰罗罗。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诗经·生民》追述后稷事迹的神话故事中,有关祭祀场面的描写也同样颇具审美价值:“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甚至更深层次的审美意识也在上古神话故事之中诞生,例如悲剧意识。中国先民早期认知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征服和支配自然的美好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能够实现,这本身就具有一种悲剧色彩。例如《山海经》中填海之精卫、逐日之夸父、治水之鲧,均为上古神话中渴望战胜自然而不得的悲剧英雄,在这些有关英雄的神话传说中体现出中国先民最早的悲剧美意识。上古神话中还保存了不少因部落间的争斗或者政治斗争而产生的悲剧人物,例如《山海经》中与帝争神之刑天、作兵伐黄帝之蚩尤,《淮南子》中与颛顼争帝之共工、被尧帝消灭之楚伯、被夏启攻灭之有扈氏等等。这些战争悲剧中的主人公最终以战败身亡成就了他们的悲剧;更可贵的是,他们失败后精神永不屈服,于是有不畏强权的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千古绝唱,从而使得这些神话传说具有了悲剧美的“永久的魅力”。当然,上古神话中除了表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抗争的悲剧主题,也不乏描绘美好事物、憧憬美好生活之主题,如《庄子·逍遥游》中对“藐姑射之神”美好生活的想象,《诗经·生民》中对美好丰收景象与祭祀场面的描绘,《楚辞·九歌》中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山海经》中《大荒南经》《大荒西经》《海内经》等篇什对美好的生活环境的表现。这些上古神话叙写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故事,描绘美好生活理想蓝图,其记录虽然极为简略,思维较为原始,但绝不是一种本能的认知表现,其蕴含着具有理性色彩的审美意识,中国先民审美思维的早期萌芽正是孕育于此。
三 审美意象的符号表达
刘师培说:“上古造字,以类物情,极意形容,有如图绘。”[12]汉字起源于对自然界各种物象的摹写,中国先民通过用形象性的线条组合来摹绘物象之轮廓,以达到显示其意义的目的,所谓“象中寓意”。最早的汉字或曰为甲骨文,或曰为新石器时代先民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陶器上的许多类似于象形文字的刻符。裘锡圭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已经用作原始文字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13]不管哪种说法更接近于事实,我们还是不能因此就汉字符号诞生于何时的问题给出一个具体而明确的答案,这就如审美意识于何时诞生的问题一样,我们认为它同样有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所谓“仓颉造字”,只不过是一个传说,仓颉或许只是一个在汉字符号的生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汉字的造字原则,东汉许慎提出“六书”(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说,学者们一般都认为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而非造字法;所以,唐兰先生把“六书”约简为“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认为其中又以“象形”为基本。汉字中的象形字(如“日”“月”“山”“水”等)是汉字之源,主要见于摹写比较简单而常见物象的名词。后来发展起来的指事字(如“上”“下”“刃”“王”等)和会意字(如“行”“伐”“析”“从”等)用来表达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观念,但其造字原则,仍然由“象中寓意”观念所支配。随着用字量的增加,形声字(如“钱”“放”“茅”“柴”等)所占比例逐渐上升,到了东汉许慎所著的文字学经典著作《说文解字》时,形声字占比已经达到了80%以上。形声字由意符和声符组成,然而其意符和声符也是分别由不同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充当。所以说,汉字起源于中国先民的记事图画,故有“书画同源”之谓。常任侠先生谈到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与绘画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的古文字原是从象形开始的,文字与绘画同源,文字本身就是缩小了的绘画。”[14]陈梦家先生也认为,“中国文字(汉字)发源于图像,逐渐的经过简化和人意的改作成为定形的简省的概略的象形,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15]由此可见,汉字具有鲜明的重“象”特征并传承至今,这明显区别于拼音文字。从这一角度看,汉字的审美特性是显而易见的。汉字的重“象”特征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重直观表象而轻逻辑思辨的特征十分明显。象形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文字表意方法,“它在观察事物的基础上,把握和抽象出其典型持怔,因而具有‘原型’认知模式的意义;其次,象事或指事具有察而见意的特点,当它用形象性和象征性的符号将无形之事表达出来时,就只有了特殊的心理意义。”[16]因此,我们在阅读汉字的时候,可以在领会其意的同时,还可以感受其潜在的形象,这种对文字“意”与“象”的双重感受,使中国先民的思维富于艺术性和审美特征。
汉字的重“象”特征,是人类早期形象思维作为最主要的一种原始思维方式运用到文字创造方面的一个结果;然而象形文字的使用,反过来对人们主要思维方式又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汉字字形的多样性、汉字结构排列的复杂性,使汉字的书写(书法)能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汉字的诞生,是中国先民原始思维方式的诗性表现,其一开始就具有审美意象特征。汉字数千年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语言思维方式,使得中国哲学美学之重直观、重整体的形象思维特色有别于西方的重逻辑、重分析的抽象思辨特色。毛宣国先生根据甲骨文字以上造字原则,论证了中国古代艺术中的“虚实”观、“象意”观之生成。毛宣国先生说:“甲骨文中表示动物的象形字,常抓住最具代表性特征来作全体之象形,这实际上已含有某种虚实关系的处理和把握了。”[17]
审美意象的符号化表达最直接、最典型地体现在汉字“美”上。许多人在谈到汉字作为审美意象的符号化表达时,大都会关注到这个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18]日本学者笠原仲二据此认为,“美”字就源于对“羊大”的感受性,它表现出羊的体肥毛密、生命力旺盛的强壮姿态。中国人最原初的美意识就源于“肥羊肉的味甘”这种味觉感受性[19]。甲骨文中的“大”字是在甲骨文“人”的基础上表现出一个人张开双臂的形状,意即区别于小孩的“大人”,因此在甲骨文中,“美”之造字就像是人的头上顶着羊角之类的兽角的形象。于是有人提出,所谓“羊大为美”在甲骨文中的最初的含义应该是“羊人为美”的观点。头戴兽角翩翩起舞的原始舞蹈是原始先民最为普遍的舞蹈表演形式,这种原始舞蹈或为原始先民狩猎前头戴动物面具举行的舞蹈仪式,或为祭祀时头戴图腾面具举行的舞蹈仪式,其都与原始部落的劳动生产、图腾崇拜和祭祀活动息息相关,因此,“美”之意象源于中国先民对图腾美的感受。但马叙伦先生在其巨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中提出,“羊大则美”为附会之说。他认为,“美”字为形声字,上声下形,“羊”,只表读音,不表意义。“美”,从“大”,不从“羊”。“美”,即“媄”,“媄”,色好也,从女,媺声。美字的最初意象源于对“色”、对女人的美丽的感受。以上三种观点各有所持,但并不根本对立,这表明中国先民最初的审美意象,或起源于味觉感受性的美味,或起源于视觉感受性的图腾美、美色,其体现了原始先民强烈的生存愿望和生命意识。
有学者指出,“汉字的具象特点正是它的审美特性的反映,对汉字字形的理解和把握不是靠解释,而是靠经验、体会和领悟,汉字字形的‘不落言筌’之处在于它和盘托出了一种形象、—种情境、一种吁请结构,它本身的动态形象也邀请读者的动态参与。”[20]汉字符号的生成过程,始终伴随着汉字本身的审美特征的反映,具有深厚的原始文化内涵,中国先民的早期审美意象蕴含其中,并以此获得符号化表达。
四 审美经验的寸铢累积
中国先民早期审美意识的生成,离不开各门类原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它是以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所积累的一定审美经验为前提的。上古时代的中国先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已经创造了丰富的原始艺术,其中主要包括乐舞、绘画、建筑、青铜器等。
中国先民早期审美经验的累积所受到的最直接影响的艺术应该首推音乐。先秦时期的审美思想与音乐理论几乎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特点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在中国古代,音乐艺术极受推崇,因此也获得高度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上古时期的音乐是各门艺术的中心和源泉。在原始氏族社会中,狩猎等劳动生产活动前的歌舞仪式、部落祭祀场合的歌舞仪式、庆功庆典上的歌舞仪式都离不开音乐。到了奴隶社会,这些原始歌舞仪式的传统风习被大量保存下来,并且因为上升到了社会政治活动的层面,而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据《吕氏春秋》的《古乐》记载,古代帝王作乐,是用于祭祖和庆功等典礼活动的。如帝颛顼命飞龙作《承云》,帝尧命质和瞽叟作《大章》,都是为了‘祭上帝’。帝舜命质修《九招》、《六列》、《六英》是为了‘明帝德’。禹命皋陶作《夏龠九成》是为了‘昭其功’(治水之功),汤命伊尹作《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是为了‘明其善’,表彰汤‘率六州以讨桀罪’的功德。武王命周公作《大武》是为了歌颂武王伐殷,‘以锐兵克之于牧野’的武功。”[21]66由于音乐在统治者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此,到周代时,统治者就专门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乐官制度。《周礼·春官》中就有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蒙、眠除、典同、磬师、钟师、笙师等等一系列的乐官,并且,每一类乐官都有固定的成员及其官阶。上古时期,最早的乐器主要由一些常见之物制作,或者本身是一些日常所用器具,如最早用石、竹管、动物骨筒制作成磬、竹笛、骨笛、骨哨等乐器,后来还把某些特定的兵器、贮具、炊具、饮具等当作乐器,如铙、缶、龠、角等。《周易》卦爻辞《离》九三说:“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22]缶是一种陶器,类似今天的坛子,最初应该是一种贮具或炊具,先秦两汉文献有大量击缶的记载。有人考证,古乐器铜鼓就是由炊具“釜”演变发展而来。据文献记载,古筝在战国时期是作为武器使用的,传说为战国晚期秦国大将蒙恬所发明,亦称秦筝,所谓“筝横为乐,立地成兵”,进攻时可击打敌人,防守时可以作为盾牌抵挡刀枪和箭镞。这种将生活用具或者兵器当作乐器的情形一直延续到后代。早在周代,制造乐器的材料已十分丰富,有金、石、土、革、丝,木、竹等,其中以青铜制造的编钟地位最为重要。湖北随县出土战国初期曾侯乙墓中的青铜编钟规模巨大,多达64 件,共重2500 多斤。其工艺精湛、音域宽广、乐律完备,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罕见的奇迹,体现了中国古代乐器制作和音乐艺术发展的极高水平。这种大型的编钟一般在古代祭祀或庆典仪式上演奏,能够产生庄严、隆重、崇高、肃穆的效果,其在发挥音乐的社会政治作用的同时,能够给人以审美的感受。故有学者云:“在先秦哲学和美学中,最初由史伯、晏婴所提出的‘和’的观念是直接和音乐相关的。单穆公、伶州鸠、伍举等人对音乐对人的情感的影响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分析,也包含了对艺术所特有的审美特征和社会功能的分析,从音乐去观察美与艺术,高度重视音乐性的美,这对中国古代美学和各门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特征的认识上,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21]68
绘画艺术方面,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文物遗存,我们了解到,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具备了初步的绘画技能及原始的绘画审美意识,他们把自己的审美感受、审美思维,通过具有美感的线条性结构描绘表现出来。上古绘画的载体主要包括岩石、陶器、丝帛、武器以及原始的生产生活工具等,其中以陶绘最为典型。我们可以通过对以陶器尤其是彩陶为载体的绘画艺术为例来进行分析。黄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公元前6000 年—公元前5000 年)、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 年—公元前3000 年)、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 年—公元前2000 年),以及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 年—公元前3300 年)、大溪文化(公元前4400 年—公元前3300 年)、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300 年—公元前2600 年)等文化遗址中,均发掘出大量的彩陶。原始先民制作陶器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其实用功能,早期的陶器基本上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盆、罐、釜、盘、钵、豆、盉、鼎等,均为炊具、饮具或贮具。其审美特征除了体现在其形制上的装饰技巧和艺术效果上,还表现在其彩绘纹样上。考古发现的这些彩陶上,有着极为丰富的纹样。早期彩陶上的纹样主要表现为对与人有关的自然之物的模拟,例如半坡村等地出土的陶器中的人面纹、鱼纹、鸟纹、鹿纹、蛙纹、蜥蜴纹以及模拟植物的植物纹样等。这种人类最初的审美创造,既是原始先民劳动生活的缩影,也体现了原始先民对自然的模仿与探索。其后,伴随着智力的发展和审美的提高,原始先民开始关注到均衡、运动、频率、节奏等自身的一些独特体验,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几何纹样,如三角纹、菱形纹、方形纹、螺形纹、波浪纹、圆圈纹等,其表明,原始先民已经开始摆脱纯粹模仿的阶段,进入到了更高层次的创造阶段,已经能够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抽象与概括了。这无疑是人类审美意识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敏泽先生认为:“这些画绘中,包含着夸张与变形,想象和概括,特别是它的以线条作为造型的基本手段,充分说明了此时进化了的原始人在审美意识、能力等等方面的进一步提高。并作为文化遗产传承下去,为以后我国工艺美术的图案奠定了初步的、然而又是坚实的基础。”[23]
上古的建筑艺术虽然现在已经很难看到实物遗留,但从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上古的建筑艺术已有了相当高的成就,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西安半坡遗址的大方型房屋、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约在仰韶文化晚期)的窑洞等等,都是新石器时期中国先民在建筑艺术方面的杰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远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先民的建筑中就已经蕴涵着一定的审美意识。如在河南安阳史前遗址中发现以白灰涂墙面的做法,不但能够增加建筑物内部的亮度,也增加了建筑物的美观;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属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中,主体建筑由女神庙主室和若干侧室组成,神庙墙体内外敷泥,表面压光或施用彩绘,这也表明了,其时的彩绘装饰已不限于陶器装饰,也运用到建筑装饰中了。至夏商周三代,建筑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宫殿、坛庙、陵墓、官署、监狱、作坊、民居等建筑均已出现。当时建筑的屋盖形式有两坡、四坡、攒尖等多种;色彩方面,除柱按等级着色外,又有墙面刷白、地面涂黑的做法;建筑构件的装饰构图方面,有同心圆、卷叶、饕餮、龙凤、云山、重环等纹样。相传夏朝建国之前就有城池建筑,《礼记》引《世本》云:“鲧作城郭。”而现今发现的最早城池城墙建筑遗址属于商代城墙建筑,如河南郑州商城和湖北盘龙商城,它们都属于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期。商代后期以至周代,建筑技术和建筑规模得到极大发展,特别是周代已经非常注重建筑的整体设计和内部构造。刘向《说苑·反质》云:“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24]《竹书纪年》亦云:“纣作琼室,立玉门。”[25]商周建筑的精心设计及其居室内部的华美装饰,不仅是实用的需要,同时蕴含着商周先民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
此外,青铜器艺术在上古艺术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大量遗存到现在的殷周以来的青铜器艺术,其成就之辉煌,获得了全世界的公认,就像古希腊的雕塑艺术获得了全世界的公认一样。彼时的青铜器不但以形体的巨大、技艺的精巧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赞誉,而且还非常强烈地体现了它们所产生的那一历史时代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具有超出于一般工艺品的高度艺术价值。因为许多青铜器的制造,本来就是一种有着重大纪念意义的艺术创造,其不同于一般日用品的生产。郭沫若先生认为,殷周青铜器所特有的那种狞厉、崇高的美,战国青铜器所特有的那种轻灵、飞动的美,都是后世所难以仿效的。但是,上古造型艺术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没有受到当时思想家们的充分重视,因为从事造型艺术在上古是被轻视的匠人们的事,这种情况直到秦汉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造型艺术的发展对于早期审美意识的生成,其影响虽不如音乐那样明显直接,但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的来看,图腾崇拜、上古神话、上古文字等原始文化,以及音乐、绘画、建筑、青铜器等上古艺术,对早期审美意识的生成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中国原始文化和艺术中所提供的实证材料,有助于我们探索中国先民审美意识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在认知论上的前提。没有这些文化和艺术就不会有早期审美意识的生成。蕴含着浓郁审美意识自觉特征的中国早期审美思想,是对上古时期各类原始文化和艺术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哲学概括和升华。这些原始文化和艺术对于中国先民审美形象的建构、审美思维的创生、审美意象的表达、审美经验的累积影响深远,中国先民早期审美意识的生成,乃至早期审美思想的生成,就是一个在这些不同文化形态的合力作用下得以不断创生的过程,其对后世艺术创作、审美思想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