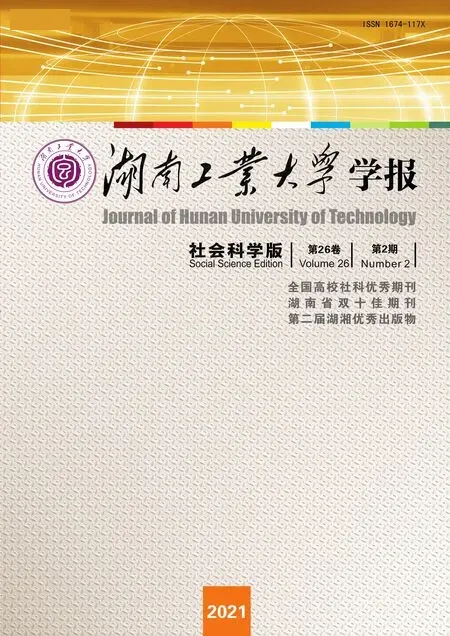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资本主义早期工人生活的真实语境
——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的谬误
牛晓迪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一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记录
19 世纪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影响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正如梅林对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评价:“诚然,恩格斯不是第一个描写英国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人,可是他毫无疑问是最后一个使自己的先驱(他本身利用了这些先驱的著作)多少逊色的人。”[1]98恩格斯在“大城市”篇中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特别是住宅情况的真实记录,向人们展现出了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实况。他通过城市这个平台,向我们展开了资产者与无产者生活状况之间冲击性对比的画卷。 “大城市”开篇便提出:“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是看不到尽头的。”[2]303它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密集的工业,热闹的街头,甚至有难得的自然风光,但就是这样令人陶醉的景象背后却隐藏着工人阶级难以言喻的悲苦生活。恩格斯称工人阶级居住的地方为“贫民窟”,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性的称呼——尽管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同样是社会生活的个体,同样参与了社会的建设,但与资本家富丽堂皇的住宅相比,工人阶级居住的地方只能被称为贫民窟。城市中最劣质的房屋横七竖八地立在环境最恶劣的地方,拥挤而肮脏,坑坑洼洼的街道积满了脏水——因为没有下水道,垃圾被随意丢弃在街道中。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贫民窟的“建筑风格”。正如恩格斯所言:“穷人总是有的。贫穷会在任何地方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总会以各种丑恶的形式存在于富庶的大城市的心脏里。”[2]312大城市总是富有和贫穷对比最鲜明的地方。
恩格斯挑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对其区域内工人阶级的住宅状况进行了描述。从伦敦到都柏林再到爱丁堡和利物浦等等,恩格斯的考察范围涵盖了英国各个地区内的重要城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曼彻斯特。那里的情况像其他地区一样糟糕,工人阶级的饮食、身上的穿着、暂居的住房、活动的区域、纵横在区域内的街道、环绕着这片区域的空气、空气笼罩下的疾病……这一切都糟糕得难以形容。或许用恩格斯这句话来表达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最为贴切:“如果想知道,一个人在不得已时有多么小的一点空间就够他活动,有多么少的一点空气(而这是什么样的空气呵!)就够他呼吸,有什么起码的设备就能生存下去,那只要到曼彻斯特去看看就够了。”[2]335
然而恩格斯这种基于亲身观察和可靠资料反映的历史事实,却遭遇曲解与批判。一些学者给马克思、恩格斯戴上了悲观主义历史学家的帽子,认为其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描述是否定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历史进步意义的表现,实质是为了宣传共产主义的专制集权体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中由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收录了多篇论文,集中表达了这种指责。面对这种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观点的误读,我们需要还原历史真相,重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劳动与生活状况评价的真实语境。
二 哈耶克等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读
面对工人阶级在19 世纪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发展背景下困苦生活的历史真相,哈耶克等人却不以为然。他们逃避这个事实,认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是受益的人群,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切实的提高。在这些资本主义历史学家眼中,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与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成就。哈特威尔对弗劳德一段话的引用很能说明这种态度:“19 世纪的人们在反思他们的状况和前景的时候,不管怎么样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看法:我们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进步,不管是事业,还是享受,不管是信仰还是理论,不管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信念——感谢上帝,我们跟自己的父辈的生活不同了。我们承认他们的美德,我们体谅他们被条件所限,但我们不会让自己过于谦逊而不承认自己具有无比的优越性。”[3]202在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上,哈耶克等人控诉马克思、恩格斯是悲观主义的、反社会进步的历史学家,他们为了反驳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与真切同情,虚构了许多看似可信的理由。
(一)对前工业化时代的浪漫想象
哈耶克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描述得如此苦不堪言,在于他们对前工业化时代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想象,认为那时人们的生活状况要远远幸福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T. S.阿什顿在《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一文中,对人们过分赞誉农业以及返归农村生活的愿望逐渐增强的趋势表示不满,并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看作是这种思想倾向的表现。刘易斯·M.哈克尔在《美国历史学家的反资本主义成见》中支持了T. S.阿什顿对前工业化时代浪漫化的批评。在他看来,19 世纪之前人的生活相较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而言是粗野而恶劣的,19 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人的生活状况相较于前者而言毋庸置疑是一种进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同样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前,传统家庭作坊制下的产业工人并没有比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工厂制度下工人的生存境遇要好。急剧增长的人口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下无法得到充足的生活资料的保障,在此种情况下人们的生活状况苦不堪言,而工厂制度则开启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其生产的廉价商品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因此,“历史的真相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极端不能让人满意的”[3]175。
约翰·马犹斯基则坚持认为工人的工资相较于前工业化时期得到了实质的增长,并认为工人工资的增长会直接促进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人都可以想象,实际工资的增长会促进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3]218然而,面对这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工资增长,E. P.汤普森却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如果从探讨那种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假定的平均工人的工资水平,转向对食品、衣服、住宅等消费品乃至健康和道德状况的注意,那么,有关工业革命期间生活水平的争论也许就会有最高的价值。”[1]361事实上,工人阶级并不是增长的物质资料的消费主体,工人工资的增长与其生活水平的提高或是生活质量的改善更不能划等号。工人的生活成本始终在不断增长,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仍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工资仍然只能勉强维持其生命的继续,“在国民财富增加了的同时,‘平均的’工人却仍然在接近于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生活”[4]366。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仍然不足,其生活物资依旧短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善。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是历史退化论的跟随者,唯物史观坚信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他们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创造的物质资料、提供的就业机会,更未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看作是历史的退步。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形容“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5]127。将工业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阶段。恩格斯更是认为“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6]402。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相较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这却不能遮蔽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工人阶级的生产与生活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否认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工人的生活已经面临的各种苦难,而是拒绝借用这种苦难的面纱掩人耳目,造成无视工人阶级在19 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依然甚至深化的困苦生存状况,相对而言的社会进步并不能掩盖工人阶级表现不同但实质相同的异化处境。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力图展现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影响工人阶级生活与劳动状况的完整图像。
(二)反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者
不同于韦伯从宗教维度考察资本主义精神的方式,R. M.哈特威尔完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言说资本主义精神。在他那里,反资本主义精神是历史学家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这种反资本主义的精神本来就不是源于日常体验,它是知识分子炮制和传播的一种人工文化制成品(cultural artefact)”[3]137。他将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反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学家的代表,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无视现实社会的进步,意图脱离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沉醉于其政治立场,对资本主义作出纯粹意识形态的解读——资本主义始终是负面的,资本主义只有缺陷没有成就。他将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反映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攻击,进而对资本主义的存在进行盲目的维护。这种荒谬的解读和天真的自信背后是其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与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暴露。T. S.阿什顿则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负面影响归咎于在此之前的历史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容忍的东西,其实大多都是属于较早历史时期的、很快就要过时的法律、风俗、习惯和组织形式导致的后果。”[3]23然而,这种为了维护资本主义而将一切负面影响转嫁到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借口并不能令人信服。
刘易斯·M.哈克尔则将19 世纪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发展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视为一种恶意诽谤。他肯定19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进步:“在人类历史上,到了19 世纪,国家才第一次大规模地实行了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政策。19 世纪生产出了廉价商品,从而使工业化经济体中的实际工资得以大幅度地提高。19 世纪允许资本大规模自由流动,从而为落后国家内陆地区的开发和生产开辟了道路。”[3]43同时他也否认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发展强迫工人阶级作出的牺牲。在他看来,工人阶级之所以生活在贫民窟,面对恶劣的生活条件与劳动环境的窘境,的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工人们自己建造的简陋低劣的住宅、政府严苛的税收、外来移民对本地工人工作机会的抢占等等,但唯独资本家的剥削不在其中,资产阶级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资本主义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在他看来,否认这一“事实”的马克思、恩格斯是居心叵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动者。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相较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历史进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7]471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资本主义历史贡献的肯定并不能遮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以及其给工人阶级带来的真实苦难。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它是有存在必然性的,但这种存在的必然性并不等于时间上的永恒性。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正如封建社会让位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般,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也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形而上学地定义过资本主义,他们既看到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性,也预测出了其消亡的不可避免性。R. M.哈特威尔等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盲目维护恰恰表明了其没有用历史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
除此之外,R. M.哈特威尔等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生活与劳动状况记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将其曲解为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虚假作为。然而,我们只要耐心阅读过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异化劳动的理论与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叙述,这种谎言便会不攻自破。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工人与其劳动产品、自身劳动、人的本质以及人与人的异化的分析,从四个方面向我们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阶级劳动产品的生产即是其劳动产品的丧失,工人劳动对象化的结果是他与自己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的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5]90至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方面,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具体向我们展现了矿业无产阶级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农业无产阶级极其贫困的生活状况。恩格斯从工人的构成年龄(从儿童、妇女到成年男性不等)、工作时间(长达12 小时、24 小时或36小时的工作时间更是经常发生)以及工作环境(潮湿肮脏且非常拥挤)三个方面向我们说明了工人阶级恶劣的生存境遇。工人阶级的住宅状况何等不堪以至于恩格斯发出怒声:“这并不是美国运奴隶的船只的统舱,而是‘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住所呵!”[2]532工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存状况导致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工人成为各种疾病的载体,这一切都加剧了对矿区工人生命的摧残,过早的衰老和过早的死亡(35 至40 岁)在矿区工人身上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这一切使得恩格斯不禁发出感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2]382
(三)对于共产主义的误解
R. M.哈特威尔给了资本主义过多的荣誉。他将资本主义制度推崇为前所未有的能够为普通民众提供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制度,更是为其在经济生产方面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而感到无比自豪。他将资本主义的生产贴上平等为民的标签,“资本主义的生产从一开始就是为大众而生产,大众消费者一直是资本主义生产永恒的特征”[3]141。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对其民众允诺的平等与自由的初心,也多次肯定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能力,这相较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社会制度的文明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社会成员是否大都享受到了社会进步带来的实际收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成就是无法超越的吗?乔伊斯·阿普尔比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考察,基于价值观的异质性指出了资本与民主之间存在的冲突:“民主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资本主义是指对生产过程的投资,是否依靠拥有政治权力的参与者对资本主义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资本主义与道德无关,而民主则充满着道德关怀。”[8]466-467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深化了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资产阶级的丰裕富足与无产阶级的贫困悲惨对比鲜明,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资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的维护者在分配领域并无实质性的作为。
不仅如此,在R. M.哈特威尔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十分惨淡:“很显然,社会主义所创造的财富没有资本主义多,它总是与限制自由和生活选择的极权主义政权联系在一起;在平等地分配财富方面,它也无足称道。”[3]142“现在,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相信,资本主义处于‘垂死状态’;也几乎没有人支持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政策;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3]137R. M.哈特威尔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是肤浅的,他用来抵制社会主义理想的种种理由并无任何说服力。正如科恩所言:“任何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尝试,都会遭遇处于牢固地位的资本主义力量和个人人性的自私……然而,这些障碍不是贬低那一理想本身的理由。”[9]75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前提,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力量,以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出发点,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指向的社会。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已经有了将一般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哲学前提的意识,并论述了法国唯物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作出了描述:“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6]537这是只有在分工得到消灭,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场景。马克思意在强调只有处于物质资源极其繁荣的情况下,人们才不再局限于分工的限制,从而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兴趣与能力,从事能够体现自己创造力的活动并以此来发挥生命的本质力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消灭异化与分工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在于它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它克服了以往社会形态中狭隘的生产关系,在更加充分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构建更和谐的社会交往关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其共产主义思想区别于过去一切社会主义思想之处作出了说明。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具有其他社会交往形式不具备的现实基础,那就是将以往社会发展的结果作为自身发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条件不是脱离于他们的先验存在,而是处于一定交往关系中的个人凭借其物质生产活动所建构的。重要的是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规律即个人的自主活动与其相应的交往形式并不是永远一致的。最初作为物质生产活动前提的交往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生产实践活动的阻碍,进而被适应于人的自主活动的新交往形式所替代。随着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这些交往形式随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链条。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揭示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这既解释了资本主义的退场,也解释了共产主义的出场。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透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局限性的分析,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作出了鞭辟入里的诊断,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认为不能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仅凭思维构建出未来社会的完美乐园,要想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来的社会弊端,其钥匙隐藏在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中。在恩格斯看来,生产方式由个体生产向社会化生产转变,劳动产品的占有形式也应由个人占有转变为参与生产者共同占有。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占有形式并没有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仍然以私人占有的形式配合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10]551。恩格斯分析了生产力的资本性质与社会性质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后果,即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阶级矛盾。其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占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方式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10]557。因此,只有将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由无产阶级管理国家,“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10]562。如此一来,才能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运动,阐释了社会主义由空想走向科学的发展。
三 历史真相争论背后的政治立场交锋
历史的展现在最初便是作者价值观涉入的结果。对于历史事实的解释,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政治立场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正如哈耶克所言:“在政治性理想或政治思想中,恐怕没有几个不涉及对整个历史进程看法的;而历史记载,恐怕也没有几个不是被用为某些政治目标之象征的。”[3]1历史纪录背后隐藏的是政治立场之间的交锋。
哈耶克等人将恩格斯依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对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下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记录,看作是敌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献,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辩护士,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出发作出的误读。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工人阶级生活状态的记叙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在当今仍有重要的价值:“基于当今社会研究的参与观察法、材料征引法和田野笔记写作法,可以发现,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资料’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具有方法上的示范价值,《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堪称参与式观察、材料综合运用和田野笔记写作等方面的先驱文本。”[11]恩格斯对材料的甄别与引征建立于其在曼彻斯特棉纺厂的亲身经历以及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深入观察之基础上,并不是历史材料毫无生气的选择与堆砌。
哈耶克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无视工人阶级真实的生活状况以及恩格斯基于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的科学方法,以虚构历史来定义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考察,将其看作是在政治目的驱动下建构的虚假神话。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带给工人阶级的并不是生活境遇的恶化或是剥削,而是给他们提供了继续生存的机会,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机器的使用为那些丧失劳动工具从而面临生存困境的工人阶级提供了继续生存的可能。然而,哈耶克看到了工人阶级的生存,却没有看到工人阶级是如何生存——工人阶级是如何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靠一点仅能够维持他们呼吸的收入艰难地度过生活。工人阶级为了如此微弱的生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国在工业化初期所遭受的严重的固体废物污染、可怕的空气污染以及容易被忽视的水污染让城市环境在工业化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处于底层的工人阶级的境遇则是这样的代价中最沉重的一笔”[12]。
除此之外,哈耶克用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依据是,相较于资本主义之前社会底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言,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带给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并不会更严重些。他把工人阶级的遭遇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发挥其优越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并认为这种副作用不应作为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理由。哈耶克等人基于资产阶级立场,用社会进步的副作用来搪塞工人阶级非人的生存境遇,对工人阶级的这种牺牲持虽然无可奈何但也理所当然的态度。他在将前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进行比较时,试图用工人阶级相对缓解的贫困来证明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仁慈。然而,这只不过是其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的再一次暴露。实际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相对缓和与从根本上消灭工人阶级异化的生存状态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命题。很显然,后一个问题在哈耶克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那里并不重要。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立足于工人阶级的立场,看到了所谓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使得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种言论的虚假性,力图反映出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历史真相,并且通过观察工人阶级为了改变异化的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斗争,发现了工人阶级作为变革社会的历史主体所背负的伟大使命。列宁评价道:“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制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13]91-92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向我们展现了1844 年的一次工人罢工,在这次罢工中工人阶级显现出了承担社会变革的潜力:“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这样在去年(1844 年)多雨的深夏在露天里度过了八个多星期。除了床上的印花布帐子,他们和婴儿就再没有其他可以遮蔽的东西;除了工会的微薄的补助和小铺老板的愈来愈少的赊欠,他们就再得不到其他的帮助。”[2]545难以想象,工人们忍受饥饿和欺凌于1844 年那个多雨的深夏在露天里度过了八个多星期!在与身体的饥寒、渺茫的希望、资产阶级的迫害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以文明和守法的姿态为自身赢得了尊严。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记叙,不仅仅表达了对工人阶级的深切关怀,更是为了让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异化处境,“正是共同的恶劣生活与共同条件或者异化的现实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个独立阶级”[14],进而自觉形成工人阶级的整体意识,“这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阶级,而不单单是分类学意义上的阶级”[15]109。处于相同社会关系中的工人阶级为了改变现状而进行斗争,也正是在工人阶级为自身权益做斗争的过程中,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觉悟、自制力以及抗争精神,明确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便明确了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并指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从而实现了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的结合。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便是社会革命的潜在表现:“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6]17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是对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直言不讳:“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7]504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是以人类解放为目标,将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使命。正是基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出于对无产阶级的深情关切,马克思、恩格斯才能如此关注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苦难以及他们真实且迫切的希望与要求,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耗尽心力。
当我们在言说19 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事实时,哈特威尔等一些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们却意图混淆问题的关键,转而强调相较于前工业化时期,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前文所言,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表示过反对。对19 世纪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记叙并不是弱化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同样也不是将工业革命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画上等号。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之前工人们的生活已经面临的各种苦难,而是认为在19 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依然困苦甚至进一步深化。相对而言的社会进步并不能掩盖工人阶级表现不同但实质相同的异化处境。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们将工人阶级非人的生活状况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他们希望工人阶段在资本主义精神的规训下“抱有同样的理想,服从听话,干活不怕辛苦,而且深信人人必须承担天命所指派的职责,而不必追问自身所处的境况”[16]8。他们试图用部分人的获益来合理化工人阶级的献祭,以此来安抚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达到巩固资本主义大厦的目的。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那“部分人的获益”永远与工人阶级无缘,正是工人阶级被压迫与剥削的现实为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提供了主体力量。
围绕着19 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争论实质上是哈耶克等人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立场对立的表现。这些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们只愿意与以往历史阶段作比较,借此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从来不是他们的关心事项。然而马克思早就言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506。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既看到了无产阶级生存境遇的水深火热,也看到了无产阶级作为人类解放的心脏所具有的关键作用,并为无产阶级争取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实践保驾护航。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们无法阻止无产阶级向着更合乎人的发展的社会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