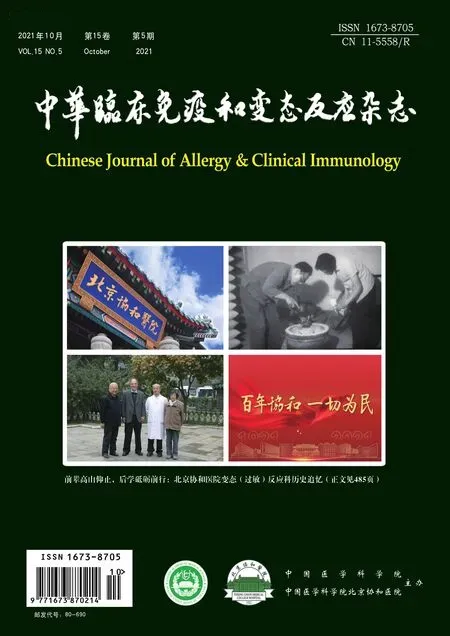风湿性多肌痛的发病机制
何烨,陈伟钱,林进
风湿性多肌痛(polymyalgia rheumatica,PMR)是一种好发于50岁以上人群,表现以肩部、颈部和/或骨盆带近端疼痛和僵硬并伴有强烈全身炎症反应的自身免疫性疾病[1-2]。PMR男女患病比例约为1∶2甚至1∶3[3],一项队列研究表明2000年至2014年间,本病在美国奥姆斯特德县50岁及以上人群中的发病率约为63.9/10万[4],我国目前尚无相关流行病学调查。PMR与巨细胞动脉炎(giant cell arteritis,GCA)密切相关,GCA患者中约40%~50%有PMR样表现,而约20% PMR患者同时合并GCA[3],尽管GCA发病机制已被广泛研究,但PMR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本文以感染、遗传、免疫和炎症为主线,系统阐述PMR发病机制,探讨PMR治疗,旨在为临床诊疗提供新思路。
1 环境因素与PMR
1.1 感染与PMR
尽管PMR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多数学者认为感染是触发PMR发病的原因之一。丹麦学者在一项自身免疫疾病与感染的研究中发现,所有需要住院治疗的感染均可增加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的风险。感染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的可能机制包括靶细胞改变,免疫细胞改变,针对病毒和宿主共有决定簇的免疫应答及特异型抗体和抗病毒抗体与自身抗原之间的交叉反应[5]。有研究表明病原体如肺炎支原体、细小病毒B19、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能通过诱导单核细胞/树突状细胞活化,产生促炎细胞因子,进而诱发PMR发生发展[6]。这些病原体的触发作用似乎与季节相关,但Hysa等学者的荟萃分析结果不支持PMR的季节性模式[7]。临床提示感染或流感疫苗接种后触发的PMR/GCA与特定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B1和HLA-DQB1有关,尤其是HLA-DRB1*04和HLA-DRB1*13∶01[8]。这类患者或是PMR的一种特定亚型:对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GC)反应更快,在诊断时CRP数值更高且盂肱关节滑膜炎发生率更低[9]。
1.2 衰老与PMR
GC是目前治疗PMR的一线药物[10],未经治疗的早期PMR患者皮质醇和硫酸脱氢表雄酮生成减少,提示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的抑制可能与PMR发病有关。衰老导致抗炎激素如性腺和肾上腺激素(即睾酮、脱氢表雄酮、雄烯二酮)的水平下降是HPA轴改变的重要原因,故PMR常发生于老年人群[11]。免疫系统的衰老也与PMR发病相关,PMR患者中自然杀伤族2D受体(nature killer group 2D, NKG2D)优先在衰老的CD4CD28-、CD8CD28-以及CD8CD28 T细胞上表达,并上调炎症因子IFN-γ和TNF-α,参与PMR发病过程[12]。同时在PMR患者中也可以观察到效应记忆和终末分化的CD8+T细胞过早的免疫老化(CD28丧失)[13]。
1.3 损伤与PMR
轻度损伤如跌倒所导致的免疫刺激机制可能会诱发疾病[14],外科手术等组织损伤则通过释放细胞因子(如IL-1、IL-6等)和其他细胞产物激活DC诱导CD4+T细胞极化为Th17细胞,后者释放IL-17与IL-6进一步刺激IL-6产生,参与PMR发病机制[15]。
2 遗传背景与PMR
2.1 HLA等位基因与PMR
PMR发病具有家族聚集性和地域种族差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北欧后裔中尤为常见[16]。PMR是一种多基因易感性疾病,许多等位基因可能参与疾病的发病和进程。其中主要组织兼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II变异型是主要的基因遗传背景,HLA-DRB1等位基因变异构成了PMR的基因危险因素[17]。与健康对照组相比,PMR患者中HLA-DRB1*0101/0102和HLA-DRB1*0401等位基因显着增加[18],且HLA-DRB1*0101/0401等位基因可能影响PMR预后[19]。PMR与GCA通常伴发,或可归因于部分共同的遗传背景,如HLA-DRB1*04等位基因与PMR合并相关,且与GC抵抗存在联系[20]。Prieto等[21]报道HLA-DRB1基因相关GCA以颅外大血管受累为主型,PMR多为首发表现之一,而孤立型PMR与该等位基因的相关性则在不同地域种属之间存在差异[6]。
2.2 非HLA等位基因与PMR
2.2.1 细胞间粘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基因与PMR
ICAM-1广泛分布于活动期PMR患者的肩关节滑膜中,意大利学者发现ICAM-1蛋白G241R变异与PMR易感性相关并增加PMR的复发风险[22]。ICAM-1基因多态性可能通过改变配体结合或细胞表面多聚ICAM-1的稳定性,影响细胞信号转导,最终导致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发生[23]。但由于研究群体存在不同的种族背景,在另一项有关西班牙PMR患者的研究中Amoli等认为ICAM-1蛋白G241R变异并非PMR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20]。
2.2.2 一氧化氮合酶(nitric oxide synthase,NOS3)基因与PMR
PMR疾病发生与内皮损伤和修复的严重失衡相关,与健康对照相比,PMR患者外周血中循环内皮微粒与内皮祖细胞的比率更高,这可能和疾病相关炎性介质参与内皮微粒的形成和内皮祖细胞的消耗有关[24]。一氧化氮是内皮功能障碍的重要标志物之一,NOS3基因T-786C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孤立型PMR有显著相关性[25]。
2.2.3 细胞因子基因与PMR
西班牙学者发现,PMR和GCA与TNF微卫星多态性有关,其中TNFb3与孤立型PMR呈正相关,TNFd4与孤立型PMR呈负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相关性似乎独立于HLA-DRB1关联[26]。细胞因子基因如IL-1RN*2等位基因、IL-6基因-174 G/C位置启动子多态性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PMR发病[27]。
3 固有免疫与PMR
天然免疫系统是机体抵御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线,DC经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识别不同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介导机体的天然免疫,并在获得性免疫中起着重要作用[28]。有研究显示PMR患者颞动脉外膜中DC被激活[16],并产生趋化因子CCL19和CCL21。急性期PMR患者外周血中单个核细胞TLR7表达升高,并随着疾病的完全缓解而消失[29]。西班牙学者提出PMR及其他年龄相关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发生与固有免疫系统功能异常相关,尤其是吞噬细胞功能障碍。众所周知吞噬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是执行固有免疫作用的效应细胞,其效应功能被定义为趋化性、吞噬作用和呼吸爆发。活动期PMR患者体内的呼吸爆发被抑制,而缓解期得以恢复,因此lvarez-Rodríguez等[30]认为固有免疫系统功能异常可能是PMR的发病机制之一。
4 获得性免疫与PMR
4.1 细胞免疫与PMR
人类慢性炎症性疾病的一大特征是效应T细胞(例如Th1或Th17细胞)与免疫抑制细胞(如Treg细胞)之间的不平衡。PMR患者外周血中Th17细胞显着增加而Th1细胞和Treg细胞减少,GC治疗后可纠正Th17细胞与Treg的失衡。Th17细胞通过IL-17诱导慢性炎症,随着Th17细胞表面的CD161表达增加,未经治疗的PMR患者体内CD161+CD4+T细胞较对照组能表达更多IL-17。CD161+CD4+T细胞及通过STAT-1/STAT-3磷酸化参与Th17细胞极化调节的细胞因子,被认为是PMR发病过程中的关键[31]。日本学者分析了来自PMR患者的T细胞和先天淋巴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s,ILCs),结果表明PMR患者外周血中的T细胞和ILCs细胞均被激活,这种激活可能与衰老引起的免疫系统改变有关。粘膜相关不变T(mucosal associated invariant T,MAIT)细胞是ILCs的重要组成部分,缓解期PMR患者外周血HLA-DR+CD38+MAIT细胞频率高于对照组和活动期PMR患者,且与缓解期PMR活动评分和CRP水平正相关,提示MAIT细胞活化可能与PMR亚临床疾病活动性相关[32]。这些发现表明T细胞和ILCs细胞均参与PMR的发病机制。活化的细胞毒性/抑制性T细胞减少和循环Th1和I型细胞毒性T细胞(type I CD8+cytotoxic T cells,Tc1)增多是PMR和血清阴性对称性滑膜炎(RS3PE)的共同特征[33],且在PMR患者血清中可以观察到可溶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sCTLA-4)浓度升高,这可能与细胞因子异常产生或细胞间信号通路异常激活有关[34]。目前,针对CTLA-4和PD-1/PD-L1轴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是癌症治疗的热点,但由于阻断PD-1/PD-L1轴在激活免疫细胞攻击癌细胞的同时也释放自身反应性T细胞的潜力,因此使得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增加[35]。近期研究发现抗PD-1或抗PD-L1免疫治疗过程中,部分肿瘤患者出现了PMR样表现[36],发生率约为0.2%~0.4%[37]。与抗CTLA4单药治疗相比,抗PD1/PDL1单药治疗更容易发生PMR-irAE,并且临床表现通常不典型[38],使用GC及DMARDs药物如甲氨蝶呤可使部分患者在不停止ICIs的情况下受益[39]。
4.2 体液免疫与PMR
B细胞激活因子(B cell activating factor,BAFF)和增殖诱导配体(a proliferation-inducing ligand,APRIL)是维持B细胞池和体液免疫的关键因素。PMR患者血清BAFF水平较健康人群升高,治疗缓解期血清BAFF显着降低,且与患者体内ESR和CRP水平正相关,提示血清BAFF水平或可作为PMR疾病活动度的标志物[40]。van der Geest等[41]研究GC治疗前后PMR患者外周血B细胞亚群分布变化时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新诊断的PMR患者外周血B细胞数量减少,治疗缓解后B细胞数量又迅速恢复。深入研究表明,循环B细胞数量的减少与疾病活动期间效应B细胞重分布有关。Carvajal等[42]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外周血B淋巴细胞减少和异常B细胞亚群的分布与PMR疾病活动相关,且使用托珠单抗(IL-6受体单克隆抗体)治疗后患者外周血B细胞数量与分布可得到纠正。在趋化因子配体(CXC chemokine ligand,CXCL)9-趋化因子受体(CXC chemokine receptor,CXCR) 3和CXCL13-CXCR5轴中,可以观察到PMR患者外周血与B细胞迁移相关的趋化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通路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B细胞在血管壁中的归巢,进一步佐证了B细胞参与PMR发病[43]。
5 炎症因子与PMR
5.1 IL-6与PMR
PMR患者上肢受累时,其典型超声表现为三角肌下滑囊炎和肱二头肌腱鞘炎[1];受累的斜方肌和股外侧肌中IL-6、IL-8和IL-1β等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升高,全身炎症反应明显,伴随PMR相关的肌肉骨骼不适症状[44]。其中IL-6是PMR发病机制中关键促炎细胞因子之一。研究表明PMR患者血清IL-6水平明显升高,并与血沉和CRP正相关[40]。IL-6可能通过影响外周血B淋巴细胞数量和异常B细胞亚群分布[42]或Th17细胞和Treg细胞之间的平衡参与PMR发病[31]。Devauchelle-Pensec等[45]发现托珠单抗单药治疗对早期PMR有效。早期PMR患者血象中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血红蛋白水平降低,且这些炎性标志物与患者血清中的IL-6水平呈线性相关;托珠单抗治疗后患者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的水平有所减少,血红蛋白增加,且不再与IL-6线性相关,提示IL-6在PMR发病机制中至关重要[46]。
5.2 其他炎症因子与PMR
van der Geest等[40]发现PMR患者血清CXCL9和CXCL10水平升高,可能与Th1细胞迁移相关。尽管PMR患者血浆及受累肌肉中TNF-α水平均升高,但与GCA不同的是,其在PMR病理生理中并不起核心作用[47]。TNF-α抑制剂英夫利昔单抗治疗PMR患者没有获益且增加不良反应,因此ACR/EULAR指南强烈不推荐PMR患者使用TNF-α抑制剂。此外,褪黑素调节细胞因子,可促使PMR患者中IL-4、IL-8和IL-10血浆浓度显着升高并与昼夜节律变化平行[48]。Kreiner等[49]发现PMR患者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且与细胞因子IL-6、IL-8和脂肪因子脂联素异常有关。
5.3 炎症因子传导通路
Wnt通路通过促进成骨细胞活性刺激骨形成,同时下调核因子kappa-B受体激活剂配体(RANKL)的产生来抑制破骨细胞骨吸收。在未经治疗的PMR患者中,全身炎症与 Wnt通路的失调有关[50]。近年来发现酪氨酸激酶(janus kinases,JAK)/信号传导、转录激活因子(STAT)信号通路与GCA发病相关,抑制JAK/STAT通路可有效阻止大中型血管炎中的病原性免疫反应[51]。托法替布是一种口服JAK抑制剂,主要选择性抑制JAK1、JAK3介导的信号通路,对 JAK2也有轻微影响,在GCA小鼠模型中可减少T细胞增殖及血管内膜增生。鉴于PMR与GCA发病机制联系紧密,且PMR发病的关键促炎因子IL-6在骨骼肌中激活JAK/STAT通路[52],因此推测JAK/STAT通路或参与PMR发病机制。
综上所述,PMR是一种机制复杂的疾病,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感染、遗传、免疫和炎症等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举足轻重。与GCA发病机制类似,在特定的遗传背景下,PMR患者肩部、颈部及骨盆带相关滑膜囊中的DC可能通过PAMP激活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其中IL-6通过影响外周血B淋巴细胞数量和异常B细胞亚群分布并经STAT1或STAT3磷酸化参与Th17细胞极化调节,可能是PMR发病的关键机制。进一步研究PMR的发病机制,发现新的靶点,可为疾病的治疗提供更多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