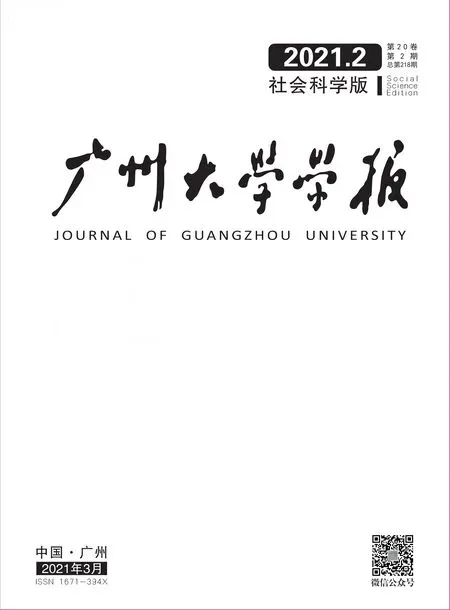创伤历史、文学的命运与跨文化记忆:文学记忆与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①
阿斯特莉特·埃尔 著, 王小米 译
(1.法兰克福大学 新英语文学与文化系, 德国 法兰克福 60629;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语言文学跨学科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44)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将文学与媒介研究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记忆研究是一个文化史学、社会心理学、媒介史学、政治哲学和比较文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在“文化记忆”这一术语引领下,学者们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过去与现在(还有将来)关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具备生理的、媒介的和社会的属性。文化记忆既包括“记忆”又包括“遗忘”,既有个人的维度,又有集体的维度,并且两个维度之间紧密联系。(1)参考:Astrid Erll, Memory in Cultu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原注
记忆研究介入文学和媒介研究有多种可行方式。例如,有学者对古代记忆术带给文学和艺术的意义产生兴趣,还有学者从“文学的记忆”的角度研究文本间性,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研究所谓正典的形成。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议题包括叙事、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媒介(如照片和电影)在记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不同记忆模式的口述和文本以及数字媒介时代的记忆等。本文将从中择取三个议题,这三个议题不仅是当下跨学科的记忆研究所热切关注的,同时也关涉到文学和媒介研究中的核心领域。它们是:
1.创伤历史的媒介表征,如文学和电影。这个话题将记忆研究指向大屠杀研究以及战争和暴力的文化史研究。各种历史的不公正以及人权被侵犯的状况(如殖民战争、美国的奴隶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或者澳大利亚的“被偷走的一代”)在全球范围内的多重表征,如大屠杀书写、战争影片、“9·11事件”小说和一战诗歌,这一切让我们有了被媒介化的“创伤”记忆。个体创伤和文化创伤的逻辑关系、表征记忆的叙事和其他审美形式以及文学和电影的社会功能等是这一研究领域要应答的核心问题。
2.文学的“命运”。对文学“命运”的研究(呼应了阿比·瓦尔堡的艺术史研究)采取的是一种历时的角度。故事从被人知晓到湮没无闻到再一次被人知晓,在跨越几十年、几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文学作品从首次被人阅读到重读再到被重写,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总是被不间断地改编并付诸新的用途。从记忆的视角研究文本及其他记忆载体的“社会生命”时,文本间性、重写、媒介间性以及修复等都是其中的关键概念。
3.跨国记忆与跨文化记忆。近来,记忆研究已经逐渐偏离之前流行的民族主义路径,跨国界的、跨文化的记忆引起了学界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在比较文学和媒介研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媒介全球化、跨文化写作、世界文学以及在文学和其他媒介中出现的殖民主义与去殖民主义、移民、文化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等议题正成为研究的热点。
文学和电影中的记忆表征:“创伤历史”
文学和电影借助叙事结构、象征和隐喻等审美形式的编码,可以生动地描绘个体和集体的记忆,包括记忆的内容、机制以及记忆的多变与扭曲。这种“虚构”的记忆与心理学、宗教、历史以及社会学等象征体系中的记忆之间具有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它可能延续记忆与遗忘体系中固有的形象,也可能创造新的形象。
至少从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弗吉尼亚·沃尔夫的现代主义写作开始,文学与记忆的社会话语之间的关联变得明显起来。个体记忆自20世纪初就受到诸多关注(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记忆和亨利·柏格森的不自觉的回忆),在诸如沃尔夫的《达洛维夫人》(1925)的“记忆小说”中,个体记忆也以独特的文学形式如意识流话语体系和复杂的时间线被表征。
文学研究揭示了记忆如何被诗歌、戏剧和小说等文学形式表征。(2)例如:Aleida Assmann,Memory Spaces: Form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Cultural Memory, Beck, 1999; Ansgar Nünning,Marion Gymnich, Roy Sommer (eds), Literature and Memory: Theoretical Paradigms, Genres, Functions, Narr, 2006。——原注在文学记忆研究中,记忆的隐喻、个体意识的叙事表征、记忆空间与主观时间的文学生产是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作为“亲历者”的我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是有区别的,有意思的是,这个区分本身建立在记忆的有关概念基础之上,即叙事前的经历不同于叙事记忆,因为后者在回忆的过程中会创造意义。以第一人称作为叙事者的叙事总是以个体记忆的文学表征的形式存在。这种文学叙事通过一些叙事手段将叙事记忆包装幻化为一种貌似真实的自传式记忆,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就是一个例子,马丁·劳什内格(Martin Löschnigg)将这些叙事手段归入“记忆修辞学”[1]。
在暴力历史如战争、恐怖主义和大屠杀的问题上,文学表征记忆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被进一步考量。近期的一些研究经常采取比较的方式来审视一些创伤历史的文学记忆,比如世界大战、殖民和去殖民的经历、独裁统治、大屠杀以及全球恐怖主义等。“9·11事件”可以被看作是全球性的创伤事件,围绕这一创伤事件衍生出大量的英语文学作品(唐·德里罗、乔纳森·萨佛兰·福尔、莫什·哈米德、麦克·尤恩等作家的小说),这些写作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呈现这一事件对文化记忆的影响。通过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表征创伤历史时,显然大屠杀在其中占据核心位置。和对其他事件的记忆史研究一样,对于大屠杀的书写,我们可以区分出不同代际和不同视角——比如亲历者的见证型文学(普里莫·莱维)、亲历者后代的创作(阿特·斯皮格曼)和其他多种形式的想象虚构型作品(从安妮塔·德赛到安·迈克尔斯),并思考记忆是如何从亲历者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孙辈(跨代际的记忆)以及那些与创伤事件没有直接关联的人( “假肢记忆”,见下文)。
创伤的概念本身指涉“表征的危机”,这在美国学界尤其受到关注。这种观点是在后结构主义的思维框架下被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的《无主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3)参考: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原注。鲁斯·莱斯(Ruth Leys)的创伤研究,观点清晰独到,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即“后屠杀、后广岛、后越战时代语言表征的彻底失败”[2]。在后结构主义创伤话语中,“是大屠杀诱发了认识论、本体论上的见证危机,这种见证危机就体现在语言层面上”。这种将个体与文化、生理与语言层面对等的倾向可能极具误导性,在创伤研究中我们必须辩证地分析将文本人格化(例如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人物混为一谈)所带来的伦理后果。
媒介记忆的研究更适宜回答文学和电影等媒介如何表征创伤历史,以及从何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过去”本身已经是一种被媒介化的记忆。例如,玛莉塔·史特肯(Marita Sturken)就在《纠葛的记忆》中研究了越南战争和艾滋病如何通过电视、电影和其他大众媒介转变成文化记忆的一部分(4)参考:Marita Sturken,Tangled Memories: The Vietnam War, the AIDS Epidemic, and the Politics of Rememb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原注。史特肯是在社会语境中探讨记忆与媒介之间复杂的关联。她强调媒介扮演的是一个能动地建构记忆的角色:“文化记忆是通过物品、图像和其他表征形式建构出来的。它们是建构记忆之术,而非被动承载记忆之所。”[3]在谈到被媒介化的记忆所具有的经验性时,艾莉森·兰茨贝格(Alison Landsberg)引入了“假肢记忆”(5)参考:Alison Landsberg,Prosthetic Mem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Remembrance in the Age of Mass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原注(prosthetic memory)的概念。兰茨贝格重点研究了在大众文化时代,通过文学、电影和博物馆展览等形式表征的奴隶制和大屠杀的历史对于记忆的形成有什么影响。她认为,大众媒介之所以对记忆文化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们就“如同一个假肢”[4]20,借此我们得以感知他人的经历和记忆。对兰茨贝格而言,“假肢记忆”的概念背后蕴含深刻的伦理意义:“它能够激发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也能缔造跨越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政治同盟。”[4]21
文学的“命运”
研究文学故事和文学模式的“命运”,追问它们持续不断的影响力,其实就是研究记忆在文化中的“命运”:如何被不断传承、被人们“经验”。要还原一个文学文本的“社会命运”,我们需要回答在漫长的时间里它是如何被接收、被讨论、被使用、被正典化、被遗忘、被审查继而被重新利用。在不断更替的社会情境中,到底是什么让一些文学作品能够一次次被赋予新的生命,而另外的作品则被遗忘而后束之高阁?我们可以分别从社会、媒介和文本叙事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有将三个角度结合起来才最能阐释文学的“命运”问题。
1.从社会视角阐释文学的“命运”重在考察社会行动者如何积极地利用文学文本。社会形态不同,对待历史的态度就不同,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同,并且有其各自的关切和期望,话语和阅读实践也不同,文学在其中又如何被接受、被经验呢?同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时代被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代际又对此如何反应?莎士比亚、班扬亦或弥尔顿历经几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流传,这一过程足以供我们考察不同的受众如何将文学作品奉为经典或者将其去经典化,以及对这些作品的不同解读如何与社会变革相互关联。
2. 从媒介文化视角阐释文学的“命运”重在考察承载着那些文学故事的媒介网络:文本间的和媒介间的相互指涉、重写与改编、各种评介及交叉指涉。在其他的研究中我使用前媒介化(premediation)和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概念,分析了“1857年印度兵变”(发生在印度北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战争)的相关叙事模式和图像可以追溯至早期类似的历史事件的叙事和图像,是后者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借助新的媒介载体(从报纸文章到小说、摄影、电影以及网络)修正后的结果,其最终的命运是再次成为其他故事和事件叙事(比如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20世纪50年代后帝国时代的怀旧小说或当下对恐怖主义的讨论)的源头。(6)参考:Astrid Erll, Premediation-Remediatio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dian Uprising in Imperial and Postcolonial Culture Media (from 1857 to the present),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2007。——原注
3.以文本为中心阐释文学的“命运”重在考察文学作品的哪些特质让它们比其他作品更容易“存活”,能够不断被人们重读、改写,进而被媒介化、被讨论。比如安·里格尼(Ann Rigney)认为,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艾凡赫》之所以有漫长而丰富的“生命”,得益于作品情节的两个特点(表面上看起来自相矛盾):既看似聚焦又飘忽不定。在这一点上,比起司各特其他的小说,《艾凡赫》无疑最具代表性。一方面,小说始终坚持一种基本的叙事范式,即 “作为他者的历史事件”的叙事,而另一方面,它通过“打破故事的结局和固有的情感期待之间的张力”[5],使读者困惑不解进而牢牢抓住读者的心。
从历时的角度追溯文学的“命运”,就是研究其持续不断的影响力,即它是如何“存活”下来并且在读者的眼中一直“有用”、有意义。这样一个动态过程涉及复杂的社会、文本和媒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需要巧妙地综合多种路径进行研究,其中有些研究路径在文学研究中早已被采用,如细致的文本和媒介分析、对文本间性和媒介间性的研究、对文学历史功能以及文学艺术的社会史研究。
跨国记忆与跨文化记忆
记忆研究长期采用民族主义的研究路径。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就是最好的例证,里面收录的文章都是有关法国民族记忆之场的。不少批评家都指出诺拉的研究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记忆之场”实际上“遗忘”了欧洲内部的、法国殖民地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以及移民记忆所带来的影响。这种相互纠葛的历史实际上对英语国家的记忆也有明显影响:英国贸易及殖民主义、加拿大和美国的多元民族主义、20世纪复杂的移民形势等,这一切共同创造了大量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共享的记忆之场。(7)参考:Udo J.Hebel,Transnational American Memories, de Gruyter, 2009。 ——原注
关注殖民文化残存的后殖民研究可以给跨文化记忆研究带来一些有价值的启发。一些核心概念如“逆写”、作为“创伤事件”的中途航道或者“殖民怀旧”都明显包含一种记忆维度。新英语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经常表征或者建构跨文化的记忆:加勒比文学中对“黑色大西洋”(8)参考:Lars Eckstein,Re-membering the Black Atlantic: On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Literary Memory, Rodopi, 2006。 ——原注的回忆;黑人英语文学中的原型记忆(9)参考:Jan Rupp, Genre and Cultural Memory in Black British Literature.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2010。 ——原注;移民与流散书写中的“错位形象”(10)参考:Marie-Aude Baronian,Stephan Besser,and Yolande Jansen, eds.,Diaspora and Memory: Figures of Displacement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ts and Politics, Rodopi, 2007。——原注。在研究大屠杀记忆在去殖民化时代的意义时,迈克尔·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提出了“多向记忆”(11)参考:Michael Rothberg,Multidirectional Memory: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the Age of Decoloniz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原注的概念。不同的种族群体必然形成充满争议的记忆,在研究南非小说时,莎拉·纳托尔(Sarah Nuttall)就提出了“磋商”“纠葛”的概念来解释这种记忆在文学中的体现(12)参考:Sarah Nuttall, Entanglement: Literary and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Post-Apartheid,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09。 ——原注。
事实上,跨文化记忆历史悠久,当下流行的全球化、“全球化时代的记忆”(13)参考:Daniel levy,Natan Sznaider,The Holocaust and Memory in the Global Age, trans: Assenka Oksiloff,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原注这样的话语体系有时会遗忘这一点,但好在记忆研究所内含的决定性的历史维度总会及时地对此加以强调。自从古代,记忆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就已经跨越了时间、空间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并在各种本土化的语境中被赋予新的活力和意义。
因此,可以说“跨文化”记忆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要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研究记忆,亦或仅仅是取代上述前两种研究路径的新路径,而是当我们具体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在研究记忆的共时表征(如“创伤历史”的表征)和记忆的历时传承(文学的“命运”)时必然要选择的一种研究视角。我们在文学与媒介研究中力图还原有影响力的故事(如《奥德修斯》或者《天路历程》)、纪念仪式(如“两分钟默哀”)或者一些媒介记忆实践(如伪纪录片)在区域内、跨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路径,正是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的“旅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