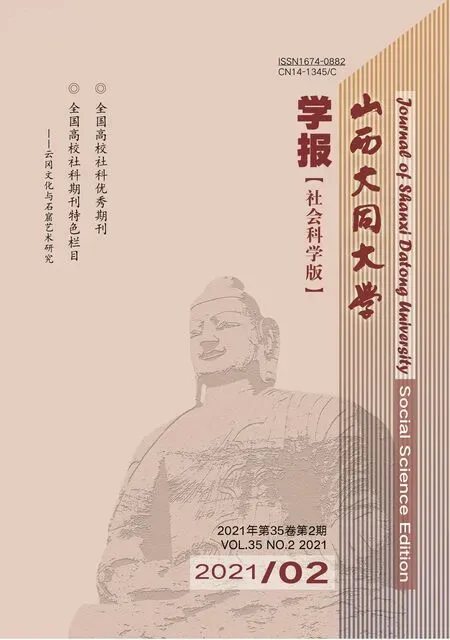北魏《鹿苑赋》创作背景及书写策略考论
潘 尧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一、写作时间和流传情况
《鹿苑赋》[1](P3651a-b)是高允现存唯一的一篇赋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北史》与《魏书》并未提及《鹿苑赋》,它的创作时间是一个谜团。张秀丽认为《鹿苑赋》写于孝文帝元宏即位之初,但是没有给出任何证据。[2](P34)
《鹿苑赋》中写到“暨我皇之继统,诞天纵之明叡”。其中“我皇”二字,是考证《鹿苑赋》创作时间的关键。文中所出现的“我皇”,当是作者属文时在位的君主。曹植在黄初三年写给魏文帝曹丕的《上责躬应诏诗表》,言“笃生我皇,亦世载聪”,[3](P37-38)“我皇”指曹丕。鲍照写于元嘉二十四年的《河清颂》中提及“云何其瑞,实钟我皇”,[4](P905)其中“我皇”指宋文帝刘义隆。王筠写于天监四年的《侍宴饯临川王北伐应诏》有言“我皇俊圣,千年踵武”,[5](P118)以及庾信写于大同二年的《将命至邺酬祖正员》文中有“我皇临九有,声教洎无堤”,[6](P197)“我皇”均指梁武帝萧衍。徐陵写于太清六年的《与王僧辩书》,其中有“我皇受命中兴,光宅天下”,[7](P533)“我皇”指梁元帝萧绎。类似用例很多,此处不赘述。
高允生于登国五年(390),逝于太和十一年(487),一生共仕五君,分别是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献文帝拓跋浚、文成帝拓跋弘和孝文帝元宏,这意味着“我皇”可能是五位君主中的任何一个。
《鹿苑赋》文中又写到“(按:我皇)于是命匠选工,刊兹西岭。注诚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仿佛,耀金晖之焕炳。即灵崖以构宇,竦百寻而直正。絚飞梁于浮柱,列荷华于绮井。图之以万形,缀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对,孰道场之涂迥。”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知,“我皇”下令在“西岭”修建佛像和庙宇,装饰华美,工艺精湛。这段文字背后涉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魏书·释老志》中有云:
(按:显祖)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8](P3300)
其中“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的“西山”即《鹿苑赋》中的“西岭”;“佛图”即“仰模神影”。由此可知,“我皇”就是北魏显祖文成帝拓跋弘。他在禅位高祖孝文帝元宏后,在西山修建佛像,那么《鹿苑赋》写作时间应不早于延兴元年(471)。
《鹿苑赋》中还写到“羡顶生之高蹈,思离尘以迈俗,涉玄门之幽奥。禅储宫以正位,受太上之尊号。既存无而御有,亦执静以镇躁”,这里透露出的两点信息可以进一步证明“我皇”指的就是显祖文成帝拓跋弘。第一,这段文字刻画了“我皇”向往隐居,远离尘俗,精研佛法的行为特征。《魏书·显祖纪第六》将拓跋弘描述为“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8](P158)“早怀厌世之心”[8](P159)。第二,这段文字提到北魏禅让的历史事件。北魏一代,只有显祖拓跋弘在皇兴五年(471)禅位太子元宏一事。而且拓跋弘传位元宏之后,上尊号为“太上皇帝”,而非“太上皇”。[8](P158-159)仅从《鹿苑赋》和《魏书》相关记载的字面意思来看,拓跋弘性爱佛法,无意国事,于是在皇兴五年传位年仅五岁的儿子元宏,自己做起了太上皇帝。五年之后,即承明元年(476 年),拓跋弘驾崩于永安殿,时年二十三岁,则《鹿苑赋》写作时间不晚于476年。
综上所述,《鹿苑赋》的写作时间大致在延兴元年至承明元年之间,即公元471 至476 年之间。这段时间正是文明太后冯氏与拓跋弘展开激烈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拓跋弘的禅位与暴死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鹿苑赋》是北魏初期渤海高氏允现存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唯一一篇赋作。北魏时期包括高允在内的赋作大多亡佚,《鹿苑赋》却得以流传至今,完全有赖于初唐时期编纂的《广弘明集》的收录。这说明《鹿苑赋》与早期北魏佛教流行以及佛教与当时文学创作的关系密切。《鹿苑赋》以三种版本流传至今,分别保存在《高允集》和《广弘明集》,以及在清代作为单篇作品被收录在总集中。
最初可能是以《高允集》的形式流传。《隋书·经籍志》载“后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10](P1079)《旧唐书·经籍志》载“后魏高允集二十卷”,[11](P2071)《新唐书·艺文志》载“高允集二十卷”,[12](P1595)南宋初年郑樵编纂的《艺文略》载“司空高允集二十卷”,[13](P1761)由于郑樵秉承“编次必记亡书”[13](P1806)的原则,因此无法据此判断当时《高允集》是否还存于世。在稍后的南宋官修书目《崇文总目》和私人目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中,《高允集》均不见记载。由此,大致可以推断,《高允集》在北宋后期亡佚。清人李正奋《补魏书艺文志》载“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9](P333)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载“高允集”,[9](P556)未列卷数,不够很精审。
直到晚明,才开始出现《高允集》的辑本,主要有三个版本系统:一是张燮《七十二家集》本,这套丛书比较常见的是《续修四库全书》本。二是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常见的是《四库全书》本和扫叶山房本,《丛书集成》三编中的《高令公集》就是以扫叶山房本为底本排印出版。三是王灏的《畿辅丛书》本,比较常见的刊本是王氏谦德堂本,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即以此版本作为底本。2014 年有两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对《高允集》作了基础的校勘工作,一位是河北师范大学的辛娇,一位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张秀丽。不过后者的校注工作似乎令人心生怀疑,张氏在校勘《鹿苑赋》时声明使用了“四库”本中的《广弘明集》。实际上“四库本”中的《广弘明集》以吴惟明本为底本,只有28卷,缺“统归篇”部分,而《鹿苑赋》恰好收录在“统归篇”中。这意味着“四库本”中的《广弘明集》是个残本,并没有收录《鹿苑赋》。
刘林魁系统地梳理过《广弘明集》的版本系统。他认为《广弘明集》主要有两个流传系统,一个是单刻本,一个是刻本藏本。单刻本有两个源头:一是明代汪道昆本,共三十四卷,《四部丛刊》初编即以汪本为底本。二是吴惟明本,共二十八卷,缺“统归篇”,是个残本,《四库全书》中的《广弘明集》即来源于此本。《鹿苑赋》正好在“统归篇”中,因此吴惟明本没有收入《鹿苑赋》。藏本也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永乐北藏、龙藏为代表,共三十卷。此版本和天宁寺四十卷本关系密切,属于同一源流。今天常见的《四部备要》本《广弘明集》的底本就是天宁寺本。另一个是来自开宝藏、赵城金藏的三十卷本,代表是今天大正藏本中的《广弘明集》。[14](P51-62)总体而言,大正藏本《广弘明集》最为可靠。
单行的《鹿苑赋》主要出现在清人编纂的两个总集中:一是陈元龙的《历代赋汇》,现在常见版本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的《历代赋汇》,以康熙四十五年本为底本;一个是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鹿苑赋》采自汪道昆本《广弘明集》。
以上便是高允《鹿苑赋》简要的版本和流传谱系,可简略归纳为《高允集》系统、《广弘明集》系统和单篇系统。
二、“二乾重阴,明离并照”:献文帝与冯氏的权力斗争
自平和六年(465)五月登基到承明元年(476)二月晏驾,献文帝拓跋弘与冯太后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博弈中有四个重大事件:第一件是天安元年(466)二月,乙浑集团被诛杀,权柄落入冯氏手中,献文帝拓跋弘处于被动状态。第二件是皇兴元年(467)九月,献文帝拓跋弘亲政,冯氏交出大权,却将献文帝刚出生的嫡长子牢牢控制在手中。冯氏暂时退入幕后。第三件是皇兴三年(469)六月,一直由冯氏抚养的孝文帝元宏被册封为太子。第四件是延兴元年(471)年八月,献文帝拓跋弘禅位给孝文帝元宏,做了太上皇帝。从献文帝禅位到驾崩的5年间,是拓跋弘与冯氏权力斗争日趋恶化的时间段,最终以拓跋弘暴崩、冯氏临朝称制收场。这五年正是高允写作《鹿苑赋》的时段。他在赋的结尾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资圣王之远图,岂循常以明教。希缙云之上升,羡顶生之高蹈。思离尘以迈俗,涉玄门之幽奥。禅储宫以正位,受太上之尊号。既存无而御有,亦执静以镇躁。睹天规于今日,寻先哲之遗诰。悟二乾之重荫,审明离之并照。下宁济于兆民,上克光于七庙。一万国以从风,总群生而为导。正南面以无为,永措心于冲妙。[1](P3651a-b)
其中“悟二乾之重荫,审明离之并照”两句隐晦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因此,勾勒出这段时期内献文帝拓跋弘与冯氏的斗争局面,有助于阐明《鹿苑赋》的创作动机,分析高允的劝谏艺术。
乙浑伏诛,冯氏还政献文帝后,北魏朝廷逐渐形成了献文帝集团和冯氏集团两个权力中心。皇兴四年(470)十月,李敷、李弈兄弟及其连带亲属被诛,轰动北州,拉开了北魏宫闱政治斗争的序幕。李氏家族乃北地汉族高门著姓,家族成员遍布朝中要职,权势显赫,但是李敷、李弈兄弟二人在当时两派斗争中所处位置颇显尴尬:
初,魏南部尚书李敷,仪曹尚书李欣,少相亲善,与中书侍郞卢度世皆以才能为世祖、显祖所宠任,参豫机密,出纳诏命。[15](P4154)
敷既见待二世,兄弟亲戚在朝者十有余人。弟弈又有宠于文明太后。[8](P924)
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8](P384)
李敷担任南部尚书,掌管献文帝诏令的撰写与发布,同时又是献文帝的核心决策层成员,能够接触到献文帝集团的机密信息。献文帝集团头号政治对手是冯氏集团,而此时李敷胞弟李弈却是冯氏的情人。这层关系难免会让献文帝担忧自己的谋划泄露到冯氏集团中,冯氏恐怕亦存在同样的担心。
借机铲除李敷兄弟及其盘踞朝廷要职的亲属,不仅可以平息隐患,还可打击冯氏集团。李敷至交李诉为献文帝提供了这个机会。李诉时任相州刺史,为官贪鄙,广收贿赂,被军民告到中央。献文帝授意迅速拿下李诉,判处死罪;同时又派人暗示李诉赎罪的方案:
时敷兄弟将见疏斥,有司讽诉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诉吿列敷等隐罪,可得自全。[8](P1147)
李诉在女婿裴攸的建议下,向献文帝揭发李敷、李弈兄弟的罪状。范檦趁机向献文帝举报李氏兄弟,列二人三十余条罪状。献文帝下诏族灭李家,褫夺封号,李敷从弟及妹夫均伏法。
李氏兄弟被诛,主要是二人深陷当时献文帝集团和冯氏集团的政治冲突中,成为宫闱之争下的牺牲品。献文帝与冯氏冲突之激烈,可见一斑。范檦属于见风使舵、毫无操守的小人之流:
范檦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辞,未闻德义之言,但有势利之说。听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贼,所谓谄谀、谗慝、贪冒、奸佞,不早绝之,后悔无及。[8](P1147-1148)
这等人从古至今不绝于书,他们对局势变化发展洞若观火,以期随大势之变化从中为己捞取最大利益。范檦对李敷兄弟的落井下石行为,一定程度上表明献文帝集团占据上风。承明元年(476)六月献文帝遇害之后,范檦果谮李诉于冯氏,致使李诉被诛。
翌年八月丙午,刚亲征敕勒回京的献文帝却突然逊位于年仅五岁的孝文帝元宏。《魏书·天文志》将逊位的原因归结于斗争中冯氏的施压:
是岁十一月,太白又犯之,是为内宫有忧逼之象。占曰“天子失其宫”。……明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8](P2633)
《魏书·高允传》中委婉地提及:
又显祖时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诸大臣以次召问。[8](P1196)
然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献文帝是出于对佛法的崇信与热爱,不愿让繁杂的政治事务干扰到自己的信仰与修行:
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8](P158)
陛下必欲割捐尘务,颐神清旷者,冢副之寄,宜绍宝历,若欲舍储,轻移宸极,恐非先圣之意,骇动人情。[8](P531)
陛下富于春秋,始览机政,普天景仰,率土傒心,欲隆独善,不以万物为意,其若宗庙何!其若亿兆何
若圣性渊远,欲颐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8](P2187)
这种说法在大约6个世纪后被司马光采纳:
魏显祖聪睿夙成,刚毅有断;而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15](P4164)
献文帝出于宗教热情而逊位的说辞可能是史家出于“为尊者讳”的书写策略。献文帝崇信佛教固然不假,但是他也是一位充满抱负、想有所作为的君主,断不可能因此而拱手放弃大位,更何况处在与冯氏竞争的时局下:
夏,四月,诸部敕勒皆叛。魏主使汝阴王天赐将兵讨之,以给事中罗云为前锋。敕勒诈降,袭云,杀之,天赐仅以身免。……丁未,魏主如河西。……丙寅,魏主至阴山。……八月,丁亥,魏主还平城。[15](P4164)
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于北郊,诏诸将讨之。虏遁走。其别帅阿大干率千余落来降。东部敕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之,至石碛,不及而还。[8](P162-163)
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于怀州。所过问民疾苦,赐高年、孝悌力田布帛。[8](P166)
献文帝在逊位前后有不少亲征柔然和南巡江淮的军事行动。而且献文帝十分重视赏罚的作用,因此而忙于政务:
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帝勤于治功,百僚内外,莫不震肃。及传位高祖,犹躬览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显祖末年,尤重刑罚,言及常用恻怆。每于狱案,必令覆鞫,诸有囚系,或积年不断。群臣颇以为言。[8](P3131)
在不得不逊位已成定局的情形下,献文帝一直试图避免最坏结果的出现,也即将大位传于被冯氏牢牢掌控的皇太子孝文帝手中。然而事与愿违,献文帝提出让位于皇叔拓跋子推的建议遭到拓跋云、源贺、陆馥、赵黑、高允等王公大臣一致反对,最终不得不传位于元宏:
显祖将传位京兆王子推,访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贺等词义正直,不肯奉诏。显祖怒,变色,复以问黑。[8](P169)
由此可见,逊位之事实属被迫,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斗争,折射出献文帝与冯氏之间激烈的政治冲突。
延兴六年(476)六月辛未,年仅23岁的献文帝突然晏驾,孝文帝登基,冯氏再次临朝称制。献文帝的死因,疑云密布。驾崩前夕,平城内外宣布戒严,拱卫京城的卫戍部队出现大规模调动:
六月甲子,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年。大司马、大将军、安城王万安国坐矫诏杀神部长奚买奴于苑中,赐死。[8](P892)
献文帝驾崩后,紧接着就是掌握军权的万安国被赐死。万安国与献文帝关系密切,而且与献文帝同龄:
安国少明敏,有姿貌。以国甥,复尚河南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显祖特亲宠之,与同卧起,为立第宅,赏赐至巨万。超拜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8](P892)
可以推测献文帝试图联合万安国等人,依靠手中握有的兵权发动政变,铲除冯氏。不料谋划泄露,冯氏提前行动,文献帝等人遭遇不测。
公元471 至476 年间,献文帝与冯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角逐。政争最终逐渐滑向失控的零和局面,献文帝试图凭借手中掌握的军队先发制人,不料却遭到冯氏的反杀。这就是高允写作《鹿苑赋》的历史语境。
三、无为与冲妙:高允的劝谏策略
在471 至476 年间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中,高允在双方之间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直接关系到《鹿苑赋》的创作动机。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大臣,高允为什么选择赋这种文体向献文帝表达自己的看法?高允在《鹿苑赋》的写作中又是如何向献文帝传达自己的看法?
高允当时已是杖朝之年,但是在献文帝与冯氏斗争中却能如履平地,受到双方的信任与倚重,实属难得:
高宗崩,显祖居谅闇,乙浑专擅朝命,谋危社稷。文明太后诛之,引允禁中,参决大政。[8](P1187)
皇兴中,诏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庙,谓允曰:“此简德而行,勿有辞也。”后允从献文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帝览而善之。又帝时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诸大臣,以次召问。允进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劳神听。愿陛下上思宗庙托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于是传位于孝文,赐允帛百匹,以标忠亮。[8](P1195-1196)
自文成迄于献文,军国书檄,多允作也。[8](P1196)
太和二年,又以老乞还乡,章十余上,卒不听许,遂以疾告归。其年,诏以安车征允,敕州郡发遣。至都,复拜镇军大将军,领中秘书事。固辞,不许。扶引就内,改定皇诰。……诏允乘车上殿,朝贺不拜。明年,诏允议定律令。虽年渐期颐,而志识无损,犹心存旧职,披考史书。又诏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贫养薄,可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赐珍味,每春秋致之。寻诏朝晡给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绵绢,每月送给。[8](P1196)
冯氏初次摄政,即将高允引入权力核心层,参与大政方针的裁决;再次摄政后依然重用高允,并给予丰厚的物质赏赐。献文帝在位期间的军国诏书多由高允撰写,而且北征时令高允随行,禅位之事专门咨询高允的意见。可以说,高允与冯氏、献文帝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或许还起着中间人的作用。高允之所以能够在政治斗争中不选立场,还能得到双方的尊敬,除了他德高望重的政治影响外,恐怕还与他的人格有关: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无也。而前史载卓公宽中,文饶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矣,未尝见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为“文子”。崔公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谴,起于纤微,及于诏责,崔公声嘶股战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都无人色。高子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明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称善。仁及僚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谓矫矫者,更在斯乎?宗爱之任势也,威振四海。尝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毕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谓风节者,得不谓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内,崔亦漏之于形外。钟期止听于伯牙,夷吾见明于鲍叔,良有以也。[8](P1187)
高允在长期的为官生涯中培养出了“喜怒不形于色”的素养,为人谦虚而又充满韧性,使得共事过的朋友游雅对他称赞不绝,而且获得掌权者的敬仰。
对于献文帝和冯氏之间政治斗争的最终结果,高允或许看得很清楚,毕竟他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8](P1179)
高允听说崔浩与恭宗关于人事安排的纷争,推断出崔浩将来因此性格取祸官场。后来“国史案”爆发,高允受到牵连,多亏太子拓跋晃力保才得以幸免于屠戮。
高允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或许早已预料到持续相争下去,将以献文帝的失败收场。然而作为深受献文帝信赖的臣子,高允不能坐视事态恶化,必须劝谏献文帝趁着禅位这个名义,主动退出政治斗争以求保全;但是如何将这个意见传达出去,既要让献文帝能够明白,同时又能避免自身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惹来灭门之祸的风险呢?选择恰当的创作文体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文体,只有“赋”能够胜任。相较于正式的公文体“表”、“奏”等,“赋”能够将看法包裹在华丽的辞藻中,做到言者有意,听者无心。例如北魏东阿公元顺得知城阳王元徽和徐纥向灵太后进谗言,试图陷害自己后,写下《蝇赋》自表心迹。元顺既没有撕破局面,又传达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特性使得“赋”能游走在一些模糊地带。
学识渊博的高允深谙官场和文体之道,那么在选择用“赋”向献文帝传达自己的看法后,他又是如何具体书写《鹿苑赋》的呢?某种程度上来说,文体的书写策略和所展现出来的内容比文体本身更有意义。
通读《鹿苑赋》,可以明显看出,高允铺彩摛藻,将献文帝描绘成一位热心佛教事业,参与佛法探究,有着极高佛学造诣的太上皇帝。高允在《鹿苑赋》中的书写可以分解成以下几个步骤:
1.虔诚的供养人
暨我皇之继统,诞天纵之明叡。追鹿野之在昔,兴三转之高义。振幽宗于已永,旷千载而有寄。于是命匠选工,刊兹西岭。注诚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仿佛,耀金晖之焕炳。即灵崖以构宇,竦百寻而直上。絚飞梁于浮柱,列荷华于绮井。图之以万形,缀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对,孰道场之涂迥。嗟神功之所建,超终古而秀出。实灵祇之协赞。[1](P3651a-b)
这段话讲述了献文帝登基之后对佛教事业的贡献:开凿佛像和修建庙宇。这件事情在《魏书·释老志》的记载是:
其岁,高祖诞载。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
巧密,为京华壮观。[8](P3300)
志盘在《佛祖统纪·法运通塞志》中记录这件事时透露出献文帝塑佛像、修庙宇的动机:
皇兴元年,敕于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像五躯,各长丈六,用赤金二十五万斤。[16](P878)
献文帝为了纪念孝文帝的诞生和为先祖祈福,下令修建佛像,耗资巨费,工艺精美。《鹿苑赋》中用华丽的文辞对此反复渲染,刻画得栩栩如生。似乎有意凸显献文帝作为一名供养人的慷慨。从《释老志》和《法运通塞志》的描述来看,献文帝这次塑像和修庙活动花费巨大,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一个佛教得到普遍信奉的时期和地域。
2.热忱的修行者
故存贞而保吉,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述。澄清气于高轩,伫流芳于王室。茂花树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龙宫以降雨,侔膏液于星毕。[1](P3651a-b)
这段话讲述了献文帝的禅居生活,以及修禅为皇室和国家带来的福报。献文帝的禅居生活始于禅位之后。成为太上皇帝后,献文帝离开太华殿,移居崇光宫:
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8](P3300)
己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斲,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8](P159)
第一条材料来自《魏书·释老志》,似乎献文帝禅位后,将精力全部放在修禅上。第二条材料来自《魏书·显祖本纪》,很突兀地补充说,国家的重大事情都得让他知晓。高允的描述当然不愿意,也不会提及献文帝此时还在参与政治事务,因为这和高允将献文帝描述成修行者的定位相悖。在献文帝从皇宫徙御北苑崇光宫不久前,发生了一件颇有深意的事件:
魏主使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莫寒大纳货赂,众怒,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夏,四月,诸部敕勒皆叛。魏主使汝阴王天赐将兵讨之,以给事中罗云为前锋;敕勒诈降,袭云,杀之,天赐仅以身免。……(按:六月)丁未,魏主如河西。……丙寅,魏主至阴山。……八月,丁亥,魏主还平城。[15](P4164)
献文帝任命胡莫寒从敕勒部中挑选一些人担任殿中武士,结果胡莫寒大收贿赂导致敕勒叛反。在一系列镇压无效后,献文帝亲自带兵平叛,六月出发,八月丁亥才回平城。刚回来不久,献文帝于同月己酉禅位孝文帝,移居北苑崇光宫。接下来就如以上材料所述,献文帝专心修禅和研读佛典。献文帝之所以要更换殿中武士,恐怕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对此前的殿中武士产生怀疑。然而更换卫士出了差错,献文帝外出征讨。回京之后,借禅让之事迅速搬离皇宫,可能是应对殿中武士更换失败的策略。当然这只是猜测,但是从禅位的突发性来看,在献文帝离开的两个月内,平城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平叛回来的献文帝仓促之中不得不接受施行禅让的提议。即使如此,在高允的描述下,献文帝禅位之后专心修禅,为皇室和国家祈福。这种处理方式似乎有意淡化政治冲突,暗示献文帝接受修禅的生活方式,做一名热忱的修行者。
3.法界声名显赫
若乃研道之伦,行业贞简,慕德怀风,杖策来践。守应真之重禁,味三藏之渊典。或步林以经行,或寂坐而端宴。会众善以并臻,排五难而俱遣。道欲隐而弥彰,名欲毁而逾显。[1](P3651a-b)
这段话说明献文帝和僧侣联系密切,而且在佛教界具有不小的感召力,以至于很多探究佛法的僧人主动前来拜见献文帝,甚至和他一同修行,共同探讨佛理。这种情况导致献文帝在佛教界名望日益隆盛,尽管和他想要远离世俗、专心修行的意愿相违背。《魏书·释老志》对献文帝和佛教界僧侣的关系却是另一番描述:
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8](P3299)
献文帝自身喜好佛理和老庄,即位之后运用行政力量邀请沙门和谈玄之士,与他们相互探讨。换句话说,是献文帝邀请僧侣和谈玄之士前来,而不是高允所呈现的情况,即僧侣和谈玄之士受到献文帝德行和学问的感召,主动前来拜谒。这点在《法苑珠林》的记载中也可以窥见:
魏显祖献文帝造招隐寺,召坐禅僧。[17](P2892)
可见,高允的叙述可能是有意为之,暗示献文帝在佛教界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号召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献文帝这种威望和号召力仅仅限于佛教界。
4.志在山野,心怀慈悲
伊皇舆之所幸,每垂心于华囿。乐在兹之闲敞,作离宫以营筑。因爽垲以崇居,抗平原之高陆。恬仁智之所怀,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游思,绝鹰犬之驰逐。眷耆年以广德,纵生生以延福。[1](P3651a-b)
这句话的关注点是献文帝的性格,即热爱山野之乐,心怀慈悲之念。这两点非常契合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修行品德。高允此处提及的“绝鹰犬之驰逐”,可能与《魏书·释老志》中的一段记载指的是同一件事情:
三年十二月,显祖因田鹰获鸳鸯一,其偶悲鸣,上下不去。帝乃惕然,问左右曰:“此飞鸣者,为雌为雄?”左右对曰:“臣以为雌。”帝曰:“何以知?”对曰:“阳性刚,阴性柔,以刚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叹曰:“虽人鸟事别,至于资识性情,竟何异哉!”于是下诏,禁断鸷鸟,不得畜焉。[8](P3301)
献文帝打猎捕获一只鸳鸯,被另一只鸳鸯的悲鸣声所感,于是下诏禁止捕鸟或者养鸟。单纯从这件事看,献文帝确实充满慈爱之心。实际北朝诸多奉法帝王都下过类似诏书,例如北齐文宣帝高洋。高允的表述将献文帝的这个诏书与佛教信仰关联起来,认为献文帝的慈悲之心在为黎元谋取福德。
5.谦卑虔诚,严格持戒
惠爱内隆,金声外发。功济普天,善不自伐。尚咨贤以问道,询刍荛以补阙。尽敬恭于灵寺,遵晦望而致谒。奉清戒以毕日,兼六时而宵月。何精诚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1](P3651a-b)
这段话凸显了献文帝作为一名宗教信仰者的核心品格之一,即谦卑。献文帝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不以此自伐功业,依然以谦卑的心态问道贤者,敬拜寺庙,而且在清戒的遵守上非常严格,由此可见献文帝内心的虔诚。关键是,高允在此处并没有明确指出献文帝是在世俗还是法界内取得的功业。从高允竭力塑造献文帝的宗教者形象角度来看,若是指法界的功业,那么高允可能会明确指出。因此,这里可能是指世俗的功业,比如行政、军事等方面。
6.为佛法舍皇位
咨圣王之远图,岂循常以明教。希缙云之上升,羡顶生之高蹈。思离尘以迈俗,涉玄门之幽奥。禅储宫以正位,受大上之尊号。既存亡而御有,亦执静以镇躁。[1](P3651a-b)
这句话核心意图是将献文帝禅位的动机宗教化,进而合理化。根据高允的表述,献文帝试图修道成仙成佛,皇位成了他修行过程中的一大障碍,于是主动禅让给孝文帝,接受“太上皇帝”的尊号。这种描述,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中的记载:
今我所以欲离世者,以自所见,恩爱如梦,室家欢娱,皆当别离。贪欲为狱,难得免出。故曰:“以欲网自蔽,以爱盖自覆,自缚于狱,如鱼入笥口,为老死所伺,如犊求母乳。吾恒以是,常自觉悟,愿求自然,欲除众苦。诸未度者,吾欲度之;诸未解者,吾欲解之;诸不安者,吾欲安之;未见道者,欲令得道。故欲入山求我所愿,得道当还,不忘此誓。”[18](P475c)
佛前世是太子时,为了修行得道,不愿继承皇位,于是深夜逃出皇宫。高允似乎有意将献文帝与佛太子进行比照,将禅位事件圣化。这既是一种称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束缚,即献文帝禅位之后的举动不得不依照佛太子出逃皇宫之后的行为来演进。
7.夸赞禅位举动,建议永心奉法
睹天规于今日,寻先哲之遗诰。悟二乾之重荫,审明离之并照。下宁济于兆民,上克光于七庙。一万国以从风,总群生而为导。正南面以无为,永措心于冲妙。[1](P3651a-b)
高允这段文字描绘了太上皇帝与皇帝(名义上是孝文帝,实际是上冯氏)并存带来的繁荣场景,从内政延伸到外交。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高允认为“二乾”并存的现状有利于国计民生,应该保持。其中暗含建议献文帝不要试图破坏现状。这种建议在全文中最露骨的表述就是“永措心于冲妙”,这是全赋的核心所在。按照高允的意思,献文帝不要再过问政事,主动退出与冯氏的竞争,将精力与心思全部投入到修行之中。
高允通过《鹿苑赋》指出献文帝适合、擅长和应当从事的领域,即一心奉佛,而不是与冯氏的政治竞争。这点主要通过以下几种书写策略传递出来:第一,深入挖掘献文帝作为一名佛教徒的所具备的品格。第二,弘扬献文帝在法界内的功业,忽视作为君主的政绩。第三,从佛经中寻找禅位的依据,并藉此提供一套禅位后的行事规范。第四,肯定禅位后的局面,并直接提出“永措心于冲妙”的建议。可以说,这种书写策略让高允避免了置身党争的风险,同时又实现了告诫献文帝的目标。从中也可以看出,赋虽然作为一种偏向艺术性的文体,有时也能作为一种准公文体发挥作用,有效弥补公文体在政治斗争中发表意见的某些缺陷,躲避政治风险。
四、余论
上文对《鹿苑赋》的创作时间、创作背景进行了初步的考证,阐释了创作中的书写策略,提出了一个观察北魏初年文学与政治之间互动的视角。但是围绕《鹿苑赋》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例如为什么高允会选择创作一篇极富宗教色彩的赋来进行劝诫?在赋中高允运用了哪些佛教知识?这些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北魏初年佛教知识在文人群体中的流传情况,以及对文学创作的渗透和带来的新变,进而从另一个侧面理解北魏文学的成立过程。这又是北魏文明化,或者说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