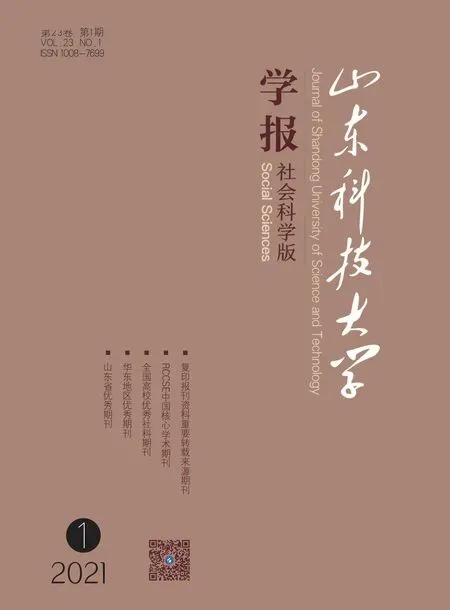土地经营权流转及其登记对抗规则
李宗录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山东 青岛 266590)
土地经营权因应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改革而生,民法典最终采取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结构。该结构中存在两层架构: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上,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置出土地经营权。由于土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导致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存在争议,而民法典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后仍然对土地经营权的性质采取搁置争议的态度。(1)在民法典颁布前后,学界对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性质存在“权利属性不明确说”“债权说”“物权与债权二元定性说”等争议。
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五年以下的为债权,流转期限五年以上的则为用益物权。将流转期限五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认定为用益物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法典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了流转期限为五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可以申请登记,不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2)5年以上期限的经过登记可以为物权,5年以下的因期限较短不予登记,不宜被定位在物权,仅作债权。 在2020年1月16日上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组织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研讨会上,有关领导介绍了这种立法计划和立法目的,一些学者也有如此主张。转引自崔建远:《物权编对四种他物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三百四十一条的表达完全符合民法典中特殊动产所有权、动产抵押权等物权登记对抗规则的表达模式,因而会将土地经营权纳入物权的行列而等同视之。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登记与否并非认定权利性质的依据,例如预告登记虽属登记但登记的权利仍属于债权。(3)有的学者还列举了有些权利虽未作登记却为物权的例子,例如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未经登记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自法律文书或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即转移到另一主体的物权等。该质疑虽不无道理,却不能直接否定登记对抗规则下的权利性质认定,因而针对性不足。若对民法典中有关登记对抗规则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物权编中特殊动产所有权、动产抵押权等物权登记对抗规则,合同编中第九章第六百四十一条关于所有权保留的登记对抗规则、第十五章第七百四十五条关于租赁物所有权的登记对抗规则,均是对物权登记对抗效力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登记对抗规则是关于物权效力的表达。值得探讨的是,民法典第十六章第七百六十八条关于多个保理合同优先取得应收帐款顺序的规定。该规定并没有采用“不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表达方式,但第七百六十八条的确是依登记来确定数个保理合同优先取得应收帐款的顺序,而依据保理合同登记的应收帐款不属于物权而是债权。严格来说,第七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因其不符合登记对抗规则的表达方式,因而不能归入登记对抗规则。所以,从登记对抗规则立法的归纳角度考察,还是难以否定土地经营权为物权的观点。
民法典中土地经营权的规则均从其流转的角度予以设置,如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四十二条。可见,确立土地经营权的根本功能在于增强农村土地的流转能力,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及其产生的系统效益。因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性质也应从流转的角度予以界定。(4)这里应区分的是,土地经营权本体(原始取得)的性质与土地经营权流转(依据流转合同的继受取得)性质界定存在不同视角。
民法典第三百四十一条的诡异之处在于,土地经营权的设立是在流转合同生效之时,这意味着土地经营权本体没有特定的设立方式,而是需要依据其流转合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而设立,由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始取得的必经初始环节,且该合同不属于合同编中的合同种类,因而依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独特性设立用益物权尚无不可。但是,流转合同因流转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多种性质不同的合同,这些合同往往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合同种类重合而没有独特性,这就很难将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与流转合同的性质分离开来。由此可见,依据流转合同设立土地经营权的设立方式,并不是原始取得的权利变动方式,而是权利继受取得的方式。
以出租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承租人享有的是债权性农地利用权。在土地经营权出租时,租赁合同生效即取得土地经营权的使用权,该权利是否登记,对承租权设立没有法律意义;那么,登记是否产生对抗效力呢?一般而言,承租权属于债权,根据租赁合同的相关规定,这一债权仍然不能通过登记获得对抗其他承租权的效力,既不能使后订立的租赁合同失效,也不能使其获得优先的顺位。在此情形下,只能通过合同履行的规则,来确定是否能够实现合同目的,已经得以履行的,则可以实现合同目的,而未能得到履行的,则可以违约责任或者解除合同予以救济。而且,在出租情形下,第三人是否为善意并不重要,在数个出租之间并不能产生对抗效力。
以入股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需订立土地经营权投资入股合同,该合同若没有附条件,一般自成立时生效,此时无需登记,即由合同受让一方当事人的企业或经济合作组织取得土地经营权;但按照我国公司法等股权设立规则,此时土地经营权并不能即时转换为股权。依据第三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投资入股合同生效后,土地经营权即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丧失土地经营权,在流转期间,其再与他人订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可能构成无权处分,(5)还存在另一种解释,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与他人再次签订的入股合同也发生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效果,前后两个土地经营权流转需要依据登记对抗规则由取得登记的人最终取得;此种情形排除了无权处分的适用。原则上土地经营权不发生变动,但存在善意取得的可能(将土地经营权认定为用益物权时)。在此情形下,依据登记对抗规则,登记不是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必要条件,因而土地经营权的善意取得似乎不需要登记,因而以入股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依登记能否对抗善意取得人存在疑问,这需要对登记的推定效力作出扩大解释,即登记后的其他受让第三人皆为非善意第三人。
《土地承包法》在2018年修订时,由于土地经营权属于债权还是用益物权存在争论,因而以土地经营权担保融资应采“抵押”还是“质押”就存在不确定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七条对此采用“融资担保”的表达方式予以处理。对于土地经营权能否采取抵押流转方式,民法典第三百四十二条对此明确使用了“抵押”这一术语予以表达。但是,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九条和第三百四十二条对于能否采取抵押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分别不同情形作出了不同规定。第三百三十九条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主决定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没有明确列举抵押方式;而第三百四十二条对于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土地的,(6)主要针对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四荒”土地。对抵押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对照这两个条文表达上的差异,似乎意味着第三百三十九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主流转土地经营权的,不可以采取抵押流转方式。根据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抵押,但是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土地经营权应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范围,因而属于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项中不得抵押的一般财产范围,但是否属于“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例外情形呢?由于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五条所列举的可以抵押的财产范围没有包含土地经营权,而且《土地承包法》和民法典其他条文(第三百四十二条的情形除外)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可以认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主流转土地经营权情形下,不得采取抵押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7)有些学者认为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九条中的“其他方式”包含了抵押流转方式,这种观点采取了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融资担保的实践态度,但是从严格法律解释的角度是不成立的。那么,只有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取得承包地而流转土地经营权时,可以采取抵押流转方式。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依民法典设立的土地经营权抵押权属于不动产抵押还是权利抵押。由于“权利”作为抵押权客体不符合民法基本原理,而且,以土地权利抵押的,民法典将其纳入了不动产抵押。例如,以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抵押的,仍属于不动产抵押,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然而,根据民法典第三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抵押合同是设立土地经营权抵押权的依据,登记不产生抵押权变动的效力,这就与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生效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相符。若抛开立法论上的瑕疵,单纯从解释论上来看,依据“流转合同生效+登记对抗规则”,土地经营权抵押不能消除多重抵押的可能,在多重抵押的情形下,需要确定土地经营权抵押权的顺位,对此应以登记的先后来确定。在此情形下,则存在融资担保的风险,无疑会增加抵押权人(金融机构)的融资风险,经营权人可能会向不同的金融机构融资,因而金融机构应当要求登记以化解风险。
仅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或者仅从登记对抗规则的静态视角考察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皆不合理。第三百四十一条实际上是从流转的动态角度来确定土地经营权继受取得方式和效力,因而土地经营权本身的性质仍不能确认;能够予以确认的,只能是土地的承租权、取得的股权以及抵押权等性质,至于土地经营权自身的性质则须回归原始取得的状态来判断。在现行三权分置的民法结构中,土地经营权的原始取得状态应包含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之中,在此状态下,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没有被直接表达为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结合,因此,从物权法定的角度土地经营权并不是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而是包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中,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之一。(8)崔建远教授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母权何以能够催生出土地经营权这一子权(他物权)”这一疑问,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结论认为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九、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新创了一种权利产生的机制,即出租、入股、抵押等流转方式“催生”出土地经营权。参见崔建远:《物权编对四种他物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原因在于,依据现行“三权分置”的民法架构,在原始取得环节,若土地经营权并非一种独立存在的他物权,那么在继受取得的流转环节不可能使土地经营权(实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转变为一项独立的他物权。因而,当以出租、入股、抵押方式流转时,名义上是一种衍生出来的权利,实质上却表现为依据流转合同取得对土地的直接利用或者价值担保的权能,这与民法典第三百四十条关于土地经营权内容的阐释相吻合。
农地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兼顾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要保障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的权益不受损害,另一方面要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三权分置曾有两种架构之争,一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另一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民法典编纂注重了法律概念立法上的延续性,因而最终选择了前者,而对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则采取不予明确界定的方式处理,因为民法典确立了土地经营权这一概念,就为社会实践和土地政策提供了广阔的实验空间。从立法意图和当前不断推进的土地改革政策来看,土地经营权更倾向于作为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更符合当前集体土地股份化产权改革以及产业化经营融资担保的需求。(9)这也是笔者不赞同将土地经营权界定为债权的原因之一。另外,土地经营权本身包含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结构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将分离出的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会违反性质的一致性;而且,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不能从流转方式中考察,尤其在《民法典》明确了抵押这一流转方式的情形下,将其界定为债权则须采取权利质押方式,而权利质押基本是以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个别为权利凭证交付时设立),这就与土地经营权流转采用登记对抗规则明显不同。但是,在以上两种法律架构中,若以独立的用益物权认定土地经营权的属性,皆存在法理困惑。学界有人主张将土地承包权界定为社员权而否定其用益物权属性,为土地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留出法理空间。(10)反对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二元学说的学者,往往提出“定限物权之上何以再度产生权利内容相似的定限物权”之诘问,而主张二元学说的学者则以“社员权+用益物权”或者“自物权+他物权”等阐释予以回应。但是,由于社员权与用益物权并不基于同一标准划分,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因而土地承包权可以界定为以社员权为基础的用益物权。
在尊重民法典权威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在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概念的情形下,笔者认为,应当将其解释为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组合,(11)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九条的表达,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于内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在原始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就包含着土地经营权,进而可以向他人流转,而不是由于流转创生了土地经营权。因此,在原始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分离出土地经营权的情形下,土地承包经营权若解构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则存在同语与同义反复的不合理性,进而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后仍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将会导致土地经营权的重叠;但若解释为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结合,将其解构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则会避免上述问题。有利于从土地经营权原始取得的来源认定土地经营权的属性,即土地经营权同土地承包权一样皆为独立的用益物权。同时,须对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独立性的阐释,以避免二者作为性质相同、内容相似的用益物权的并存。于此,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逻辑之中包含着一个预设前提——之所以能够通过流转合同设立土地经营权,是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始取得时土地经营权即隐含其中,从而土地经营权可以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在原始设立状态下分离出土地经营权,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权益并无害处,在实践中将其作为一项原始取得的独立的用益物权更易于实现市场化的运作。由于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这两项权利在现行民法典中皆包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因而同为用益物权的存在不可避免;但这两项权利的内容相似并非内容相同,在民法典第三百四十条对土地经营权的内涵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当下应当着手对土地承包权的独特内涵进行阐释。例如,依据民法典第三百三十四条至三百三十八条,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后,土地承包权仍可以互换、转让但不得对抗在先流转的土地经营权,承包地在调整、收回时对土地经营权人的损害赔偿以及是否存在免责作出解释,承包地在征收时应由土地承包人作为接受补偿的主体等,上述内容使民法典第三百三十四条至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更为丰富并有利于执行。概而言之,土地承包权始终以社员权为基础,可以在集体成员之间互换、转让,但禁止以入股、抵押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应由集体成员初始取得,但不禁止向集体成员外的人流转,且流转期限受到土地经营权期限的约束(在原始取得时土地经营权期限与土地承包权期限相同,统一适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土地经营权在流转期限届满后回归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另外,对于以入股、抵押方式流转的,基于前述分析,采登记对抗规则弊大于利,应明确遵循以土地不动产入股和抵押的相关规则,采取登记生效主义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