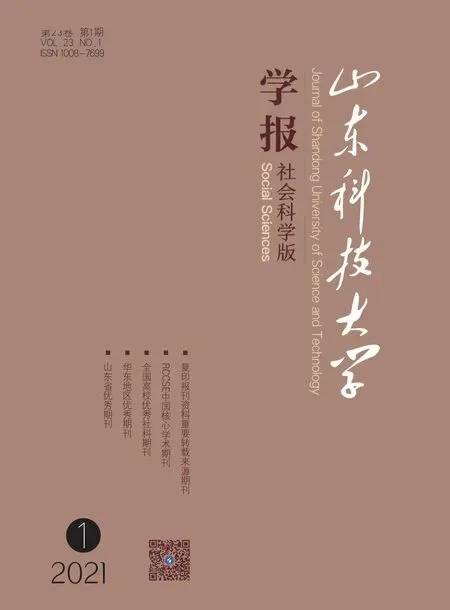抵押之外,土地经营权是否可以设定质押?
刘云生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 510006)
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九条删除了耕地抵押禁止的表述,显然是为了对接《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下称“新法”)及政策文本层面的三权分置法权体系,为未来深化农地改革预留空间。但民法典并未就耕地担保进行具体、全面的制度设计,第三百九十九条如何与其他法律和政策文本实现无缝对接就成为当务之急。比如,“修正案”涉及耕地抵押部分立法用语是“担保”,除了抵押显然还应当涵盖质押等担保方式;而民法典用语则是“抵押”,体系化位置居于一般抵押权项下。那么,土地经营权抵押设定的范围与对象是什么?抵押法权关系如何界定?是否允准土地经营权设定质押?
一、抵押权设立的范围与对象
新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受让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此条从法律层面认可了土地经营权的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可以有效激活土地融资新动力。
揆诸文义,民法典所涉耕地抵押,与新法高度契合:既不是作为集体所有不动产的耕地的所有权抵押,也不是具有浓厚身份性的农户承包权的抵押,耕地所能设定抵押的对象与范围仅限于农地经营权。
从宏观层面而论,修正案与民法典所涉耕地抵押并未实质性突破原有农地法权的保守、封闭格局。
首先,一如前述,抵押对象与范围限定。
其次,经营权抵押的设立负有前置性义务。经营权抵押面临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承包权两项排他性、优先性、身份性权利。经营权抵押的设立必须同时满足两项前置性条件,不仅需向集体所有权人备案,尚需征得承包权人书面同意。
最后,法权关系认定。按照民法原理,设立抵押属于处分权,是对物的自由处分行为;同时,抵押合同是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之间缔结的合同,不应受合同外第三方的限制、牵连。但根据修正案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此条无疑切断了抵押权人与发包方的法权关联,一方面阻遏土地经营权设定担保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还危及担保权的行使与实现,最终影响“修正案”所确证的土地经营权担保制度的效能。
二、向谁抵押?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第二条,土地经营权人只能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抵押贷款;根据新法第四十七条,承包方以土地经营权抵押,也只能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
这是目前经营权抵押或担保的核心文件和主要法条,一致承认了未转让经营权的承包农户和取得经营权的农业经营主体可以经营权抵押或担保进行融资,规定了耕地抵押只能针对金融机构设定,不得向其他任何主体抵押,否则会导致抵押合同无效等消极后果。
耕地抵押有限解禁无疑会缓解制度刚性,突破农地法权的封闭性、内部性,为农地市场化、资本化注入一线生机。但民法典实施以后,尚需考虑农地金融市场的行为偏好与行为选择,开辟新通道,让农户与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形成良性资金融通循环,否则经营权抵押要么流于形式,有名无实,要么难有实效,徒成画饼。
根据近十年来的调研结果,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
第一个现象,农户以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意愿偏低。学者们分别对成都、重庆、辽宁等地十多个省市进行实地调研,成都农户以农地、农房抵押融资的比例为37.6%(绝大部分为农村房屋产权抵押);重庆农民农地抵押贷款意愿最高,但也仅为38.4%;辽宁则有45%的农户明确表态不愿意通过农地抵押贷款;有学者对十个省的调研数据进行综合,愿意以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农户只有13.6%。(1)参见程郁、张云华、王宾:《农村土地与林权抵押融资试点调查》,《中国经济时报》2016年04月15 日A10版。
为什么土地经营权抵押意愿低?一方面固然与此前经营权法权建构不成熟且未通过法律固化,农户与经营权人担心法律风险有关,但经营权抵押条件、流程不明确,各地也处于试点、试错阶段,经营权人难以获得透明、确定的预期,才是最直接的原因。根据新法第四十七条第四款,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迄今为止,此类办法尚未出台,客观上消减了土地经营权人的融资意愿。
第二个现象,金融机构接受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意愿同样偏低。探究其因,高风险、低收益无疑是其最主要原因。
针对如上两种情形,如果于抵押之外,新增土地经营权质押等担保类型,则可有效实现民法典开禁的立法目的。
三、土地经营权质押问题
如前所论,新法立法用语采用的是“担保”,显然涵盖了土地经营权的质押。按照法律适用规则,作为单行法、特别法,新法应当优先于普通法而适用;按照权利类型设定而论,一项权利如果法律赋权可以抵押,理应也可以质押。据此,土地经营权的担保逻辑上自然不止抵押一途,尚包含了权利质押等担保手段。
单纯的权利质押方面,可以衔接民法典第四百四十条第七款。按照本条宗旨,土地经营权属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性权利,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出质,进行担保融资。循此思路,经营权质押放开,自然可以打破经营权人与金融机构的单向抵押融资格局,为经营权人提供更为便利、迅捷且多元的融资空间和通道。
土地经营权所涉股权质押情况略显复杂。按照目前的试点模式,农地经营权一般存在两种股权:一种是经营权入股土地专业合作社,此类股权原则上不能质押;另一种是公司化经营组织体项下的土地经营权股份,此类股权应当允许质押。循此思路,首先需对民法典第443条所涉股权进行扩张解释,将采用公司化经营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所设定的股权视为可设定质押的股权。其次,新法与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2018年12月19日颁行的《关于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的指导意见》均规定了承包方入股的权利。如果承包方转让了土地经营权,继受权利人逻辑上、价值上均有权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同时,入股后的股权本身就是土地经营权的实现方式和转换形式,不会对承包方的权利构成任何危险危害。
回顾历史,土地权利的抵押和质押一直是中国农业、农村、农民进行融资的最主要手段。宋代以降,典、质、当、押是农民通过土地和土地权利融资的最习见方式,不仅可以有效进行融资,还同时实现了土地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最终推动传统土地、劳动力、货币三大资本的有机融合。更重要的是,土地权利质押拓宽了农村土地融资的路径,土地经营权人不仅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还可以通过土地权利质押向金融机构之外的第三方主体进行短期融资,缓解资金困难,降低融资成本,节缩融资期间。
土地经营权质押是否可行?是否存在风险?
关于土地经营权质押的可行性问题,个人以为并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首先,目前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土地经营权质押。只要比对新法和民法典质押部分,即可实现有效的文本衔接。
其次,按照物权法定原则,即便民法典只承认土地经营权抵押,但新法的立法表述为“担保”,按照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适用的规则,理应将质押视为担保之一种。
最后,就权利设定而论,土地经营权既然可以转让、可以抵押,逻辑上也理应可以质押。关于土地经营权质押的风险问题,根据宋代倚当的历史经验,土地经营权的质押并不存在任何风险。倚当纯以土地权利当事人自由意志为中心,奉行“四不主义”——“不批支书”“不过税”“不过业”“不离业退佃”,既不影响承包经营权,也不会危及集体土地所有权,还不会影响土地的实际耕作权。
——基于农地福利保障调节效应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