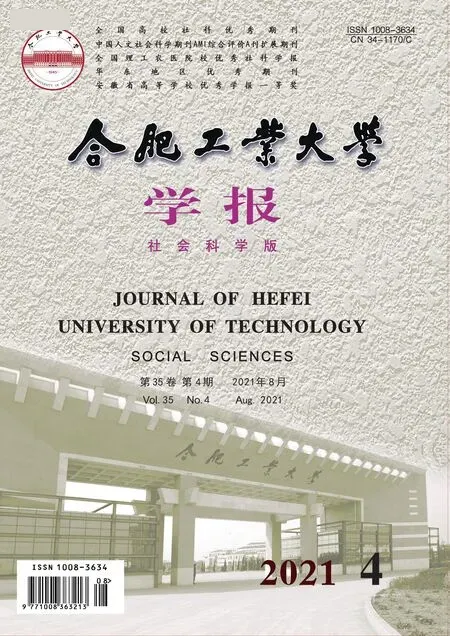《藻海无边》中欧洲裔白人的心理异化
张雪峰
(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
一、引 言
欧洲殖民侵略使得西印度本土民族消失殆尽 ,奴隶制庄园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大量非洲奴隶被运送至西印度各个岛屿,1834年废奴令的实施,在解放奴隶的同时亦损伤了欧洲白人庄园主的利益。为了补充劳动力资源,印度裔、华裔等契约劳工被紧急输入,这导致曾经的黑奴纷纷失业,继而加剧了西印度地区白人与非裔之间的种族矛盾。殖民历史及其激发的殖民利益无疑是导致西印度各个民族、种族苦难的根源,被卷入殖民利益链条的英国白人、西印度非裔无一幸免。然而,这种在西印度殖民历史中不分种族、民族,无一幸免的苦难,却被隐藏于白人与黑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等固化的民族与种族二元对立标签之下,当后殖民批评者纷纷引用那句“妈妈,看那个黑人,我好害怕”来批判白人殖民者对非裔被殖民者形成理所当然的伤害之时[1],那个白人小女孩以及她的母亲所代表的西印度欧洲裔白人群体,也理所当然地被贴上欧洲殖民者的标签,而西印度白人所遭受的恐惧心理与心理异化亦相应地被自动屏蔽。本文通过聚焦于《藻海无边》中的两位白人男性人物梅森先生与罗切斯特先生的叙述,解析19世纪西印度地区欧洲(裔)白人的恐惧与异化心理,指出西印度地区欧洲裔白人的恐惧一方面源于西印度社会变迁给英国白人家庭生活与文化心理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源于西印度非裔族群文化对于英国白人的反噬。双重合力最终导致了西印度地区白人想象性建构世界的坍塌。
一、 梅森先生——“无知的白人”
殖民贸易与庄园制经济的巨额利润使得许多白人纷纷将目光转向殖民地,寻找发财机会,这是《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Park, 1814)中的托马斯先生(Sir Thomas Bertram)仅仅依靠在安提瓜经营的庄园,就能够保证其家人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的原因,也是《藻海无边》中出现的第一位白人男性人物梅森先生之所以来到西印度的直接原因。“和其他人一样,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一些大庄园已经变得越来越衰败了,一个不幸者的损失,永远会使得另一个聪明人受益”[2]25,只不过与托马斯先生不同的是,梅森先生需要借助于婚姻这一外在推动力——迎娶库布里庄园的女主人安内特,才能够实现他在西印度的财富梦,即使库布里庄园在废奴令之后已经一片萧条。而这场以利益为基础的婚姻也是“聪明人”梅森先生逐步走向无知愚昧的起点。
实际上,像梅森这样的英国白人,其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受到西印度殖民地社会影响的叙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屡见不鲜:《简·爱》中的那个西印度疯女人伯莎不仅成为罗切斯特与简·爱浪漫爱情的碍脚石,也差点让罗切斯特先生背负重婚罪的罪名;而皮科克(Lucy Peacock)的短篇作品《克里奥尔人》(TheCreole)中的克里奥尔女性仄米拉(Zemira)则同样成为赛德里先生(Mr. Sedley)与夫人平静生活的破坏者。西印度殖民地人常成为扰乱英国白人构建和谐家庭的最大威胁。此外,随着英国白人与西印度殖民地人交流的增多,就出现了跨越种族界线的婚姻联盟,这就打破了英国白人高贵血统的神话传说。与文学虚构世界里的想象展现形成对照的是,这种跨种族婚姻早在17世纪初的巴巴多斯(Barbados)早已出现。当时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发生在黑奴柏金斯(Peter Perkins)和白人女性朗(Jane Long)之间的婚姻,他们的名字出现在1685年12月4日圣·米歇尔教堂的登记簿中,而他们儿子的名字亦出现在1715年人口调查簿中[3];而在1781-1813年间,就有14起白人女性嫁给西印度非裔的跨种族通婚的事实[4]。因此,英国的殖民进程同时也是英国接受殖民地影响的过程,殖民历史与奴隶庄园制经济在影响西印度社会的同时,西印度社会文化也带给英国白人深远的影响与冲击,使得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思维方式悄然发生改变。
如果说以金钱利益为基础的婚姻只是梅森先生走向无知愚昧的起点,那么一味沉醉于殖民幻想且无法适应废奴令之后西印度社会变迁的思维方式,更使得梅森先生走入无知与愚昧的深渊。来到西印度寻求财富的梅森先生对于西印度社会却一无所知,他对西印度社会的了解与理解,只是停留在英国白人殖民者对于西印度殖民地的想象性建构层面。在《藻海无边》中,里斯主要是以梅森先生与不同女性的对话形式,呈现出梅森先生对于西印度的想象性世界。这其中以三组对话最为典型,第一组对话发生在年幼的安托瓦内特与梅森先生之间,主要谈论对象为安托瓦内特的姨妈科拉。
“为什么她都不帮助你们?”
“胡说!”他说。
“我没有胡说。他们住在英国,如果她给我们写信,他就会生气。因为他憎恨西印度。不久前他死掉之后,姨妈才回到这里,在此之前她又能做什么?她也没有钱。”
“这是她骗人的,我才不信呢。她只是一个轻浮的女人罢了。如果我是你的母亲,我会憎恨她的行为。”
“你们全都不了解我们。”[2]26
对于科拉姨妈,梅森先生与安托瓦内特各持己见,二人的对话中也充满了各种不和谐的声音。金钱首先是造成这种不和谐对话的隐含因素,若我们把梅森先生“胡说”之后的叙述补充完整,就可以理解为“胡说,英国人不会不喜欢你们,因为你们才是我们的财富源泉。”在此,梅森先生只是从白人殖民者敛取财富的立场出发,将西印度视作为白人财富的集聚地, 却忽略了废奴令后西印度社会的变迁。据统计,仅在1502-1870年间,“就有1 000-1 200万黑奴被运送至美洲与西印度地区”[5],非裔成为西印度社会的主流群体;而废奴令又加剧了西印度地区白人与非裔之间的矛盾,白人逐步失去其经济与权力地位,“西印度的事务麻烦不断,黑奴都很快乐也很富有,反倒是西印度的白人一点都不快乐,西印度殖民地几近毁灭。”[6]这也就是为何梅森先生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库布里庄园化为灰烬却无能为力,唯有落荒而逃的根本原因。
其次,对于科拉姨妈在英国的生活,安托瓦内特与梅森先生产生分歧。通过安托瓦内特的叙述声音,我们洞察到科拉姨妈在英国的窘迫生活,克里奥尔白人身份使得她无法被英国殖民社会所接纳 ,女性身份也使得她无法被男权社会所接纳,最终招致的只有种族的憎恨与经济的贫穷。科拉姨妈的这种窘境尚且能被年幼的安托瓦内特所理解,却无法被成年的梅森所理解。这其中不无讽刺,里斯在此也以这种强烈的对比揭示出英国白人世界的冷漠与残暴。而安托瓦内特的那句未被言说的内心独白“你们全都不了解我们”,一方面揭示出克里奥尔白人与英国白人之间无法弥合的民族与种族隔阂;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梅森先生对于西印度社会想象性建构的最终坍塌。
第二组对话则发生在婚后一年的梅森与安内特之间,当安内特对西印度非裔仇恨克里奥尔白人的表现出担忧,提议离开西印度之时,梅森先生说道:“他们太懒了,不会造成什么危险。我太清楚了。”[2]28西印度非裔给梅森先生留下的只是懒惰、愚蠢与无能的印象,这种固化的种族偏见是英国白人为了建构起英国性而刻意塑造出的印象。在英国白人殖民者的世界里,远离非洲故土的西印度非裔首先就被建构为一个“奇怪的种族”,“他们没有任何关于国家的概念,没有种族的自豪感,甚至在非裔群体之间,黑鬼都成为非裔斥责彼此的最恶毒的词汇。”[7]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就此被贴上种族低劣、思想原始、智力低下的固定标签。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在其著名的游记作品《西印度与西班牙大陆》(TheWestIndiesandTheSpanishMain, 1859)中就曾记载道:“西印度黑人有能力从事最繁重的劳动,但却懒惰至极、毫无抱负……几乎不懂什么是工业,对于什么是真理或是诚实更是一无所知。”[7]这种英国白人高贵与非裔黑人卑贱的殖民思想灌输,使得梅森先生不可能对西印度社会现实做出最客观的判断,他只能沉溺在自己幼稚的想象性世界中,最后沦为这场殖民矛盾的又一牺牲者。
选择该科收治的肺癌合并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抽选出80例患者将其按照治疗时间顺序分为对照组(40例)、观察组(40例)。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观察组围手术期开展目标性护理,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患者知晓该次研究,在家属的陪同下签署知情书。
第三组对话则发生在梅森先生与姨妈科拉之间。承接第二组对话,梅森先生当着家中黑奴玛拉(Myra)的面,探讨从东印度输入劳工的话题,这引起了姨妈科拉的不满,梅森先生与科拉就此展开争执: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讨论这件事,玛拉在这儿听着呢。”
“但是这里的人都不劳动,他们也不想劳动,看看这个地方,太让人伤心了。”
“心早就伤透了,我以为你早已知道该做什么了。”
“你的意思是?”
“没什么意思,最明智的办法是别当着那个女人的面说你的计划,这一点极其有必要,我不相信她。”
“你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却对这里的人一无所知,太让人惊讶了。他们只是孩子——他们连一个苍蝇都伤害不了。”
“不幸的是,孩子真的会伤害苍蝇。”[2]30
在这一组对话中,科拉姨妈的理性与梅森先生的非理性形成鲜明的对比。科拉对于西印度社会的现实有着清醒的判断,她深知克里奥尔白人的苦难,也了解西印度非裔的积怨与仇恨。借助于科拉理性化的言语,里斯不仅戳穿了白人殖民者梅森先生对于西印度社会狭隘的认知,也指出西印度社会中白人与非裔不可调和的种族矛盾。与科拉姨妈相反,已经被殖民利益与殖民思想固化的梅森先生,则是完全失去了理性的判断能力,一面标榜英国白人“不愿伤害孩子”的善良,一面又带着殖民者残暴的心理,无视庄园制经济带给西印度非裔的灾难。正如评论者布朗(J. Dillon Brown)所言,“科拉对于梅森的驳斥显示出他的无知与自私自利,为了追求单方的商业利益,他却忽略了黑奴遭受到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与剥削。”[8]因此在库布里庄园被烧毁之夜,黑奴玛拉丢弃了安托瓦内特的弟弟,“她丢下他,逃走了,只留他一个人等死”[2]34,也只是再次验证了梅森先生的无知与愚蠢。
实际上,梅森先生对于西印度社会的无知及其对西印度非裔愚蠢的判断并非个人原因使然,而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长期构建的“白人至高无上”的集体性无知的认识论使然。米尔斯(Charles Mills)在《白人无知论》(WhiteIgnorance)一文中指出,白人无知论根源于“白人至高无上”观造就的“虚假信念”与“真实信念的缺场”[9],即欧洲帝国对于白人殖民者与非裔被殖民者建构并固化的双重虚幻世界。欧洲殖民者一面构筑起“白人至高无上”的殖民文化意识形态,形成白人种族优越论的自我欺骗式虚幻社会建构;一面又构筑起无视、贬低、歪曲被殖民者的殖民文化意识形态,形成非裔卑贱论的似是而非式的虚构知识建构。陷入双重虚幻世界的梅森先生,只能落入虚假社会建构与虚假知识建构起的无知认识论囹圄,对于西印度社会与西印度非裔形成固化的认知。通过叙述梅森先生与年幼的安托瓦内特、疯癫的安内特以及理性的科拉姨妈这三位边缘女性的对话,里斯一方面揭示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白人种族优越论的虚假性,展现出白人种族的社会建构性;另一方面则巧妙地逆转话语视角,将幼稚、无知、愚蠢与非理性等这些英国白人曾经贴在西印度非裔身上的标签,重新反射回白人梅森先生的身上,使其成为幼稚、无知、愚蠢与非理性的白皮肤“黑鬼”,并以此曝光那些被殖民利益与固化殖民思想所俘虏的英国白人在西印度殖民地社会受到的反噬影响。
三、 罗切斯特先生——“白皮肤的非裔”
继梅森先生之后,《藻海无边》中出现的第二个英国白人就是小说的男性主人公罗切斯特。小说的第二部分整篇都是以罗切斯特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讲述他与安托瓦内特的情感纠葛以及他在西印度社会中的心理感知。但是值得玩味的一点是,尽管里斯在第二章赋予了这一人物叙述声音,但却未赋予其确切的名字,“罗切斯特”这一名字自始至终都未出现,甚至里斯本人在创作这一人物之际,也只是将其称为“Mr.R”。“Mr.R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是否可以叫做拉沃斯(Raworth)先生呢,会不会听起来似乎更像约克郡(Yorkshire)人的名字?”[10]而在文本中,我们能够得到这一男性人物有效身份的信息,首先是通过安托瓦内特获得,即他是她的丈夫;其次是通过他的父亲与兄长获得,得知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最后是通过女仆普尔(Grace Poole)获得,他是一个有钱人,“他爸爸和哥哥死的时候,他还在牙买加,他继承了全部家产,不过在这之前他已经是个有钱人了”[2]145。 因此,罗切斯特的主体身份只能依靠与他者的关系来建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主仆关系等复杂的关系网建构起他的身份。倘若将名字视为身份的象征符码,我们就可以说与安托瓦内特一样,深陷英殖民文化与西印度社会文化间的罗切斯特,同样也遭受到了双重文化而致的心理异化,既无法找寻到自己的身份,也无法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
与梅森先生到西印度一出场就成为新郎的喜庆叙述不同,罗切斯特的出场却带着无限的落寞与凄凉,“所以这一切都结束了,前进与后退,怀疑与犹豫,这一切都结束了,无论好坏与否”[2]55。对于罗切斯特而言,尚未开始的叙述业已结束,这种极度抑郁而致的心理异化感贯穿罗切斯特叙述的始终,成为其叙述的基调。初到西印度的罗切斯特,首先就遭受到了西印度异域风景的冲击,“我疲惫地跟在她的后面,心里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太过浓烈了,太多的蓝色,太多的紫色,太多的绿色。花太红了,大山太高了,小山又太近了。而这个女人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陌生人,她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让我心烦。不是我买了她,而是她买了我,或者她也是这样想的。”[2]59罗切斯特无法适应西印度社会,甚至无法接受西印度的异域风景,此处的景物描写以及由此而至的感官变化,都成为展现罗切斯特失去其殖民权力的话语场,而遵从父命的婚姻交易又使得他失去了男性尊严,只能成为西印度社会与父权社会的双重奴隶。除了无法接受西印度浓烈的异域风景之外,罗切斯特亦无法接受西印度混杂的克里奥尔语言 。在与安托瓦内特前往度蜜月的山庄途中,罗切斯特叙述道:“两个女人站在草棚门口指手画脚,她们说的不是英语,而是这个岛上使用的粗劣的法语。雨水开始流进我的脖子里,令我的苦恼与抑郁又增加了几分。”[2]56-57被视为英帝国民族性文化象征与体现帝国文化思想和价值理念的英语语言在西印度却受到了挑战,这极大地损伤了罗切斯特作为英国白人的民族自豪感,致使其心理异化感再次加重。
当然,每当罗切斯特在西印度社会遭受到冲击,他会下意识地寻找一种自我保护,给父亲三次写信就成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心理保护机制。面对克里奥尔语言增加的苦恼与抑郁,罗切斯特的即刻反应就是他想到了那封一周前就应该寄到英国的信,“亲爱的父亲……”[2]57想要通过写信继续捍卫英语语言的强大效力;来到异国他乡,感到自己被奴役时,罗切斯特第二次提及给父亲的信件,“亲爱的父亲,我已经无条件地拿到了那3万英镑……所以我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我再也不会给你或是你最爱的儿子我的哥哥丢脸了,再不会给你们写信要钱了,再不会有那些卑贱的请求了,再也不会做出只有小儿子才会干的那些卑鄙的勾当了。”[2]59借助于已经被自己占有且能为自己操纵的财产,罗切斯特才能言说长子继承权(primogeniture)带给他的心理创伤,寻回作为次子的尊严,弥合这场婚姻交易中的心理落差。
罗切斯特第三次给父亲写信的地点则发生在梅森先生的房间。代表英国文明的物品,即一块英式地毯、一张放着笔墨的写字桌,让罗切斯特寻找到了暂时的安全感,他将这个房间视为自己的“避难所”[2]63。而一个简陋的书架以及陈列于书架上的书籍又很快驱散了他的安全感,“一个用三块木瓦板粘在一起搭成的书架放在桌子上面,我看了看,有拜伦的诗集、沃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小说、《一个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ofanOpiumEater)、一些破烂泛黄的书卷,最后一层架子上还有一本《……的生平与信札》(LifeandLettersof…),标题前面的字已经被磨损掉了”[2]63。在这些书籍中,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ofanEnglishOpiumEater)中的英国(English)已经悄然消失,而《……的生平与信札》的书名也已经不再完整,在英国被奉为经典、被视作英国民族性构建要素的文学作品在西印度却变得残缺不堪,甚至都无法辨析其完整的书名。这些破烂的书籍与残缺的书名,投射出的正是罗切斯特在西印度无法找到自己的殖民权威以及遭受西印度异域社会文化冲击后的碎片化的心理。紧随其后,罗切斯特则写下了给父亲的第三封信。“亲爱的父亲,一连几天的折腾后,我们终于从牙买加来到这里。这是位于温德华群岛处的一个小庄园,也是家庭财产中的一部分,安托瓦内特对它很有感情,总希望能快点到达这里。一切都按您的计划与愿望顺利地进行……”[2]63虽然充满挫败感的罗切斯特意图以再次占有财产的方式,重新找回英国白人殖民者建构的权威感,以再次控制财产的方式填补长子继承权留给他的心理创伤,但那些信件却从未寄出去,只能成为尘封的痛苦记忆。“我不知道这里的人是怎样寄信的,只好把信收起来,放进书桌的抽屉。至于头脑里那些混乱的印象,我永远都不会写下来,只剩那些无法填满的空白。”[2]64与梅森先生一样,罗切斯特最终仍然无法逃脱西印度社会文化的反噬影响。
《藻海无边》中对于罗切斯特影响最大的人是非裔女性克里斯蒂芬。初次见面,罗切斯特就感受到了克里斯蒂芬的敌意。“她平静地望着我,眼神中看不出任何的赞同。我们对视了一下,但我先把挪开了目光,而她却暗自微笑了一下……”[2]61正如沃霍尔(Robyn Warhol)所指出的那样,“注视”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权力的内涵”[11],在这场以罗切斯特代表的男性白人殖民者与克里斯蒂芬代表的女性非裔被殖民者之间的对视中,男性凝视女性、殖民者凝视被殖民者的权力关系已经被逆转,罗切斯特成为被看的一方,而 “挪开目光”的行为也已经被涂上了女性化的色彩。因此,在这场无声的“注视”的较量中,罗切斯特的权威感受到了挑战。从一开始,他就已经失去其殖民者与男性的话语权力,反而陷入被女性化注视的尴尬处境。
接下来,罗切斯特则是走入完全失去其殖民者与男性话语权力的境地。安托瓦内特疯癫之后,罗切斯特决定带她返回英国。在此之前,克里斯蒂芬与罗切斯特有一次长谈。在谈话中,克里斯蒂芬一面愤怒地揭穿了罗切斯特夺取钱财的婚姻目的,谴责罗切斯特的卑劣行为。一面理清了安托瓦内特的家族矛盾,解释了安托瓦内特母亲疯癫的原因。克里斯蒂芬的言辞句句指向罗切斯特的贪婪与愚蠢,而罗切斯特在听到这一切之后的心理活动却是“我回头看着她,她的脸上像罩着层面具,但是眼睛里却毫不畏惧。她是一个勇士,我不得不承认”[2]133。评论者厄文(Lee Erwin)指出,《藻海无边》中的混杂叙述使得“白皮肤的非裔”(white nigger)与“黑皮肤的白人”(black Englishman)这两个具有种族与民族之分的术语发生“互换”[12],因此我们可以将此刻罗切斯特与克里斯蒂芬的反应视为一种身份的互换,克里斯蒂芬的理性与勇敢使得她成为黑皮肤的白人,而罗切斯特的愚蠢与懦弱则将其转变为白皮肤的非裔,在罗切斯特与克里斯蒂芬的对话中,二人的身份已经发生互换。于是,失去其自我身份的罗切斯特企图再次以写信这一行为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你可以给她写信”[2]133,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不认识字,也不会写字,但其他的事情我都懂”[2]133。
克里斯蒂芬提到的“其他的事情”指的就是她精通的奥比巫术(Obeah)。“奥比”一词起源于非洲西部阿善堤地区(Ashanti)的部落术语Obayifo或obeye,分别指涉该部落的男巫、女巫或是暗藏巫术的精灵[13]。在17世纪,由于非洲西海岸的大批黑奴被运送到西印度,这一民俗文化形式也就此落根于巴哈马、安提瓜、巴巴多斯以及牙买加等地,经过重新适应与调整,成为克里奥尔文化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印度奥比巫术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施咒语,可以是行善的咒语譬如祈福、庇佑,亦可以是施恶的咒语譬如诅咒敌人等;二是将草木与动物视为治愈疾病之用,大自然界的植物与动物都被赋予超自然的功效。因此,奥比巫术不仅能够为抵达西印度的黑奴提供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治愈功能,更是维护西印度黑奴内部稳定的重要方式。然而,这一文化形式却极大地影响了白人庄园主的生活,对英国殖民统治造成潜在的威胁。于是在1787年,英国政府明令“任何假装自己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奴隶,一旦有危及他人健康或生活或是有蓄意反叛之目的,重者以死刑论处,轻者交由法庭审判”[13]。这也就是为什么恐惧无助的罗切斯特最后只能拿出地方法官弗雷泽(Mr. Fraser)的回信威胁克里斯提芬的原因所在。
克里斯提芬不仅使得罗切斯特对她产生莫名的恐惧感,更是让他成为奥比巫术的俘虏。为了挽回罗切斯特对于自己的爱,安托瓦内特乞求克里斯蒂芬的帮助,克里斯蒂芬以巫术调制的迷魂剂(催情剂)最终亦使得罗切斯特痛苦不堪。“梦见自己被活埋的我在黑暗中被惊醒了。醒来后,我却感到无法呼吸……我觉得很冷,身体如尸体般的冰冷,浑身疼痛……我想自己是中毒了。”[2]113此时的罗切斯特在奥比巫术的影响下已经成为一个失去灵魂的僵尸,任由安托瓦内特操控。僵尸(zombie)在非洲与西印度巫术文化中又常被视作奴隶的象征,指涉被剥夺了意志、被迫为主人劳动的奴隶。因此,克里斯蒂芬实际上是利用巫术逆转了白人奴隶主与非裔奴隶的建构关系,使得罗切斯特成为失去灵魂与自我的活死人,重新体验被白人殖民者(奴隶主)带给非裔被殖民者(奴隶)的身体苦痛与心理折磨。然而,相继被逆转为女性、被殖民者与非裔奴隶的罗切斯特终究还是未能逃离克里斯蒂芬奥比巫术的诅咒,当克里斯蒂芬谴责罗切斯特“像撒旦一样邪恶”时[2]132,罗切斯特辩解道:“你以为我想要这一切吗……我宁愿失去眼睛也不想再看到这个让人厌恶的地方。”[2]132如他所愿,罗切斯特最终还是应验了克里斯蒂芬奥比巫术的效力,以失明为代价偿还了自己曾在西印度撒旦式的邪恶罪行。
里斯对于罗切斯特的叙述与其他作品中的白人男性人物形成极大的反差,无论是《黑暗中航行》(VoyageintheDark, 1934)中的沃尔特先生(Walter Jeffries),亦或是《四重奏》(Quartet, 1929)中的海德勒先生(Mr. Heidler)都有名有姓,是手握殖民权力与父权权力并能主宰女性人物安娜(Anna Morgan)与玛利亚(Marya Zelli)命运的叙事主体,而《藻海无边》中的罗切斯特却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类型。“罗切斯特是里斯笔下最复杂、描述最充分的一个男性人物”[14],他并非一个十足的恶棍,与安托瓦内特一样,都是“被遗弃的孩子,在异国他乡,都害怕孤独也害怕受到伤害”[15],这种害怕并非个人因素使然,而是社会历史因素使然。
正如安托瓦内特所言,“任何事情永远都有另一面”[2]106。倘若说里斯赋予安托瓦内特与安内特言说的能力,是要折射出殖民历史与父权社会对于克里奥尔女性的影响,那么,她赋予罗切斯特与梅森先生发声的机会,则是要展现西印度地区英国白人的心理异化世界,撕裂西印度地区欧洲裔白人的虚幻殖民面具——“白皮肤只是一副面具”[16],折射西印度社会变迁与西印度非裔文化传统对于英国白人的反噬性影响,揭开西印度地区英国白人以及欧洲裔白人异化心理的社会历史原因,展现民族、种族与性别的文化建构性,诉说西印度地区英国白人与西印度非裔共同的心理创伤。
四、结 语
漫长的欧洲殖民带给西印度非裔的精神创伤无法否认,存在于白人殖民者与西印度非裔之间的民族与种族矛盾亦不容否认。但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的殖民历史与奴隶庄园制经济将欧洲裔白人殖民者与西印度非裔同时卷入,使得在西印度非裔遭受奴役与心理异化的同时,也使得西印度地区的欧洲裔白人同样遭受心理恐惧与精神异化。这种心理恐惧与精神异化正是西印度社会变迁与西印度非裔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这种合力是西印度非裔牵制英国白人、反击殖民统治、对抗殖民文化的有效力量,但同时也带给英国白人家庭生活与文化心理巨大的冲击,使得英国白人遭受到“无知、白皮肤黑鬼”等一系列反噬性文化影响。因此,从这一层面而言,《藻海无边》中关乎梅森先生与罗切斯特先生的叙述,不仅仅诉说的是西印度非裔对于欧洲裔白人殖民统治的反抗与斗争,也是一曲“白皮肤、黑面具”的低声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