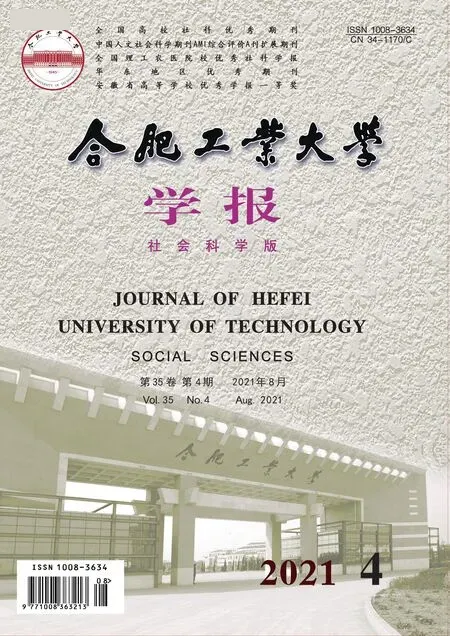博弈与融合
——巴赫金对话理论观照下的《亚瑟王之死》
锁 娜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托马斯·马洛里生年不详,卒年为1471,其出生于沃里克一个伯爵家庭,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曾八次被捕入狱,出狱后参加骑士团支持沃里克伯爵,而伯爵在巴尼特战役中被杀,马洛里也第九次入狱。《亚瑟王之死》就是他作为战俘于狱中为英国文学献上的一份大礼,其在亚瑟王传奇、兰斯洛特,梅林和圆桌骑士的英法故事基础上揉合了自己的想象,至今仍是历史上关于亚瑟王传奇最著名也是最完整的作品,是后世研究亚瑟王的主要参考资料。从文化史角度看,马洛里在乔叟和斯宾塞之间起着重要的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使用的英语比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还要更加接近早期近代英语,德里克·布鲁尔(Derek Brewer)曾评论此书“既有绅士风度又很虔诚的现代主义”[1]。
因为要覆盖的内容过多,马洛里会经常使用“所以-接着”来过渡他的重述,这种重复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增加了一种与故事的规模和宏伟相称的连续性,这样整个故事都成为情节而非间断的例证”[2]。有的学者由此入手,认为作品的叙事结构是骑士文学中的契约型组合,有的着眼于作品中的骑士爱情和骑士传统,而本文拟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分析作品的中世纪基督教、骑士和巫术文化,从而展现作者对骑士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二、基督教文化对骑士文化的支配
1.教会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关系
与教会文学完全不同的世俗文学于中世纪后期产生,在那之前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对人类精神生活有贡献的都是僧侣。到14世纪为止,教士们就彻底垄断了哲学,从那时开始,“哲学的写作都是从教会的立场立论的”[3]。在马洛里生活的15世纪,骑士阶级开始没落,教皇的权利也开始旁落,但是基督教的精神和教会文学的叙述体系早已和世俗文学尤其是骑士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基督教用自己的原则和观念意识整理、编辑文学文本,并为文学提供了思想内容,而世俗文学也用自己的经验规定了基督教的表现方式”[4]。从作家的角度来说,马洛里身为被册封的骑士会比同时代的作家更加信奉基督教,再加上作品描述的是中世纪骑士冒险故事,那时候的教会地位甚至“在国家之上”,基督教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不管是这部传奇中描绘的骑士之爱和骑士精神,还是圆桌骑士追逐圣杯的故事都可以看出中世纪的教会文化对骑士文学的影响,骑士们忠贞、勇敢,追求冒险和无畏殉身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巴赫金曾经说过,“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5]。在对话理论中,意义产生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话语的对话之中,产生于前后语言构成的语境之中,语篇也不例外,但是与二者不是处于理想的对话状态时就会形成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霸权。
在作品中,骑士精神是基督教文化宣扬的,寻找圣杯是基督教倡导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宣讲基督教的教义,甚至亚瑟王之死部分地也是因为犯下了乱伦之罪。马洛里作为一名受封的骑士,信仰基督教既是品质也是资格,因此他在描写两种对话时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基督教文化成为当时文学的评价维度后,就已经形成了话语霸权,即基督教文化对骑士文学的支配,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理想状态下的对话关系已经被破坏,但是基督教传统也被打上了世俗文学的烙印,使其叙述被骑士文学的经验规范着,两个独立的主体意识在时代的影响下开始建立起了联系。从追寻圣杯中尤其可以看出两个话语是如何相互影响并互相阐释的。
2.骑士追寻圣杯是为了宗教信仰
圣杯的故事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关于圣杯的传统观点是:它是一只曾经盛放基督血液的圣餐杯,后来亚利马太的约瑟把圣杯带到了英国。但是《圣经》中并没有提到圣杯,更没有提到约瑟曾经用圣杯接取耶稣流下的血,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圣杯传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基督教的传说,而是源于一些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并在后续的发展中逐渐被教会文学所吸收和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即使基督教和教会文学曾经长时间地统治人们的精神世界并作为文学创作的标杆,教会仍然不得不向世俗文学做出一些让步而不是赶尽杀绝,他们选择了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学系统并进行改造,以便让世俗文学为教会服务。
在中世纪,新基督教徒已经很好地接受了圣杯的传说并把寻找圣杯看成是骑士精神的一部分,寻找圣杯不仅代表着“骑士冒险”,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骑士所经历的“灵修”,这不仅仅要求骑士要在精神上变得纯洁,也要在肉体上完成“神性”的转变。其实圣杯本身只是个具有神奇力量的容器,比起结果更重要的是骑士在这一过程中的蜕变,他们不再是世俗眼中的战士,而是虔诚的教徒在寻求精神的净化。在圣杯城堡中,也“只有受洗过的基督徒才能看见圣杯;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它”[6]。《亚瑟王之死》中,高文骑士在寻找圣杯前做了一个神奇的梦,一位修士曾经解释了梦的含义:“那片肥美的草场和羊群,应当视作圆桌,至于牧场可以理解为谦顺和忍耐,代表了青春和活力……又如三只白色熊牛,其中两只全白,一只生有黑斑的意义,我认为两只白牛代表加拉哈德骑士和博西华骑士,因为他们贞洁而无污点;至于第三只带有斑点的白熊牛,是指鲍斯骑士而言,由于他失去过一次童真,但从此以后他还能保持纯洁的生活,所以他的罪最终被神饶恕了……”[7]691最终知晓了圣杯奥秘并回归上帝怀抱的加拉哈德骑士更加接近基督教的圣徒形象:高贵的血统、品德高尚且见证过神迹。而兰斯洛特则是因为不够贞洁,拘泥于世俗的情爱而不能被人类的牧者所召回。
不难推断,那时起骑士文学已经和教会文学的精神要旨联系在了一起,骑士不再一味追求功名和利益,精神的净化才是他们追寻圣杯的动力和奖赏,而教会文学也是逐步吸收世俗文学中的传奇故事,写作手法等来传达教会的教义和原则,彼此都打上了对方的烙印。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发现里面的人物是在与自己和他人的不断对话中逐渐界定自身并找到自己的价值的,因为“只有与其他人思想建立起实质性的对话关系,思想才能获得生命”[8]95。在《亚瑟王之死》中也可以看到骑士与多类人都进行了对话,比如说代表着俗世的国王、代表着巫术的女巫和梅林,而与他们接触最多的是代表教会的修士。骑士在与这些人对话的同时也是在与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文化进行博弈,或吸收或摒弃并形成骑士文化“有理论,有行为规则,有艺术形象的”体系[9]。
3.宫廷爱情与圣母崇拜
在书中,马洛里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骑士们对圣杯的追寻,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完成这场冒险的只有三位骑士,而被上帝提前召回的只有一位,那就是加拉哈德。他的父亲是骑士之花兰斯洛特,在书中,兰斯洛特可以说是第一骑士,但却是其子先找到了圣杯,究其原因是“他犯了色戒,罪孽深重失去了担当如此神圣任务的资格……论武功,他都远远地超过他的同代人,但在性灵反面,却有许多人在他之上”[7]580。兰斯洛特和王后的宫廷爱情阻碍了他追寻圣杯的脚步,而作为一名“基督的骑士”,他对上帝的爱应该占据首位,他必须先为上帝和教会而战,然后才是他的情人。从这一点上看,其子加拉哈德一直保持着童真,这正是兰斯洛特无法做到的。
但即使兰斯洛特犯了色戒,奇怪的是上帝仍然一直给予他荣誉,还不断赠予他机会,不断启示他,甚至没有对他和王后之事过多干预。然而若是联系时代背景也就不难解释这一现象。在中世纪,骑士就是自己情人的“奴仆”和“囚徒”,“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她们稀奇古怪的要求和折磨。骑士最高的使命就是伺候和保卫情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获得情人的回报”[9]。在书中,兰斯洛特为了王后甚至与亚瑟王决裂。如刘易斯所指出的,宫廷爱情实际上也是一种“宗教”,骑士的情人就是他们的上帝。而在这种爱情盛行的同时,恰好也是圣母崇拜发展的时期。有学者指出,宫廷爱情对于女性情人的崇拜和颂扬实际上也促进了圣母崇拜的发展,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可以得知,骑士对于自己情人的崇拜,或多或少也掺杂了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而这种融合是教会乐于看到的:将包含了圣母崇拜的基督教文化灌输给以宫廷爱情为核心的骑士文化,有助于建立规范化、规则化的骑士阶级。所以书中上帝对于兰斯洛特一次次破戒的纵容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骑士文学中关于爱情的浪漫传奇,就像话语一样被基督教文化听到和理解,而基督教虽推崇贞操和神圣的婚姻,但既然并不属于异教,它针对骑士文学的回答就是:没有特别排斥宫廷爱情的理由。
卢米斯曾经指出,文学自身具有强大的涵盖性和应变能力,但它受到另一种强势话语的威胁时,“会将所包含的经验内容让渡到这种强势话语中,从而以自己的方式规范这种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4]。而在中世纪,基督教及其文化是无人能够置身事外的东西,包括文学。而当骑士文化中的宫廷爱情与基督教的贞操观发生碰撞,两个意识处于相同的话语交锋点时,基督教文化也不得不接受世俗文学并借助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不反对宫廷爱情但是基督教宣扬的高尚贞操观更胜一筹。
三、教会文化是巫术文化发展的结果
1.教会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关系
那么既然在作品中已经有了如此强烈的教会文化的色彩,为何又出现了似乎和上帝一样神通广大的巫师梅林呢?他是否是为了衬托上帝的纯洁和万能而存在的呢?
巫师梅林,其长期活跃在关于亚瑟王的传奇和威尔士的诗歌之中。关于梅林的描绘首次出现在《不列颠诸王史》中,在这部著作中,巫师“梅林”融合了大量的早期历史人物和传奇人物的故事。而在《亚瑟王之死》中,梅林已经是中世纪最强大的巫师,他通过魔法和阴谋使亚瑟诞生,此后成为亚瑟的顾问和指导老师,直到被所爱女子欺骗并被封印进石头后才从书中消失。
在书中,梅林似乎是上帝的反面,他有人的七情六欲也会耍阴谋诡计,这和默默观察世间发展的上帝有着很大不同,但是二者又都全知全能,在某种意义上又有着相似之处,其实这体现了巫术文化和教会文化的关系。
首先从信仰上看,巫师以己推神,认为自然界背后有着人格化的神灵,而基督徒则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其次,从崇拜的对象看,原始人认为可以通过威胁自然界背后的神灵从而使自然听从自己的命令,但是随着不断地尝试,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弱小,并宣称人只有通过祈祷才能获得神灵的怜悯和恩赐,之后人为了凸显自己创造出的神的全能,将神的世俗情感抽离,化为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在某种程度上是神灵崇拜进化的产物。最后,圣·雅各曾经说过:“没有实践的信仰是没有什么用的。”因此从古至今巫术和教会为了展现自己的神圣都有着不同的仪式,原始的巫术仪式充斥着暴力和血腥,活人献祭也屡见不鲜,发展到祭司主掌仪式时已经用人形偶像来代替活人,而到基督教的时候,教会的仪式已经变得繁复却较温和,虽然仍可以看出遗留的巫术仪式,比如说早期社会为了获得神性而食“神肉”,即分食他们所认为的神之化身的某些动物的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仪式也可在基督教的圣餐中找到一些相似之处:圣饼为基督之肉身,葡萄酒则为基督之血。然而关于巫术和宗教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但学者们关于二者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却是大多赞同的。
在14世纪,自然魔法在欧洲文化中心地位得以确立,那时的宫廷贵族对魔法抱有恐惧心理,但“在文学作品中他们喜欢魔法带来的微妙感觉,并赋予它很高的地位,因为这有助于人们逃离枯燥的现实”[9]。所以说在马洛里生活的时代,人们对魔法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恐惧又着迷。但是带有异教色彩的巫师和魔法却并不是“反基督教”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因素能够为基督教文化所用,借以扩大信徒数量和传播范围,教会也不介意巫术文化在文学作品中出现。
2. 梅林在作品中的定位
从能力上看,梅林可以说是有着人性的上帝。他可以预言:大不列颠存亡之际,他(亚瑟)必将醒来[7]37;可以变形:乞丐说,我就是你要找的梅林,如果亚瑟国王能重赏我,并发誓满足我的要求,我就能让他得偿所愿[7]40。从其对亚瑟王的影响来说,他使得亚瑟王的出生披上了神秘的传奇色彩。弗雷泽在《金枝》中描述过早期人们在五朔节和降灵节的纵情狂欢,而女子若于此期间怀孕,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孩子父亲就是祭奠的神灵,比如说国王纽玛就是在这种节日孕育诞生的。由此可以表明在早期社会,人们更希望伟人的出生是某些超自然力量的显现。而梅林在书中就是扮演了重构亚瑟王身世的角色,符合了社会公众对贵族或皇室继承人的期待。但是在书中,全能如梅林者也信奉并尊重上帝的旨意;另一方面,主教也会听取巫师的建议——主教采纳了梅林的建议,派人通知各地的骑士贵族,让他们于圣诞前到伦敦来[7]88。这时,梅林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对话艺术原则。巴赫金认为,主体与客观世界的沟通只能靠对话,平等、民主的对话要求尊重对话者的思想观点,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自由对话的文化意识。梅林所代表的巫术文化在作品中看似有话语权并且对作品的走向有着相当的影响,他可以在作品中和各类人物对话,甚至与上帝对话,但他是以传话的媒介而存在的:上帝自有旨意,请诸位大臣明日齐来参见国王,我会让他开口说话的[7]49。
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也曾与其他俄国作家做了对比,提出有些作品没有体现出主人公意识的未完成性和无限性,而是一个封闭的独白,主人公完全沦为了作者的传话筒,缺失了独立性。书中梅林的出现仿佛就没有自己的话语和思想,他似乎是上帝派来辅佐亚瑟王的巫师,但也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作品中梅林的死也颇有讽刺意味,能够预言的梅林死在了爱人之手,他全知全能却依然没有跳出世俗的束缚,和上帝的对比更是让人清楚二者的高低之分,梅林的死其实也是宣布作品中带有的巫术的原始神秘色彩会开始降低,教会的神圣会被更加凸显出来,巫术在可以为教会服务的基础上可以有与他人甚至上帝的对话,但终究会隐退。
四、巫术文化是骑士文化的工具
1.亚瑟王与梅林
在《亚瑟王之死》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骑士文化,巫术文化可以说是隐藏其中的暗线,其作用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突出宗教,巫师本身的职能修士也可以做到,巫师原本尊崇的神灵也开始被上帝替代,骑士也需要遵从基督教教义开展行动,必须保持自己的纯洁。整部作品中也没有太多语篇可以表现二者的对话,因为根本上骑士文化体现出的骑士精神,实际上都是为了巩固和美化已经腐朽的封建贵族制度。男巫梅林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利用魔法和阴谋制造了亚瑟的诞生,利用各种神奇的巫术来预言、指导、帮助年轻的骑士和国王,反过来亚瑟王——骑士的代表,似乎也拥有着某些可以和精灵交流并获得他们帮助的力量:那位仙女马上就要来见你,只要你应对得体,她就会把那把宝剑送给你[7]331。在作品中,亚瑟王符合中古时期宣扬的君主形象:明君总是有着神奇的能力。至今英国人民还普遍认为国王的触摸可以治疗腺病[11],国王的出生和能力总是被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巫术文化实际上也是骑士文化所代表的封建制度为巩固和神化君主地位的工具之一。
在作品中,亚瑟王既是国王也是骑士,很明显他也具有某种和普通民众不一样的能力或者说和巫术类似的能力,众多实例也表明,很多地区的国王确实都是古代巫师的承继者[11]36,这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亚瑟王身边为何总是有神秘力量在辅助他,为何他的出生和经历都富有传奇色彩,但是《亚瑟王之死》中的巫术文化是为骑士文化所代表的封建制度服务的,巫术的话语处于被骑士文化和教会文化的双重压制之下,只有符合主流话语的趋势,它才能表达出“自由的”想法,那就是为上帝发声,为骑士王亚瑟铺平道路。
然而除亚瑟王,仍然有骑士不乏神秘力量的加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高文骑士力量的巫术体现。
2.高文骑士和巫术
书中对于高文骑士力量的解释出现在其与兰斯洛特第一次决战时。“先前有一位圣人向高文爵士传授过一套武功,使得他每天在正午前三个时辰内身上的力量都能陡增三倍。”[7]846这意味着高文在正午前虽不说无敌也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是兰斯洛特也需采取拖延战术。而如此强大的神秘力量不止高文拥有,书中另一位曾与鲍曼骑士拼杀过的、身着红色铠甲的绯红骑士也有着类似能力。“正午前请你别吹响号角,因为现在是早上六点,他的力量仍在不断增长。”[7]222这种神奇力量和之后上帝所行的奇迹有所不同,它不需要祈求上帝的帮助,反而类似习得的巫术。
在《金枝》中,弗雷泽曾经提及早期社会人们认为灵魂是存在的,且某些人相信影子和水中映像也是灵魂的一部分,纳西索斯的神话可能也是由此而来。而影子相当于人身力量甚至生命的想法也并不罕见,早期社会的人会将影子的缩小视为生命力缩减的预兆,从而焦虑不安、忧心如焚。芒艾亚岛上的土著人中流传着一个关于非凡勇士图凯塔瓦的故事,据说他的力量会随着他影子的长度消长。早上当他的影子最长时,他的力量也最强大;临近中午,随着影子的缩短,他的力量也开始减弱;正当午时他的力量减退到最低点;到了下午他的影子又逐渐拉长,力量也随之恢复。一位英雄发现了他力量的秘密,便在正午时分将其杀害[11]115。与书中对于高文力量的描述一样,都是正午之前逐渐变强而后随着日光下沉,影子缩短力量也随之衰退。总体来看,高文骑士这一特点在众多身为虔诚基督教徒的骑士中显得突兀,而他的力量与某些原始部落的传说有着相似之处,不妨大胆推测:高文在圆桌骑士中有可能是和巫术甚至是异教有着一些联系的骑士。在其他有关高文的传奇中,比如《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部分学者认为故事从绿衣骑士在亚瑟王宫廷提出砍头的挑战开始,其中异教与基督教成分就已经并存,但这一观点仍有待商榷。不过在作品中,如果说男巫梅林是巫术文化和骑士文化相互交织融合的生动代表,高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骑士文化在和巫术文化对话交流后,在骑士文学中对骑士文化的意识进行积极扩展的例子。“这种扩展不仅具有掌握新客体(人的典型,人的性格,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这样的意义:与具有充分权利的他人意识进行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对话交流;通过积极的对话深入人心”[8]77。
五、结 语
《亚瑟王之死》作为中世纪骑士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涵盖了多种文化,尽管后来教会文化的精神之旅已经成为骑士文化尤其是圣杯追寻的目的,骑士精神仍然闪耀着自身的光辉并为教会文化吸收;而巫术文化则是处于教会文化和骑士文化的狭缝中艰难发声,但仍可以看出原始巫术的神秘色彩,为亚瑟王的故事更添了传奇意义。这本小说不是封闭的,人物也不是聋哑的,他们的世界是相互交织交流的,他们彼此了解,交换着自己的“真理”,或反驳或赞同对方的观点,进行着对话。因此作品中的三种文化尽管看上去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权力和力量的中心,它们的相互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式都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12],这就意味着读者应看到马洛里背后所代表的权力运作和作为权力出场形式的各种话语。虽然书中巫术文化和骑士文化的出现绝大部分都表现了二者对基督教文化的妥协,但是二者同样也被纳入基督教文化的内部,以独有的方式保持着自我,边缘文化即使面对强势的主流话语仍然有着自己对话的方式,并以此产生巨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