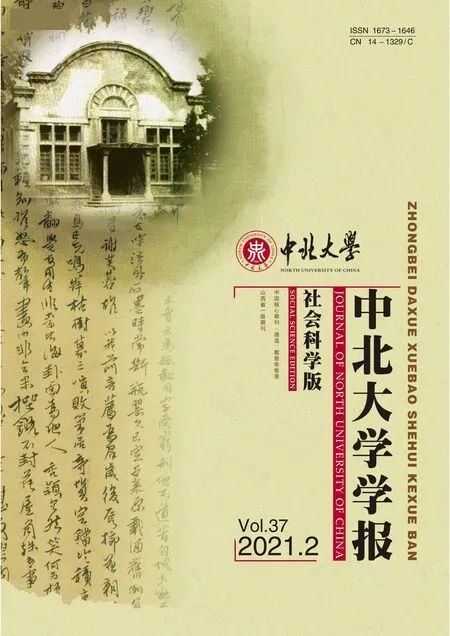试谈清宫演剧中的六郎庄
张紫阳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0 引 言
清代宫廷演剧的外学制度作为宫廷与民间演剧交流的重要渠道, 体现了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民间戏曲的态度, 也持续影响着清代戏曲的审美风尚。 这样一个重要机构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 其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外学的基本形态早在康熙年间就已见轮廓, 后随历代帝后之好尚而时有调整。 过去学者对于清宫演剧机构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南府、 景山、 昇平署的发展变迁, 从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 周明泰《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 到刘政宏《清代宫廷皇家剧团管理机构沿革考》和朱家溍、 丁汝琴《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等, 始终是把南府、 景山和昇平署的人员架构、 承应职能、 演剧内容等作为关注点, 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出现的六郎庄学艺处则乏人问津。 这固然有利于集中收集清宫演剧的相关资料, 但也容易遮蔽其他相关机构的历史价值, 通过对六郎庄学艺处的设立与消失之探寻, 我们可以尝试跳出以往的研究聚焦点, 还原清代宫廷演剧真实而复杂的文化生态, 对清宫演剧与外学制度做一个更为全面、 完整的把握。
1 康乾年间的外学演剧与档案资料中的六郎庄学艺处
清宫外学不同于太监伶人组成的内学, 其主要人员均为民间伶人。 这些人员中, 有自江南选进的汉籍人等, 也有隶属旗籍者。 外学人员中有不登氍毹、 专门负责教授技艺的教习, 也有身傅粉墨担当演出的演员。 齐如山在《谈升平署外学脚色》中提及“乾隆下江南带回来昆班昆曲名宿若干人, 在内廷供奉, 但因人数添多, 遂迁入南长街驸马府, 即改名南府, 专教太监, 自己则绝不登台”[1]335。 其实, 乾隆朝已有外学人员参与内廷演出的记载, 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提到乾隆年间南府、 景山皆有外学。 王引道光二年(1822年)总管禄喜所上奏折云: “遵旨查得乾隆十九年(1755年)正月初二日, 万岁爷请皇太后金朝玉粹早膳, 内头学承应节戏一分毕, 前台内外学接唱节戏。”[2]8-9则乾隆十九年(1754年)已有外学之名。 王氏又据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刻《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考定, 当时外学演剧机构为:
南府: 外大学, 外小学。
景山: 外头学, 外二学, 外三学。
查《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中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刻《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中确有“外二学内三学公官众等信官众等景山钱粮处三学”之记载。[3]913
虽则外学之名迟至乾隆年间才出现, 但具有外学基本形态的演出机构却早在康熙朝就已经建立。 “从《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中收入的材料, 和《李煦奏折》等残存史料中可以得知, 康熙时代的宫廷演剧事宜均由内务府主管。 具体做法是:内务府有专职官员, 源源不断地从南方挑选技艺卓著的乐人和伶人入宫。 有的作为‘授艺教习’, 职责是教授包括太监演员在内的皇家剧团演员‘弹乐’‘杂耍’‘弋腔’等。 有的是专职演员, 担当承应演出。”[4]3
现存资料中对于康熙时期南府和景山中“卿客” “教习”的记载并不少见。 据朱家溍、 丁汝琴《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所引[5]9-16: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总管内务府下各司关于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
(十月初六日)当日, 准掌仪司来文, 教弹琴太监之人朱之清、 徐有成, 教舞碟子太监之人孙光祖等, 每人每月租银以四两五钱计。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六月二十日“郎中费扬古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题本”:
(五月初一)当日, 准郎中兼云麾使苏博来文, 支给授艺教习(音译)周友德、 乐以德, 教学弹琴太监之教习朱志清、 孙光组……给卿客李玉油缸青靴子一双……给教习王正祥绒缨子凉帽一。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七月二十二日“李孝生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问题的题本”中 :
给景山授艺教习王国川、 王世元、 金有成、 张文灿、 唐国俊……景山卿客古大伦、 申次连、 秦希范……(二十六日)教学艺诸太监之教习……教学弹乐之太监朱之清、 孙光组、 钟其道、 吕文德、 李万仓、 教习杂耍(音译)之教习张国柱……每人每日按一钱五分计……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初六“恰金泰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问题的本”中提到:
准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来文, 学艺处食八两钱粮之教习二、 食四两五钱之教习十三、 食四两之教习一……
承上可知, 最晚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内廷已经有专门负责教授太监技艺的教习。 自是时起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 其人数不断增加、 称呼上有教习、 卿客之分; 教授技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从早期的弹琴到后期的舞碟子、 杂耍和昆腔、 弋腔等大型戏曲, 名目繁多; 根据教授技艺的不同, 所发放的薪酬也有高低之分。 体现了一个演剧机构渐趋形成、 逐步扩张, 管理体制日渐完备的过程。 总体看来, 教习、 卿客的人事关系隶属之机构只有两处: 南府和景山。 日后乾隆年间的南府、 景山之外学制度, 正是在此教习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保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问题的本”中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
准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来文, 学艺处食八两钱粮之教习一、 食四两五钱之教习十、 食四两之教习一……准管理景山学艺人之李深贵等来文, 学艺处食八两钱粮之教习三、 食六两之教习一、 食五两之教习四、 食四两之教习三十五、 食三两之教习二十一……准学艺处治仪正苏博来文, 六郎庄学艺处食四两钱粮之教习七、 食三两之教习四十一。
此时的宫廷演剧机构, 在南府、 景山之外又多了一处可以与之平行并列, 名为六郎庄学艺处的所在。 这一名称不见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之前的档案, 在此后的清宫文献记载中亦杳如黄鹤。 对此, 朱家溍、 丁汝琴的看法是“西郊六郎庄毗邻畅春园, 当是康熙帝驻跸皇家园林畅春园时承应戏差所用”[5]17。 其解释似乎失于简略, 它虽然可以回答六郎庄学艺处何以出现, 却不能充分说明六郎庄学艺处何以消失, 也缺乏对这一特殊演剧机构的深度把握。
从前述资料中统计可知,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府教习为12人, 景山教习为64人, 而六郎庄学艺处教习人数则为48人, 人数虽不如景山之多, 但亦是南府之4倍, 规模不可谓不大。 如此重要的演剧机构, 在上举乾隆十九年档案资料及乾隆五十年(1785年)《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中都未提及。 详细记载后世嘉道以降演剧活动的《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中也只记有南府、 景山和昇平署, 未见六郎庄之名。 相较于南府、 景山的教习制度都于乾隆年间顺利发展为机构庞大、 人员众多的外学, 六郎庄学艺处却于清宫演剧相关文献中消失, 这不得不使人生疑。 笔者以为, 这一变化应该既与畅春园在清代皇室宫外活动中的地位变动有关, 也受制于六郎庄演艺人员所从事之表演的特殊性。
2 畅春园在皇室活动中地位的变迁与六郎庄演剧
六郎庄今属北京海淀区海淀镇, 位于玉泉山脚下, 紧靠昆明湖东南角, 西北方为颐和园, 东临畅春园。 清代后期, 为就近服务于常驻颐和园的皇帝和太后, 都察院在此设有衙门, 荣禄和张之洞等重臣也在六郎庄建设过别墅。 因其位置正处于清代“三山五园”区域之中, 故而六郎庄参与皇室生活可谓得天独厚。 有清一代, 六郎庄与清代皇室宫外活动的联系也确实非常紧密。 畅春园则是对其影响最密切的皇家园林。
“三山五园”中, 畅春园最早修建, 大约落成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二十六年(1687年)间, 建成之后便一直充当康熙帝集休养、 行政为一体的“御园理政”之所在。 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首次驻跸畅春园至六十一年(1722年)于此驾崩, 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康熙帝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都会奉请皇太后到畅春园度过上元节, 并赐宴外藩王公大臣; 二月份巡视京畿后再回到畅春园; 四、 五月份启程巡幸塞外或避暑山庄, 九、 十月份返京后仍驻畅春园, 年底回宫过年。 每年居住时间大概为170天, 在此召见臣僚、 任免官员、 勾决人犯、 策试选士、 接见使臣、 举办千叟宴。 此外, 康熙还曾奉请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于园内长期供养, 且命皇子于园内无逸斋中读书。 此时的畅春园可谓皇室的一处重要活动中心。[6]与之毗邻的六郎庄受其影响而出现为皇室提供表演娱乐的演剧机构亦可谓合乎情理。
限于相关档案资料的匮乏, 六郎庄演剧活动在此时的痕迹殊难考证。 只能从残存史料中窥见蛛丝马迹。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六十万寿时, 六郎庄真武庙曾作为一处戏台场所出现。
六郎庄真武庙的修建, 见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内务府总管赫奕的奏折[7]:
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据曹寅家人陈佐呈称: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间, 奉大人谕……六郎庄真武庙, 配殿六间, 和尚住房八间, 用银一千四百三十五两二钱; 在六郎庄修造园户住房三十间, 用银一千两……(译自内务府满文奏销档)
负责建庙的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应是在督造畅春园西园之余所建。 当地传说康熙曾册封此地为“敕赐静安院”, 并为之作匾悬于门首, 且镌有“康熙御笔之宝”字样。 六郎庄真武庙里曾立有相关碑刻, 但1966年被磨平改为六郎庄烈士纪念碑。[8]
神庙与戏台自古以来就呈现出高度融合的面貌, 清代真武神庙被作为剧场使用的情况更是相当普遍, 多地真武庙都建有戏台, 如太原高家堡村真武神魔戏台等。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万寿庆典时曾于神武门至畅春园路旁大摆戏台, “辇道所经数十里内, 结彩张灯, 杂陈百戏”。 宋骏业、 王翚、 冷枚、 王原祁所绘的《万寿盛典图》中描绘了从西直门外到畅春园前这段路程中, 巡捕三营在真武庙前戏台献戏的活动, 而巡捕三营正是康熙时负责畅春园守备工作的机构。 朱家溍《〈万寿图〉中的戏曲表演写实》中对此有分析: 戏台为五脊揭山式、 后台卷棚式。 台上上演的是《金貂记·北诈》一出。[9]虽然提供表演的应该是外请的民间戏班, 而非六郎庄学艺处伶人自己, 但从中亦可看出此时六郎庄在戏剧演出方面的活跃。
这种情况在康熙帝驾崩后发生了较大变化。 不知出于何故, 康熙的接班人雍正帝在位十三年间, 对自己父亲格外热衷的畅春园显示了出人意料的冷淡, 只有在去恩佑寺祭拜先皇、 为其荐福时才会驾临畅春园。 平日宫外的休养、 行政则转移至圆明园; 加之雍正帝生母早逝, 所以畅春园供奉皇太后之功能也不复启用。 后来到乾隆朝虽然仍有于畅春园奉养东朝之事, 但乾隆帝本人平日依然是以圆明园为活动中心。 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崇庆皇太后去世后, 乾隆帝下旨将畅春园与圆明园之功能做了明确制度化, 规定:
若圆明园之正大光明殿, 则自皇考世宗宪皇帝爰及朕躬, 五十余年莅官听政于此……所当传之奕禩子孙, 为御园理政办事之所……若畅春园, 则距圆明园甚近, 事奉东朝, 问安视膳, 莫便于此, 我子孙亦当世守勿改。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二六,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丙申)
此后, 畅春园的功能被固定为奉养皇太后。 皇帝的宫外休养、 行政任务被赋予圆明园承担。 而嘉庆生母早逝, 畅春园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无皇太后可奉。 至道光年, 畅春园因年久失修又被道光帝剥夺了奉养皇太后的资格, 此后畅春园便彻底失去了成为皇室生活中心区域的可能[10]:
惟是畅春园自丁酉年扃护以后, 迄今又阅数十年, 殿宇墙垣多就倾敧, 池沼亦皆湮塞。 ……朕再四酌度, 绮春园在圆明园之左, 相距咫尺, 视膳问安, 较之畅春园更为密迩……当于近奉东朝之旨尤相契合也。(《清宣宗实录》卷一八, 道光元年五月戊辰)
可以看出, 在康熙之后畅春园的核心地位总体呈下滑趋势, 因之而兴的六郎庄演剧活动自然也随之渐趋沉寂, 在后世清宫相关戏曲演出中被边缘化。 但若以此作为六郎庄学艺处消失的原因, 似仍不足。 雍正之后, 乾隆帝因为奉养皇太后的缘故仍有驾临畅春园的记载。 乾隆二年(1737年)畅春园也曾有庙会之类的活动。[11]以乾隆帝崇尚浮华、 热爱戏曲的性格做派, 为何没有再次重振六郎庄学艺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不得不讨论六郎庄学艺处的人员所授受传承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技艺。
3 六郎庄童子棍的小戏表演形式
光绪年间《内务府承应各项香会花名册》中记载有一批京城香会, 曾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二十四年(1898年)间参与内务府承应活动。 这些香会的承应节目包括五虎棍、 少林棍、 秧歌、 太平歌词、 太平花鼓、 舞狮等。 其中记载有“六郎庄村童子棍会”四十人[12]:
前引: 何恒福、 邱德山、 刘广福、 阎德顺。
会首: 刘福寿、 董文徵、 苏彭年、 周永寿、 杨长奎、 田兴义。
文场: 周广玉、 周广喜、 刘文喜、 杨浦庆、 高顺立、 王成瑞、 杨玉海、 尹长海、 潘吉亮、 李永长。
武场: 薛长方、 蒋春荣、 王福善、 何长路、 潘吉兴、 刘续起、 苏彭连、 李文瑞、 董连增、 安文元、 刘万顺、 袁长顺、 薛长海、 于福珠、 王小仓、 葛福全、 谭吉庆、 王德山、 苏彭寿、 姜来小。
此外, 《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第44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恩赏日记档记载:
第23696页, 八月十七日, (赏)五虎棍教习吉星、 薛祥、 薛六、 安俊芝、 苏六羊五名每名银二十两……奎顺、 奎福、 五虎棍教习玉德、 广福每名传二两钱粮米二分。
第46册, 光绪三十年(1904年)恩赏日记档记载:
第24667页, (五月初五日)赏银……童子棍:广福、 玉德、 安文元、 潘吉兴、 苏彭寿、 蒋来福六名每名银二十两。
第24734页, (九月十七日)赏银……童子棍:广福、 玉德、 安文元、 潘吉兴、 苏彭寿、 蒋来福、 葛福全、 尹福、 何文禄九名每名银十两。
第24780页, (十月十五日)赏银……童子棍:广福、 玉德、 安文元、 潘吉兴、 苏彭寿、 蒋来福、 何常禄七名每名银八两。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旨意档记载:
第24841页, (十月初一日)童子棍:文元、 吉兴、 来福、 彭寿、 常禄每名赏食二两钱粮米。
通过文献中人员对比等可以看出, 晚清光绪年间昇平署内表演五虎棍并得以食宫廷钱粮的诸位教习, 正是出自六郎庄。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时隔184年, 六郎庄一名再次出现在了内廷档案之中, 却不再附以“学艺处”名号, 而是换成了“童子棍”。
童子棍, 又称五虎棍, 因表演者多为十来岁的孩童、 表演内容以斗五虎为中心而得名。 五虎棍表演之名亦非六郎庄独有, 今天传承下来的还有北京双榆树西里社区翰林院五虎棍、 河北黄骅市后街村五虎棍等。 大体来说, 各地五虎棍的表演形式与演出内容相差无几, 唯有历史渊源方面则说法不一。
流传至今的以关于六郎庄童子棍会的记载为相对可靠。 隋少甫、 王作楫《京都香会话春秋》[13]和朱佳、 顾军《六郎庄五虎棍保护与发展现状调查研究》[14]都有详细说明。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曾于2012年11月5日《夕阳红》节目播出了一档名为《五虎棍情缘》的电视节目; 北京卫视曾于2014年播出了一档名为《守望之六郎庄五虎棍·横扫二百年》的电视节目, 也记录了很多重要史料。
由于年世绵渺, 今日流传下来的关于棍会成立及发展的各种记载中亦有矛盾之处。 例如: 《京都香会话春秋》中记载棍会由村民阎发创立于乾隆年间, 称“六郎庄五虎棍童子会”, 后因受到淳亲王允佑赏识而改称“允佑万善老会”。 然而, 允佑卒于雍正八年(1730年)(清史稿卷零零九世宗本纪), 不可能于乾隆年间收编该会。 此外庄亲王允禄曾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万寿时, 于自己府第门外的大街上搭建戏台, 为皇父祝寿, 上演过《安天会》中“北饯”一出。[9]允禄还曾在乾隆年间与张照“兼领乐部”, 组织周祥钰等翰院词臣编纂节庆戏《月令承应》 《法宫雅奏》 《九九大庆》, 以及宫廷大戏《劝善金科》 《升平宝筏》 《鼎峙春秋》等, 或许收编奉齐天大圣孙悟空为祖师爷的五虎棍会的人实是允禄亦未可知。
《六郎庄五虎棍保护与发展现状调查研究》中称棍会由村民阎发创立于康熙年间, 不知以何为根据。 电视节目《五虎棍情缘》中称其成立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 更似传说之谈。 此外, 电视节目《守望之六郎庄五虎棍横扫二百年》采访了六郎庄童子棍会成员, 棍会会首展示了棍会的皇家御制小拨旗。 旗上记载乾隆帝曾于辛巳年四月, 在寿福禅林寺观看五虎棍演出。 但《六郎庄五虎棍保护与发展现状调查研究》称此旗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六郎庄棍会重制。 考之旗上记载确实讹谬颇多: 既称为乾隆帝观看表演, 却又有“昇平署”与“孝端皇太后”字样。 孝端皇太后为皇太极之妻, 顺治帝之母, 卒于顺治六年(1649年), 昇平署于道光七年(1827年)方告成立, 前后与乾隆辛巳年(1761年)间相差遥远。 另外一个关于半份銮驾的传说, 更是岐说并出。 《六郎庄五虎棍保护与发展现状调查研究》中称是因供奉孝端皇太后尊像得到乾隆赏赐。 《京都香会话春秋》 《守望之六郎庄五虎棍横扫二百年》的记载则为允佑赐予。 此外当地还有所谓慈禧赐予銮驾等说, 皆莫能详辨。
幸运的是, 六郎庄五虎棍的演出传承未曾断绝, 两百年来一直为当地父老代代传习。 今日我们还可以完整考见其基本的舞台表演形式:
表演分为文场和武场。 武场表演以民间传说“赵匡胤斗董家五虎”为蓝本, 讲述尚未发迹的赵匡胤路过董家桥遭遇董家五虎收取过桥费, 遂与柴王及卖油郎郑子明3人合力斗败五虎为民除害的故事。 六郎庄五虎棍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为赵匡胤牵马的马童和为柴王推车的车夫, 共计 10人, 构成了武场表演的10大角色。 10大角色以对打、 群打的形式表现赵匡胤、 柴王等人斗败五虎、 三侠结义、 五虎从军等剧情。 此外, 会中还保留着其他五虎棍会早已失传的“藤牌”, 并能演练“群牌围(五虎持藤牌围攻车夫)”“对藤牌(任意一大角和一小角以藤牌对战)”“十人藤牌(10人皆持藤牌套打)”等独有套路。 据传该会原有武打套路72套, 目前传习下来的也有40余套。 文场乐器一般须有“一架单皮、 一面战鼓、 一副大锣、 两副大铙、 两副大钹、 两副大镲”参与演奏。(《六郎庄五虎棍保护与发展现状调查研究》)
五虎棍的表演中注重化妆和服饰, 勾脸仿京剧, 没有唱腔和对白。 虽有使用乐器参与演奏的文场, 但主要还是藉由棍棒、 藤牌、 单刀等做武打动作, 演绎赵匡胤斗董家五虎传说。 故事情节相对简单, 上场人数较少, 角色比较固定。 以戏曲类型区分, 至多属于“小戏”阶段的表演艺术。 《内务府承应各项香会花名册》列之于“杂耍”, 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中则将五虎棍教习列于“玩意教习”中。 这些命名虽不十分准确, 但从中可以看出时人对于六郎庄童子棍表演的认知和态度。
4 被忽视的宫廷表演、 被简化的文化生态
如果六郎庄童子棍会的成立时间果真可以上溯到康熙年间并由亲王收编发放钱粮, 那么是时六郎庄学艺处的教学活动可能主要集中于童子棍表演的武打动作演练, 缺乏戏曲应有的声腔、 唱词、 念白, 更无从谈起依照剧本做大型戏剧演出。 而缺乏“曲”之因素的六郎庄教习与传统意义上的戏曲从业人员也存在差距。
此外, 从前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所记载的教习们所食钱粮中也可以看出, 六郎庄学艺处与南府、 景山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南府教习12人, 1人食八两, 10人食四两五钱, 1人食四两; 景山教习64人, 3人食八两, 1人食六两, 4人食五两, 35人食四两, 21人食三两; 六郎庄教习48人, 却只有1人食四两, 剩余41人所食钱粮等级只有三两。 六郎庄学艺处的教习整体等级比南府、 景山要低, 这或许正是因为其所授受习练之表演与南府、 景山的昆腔、 弋腔大戏不可同日而语, 戏班结构简单, 表演之复杂性相对较低的缘故。 故而随着康熙驾崩后历代帝后对畅春园的需求下降, 作为机构的六郎庄学艺处由于其“非曲化”的特点, 走上了与南府、 景山完全不同的道路。
纵观整个清宫演剧历史, 虽然六郎庄学艺处的名称如昙花一现, 但与六郎庄相关的演出活动却从未止歇。 从康熙朝到光绪朝, 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六郎庄童子棍与宫廷演剧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若存若续、 绵延不绝的联系。 前述有关童子棍会的记载已足为证。 在此之外, 任万平《从清代〈万寿庆典图〉看乾隆时代的百戏》中曾经提到乾隆时宫廷百戏中的棍术表演: “这些历史画卷可以印证文献记载的大体有马术、 马戏……武术(棍术)……有的属于杂技与技击的综合表演内容。”[15]304其中记载的棍术表演是否即是六郎庄童子棍, 目前还无法断定, 然而考虑到六郎庄在宫廷演出方面曾经的活跃, 乾隆皇帝在选用百戏表演时点卯六郎庄棍会,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戏剧的发展历史中, 百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它不只包括乐舞形式的表演, 更包含角抵寻撞、 跳丸走索等杂技杂耍和“东海黄公”那种附带简单故事情节的戏剧演出。 随着后世包含唱词的乐舞与杂技渐渐分道而驰, 百戏也渐渐将音乐形式附庸化, 更多地依靠动作演出来炫人眼目。 这种不借助唱词而诉诸于动作的表演形式与马上得天下而推崇尚武精神的清代统治者似乎有着天然的契合。 前引康熙朝史料中就有“舞碟” “杂耍”之记载, 而到了乾隆朝更是将宫廷百戏表演推向一个巅峰。 《清昇平署志略》中就载有乾隆朝南府中设置“跳索学”专管散乐百戏。 到光绪年间, 慈禧太后屡次征召各香会承应表演, 都反映出清代百戏演出在宫廷演剧中的份量。
乾隆年间百戏表演还屡屡出现在清帝赐宴外邦使臣的场合, 既带有娱乐成分, 亦包含政治意图。 清代重臣和珅所做《钦定热河志·山庄灯词八首》 之八对此就有描述: “倒椀吞刀百戏陈, 升平歌里踏灯轮。 重裀列坐欢情洽, 底用通言藉舌人。” 外邦使节朝见, 纵使其中有通晓中国语言之人, 言语交流上到底还是存在不便, 此时对戏曲唱词的欣赏便退居二线, 而诉诸视觉的动作表演之地位则得到提升和凸显。
这种百戏竟陈于宫廷的娱乐文化生态下, 既包含丰富的武术技击因素, 又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六郎庄童子棍表演便具备了生存的土壤。 童子棍表演在故事情节和演出套路上对传统的百戏又有较大发展。 斗败五虎、 三侠结义、 五虎从军等剧情, 早已经突破了“东海黄公”式的单一场景、 向着真正的戏剧演出跨出了一大步。 而固守无唱词、 念白, 非语言表演等艺术传统, 又给予了其区别于戏曲演出的特殊审美品质。 假使我们能够暂时撇开传统戏曲研究的“曲本位”观念而换个角度来审视, 小戏范畴的六郎庄童子棍表演能够进入宫廷文化之中, 本身就代表着另一种演剧形态在历史发展中对被忽略、 被埋没之命运的抗争和努力。
5 结 语
作为演剧机构的六郎庄学艺处, 其迭起兴衰受制于清代帝后在戏曲表演方面嗜好的不同和皇室生活中心的变迁, 最终消失在南府、 景山、 昇平署辉煌演剧活动的背影下; 但作为演剧形式的六郎庄童子棍表演, 却以其独特的魅力在花雅大戏争奇斗艳、 各逞其能的两百年历史中传承不绝、 存续至今; 其与清代宫廷之间的联系并未随机构之消失而断绝, 甚至在清末又一度重回内廷、 再称供奉, 体现了清宫演剧外学制度非线性的动态变迁, 也为我们展现了以往被简单化和同质化表述之下的清宫演剧娱乐文化真实、 复杂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