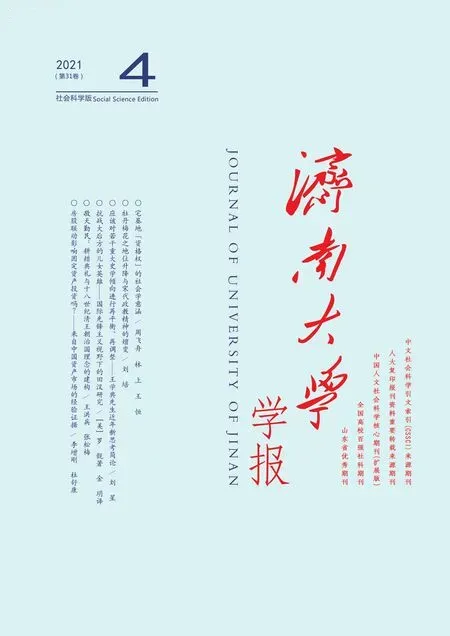《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若干基本问题考辨
阳 勇
(遵义师范学院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贵州 遵义 563006)
长征中,《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刊发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以下简称《原则指示》)。对中央红军长征中开展的民族工作,《原则指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史和长征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数十年来《原则指示》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成果很少。什么机构发出了《原则指示》?发出《原则指示》目的何在?《原则指示》刊发于何时?这些都是研究《原则指示》首先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各有关著述涉及这些问题时,或错误表述,或含糊其辞,或避而不谈,以讹传讹者更可谓俯拾皆是。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考辨。
一、什么机构发出了《原则指示》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除《红星》报外并无其他载有《原则指示》的原始档案问世。《红星》报所载《原则指示》文末所署发文日期为“十一月廿九日”(1)除《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出版日期尚需考证外,本文所引《红星》报内容,文中均已列出篇名、出版日期和期号,不再注明出处。,但原文既无发文机构,也无受文单位。那么,什么机构发出了《原则指示》?
(一)关于《原则指示》发文机构的三种说法。
1.“红一方面军政治部”说。部分著述持此说。最早提出此说的应是《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以下简称《汇编》)。收录《原则指示》时,《汇编》为其拟定的标题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标题将“瑶苗”误为“苗瑶”,“的原则”误为“原则的”,编者特别在脚注中对题目作了说明:“此件所称红军政治部是红一方面军政治部。”(2)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汇编》是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汇编,成书较早,且为中央统战部所编,具有权威性。“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之说大抵滥觞于此。
2.“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说。绝大部分著述持此说。最早提出此说的应是《红军长征》。该书未收录《原则指示》,但收录了李富春1934年12月24日签发的《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以下简称《纪律检查的指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编者特别在脚注中对“本部对苗民指示”作了说明,“据现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似指1934年11月29日红星政治部(即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3)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第623页。。“红星政治部(即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一语,明确表达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原则指示》的意思。《红军长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之一,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由多家权威机构联合编纂出版,成书较早,权威性很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之说大抵滥觞于此。
3.“中共中央”说。《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邓小平年谱》)持此说。邓小平曾任《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中有大量关于《红星》报的记载。《邓小平年谱》称《红星》报第六期“刊发中共中央《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邓小平传》称“邓小平在《红星》报第六期及时地刊登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两书成书较晚,均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也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上述三种说法显然均系论者推定。至于所据为何,论者并未说明,笔者不得而知。
(二)《原则指示》应是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
1.“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之说错误。1934年1月中旬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所部改称中央红军,直属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指挥部指挥(6)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红军长征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第188页。。由此,红一方面军番号被撤销。1935年8月上旬沙窝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⑥,8月11日中革军委常务委员会发出通令,“特组织一方面军司令部”⑦。六届五中全会后直至沙窝会议,期间并不存在红一方面军番号,自然也就不存在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显然,《原则指示》不可能由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发出。
2.红军总政治部确实发出了《原则指示》,但并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发文机构。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在发出《纪律检查的指示》之前,除《原则指示》外无论中央还是红军总政治部均未发出任何“对苗民指示”。李富春曾于12月21日签发《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以下简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根据地工作的训令》要求“明确的执行本部对苗、瑶少数民族的指示”(7)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印:《军事文献》(二),延安:内部刊物,1942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1957年翻印,第688页。。“对苗、瑶少数民族的指示”指的就是《原则指示》,“本部”则表明红军总政治部是《原则指示》的发文机构。但是,红军总政治部并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发文机构。
3.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了《原则指示》。1935年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以下简称《民族工作的训令》)。《民族工作的训令》指出,“各政治部(处)应将本训令及中央、总政以前关于少数民族的原则的指示,提出在政治部讨论”(8)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第345页,第345页。。“中央、总政以前关于少数民族的原则的指示”显然并不是指《纪律检查的指示》,而是《原则指示》,另一方面也说明《原则指示》不是中央或红军总政治部单独发出,而是两者联合发出。
此外,《原则指示》完全符合“关于少数民族的原则的指示”这个条件。《原则指示》虽然特别突出了瑶族和苗族,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但并不只是针对瑶、苗两个民族,也是关于广西、贵州、湖南、云南等省所有少数民族的具有普适性的指示。《原则指示》第一句即说明:“瑶民(或称瑶子)苗民(或称苗子)等是散布在广西、贵州、湖南西部、云南等省的弱小民族,总的人口不下千万。”瑶民苗民后面的“等”表明《原则指示》并不只是针对瑶族和苗族,“人口不下千万”更表明《原则指示》并不只是针对瑶族和苗族。到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也仅有瑶族665933人,苗族2511339人(9)姚新武、尹华编:《中国常用人口数据》,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全国瑶苗人口合计不到318万。另一方面,《原则指示》符合“……原则的指示”的条件。《原则指示》全文千余字,内容丰富,并非单就民族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局部问题发出的带有特殊性的指示,如《纪律检查的指示》,而是就民族工作中涉及全局问题发出的带有普遍性、原则性的指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则指示》的标题是当时发文机构所拟。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发出《民族工作的训令》之前,除《原则指示》外无论中央、中革军委还是红军总政治部都没有发出过任何以“原则指示”或“原则的指示”为标题的关于民族工作的指示。不仅如此,在《原则指示》之前无论中央、中革军委还是红军总政治部甚至没有发出过以“原则指示”或“原则的指示”为标题的任何指示。
4.中央、红军总政治部有联合发出《原则指示》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原则指示》发出前,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于11月25日曾联合发出《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以下简称《政治命令》),文后署名为“党中央及总政治部”(10)④⑤⑥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第45页,第45页,第36页。;《原则指示》发出后,中央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于12月1日又联合发出《关于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致红一、三军团电》(以下简称《致红一、三军团电》),文后署名为“中央局 军委 总政”④。既然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能联合发出《政治命令》,中央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能联合发出《致红一、三军团电》,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十分重要的《原则指示》,当然是非常可能的。
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政治命令》的日期是11月25日,中央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致红一、三军团电》的日期是12月1日早晨“三时半”⑤,意图都是为了“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⑥,联合发文是为了强调《政治命令》《致红一、三军团电》的重要性。《原则指示》的发出在《政治命令》发出之后、《致红一、三军团电》发出之前,发出《原则指示》同样也是为了“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正如《致红一、三军团电》所强调的:“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⑦湘江战役关乎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当然有必要联合发出《原则指示》。
二、发出《原则指示》目的
在湘江战役正在紧张进行军情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为何要发出《原则指示》?《原则指示》为何特别突出了瑶苗?
学界普遍认为,发出《原则指示》是为了使中央红军顺利通过桂北地区。但没有深入探讨其所以然。本文认为,发出《原则指示》并特别突出瑶苗,既是当时争取以瑶苗为主的桂东北(11)桂东北位于广西东北部,历史上称桂北。本文认为使用“桂东北”更准确,可以更好地与“桂西北”区分开来,不致引起理解上的偏差。少数民族的支持以使红军顺利通过桂东北的需要,也是将来争取以苗族为主的湘鄂川黔边少数民族的支持以在湘鄂川黔边创造新苏区的需要。
1.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原则指示》并特别突出瑶苗,是在红军突破湘江之后,争取以瑶苗为主的桂东北少数民族的支持以顺利通过桂东北的需要。
桂东北是多民族聚居区,顺利通过桂东北需要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
红六军团西征时中革军委要求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军团参谋长李达“每晚均向总部报告”(12)李达:《寻找贺龙同志——忆红二、六军团会师》,《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红六军团西征于9月2日由湖南道县进入广西灌阳县,3日渡过灌江,4日在兴安县界首渡过湘江,接着进入全县西延(13)西延时属全县,1935年划归新建置的资源县。休整,7日从西延大埠头向兴安车田进发,10日全部离开车田进入湖南城步县。红六军团在兴安时,中革军委还曾于9月8日发出《关于红六军团今后行动的补充训令》对其进行指导。红六军团西征过广西,途经桂东北灌阳、全县、兴安三县,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对桂东北特别是灌阳等三县的政治、经济、民族等各方面情况应该是早就比较了解了的。
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前,彭德怀即曾于11月10日向中央提出改变行军计划的建议:“以争取我野战军全部由永南出武冈为有利,否则经西延、城步出会同,山势苛大险多狭道,大军团运动较困难,给养亦差。”(14)⑦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第26—27页,第36页。彭德怀回忆说:“我建议,……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纳。”(15)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杨尚昆回忆说:“彭德怀同志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红军可以避免进入西延山区。……但是博古、李德既不采纳,又不答复,执意沿着两个多月前红六军团开辟的行军路线前进。”(16)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中央红军不仅要渡过灌江与湘江,经过开阔地带和敌之部分堡垒,还要经过湘桂边界“粮食较缺乏”的都庞岭山区和越城岭山区,即将进行的是“最复杂的战役”,“任务是复杂与艰巨的”⑦。从《政治命令》来看,至迟到11月25日,对于通过桂东北的困难,包括粮食供应的困难,中央、红军总政治部是有着比较充分的认识的。
桂东北是多民族、多族群聚居地区,特别是在都庞岭、越城岭山区聚居着瑶、苗、侗、壮等少数民族。“红军到来之前,反动派大肆造谣诬蔑共产党和红军……是‘专杀瑶苗人的魔鬼’,总之把一切最恶毒的语言都集中到红军身上了。国民党还煽动和强迫群众躲进深山老林,企图困死红军于湘桂黔边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于敌人的造谣欺骗,当地的群众对红军十分恐惧,许多村寨空无一人。”(17)陈靖:《重走长征路》,北京:长征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显然,要顺利通过桂东北,中央红军需要争取桂东北少数民族的支持。仅就在“粮食较缺乏”的都庞岭、越城岭山区获取部队必需的粮食而言,中央红军也需要争取桂东北少数民族的支持。这是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原则指示》的原因之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事实上,中央红军在越城岭山区确实遭遇了许多困难,尤其是严重缺粮的问题。一是越城岭山区本就缺粮,二是桂军、反动当局派出密探故意纵火烧毁群众的粮食。不过,在红军的感召下,少数民族群众拿出不少粮食帮助红军渡过了难关。“进入湘桂边的西延山区。……部队连吃包谷也有困难。”(18)③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114页,第105页。“明天要是再找不到老百姓,我们就真要断粮了”。“反动派的罪行和红军奋不顾身救火的生动事迹教育了苗族群众”,“苗族群众把红军当成了救命恩人,纷纷把藏起来的粮食拿了出来”(19)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23页。。
2.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原则指示》并特别突出瑶苗,是将来争取以苗族为主的湘鄂川黔边少数民族的支持以在湘鄂川黔边创造新苏区的需要。
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计划,是到湘西去创建新苏区。“延安整风时,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③中央红军全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后,中革军委正式通知说战略转移是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造新苏区(20)李聚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这个计划直到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才被中央政治局放弃。
湘西与湖北、贵州、四川接壤,湘鄂川黔边是多民族聚居区。中央红军长征时湘鄂川黔边共有多少人口,各少数民族分别有多少人口?由于民国时期人口统计不那么真实,且对少数民族人口少有统计,1934年湘鄂川黔边准确的人口数和人口民族结构现已不得而知。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湘鄂渝黔边居住着土家、苗等37个民族,总人口数为14276524,其中土家族人口数为6712031,汉族人口数为4818986,苗族人口数为2015808,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数共计729699(21)王世枚:《武陵地区师资队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从以上数据来看,2000年在湘鄂渝黔边总人口中汉族人口占33.75%;少数民族人口共占66.25%,其中土家族人口占47.01%,苗族人口占14.12%,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5.11%。由此可以推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湘鄂渝黔边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土家族是湘鄂渝黔边最主要的少数民族。
到达湘西后,中央红军需要创造新苏区。既然湘鄂川黔边居住着30多个少数民族,又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红军要在那里创造新苏区,当然必须大力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这是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原则指示》的原因之二。
土家族是湘鄂川黔边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按理说,在湘鄂川黔边中央红军最需要争取的是土家族而不是苗族,那为何《原则指示》特别突出的却是苗族而不是土家族?一方面,当时土家族尚未得到国家承认和社会认可,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严重的民族歧视之下,许多土家人更改、隐瞒了民族成份。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社会并不了解土家族,土家人往往被误认为是苗人。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将苗族误认为湘鄂川黔边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这是历史的误会,无可厚非。此前于1934年7月作出的《关于苗族问题决议》,同样是为了适应红三军创建黔东苏区的现实需要而产生,同样因为历史的误会,在土家族占黔东苏区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出台的却是《关于苗族问题决议》。
三、《原则指示》刊发于何时?
目前可见的《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报头处受损严重,以致出版日期完全无法辨认。那么,《原则指示》何时在《红星》报上刊发?
关于《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出版时间的五种说法。
1.“11月”说。《党在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持此说。据该文文后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载1934年11月《红星》报第6期。”(22)赵雅琴、田正惠、莫宝文:《党在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2.“11月28日”说。《中央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篇名索引(个人部分)》持此说。据该书,《红星》报第六期出版日期为“1934、11、28”(23)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篇名索引(个人部分)》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726页。。
3.“12月29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持此说。该书第二册收录了刊发于《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的《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等三篇文章,文后均特别说明“根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红星报》刊印”(24)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4.“12月上旬”说。《邓小平年谱》持此说。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34年“12月上旬”,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油印版第六期出版”(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13页。。
5.“12月上旬在龙胜期间”说。《邓小平传》持此说。据《邓小平传》记载:“十二月五日……中午,队伍来到著名的苗山——老山界下。……邓小平……连夜翻过了山顶。越过老山界后,进入广西的龙胜县。这里是瑶族、苗族和侗族聚居地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造谣,红军到达之前,不少群众躲避到山上去了。为了让广大红军指战员了解和掌握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邓小平在《红星》报第六期及时地刊登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第230页。《邓小平传》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其一,邓小平12月6日越过老山界后进入龙胜县;其二,邓小平进入龙胜后出版了《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邓小平传》实际上提出了《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是12月上旬在龙胜期间出版的观点。
本文认为,《原则指示》在11月29日至12月上旬间刊发于《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应是比较准确、稳妥的说法。
1.“11月28日”之说错误。《红星》报第六期所载《原则指示》文末所署发文日期为“十一月廿九日”,如果《红星》报第六期于11月28日即已出版,怎么可能刊发第二天才发出的《原则指示》?显然,“11月28日”之说是错误的。
2.“12月29日”之说错误。《红星》报1934年12月25日出版第七期同样毋庸置疑。既然如此,第六期又怎么可能在第七期出版四日后出版?显然,“12月29日”之说也是错误的。
3.“11月”之说、“12月上旬”之说、“12月上旬在龙胜期间”之说都不能令人信服,值得商榷。
(1)对“11月”之说,《党在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没有给出理由,该说不能排除12月1日至24日《红星》报刊发《原则指示》的可能。
(2)对“12月上旬”之说,《邓小平年谱》也没有给出理由,该说既不能排除11月29日至30日《红星》报刊发《原则指示》的可能,也不能排除12月11日至24日《红星》报刊发《原则指示》的可能。
(3)对“12月上旬在龙胜期间”之说,《邓小平传》倒是给出了理由:因为龙胜是瑶族、苗族、侗族聚居区,群众躲到山里去了,为了做好民族工作,所以邓小平在《红星》报第六期及时刊发了《原则指示》。不过,这并非可以支撑起该说的确凿证据。而且,这样的理由也太过苍白。试问,《原则指示》11月29日即已发出,邓小平为何要拖延至进入龙胜后才在《红星》报上刊发?再者说,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原则指示》时并没有计划经过龙胜。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实际途经灌阳、全县、兴安、龙胜四县,但原本计划如红六军团一样经灌阳、全县、兴安三县然后北上进入湖南城步等地,并没有计划经过龙胜。中央红军在西延集结休整时,湖南军阀何键已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等地调去重兵。中央红军如按原计划北上进入城步等地必遭湘军和桂军合击,因此中革军委才改变计划于12月4日下午电令“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27)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第49页。。陈伯钧回忆说:“过了湘江以后,本来还想向北转到二方面军那里去,结果城步、武冈都到了敌人,把去路给堵住了。没有办法向北,只好向西。”(28)陈伯钧:《陈伯钧日记·文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5页。莫文骅回忆说:“本来,红军总部拟在西延地区休整一两天,然后向湘西前进,与贺龙、肖克率领的红2、6军团会合,但敌人已于12月2日、3日占领了界首、资源一线,全州的敌人也紧追上来,将红军紧紧缠住,另外,蒋介石也急调湘军向新宁、城步、武冈一带转移,妄图配合桂军,前堵后追,于湘桂边境歼灭我军。在这种情势下,我军决定尽快脱离敌人,放弃从西延地域出湖南城步的打算,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29)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可见,该说既不能排除11月29日至12月5日《红星》报刊发《原则指示》的可能,也不能排除12月11日至24日《红星》报刊发《原则指示》的可能。
4.11月29日或30日《原则指示》刊发于《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的可能性非常大,11月29日至12月上旬刊出的说法相对稳妥。
《红星》报第六期不可能迟至12月10日以后出版。长征中《红星》报上所有其他文章,所署写作日期或发文日期与出版日期相距时间最长仅为七日(30)《红星》报1934年11月11日第三期社论《关于目前居民中的工作》写作日期为“十一月四日”,与出版日期相距七日。。《原则指示》如迟至12月11日才刊发则距发出指示已有十二日,《红星》报将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的重要指示拖延这么久才刊发的可能性很小。又,在湘江战役紧张进行、军情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原则指示》的主要意图,是要帮助中央红军“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争取以瑶苗为主的桂东北少数民族的支持以顺利通过桂东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红军总政治部的喉舌,《红星》报不可能认识不到《原则指示》的重要性,不可能认识不到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对《原则指示》的高度重视,一定会力争尽快刊发,绝无延宕之理。
事实上,无论是发出《原则指示》时还是以后,红军总政治部对《原则指示》都是高度重视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涉及民族问题,红军总政治部总会要求传达、执行、讨论《原则指示》。如前文所引《根据地工作的训令》要求“明确的执行本部对苗、瑶少数民族的指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各政治部(处)应将本训令及中央、总政以前关于少数民族的原则的指示,提出在政治部讨论”。《纪律检查的指示》,尤其是《民族工作的训令》,对于中央红军长征中做好民族工作不可谓不重要。不过,无论是《纪律检查的指示》还是更重要的《民族工作的训令》,在《红星》报看来其重要性也是远不及《原则指示》,《红星》报都没有刊发,只刊发了《原则指示》,而且安排在头版刊发。这表明《红星》报对《原则指示》的重要性和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对《原则指示》的高度重视有着充分认识,一定会力争尽快刊发,绝无延宕之理。
因此,本文认为,《红星》报第六期11月29日或30日出版刊发《原则指示》不仅可能,而且可能性非常大。
首先,《原则指示》系11月29日发出,《红星》报当日即刊发是可能的(31)文章完成当日即在《红星》报刊发的情况不少。如1935年2月10日第九期社论《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所署写作日期就是“二月十日”,1935年4月10日第十四期社论《一切为着创造新苏区》所署写作日期也是“四月十日”。。长征中《红星》报出版时间并不固定,两期之前相隔最短仅两天,最长达二十六天(32)《红星》报1935年5月30日第十八期与1935年6月1日第十九期相隔两日,1935年3月10日第十二期与1935年4月5日第十三期相隔二十六日。,《红星》报第六期于11月29日或30日出版,也不会因与第五期、第七期相隔时间过短或过长而不可能。
从出版所需稿件准备情况、刻版油印用时情况来看,《红星》报第六期在11月29日或30日出版的可能性很大。《红星》报第六期所刊诸文均没有谈及11月29日以后才发生的事情。第五期在11月25日已经出版,除《原则指示》外出版第六期所需其他稿件完全可能在11月29日前即已准备好。11月29日收到《原则指示》后,《红星》报只需刻版油印即可。据长征中担任红军总政治部文书科科长的赵发生回忆:长征中《红星》报“发行量改为五、六百份”。“大约三小时之后,版面刻好,再叫两位负责油印同志接班。”(33)赵发生:《长征号角〈红星报〉》,《新闻三昧》,1996年第9期。刻版“大约三小时”,两个人油印五六百份报纸也不需要多长时间,刻版油印全部工作只需数小时即可完成。
从《红星》报第六期所刊文章的主题来看,刊发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湘江战役顺利进行,《红星》报第六期在11月29日或30日出版的可能性非常大。
前文已述,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原则指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中央红军“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在第二版和第四版,从题名即可看出,刊发《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掉队——真危险》《再不要掉队了!——黄英南同志的教训》《反对故意掉队》《把巩固部队的飞机送给我们的模范连》这几篇文章的目的,都是为了消灭掉队落伍现象以巩固部队。《发扬阶级友爱》一文表扬先进连队和模范个人发扬阶级友爱做好了收容工作,刊发该文同样是为了消灭掉队落伍现象以巩固部队。湘江战役开始前,中央红军在湘南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掉队落伍现象。《红星》报很容易认识到,在“任务是复杂与艰巨的”“最复杂的战役”湘江战役中掉队落伍现象可能会更加严重。显而易见,《红星》报第六期刊发这几篇文章是希望消灭掉队落伍现象以保障湘江战役的顺利进行。
在第三版,《红星》报不仅刊发《学习“攻”团三营的河川战斗》《负伤不下火线战到最后一滴血》《怕死的份子大家都要反对》《模范的指挥员值得大家学习》等文大力表彰战斗英雄群体和个人,严厉批评在战斗中动摇怕死的坏分子,还专门设计了统领这几篇文章的栏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决消灭敌人!”显而易见,《红星》报第六期刊发这几篇文章是希望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以保障湘江战役的顺利进行。
可见,《红星》报出版第六期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湘江战役顺利进行。湘江战役是11月25日开始,12月1日结束的(34)关于湘江战役起止时间有多种说法,本文从11月25日至12月1日之说。。为了保障湘江战役的顺利进行,《红星》报第六期在11月29日或30日出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尽管《红星》报一定会力争尽快刊发《原则指示》,且第六期于11月29日或30日出版刊发《原则指示》的可能性非常大,但12月上旬出版刊发《原则指示》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被排除,只是较之11月29日或30日可能性要小,且日期越靠后可能性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