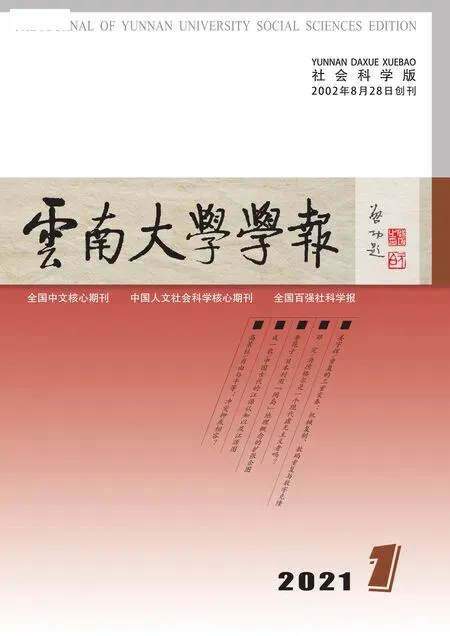“辞尚体要”说与宋代文风的嬗变
白建忠
[山西师范大学,临汾 041004]
“辞尚体要”一语最早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篇,其言云:“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孔颖达曰:“商之旧俗靡靡然好相随顺,利口辩捷阿谀顺旨者惟以为贤。”(1)孔安国 传,孔颖达 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54页。商朝末年,纣王无道,阿谀逢迎、巧言无实之风盛行,“辞尚体要”是周康王册命毕公之语,是针对“商之旧俗”提出来的。 从近些年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对《文心雕龙》“体要”的阐释。其实,“辞尚体要”说对宋代以迄清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几乎付诸阙如。本文在阐释“辞尚体要”含义的基础上,主要围绕“辞尚体要”说与宋代文风的嬗变展开论述。
一、“辞尚体要”的内涵及其文章学价值
何谓“体”?何谓“要”呢?汉代孔安国曰:“政以仁义为常,辞以体实为要,故贵尚之。”孔安国将“体要”解释为“体实为要”。唐代孔颖达曰:“为政贵在有常,言辞尚其体实要约,当不惟好其奇异。”(2)孔安国 传,孔颖达 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754页。孔颖达将“体要”解释为“体实要约”,显然与孔安国的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与孔安国不同的是,孔颖达将“要”解释为“要约”。但究竟何谓“体实”?二人均未作出更明确的阐释。到了宋、明时代,这种疑惑才逐渐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答。宋代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三《文类·大体》曰:“体如人之有体焉,四支与身皆体也。又作屋作文,皆有大指,如曰‘辞尚体要’是也。”(3)程大昌著,张海鹏订:《演繁露续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页。宋代蔡沈《书经集传》卷六曰:“趣完具而已之谓体,恒体所会之谓要。”(4)蔡沈:《书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明代王樵在宋人的基础上,对“体要”二字作了更详细的诠释,其《尚书日记》卷十五说:“趣谓辞之指趣也,趣不完具,则未能达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则为枝辞衍说,皆不可谓之体。众体所会之谓要,人身上有领,下有要,乃体之关会处,事理之有要亦犹是也。”(5)王樵:《尚书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45页。宋、明人探本溯源,指出“体”“要”都与人的身体有关,颇中肯綮。许慎《说文解字》云:“体,总十二属也。”段玉裁指出十二属即顶、面、颐、肩、脊、手、足等人体的十二个部位。(6)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广雅·释亲》云:“体,身也。”(7)王念孙著,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3页。体,全身的总称,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趣”是指旨趣,文章所表达的旨趣有序、切实、完备谓之“体”。孔安国、孔颖达都将“体”解释为“体实”,就是指言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
《说文解字》以“要”为“腰”的本字:“要,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素问·痿论》注:“要者,身之大关节,所以司屈伸。”殷仲文曰:“以一管众为要。”(8)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8页。腰在人的身体中部,乃“身之大关节”,“体之关会处”,后引申为要领、要点、关键。综合以上各家之说,在《尚书》中,“辞尚体要”是指文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
“辞尚体要”说被真正运用到文章理论之中,当首推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文心雕龙》中,“体要”一词共出现了9次:
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征圣》)
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诠赋》)
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奏启》)
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风骨》)
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序志》)(9)本文所引《文心雕龙》语均出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以下不另注。
大致来说,刘勰笔下的“体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继承了《尚书》中的意思,刘勰《序志》篇主张“宜体于要”,就是指文辞要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如《镕裁》篇说:“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万趣会文,不离辞情。”刘勰直接用人体作喻,指出各种情趣有序地会合成一篇文章,就像人的许多关节组成身体一样。还有《章句》篇曰:“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又曰:“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中的“体”都是指一篇完整有序的文章,就像身体一样。“总义以包体”与“意穷而成体”的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是指一篇文章所表达的旨趣有序完整才能“成体”。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没有原封不动地搬用“辞尚体要”说,第二层含义是指刘勰从文体的角度赋予了“辞尚体要”以新的含义,使“辞尚体要”说的内涵有所拓展。左东岭先生在解释《征圣》篇中的“体要”时说:“后来所有的文体, 都源于经书, 所谓‘百家腾跃, 终入环内’。按照这个思路, 则刘勰的体要其实也就是体‘经书’之要了。因为‘文能宗经, 体有六义’。这是刘勰将《尚书》的体要向文体的体要所做的一次引伸。”(10)左东岭:《〈文心雕龙〉范畴研究的重构与解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85页。左先生的见解很合理。毋庸置疑,刘勰对文体十分重视,《文心雕龙》的20篇文体论,刘勰称之为“文之纲领”。他写文体的四项内容中,其中的“敷理以举统”很重要,“敷理以举统”是指每种文体遵循的根本的写作规范,若能按照规范来写作,刘勰称之为“正体”,否则就成了“变体”“谬体”“讹体”。刘勰将“敷理以举统”往往称之为“大体”“大要”“枢要”等,有时甚至直接称之为“体要”,如前文所引《诠赋》与《奏启》篇中的“体要”。在《文心雕龙》中,“要”大多是指要点、关键,(11)参见周振甫:《文心雕龙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3页。如《奏启》篇说:“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刘勰总结“奏”的体制要求,其中之一是“治繁总要”,整理繁杂,抓住要领。总之,从文体学的视角来看,刘勰所谓的“体要”,主要是指各种文体在情志、事义、辞采、气势、风格、宫商等方面的规格要求,(12)参见陈博涵:《释“体要”——〈文心雕龙〉“体要”范畴之重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16页。这就是“刘勰将《尚书》的体要向文体的体要所做的一次引伸”。(13)刘勰的这一观念,影响了后代的人,如宋代李廌《答赵士舞徳茂宣义论宏词书》曰:“故训、典、书、诏、赦、令、文、赋、诗、骚、箴、诫、赞、颂、乐章、玉牒、露布、羽檄、疏议、表笺、碑铭、谥诔,各缘事类,以别其目,各尚体要,以称其实。”李氏列举二十多种文体,并指出“各尚体要,以称其实”,意谓每种文体都要遵循各自的写作规范。
刘勰为何如此重视“辞尚体要”说,与他所面临的文化背景有关。首先是南朝以来文风的渐趋诡异讹滥,即《通变》篇所说的“从质及讹,弥近弥澹”,《定势》篇所说的“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稍晚于刘勰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也说:“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14)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9页。文章追新逐异,“言隐于荣华”,使作者的旨趣不能完整、准确地通过言辞表达出来。其次就是东汉以来文体学的逐渐兴盛,当代有学者指出:“东汉以来文体学繁荣。……从曹丕《典论·论文》开始,到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直至刘勰《文心雕龙》,文体分类和文体批评开始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式。”(15)参见吴承学、何诗海:《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第28页。由于人们对文体愈来愈重视,辨体观念也就随之产生了,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刘勰针对“文体解散”之弊,又重拾《尚书》中的“辞尚体要”以“详其本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辞尚体要”说的重新强调与阐释,赋予了“辞尚体要”说在中国古代文章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二、“辞尚体要”说与北宋古文革新的成功
“辞尚体要”说的文章理论价值经刘勰揭橥之后,对宋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唐代,明确指出“辞尚体要”的人并不多。可以说,“辞尚体要”说对唐代的文风几乎未产生影响。与唐代相比,宋代很重视“辞尚体要”说。由上述可知,从“辞尚体要”说最初提出的背景来看,它就与帝王、朝廷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为后代帝王和朝廷利用“辞尚体要”说以扭转浮华不实的文风所继承。北宋初年,杨亿等人所倡导的“西昆体”风靡一时,其诗文宗法李商隐,语辞华赡,崇尚对偶,“极一时之丽”。(1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307页。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下诏禁文体浮艳,曰:“夫博闻强识,岂可读非圣之书;修辞立诚,安可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为主,典训是师,无尚空言,当遵体要。……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素风。”(17)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六册,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41页。“无尚空言,当遵体要”,指的就是“辞尚体要”。真宗此诏实为杨亿等人的诗歌寓含讽意而发,但未必不是针对整个文坛风气的。宋真宗的诏书,强调为文要有助于教化,重视实用,反对浮靡空洞的文风。宋真宗本人也欣赏体要之文,《职官分纪》卷十五记载:“祥符三年,直史馆陈靖上《祥符超古颂》,因对言:今三馆学士,皆年少俊迈,恐见而贻诮。上谓宰臣曰:自古为之,风格随时而变。今之词人,志尚体要,有古雅之风。”(18)孙逢吉:《职官分纪》,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9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77页。宋真宗还说作文:“当戒于好奇而尚浮靡,好奇则失实,尚浮靡则少理也。”(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94页。这是宋朝皇帝第一次直接干预文风,也开启了宋代帝王和朝廷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文风的先河,为古文的发展做了很好地准备。
宋真宗虽然倡导“体要”,但效果并不明显,“自景德后,文字以雕靡相尚,一时学者向之”。(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482页。至宋仁宗初年,文风未发生根本变化。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曰:“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21)吴曾:《能改斋漫录》,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418页。宋仁宗执政后,曾多次下诏,反对浮华靡曼之文。景祐五年,宋仁宗下《谕天下士勤修学业诏》:“贡举人等,自今当研覃古义,景慕前良,为学务于资深,属词尚乎体要,宗师雅正,斥去浮华。”(22)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295页。此诏明确指出为文要“尚乎体要”。宋仁宗庆历八年,针对自庆历二年以来“国子监生,诗赋即以汗漫无体为高,策论即以激讦肆意为工,中外相传,愈远愈滥”,礼部贡院言:“古今文章,务先体要”。(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946页。国子监生的诗、赋、策、论是指宋仁宗庆历年间流行于太学与科场的一种文体,即“太学体”,以石介为代表。石介于庆历二年起担任国子监直讲,不满于杨亿等人的西昆体诗文,起而矫之,但又形成了一种奇涩怪诞的文风。石介希望通过“太学体”纠正当时的文风,但他并没有给古文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所以礼部贡院针对“太学体”之流弊,又不得不推出“古今文章,务先体要”加以引导。据《宋会要辑稿·选举》记载,当时以张方平等人为代表的贡院打击“太学体”,得到了宋仁宗皇帝的认可,后来又经过欧阳修的“痛排抑之”,“太学体”之弊端才摈黜殆尽。(24)参见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36页。
宋神宗时期,“初置大理寺,命李清臣为记。清臣以谓王者立政,以诏天下,必辞尚体要,则《书》为近”。(25)李攸:《宋朝事实》,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4页。李清臣,字邦直,历官至中书侍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说:“欧阳公(修)爱其文,以比苏轼。”(26)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08页。宋神宗时期,初置大理寺,命李清臣为记,李清臣认为王者临政,其诏书应学习《尚书》“辞尚体要”的风格。宋哲宗绍圣元年,贡举科目置宏词科,据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卷二记载,绍圣四年,宏词科的试题是《诫谕学者辞尚体要》,(27)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63页。这大概是古代科举学史上最早明确以“辞尚体要”命名的试题,与以前由朝廷直接降诏提倡“辞尚体要”说不同,这次是以试题的形式出现于考生的面前,更具有广泛性与普遍性,毋庸置疑,它对于当时文风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章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宋哲宗本人也赞成体要之文,吕陶代拟的《起居郎姚勔可中书舍人仍赐紫金鱼袋制》曰:“夫辞以体要为尚,庶几助风化之纯。”(28)吕陶:《净德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页。姚勔,字辉中,曾在宋哲宗年间担任中书舍人。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不仅北宋的帝王和朝廷强调“辞尚体要”,就是文人臣子对“辞尚体要”也十分重视。宋代古文革新的领导者或参与者大多主张作文须体要。欧阳修《回贺集贤韩学士启》称赞韩绛曰:“学通今古之渊源,言合质文之体要。”(29)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5册,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635页。曾巩《知制诰制二》曰:“维能守其所闻,可以辅予不逮;维能明于体要,可以见于文章。”(30)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72页。黄庭坚《朝奉郎通判泾州韩君墓志铭》赞扬韩复曰:“庄重寡言,作文词务体要”。(31)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8页。由欧阳修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苏轼,后来成为了宋代古文革新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苏轼说:“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32)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84页。“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33)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第87页。等等。还有王安石,出于欧阳修的门下,主张文学“务为有补于世”,他说:“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34)王安石著,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5页。二人虽然未明确主张“辞尚体要”说,但这些表述都与“辞尚体要”说的内涵很接近。
综上所述,在宋仁宗之后,历经英宗、神宗、哲宗(主要指元祐年间)几朝,经过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的不懈努力,北宋的文章创作出现了繁盛的局面。汪藻《苏魏公集序》曰:“宋兴百余年,文章之变屡矣。杨文公倡之于前,欧阳文忠公继之于后,至元丰、元祐间,斯文几千古而无遗恨矣,盖吾宋极盛之时也。”(35)汪藻:《浮溪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4页。北宋的文章创作之所以能渐趋繁盛之局面,古文革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有诸多因素使然,包括科举取士的标准以及文人的审美旨趣与创作追求等,尤其是帝王和朝廷利用诏书的干预也起了重要作用,陆游《尤延之尚书哀辞》评宋初的文风曰:“诏册施于朝廷兮,万里雷风;灏灏噩噩兮,始扫五季之雕虫。”(36)陆游著,马亚中校注:《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70页。“辞尚体要”说以其语出五经之一的《尚书》,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指导性作用。
三、“辞尚体要”说与北宋末年、 南宋初年文弊的反思
绍圣元年,宋哲宗亲政后,开始贬斥元祐党人。宋徽宗执政后,蔡京擅权,又紧承宋哲宗之后,禁锢“元祐学术”,三苏及门人文集遭禁。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云:“时禁元祐学术甚厉,而以剽剥颓闒熟烂为文。”(37)陆游著,马亚中校注:《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第313页。何谓“元祐学术”,历来说法不一,但它无疑包括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思想言论和文学,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一种健康的文风。宋徽宗时期,韩驹屡次进策论文,其《论时文之弊疏》指出当时的文风是“纂错以为工,繁杂以为美”,(3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71页。其《请慎择司文以风动天下疏》曰:“前日陛下制诏多士,词尚体要,使复三代之盛,甚大惠也。”徽宗初期,朝臣所作之诏书辞尚体要,但科举取士“违明诏,失圣意”,士人以浅易之文应选,“烦言碎词,刊落不尽”。韩驹又说:“仁宗之复古风,神考之立经义,比于陛下之欲词尚体要,可谓难矣,士犹勉力以副科举,而顺上之好恶,何则?利之所在,固众之所趋也。”(3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1册,第373页。韩驹认为“辞尚体要”之文风能否再次出现,与“上之好恶”有关。韩驹主张将“辞尚体要”与朝廷在科举取士方面的引导结合起来,恢复三代之文风指日可待,其《论文不可废疏》说:“至体格卑弱者,又曾不屏黜,此固宜其不勉者矣”,(40)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1册,第370页。《请慎择司文以风动天下疏》说:“欲士之深于文,则亦择司文者而已”。(4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1册,第374页。韩驹的建议得到了一定的回应,如宋徽宗政和四年,葛胜仲擢国子司业,科场文风有所改变。章倧《葛公行状》曰:“四年,(葛胜仲)擢国子司业。时兴学久,成均之士为文转相模仿,率一律,公恐其渐入卑陋,每考试必取卓然不群者置之上列,文格翕然大变。”(4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86册,第187页。但这种改变是暂时的。政和六年,宋徽宗又有《学校士能博通诗书礼乐置之上等御笔手诏》:“士牵于宾贡,蔽于流俗故习,尚秦、汉、隋、唐,而不见尧舜三代。比阅时文,观其志趣,率浅陋卑近,无足取者。”(4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5册,第178页。
宋徽宗时期,除了韩驹,还有李纲拟写的《诫谕学者辞尚体要诏》:
朕之待士至矣,比览贡士程文,猥酿不醇,气格卑弱,刻意以为高者,浮诞诙诡,而不协以中;骋辞以为辩者,支离蔓衍,而不根于理。文之不振,未有甚于此者,朕甚羞之。岂子大夫平日所以讲贯之者未至欤!抑偷取临时,务应有司之求,而怵于得失欤?夫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为之卫翼;本之固者,其发为英华必茂;源之深者,其流为波澜必远。子大夫其思所以完养意气本源者,博极古今,根柢仁义,《六经》之书、诸子百家之说,必深究而明辨之,则见于文辞者,体要兼备,宜有可观。朕有好爵,与尔縻之,可不勉欤!故兹诏谕,想宜知悉。(44)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460页。
李纲批评贡士之文章“猥酿不醇,气格卑弱”,“支离蔓衍,不根于理”,李纲继承孟子的“知言养气”、韩愈的“气盛言宜”,还有杜牧的“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等观点,指出作文应注重道德修养,以仁义为本,以辞采为辅,崇雅黜浮,体要兼备。北宋末年,国家日益衰弱,文章也步入衰世。杨万里《杉溪集后序》称宋徽宗时期“崇奸绌正”,以元祐学术为邪僻之学,“禁而锢之,盖斯文至此而一厄也”。(45)杨万里著,王琦珍整理:《杨万里诗文集》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04页。陈亮《书欧阳文粹后》说:“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46)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7页。政和、宣和属于宋徽宗时期。宋徽宗时期之文弊,于此可见矣。
宋室南渡后,宋高宗时期,文风基本上沿袭北宋末年的余风。宋高宗重用权相秦桧,又制造了“绍兴党禁”,文坛弥漫着谀佞之风,出现了所谓“文丐奔竞”的现象。(47)所谓“文丐”,顾名思义,以文讨乞,以谄诗谀文乞取官禄。参见沈松勤:《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第64页。这一时期,朝廷中的有识之士继续重申“辞尚体要”说,如翰林学士周麟之上奏曰:“今肄业之士服勤有年,秋试不远,臣愚欲望圣慈申饬儒臣,慎劝士类,戒志尚之不一,革文体之未纯,毋好髙以异论相矜,毋因陋以陈言自蔽,毋泥迂僻之习而失其正,毋纵浮靡之说而溺于夸。坯冶一陶,圣风云靡。将见四方俊茂试于有司者,无不丕应徯志,咸知以体要为宗。文弊既除,而文格益胜。用之以黼黻一代,羽翼六经,实斯文之幸。”(4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7册,第155页。周氏指出了当时的文弊,希望朝廷自上而下地“革文体之未纯”,“咸知以体要为宗”。
总之,北宋末年、南宋初年,一些文人臣子虽然继续重提“辞尚体要”说,但由于政治生态、文化环境、学术氛围以及科举取士政策的改变,尤其是帝王对文学的态度,会一定程度地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如宋徽宗本人“好雕虫之小技,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49)陈次升:《上徽宗论豫戒六事·稽古》,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9页。这些都是造成文章衰落的因素,改变了北宋以来古文健康发展的走向。
四、“辞尚体要”说与南宋文章的中兴与衰落
到了宋孝宗时期,自宋徽宗时期所出现的文弊才有所革除。宋孝宗好文,尤喜好苏轼文,称苏轼为“一代文章之宗”。他作为一代帝王,也提倡“辞尚体要”,其《进读正说转朝请郎告》赞扬木待问曰:“尔思好深湛,辞尚体要”。(50)崔敦诗:《崔舍人玉堂类稿·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1页。再加上宋孝宗本人励精图治,并下诏打击科场的谀佞之风,文章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有人冠之以“小元祐”的称号,(51)参见周密:《武林旧事·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如叶适的散文继承了欧阳修、苏轼的文风,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成就。宋孝宗时期所出现的文章中兴的局面,一方面与帝王的提倡有重要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有宋以来一直未中断的“辞尚体要”的呼声有关。
宋宁宗嘉定七年,曾从龙知贡举,疏奏:“比来循习成风,文气不振,学不务根秪,辞不尚体要,涉猎未精,议论疏陋,缀缉虽繁,气象萎薾。愿下臣此章,风厉中外,澄源正本,莫甚于斯。”(52)脱脱等著:《宋史》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48页。除此之外,“辞尚体要”在皇帝的诏书中也时有出现。如宋宁宗嘉泰二年:“朕践祚以来,再取士矣。今虽嬛然在疚,复遴选侍从台省之臣典司文枋,士有抱负,彪为词采,必刊去浮华,体要为尚,基异时之实用。”(53)潜说友原纂修,汪远孙校补,《咸淳临安志》第4册,据清道光十年重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43页。宋度宗咸淳七年:“近年士风盛而古意衰,习竞浮华,辞昧体要,真才不足以胜謏闻,雷同反得以蔽颖出,朕甚非之。”(54)潜说友原纂修,汪远孙校补,《咸淳临安志》第4册,第148页。这两则诏书均对当时浮华的文风提出了批评。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章的变化与时代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史》卷一百五十六曰:“理、度以后,国势日迫。”(55)脱脱等著:《宋史》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54页。随着南宋末叶朝政的日趋腐败与没落,文章萎靡之势已无可挽救,即使“辞尚体要”说仍被朝廷和臣子屡屡提出或强调,但它所起的作用已微乎其微。“辞尚体要”作为一种文章创作观念,它能否被付诸实践,并取得成效,不仅取决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客观因素,而且也与帝王的好尚、作家自身的理论修养、胸襟气魄以及审美兴趣等因素有关,只有当这些主、客观的条件都具备之后,“辞尚体要”说真正的作用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有宋一代,“辞尚体要”说继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后,又一次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宋代的帝王和文人臣子,或提倡“辞尚体要”说,或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当时的文风,使“辞尚体要”说一直回荡在宋代的文坛上,可谓不绝如缕。“辞尚体要”说与宋代的古文革新尤其是科举制度密切相关,而科举考试是历代文风变革中的一个重要指挥棒,“辞尚体要”说便成了反对空疏浮华文风的一个有力武器。宋人所倡导的“辞尚体要”说,比诸刘勰所面临的社会文化背景更为复杂。
五、余 论
宋代为何重视“辞尚体要”说,其缘由有四。
其一,与宋代好议论之文风密切相关。明清人士对宋人的议论之风甚为不满,明代杨慎《辞尚简要》批评说:“吾观在昔,文弊于宋。奏疏至万余言,同列书生尚厌观之,人主一日万几,岂能阅之终乎?其为当时行状墓铭,如将相诸碑,皆数万字。朱子作《张魏公浚行状》四万字,犹以为少,流传至今,盖无人能览一过者,繁冗故也。”(56)杨慎:《升庵全集》,见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04页。《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卷一六〇《应斋杂著》提要说:“宋人奏议,多浮文妨要,动至万言,往往晦饰其本意。”(5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379页。宋代文人好议论,这势必造成文风枝蔓繁芜,冗长拖沓,而“辞尚体要”说实为一剂对治之良药。
其二,宋代的文人在论及“辞尚体要”的同时,往往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推崇三代的文风。(58)关于宋代推尊三代的政治理想,参见曹家齐:《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69页。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不仅推尊三代,就是作文也推崇三代的文风。范仲淹《赋林衡鉴序》云:“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复两汉,由两汉而复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颂之致;斯乐也,亦达乎韶夏之和。”(59)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54页。苏轼《谢欧阳内翰书》曰:“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60)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351页。南宋的杨简也推崇三代淳厚质朴之文风,他指出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文章异乎三代之文章,他说: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书》曰‘辞尙体要’而已。后世之为辞者大异,冥心苦思,炼意磨字,为丽服靓妆,为孤峰绝岸,为琼杯玉斝,为大羹玄酒。”(61)杨简著,董平校点:《杨简全集》第9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92页。南宋末年陈宗礼《南丰先贤祠记》曰:“宋以文治一兴,涤凡革腐,几与三代同风,而士以文名者称之。”(6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0册,第7页。范、苏、杨、陈四人都以三代的文章为最理想的文风。以《尚书》等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是三代文风的集中体现,也是“辞尚体要”的典范之作,再加上《尚书》记录的是治世之言,颇为符合宋人的政治理想。宋代崇尚三代文风的志趣,直接催生了“辞尚体要”说的被重新重视。
其三,宋人普遍重视文章的实用性,(63)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9页。而“辞尚体要”的内涵之一就是针对时弊,有的放矢,反对空言不实,正与宋人重视文章实用性的观念产生了契合。
其四,与宋代《尚书》学的兴盛有一定关系。宋代的《尚书》学著述有500部左右,较之汉以来一千多年时间的《尚书》研究著作,数量多了数倍。(64)参见王小红:《宋代〈尚书〉学文献述评》,《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五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9页。“辞尚体要”出自《古文尚书》,南宋虽然开始有人质疑《古文尚书》的真伪,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疑古考辨之风更促使了不论是《今文尚书》、还是《古文尚书》的流布与传播,“辞尚体要”说在宋代受到重视也与此有一定关系。再加上宋代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刊印书籍较为便利,使作品以及文学观点能得到更迅速的传播。
综上所述,“辞尚体要”从在《尚书》中首次出现,到成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再到成为宋代文坛上一个被反复拈出的说法,在这三个时段中,虽然各自面临的时代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辞尚体要”说的提出或受重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由其客观现实所决定的。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辞尚体要”已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个经典性的命题,并对明清时期的文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刘象愚先生在谈到“经典”的问题时,曾说:“经典应该具有时空的跨越性”,“过去任何时代的经典,其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在它总是现在时,总是与当代息息相通”。(65)[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总序(二)》,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页。刘先生谈的虽然是著作的经典性,但对于本文所探讨的“辞尚体要”说也甚为合适。“辞尚体要”可以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经典命题,它不仅在矫古代文风之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对于当代文章的写作与当代文论的建设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